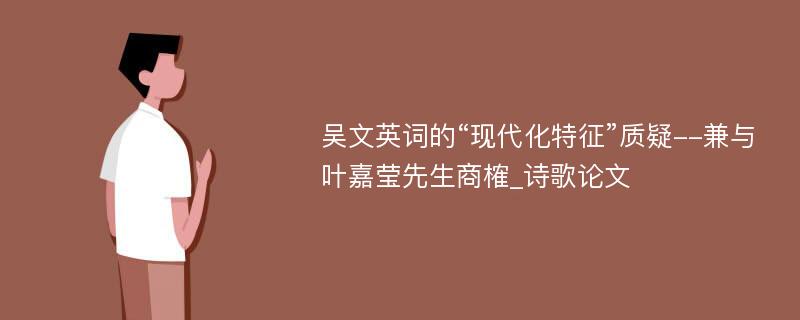
吴文英词的“现代化特色”献疑——与叶嘉莹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色论文,吴文英论文,叶嘉莹论文,献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6)06-0061-08
一
在中国词学史上,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其人其词一直是充满争议的对象。尤其是建国以来头30年(1949-1979年),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以梦窗词为代表的南宋“典雅派”词在一片贬黜之声中趋于沉寂,吴词的研究也处于销声匿迹、一片空白之中。据《1949-1979年词学研究论文索引》统计,对梦窗词的研究,仅有论文1篇,赏析文章2篇[1](P496-543)。也就是说,除了20世纪50年代《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过陈廉贞的《读吴梦窗词》一文以外,全国报刊没有刊登梦窗词的专论。这期间出版的文学史、词选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吴词视为忽略思想内容、只注重形式技巧的样板,加以贬斥否定。因此,叶嘉莹先生《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以下简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的发表①,好似惊雷之震,使埋没已久的“七宝楼台”破土而出,梦窗词的研究为之一变。叶先生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突破,令人耳目一新,不但为吴词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时期词学界开始拨乱反正,对婉约词和典雅词派进行重新评价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在《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中,叶先生对梦窗词给予了高度评价。她的主要观点集中表现在关于吴词现代化的两点特色的新发现上,这是词学研究由古典进入现代以后叶先生以新的时代眼光作出的再评价,其曰:
梦窗词之运笔修辞,竟然与一些现代文艺作品之所谓现代化的作风颇有暗合之处,于是乃恍然有悟梦窗之所以不能得古人之欣赏与了解者,乃是因其运笔修辞皆大有不合于古人之传统的缘故;而其亦复不能为现代人所欣赏了解者,则是因为他所穿着的乃是一件被现代人目为殓衣的古典衣裳,于是一般现代的人乃远远地就对之望而却步……。[2](P62)
叶先生指出,吴文英不得古人之欣赏是因为其不合于古人的传统而近于现代化的缘故,同时又不得今人之了解则在于吴词早已是入殓沉埋数百年的古典了。
又曰:
梦窗词之遗弃传统而近于现代化的地方,最重要的乃是他完全摆脱了传统上理性的羁束,因之在他的词作中,就表现了两点特色:其一是他的叙述往往使时间与空间为交错之杂糅;其二是他的修辞往往凭一己之感性所得,而不依循理性所惯见习知的方法。[2](P63)
第一点特色可简称为“时空杂糅”,第二点叶先生自称为“感性修辞”,这两点即叶先生所谓梦窗词遗弃传统而近于现代化的特色,此为全文立论的核心,是前所未有的现代新评价,也是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关键之所在。
那么,何谓现代化特色?叶先生具体所指的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尤其是意识流小说、电影和后期象征主义诗歌所体现的特色。如法国阿伦·雷乃的电影《广岛之恋》、《去年在马伦巴》,美国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艾略特的诗歌《荒原》等。
自此,新时期治梦窗词者鲜有不为叶先生的观点所笼罩者。研究者大多沿着此种思路生发、扩展,纷纷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如“意识流”、“变态心理”、“张力论”等来研讨吴词的艺术,试图阐明其与一些现代诗歌的“暗合”之处。如陶尔夫先生在《南宋词史》中就以“意识流的结构方式”、“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和“感性的造句与修辞”等来说明梦窗词的艺术特色[3](P371-382)。蔡起福先生的《梦窗的词意识流手法初探》从“时空结构的错综杂糅”、“自由联想的跳跃穿插”、“潜意识的自然流露”三方面来探讨梦窗词意识流手法的主要表现[4]。徐安琪先生则在《梦窗词变态审美心理初探》中提出吴文英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变态审美心理[5]。诸家在分析时虽然角度不同,高下有别,但都与叶先生的基本观点有似曾相识之感,都没有突破其范围,超越其水平。
笔者以为叶先生《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是颇有力度的翻案之作,其所具有的启发性和实际影响,已经超越了单个的梦窗词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历史功绩不容置疑。但是,如果我们对梦窗词进行一番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后,不得不承认叶先生的创造性研究还是有令人困惑、值得商榷之处的。梦窗词是否真的如叶先生所言是既“不能得古人之欣赏与了解”,“亦复不能为现代人所欣赏了解”,以及梦窗词是否具有“与一些现代文艺作品之所谓现代化的作风颇有暗合之处”,从而具有“遗弃传统而近于现代化”的“时空杂糅”、“感性修辞”两点特色等都是值得探究的。
二
叶先生认为梦窗词既不能得古人亦复不能为现代人所欣赏和了解,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梦窗词在南宋即已受到选家和词论家的欣赏与重视。
在宋代有《花庵词选》、《阳春白雪》和《绝妙好词》三种选本②各选梦窗词9首、13首、16首,其入选率均大大超出三、五首的平均数,表明梦窗词在当时就颇受欢迎。
当时两部著名的词论著作也都对梦窗词有所称述。
沈义父《乐府指迷》首开其端记录吴文英的“论词四标准”,并把它作为全书的总论和纲领,足见沈氏的推重。张炎《词源》虽以姜夔词的清空为尚,不喜梦窗词之质实,但仍然肯定了梦窗的自成一家、称名于世,并称赞梦窗词讲究句法、善炼字面等。
宋词的创作虽然在南宋已经达到了极度的辉煌,但是宋代的词学理论却是相对滞后的。元、明两代则创作与理论同时衰微,词学至清代才走向繁荣,对梦窗词的研究也留给了复兴的清代。伴随着清人对词体文学认识的深入,梦窗词亦渐行渐盛,自清中叶至清末民初吴词被常州词派、吴中词派所推崇、激赏,以至于民初“学梦窗词者几半天下”(吴梅语),其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吴词被常州词派肯定与赞赏的过程是与常州词派对词学传统的认识和建立相一致的。从张惠言、周济的寄托说,到谭献的柔厚说、陈廷焯的沉郁说,最终至况周颐的重拙大说,是常州词派经过了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孜矻求索而最终成熟的词学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是对中国传统词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在经历了上千年的词学演进历程后对词学理论的历史性总结,而梦窗词所具有的沉著醇厚、密丽幽邃之特色正好符合常州词派的审美理想而逐步被推上了大家词人的行列。要之,常州词派等岂止是欣赏吴词,而是对其推崇备至!但他们的崇尚并不是基于所谓“现代化特色”,他们完全是站在中国传统词学理论的立场上来欣赏和评价梦窗词的。
再则,现代学者也并非一概认为吴词穿着古典的殓衣而不能欣赏与了解。有相当一部分对古典词学传统有良好传承的学者,如吴梅、王易、唐圭璋等先生对梦窗词的价值和意义都有充分的认识和肯定。唐圭璋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发表于《读书月刊》的《论梦窗词》认为:
一代大家,大抵不随人俯仰,转益多师,自具面目。乌有毫无生气之作,而可以蒙蔽六百年来才士之耳目心思者。……近人反对凝炼,反对雕琢,于是梦窗千锤百炼、含意深厚之作,不特不为人所称许,反为人所痛诋,毋亦过欤。[[6](P982)
在此,唐氏旗帜鲜明地驳斥某些不能欣赏梦窗之呕心沥血、精雕细作的近人。此外,有些学者甚至在“文革”前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占统治时期亦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刘永济先生1960年秋写成的《微睇室说词》,取梦窗词79首,逐一诠释,或申或辨,折中己意,对现代学人、读者理解欣赏梦窗词大有裨益。
当然,近现代学者中的确有不少对梦窗词持反对态度,不能欣赏其独特的风貌者。虽然这些学者有着各自的出发点,但他们众口一词的声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持西方理论立场。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标举境界,推崇真挚自然,对于梦窗词颇为不喜,认为吴词以雕琢、以技巧掩盖了真情,终失之于浅薄,并由此导致了词的衰微不振。众所周知,王国维的论词标准深受叔本华直观论的影响。胡适对梦窗词亦近乎全盘否定,认为梦窗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他的立论点则是以西方“意象派”为理论背景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就指出,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深受外国影响,在其主张中留有明显的意象派理论的痕迹,而意象派的核心主张就是“清楚明白”。刘大杰则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标准,要求文学艺术要体现人民性、阶级性、爱国主义等。要之,王国维强调直观,所以反对吴词之“雕琢”;胡适强调意象明晰,所以反对吴词之“晦涩”;刘大杰等强调思想内容,所以批判吴词之“形式主义”。尽管他们的理论来源不同,但都是站在与中国传统相悖的外来理论立场上发言的。
由上可见,吴文英词并非不能为传统所认识和欣赏。否定者反倒是标举现代文艺观的学者,即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持西方现代文艺立场的学者。
三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叶先生便开始采用西方理论来评析中国古典诗歌,后来又游历讲学于西欧、北美等地,最后定居加拿大。处于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叶先生开始有意识地将此新旧中西的多元多彩之文化加以别择去取、融会结合,力图把西方理论长于分析、富于思辨的长处融入中国传统诗学中。是故,叶先生对梦窗词的评价亦加入了现代化的批评元素——那就是“时空交错杂糅”和“感性的修辞”的提出。对于时空错综的叙写方法,叶先生认为在中国旧文学中是“极为新异”、“背弃传统”的。因为中国文学传统中,无论叙事、抒情或写景,大多是合于理性,有始有终,层次分明的,而梦窗词则完全摆脱了理性的羁束,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假想作无可理喻的结合。所以,早在宋代即有张炎的“七宝楼台”之批评,近世则有胡适之“时而说人,时而说花,一会儿说蛮腥和吴苑,一会儿又在咸阳送客了”[7](P297),刘大杰之“前后的意思不连贯,前后的环境情感也不融和,好像是各自独立的东西”[8](P654)之讥议。但是,叶先生指出梦窗此种时空错综的手法在今日现代化的电影、小说及诗歌中则是极为习见的,因而“梦窗词昔日所为人讥议的缺点,岂不正成为了这一位词人所独具的超越时代的深思敏悟的创作精神之证明”[2](P67-68)。
叶先生以其灵心慧质概括出梦窗词在章法结构上的“时空交错杂糅”,这本是对梦窗词之艺术深思细绎后的独到见解,但“时空杂糅”是否就是“极为新异”、“背弃传统”、“超越时代”、具有现代化的色彩,却是值得商榷和深究的。
早在1968年,即《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在台湾《纯文学》月刊刊出后的当年,台湾学者高阳先生就提出了质疑:
对于梦窗词,我的看法,恰好跟她的“现代观”相反。以我看,梦窗词的叙述,在时间、空间,乃至人物、情况上,相当清晰,本未错综,此即疆村的所谓“脉络井井”。[9](P134)
又,197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在《北宋的主要词人》一书的“结束语”里,就吴文英词发表了看法:
近来有人宣称吴文英有一种独创性是言过其实的。诚然,吴文英常常使用出人意料的或超现实的意象,也喜爱把过去和现在混为一体,他在词的结构方法上多依赖感情的联系而不是逻辑的连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③
刘先生认为这些艺术表现手法几乎和中国的诗歌本身一样古老,上可追溯到《诗经》中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之一——“兴”。在该书中,刘先生还数次列举北宋词人作品中的一些实例加以说明。也就是说,吴文英词并不是背弃传统、超越时代的。
此外,大陆学者谢桃坊先生最初发表在1983年8月30日《光明日报》上的《略谈梦窗词与我国传统创作方法》一文,也对梦窗词的现代化提出了异议。谢先生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我国古代文学有着历史文化条件的重要区别,西方现代派是反社会、反理性、反现实的,而梦窗词并非如此。至于时空错乱、内心独白等表现手法,在我国传统中也是常见的,在宋词中也不乏见,并非仅见于梦窗词。
可见,高阳、刘若愚和谢桃坊三位先生都一致认为梦窗词是传统的,反对给梦窗词贴上“现代”的标签。他们三人的不同在于,高先生否认“时空交错”的存在,而刘先生和谢先生则是认可的,但是认为这种特色并非吴文英独创,更非西方现代派所独有。
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各有其道理,但问题的关键需从词体内部的发展来观照。词这种体裁,较之诗歌是一种更纯粹的抒情文学,重在以意达情,往往按照情感流动的线索将一些并无直接关联却有着共同情感指向的意象片断连缀起来抒发情感。词从小令到长调的发展适应着从单纯明朗到复杂深曲的情感表达的需要,形式上的时空跳跃是同这种回环往复的复杂情感内容相适应的。因此,随着词的高度成熟,更加注重主观心灵的感受,对时空线索完整性、连续性的依赖越来越小,词的艺术技巧也日臻复杂多样,长调慢词中时空断裂、跳跃、倒流、交叉等手法的运用越来越多。周邦彦词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吴文英的长调代表作《莺啼序》结构复杂多变,看似极为新异,但其实明显受到清真词《瑞龙吟》的影响。请看他们的词作: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黯凝伫。因念箇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周邦彦《瑞龙吟》)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吴文英《莺啼序》)
《瑞龙吟》和《莺啼序》都是重游旧地、追怀往事、思念情人的作品。周词以景起,以景结,中间则以今日与往昔两条线索互相交织。首写今日旧地重游之所见所感,次则倒叙往昔旧人旧事,末写抚今追昔之情,今昔错综交结不复可分。全篇妙处正在于回环往复、多有时空转换跳荡之处,从而造成曲折盘旋、欲言又止、神味无穷之艺术效果。周词集中类似的篇章较多,对南宋词人有着巨大的开启作用。
吴词全篇由回忆组成,分为伤春、欢会、伤别、凭吊四段。作者不以传统的直抒胸臆或叙事顺序来表现,而是继承并发展了周邦彦精心组织章法结构的手法,从“伤春”起经过许多转换、曲折、跌宕才达到结尾的“凭吊”。其间时空的跳跃起伏、腾天潜渊,意脉的神龙夭矫、峰回路转,相较于周清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要读懂这首词并不容易,但是只要细心寻绎还是有脉络可寻的。正如海绡翁所评:
通体离合变幻,一片凄迷,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然得其门者寡矣。[10](P4848)
彊村、海绡翁以及高阳等所谓“脉络井井”,正是把握住了梦窗词之情感发展的线索和组织结构的方式而发出的有得之言。
可见,吴文英的“时空杂糅”并不是杂乱无章、无迹可寻的,也不是出于他个人的天才创造,更不是这种天才使他能够跳出传统而与几百年后的西方现代化暗合,而恰恰是与传统的发展一脉相承的。
又,吴文英这种“时空杂糅”与西方意识流文学之关系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意识流小说有两个基础,一是詹姆士的心理时间,一是自由联想的理论。二者又都是以非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总是先有非理性的社会生活和思潮,才会有非理性的艺术方法和表现;总是先有非人化的社会现象,才会产生非人化的艺术形象。”[11](前言,P21)可见,现代主义文艺中的时空错综、意识流结构方式是文学与时代相协调的产物,是非理性的社会生活和思潮的反映,是为了更真实地表现现代西方社会的两大精神实质——精神危机和非理性主义。如叶先生所举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就是20世纪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典范之作。该书描写的是美国南方大户康普生家族几十年的兴衰与沉浮。全书共分四章,前三章分别是康普生家的幼子班吉、长子昆丁和次子杰生的内心独白,而班吉是个白痴,昆丁是个精神崩溃者,杰生则是个丧失人性的偏执狂,他们的独白叙述、时间空间自然都是颠倒跳跃、支离破碎的。正如让-保罗·萨特在《福克纳小说的时间:〈喧哗与骚动〉》中所言:
为什么福克纳要把他故事的时间打乱,把一个个片断安排得七颠八倒?为什么让一个白痴的心灵来给福克纳的想象世界揭开第一扇窗户?……如果认为这些反常情况仅是写作技术上的小手法,那就错了;小说家的美学观点总是要我们追溯到他的哲学上去。批评家的任务是要在评价他的写作方法之前找出作者的哲学。[12](P158-159)
同样,我们认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时空错综”也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正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也无不打上儒家文艺思想的烙印: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主张“文以载道”;在感情的表达上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审美崇尚“思无邪”以及“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文艺的社会作用则是“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以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等等。因此,在儒家“诗教”熏陶下的中国古典诗词,其抒情写意都是有理性、有规范、有节制的,追求的是真善美。这与西方现代派文艺的非理性主义有着天壤之别,本质之分。
总之,梦窗的时空杂糅绝不是脱弃传统的非理性主义表现,用西方意识流和现代化来解释,就如同给李白、杜甫戴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一样,掩盖了古代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重大差别,是非历史主义的。
四
叶嘉莹先生关于梦窗词现代化的第二点特色是“感性的修辞”,关于此点,叶先生主要从梦窗喜用僻典和自创新词上予以说明。如叶氏指出吴词《锁窗寒·玉兰》中的“汜人”和《齐天乐·禹陵》中的“翠蓱湿空梁,夜深飞去”用的都是僻典。而《高阳台·丰乐楼》“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句中“愁鱼”是一个毫无出处的生词。《八声甘州·灵岩》“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句中“酸风”袭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东关酸风射眸子”之句,“花腥”则是梦窗自创的新词。这些都表明梦窗与长吉一样同为最善于以感性修辞的诗人,遣词用字有脱弃传统,不合于理性上惯见习知之处。叶先生又以艾略特诗歌为例来比照说明,认为梦窗背弃传统理性,纯以感性修辞的方法,被昔人所指为“用字下语太晦,人不可晓”之处,以新的观点视之,却正是合于现代化之写作途径的地方。
对此,高阳先生也不能苟同:
梦窗词的修辞,千锤百炼,多出于理性的推敲,而不止于凭一时的感受,率尔下语,此即彊村的所谓“沉邃缜密”(语见《彊村丛书·梦窗词跋》)。[9](P134-135)
又曰:
至于“感性的修辞”,凡是文艺创作,莫不皆然;文艺本出于感情,若无“感性”,不能成物。但一时的“感性”,在诗词中必经反复推敲,千锤百炼,既欲求意境之深,又欲求音节之响……是则词的修辞,出于“感性”,成于理性。[9](P143)
谢桃坊先生则指出梦窗词“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者,并不是背弃传统的,如叶先生所举“愁鱼”,即“愁似鳏鱼”之意,来自李商隐“鳏鱼渴风真珠房”(《李夫人》)和张先“愁似鳏鱼知夜永”(《安陆集》)句,并非“毫无出处的生词”。而“花腥”一词,屈原《九章·涉江》就有“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将恶臭的气味与芳香对举;李贺的《假龙吟歌》也有“莲花去国一千年,雨后闻腥犹带铁”之句。可见,“花腥”也是来自传统的[13](P241-242)。
高先生和谢先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叶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言之有理,但遗憾的是都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笔者以为叶先生提出的“感性的修辞”与其向来所倡导的“兴发感动”的评赏标准不无关系,所以,我们在此需要对叶先生的“兴发感动”说稍作了解。
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叶先生通过对自身批评实践的追寻,总结并提出了“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主张。她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诗歌之所以为诗歌,在其本质方面原是一直有着某些永恒不变的质素,这种质素就是“诗歌中兴发感动之作用”。而这种感发生命的来源,大体上得之于自然界景物节气之变化的感发和人事界悲欢顺逆之遭际的感发两个方面。因此,她对诗歌的评赏一向以其所传达出来的感发生命之有无、多少、大小、厚薄作为衡量其高下的标准。其《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代序)》中有曰:
我在《境界说与传统诗说之关系》一文中,就曾提出说:“兴发感动之作用,实为诗歌之基本生命力。至于诗人之心理、直觉、意识、联想等,则均可视为心与物产生感发作用时,足以影响诗人之感受的种种因素;而字质、结构、意象、张力等,则均可视为将此种感受予以表达时,足以影响诗歌表达之效果的种种因素。”对于前者,我曾简称之为“能感之”的因素;对于后者,我曾简称之为“能写之”的因素。一般说来,我在批评的实践中,对于这两种因素是曾经同时注意到了的。[2](序,P7)
叶先生提出梦窗词“感性修辞”的特色并且极为赞赏,就因为在其“兴发感动”的理论背景下,她尤为看重作品中的敏锐感受和感发。如在《唐宋词十七讲》中她评价梦窗词曰:
吴文英在用典故之中,常常加进去感发。吴文英是南宋最后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作者。一方面有南宋的长处,一方面有北宋的长处。他是把周邦彦的安排思力跟辛弃疾、苏东坡的感发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人。[14](P405)
“感发”的确是文学创作中的基本条件,情感、感受之于诗词至关重要,作品的感发力量也主要取决于情感的力度,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作品中的“兴发感动”能否传达出来,并且能传达到怎样的效果,又不仅在于“能感之”,也在于“能写之”的因素。叶先生所谓“感性的修辞”自当属于“能写之”的因素。“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心有所感(即“能感之”)形之于言(即“能写之”)是诗歌构成的基本要素。其中感发是文学创造的先决条件,表现能力则是必要条件。常人心中也能有所感,但如何遣词造句、如何修辞润饰才能把心中的感发表达得出神入化、感人至深,这才是作家与常人的质的区别。心物相交的感发是感性的,但感情形诸笔端之时,则又有因心而命物之技巧,之冥思苦想,之构思安排,这无疑是理性的创作,这种创作的表现形式就是修辞、结构、章法等等“能写之”的因素。无论是修辞、结构还是章法等无一不需要进行精心的选择、组织、调整直至修改。如张炎《词源》卷下论“制曲”曰:
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方始选韵,而后述曲。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词既成,试思前后之意不相应,或有重叠句意,又恐字面粗疏,即为修改。改毕,净写一本,展之几案间,或贴之壁。少顷再观,必有未稳处,又须修改。至来日再观,恐又有未尽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无瑕之玉。倘急于脱稿,倦事修择,岂能无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协音声。作诗者且犹旬锻月炼,况于词乎。[15](P258)
可见,文学创作必定是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产物,创作中修辞、结构、意象等“能写之”的因素也都是“出于感性”,而“成于理性”的。因此“感性的修辞”这一提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此外,是否因为梦窗的用典用字、修辞着色独具特色、与众不同,就可用“感性的修辞”来概括呢?
众所周知,诗词的创作要想在极短小、紧凑的篇幅内发挥出最强的表现力、最大的创造力,诗人的炼字炼句功夫是必不可少的。刘勰《文心雕龙·练字》即曰:“缀字属篇,必须练择。”沈祥龙《论词随笔》亦云:“词之用字,务在精择。”为此,作家们往往绞尽脑汁、苦搜冥索并经过反复推敲修改始成。
且不说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句中的“绿”字,反复斟酌修改了十几字乃定,也不说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事例,就拿叶先生认为的最善于以感性修辞的诗人李贺来说,他的诗常常出现出人意表的语言和意象,因此而被称为“鬼才”诗人。但是,在他那些刻意描摹渲染的看似直观敏锐的事物形象背后,总是隐藏着极其苦痛的煎熬。李商隐著《李长吉小传》曾记叙了李贺苦吟的情况,说他经常骑驴背一古破锦囊去野外搜集诗料,遇有所得便书投囊中,及暮归家再重新编排提炼。他日日夜夜苦读写作,带着病痛喝着汤药还要读,他母亲常为之担心:“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清人叶衍兰《李长吉集跋》亦云:“李长吉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16](P93)可见,李贺那些感受强烈、令人触目惊心的修辞又何尝不是苦心经营的结果。
至于用典,这种修辞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最为普遍,也是最为讲求的。因为我国古代诗词的语言是一种最精微、最凝练的语言,而贴切、精彩的典故,往往片言只语、寥寥数字就能表现极丰富、深刻的情景、内涵。所以,典故不是一般的语言,它的恰当运用必须是作者经过长期积累、再三锻炼的结果,它是作者学问广博、功力深厚的标志。
可见,诗词中无论是用典还是用字,都是创作者丰厚积累、精心思索、深加锻炼的产物,绝非纯然援笔而成的感性所为。
吴文英作为一名布衣词客、专职词人,除了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词作之中,别无所立。因此,梦窗词是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的。身处周邦彦、姜夔之后,要想另辟蹊径、独树一帜,非“炼字炼句,迥不犹人”,别无他法,正如唐诗中韩愈一派“怪词惊众”,宋诗中江西诗派“点铁成金”、“夺胎换骨”,都是为了自成一家的创新一样。但这种创新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梦窗词既效法韩愈、李贺的求险求怪,更继承江西诗派大量使事用典、融化古诗的手法。如果说江西诗派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学人之诗”,那么,梦窗词则是“以文字为词,以才学为词”的“学人之词”。梦窗词中之“汜人”、“愁鱼”、“花腥”之类,既是他独特的敏锐感受,也是他刻意追求与众不同的结果,更是他学识广博、锻炼渊雅的深厚功力之体现。正如王鹏运所评:“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几如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17](校本《梦窗甲乙丙丁稿跋》)总之,梦窗词的感性是与自觉的艺术锤炼结合在一起的,他的感性与理性水乳交融,不可割裂分离。梦窗词的修辞也多从典故史实、前人诗句、对比借代等中国传统的表现手法而来,与西方现代派全然无关。
综上所述,叶嘉莹先生对吴文英词的全新评价,使梦窗词得以重见天日,其拨乱反正的意义是重大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虽然叶先生高度赞赏梦窗词,与王国维、胡适等人的贬斥截然相反,但他们都是立足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上所进行的观照,由此导致了中国文学自身特点和西方现代文艺本原意义的双重丧失,是用某种新理论、新观念来统制和抹煞了历史存在的差别,因而都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梦窗词。而诸生后学在叶先生文章的中西结合所散发出的新颖独异之魅力感召下,又恰逢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引进学习西方文艺思潮的狂热之中,于是在缺乏冷静思考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纷纷以叶先生之论为参照,急于用西方现代派的钥匙来开启吴文英词——这座中国古代的“七宝楼台”,无疑是走得更远更偏了。
收稿日期:2006-02-12
注释:
①《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一文,在中国大陆最早刊载在《南开学报》1980年第1期(P41-56)和第2期(P34-41)上。
②吴熊和先生汇编宋人选宋词十种,其中有的早已亡佚,有的成书年代早于吴文英的出世,所以仅剩有上述三种词选本选录梦窗词。
③转引自阎华《国外学者关于吴文英词的争论》,载1983年1月18日《光明日报》第3版。
标签:诗歌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吴文英论文; 叶嘉莹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反复修辞论文; 读书论文; 意识流论文; 瑞龙吟论文; 莺啼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