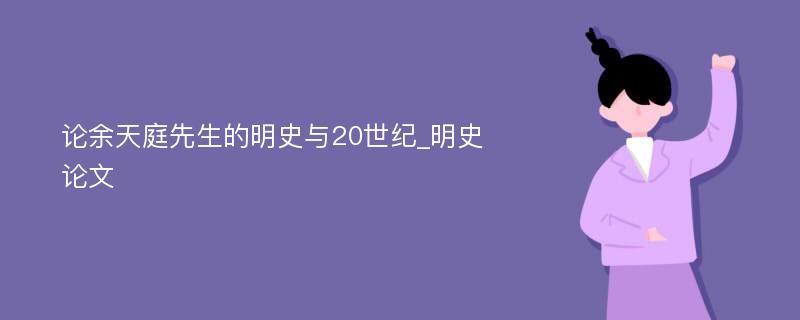
鄭天挺先生與二十世紀的明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二十论文,鄭天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鄭天挺(1899-1981)是中國著名的明清史專家,翻開任何一本有關中國20世紀明史研究概况的著作,①幾乎無一忽視鄭天挺的重要地位。但他對明史學界的獨特貢獻,在明史領域的獨到見解,即使回顧與總結性的著作,以及關注鄭氏史學成就的論文,也鮮有詳細介紹。②在明史研究領域,鄭天挺既没有在清史領域像《清史探微》③那樣的標志性專著,甚至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亦不多。可是,却無人否定他對於中國20世紀明史研究的重要貢獻。這實際上是一個矛盾。本文試爬梳相關資料,尤以鄭天挺多年的明清史講課學術卡片和尚未出版的日記爲據,結合時人的回顧與研究,對此問題略作探討。
一 孟森傳人及其明史教學之歷程
20世紀的中國學術,大體可以1949年和1977年爲界,分爲三個時期,明史研究的發展階段也基本如此。④該世紀我國最重要的明史專家,誠如黄冕堂所言,“老一輩學者吴晗(1909-1969)、鄭天挺(1899-1981)、謝國楨(1901-1982)、傅衣凌(1911-1988)、王毓銓(1910-2002)、黄雲眉(1897-1977)等追踪前哲,博覽精研,碩果纍纍,爲今日我國的明史學奠定了基礎。新一代繼起治明史者許大齡(1922-1996)、洪焕椿(1920-1989)、李洵(1922-1995)、韋慶遠(1928-2009)、韓大成(1925- )以及近年不斷脱穎而出的中年俊秀,學風篤實,已初步顯示出實力。”⑤這話是二十多年前所説,已不足反映整個20世紀的情况,“老一輩學者”中,尚應加上孟森(1869-1937)、朱希祖(1878-1944)、柳亞子(1886-1958)和王崇武(1911-1957)、梁方仲(1908-1970)。在這些“老一輩”明史專家中,只有鄭天挺、謝國楨、傅衣凌、王毓銓四人的學術生涯跨越20世紀的三個學術階段,而鄭天挺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明清史學科化與專業化的建立過程中,上承孟森,在後來明清史學科進一步發展過程中,廣育門生,地位更顯重要。
20世紀初期,隨着現代教育體制的創立,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出現組織化、制度化、專業化的趨向”⑥。在此過程中,對於史學而言,大學如何開設現代學科意義上的課程,對史學的學科化與制度化建設至關重要。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在草創階段,課程很不完整。如北京大學,直到1929-1931年,開設的課程中才有比較完整的斷代史,但尚未見明史、清史。⑦在20世紀前期北大明清史課程的創立與發展上,作出主要貢獻的是孟森和鄭天挺。⑧“北京大學的明清史研究,是由孟森一手開創的,繼孟森之後,鄭天挺以自己獨創性的研究將北大的明清史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學術高度”。⑨
鄭天挺,原名慶甡,字毅生,别號及時學人,原籍福建長樂,生於北京。1917年,入北京大學國文系,1921年秋入北京大學國學門爲研究生,師從錢玄同。1924年秋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預科講師,教授人文地理及國文。此後去廣州、杭州等地任職,1930年冬再回北大,繼續在預科講授國文。之後,一直在北大任教。1933年12月,任北大秘書長、中文系副教授,隨後陸續講授過古地理學、校勘學、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鄭天挺儘管不是孟森的弟子,却是孟森的傳人,自1931年相識以來,彼此交誼很深:
一九三四年余得見鈔本《國史列傳》二百册,知心史先生方輯清史列傳匯編,亟以送之先生,是爲余與先生以學問相往還之始。余舊治國志,繼探求古地理、心儀趙誠夫之學,偶得趙氏《三國志注補》,付之景印,既成,以序文實《讀書周刊》,先生方校《大典·水經注》,讀之大喜,爲跋尾一篇論趙氏生卒年歲,余於趙氏年歲,亦别有論列,遂書陳其所見。舊作《多爾衮稱皇父之由來》一文久置箧衍,亦以就正於先生,是爲余與先生論學之始。一九三七年盧溝變作,余從諸先生後守平校,先生時督其所不逮,以是過從漸密。十一月余從南來,别先生於協和醫院,執手殷殷潸然泪下,不意遂成永訣!⑩
1938年1月,孟森在北平逝世。1938年5月22日,鄭天挺在與西南聯大歷史社會學系教授錢穆和姚從吾談話會上,特地講述孟森晚年生活,寄託追思。(11)1939年6月,又在《治史雜志》第二期上發表《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紀念孟心史先生》以兹紀念。此後學界皆將鄭天挺視作孟森傳人,即如王永興所言:“他是精於清史的史學大師孟森先生的傳人。”(12)鄭天挺繼承孟森遺志,以研究明清史爲主,此後所授課程也主要是明清史。
鄭天挺正式講授明清史乃從1939年在西南聯大開始,在《自傳》與日記中均有記載。《自傳》曰:“我在一九三九年後,在聯大即講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國目録學史等課程。”(13)尚未刊行的《鄭天挺日記》,(14)亦可印證。1939年1月1日:“年四十一歲。時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教授,授明清史。本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兼秘書長。”(15)1940年1月1日:“年四十二歲(以陰曆計),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教授,授歷史社會學系史學組明清史及清史研究。”(16)1941年1月1日:“年四十三歲。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史學系教授,授明清史。兼大學總務長。”(17)開設的明清史課程,頗受學生歡迎,《五十自述》説:“當時年青的學生激於愛國熱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國的近世史,尤其矚目於明清時期,故每次選修該課的多達一百數十人,情况前所未見。”(18)
此後儘管也講過其它課程,但明清史、明史專題、清史研究等課程,是鄭天挺反復開設的課程,一直堅持到1981年去世前不久。對於斷代史課程明清史的學科化與專業化,貢獻良多。講授有關明清史課程,長達四十餘年,這在20世紀中國的明史學界,實爲鮮見。
二 明史史料之整理與清修《明史》之點校
20世紀明史研究一個重要方面是史料的收集與整理。在鄭天挺六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很多時候正是以整理明清史料爲己任。1954年,他特地給南開大學學生開設史料學課程。1956年發表《史料學教學内容的初步體會》一文,一開始就提及蘇聯所開設史料學課程,指出蘇聯對史料學的重視,“這是歷史科學研究的一個新方向”(19)。此課程就是模仿蘇聯的結果。借用蘇聯百科辭典的解釋,稱史料學乃是“探求研究各種史料的方法,以補助歷史學的訓練”(20)。其實,重視史料、解讀史料,與他治學的路徑一脉相承。馮爾康回憶史料學上課情形,聽到鄭天挺提及“史料批判”的説法,感覺新鮮。鄭天挺解釋:“對於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記載,這就是差異,差異就是矛盾,就要解决,就是‘史料批判’。”(21)他强調歷史研究遵守“深、廣、新、嚴、通”五字原則,“廣”就是“要求詳細占有材料,還要廣泛聯系”。(22)
20世紀50年代以後,鄭天挺開始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對當時有人不顧史料,僅以理論貼標簽的做法,提出批評。他説:“關於不明晰的史料,不作深入的分析,只依靠主觀地引用經典作‘脚注’,而又忽略經典所闡述的時代和範疇,是不容易解决問題的。”(23)這種論斷,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難能可貴。他對於發現史料者表示由衷的尊敬,在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吴晗最早發現《織工對》這篇史料,鄭天挺説:“歷史專家發現一條史料,和發明一個創見,功績是一樣的,我們對這方面勞動的尊重是不够的,幾乎没有人在引用史料時提到某人首先發現。這是不公道的。資本主義萌芽史料中,徐一夔《織工對》是一個極重要的資料,假使不是吴晗同志指出,我是不會去找的。”(24)鄭天挺同時認爲,從史料出發,不能僅僅依據一兩條史料,就故作高深地進行論斷。“在反對孤立和片面處理史料時,分成兩個方面:一個是要注意歷史事實的前後發展關係,即‘縱的關係’;一個是要注意歷史事實各方面之間的普遍聯系,即所谓‘縱横兼顧’。”(25)可見,他重視史料,也不忽視理論,但反對不顧史料,僅借理論貼標簽,運用史料,講求歷史的縱横兼顧,秉求實事求是的態度。
鄭天挺既是明史史料整理的積極參與者,更是重要的組織者與主持者。早在1921年,在北大國學門爲研究生之際,就加入清代内閣大庫檔案整理會,因而奠定他清史研究的基礎。鄭天挺自言:“我在作研究生期間,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内閣大庫檔案整理會’,參加了明清檔案的整理工作,這無論對國家、對我個人都是一件大事情,從而奠定了我以後從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礎。”(26)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恢復明清史料整理室,鄭天挺親自主持工作,曾與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編《清内閣舊藏漢文黄册聯合目録》,親自寫序,加以推介;還幫助東北圖書館印行《明清内閣大庫史料》第一輯明代卷上、下兩册。(27)1950年5月舉辦“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展覽。(28)1954年,主編并由中華書局出版了《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和《宋景詩起義史料》。1950年代組織南開大學歷史系編纂《清實録史料選編》由中華書局出版;後來又組織編纂了《明實録資料選編》。20世紀80年代初,還主編了《明清史資料》(29)。在所有整理出版的明史資料中,最重要的是清官修《明史》的點校與出版。
1952年,因院系調整,鄭天挺離開北大,來到南開大學,主持歷史系工作。他將北大嚴謹、踏實的治學風氣帶到南開,從此也奠定了南開歷史系良好的學風。1956年,創建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乃是1949年以後中國最早建立的研究機構之一,從此開創了南開明清史研究的傳統。南開明清史研究室成立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主要從事標點、校勘《明史》,這是當時整個“二十四史”點校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五十年代末開始,中華書局就計劃出版點校本“二十四史”,由全國高校著名歷史學家主持相關工作。清官修《明史》乃指定鄭天挺負責。點校過程,最初由南開歷史系林樹惠、朱鼎榮、傅貴九等承擔,後來鄭克晟、湯綱、王鴻江也參加。鄭天挺制定原則,解决疑難,審核成稿。
爲盡快完成校點工作,1963年9月底,鄭天挺與負責其他史書點校的學者,一同居住在中華書局西北樓招待所,在中華書局工作近三年時間。他以札記的形式寫成《明史零拾》數十篇,并打算《明史》點校完成之後,將其整理出版。(30)内容涉及《明史》的成書經過、史實考訂、與其它史書的比對、字詞糾謬、文字斷句等等。後來有部分取名《明史讀校拾零》,收入《探微集》。閻文儒説:“《明史讀校拾零》共四十餘頁,雖名爲拾零,實以百衲本《明史》爲主,與明歷代《實録》、《明一統志》爲主,《寰宇記》、《遼東志》、《禮記》、《漢書》等,互相校正得數百條,由洪武至崇禎,二百七十餘年,能按年校正其不同之處,誠清代漢學家所少見者。”(31)即如《明史》中之《太祖本紀》中,有一條“是年,張士誠據高郵,自稱誠王”(32),鄭天挺考之曰:
《太祖實録》卷一,張士誠據高郵係於至正十三年五月,稱誠王係於十四年正月,《史稿》紀一與《實録》同,惟十四年正月作十四年春。《明史》卷一二三《張士誠傳》作“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佑,是歲至正十三年也”。案:《元史》卷四三,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建國、建元均系於至正十三年五月乙未,《明史》紀傳均從《元史》。(33)
可見,爲考證張士誠據高郵稱王的時間,鄭天挺參考了多種材料,發現此條史料與《明太祖實録》和《明史稿》皆不符,而考出其原來出自《元史》,揭示了《元史》對於清修《明史》也相當重要。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儘管《明史》點校工作尚未完成,鄭天挺被迫回到南開大學,致使《明史》點校工作停頓下來。“文革”後期,中華書局重啓“二十四史”標點工作,校方却以“文革”爲理由,不同意鄭天挺再前往中華書局完成未竟之工作,中華書局只得另請白壽彝、周振甫與王毓銓負責完成,在點校過程中,他們時常與鄭天挺聯系,往來商榷。1973年鄭天挺審閲《明史》三校稿,又提出了不少意見,他的工作本“復校異議”百餘頁,詳細記載復校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張廷玉《明史》點校本,終於在1974年4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姜勝利在談到1949年至“文革”結束前近三十年的《明史》研究時,指出:當時《明史》研究陷入沉寂,幾無力作問世,“這時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在鄭天挺主持下……完成了《明史》的標點和校勘,并於197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34)可見,標點本《明史》的出版,乃是那個時期《明史》研究最重要的學術貢獻。
20世紀出版了不少明史史料,但最基本的莫過於點校本《明史》的問世,因爲這是研究明史最基本的史料,也是學習明史的入門典籍。點校本《明史》的問世,對剛剛邁入明史研究的學生們來説,大大開啓了方便之門,提高了他們的學習興趣。(35)《明史》點校這項工作,主要是在鄭天挺領導之下完成的,而且完成於風雨如晦、學術暗淡的“文革”期間,因此也奠定了鄭天挺在20世紀明史學界的重要地位。
三 鄭天挺的明史專題研究與獨見
自20世紀30年代後期以來,鄭天挺就以研究明清史而著名。1940年元月,有不少人勸鄭天挺就任西南聯大總務長,但他不願爲之。好友羅常培(1899-1958)勸他,“君欲爲事務專家乎?爲明清史專家乎?”《鄭天挺日記》中説:“此語最誘人。沈茀齋(即沈履,清華秘書長,時任西南聯大總務長,但他要離開昆明,赴重慶任職,即勸鄭天挺爲總務長)來,謂常務委員會一致通過余繼總務長,特來勸駕,并謂今後經費、人事均無問題,勸余稍犧牲、稍鼓勇氣爲之。婉謝之。”(36)因爲鄭天挺過人的行政能力和高尚的品德,所以時人咸以爲他該就任總務長,但鄭天挺志不在此,而是希望沿着學術之路,在明清史領域繼續做出成就。(37)
儘管鄭天挺發表的論文以清史爲主,但明史研究,却從未中輟。從留存下來的日記和有關明史學術卡片可知,他有不少研究計劃,涉及明史諸多層面的問題。1934年7月1日記:“讀《明史·太祖紀》。學校將以明日起,放暑假,假中惟星期一、三、五上午辦公,余擬乘間稍讀書。今日擬定功課有四:一讀《明史》一過;二考訂《明史·地理志》;三作八股文程序一篇;四作歷代公文程序一篇。”(38)當時,他已任北大秘書長,行政事務很繁忙,故而想暑假期間多讀書,并完成幾篇與明史相關的論文。而這樣的記録在1938年到1940年間尤多,幾乎每日皆有讀明史史籍之記載。1938年至1939年四、五月間他所讀之明史書籍,以張廷玉《明史》爲主。此後則涉獵王鴻緒《明史稿》、傅維鱗《明書》、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等等。九月以後,以明人筆記、明代文集和《明太祖實録》爲主。他讀《明史》的時間最長,可以推測他是精讀的,其他史書,讀的時間就少了很多,或以泛覽爲主。
在系統研讀明史典籍的同時,他還有不少論文寫作計劃。即如1940年6月2日載:“因念暑假將至,當乘時稍事學問。……擬以讀英文爲主,有暇則將年來搜集之材料,草成論文。一明末流賊十三家考;二明初之正統議;三張文襄書牘跋。此外,擬讀明清筆記。”(39)所提及的三篇文章,後來第一篇成初稿,但并未發表。最終成文的是第三篇,題爲《〈張文襄書翰墨寶〉跋》,發表於《文史雜志》第一卷第六期,後收入《清史探微》。除寫論文,鄭天挺還曾想在講課卡片基礎上編一部《明清史》,1939年2月5日載:“讀摘講述札記。近日頗思以平時講述所蓄,編爲明清史,即以札記爲長編。現每日約鈔二千字,一月可得五萬字。暑假後或可着手纂輯矣。”(40)還曾與傅斯年(1896-1950)商談合作編輯《明書》三十志之事。
傅斯年與鄭天挺是北大“五四”時期國文系同學,傅比鄭高一班。西南聯大時,傅斯年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鄭是副所長,工作上他們互相幫助。北大文科研究所曾設斷代史工作室,鄭天挺日記1939年6月12日載:“開文科研究所會議。决議所中設工作室,余主明清史工作室事,從吾(即姚從吾,1894-1970)主宋史工作室。中國斷代史工作,暫以宋明清爲始。十時散會。”(41)可見,當時無論是教學還是工作,凡與明清史相關的,都由鄭天挺負責。傅斯年對明史也下過不少功夫,就在這一年,他與鄭天挺商談,共同編著一部《明書》,鄭天挺日記中三次提及此事。1939年6月20日載:“晚與孟真談。孟真欲纂輯《明編年》及《明通典》,約余合作,余於此本亦有意。子水勸余作《續續資治通鑒》久矣,慨允之。余擬别纂《明會要》,孟真亦贊成。”(42)四日後,他們就共同擬出目録來。1939年6月24日載:“晚飯後,傅孟真來。謂前談之《明通典》擬改爲《明志》。遂共擬篇目如次:一曆法、二地理(附邊塞)、三河渠、四禮俗、五氏族、六選舉,七職官、八兵衛、九刑法、十食貨、十一經籍、十二文學、十三理學、十四釋老、十五書畫、十六土司、十七朝鮮、十八韃靼、十九烏斯藏(附安南)、二十西域、二十一倭寇、二十二建州、二十三南洋、二十四西洋。”(43)又過了兩周,他們再詳談此書,擬定了詳細目次,載於1939年7月11日日記:
孟真來談《明書》三十志事。孟真新擬目如次:一《曆法志》。此中有二綱,一明人如何承用元人曆法(尤其重回回曆);二崇禎新曆。此志孟真擬自任,余初推子水。二《皇統志》。此中編歷世之繼承,而以宗室系表附之。孟真任之。三《祖訓志》。此載《太祖寶訓》而申述其義(此實關係有明一代開國之規模)。孟真任之。四《地理志》。孟真任之。五《京邑志》。南京、舊北京、中京、京師宫闕衙市。六《土司邊塞志》。七《氏族志》。仿《宰相世表》,余意此表較難作,因明代不尚門第也。八《禮樂民風志》。孟真意由余任之,尚未决。九《學校選舉志》。余任之。十《職官志》。尤注重其實質之變遷,《明史》原式不可用。余任之。十一《刑法志》。余擬任之。續借閲董綬金藏書。十二《兵衛志》。孟真任之,余初推吴春晗。十三《財賦志》。余擬任之。十四《商工志》。難作,且無人,擬闕。十五《河渠志》。十六《儒學志》。十七《文苑志》。十八《典籍志》。不易作,且難其人,擬闕。十九《書畫志》。仝上。二十《器用志》。仝上。二十一《宦官志》。二十二《黨社志》。余擬任之。此於晚明、南明加詳。二十三《釋道志》。擬由錫予任之。二十四《朝鮮安南志》,琉球附。二十五《韃靼西域志》。二十六《烏斯藏志》,喇嘛教附,擬闕。二十七《倭寇志》,附入知利氏之受封及平秀吉之戰。二十八《南洋西洋志》。擬由受頤任之。二十九《遠西志》。仝上。三十《建州志》。直叙其大事至左灣之亡。此書期以五年完成。余初意用《明志》之名,以别於傅維鱗《明書》,孟真以爲不相礙也。(44)
不僅擬定了詳細目録,且對參編人選,亦有考慮,除傅斯年、鄭天挺外,他們還擬請毛子水(1893-1988)、吴春晗(即吴晗)、湯用彤(錫予,1893-1964)、陳受頤(1899-1978)等參與。傅斯年專就此事給鄭天挺信曰:“前所談明書三十志,兹更擬其目,便中擬與兄商榷其進行之序。果此書成,益以編年,《明史》可不必重修矣。弟有心無力,公其勉之。”(45)可見,傅斯年非常看重此書,計劃五年完成,假若此書編成,一定會大大推進明史研究。只是因爲時當亂世,他們又事務繁雜,次年春,鄭天挺兼任西南聯大總務長,1940年11月初傅斯年前往重慶,因此合作計劃未能完成。盡管這次合作未成功,但他們之間的學術交流更爲密切,傅斯年對鄭天挺學術上有很高的評價,説鄭天挺“不爲文則已,爲文則爲他人所不能及”(46)。
鄭天挺對明史的研究,還體現在他留存下來的明史學術卡片中。鄭天挺多年講授明清史,卡片中已有系統的講課大綱,列出了章節標題,主要内容則分成十數大類,主要有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法律、文化、民族、宗教、地理、對外關係、人物等類别。每張卡片上都有分類標題,即如“事·明·政 明太祖主仁厚”,表示該條内容屬於“史事,明代政治”類,具體是“明太祖仁厚”之事。“人·事·明 明太祖生地異説一”,表示該條有關明代人物的事情,而本條乃是關於明太祖出生之地異説之第一張卡片。“事·明·法 李善長之死一”,該條乃是屬於“史事,明代法制”類,具體是關於“李善長之死”的第一張卡片。(47)每張卡片都按照課程大綱所設定的章節位置排列,就這樣將有明一代史事及一些重要問題,都陳述出來。這些學術卡片,既是講課的講稿,亦是他多年來研究明史的結晶,因而頗具學術價值。
鄭天挺是最早關注明史分期的學者之一,提出了頗具創建的論説。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歷史學界非常重視歷史分期的研究,因爲要重建新的歷史解釋系統,把握中國歷史總體特點與歷史大勢,就必須重視歷史分期問題。搞清明代歷史的分期,是把握明史總體特點的關鍵,鄭天挺對此進行了深入思考。早在1938年,就在日記中寫道:“余私見以爲明史宜以嘉靖先後分爲兩期。嘉靖前後,國勢、物力、朝政、文風,顯有不同也。嘉靖以前又可分爲兩段:自洪武至宣德爲一段,此時國勢最强。自正統至正德爲一段,此時國勢漸弱,尚可守成。嘉靖以後亦可分爲兩段,自嘉靖至隆慶爲一段,此時國勢已替,自萬曆至崇禎爲一段,此時亂亡之象已成矣。”(48)而在其明史教學卡片中,有更詳細的説明。鄭天挺還在卡片上寫了一句自謙的話,説“此是一時所見,尚待詳定。”
在具體分期上,他將元至正八年(1348)郭子興起兵到明太祖即位前(1368)共21年,劃爲前期,并言:“元末之亂與明之肇建,通史則并入元代,斷代則應補述。”自洪武元年(1368)到正德十六年(1521),凡154年,視爲第一期。“嘉靖以後宰相權重,朋黨漸起,宦官驕横更甚,國力日蹙,外侮日亟,賦税制度亦有變更(萬曆一條鞭法),故以嘉靖劃時代。”而這一期,又以宣德十年(1435)爲界,劃爲前後兩段,前段68年,“蓋此段爲明代國勢最强,民力最富時期”。自正統元年(1436)到正德十六年(1521)爲後段,凡80年。“蓋此段明之國威民力已漸替,幸賴舊德,尚可守成,得不滅亡,孝宗勤政愛民,武宗振奮一時,終不能望中興也。”從嘉靖元年(1522)到崇禎十七年(1644),爲第二期。又以隆慶六年(1572)爲界劃分兩段。前段51年,“蓋此段明世衰亂之象已見,外侮日亟矣”。後段72年,明朝隨着崇禎帝的自盡而滅亡。而南明18年(1644年五月至1661年),則劃爲後期。(49)
自1938年,鄭天挺開始思考明史分期問題,不久即形成系統的教學内容,以後每次講授明清史時,皆會重點講授,但幾十年來,他的認識基本上没有什麽變化。當然在每次講課中,可能會有詳略不一的情况,陳生璽在總結鄭天挺明史領域的獨特見解時,首先就强調鄭天挺對明史分期與明史特點的深入研究和概括,認爲鄭天挺以1435年和1521年作爲兩個分界綫,劃分爲前期、中期、後期,并對三個時期的特點給予概括,認爲他“把明代的歷史從縱的方面放在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進行比較,從横的方面放在與周邊民族及其它國家的關係中進行考慮,可謂不移之論”。(50)現今對於明史的研究已經深入細致得多,出版的專著也不勝枚舉,關於明史的分期也頗有不同説法,但大體上未出鄭天挺所設定的原則。
與明史分期相關的是對明清史的歷史定位問題,馮爾康總結鄭天挺在明清史學界四大重要貢獻,第一點即“對明清時代在社會發展階段上的地位提出精闢見解”,鄭天挺認爲,明清時期是封建社會晚期,不是“末期”或“末世”。當時有研究者將明清看成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或者末世,乃基於這樣的認識,即1840年以後中國歷史既然屬於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社會,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那麽明清時期被視爲末期。這樣的論斷以近代的變化來解讀明清史,存在很大問題:明清時期商品經濟有很大發展,尤其是江南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一個末世階段,怎能衍生出繁榮的經濟?實際上,晚期與末期雖只有一字之差,却有本質不同。“晚期表示該時代的社會制度的衰敗,即已開始逐漸走向崩潰,但在某些方面還有一定發展餘地;而末期則揭示那種制度的滅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過程。”(51)“‘末期’是指舊的生產關係完全崩潰瓦解,并向新的制度過渡的階段;‘晚期’是指這個制度已經開始走向崩潰,但是還没有完全崩潰,在個别方面還有發展的餘地。”(52)鄭天挺提出的後期説或晚期説,還原了明清歷史的真實地位,既看到歷史的變化與進步,同時又顧及明清時期的特點。“可以説這是舊制度慢慢地向一個新制度蠕動的歷史時期”,“封建制的危機很嚴重,但還没有到行將瓦解的程度,還不可能使中國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53)他認爲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根本原因,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在此基礎上,鄭天挺概括明清歷史特點:中國歷史上最長的統一時期、中國封建經濟最發展的時期、資本主義的萌芽時期、階級矛盾尖銳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與發展時期、抗拒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時期等等。(54)這就既明確了歷史時代的定位,又把握了明清時代的總體特點。
資本主義萌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史學界討論最熱烈的問題之一。像鄭天挺這樣原本奉行史料先行的“舊派”史家,可能不大會關注此類問題,但鄭天挺却始終保持高度的學術敏銳,積極參與討論,并發表了《關於徐一夔〈織工對〉》的論文(55)。最初,在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吴晗發現徐一夔《織工對》這一極重要的史料,當即引起明史學界的廣泛關注,但對於此史料反映的是元末還是明初的絲織業或棉織業的情况,學術界争論甚多,莫衷一是。鄭天挺根據徐一夔《始豐稿》一書的編排體例,指出第一卷的《織工對》應爲元末之作,從元、明兩代使用的金融用語的差别等問題入手,指出當時徐一夔在杭州,《織工對》中的“日傭爲錢二百緡”的“緡”一詞的使用,是元末一千錢的習慣稱呼,明初稱一千錢爲一貫,因而斷定《織工對》寫於元末而非明初,反映的乃是元末杭州絲織業的情形而不是明初的情况。此論一出,即被視爲權威論斷。
《明代的中央集權》(56)亦是鄭天挺的一篇代表作。此文指出明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幾個支撑點,乃是中央掌控地方的官吏任命權、軍權、財權、司法權,明代中央幾乎掌控了地方上的一切權力。進而對於廢丞相制度、升六部,内閣與六部權力的消長,以及廷臣與内臣的矛盾,皆進行了闡述,對明代政治制度的特徵進行了相當精闢的論斷。又如對明代分封制度,亦有十分詳盡的探究。講義中乃是作爲“明初内政”問題之一,進行探討,分爲四個問題分别討論:“A、分封之始;B、分封目的;C、分封制度;D、永樂後之流弊。”下面再細分爲近二十個論題:“明太祖始封諸王詔”、“明初諸王之封地”、“明代諸王封地”、“明初分封之目的”、“明代藩王之制”、“明初分封制度”、“明初諸王預軍務”、“明初諸王備邊理軍”、“明初備邊諸王專制國中”、“諸王歲供”、“明初諸王草場及世宗神宗之濫予”、“明初諸王食賦”、“明宗室應試”、“太祖遺詔抑諸王權”、“明初諸王减禄”、“永樂後諸王不得擅役軍民”、“明諸王護衛”、“明代分封宗藩諸書”等等論題,逐一説明,將明代分封制度的沿革、特徵、職掌、對明代政局的影響等等諸多方面,均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明初封建與前代之不同曰:“一、分封不錫土;二、列爵不臨民;三、食禄不治事。”更具體鈎稽出明代藩王制度的幾個特徵:
一、封國連邑數十;二、府置護衛甲士三千人至萬九千人,隸籍兵部(《明史》卷一六六),三護衛每衛5600人;三、近塞者預軍務,有事將兵出塞,軍中大事方以聞;四、備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明史紀事本末》十五);五、遣將征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明史紀事本末》十五);六、餉不敷,得就他郡租賦;七、親王歲供: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紵絲三百匹,紗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斤,鹽二百引,茶千斤;八、歲禄外,量給草場牧地;九、所在文武吏士聽節制(《明書》三);十、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無敢鈞禮;十一、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57)
他一一列出明代藩王的權限,從藩王的規模、護衛的數目、歲貢、與地方的關係等等問題,都考訂出來,并且將出處也列出,可備查考。鄭天挺對明代分封制度的研究不可謂不深入,惜乎并未寫出論文,即便他逝世三十年後的今天,明史學界對於明代藩王制度的研究仍無比較系統深入的論著問世。
總之,鄭天挺對明代許多重要領域都有獨到的看法,只是生平慎重爲文,不熱衷於發表論文,故而許多重要論斷皆止於課堂之中。值得慶幸的是,他的許多觀點,爲後人所繼承和弘揚,進而融入了20世紀中國學術的大潮之中。
四 明史人才之培養與學術思想之傳承
鄭天挺培養了大批明清史專業人才,他的弟子最集中的地方,莫過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和南開大學歷史系,“鄭天挺把自己前半生的黄金歲月獻給了北大最艱苦的時期,又把他晚年最成熟的學術帶到了南開”。(58)早在西南聯大期間,鄭天挺就培育了何鵬毓。抗戰結束後回到北大,又教導出了戴逸、袁良義。在北大歷史系許多其他專業的專家,皆受過鄭天挺的教澤。五十年代進入南開後,鄭天挺培育學生有三途:“一,南大歷史系本設有明清史研究室,其中不少骨幹分子和後起之秀,這些人都是在毅老精心指導下壯大成長起來的;二,外校的中青年進修教師……三,指導研究生。”(59)“文革”前,鄭天挺招收過陳生璽、馮爾康、彭雲鶴、夏家駿等十餘位研究生。“文革”後,又招收過白新良、汪茂和、林延清、王處輝、何本方等5位研究生。這些弟子們學術上皆有建樹。此外,1959年,鄭天挺指導了明清史研究班。1979年下半年,受教育部委托,在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主辦了全國高校明清史教師進修班,一共有十二位青年教師參加了此研修班,日本東北大學教授寺田隆信亦前來進修。(60)這些弟子絶大多數在全國高校講授和研究明清史,將鄭天挺的學術思想在各地廣泛傳布。
更重要的是,鄭天挺一生未離開本科教學的講臺,在後人回憶鄭天挺的許多文章中,都提到過他一生都以教學爲己任。任繼愈説:“鄭先生工作忙,但從未放棄教學工作,他講授校勘學、明清史。”(61)田餘慶説:“鄭師的教學工作,并没有由於行政負擔太重而有所减免。他的明清斷代史課程年年照開。”(62)鄭天挺的教學有以下特點:
第一,上課没有講義,只携帶一系列卡片,所有資料與授課内容都寫在卡片上。田餘慶回憶:“鄭師用卡片講隋唐史,與講明清史辦法一樣。”(63)戴逸回憶:“他講課是没有講稿的,只帶一迭卡片,講起來却成竹在胸,旁徵博引,滔滔不絶。他知識淵博,觀察力敏銳,講話既清晰扼要,又條理井然,記録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64)鄧銳齡更形象地回憶鄭天挺講課情形説:“那時鄭師大概五十歲了,髮往後攏。臉色紅潤,態度和藹,笑容滿面,戴着近視鏡,穿着一領潔净的長衫,手持一迭卡片,滔滔不絶地講授……”(65)鄭天挺遺留下來的講課卡片體系完備,基本保存了講課的内容。(66)從已發現的教學卡片可知,鄭天挺授課非常重視介紹明清時期的特點,重視明清時期的歷史定位及與前代之比較和對後世的影響。如一份教學大綱記載:
第一編緒論;第一章明清史之特點:第一節明清兩代與前代之比較;第二節明清兩代對於近代之影響;第三節明史清史在史學上之地位;第四節對於明清史應具之認識。第二章明清史之分期:第一節明史分期;第二節清史分期;第三節講述分段;第三章明清史之參考書籍:第一節史籍(已整理者);第二節史料(未整理者);第三節國外論述與實物;第四章本課之要點。(67)
可見,他注意講述明清史的歷史特點、分期、地位、影響,以及學習明清史的主要史籍、史料和研究著作,其授課既有利於學生全方位地了解明清史,又爲學生繼續深入研究明清史提供了門徑。
第二,重視史料的介紹,將歷史事實與原始史料結合起來,以讓學生在接受歷史事實之同時,也指示他們一條繼續追尋的途徑。熊德基説:“他教課是在講内容之前,首先介紹‘明清史’的主要史籍,這使我可以擺脱一般參考書而直接閲讀原著。”(68)馮爾康也説:“明清史研究班開業的第一課,先生講《明史的古典著作與讀法》。”(69)程溯洛有更詳細的回憶:“那是三年級的上學期,我選修了鄭先生的明史課。……記得他在講正課之前,照例先介紹這一課程的資料目録學,光用板書寫出明史的史料和參考書刊,就足足花去了兩小時。等到講正課時,他就不再帶講稿,只在黑板上寫幾條重要的提綱,於是逐條憑記憶口述,由淺入深,順序闡明。”(70)可見,鄭天挺乃是在史料的基礎上,加入分析與解讀,把史實與史料結合起來,使學生直接接觸原始材料,既傳授了知識,也指示了治學的門徑。
第三,教學過程中,經常介紹學術動態。尤其是不同説法、不同觀點,都一一介紹,讓學生能够清楚地了解學術發展的態勢。鍾文典回憶:“一部《明清史》,從《緒論》到《南明與滿洲入關》,分七章講完。他不但對明清史中的重大問題進行精闢深刻的講解,而且對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人物、制度等也都作了精細的介紹和考證。每次講課,從不拘於一家之言。對一些重大問題,除了闡述自己的見解外,還經常介紹孟森、朱希祖、吴晗等先生的看法,以開闊同學們的視野,啓發大家獨立思考。”(71)程慶華也説:“鄭師講課,注意講清楚基本問題,每講到關鍵處,輒結合史源及有關研究,闡述自己看法。”(72)時刻把握學術動態,并將其介紹給學生,使學生們能够掌握最新的學術發展狀况,同時也給學生介紹自己最新的研究心得,在傳授知識的同時,開啓學生的眼界。
總之,鄭天挺一生未離開講臺,培養了一代又一代英才。(73)1981年秋,慶祝鄭天挺執教六十周年時,西南聯大校友會向鄭天挺獻上“春風化雨”的條幅,南開大學全體師生獻上“桃李增華”的條幅,乃是對鄭天挺作爲教育家的高度褒揚。
就學術機構建設而言,南開大學歷史系是鄭天挺一生最成功的傑作。雖説歷史系在1919年南開大學創立時,就已成立,且曾有蔣廷黻(1895-1965)擔任教授,梁啓超(1873-1929)曾來授課,但數年之後,蔣廷黻調入清華,南開大學歷史系於1926年改爲副系,失去了獨立性,一直到抗戰以後,從昆明搬回天津復校时1946年才再恢復。(74)當時南開歷史系師資匱乏,在全國是名不見經傳的。1952年鄭天挺奉調南開大學,任歷史系主任,他决心“要使南開歷史系步入强勁之林,與國内素享厚望的幾間大學并駕齊驅”。劉澤華深情地回憶,“先生以他特有的宏恢氣量和忠厚長者之風,團結了全體教師。……先生於中,發揮了伯樂與老驥的雙重作用,爲後人念念不忘”。認爲鄭天挺對南開大學歷史系的貢獻,“可稱之爲一篇無文的文章”。(75)在鄭天挺三十年的經營下,南開歷史系將北大史學科那種踏實嚴謹、維新開拓的治學風範加以繼承和弘揚,如今不僅成爲南開大學文理學科“四大支柱”之一,(76)而且在全國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歷史學陣地。這不僅因爲鄭天挺培養了一大批弟子,更重要的是因爲鄭天挺高尚的道德文章(77),給歷史系營造了一種祥和互助的氛圍,奠定了務實求新的學風,使得南開歷史學科多年來能够立於不敗之地。(78)明清史的研究更是有口皆碑的,自1956年,鄭天挺在南開建立明清史研究室以來,就成爲全國最重要的明清史陣地之一。即如任繼愈説:“鄭天挺先生早年得明清史專家孟森(心史)的真傳,由於不斷努力,繼續攀登,他的國際聲望甚至超過孟森先生,在南開大學創建了明清史的中心。”(79)王德昭亦言:“毅生師於明清史既有夙緣,加以和孟師的情誼,他之從中年以後以明清史研究爲身命之學,可説是繼孟師之後,維持北大明清史學的一脉,而更發揚光大之。其後毅生師移帳到南開任教,中國明清史研究的重鎮也遂移到南開。”(80)
鄭天挺在北大繼承和弘揚了孟森所開創的風範,又開創了南開大學明史研究的傳統,現在明史是北京大學與南開大學歷史學的重要陣地。鄭天挺之後,北大明清史先有許大齡、商鴻逵、袁良義,後有王天有、徐凱等人。南開的明史則在鄭天挺一手培植下慢慢發展起來。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部《明史》,就是由當時在南開工作的湯綱與南炳文撰寫的。湯綱本科畢業於復旦大學,成長於南開大學,他回憶説:“我在復旦歷史系學習期間,就對明清史感興趣,但并没有系統的學習,對明清史遠未入門。……對中國歷史和其它基礎知識都很貧乏。爲了彌補這方面的缺陷,在鄭先生的同意下,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了當時由鄭先生主持的明清史研究生班的學習。”(81)正是在鄭天挺培育下,湯綱後來成爲很有成就的明史專家。南炳文則一直在南開求學、工作,曾經多年擔任鄭天挺的助手。他説:“我雖然没有做過鄭先生的研究生,但鄭先生在學術上對我的熱心培養,却是我畢生難忘的。我今天之得以成爲一個明清史專業工作者,是和鄭先生的指導分不開的。”(82)1978年開始,湯綱與南炳文在鄭天挺的關懷下,開始《明史》的撰寫,《明史》上册成稿之後,邀鄭天挺爲其寫序。鄭天挺序中説:“這部書對作者自己的學習和研究是一個總結,對於其它學習和研究明代歷史的同志,或許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我祝賀這部《明史》的出版,更殷切希望今後出現更多更好的明代史專著。”(83)書中繼承和弘揚了不少鄭天挺對明史的思考。
鄭天挺的學術思想不管是無形還是有形地被後人所繼承和弘揚,我們雖然可以把握其綫索,而其弟子也或多或少地提及,但具體方面,尚需更嚴謹的研究。不過,在鄭天挺哲嗣鄭克晟的叙述中,爲我們探討這種學術淵源關係,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實例。鄭克晟的代表作《明代政争探源》(84),被視爲“是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具體運用於傳統中國社會歷史研究的一種富於建設性的嘗試”,“透過政治鬥争的表象揭示其社會經濟内涵”,并“獲得某種文化層面上的體驗”(85)。此書還被看作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明史學界“社會史取向的政治史研究”的代表作,“該書試圖爲明代近300年間的政治鬥争史找到一以貫之的社會經濟根源,認爲明代政争的實質在於北方地主集團和江南地主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兩大地主集團之間的對立長期延續下來,并在政治舞臺上表現爲尖銳的政見和權力之争。”(86)此書問世以來,受到學術界好評。(87)
對於此書的寫作緣起,鄭克晟在《緒論》中提及其雛形來自一篇會議論文《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與北方地主的興起》,概括其論文所涉及的八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麽明初的江南地主(主要指蘇、松地區)及士人,都對元朝懷念,甚至連宋濂、劉基這樣的開國勛臣,亦都如此?”接着他提及錢穆1964年發表於《新亞學報》六卷二期的論文《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所論證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最初并非是受錢穆影響,在本書《後記》中説:“我研究江南地主在政治上與明王朝的關係,係受先父鄭天挺教授的教導。若干年前,他對我説:1938年他在西南聯大歷史系開始講授明清史時,曾注意到明初許多江南文人都對元朝異常懷念,并舉宋濂等人的許多材料爲例,提出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這番話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决心遵循他指引的門徑進行初步鑽研。”(88)正是受到鄭天挺啓發,鄭克晟從明初入手,一直研究到明末清初,解剖了整個明代政治鬥争背後深刻的社會與政治根源。
筆者在鄭天挺明史教學卡片中,發現涉及明初士人懷念元朝的卡片有四十多張,略可分爲七個小問題,恰好印證了鄭克晟的話:
第一,“明人追念元代之原因”,共有兩張卡片。其曰:“明代尚有追念元代及張士誠之人——雖名公巨卿亦有之。追念元代者,其故不外下列數者:1.元代刑律寬仁,囚多老死而少誅戮。2.英宗有遺愛,在位三年免民租,罷金銀冶,减海運糧,行助役法,求隱逸,上書者得直達。3.脱脱有惠政(至元六年爲中書右丞相),復科舉,禁减鹽額,蠲負逋;4.元順帝有惠政;5.民間傳言順帝爲宋後。”第二,“元順帝之遺惠—明初人民追懷元代原因推測”,共七張卡片。逐一列出元順帝的惠政十餘件,如整治學校、禁私創寺觀庵院、遣使詣闕里祀孔子、復科舉取士制等等。第三,“元之取民甚寬——遺愛之一”,一張卡片。第四,“明初文字之元末紀年”,共十五張卡片,乃摘録宋濂、貝瓊、蘇伯衡、王祎等人文集中的相關史料,逐一説明此間題。第五,“明初人對元帝統及明得天下之觀感”,共十六張卡片。第六,“明人對於世變之觀念”,一張卡片。第七,“明初文人歸太祖之先後”,兩張卡片。(89)
可見,鄭天挺對於明初士人懷念元朝的問題,考慮得非常周詳。其日記也清楚記載了他讀明初史料與文集的事情,正可印證教學卡片,如1939年8月18日載:“讀《明史》開國諸臣傳、元末群雄傳。”(90)8月21日載:“讀《明書》開國諸臣傳,開國諸臣,太祖與之結姻婭者得十四人。”(91)日記中將十四人及所配婚姻之子女,皆考訂出來。1939年12月1日載:“讀清江貝先生集,録鐵崖先生傳中《正統辯》。”(92)次日則有讀《遜志齋集》的記載,三日,“讀《宋學士集》,摘其書元末紀元者,録之。”(93)一直到十日,方讀完《清江貝先生集》,因《明史·文苑傳》中,并未録入貝瓊(1314-1379)的傳記,鄭天挺在日記中考訂出了貝瓊的生平經歷。而那些教學卡片上,也標明所記録的時間,大多是在民國二十八(1939)年八月至十二月間所摘録的,正是日記所記的這段時間。當時鄭天挺與錢穆皆是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他的這些思考,是否與錢穆有過交流,或許錢穆對於此問題的思考是否受過鄭天挺的啓發,現在無法考證。鄭天挺在課堂上肯定講過此問題,儘管他没有寫出比較成形的論著,但他顯然早已涉及了這個重大問題。
鄭克晟則以此爲起點,進行了更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明初儘管出現了江南士人懷念元朝的現象,但這只是明初江南地主與北方地主鬥争的一個迹象,其深厚的根源則在於南北地主的鬥争以及利益紛争,鄭克晟以此爲契機,將其作爲解剖整個明代政治史的鑰匙,并將明初至明末的許多關鍵問題串聯起來,即如明初的蘇松重賦問題、建文改革、靖難之役、永樂遷都、明代莊田、萬曆北方水田,甚至於耶穌會士來華等問題上的紛争,全都看到背後南北地主政治與經濟利益上的鬥争,“上面所舉一系列的争論,均由於南北地域不同,地主階級内部利益各異,而明朝皇帝堅持扶持北方地主,打擊江南地主所造成的結果。”(94)從而抓住了整個明代政治與社會的歷史特徵,進而發展和深化了鄭天挺的學説,進一步讓學界認識了明代政治史、經濟史、甚至文化史的一些獨特之處。也可以説是鄭天挺學説的一種深厚的影響。但是鄭克晟并没有止於鄭天挺所關注的明初,而是將其鋪開到整個明代,甚至及於清初,視野更爲開闊,論證也就更爲系統和深入了。
關於鄭天挺明史方面的創見及其學術影響的研究是個很大的課題,本文祇是提出這個話題,當《鄭天挺明史講義》等材料整理出版後,當有更多發現面世。
五 餘論
20世紀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動蕩的時代,前半期的外侮,後半期的内亂,使得中國學術的發展頗受影響。鄭天挺儘管有過一定的波折,却是爲數不多的幾位一生政治與學術地位都没有太大改變的學人之一。自1933年到1951年,他一直擔任北大秘書長(西南聯大期間,任總務長),并曾兼任北大歷史系主任;1952年調任南開歷史系主任,1963年到1980年,爲南開大學副校長。四十餘年一直是明清史研究領域最爲重要的專家之一。誠如前文提及王永興、任繼愈、王德昭所言,自1938年春北大明清史教授孟森逝世後,學術界就將鄭天挺視作孟森傳人,被看成中國明清史研究的代表與化身,這反映了他在20世紀中國明清史學界的重要地位。在整個中國史學界,他也有較大的影響。
1949年7月1日,中國新史學會籌備會在北平成立之際,鄭天挺與郭沫若(1892-1978)、范文瀾(1893-1969)、陳垣等人一起五十餘人,皆爲發起人。(95)1951年7月,中國史學會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會,鄭天挺則未入選。隨着時間的流逝,他的政治與學術地位又得到各界人士的肯定。“在中國史學由百花凋殘的70年代進入百家争鳴的80年代之際,鄭天挺的學術聲望與長者人品,似乎在當時歷史學界獲得了一致的推重。”(96)1980年4月8日至12日,中國史學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召開第二届理事會。選舉理事會時,當時鄧廣銘以爲鄭天挺最合適,而劉大年以爲“唯有張友漁先生勝任”(97)。后來根據胡喬木(1912-1992)的建議,不提候選人,由各位大會代表自由選舉。(98)在這次選舉中,鄭天挺得125票,周谷城、白壽彝124票,鄧廣銘、黎澍(1912-1988)、劉大年各123票,鄭天挺得票第一,這樣選出了61名理事。“復由這61名理事中選出15名常務理事,再由常務理事選出5名主席團,此即鄭天挺、周谷城(執行主席,1898-1996)、白壽彝(1909-2000)、劉大年(1915-1999)、鄧廣銘(1907-1998)。鄭天挺仍居首位。”(99)這是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兩次選舉,鄭天挺皆得票最多,真可謂德高望重、衆望所歸。也正是在1980年8月,鄭天挺倡議并在天津舉辦了建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者來自八個國家,一百三十多人,轟動學林,鄭天挺再一次走在時代前列,開啓了與國外明清史學者交往的先聲。(100)
總之,鄭天挺在明史研究領域留下的論著雖然不多,但他對20世紀中國的明史學界,却寫下了一篇“無文的文章”。(101)
本文得到鄭克晟師、常建華、喬治忠、姜勝利、封越健和朱洪斌等師友的指教;2011年4月11-12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與香港珠海學院合辦的“明史認識與近代中國歷史走向”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得到朱鴻林、徐凱、毛佩琦、王春瑜和沈定平等教授指教,特此一併致謝。
注釋:
①相關研究參見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啓示:20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趙毅、欒凡編著:《20世紀明史研究綜述》,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②既往探討鄭天挺史學成就的論文大都側重他在清史方面的貢獻。陳生璽在《史學大師鄭天挺的宏文卓識》一文中,較詳細介紹他對於明史分期、明代歷史特點以及朱元璋評價方面的論點。常建華在《鄭天挺教授與明清史學》一文中,介紹了鄭天挺對於明清史分期、明代政治制度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等方面的成就。(參見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07-312,350-364頁。)
③《清史探微》1946年由獨立出版社在重慶初版。1980年補入相關論文,改名爲《探微集》,由中華書局出版。199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清史探微》修訂本。2009年,中華書局再版修訂《探微集》。此書版本不一,但集中了鄭天挺最爲重要的清史研究論文。
④參見南炳文:《二十世紀的中國明史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⑤黄冕堂:《明史學記》,《文史哲》1987年第3期。文中相關人物的生卒年,是筆者引用時所加。
⑥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爲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年,第2頁。
⑦參見尚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之表16《1929-1931各年度北大史學系開設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7頁。
⑧尚小明在其《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書中第36-41頁,有一表格《1917-1937年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講師》,其中一欄“開設課程”,涉及明史課程的有倫明(1930-1933年北大史學系),開設過“明清史籍研究”;孟森(1931-1938年在北大史學系),開設過“滿洲開國史”、“明清史料擇題研究”、“明清史”等;錢穆(1931-1937年在北大史學系),開設過“宋元明思想史”;向達(1934-1937年在北大史學系)開設過“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史”等;鄭天挺(1936-1937年在北大史學系)開設過“明清史”。這是與明史相關的課程,但是與明朝斷代史相關的則衹有孟森和鄭天挺二人,其餘皆是從某個專題涉及明史。不過説鄭天挺在1936-1937年開設過明清史,與鄭天挺的日記和自傳的記載不合。
⑨王曉清:《學者的師承與家派》之《其學可感,其風可慨——鄭天挺學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1頁。
⑩鄭天挺:《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紀念孟心史先生》,參見鄭天挺:《探微集》(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617頁。
(11)郭衛東、牛大勇主編:《北京大學歷史系簡史》(初稿)之《北京大學歷史系大事記》,此書是内部發行,無出版信息,第288頁。
(12)王永興:《忠以盡己,恕以及人——懷念恩師鄭天挺》,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65頁。
(13)鄭天挺:《自傳》,吴廷璆、陳生璽、馮爾康、鄭克晟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第702頁。
(14)《鄭天挺日記》(未刊稿)是鄭天挺自1924年到1951年間的日記,其中1924年到1934年皆只簡單記載,比較詳細留存的有1938年到1945年的日記,即西南聯大期間的日記。每年日記開始的第一頁,皆會記録當年的年歲、任職、教授課程和寓居之處。所有日記,皆是繁體字,無標點符號。引文中的標點,乃是筆者所加。
(15)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四册(1939年),第1頁。
(16)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五册(1940年),第1頁。
(17)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六册(1941年),第1頁。
(18)鄭天挺:《五十自述》,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1984年,第22頁。又見鄭天挺:《自傳》,吴廷璆等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第702頁。
(19)鄭天挺:《史料學内容的初步體會》,鄭天挺:《探微集》(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46頁。
(20)鄭天挺:《史料學内容的初步體會》,鄭天挺:《探微集》(修訂本),第347頁。
(21)馮爾康:《從學瑣記》,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325頁。
(22)鄭天挺:《漫談治史》,文史知識編輯部編:《與青年朋友談治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9頁。
(23)鄭天挺:《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史料處理的初步意見》,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47頁。本文最初乃是1956年10月鄭天挺在南開大學舉行的第二次科學報告討論會上宣讀的,除南開大學歷史系的教師外,還有北大、北師大以及天津其它高校的教師參加了此次討論會。參見陳枏《記南開大學第二次科學報告討論會歷史學分會情况》,《歷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94-99頁。
(24)參見鄭天挺:《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史料處理的初步意見》,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第243頁。
(25)陳枏:《記南開大學第二次科學報告討論會歷史學分會情况》,《歷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94頁。
(26)鄭天挺:《五十自述》,參見《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1984年,第9頁。又見鄭天挺:《自傳》,吴廷璆等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第687-688頁。
(27)《明清内閣大庫史料》第一輯上、下册,沈陽:東北圖書館印行,1949年12月。
(28)參見鄭天挺:《自傳》,吴廷璆等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第707頁。
(29)鄭天挺主編:《明清史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30)《明史讀校拾零》録入《探微集》中,2002年編輯鄭天挺遺稿成《及時學人談叢》一書,亦録入部分,名《明史零拾》,二者内容多不同。
(31)閻文儒:《懷念毅生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36頁。
(32)張廷玉:《明史》卷一《太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頁。
(33)鄭天挺:《〈明史〉讀校拾零》,鄭天挺:《探微集》(修訂本),第558頁。
(34)姜勝利:《20世紀明史研究巡禮》,《南開學報》2009年第6期,第49頁。趙毅、欒凡編著的《20世紀明史研究綜述》中,對此也給予了充分肯定,在討論20世紀50年代至1978年間的明史研究問題時,説:“史料整理工作在這一時期也有較大的進展,首先是《明史》點校完成,這是鄭天挺帶領南開大學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的全體同志共同完成的。”第11頁。
(35)即如王天有、馮佐哲、萬明等回憶許大齡指導他們如何讀《明史》,分别參見《憶許大齡先生》、《憶許大齡教授教我們學習明清史》、《我隨許師學明史》,參見王天有、徐凱主編:《紀念許大齡教授誕辰八十五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36)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五册(1940年),第11頁。
(37)儘管鄭天挺不願爲西南聯大總務長,多次拒絶,但西南聯大常委會於1940年1月9日通過了决議,并且送來了聘書,北大領導爲了照顧關係,也催他上任。是年2月,鄭天挺遂任總務長一職。參見鄭天挺:《自傳》,吴廷璆等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第701頁。
(38)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一册,第285頁。
(39)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五册(1940年),第106頁。
(40)(41)(42)(43)(90)(91)(92)(93)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四册(1939年),第19-20頁、第80頁、第84頁、第86頁、第123頁、第125頁、第207頁、第208-209頁。
(44)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四册(1939年),第94-96頁。有關此事在臺灣傅斯年紀念館中,亦發現相關資料。參見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年,第105頁。
(45)鄭天挺:《自傳》,吴廷璆等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第700頁。
(46)轉引《學者、教育家的典範:鄭天挺教授百年冥誕紀念(代序)》,南開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頁。
(47)鄭天挺的學術卡片皆以這樣的方式寫的,在已出版由王曉欣和馬曉林整理的《鄭天挺元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中,有詳細的説明。
(48)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第三册(1938年),1938年12月8日日記,第490-491頁。
(49)引自鄭天挺明史教學卡片(未刊)。孟森在《明史講義》中,分“開國”、“靖難”、“奪門”、“議禮”、“萬曆之荒怠”、“天崇兩朝亂亡之炯鑒”和“南明之顛沛”等七章,叙述明朝歷史。雖然并未説是嚴格的分期,但也略可窺見孟森的分期原則。商鴻逵在《讀孟森〈明清史講義〉》一文中介紹,孟森於明史大致分三個時期:初期爲洪、永、熙、宣,中期爲正統至隆慶,末期爲萬曆至崇禎。參見商鴻逵:《明清史論著合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50)陳生璽:《史學大師鄭天挺的宏文卓識——紀念鄭天挺百年誕辰》,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307-308頁。
(51)鄭天挺:《明清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第12頁。
(52)鄭天挺:《清史簡述》,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第249-251頁。
(53)鄭天挺:《明清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第11頁。最近二、三十年來,西方學術界將16世紀以后的明清時期,稱爲“晚期中華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時期,强調市場與商業的影響以及中國自身社會與文化中的現代性因素,與鄭天挺的説法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性。參見司徒琳主編:《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趙世玲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司徒琳、萬志英:《兩卷本前言》,第4-5頁。
(54)鄭天挺:《明清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第9-19頁。
(55)鄭天挺:《關於徐一夔〈織工對〉》,最初於1958年發表於《歷史研究》第1期,後收入《探微集》中。
(56)鄭天挺:《明代的中央集權》,《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第53-59頁;又參見鄭天挺:《及時學人談叢》之《明代的中央集權、内閣和六部職權的消長》,第24-35頁。兩篇文章大同小異。
(57)以上引文皆參見鄭天挺明史教學卡片(未刊)。
(58)《學者、教育家的典範:鄭天挺教授百年冥誕紀念(代序)》,南開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1-2頁。
(59)羅繼祖:《憶鄭毅老》,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43頁。
(60)參見南炳文:《推動歷史學科發展的三十年——鄭天挺教授在南開大學》,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210-225頁。
(61)任繼愈:《西南聯大時期的鄭天挺》,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200頁。
(62)田餘慶:《憶鄭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98頁。
(63)田餘慶:《憶鄭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98頁。
(64)戴逸:《我所了解的鄭天挺教授》,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21頁。
(65)鄧鋭齡:《憶鄭毅生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15頁。
(66)有關鄭天挺的講課卡片,現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正在整理之中,將陸續出版。其中,明史講義的學術卡片,目前整理出來的篇幅近四十萬字,涉及明史的諸多方面。
(67)引自鄭天挺明史教學卡片(未刊)。孟森:《明史講義》,“商傳導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此書第一編《總論》,分兩章,第一章《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第二章《明史體例附明代系統表》,乃是分析清官修《明史》的體例、意義與學術價值。
(68)熊德基:《鄭天挺的“身教”永志難忘——敬悼鄭毅生老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45頁。
(69)馮爾康:《從學瑣記——兼述鄭毅生師的學術成就》,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321頁。
(70)程溯洛:《懷念鄭毅生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41頁。
(71)鍾文典:《回憶鄭天挺老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00頁。
(72)程慶華:《懷念先師鄭天挺的教誨》,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73頁。
(73)在20世紀20、30年代,有不少大學教授雖有滿腹經綸,但因不善講課,而受到學生批評,甚至被驅趕者也并非鮮見。那時候,某種程度上,講課風采也成爲學生評判教授的一個重要標準。參見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第280-282頁。
(74)參見常建華:《明清史學大家鄭天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近代天津十二大學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4頁。
(75)劉澤華:《教誨諄諄多啓迪》,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49、150頁。
(76)南開大學的“四大支柱”學科,乃是指文科中的經濟學與歷史學,理科中的數學與化學,在全國學科排名是名列前茅的。
(77)鄭天挺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自他1981年12月逝世之後,南開大學歷史系與北京大學歷史系聯合召開過多次紀念會,并先後出版過《鄭天挺紀念論文集》(吴廷璆等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鄭天挺學記》(馮爾康、鄭克晟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和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乃截止2008年,紀念鄭天挺文章的集大成)等多種論著。即如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詞語小記》的前言中説:“鄭毅生(天挺)先生道德文章都爲我師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第77頁。
(78)關於鄭天挺對南開史學的貢獻,可參見王昊:《南開史學與鄭門學風——寫在鄭天挺先生逝世廿五周年之際》,夏中義、謝泳主編《大學人文》第7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8-183頁。
(79)任繼愈:《西南聯大時期的鄭天挺》,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200頁。
(80)王德昭:《鏗然捨瑟春風裏——述往事憶鄭天挺毅生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68頁。
(81)湯綱:《循循善誘 誨人不倦》,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30頁。
(82)南炳文:《就治學憶鄭天挺》,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386頁。
(83)湯綱、南炳文:《明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鄭天挺《〈明史〉序》,第1-2頁。
(84)鄭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85)劉志偉、陳春聲:《揭示傳統中國政治鬥争的經濟和文化内涵——讀〈明代政争探源〉》,《廣東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第136頁、第121頁。
(86)高壽仙:《改革開放以來的明史研究》,《史學月刊》2010年第2期,第12頁。
(87)趙毅、欒凡編著的《20世紀明史研究綜述》中,評價此書:“全書史料翔實,内容豐富,立論有據,對明代一些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的研究。”第309頁。
(88)鄭克晟:《明代政争探源》之《後記》,第396頁。
(89)文中的引文,皆出自鄭天挺明史教學卡片(未刊)。
(94)鄭克晟:《明代政争探源》之《緒論》,第4頁。
(95)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6册(1947-1950),附1949年7月8日《文匯報》剪報《新史學會籌備會在平成立》,第495-496頁。有關1949年前後中國史學會的情况,參見桑兵:《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16-139頁。
(96)王曉清:《學者的師承與家派》之《其學可感,其風可慨——鄭天挺學記》,第216頁。
(97)鄧鋭齡:《憶鄭毅生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18頁。
(98)王玉璞:《劉大年與中國史學會》,中國史學會秘書處編:《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620頁。
(99)鄧鋭齡:《憶鄭毅生師》,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18頁。
(100)1978年8月,旅美華人學者魯諍特地去南開大學采訪鄭天挺,并寫出了《與鄭天挺教授談明清史的研究與教學》,1979年發表於香港《抖擻》第34期上。1979年6月,美國首次組織十位明清史專家代表團訪問中國,盡管代表團没有訪問天津,但鄭天挺還是在南京與代表團進行了會談和討論。參見魏菲德等著、孫衛國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史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可見,在剛剛打開國門之時,海外明清史學界對鄭天挺也極其關注。
(101)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澤華曾言,鄭天挺對南開大學歷史系寫的是一篇無文的文章。參見劉澤華:《教誨諄諄多啓迪》,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第15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