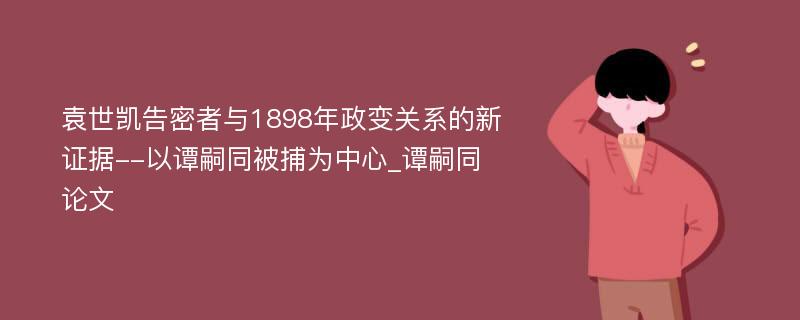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政变论文,时间为论文,关系论文,谭嗣同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3-0140-06
孔祥吉指出:关于戊戌政变的导火线究竟是不是袁世凯告密,史学界颇有争议。黄彰健专门撰文考订谓:“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①。房德邻亦持同样观点②。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戊戌政变如果是由袁氏告密而爆发,那么,八月初六日(9月21日)的上谕就应提到下令捉拿游说袁世凯的要犯谭嗣同。既然清廷只是称:“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③。清廷直到八月初九日(9月24日)才颁谕捉拿谭嗣同,说明政变的爆发,应在袁氏告密之前。孔祥吉还表示,他对黄彰健的考订“始信终疑”④。
孔祥吉的怀疑,事实上已被茅海建的新著《戊戌变法史事考》的细致深入考据所证实,尽管该书仍认为黄“提出的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起,袁告密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的判断,具有经典性”⑤。
茅海建指出:“该谕旨在军机处的《上谕档》、《随手登记档》、《交片档》、《交发档》、《交事》各档册中均不载……由此再查《清实录》,竟注明此谕旨录自《东华录》!档案中最先出现此旨,为八月十一日(9月26日)以刑部尚书为首的奏折:‘本月初六日,步军统领衙门奉密旨:工部主事康有为……’崇礼为刑部尚书又兼任步军统领,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之臣,他可能不是从军机处受旨,而是直接从慈禧太后处受旨。对此郑孝胥在该日记中称:‘长班来报,九门提督奉太后懿旨锁拿康有为,康已出都,其弟康广仁及家丁五人已被拿获’”⑥。
刑部主事唐烜在9月21日日记中也说:“是日在署,忽喧传步军统领衙门奉皇太后懿旨,查抄张荫桓,并捕拿康有为等辈……及探听数四,始知系奉口诏严拿康某……薄暮始阅邸抄,上谕恭请皇太后听政,以今日为始,至初八日率王大臣在勤政殿举行典礼”⑦。上海《中外日报》1898年9月27日记:“北京9月24号午刻发来专电云:皇太后垂帘后,即传旨将张荫桓、康有为拿办,并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梁启超革去六品顶戴举人,一体拿办”⑧。11月7日记:“当京内严拿康党之际,步军统领衙门九门提督带同骑兵四十名至南海会馆,当悉康有为、梁启超业已在逃。馆中拿获拔贡某在后进。康广仁匿在堆积煤炭之处,亦经拿获,既装车载往刑部,随即他往严拿余党如杨深秀等。如此查拿四日,乃有人奏谓恐致激变,遂中止”⑨。与唐烜说可相参证。《申报》1895年9月26日记24日康有为在吴淞口脱险事时并谓:“先是道宪蔡观察接得密电,尚有粤省举人梁启超即梁卓如系康门生……亦令一体拿究”⑩。茅海建根据《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指出,在缉拿康有为的同时,清政府亦在缉拿梁启超,因在北京遍搜未获,认为梁已潜往上海,于是在24日电旨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在上海缉捕。25日,上海道蔡钧遵命搜梁在上海的寓所,未获,仅获到司事张其时等。其父梁宝应、弟梁启芬已于22日乘永生轮船赴粤(11)。可见9月21日慈禧发出口谕,包括梁启超、杨深秀在内的康党已均在搜捕之列,而康党及其亲属在搜捕开始后已尽可能隐匿逃逸。
搜捕始于何时?《申报》1898年10月19日载:“自奉严拿逆犯康有为之旨,步军统领崇受之(礼)大金吾,于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午前十一点钟后,至南海会馆搜捕不获,随带司员人等,搜其行箧……惟将信件一一过目,约两点钟许,悉数携归提督衙门”(12)。当日下午2时,梁启超跑到日本公使馆,对代理公使林权助说:“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志士,都被逮捕。其首领是康有为,想也快要被捕被杀头!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林权助记:“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当时门房报告:门前不安,好像是捕手觉着康或是谁逃进公使馆似的。”梁启超遂在使馆避难(13)。林权助9月24日致大隈重信的密信引梁语谓:“清政府已断然镇压改革派,与康有为一起从事改革之人,均不能免遭逮捕和刑戮,若我公使馆能保护其安全,实乃再生之德”(14)。林权助引梁启超所说当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都已被逮捕之语,并不准确,但提示此4人中当时可能已有被捕者。
以上情况说明,黄彰健、房德邻引以为据的“八月初六日上渝”纯属子虚,它不过是《东华录》根据崇礼9月26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9月21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事实表明,慈禧9月21日口谕中的搜捕目标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
在围搜南海会馆前后,清廷一直未就此公开发布上谕,其用心当在尽可能麻痹未拿获者。三天之后,即9月24日,清廷才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15)。郑孝胥记:“八月初九日(9月24日),晨起作字。闻街市传言,有缇骑逮七人,即四军机章京,三人未详。”林旭确是在24日晨被捕的(16),但其他人不可能都这么巧与林同时被捕。据张荫桓自述,9月21日其住宅已被监控,23日被扣押于提督衙门,24日入刑部监狱(17)。张未参与“围园”密谋,在9月24日上谕提到的7人中地位最高,“罪行”最轻,危险性最小,且已被监控,不急于捕拿有利于安定人心,故其被捕,在7人中应属较迟之列。可见此7人的被捕时间,不能再以9月24日上谕为依据,且其被捕为“先后”而非“同时”,当从9月21日起已陆续被捕,至9月24日上谕发布前已全部拿获。梁启超无疑是清廷逮捕的重点目标,但因未能拿获,9月24日上谕竟只字不提,足可为旁证。梁启超后来宣传说谭嗣同9月25日被捕,房德邻根据谭嗣同的3封遗札,指出此说不足信,谭之被捕,应在此之前。但房仍以梁《谭嗣同传》谓谭在22日曾入日使馆与之相见为据,将谭之被捕定在22日(18)。然而,如《谭嗣同传》这一情节可信,则日使馆之报告及林权助的回忆录对此不会全无反映;而且从林权助所说21日晚使馆门口情况来看,清政府22日必已对日使馆严密监视,谭嗣同绝不可能出入自如,故《谭嗣同传》云云,应同为梁启超出于宣传目的而随意编造,同样不可信。28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处斩,但具体“罪行”未公布。29日,清廷才宣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并下令严拿梁启超(19)。10月2日上谕才查问王照下落,4日才下令严拿(20)。但这当然不等于慈禧到29日才知道“围园”密谋,决定逮捕梁启超,到10月4日才决定逮捕王照。1898年10月2日《申报》记:“同日(9月24日)礼部主事王照亦奉懿旨革职永不叙用,惟尚未降明文”(21)。结合上引资料,可知政变期间,未降上谕或事后始补发上谕,而由慈禧直接口头发号施令惩办康党,实为常例。由于牵连到光绪帝,慈禧发布消息十分慎重,在尘埃落定之后始公布密谋,而其动机无疑是尽可能掩盖真相,安定人心,稳住局面,减少社会震动,避免外界干预。“六君子”之所以未经审讯即匆忙处斩,主要也是出于同一考虑。这6个人中,康广仁、杨深秀、林旭、谭嗣同都参与了密谋,杨锐、刘光第虽非康党,但也涉嫌知情不报。
在9月24日上谕提到的7人中,弄清谭嗣同的被捕时间最为关键。魏允恭致汪康年函云:“今(9月23日)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闻避往他处。”论者或以此证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均在9月23日被捕。然而,这样说就意味着魏允恭目击此3人不但同时而且同地被捕,但是该函又云:“且近日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22)。可见这些人是“近日”先后在不同地点被捕,而不是23日同时同地被捕,所谓“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是指由被捕后的拘留地提督衙门转解,“发交刑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有《狱中遗札》,其第一札云:“昨送来各件,都不差缺……惟王五爷当能进来,并托其赶快通融饭食等事……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第二札云:“速往源顺标[镖]局王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呼]……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从内容看,第一札写于被捕后第二天,第二札写于被捕后第三天;第一、二天均押在提督衙门,第三天则已押在刑部监狱(23)。其转解刑部监狱既在9月23日,则谭嗣同之被捕,就在9月21日,即政变发生的当日。至于八月十一日(9月26日)刑部复奏所说7名官犯于初十日移交刑部收监,那是事后编造的,房德邻已指出其不足信(24)。
以上情况进一步说明,在政变发生的当天,谭嗣同即已被捕;论者以所谓“八月初六日上谕”未提“围园”、谭嗣同为据,推断慈禧发动政变时尚未获悉袁世凯告密内容,未知“围园”密谋,因而未缉捕谭嗣同,实为脱离当时具体情况的简单化臆断。
为探讨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有必要确定政变爆发的标志。笔者认为,应以光绪帝丧失人身自由之时,为政变爆发之始。政变在宫廷内发生时的具体时刻、情形,没有一个当事人留下记录,而流传至今的各种绘声绘色的生动记载的作者,不仅没有一个是当事人,而其情节亦多有经不起推敲之处。或谓政变发生于9月21日早朝,其实并无可靠证据。宫内当时实情,既难以确知,唯有退而求诸宫外。政变发生,其最早反映在社会上的标志,应是1898年9月21日对康党的突然搜捕,而不是同日稍后“训政”上谕的公开发布(25)。当然,政变的发生,应稍早于搜捕的开始。林权助引梁启超所说康党被搜捕时“皇帝不用说已被幽闭”是合理的推断。由此,可将政变发生时间定在21日约上午10~11时,或可能稍早一些。由郑孝胥所说“奉太后懿旨锁拿康有为”,唐烜所说“奉皇太后懿旨……捕拿康有为等辈”、“奉口诏严拿康某”,可知此系根据临时获悉的情报,因事出突然而仓促采取的紧急行动,故来不及以光绪帝名义拟旨,仅由慈禧匆匆口头传令,并非早有预谋。
谓戊戌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者,除引“八月初六日上谕”外,往往还以袁世凯《戊戌日记》为据(26)。其一,谓袁到天津已晚,当晚向荣禄告密后,不可能在政变发生前及时报告慈禧。其实,袁世凯到达天津是在9月20日下午3时(27)。并不晚。《戊戌日记》所谓“抵津,日已落”,恐系误记。论者说是指从火车站下车,与迎接的官员应酬,再到荣禄处,需3个小时,故到荣禄处“日已落”。然而《戊戌日记》明明说:“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28)。可见袁说“日已落”是“抵津”之时,不是见到荣禄之时;袁抵津“即”谒荣告密,时间紧密相接,是否需要3小时其实大可存疑。退一步说,即使向荣禄告密确在下午6时,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要在翌日上午10时左右报告慈禧,时间也足够了(29)。其二,论者解读《戊戌日记》,谓荣禄因为首先考虑要“保全皇上”,未即时报慈禧,第二天和袁世凯“筹商良久,迄无善策”,仍未报告,把袁世凯所说“是晚荣相(禄)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30),理解成荣禄尚未报告慈禧之前,慈禧已先发动了政变。这种理解完全悖于情理。荣禄虽然是慈禧的宠臣,但如果他获悉危及慈禧生命的惊天“逆谋”后,竟拖延了24小时以上,直到搜捕“逆党”后才报告,慈禧还会不认为他纵容包庇“逆党”而予严惩吗?亦有论者认为,由于荣禄可以肯定“逆谋”绝不可能成功,所以不急于报告。这种推断也完全悖于情理。康有为的政变图谋当然绝不会成功,但荣禄如因此而不即时报告,就不仅使“逆党”有可能逃脱,而且同样有纵容包庇“逆党”的重大嫌疑。荣禄敢这样做吗?从行文和事理分析,所谓“自内先发”并不是说“训政之电”在荣禄报告之前已先发,只是说在荣、袁筹商出善策之前已先发而已。
通读《戊戌日记》,完全看不出袁世凯有否认其告密促成政变之意。恰恰相反,他说:“然区区此心,意在诛锄误国误君之徒。该党无礼于君子,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皎皎此心,可质天日,且亦正所以保全皇上。倘该党等凶谋果逞,必将难保宗社,更何以保全皇上?此亦必然之势也。为臣子者,但求心安理得,此外非所计也”(31)。明言正是他的告密遏止了康党的“凶谋”,保全了皇上和宗社,并因此心安理得。他明确记载自己一到天津即向荣禄告密,至于荣禄是否即时向慈禧报告,怎样报告,不是他做的事,他也不一定清楚,不记载完全合乎常理。论者以“袁世凯无记载”来断定荣禄未即时报告,既悖于情理,也违反逻辑。论者还由荣禄第二天与袁世凯商谈“保全皇上”之策而未有结果,断定由于未想出办法而未报告,就更悖于情理了。袁世凯不但没有这样说,而且明确指出,告密正是保全皇上的当务之急,哪有因要保全皇上而不报告之理!他再三申说的,不过是他告密并非出卖皇上,而正是保全皇上的不得已之举,并强调自己告密之后,曾为保全皇上费尽心机。
否认袁世凯告密引发戊戌政变者,多强调政变之诱因为杨崇伊奏疏。按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在9月12日以“个人游历”的身份抵达天津,14日人北京,与康有为等人频相过从。后党因此大为恐慌。9月18日,御史杨崇伊向慈禧密呈《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声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32)。这些话当然能打动正因光绪帝谋开懋勤殿向她要权而十分恼火的慈禧。19日晚,她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加强了对后者的监视和约束。20日,林旭对郑孝胥说:“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33)。但从史料和情理分析,她收回权力所采取的手段,形式上仍较温和,尚无证据表明当时她已不顾肯定要带来的极为严重的负面政治影响,马上作出囚禁光绪帝、捕杀康党的激烈决定。她尽管在20日已实际剥夺了光绪帝本来就极有限的政治权力,却仍未决定马上恢复“训政”的形式,表面上光绪帝仍是单独处理政务,当日也就不能称之为“政变”。王照说:“杨崇伊邀合京中大员密折吁请那拉氏训政之后,虽那拉未即应允,而景帝已惴惴不自保,将前此开懋勤殿选顾问之谋已暗消矣”(34)。可为旁证。若非后来获悉“围园”密谋,受到强烈刺激,慈禧的“收权”措施本已可暂时告一段落,不致迅速演变成激烈政变。
论者又引蔡金台致李盛铎函,以否认政变由袁世凯告密引发。然该函云:“会袁世凯来,而谭嗣同说以调兵,人见语亦云然。袁乃密白略园(荣禄),电庆邸(奕劻)达之,而杨莘伯(崇伊)乃持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颐和园昆明湖)呈递”(35)。可见该函也认为袁世凯告密是引发政变的主因。论者虽也引用了“袁乃密白略园,电庆邸达之”及以下的话,却略去了关键的“会袁世凯来,而谭嗣同说以调兵,入见语亦云然”,以致结论明显与蔡函本意偏离(36)。
而主张政变确由袁世凯告密引起的论者,又或以为9月18日晚袁世凯获悉康党密谋后,立即启程,赴津告变;荣禄立即微服回京,到颐和园向慈禧泣诉;慈禧则立传内侍,驾还西苑,时为19日。慈禧认为有能力控制局势,布好天罗地网,至21日始发难(37)。然若果如是,则康、梁都早已在严密监控之下,何至任其逃逸?何以康有为出京抵津登轮,毫无障碍?揆诸事理,殊不可解。
客观地说,《戊戌日记》虽有误记,大体属实,与其他资料可互相参证。论者以误读为依据,否认袁世凯告密促成政变,恐非定论。不过,袁世凯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原因。
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说:“且奴才与杨深秀初次一晤,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38)。至其具体内容,因情节严重,文悌未公开,倒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透露了一点真相:“御史文悌满洲人也……经胶、旅后,虑国危……适同侍祠,竟夕语君(杨深秀)宫中隐事……因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燕啄王孙’四语,目眦欲裂。君美其忠诚,乃告君曰:‘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闻君门下多识豪杰,能觅其人以救国乎?’……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难成,先生见文则诘之,文色变,屡君之泄漏而败事也……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政变后之伪谕,谓康先生谋围颐和园,实自文悌起也”(39)。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亦记:“深秀尝与文悌值宿斋宫,尽闻宫中隐事,夜半奋髯起曰:‘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宾王)矣’”(40)。梁、胡政治立场相反,而所述大体相同,可证确有其事。另有人记:“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41)。无论是参考旁证或从事理分析,此类话显然都出于杨深秀而非出于文悌。
康有为曾在1898年春对人说:“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并逼胁皇上,勒令变法,中国即可自强”(42)。弄得尽人皆知。高树《金銮琐记》记:“康长素向人言:‘以兵围园,不令太后与闻国政。’此语喧传都下。余曰:‘速发传单,言我等与康无交情,免受其祸。’叔峤(杨锐)以为可,而同人畏康不敢从”(43)。王照说:“围禁慈禧之谋,蓄之已久,南海因言用兵力夺权之计。余已再三面驳,故又令他人言之,以全颜面。然深信之诤友必不泄也”(44)。唐烜说:“先是都下有知其逆谋者,喧传已旬余矣,众咸弗信”(45)。政变前夕,许世英听到有关“围园”传闻,跑去问刘光第,刘说:“确曾有此一议”(46)。“密谋”如此不密,即使袁世凯不去告发,慈禧也很快就会从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政变实属必然。
注释:
①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版,第493页。
②(18)(23)(24)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5~283、255~263、255~263、258页。
③(15)(19)(20)(3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9、100、103、105~106、574页。
④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31页。
⑤⑥(11)(14)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第163、121、494、490页。
⑦(37)(45)唐烜:《留庵日钞》,转引自孔祥吉《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读唐烜稿本〈留庵日钞〉》,《学术界》,2004年第1期。
⑧⑨⑩(12)(13)(21)《戊戌变法》第3册,第420、451、419、439、571~572、428页。
(16)(33)马忠文:《戊戌“军机四卿”被捕时间新证》引郑孝胥日记,《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17)(28)(30)(31)《戊戌变法》第1册,第489、553、553、555页。
(22)《汪康年师友信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15~3116页。
(25)叶昌炽日记:“初六日午后,史馆堂期供事,从内阁钞示本日谕旨:……(即训政诏,略)。又上谕:‘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戊戌变法》第1册,第531页。
(26)骆宝善:《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27)《国闻报》1898年9月24日,《戊戌变法》第3册,第411页。
(29)技术含量低但简易可行的方式是当晚派“折差”骑马入京,抵京时城门当已关闭,可能须待翌日晨入城。
(32)《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461页。
(35)《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页。
(36)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在骆文发表同时及其后,赵立人《重评维新运动》(《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术研究杂志社1999年5月版,第278页)及孔祥吉《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均以此函作为袁告密引发政变的论据。
(38)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戊戌变法》第2册,第488页。
(39)(40)《戊戌变法》第4册,第59~60、61页。
(41)陈声暨:《陈石遗先生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208页。
(42)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载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43)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4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3页。
(46)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标签:谭嗣同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广东社会科学论文; 历史论文; 康有为论文; 梁启超论文; 慈禧论文; 申报论文; 瓜尔佳·荣禄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思想史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