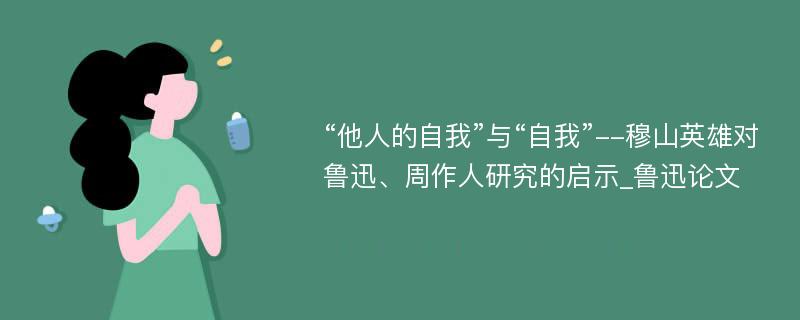
“他人的自我”与“自我”——木山英雄对鲁迅、周作人研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自我论文,启示论文,英雄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10)02-022-03
日本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时,一直贯穿着复杂的心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解,呈现出与古典文学研究不同的态势。其间的问题意识也大异于中国学界,于是便成了一个奇异的参照。考察日本学界的思维特点,自然存在着多种路向,几代学者形成了不同的传统,但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围绕中国现代性的变迁,寻找日本知识界的自我意识。中国作家提供的精神图景,作为一种对照,被内化为一些学人批判日本社会的精神因子。
竹内好① 在20世纪40年代曾写过一本《鲁迅》,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强烈的影响力。这本书的出发点是典型的日本式的自问,即带着对人生疑问而与鲁迅发生了精神纠葛。此后丸山昇② 从政治层面理解鲁迅文学,大江健三郎③ 在存在的困惑层面与鲁迅的相知,以及伊藤虎丸④ 从“近代性”的视角考察日中两国现代性的起点,都有意味深长的发现。但是在诸多研究者中,木山英雄的写作独树一帜,不仅突破了日本学界的惯性思维,更在于找到了别于中国智慧的表达式。
直到今天,木山英雄的著作只有《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苦住庵记》译成了中文。他的文本与一般日本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其更愿意从悖论的人生经验中考察日中文学的内在紧张度,而他颇富有玄学之力的内省,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是少见的。
木山英雄生于1934年,东京大学毕业后在一桥大学任教多年。他对中国的研究内容很广,包括对章太炎、鲁迅、周作人、聂绀弩、胡风、启功、李锐等的深切解读。尤其是他对周氏兄弟的研究,目光独异。他在对周氏兄弟的研究中意识到了鲁迅、周作人身上的罪感意识,精神深处被诸多不确切性、互为否定的东西所缠绕。即便是讲到文学与革命的话题,他也发现了革命话题对鲁迅的另一种意义。“而革命通过它使诚实的诗人感到幻灭,则证明了这革命是真的革命。”⑤“自己未被杀掉而活了下来,即是证明自己文章之无力的证据。”⑥ 木山看到,“五四”落潮后,胡适、陈独秀都把精神路向日趋单一化,将文艺与革命分离开来,把学术从政治中驳离出去,而鲁迅与周作人依然在艺术的深处表达着对政治的关怀和敬意。面对日中关系的复杂巨变,木山英雄发现鲁迅兄弟处理问题时的反常理性。比如他们都说“文学无用”,可是他们又积极地介入当时社会的诸多话题;他们厌恶纯然的文艺及唯美主义,但在另一层面则在杂文中将驳杂的灿烂的意象介于其中,有着诗性的骇俗之美。
在许多文章里,木山语惊四座,颠覆常识。比如他说在政治理念与审美意识间,鲁迅保持着良好的抽象概念与野性思维。这是把握了核心的论断,也解决了鲁迅认识中理性力量与审美力量并重的问题。中国的一般作家一旦嗜上理论,则损害了文艺。鲁迅却兼而得之。他的文本常常是在“是而不是,不是而是”中展开自己的主题。比如复仇,在鲁迅那里本来是一个确然的题旨,但非复仇的宽容也不能都一一加以指责,谁能说宽容没有善意,即便是对手的恶意的所为,也不能简单为之。木山英雄在鲁迅的复仇意象里找到了多重紧张的精神之力,施爱者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失去上帝信仰的绥惠略夫(鲁迅所译俄国作家阿尔志巴绥夫《工人绥惠略夫》主人翁),杀掉的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无辜的看客;热梦的寻找收获的却是虚无。在分析《孤独者》与《铸剑》时,木山写道:
以上两篇,在以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人,有意识拒绝成为卑劣俗众欲望的对象而复仇的意旨这一点上,显示了共通的曲折性。而复仇的主题在小说方面又从不同角度连续地得到了探索,产生了两篇杰作。一个是绝望的改革主义者积极的“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而以“真的失败”获得“胜利”走向自灭的《孤独者》(《彷徨·孤独者》,1927)。如果说这是内攻性的复仇之极端化的场合,那么,另一个是为向杀父的国王复仇少年的头颅为交换,承担报仇任务的“黑色的人”,砍了国王和自己的头,三个头颅在鼎中演出了一场死斗之戏,最后连谁的骨头都无法分辨的《铸剑》。⑦
日本小说类似的镜头不多,但一些诗人的意象中含有类似的因素。木山英雄惊讶的是中国的鲁迅竟用一种如此荒诞的目光打量人生,而给人的冲击力完全是形而上的感觉。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类似的表达,但是东方的文化也可以如此么?现代中国文学引人的存在,在鲁迅那里萌生出来,对于一向推崇中庸、平和的东方人来说,实在是罕见的奇观,那些高远而低回的精神之维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呢?
使木山英雄念念不忘并为之激动的是鲁迅的《野草》。他知道那是个超逻辑的世界,自己也无法以什么理论体系来说明其原貌。木山英雄在此看到了鲁迅思想里本然的存在,自己是虚无的,却又不安于虚无。活着不是为了亲人,而是为了让敌人感到不适,让其知道世界的有限,虽然自己也希望速朽。鲁迅世界纠缠的是无法理喻的存在。“五四”文人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都是闪着光彩的存在,胡适、陈独秀也是以新人的面目出现在文坛上的;而鲁迅独自在暗影里,与旧的存在是搏击与周旋的关系。他越憎恶过去,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旧的存在,必然要消失在时光中,于是自觉地去肩着黑暗的闸门,解放那些囚禁在牢笼里的人。有趣的是被放到光明处的人,却在诅咒杀戮开启闸门的殉道者。木山英雄感到了鲁迅在保守与进化间的非凡的目光。旧物未去,新物亦污。女娲以伟岸之美却造出了萎缩的人类,《颓败线的颤动》(鲁迅《野草》里的篇章)的老母以残破之躯养育了家人,未料遭到了子女的道德戕害。木山英雄意识到,鲁迅的认知哲学除了尼采式的决然外,拥有自己特有的东西。自我与他人都被罪感所缠绕,于是只能陷于苦难的大泽。解放的路应从心灵里开启,可是彼此隔膜的世界哪里是通道呢?他对鲁迅的回旋式语言的发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学者尚无深思于此者。80年代后中国学者的兴奋点,有的就是从木山那里获得启示的。
如此深地捕捉鲁迅挫折感里坚毅的东西,大概与木山的日本经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知识界意识到自己前人的失败,就在于过于自信自己的确然性,以为掌握了真理,于是自我膨胀,法西斯主义也恰恰诞生于此。鲁迅所以刺激了日本学人,就在于一个承担失败的人,也能从灰暗里表现出精神的果敢。日本缺少的或许是这样的精神界的战士。而这种带着苦涩与罪感的心进入鲁迅内心世界的人,显然与中国大陆学者色泽不同。鲁迅的另一面被遮蔽着,日本人感兴趣的地方,恰恰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的盲点。一个作家的文本在域外传播中的精神延伸,是不同语境下的有趣的转换。而中国作家能像鲁迅如此引人的,的确不多。
作为一名日本人,木山英雄慨叹鲁迅与日本作家的区别。在《正冈子规与鲁迅、周作人》一文里,他解释了周氏兄弟与日本作家的不同。鲁迅的一些作品受到日本人的影响是无疑的,像正冈子规对于死亡的描述,直接暗示了鲁迅的系列文章。鲁迅和正冈子规都写过《死后》的文章。鲁迅表现了对世俗的批判与紧张对峙的关系。可是正冈子规谈死,似乎还有着一种宗教式的解脱,文章是安详的。木山分析说:“因好奇心的作用而多次亲临自己的死后这一体验,缓解了死这一断绝,潜在地给他的生死观带来了某种通融豁达的感觉。结果,这种与死紧密相邻的生之体验,甚至给子规这位精神健全者以非宗教性的拯救,也说不定。”⑧ 但受到正冈子规影响的鲁迅,却对死表示了另一种审判倾向:“可以看到那常常是纠缠于主观和客观的相互纠葛中的。就是说,有着在试图观照生生不已的生命之矛盾,以及以死之瞬间必须消灭的主观,直接面对客观上的死之矛盾意识。其中也包含了受伤的反抗者自我毁灭式的冲动,而在这些死的种种表象之后放进《死后》这一篇,这对《野草》来说极大地丰富了其内涵。”⑨ 木山要寻找的恰恰是这个差异。在他看来,鲁迅文本无论在审判层面还是认识层面,都有可借鉴的地方,日本知识界缺乏的不也正是这些逆俗的奇异么?
有趣的是,木山对鲁迅复杂意识的解释,也有着诗哲的痕迹。这大概在日本也是少见的。他敏感于鲁迅身上的“鬼气”与“毒气”,从中分离出的果敢、顽强之气亦让其动情不已。鲁迅从庄周、韩非子那里怎样借来内力,又如何从野性之中表达批判精神,这让木山颇为兴奋。光明诞生于黑暗中,又不属于黑暗;鲁迅来自于旧营垒,可又疏离于旧营垒。这对日本左翼文人,是否是一个诱因?充分考虑鲁迅的复杂性,是竹内好以来日本学者的一个特点,包括丸山昇、伊藤虎丸、丸尾常喜等都是这样。这种由日本人的自觉的批判意识而转向对中国经验的借鉴,就把鲁迅从鲁迅之后的意识形态驳离开来,进入到日中文化的双重参照中。而中国大陆学者对鲁迅的研究那时候一直在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层面旋转,鲁迅文本的人类性价值自然被漠视了。相比较于木山英雄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鲁迅研究才形成了对话机制。日本视角下的鲁迅研究对后来中国文学的研究,无疑有着不小的对比价值。
木山英雄对周作人的解析亦多精妙之笔。那一本《北京苦住庵记》也系跨俗的文本。日本会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是难说的,可是它却系着东亚现代史中迷离的一页。周作人的文本是厚重多致的,学问也非一般人可及,但他的文章给人的多重感受也是有目共睹的。作者对周作人的学识自有评论,但其附逆却也给木山英雄带来诸多的困惑。木山是个有心的人,在周作人日记没有公布的时候,靠日本人的文献和口头记录,梳理了日本法西斯入侵北平后中国知识群落的变化。全书很深切博雅,像是个人的断代史,写出了思想界的困苦与曙色。有的地方看似资料的爬梳,其实像哲学的小品,有荡人心魄的感觉。
后来,木山英雄在《北京苦住庵记》讨论会上,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即研究周作人并不是同情他本人,而是为了和周作人一起来承担一种责任,向多数的中国人谢罪。这是许多中国学者没有料到的。他说,自己从学生时代就喜欢和崇仰中国的革命。因为热爱中国革命,却又选择了周作人作为对象。周作人的失败主义立场里有他所关注的东西,周氏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是反政治的,可是日本入侵后他陷入了反政治的政治困境。木山说,周作人承认自己的失败与挫折,所以在那时又摒弃了反政治的政治立场,用一种政治主义的态度处世。⑩ 这个理解对中国读者是很大的刺激,木山先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他的审视对象世界的视角,在我看来是难得的。
许多日本人接触中国作品,掺杂着自己的渴望。他们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的目光的。典型的例子是鲁迅的思想对日本精神空白的填补,但周作人的失败主义的抵抗,似乎更符合他们的经验。战后的日本,不正是在失败里摸索着,建立自己的新精神之塔?木山他们这一代,对政治的敏感使其带有悲剧的色泽,因为后来他们就生活在一种非政治的校园里。每个人在自己的命运中都会遇到相反的窘境,在主奴关系存在的世界里谁能摆脱政治呢?在这里,周作人展示的漩涡并不亚于鲁迅。竹内好在与鲁迅相逢的时候,也碰到了类似的漩涡。日本战败后在日美关系上遇到的主奴问题,并不亚于鲁迅、周作人那个时代面临的矛盾。我们从这里可以找到日本汉学家在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时的诱因,他们实际是借着鲁迅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绝望”的经验,对抗自己面临的苦恼与绝望。中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对美国卵翼下的日本来说,未尝没有召唤的意味。
现代东亚的悲剧是,中日两国知识界一厢情愿地讨论彼此的问题时,却遭遇了政治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木山与丸山先生的革命情结,现在的读书人就未必了解,而且还存有误会。正像欧美的左翼知识分子奇怪中国的激进读书人为何对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垂青。其实百年来我们和域外知识界一直存在这样的关照错位。只有在理解他人背景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白学术对话的基础。当年泰戈尔,与中国学者在对待东方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可以证明些什么。这也是彼此分担苦楚的一种碰撞。日本学者在鲁迅、周作人那里,发现了知识阶级面临挫折时的承担。而像周作人的苦运又恰恰与日本人有关,那么说来,木山有着双重的压力。他自己的研究,其实是流淌着内心的苦意的。他自己在日本,何尝没有遭遇黑色的风暴呢?
较之于丸山昇的浓郁的政治情怀与伊藤虎丸的史学的盘问,木山英雄更像个诗哲。近几年他在中国学界获得的呼应超过了许多日本学人。阅读木山的文本大为快意,他的哲学修养与德国现代哲学传统颇有关联,而生命感受力中诗意的成分亦让人惊叹不已。日本很少这类人文学者,其文字在诗与哲之间,有时候也不免带有晦涩的词句。他的句式是跳跃的,常规逻辑在他那里消失了。赵京华在介绍木山的特点时说:“与历史和研究对象保持一种紧张感和思想张力,不断将自己的问题和方法历史化,相对化,大概是其主要特征。”(11) 这个看法很有说服力,我在其文字间嗅出近代哲学与现代主义诗人的气息,那句评价鲁迅的话也同样适于他自己:抽象的概念与野性的感觉。这是一个矛盾,像鲁迅一样,他把这矛盾对象化了。它不仅启示着日本的汉学研究,而且在近四五年间,也给中国学人久久的冲击力。作为逆俗的研究者,木山英雄续写了东亚“被近代化”(12) 的困顿,中国文学经由他的笔,获得了超越国界的思想隐含。在某种意义上说,借他人而照到自我,某些不明晰的存在终于获得了新奇的透视。只有在“他人的自我”里,才可能相逢到真的“自我”。跨国文学研究的魅力,大约与此有关。
注释:
① 竹内好(1910-1977),日本著名汉学家,1944年出版的《鲁迅》奠定了鲁迅学在日本的基础。
② 丸山昇(1931-2007),东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鲁迅与革命文学》、《鲁迅·文学·历史》等。
③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当代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④ 伊藤虎丸(1927-2003),曾任广岛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鲁迅与终末论》、《创造社研究》等。
⑤⑥⑦⑧⑨(11)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页,第81页,第327页,第153页,第154页,第405页。
⑩ 参见2007年12月鲁迅博物馆《北京苦住庵记》研讨会会议纪要。
(12) “被近代”的概念最早在竹内好那里出现,后经伊藤虎丸的阐述得以流行。参见竹内好:《近代的超客》,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