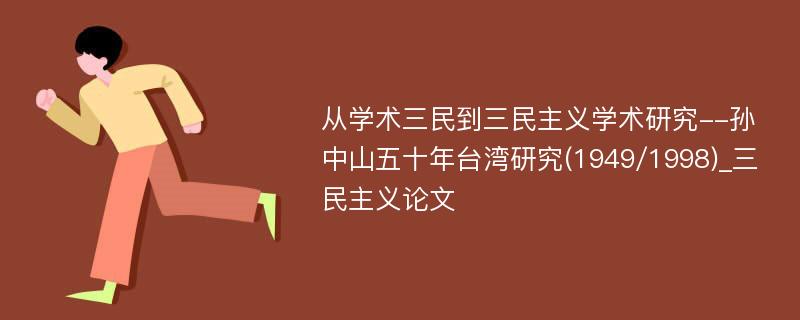
从学术三民主义化到三民主义学术化——孙中山研究在台湾50 年(1949—199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义学论文,学术论文,在台湾论文,义化到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创世人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被国民党尊称为国父,其思想亦被称为国父思想。长期以来他的思想,尤其是三民主义一直被国民党当作立党治国的根本精神。但与颂扬声相对立,近年来三民主义在台湾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特别是有些民进党人士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大陆的事情”,与台湾无关,在台湾应该废除三民主义。前民进党主席甚至说三民主义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注:郎裕宪等:《孙中山先生思想与中国前途座谈会纪录》(上),《近代中国》第110期,1995年12月25日。 )三民主义在台湾的圣经时代正在悄然逝去。
大致说来,近50年来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孙中山研究在台湾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繁荣,再到反思的过程。
发展阶段(50年代—70年代中)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迁台湾后,蒋介石就开始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并强化三民主义教育。他不仅强调要加强对国民党一般党员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而且强调用三民主义加强对学校教育的钳制。当然,这里的“三民主义”已不完全是孙中山思想的本义,实际上包含着蒋介石添加的一些内容。
首先,蒋介石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三位一体的旗号,极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要求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调整过来,从正面肯定,就能达到“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目的。表面上,他将孙中山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其潜台词则是:蒋介石是孙中山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这种强调“道统”的作法于无形中加强了他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权威和正统地位。
其次,曲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为“革命哲学”,也就是他的力行哲学。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一文中,他斥责一般党员缺少“革命实践精神”,“只知空谈幻想,不图改变”,和共产党一对阵,“力量便无形瓦解”。(注: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蒋总统革命思想》第95页。)并要求国民党党政军各级人员“切实研读”他的《行的道理》讲演词,杜绝“一旦外援断绝”,“就认为前途无望”消极情绪的蔓延,(注:蒋介石:《军校学生的求学目的及成功要道》,《蒋总统集》第2册,第1763页。)做到一旦和中共交战,“不成功, 便成仁”。
第三,“万分惭惶”地增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1925年戴季陶就有所归纳,此后胡汉民、周佛海亦涉及到此一问题。在此基础上,1939年蒋介石提出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践程序》,用“民生哲学”对抗当时颇为流行的唯物史观。50年代,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体系论得到注经般的阐扬,如罗刚的《三民主义的体系与原理》、刘修如的《三民主义教程》就是根据蒋所概括的程序内容展开的。蒋对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增补的另一个大胆举措是在1953年国民党七届中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众所周知,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作《三民主义》演讲时,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皆有六讲,而后的民生主义由于局势恶化,只讲了食、衣、住、行四讲。蒋介石认为还有“育”和“乐”两个问题有待研究,说“如不把育乐这两个问题,和衣食住行这四个问题,一并提出研究,就不能概括总理民生主义的全部精神与目的所在。”(注: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国父全集》1974年版,第1册249页。)《两篇补述》中,除了个别对大陆的攻击之外,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的。如关于人口的质与量、教育上的升学主义,以及文艺、宗教、社会环境等问题的意见,还是有很多精辟见解的。从补述中,我们也隐约发现此后“台湾奇迹”的影子。
除了加强对国民党党员和台湾民众的三民主义灌输外,蒋介石还极力加强对学校教育的控制,提出“要建立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注:蒋介石:《救国教育》,转自《台湾30年》第110页。 )“三民主义教育”的趋向,一方面是为台湾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控制,以免在利用学校教育这枚双刃剑时,一不小心斫伤自己。为了贯彻此一“三民主义教育救国方针”,1950年6月, 台湾“教育部”颁发了《戡乱建国教育实施纲要》26条,对加强三民主义教育做了详细的规定。于是,在台湾,孙中山思想遂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必修课程之一。自1956年台湾“大专联考”(高中毕业会考暨专科以上学校联合考试)开始,三民主义又成了不可缺少的考核科目。
在蒋介石对三民主义“霸道”专控中,台湾孙中山研究一直扮演着政治生活的奴婢角色。除了陶希圣、陈立夫、孙科等老牌政客忙于为一些孙中山研究著作作序外,其他学者,如崔书琴、张其昀、任卓宣、崔载阳、张铁君、罗时实、崔垂言、叶守乾、叶祖灏、罗刚、傅启学等人成为此一时期台湾孙中山研究的“佼佼者”。其中尤以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与《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两书为时所重。任卓宣(又名叶青)所著的《三民主义新解》一书,获取1966年首届中山学术奖。在大专教材方面,除了刘修如的《三民主义教程》完全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观的扩版外,其它如秦孝仪的《三民主义基本教材》、唐振楚的《三民主义要义》及《民族主义要义》更干脆变成了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选集合编。
以1966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为契机, 台湾孙中山研究形成了一股热潮。除国父纪念馆、 阳明山中山楼等硬件纪念设施相继于1961 年和1966年竣工外,一大批研究著作也纷纷“借光”推出。仅1965年台北各界就出版了12种纪念丛书,如《国父全集》、《国父年谱》、《国父墨迹》、《国父画传》等。其中《国父全集》为“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增订而成,故又称为《会本》,凡三册,2293篇;而《国父年谱》由国民党党史会编订,罗家伦任主编。此二者为以后多次增订的《国父全集》和《国父年谱》之蓝本。由张铁君主编、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二辑二十四本亦于此时推出,(注:包括陈固亭的《国父与日本友人》、任卓宣的《国父科学思想》、张铁君的《国父元学思想发微》、何名忠的《国父思想与我国乐教》、杨幼炯的《国父的政治学说》、廖枢的《国父社会安全制度研究》、梁寒操的《国父思想与人格》、林桂圃的《国父遗教与蒋总统》、李焕的《国父与青年》、崔垂言的《国父思想申论》、罗刚的《国父思想之研究》、曾虚白的《国父思想对时代的贡献》、胡秋原的《国父思想与时代思潮》、邱有珍的《国父、杜威、马克思》、涂子麟的《国父人口论》、黄少游的《国父五权宪法与现行宪法》、袁世斌的《五权宪法与中华民国宪法》、史振鼎的《国父外交政策》、周开庆的《国父的经济学说》、陈叔渠的《国父军事学说》、任卓宣的《国父科学思想》、杨希震的《国父教育思想》。)用主编者的话说,这套丛书对孙中山的“心物一元学论、民生重心的历史论、仁爱基础的社会论、济危扶倾的民族论、权能分开的政治论、五权分立的宪法论、社会价值的经济论、手脑合一的教育论、知难行易的实践论”等学说思想,“均请专家研究执笔”阐发,堪称前所未有之创举。(注:陈固亭:《国父与日本友人·序》,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由程天放、罗时实、崔载阳等人编著的《国父思想与近代学术》也是一个大部头,全书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五个方面对孙中山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和发挥。由阳明山政工干部学校编印的《思想战线丛书》中也包括一些孙中山研究方面的著作,如林桂圃的《国父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徐梅邻的《国父与组织战》、王修浩的《国父与群众战》、林大椿的《国父与心理战》、马璧的《国父思想与现代哲学思想》、任卓宣的《国父与思想战》、曾守汤的《三民主义新世纪》、薜纯德的《国父思想与现代伦理思想》、曾松友的《国父思想与现代社会思想》、田炯锦的《五权宪法与三权宪法》、吴演南的《国父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赵振宇的《国父思想与现代军事思想》、周世辅的《国父思想与中国文化》、张维松的《国父思想》、崔载阳的《国父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等。
1966年11月12日,阳明山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蒋介石发表《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大谈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再次强调“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注: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1页,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1976年出版。)此后,在孙科、王云五、张知本等1500多人联名建议下,台湾行政院规定每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先生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1967年7月, 台湾各界在中山楼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在台湾及海外开始推行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声称“三民主义以承继中华民族大道德行和传统为己任”,“使中华一贯的道统文化又一次发射出光辉灿烂的光彩”。(注: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3页,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1976年出版。)从主观上讲,蒋介石大谈三民主义和中华文化绝非仅仅为了学术研究,而是要给人一个三民主义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三民主义的印象,把自己装扮成民族文化的“保护者”,达到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为自己“正统”地位辩解的目的。因此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台湾出现了一股阐述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文章热”。陈立夫、陶希圣、梁寒操、马树礼等人,或长篇或短篇地论述“固有的优秀文化主要是一部三民主义”这句现存的结论。(注: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3页,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1976年出版。)1967年三民主义研究所“不失时机”地推出《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专题丛书》6本, 包括李霜青的《三民主义与理学修养思想》、张铁君的《三民主义与儒墨正名思想》、周开庆的《三民主义与管子经济思想》、姜汉卿的《三民主义与学庸天人思想》、柳岳生的《三民主义与春秋民族思想》、郭寿华的《三民主义与孙子军事思想》。客观地讲,这些作品著作者皆学有专长,但由于强调与“三民主义”挂钩,致使书中牵强附会之处不少。
当然,对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不能全盘否定。当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发起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对付五六十年代的“全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的理论武器主要是伴随美援而入的西方民主思潮,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而言,当然是一种反动,但它同时又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尽管主观上是为国民党“法统”请命的,但客观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提升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可惜的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强调从文化角度出发评价孙中山思想,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把孙中山思想说成是“一切学术思想的大本大经,在学术思想领域中,没有出此大经、离此大本的,社会科学如此,人文科学如此,自然科学莫不如此;不如此的,则必非世界人类所需要,亦必非宇宙自然的真理。”显然有些言过其实。其次,对中国传统文化亦有些自视过高,把中国文化说成是人类的指导文化,认为欧美人有“原子时代就是人类自己毁灭的时代”的恐惧,就是缺少了中国的文化精神。还说“自然科学是要发掘宇宙奥秘的,中国文化就能把握宇宙自然的最高奥秘,只不过中国人不屑如西洋人的钻牛角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肯如孩提之于水沟里玩小水车,在马路上玩纸风筝罢了。”(注:程天放等编《国父思想与近代学术·跋》,1975年再版。)颇有点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味道。
繁荣阶段(70年代中期—80年代)
1975年蒋介石病逝,严家淦继任挂名总统。1978年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就职当日下午,蒋经国即发表“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万岁”的指示。(注:香港《星岛日报》1978年5月30 日,转自《台湾30年》第297页。)在国民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蒋经国再次指出,“在领袖、党魂感召下,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凭藉,就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人性的指标,二十世纪人类的共同归向。”(注:蒋经国:《蒋主席十一大政治报告》,张铁君:《国父思想》,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1979年再版,第496—497页。)
蒋经国对三民主义“不改初衷”,主要体现在也要“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地“实现三民主义于全国”,(注:蒋经国:《蒋主席十一大政治报告》,张铁君:《国父思想》,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1979年再版,第496—497页。)即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蒋经国的策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故其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也是很卖力的,并且把对三民主义的无限信仰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无限“谴责”上。蒋经国的这种“嗜好”得到了台湾学术界一些人的极力迎合。1979年出版的刘珍《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研究》、胡一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际的比较》、任卓宣《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三部著作便是证明。1966年开始蒋介石曾把台湾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带上一个高潮,但彼时的比较多限于部分文章或部分章节,像这样的以三部巨著出现的比较还是首次。这三部书皆是在1979年及时出版,个中因由除了“前人(蒋介石)栽树,后人(蒋经国)乘凉”效应外,恐怕更多是受了蒋经国的“十一全会”报告精神的“感召”。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部书中,以任卓宣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影响最大。任卓宣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30年代后改信三民主义,并以研究三民主义为终身事业,著述甚丰,是三民主义的“理论家”。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序言中他就说:“共产主义无论在哲学基础、科学基础、主义本身及斗争策略方面,处处均不及三民主义,而处于劣势。这说明它比较不过三民主义,换言之,它在思想战中破绽百出,甘拜下风。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在反共战争中将‘弃甲曳兵而走’的信号,那么三民主义的胜利便可预卜了。”(注:任卓宣:《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序言》,台北,帕米尔书店1979年版。)这个结论是先于“比较”早已现存的,尽管打着“比较研究”的学术幌子,但显然是不合学术规范的。因此,与其说此书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政治宣言书。
尽管蒋经国依旧钟情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在“中华民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态度比蒋介石要强得多。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个人权威不及蒋介石,另一方面是他更加明了民主化是时代之潮流,而不得不做出“维新”的姿态。蒋经国这种既新又旧、不新不旧的政治态度,对台湾三民主义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台湾“三民主义学术化”与“学术三民主义化”的争论正是在此时出现的。“三民主义学术化”要求“以比较的方法,窥探出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学术三民主义化”则要求“政治学者研究三民主义政治学,经济学者研究三民主义经济学,社会学者研究三民主义社会学,”(注:邬昆如:《三民主义哲学》第3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 )即学术研究以三民主义为根本指导。这种新旧思维的大碰撞,为台湾三民主义研究提供了湿润的气候,是此一时期台湾孙中山研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
此一时期台湾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著述浩繁,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丛书特别多。据我们了解,至少有六种丛书——《三民主义学术理论丛书》、《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硕士论文奖助出版丛书》、《青年理论丛书》、《民族精神教育丛书》、《励进丛书》、《中华文化丛书》。其中以《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硕士论文奖助出版丛书》影响最大。由于手头掌握的材料有限,我们不能对这六套丛书作进一步的考察,只是粗略地形成了两点印象:其一,这些丛书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如《青年理论丛书》从70年代开始,每年一辑,每辑10本,1979年为第九辑,1980年为第十辑(以后是否继续“辑”下去,不得知)。《三研所奖助丛书》从80年代开始,每年一辑,每辑10多本,一直“辑”到90年代。其二,有些丛书的内容已经突破三民主义文本,把三民主义同现实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但又不同于以往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的叫嚣,而是遍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也是百花齐放,甚至出现用数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孙中山思想。总的来说,此一时期台湾的年轻一代学者已经突破上一代学者对孙中山思想的狭隘理解,视野更加开阔,立论亦较持平。三民主义研究在台湾不仅开始“学术化”,而且开始“社会化”了。
另外,此一时期台湾关于孙中山研究还有三项成果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孙逸仙先生传》、《国父年谱》和《国父全集》。
《孙逸仙先生传》是台湾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吴相湘先生的一部力作。在此之前,台湾有关孙中山的传记不少。据“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李云汉先生介绍,在台湾关于孙中山传记之撰述和翻译,为数在30种以上,其中以罗香林、黄季陆、郑彦芬、傅启学和吴相湘等人的贡献为多。(注:李云汉:《台海两岸研究孙中山思想与中国国民党党史的现状与展望》,《近代中国》第106期,1995年4月。 )但这些作品皆不及吴相湘的《孙逸仙先生传》的内容翔实。早在1953年和1965年,吴相湘即有《孙中山》、《孙逸仙先生——中华民国国父》两书问世,1982年出版的《孙逸仙先生传》可以说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搜集。《孙逸仙先生传》厚达100多万字,资料详实, 常为后学者所称道和引征。该书之特点可用梁家錞在书后《跋》中的一段话来表述:“此书名为国父立传,实为近AI写作史,凡读是书者,不但对于国父思想悉得津梁,即有清末造土崩瓦解局势之所由来,北洋军阀隆替之所自起,乃至国际方面英日同盟、华盛顿九国公约、西太平洋互不设防协定,以迄于苏俄第三国际之如何操纵国共,皆可由此机倪,寻出端绪。”(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跋》,香港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全书立论颇具个人意气,甚至有不少“开罪”国民党和台湾当局的地方。
《国父年谱》为国民党党史会历经四次增订而成,“为目前海内外最精细最完整之孙中山年谱”,(注:李云汉:《台海两岸研究孙中山思想与中国国民党党史的现状与展望》,《近代中国》第106期, 1995年4月。)可与大陆陈锡祺先生主编之《孙中山年谱长编》相媲美, 二者可相互补充印证使用。
《国父全集》亦是由国民党党史会多次编订而成的。1950年至1952年间台湾陆续出版的《总理全书》十二册,1957年在《总理全书》的基础上,正式改名为《国父全集》并出版。1965年孙中山百年诞辰纪念,复由秦孝仪主持增补改编成十六开本《国父全集》三巨册。1973年党史会根据此前出版之全书、全集,又搜罗早年出版的《中山全书》、《总理全集》等,尽发库藏重新编次, 勒成十六开本《国父全集》六册。 1981年复详加校正再版,并将其中第四册析为上下册,全集遂为七册。1984年党史会为纪念孙中山建党革命90周年,将继续征集之著述与文件,辑为《国父全集补编》一册,这样全集合成八册。1989年国民党建党95周年,《国父全集》再版,收录逾八百多万字,十六开本共十二册,实为目前海内外最完备的孙中山全集之版本。
此一时期,台湾孙中山研究开始注重对外交流。1985年11月在“国立”中山大学召开了“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美、英、法、日等国家或地区学者50人,台湾专家学者90人,为台湾当时所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此次大会有三项使命: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同盟会创世80 周年以及对日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40周年。大会共宣读论文59篇,“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论文15篇。此次研讨会的一个特点是政治性与学术性兼容。前“总统”严家淦和副“总统”李登辉亲自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他们在讲词中都认为“孙中山先生革命建国的方针和理想,确实是控中国发展的方向”,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反思阶段(90年代)
1988年李登辉登上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台湾民主化进程加快。与此同时,两岸关系也开始有所缓和。尤其是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严,以及1991年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得以加强。在此条件下,台湾三民主义的“官定意识形态”权威开始松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孙中山形象日趋淡漠。台湾学者普遍面临着“国父思想”、“三民主义”废教和废考的困惑。
这种困惑表征之一是,继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改名为“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相继有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改名为“中山学术研究所”,政治大学三研所改名为“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湾大学三研所的改名之议也一直在进行之中,有可能改名为“亚太研究所”,其名称与职能均与孙中山研究无直接关系。目前坚持使用三民主义研究所原名的,只有台湾师范大学一家。表征之二是,大学的三民主义课目改为讲授“中华民国宪法及立国精神”,内容或讲授孙中山思想,或联系孙中山思想讲解三民主义,或讲授与三民主义完全无关的宪法内容,皆不受限制。高普考已经废考“国父遗教”及三民主义,至于大学联招是否废考三民主义亦在议论之中。种种迹象表明,过去三民主义那种作为圣经不可动摇的地位现在已经开始动摇得厉害了。
面对困惑,台湾社会各界,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界的反应不一。大致说来,包括左、中、右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三民主义固然带有“救国主义”的实用色彩,但它的终极目标不仅定位于“以建民国”,更在“以进大同”,它超越中国一时一地的问题,具有前瞻性与全面性,因而能够历久弥新,放居四海而皆准。(注:宋楚瑜:《国父思想感情于历史新局中的时代意义》,《近代中国》第91期,1992年12月1日。 )他们承认三民主义在台湾民众中间的影响力的确是日益式微,但原因不在三民主义本身,而在于宣传上的不力。因此要做的事只能是“改善三民主义课程教学之道”,具体包括:编排选择适当的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充实图书设备以及视听教学;经常主办研习、参观及实习等。(注:庄政:《改善三民主义课程教学之道》,《中央日报》1996年10月26日。)
第二种观点认为,三民主义还有教学研究的价值,回归学术是三民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必须尽量摒除政治因素的考虑,从学术的立场出发对三民主义作客观的检查。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所长周继祥教授即认为:台湾“大学国父思想改为‘中华民国宪法与立国精神’,高普考废考国父遗教及三民主义,大学联招废考三民主义及高中取消三民主义课程等一连串事件,说明三民主义解除多年政治力的桎梏,回归正常的学术研究是必然的趋势。”此派观点认为政治与学术各有其领域,学术的价值要在学术的领域中去决定,而不是在政治领域中去决定,在此信念之下,日后台湾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新党执政,三民主义仍可自恃其原始之学术本质,在教学及研究上,继续开创发展的空间。
第三种观点认为,因应中国现代化特殊需要而产生的以孙中山思想为文本,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统观点作为诠释基础的三民主义,已经难以解决21世纪后现代社会的问题,应予以废除。持此种观点者大多数为台独分子,他们或直接叫嚷取消三民主义,或藉学术化为名,对三民主义实施攻击。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馆读第十四期(1997 年9月30日出版)发表的台湾大学三研所博士生曾建元《以台湾为思想本位的三民主义》一文即表露出浓厚的台独色彩。该文认为“正统三民主义”纵然有救世主义的淑世性格,但“孙中山思想及其革命事业,则当视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历史经验,而不应当要将之视为金科玉律”,因此“必须重新定位”。定位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台独——民族主义立场“不是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民族中的立场,而是以中华民国所处的台湾省为中心的文化多元主义台湾民族国家立场”。在民生主义方面,则应“避免被吸卷入大中华经济分工体系而形成另一类型的依赖经济。”(注:曾建元:《以台湾为思想本位的三民主义论纲》,《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第14期,1997年9月30日版。 )此种论调实际上是为李登辉“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作喇叭。
从以上归纳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尽管台湾“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但是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孙中山思想学说过去那种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台湾民主化日益加强,民众对三民主义强化教育所造成的刻板现象,一旦遭受到民主自由气候的浸润,就会转变于另一极端,极易形成对三民主义的反感。而且作为引导台湾民主化的三民主义在民主化之后,成为民主市场上众多的竞争性意识形态之一,愈有被分化、掏空之趋势,其“鸟尽弓藏”的难堪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台独分子的有意为之,他们攻击三民主义,就是变相攻击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将台独与否定三民主义勾连起来。
与三民主义的“官定意识形态”日渐式微相比较,进入90年代之后,孙中山思想与事功的学术研究在台湾仍呈旺盛执着势头。
首先是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主要有:张绪心的《天下为公——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思想》、林初曜的《孙中山先生容共经纬之研究》、周阳山、周世辅的《中山思想新诠——总论与民族方义》及《中山思想新诠——民权主义与中华民国宪法》、朱谌的《中华民国宪法与孙中山思想》、彭坚波的《孙中山政治发展模式与经验之研究——兼论台湾政治民主化之困境与策略》、蒋一安的《孙学阐微》、陈建荣的《国父思想:孙中山思想释论与台湾宪政经验》、邵铭煌的《孙中山先生与蒋中正先生》、李云汉的《中国国民党史述》、孙穗芳的《我的祖父孙中山》、庄政的《孙中山的大学生涯》、郭恒钰的《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张益弘的《问学解蔽》。与繁荣时期相比,此一时期孙学著作在数量上并无辉煌可言,但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良莠不齐的孙学狂热正在逝去,孙中山研究的学术时代开始来临,孙学研究在台湾正悄然从变态走向常态。
其次,值一些大学三研所纷纷改名,以及国民党有关孙中山研究单位日益不景气之际,一些民间学术团体如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和逸仙文教基金会等对孙中山的研究却日趋活跃。
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系1965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年而创设,王云五为首任董事长,现任董事长为刘真。其对孙中山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资助奖励优良学术著作的出版。前面提到的任卓宣的《三民主义新解》和傅启学的《孙中山先生传》均系该基金会奖助出版之著作。近年来,该会工作更趋积极,如不定期举办中山思想研讨会,出版孙中山研究专著,推动出版“中山文库”的计划。从1992年1月起, 该会与台北《中央日报》合作,开辟“中山学术论坛”双周专栏,发表了大量研究孙中山的文章。1995年10月,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还编印了《中山先生研究书目》,收录1912年至1995年间中外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研究书籍3731种,学者称便,可与大陆1990年出版的《孙中山研究总目》相互印证。
逸仙文教基金会成立较晚,其财力支持者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现任董事长为马树礼。对于孙中山研究,该会的主要工作是促进海峡两岸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1995年1 月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中山思想学术研讨会”就是由该会主办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民间学术团体都如同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和逸仙文教基金会般的红火,成立有年的国父遗教研究会,就因人才凋零,财源匮乏,已近于难以为继的局面。至于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的单位,如党史会和文化工作会,更是因为人力财力问题,面临“死火”的危险。
第三,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仍持续发展。举其大要者,90年代以来台湾有关孙中山的研讨活动有以下几种(见表):
研讨会名称时间 地点
主办单位
备注
党史会、国
史馆、台北论文结集
近代史所、出版,为
中华民国建 1991年8 “教育部”、
《中华民国
国八十周年 月11—台北市圆国立故宫
建国八十
学术讨论会
15日 山大饭店博物院、中 周年学术
国历史学
讨论集》,
会(台北)
四册
党史会、国
史馆、台北《国父建党
国父建党革 1994年
台北市国 近代史所、革命一百
命一百周年 11月19立中央图国立故宫 周年学术
学术讨论会 —23日书馆博物院、台讨论集》出
北中国历 版,共四册
史学会
从1994年
台北市国
中山思想学 起,每年立国父纪
国立国父
术研讨会 一次 念馆
纪念馆
全部论文
私立东吴 及记录由
海峡两岸中 1995年1台北市国
大学、逸仙逸仙文教
山先生思想 月9— 立中央图
文教基金 基金会专
学术研讨会 10日
书馆
会辑出版
座谈会记
孙中山先生 录分发于
思想与中国 1995年 台北市福《近代中 《近代中
前途座谈会 11月12日
华大酒店国》杂志社国》第
110—111
期
孙中山先生 台北市国中山学术
思想与台湾 1995年 立中央图文化基金
经验研讨会 11月12日 书馆 会
华侨与孙中 台湾华侨
山先生领导 1996年8协会总会、论文已经
的国民革命 月24—25
中研院近 结集出版
学术研讨会日
代史所
孙中山与中 1998年1国立国父
国现代化学 月3— 国立国父纪念馆、逸
术研讨会 6日纪念馆 仙文教基
金会
上表所列的八次会议中,以“海峡两岸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最具影响。17位大陆学者在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的带领下,应邀出席,实为两岸学术界共同参与的一次空前盛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尽管两岸学者因缺乏交流准备,造成认知上的差距,但是大家都能秉持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讨论,求同存异,为以后的类似研讨会树下了良好的典范。
此一时期台湾“孙学”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积极开展对外交流。除上述“海峡两岸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外,逸仙文教基金会还于1995年初举办了“中山先生思想与中国之未来研讨会”,大陆孙学研究专家张磊、黄彦等人应邀与会。另外还有台湾师范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多次赴大陆举办“孙中山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促进两岸孙学研究之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至于台湾大学三研所则更是自1991年起,每年定期举办“国父史迹学术观摩团”,赴澳门、广州、上海、北京、南京等地访问考察,既促进了两岸孙学交流,又加强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了解。台湾学术界已普遍比较理性地认识到,过去两岸间的“敌对意识”浓厚,且各自以自居“正统”作为评价历史的“合理化”依据,对孙中山的研究,不免偏向于“稳定政权”与“各自表述”的结果,即均以孙中山为合法政权的“图腾”象征,对孙中山学术价值的斩伤甚大。他们表示要抛弃过去那种对孙中山的肤浅、片面的理解,从更深层次更全面地把握孙中山思想和精神的合理内核,为两岸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寻求一个共同的话题。
进入90年代以来,孙学研究的学术气息日渐浓厚,这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良好的信息。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对于孙中山这样首先以政治家面目出现的人物来说,对于台湾这样目前尚以三民主义为官定意识形态的地区来说,孙中山研究要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子是不太现实的。举例来说,近段时间台湾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研究成果特别多,究其原因不仅是台湾民主化为一帮孙学研究者提供了所谓的“灵感”,而且其中也包含着“托孙改制”的意蕴——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寻求民主化的理由和发展轨迹。据李云汉在《台湾地区孙中山研究之进展》一文中所附录的159篇论文中,就有24篇是有关民权主义研究的,约占1/7。(注:参见李云汉:《台湾地区孙中山研究之进展》, 《近代中国》第114期,1996年8月。)这种“托孙改制”的作法,其用意不在要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寻求到多少可以直接运用的东西,而是在于把握其中的精神。台湾学者对孙中山思想和事功的学术研究,台湾民众对孙中山形象的消化容纳,更多的是从光大其精神的角度出发的,这一点同大陆学者的用心是一样的。的确,孙中山作为一位海峡两岸共同尊崇的历史伟人,其精神具有超越时空而不朽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