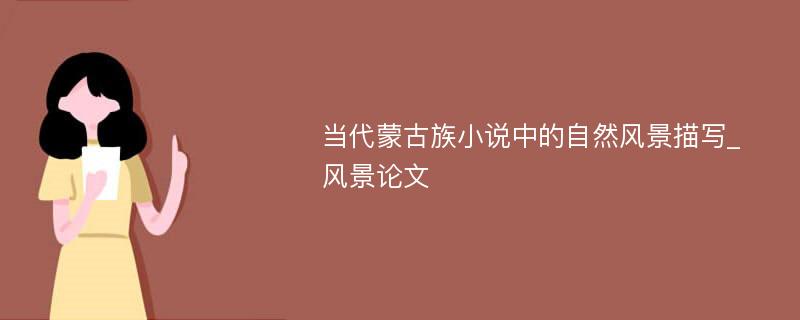
当代蒙古族小说中的自然风景描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当代论文,自然风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0-5218(1999)-02-0025-0033
“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既然是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文化的民族差异不仅是人类以民族单位生活的自然结果,而且是这种生活的前提和条件。”(注: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121页。)而造成民族差异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地理环境、地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从文化发生学意义看,地理环境是文化创造的基础。这样,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地理条件中,就不仅产生了蒙古民族粗犷遒劲的草原风格,而且,对这种自然景观本身的描写,也成为了蒙古族文学特征和风格的一部分。文化既是人创造出来的,又反作用于人自身。同样,蒙古民族创造了草原风格的文学的同时,也发展和培养了蒙古民族的审美趣味,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对草原风光等自然景观及那达慕、蒙古包等人文景观的描写,占有特殊的地位。
自然景观、自然风光的描写,对蒙古族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被看作是民族特点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被认为是蒙古族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荣·苏赫、赵永铣等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注:荣·苏赫等著《蒙古族文学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9-10页。)中总结了蒙古族传统文学的特征,其表现首先就在“……这些作品中所描绘的充满蒙古高原游牧文化草香奶味的社会生活、人物形象,不但是独具特色的,……在和形成蒙古族文学民族特征核心环节的民族审美心理的辩证关系中,都归根结底处于第一性的决定性的地位。”(注:荣·苏赫等著《蒙古族文学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9-10页。)对以1947年为开端的当代蒙古族文学中的“自然”描写,批评界也持相同意见。汪浙成在分析敖德斯尔的《阿利玛斯之歌》时,将其民族特色归纳为“……草原上一幅幅独特的风俗画和风景画:那五彩缤纷的那达慕大会,摄人心魄的摔跤比赛,一年一度考验青春和力量的骟马时节,以及迷人的草原夜月和横空出世的汗山剪影……”。(注:载《敖德斯尔研究专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茅盾显然也很重视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他在《读<遥远的戈壁>》一文中,几次谈到敖德斯尔小说对自然风景“写得很精彩。……多么开朗、寥廓、明媚。”(注:载《敖德斯尔研究专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并引用了不少这样的段落。扎拉嗄胡在回顾建国以来蒙古文学发展历程时,把“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比喻为“重武器”(注:《勇敢的大草原——回顾内蒙古17年文学历程》,载《民族文艺报》1995年5.6合期。),而所谓“地域特点”更多的也是指自然风光。
蒙古民族被称为“自然之子”,“马背上的民族”。在自然与蒙古民族之间有一种几乎宗教宗信仰般的情感。从我们的祖先至今,蒙古人都是在与大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斗争中创造自己的文明史的。因此,在蒙古族文学中,对自然的描写,对草原、马群、羊儿的描写,就始终是作者所倾其心力的,也是始终为读者阅读期待中所盼望的,同时也始终是被文学批评当作民族特色来归纳和强调的。但是,仔细分析和研究建国50年来蒙古族小说中的风景自然描写,就会发现在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风景自然描写在作品中的作用、地位、意义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和变化在实质上反映了文学观念的不同和变化,反映了不同阶段中的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认识。从这种不同和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蒙古族文学的进步、发展,看到它是如何逐渐脱离民间文学那种稚拙的朴野状态:景物——故事——景物的模式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变化的过程描述为:民族特点的标识——人情的分享者——一般意义的风景描写——情感表达的一种间接方式——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作为民族的象征。
一、自然风景作为民族特点的标识
在传统文学中,对自然的描写不是有意识去为之的。生活本身有地方性、民族性,写这个生活就自然地会有对风景的描写。只是在后人那里,它才被当作民族特点、民族文学的传统而归纳和认识的。真正有意识的以描写自然为民族特点的标志,起始于50年代的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人。在他们的小说里,草原风光是被有明确意识的大量、完整的描写,并逐渐成为一种规范、一种新的传统,贯穿和制约着从解放至1984年的前草原小说。老一代的前草原小说作家几乎都承认和强调自己受民间文学影响至深。扎拉嗄胡说自己“最早的文学兴趣”得自“民族民间文学”,他“童年和幼年时期在家乡渡过,经常通宵达旦地听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演唱《蒙古秘史》、《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和蒙古族民间故事”。(注:《扎拉嘎胡研究专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敖德斯尔也说“我生长在昭乌达的巴林旗,从十来岁就对家乡的民歌产生兴趣,……尤其说书人讲的故事,常使我废寝忘食,吸引人彻夜不眠地倾听。”(注:载《敖德斯尔研究专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这样,民间文学中大量对自然的描写,就成为他们日后创作所自然具备的养分。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描写可以被模仿、被效法,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描写自然就顺理成章地被作为最主要的一个传统继承下来,并作为民族特点的标志之一。
把“自然风光”视作民族特点,还由于这时期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实际并无多少民族差异。80年代中期曾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意见,比如尹虎彬认为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写的是当时写得滥熟的阶级斗争题材;这类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受到好的评价,是因为它适合了政治模式的小说热。它们大都是他民族(汉民族)生活在本民族生活的投影;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关注、所提炼的恰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他们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注:尹虎彬《从单重文化到双重文化的负载者》,载《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他总结说,50年代出现的这批作家,“他们的创作浓厚地带上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风尘,没有摆脱社会政治模式。”(注:尹虎彬《从单重文化到双重文化的负载者》,载《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尹虎彬的意见有些过激。对于前草原小说作家来说,他们并非是验证自己民族生活领域中的汉族生活,而是因为当时他们也在确实地经历着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同样的生活:解放、土改、肃反等等。“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风尘”哪一个民族没有经历呢?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前草原小说的题材,由于反映了蒙古民族在其发展中的某一时期的真实状况,所以题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如果抛开这点偏颇,尹文另外的观点,还是很正确的:前草原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和人物形象并没有多少民族性。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空间包括民族空间是很小的,社会话语中的“差异”的声音不多,各民族生活内容的确是很相似的。因此,前草原小说描写的也只能是一种“普遍性”。对一个民族来说,“普遍性”是事实,是民族交往、特别是50年代至80年代前期社会的事实,是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的“趋同”;而“特殊性”则提供对民族的“他性”的表述,是对具体民族的认同。当然,纯粹的、绝对的“蒙古特质”只是一个幻觉、一个文化神话,尤其在一个多民族杂居、并且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在有各种共存的文化中,表现“他性”的文化,不管它是否正在悄然消失或正在与其它文化融合,在一定时间内它总是存在的,而且也一定会和其它文化交错共生为一种新的“他性”的文化。但五六十年代的甚至70年代的作家当时所具备和所可能具备的认识能力及程度,还不可能认识到这点,还不能从精神及心理方面的“差异”的角度去表现民族的“他性”。
还要提到的是,50年代前草原小说作家大部分是革命干部。这种政治身份不可能让他们从“普遍”的价值及原则中游离出去,去表现民族和“他者”的形象,更不可能使他们的书写成为一种个人行为。这样,民族特点的流失和淡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也许不能说这些作家是由于认识到了这点而有意识地从自然景观上去进行弥补,但他们的作品却的确因为刻意追求和描绘的草原风光而大大增加了异族的风采。这个时期,对自然的描写成为一种标识,它与小说的叙述无关,只是作为作品民族特点的标志,具有直观的效果。而对作者个人说,则成为他个人化风格之一,如玛拉沁夫、敖德斯尔等都很擅长描写风景。
二、自然景物作为人情的分享者
除了作为民族特点的标识外,在前草原小说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便是用来渲染气氛、烘托情绪、引导人物出场,它是人的情感的分享者。
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开头就是一段风景描写:夕阳被遥远的大地吞没了,西北风偷偷地卷起了草浪,草原变成了奔腾的海洋;空中密布乌云好像一张青牛皮盖在头顶。人们都知道:草原的秋雨将要来临了。”这段描写好比楔子,类似戏剧中的舞台说明,在整部小说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后面的所有情节都将发生在这样一个风雨天里。恶劣的自然天气是为了加强后来情节发展的严峻,以及烘托人物在那场反革命纵火案中的坚强。但这个“自然”并不是真的“自然”,换句话说,这个“自然”不是与事件和作者感情相对的另一个自觉存在,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它在叙事中被刻意设计的刺目穿插的痕迹:每一个“自然”条件的设置都是为了情节,是情节发展需要的道具,甚至是情节发展的补充。这里,“风”是为了助火势,以突出阶级斗争的严峻;“雨”则是为了灭火。草原上起大火是不容量扑灭的,单单人的英雄精神并不足以与之相抗衡。但是,那个时期表现灾难和英雄的毁灭又是不可以的,因此,“雨”就是必然的。最后,阶级敌人抓起来了,小说也结束了。与开头的风景描写相呼应,结尾也是风景描写:“弥天的乌云一团一团向南飞去,草原的东边显出了黎明的光;遍地的花朵微笑着抬起头来,鸿雁在高空歌唱。太阳出来了。”这段明丽的景物描写,说明着一场对敌斗争的胜利,它是胜利后的人们心情的表现。
类似的例子在前草原小说中是很普遍的。正如上述分析的“风景”在小说中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自觉存在,而是为了渲染和烘托气氛,借景抒情或借景咏志的,是作为背景或人的生活环境进入作品,是被借用的。也正因此,所以在这种描写中,不管作者多么爱它,多么精心地描写它,自然风景都是因为人的观照而被动地存在的。
当然不能否定自然风景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精神及情感的影响,以及它所具有的民族、地域的独特性,也不能否认描写它就丝毫没有民族情感的因素在内。但这种描写毕竟是直观的观照自然,是将其作为人物和事件发生的客观环境或者背景被借用的,只有当人的情感、人的精神投射到它上面时,它才有生命和光辉。“观山则意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自然风景本身是一个无知无觉、无知无识的地理学意义的实在物,只是因为有了人的情感,它才具有生命和意义。所以,自然风景是作为人情的分享者。前面所举《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就说明只有人有了某种强烈的感情,自然风景也才会有同样的感情。自然风景是一抹烘托和反衬人的某种心境的色料。
三、自然风景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间接方式
80年代中后期,蒙古族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又更多地作为了一种情感表达的间接方式。作者的情感不是直接灌输进风景之中,而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和心态去描绘它,通过联想,这些景物就制造、烘托或暗示出某种人的感情。乌亚泰的《洁白的羽毛》里对白天鹅(自然)的描写,就属于此类。从想打死天鹅,到救助天鹅,以及看到从天坠落的一根白羽毛,都暗示出霍尔查对被歹徒杀害的妻子的怀恋及痛苦的心情。这篇小说里真正提到霍尔查夫妻之间关系的笔墨并不多,但他们的情感却在对自然——两只天鹅互不遗弃、难分难舍的描写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相同的例子还可以举哈斯乌拉的《两匹马的草原》。小说里有一段很长的对官布苏荣杀死怀孕的母驼的描写。母驼的哀嚎,暗示着官布苏荣妻子难产的挣扎和痛苦,而疯狂的母驼向远处蹒跚的驼羔不顾一切冲过去时,又让人想到官布苏荣对自己唯一子嗣夭折的无奈和悲愤;他亲手杀死母驼,更强调了官布苏荣对自己的忏悔及希望破灭的绝望。
这种对风景的描写,常常是插在人物情感急剧变化或大幅度波动的时候。《两匹马的草原》里在写官布苏荣赶车送妻子去卫生院时,插入了一段对月光下的土包、草滩的描写,土包上的草棚子引起了官布苏荣对当年追求另一个女人达丽玛的追忆,达丽玛与他对妻子的忏悔相连;而眼前妻子怀孕的不易,又强调了他的改邪归正和赎清罪恶;这一切又反衬出官布苏荣此时此刻在这个月夜里对生命的脆弱所感到的无奈与悲凉。查森敖拉的《山谷幽情》里,挤压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四面大山,低矮的小土屋,蚯蚓似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和粗砺的生活,伴着这些自然环境描写的是二嫂容颜的消失,美丽和青春在岁月的风雨前所形成的冷酷对照,以及在“我”的心理上产生的强大的落差,都暗示了“我”在艰难的生存环境对人的无穷无尽的种种消蚀前所感到的那一份悲凉与落寞。残酷的自然不仅消殒了二嫂的美丽,阻隔了丫头上学进城的希望,也最终成了我的情感的“屏蔽”。
当自然风景被作为一种感情表达的方式时,在许多情况下,它也就成了情感的激发物。阿云嗄的《浴羊路上》写到:“一条小溪在柴达木腹地欢快地流淌,野鸭在水中嬉戏,水边的草像铺了地毯一样平整而光滑。湿润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再看柴达木四周连绵起伏,无边无际的硬砂戈壁,你真想一辈子呆在这个地方。五家的羊群放在一起,像无数颗珍珠一样在绿草滩上滚动着。”美丽的自然成了3个刚刚蒙蒙懂懂初谙人事的小男孩情感的触媒,在这片自然中,女孩子和男孩子之间戒备、厌弃甚至仇恨的壁垒打破了,幼稚的童心融化、陶冶、纯净了,对真善美的维护和想往,在“大自然的雄伟和辽阔”中,成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
四、人与自然之间类比式或影射式的对应关系
这种对于自然的描写,是将自然物(往往选用羊、马、狼等动物)作为人的某种品性或某种人生理想的对应物来进行的。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是典型的例子。与此非常相似的还有满都麦的《碧野深处》。小说写一个跌断小腿的青年纳吉德为了一只黄羊与两只饿狼搏斗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羊代表善,狼代表恶。纳吉德发现了一只伤了后胯的黄羊,他想抓住它,因为“相互残杀,弱肉强食,这本来是动物界得以生存的前提和条件嘛。”就在他马上就要得手的一刻,来了两只饿狼,“……面对一强一弱两个对手,他那保全男子汉名声的欲望不允许他避强凌弱。那样,他良心将永世不得安宁。”在狼——恶的面前,纳吉德的良心——善苏醒了,他开始直面自己的残忍和人性的堕落。在这篇小说里,狼成为人类社会或人性中“恶”的因素或品性的对应物,人与狼之间的博斗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只是消灭吃羊的“狼”这个生物,而在于激发起人的良知,使人精神和生命重新获得力量,使人在现实中久已被泯灭和忘记的“善良”本性得到恢复。
郭雪波的《沙狐》,也同样是写善的力量永远不会被恶的力量所征服。小说中的这只沙狐是作为“恶”的对应物、“善”的象征出现。沙狐因为一年能吃掉3000只破坏草场的野鼠,成为了看林人老沙头在漫长的孤寂生活中的慰藉。可这只沙狐却被林场主任和他的秘书打死了。当人举起枪向沙狐——善瞄准时,人就把自己坚决地推到了“恶”的一方,在枪声里响起的是贪婪、实用、残忍等等人性中恶的因素,沙狐死了,这意味着“善”也死了。小说写道:“它的胸脯中了弹,鲜红的血像水一样淌出来,染红了它雪白美丽的皮毛,滴进下边那片松软的沙土里,……它的一双眼睛还没有来得及合上,还留有一丝微弱的生命的余光,呆直地望着沙漠的蓝天。”戏剧性的是,打猎的人忽然猛醒了,一生认为猎杀是天经地义,今天却怀疑起这个行为的正义了。人的良心和道德的复归,终于在“善”的毁灭中完成,沙狐以自己的死证明了“善”的力量的伟大和永恒。
此外,这篇小说还谴责了人对自然的蹂躏和践踏,试图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她孕育了人类,使人类生息繁衍。可人却出于种种功利的近期效应和目的,破坏草场种庄稼,于是自然开始报复人类。小说描绘了一副可怕的图景:“而风势仍不减弱,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吞没着一切。沙柳叶子蔫了,低垂下来,好像一条条灰色的碎布。在沙洼地上,每丛沙蓬下部集拢了一堆面粉一样的褐色细沙尘。那些艰难地生长在死漠洼地里的稀疏植物的叶子,都变色了,枯焦了。把叶子摘下来,可以用手指搓成粉末。风,转眼间这些枯叶卷走了,光剩下光秃秃的枝。哦,大漠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世界?”目前世界沙漠面积正在不断扩大,每年有大约7000万倾农田被吞没,世界性的沙漠现象日益严重,人类陷入生态危机甚至饥饿之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已经向人类亮起了黄牌。小说在对无视自然规律的愚昧、惰性和习惯于苟安的精神状态表示愤怒的同时,一方面写了沙漠——自然的狞厉、疯狂的暴虐;另一方面又写了沙漠——自然的宽厚、忍辱负重的博大深邃。
同沙狐一样,沙漠在小说中也是某种理想的对应物。在对人的道德观念丧失、人际关系虚伪感到失望后,广袤的沙漠和3只小沙狐代表了作者所持的一种对人类关系美好幻想的暗喻。面对着与人类社会纷攘、嘈杂、是是非非的庸常现实,沙柳的心疲惫不堪:“我真想家,我才发现哪儿也没有咱们家好,没有咱们的沙坨子好,我一辈子哪儿也不去了……”。在这里,自然(沙坨子和小狐崽)代表庸常现实的另一端——宁静、单纯、清朗,是作者心目中的净土,没有功利和实惠,没有尔虞我诈,表现出某种深切、执著的渴望避开污浊世风、无所他求的既无奈又不平的心境。
这种对于自然的描写,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类比的或对应的关系来看的。自然或者是人类社会中某一类人的某种品性(如《蓝幽幽的峪谷》以及《碧野深处》中的“狼”象征着“恶”),或者寓示了人生的某种理想(如《沙狐》中的“沙狐”和“沙漠”代表着纯洁、坦诚等道德观念)。在这些小说里,借自然讽喻生活,影射生活,进行是非评价的道德及社会教育,是一个很重要也明确的意识。这些自然像是一辆装货的空车,空车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它的意义在于装的货,即“自然”在小说中所承载的观念。但是,也正由于过强的功利目的,所以,作者借自然干预生活的意图,也就往往容易表现得过于直露和急迫,而使小说显得张扬有余而含蓄不足。
五、对大自然的崇拜
现代化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简陋的游牧生产方式所无法提供的文明生活。但伴随这种文明生活而共生的却有许多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负面和消极的现象,比如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疏离,空间的嘈杂和拥挤,环境生态的污染和破坏等等。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可能伴随着某种相应的退步。另一方面,人生原初的清纯、古老和质朴的情感,也渐渐在城市文明中被温文尔雅的现代情感方式研琢磨砺,变得周正规范。因此,凝眸于注定要成为过去的那渐渐消弥的旧潮,“我的笔下将出现一片牧场”(顾城)。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表现出了空前的对大自然描写的热衷和醉心。这时期的蒙古族小说,也对自然显示了更多富于文学家的感情色彩的思索。在他们笔下,自然不再仅仅是作为背景或者人的生活环境,被借用进作品中;自然也不再承担某种理念或观念。自然开始被看作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有灵魂的血肉之躯,一个骠悍的不可侵犯的强大力量。霍钦夫的《伊默塔拉的精灵》写一个年轻人与一匹野性的烈马(精灵)间的气力和智慧的角力。“你”是瘦弱的少年,而“你”要征服的马却是一匹“只有在先人的传说中,见过这样的马”,是一匹“使这里所有的骏马黯然失色”的“野性的精灵”。在它闯入“你”的马群时,“你”下定决心征服它,在经过了很久的斗智斗勇之后,“你”骑上这匹马后,“你”没有像其它驯马手那样,用皮鞭抽打它,却想“为什么不能尽其自然呢?”于是,“你由着它任性地凶猛地跳跃,飞速地驰骋,仿佛是鼓点一样的蹄声在鼓动着你。”渐渐地,“在这自由的驰骋中,你们理解了、信任了、默契了、志同道合了、魂灵与共了”,你们俩合为了一体。索德纳木旺吉拉的《云青马》中的,云青马,帮助主人打死过4只狼,救过两个人的性命,还多次在那达慕上获奖,它的体内蕴育着让人为之流泪的美丽的个性。
在这些作品中,写自然(马)的力量,以及它宽厚、伟大、忍辱负重的品格,表现出了人与自然——动物之间心灵和精神的相通。在蒙古文学中,“马”是一个具有古老传统的独特形象,对于马的描绘,无论在展示马的体态、耐力、速度等品貌特征上,还是民间文学中以拟人手法描写“马”出人声、说人语,识别恶妖,预知未来,为主人提供克敌制胜的妙计良策等等,都集中反映了蒙古民族传统的“马”文化观念。80年代末以来的蒙古族小说中对“马”的描写,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但相对前一时期小说在自然观上表现出的类比或影射的对应关系,这时期小说所持的自然观又有所不同。即自然不负荷任何一种(无论善或恶)社会观念而或多或少地被抽去自然本身的自然形态:自然不是空车而就是货物。小说着重表现的是自然同蒙古民族之间几乎类似宗教信仰般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是对“马”——自然的本原意义上的情感。换句话说,这种情感的来源并不始自(自然所负载)的某种社会的或人性的观念、理念或哲理,而就是自然本身。我想,这其实正是蒙古民族的精神支点,它昭示了一个被誉为“自然之子”、“马背上的民族”的民族的内涵。在这种情感中,“马”——自然具有着它的不朽的品质、意志和精神,在它那博大而深邃的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令人感动又让人露颤的生命。另一方面,小说又谴责了人类贪婪的欲望所导致的对自然的虐待和戕害。云青马被卖掉成了套大车的辕马,那匹精灵一样的烈马也终于死在那个卑鄙无耻的家伙的枪口下。也正是对自然(马)失去天然灵性而发出的悲怆痛苦的呼号中,在对人类自私的物欲的愤懑不平中,我们体验到了对自然(马)的爱慕和祟拜。
六、自省小说中的将自然风景作为“民族”的根的象征
90年代初开始,蒙古族小说出现了一种与前此完全不同的小说类型,这就是“自省小说”(注:拙作《后草原小说概观》,载《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自省小说不写牧区,不写牧民,所描写的蒙古人,也与人们通常意识中的蒙古人不同,这是一群不能以民族外显型标志(如语言、服饰、生活及经济方式、居住地域等)来证明自己民族身份的蒙古人。他们生活在城市中,是城市的第二代的蒙古人,或者是走进了城市就再也没有打算离开这里的“闯入者”。他们熟悉和正在熟悉城市,不管最初走进城市的心情如何,在与城市的胶合、拼争、厮杀中,他们最终和城市达到了统一和融合。
但这只是表现现象,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托夫勒在《预测和前提》(注:托夫勒著《预测与前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第一版,粟旺、德胜、徐复译。)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不同层次的认同”的问题。他认为,人的进化过程中需要某些形式的“集体识别”,这种集体识别会成为一个民族(或种族、宗教等其他形式)的内聚力。内聚力决定着一个民族(或集团)的生存能力的强弱。另一方面,任何民族还有共同的“心理领域”,这个民族的群体观念和认同观念都属于并包括在这个“心理领域”中。在一切人类社会制度里,起着根本性胶合作用的,就是这种“归属”的观念和“群体”的观念,以及与其他人认同的“行为”。但是,这种观念和行为,都不足以与人类历史中出现的任何一次文明改革的浪潮相抗衡,在每一次历史变化的时候,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在性质上都会起着革命性的变化,一些旧的标识会消亡,另一些旧的标识则会留下来,还有的旧标识会有机的和新的东西胶合在一起成为新的标识,而为人们去认同。然而,“旧的种族、民族的认同层次可能更根深蒂固,”因为“在你出生的时候,个人和集体最基本的信仰就已经定了。”(注:《预测与前提》,第154页。)
托夫勒对处在第三次浪潮中的不同集团、种族、民族、宗教等在各自“认同”问题上的描述,与自省小说中的城市蒙古人的处境非常相同。一方面,旧的集体识别在城市这个新的环境中几乎不复存在,而新的识别又没有成熟,因而与自己群体认同的依据不存在了,“归属”和“认同”不再可能是行为,甚至作为意识也不再可能与他人认同,“我”不能证明“我是谁”。另一方面,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信仰”又在心理领域中牢固的永久的保留,“归属”和“认同”的意识和渴望就因此变得更加迫切,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心理痼结,我要证明“我是谁”。这是两股相反的心理能量,以相同的量在相反的方面增长。这种灵魂和精神上的痛苦,非此中人不能理解。这样,对于草原、马、羊儿等自然的描写,就成了民族的根的替代物、象征物出现在小说里。正因为是象征物、替代物,这些自然更倾向于主观中的自然,带有更多的主观想象色彩,与真实的自然相比,它是变异的、奇特的,甚至是怪诞的,像《血缘》(注:拙作《血缘》,载《民族文学》1990年第一期。)中描写的绿色的太阳、紫色的牛羊、红色的草地、活了的白雾等等。
关于“象征”,在古希腊语中指的是作纪念用的陶片。好客的主人给客人一块所谓“招待的陶砖”,客人将其打破,留下一片,把另一片给主人,以便以后客人的后代又来到这里时,双方把两半拼成一个整块相认。所以,象征是“通行证”,人们凭借它把某人、某地、某物当作故旧来相认。汉斯·乔治·伽达默尔说:“对象征性的东西的感受指的是,这如半片信物一样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显示出与它的对应物相契合而补全为整体的希望,或者说,为了补全整体而被寻找的始终是作为它的生命片断的另一部分。”草原风景在自省小说中的象征意义正在这里。一个完整的生命被“城市”切成两半,于是,在城市喧嚣和浮华中,他们在努力不渝地寻找自己裂开的另一半,“草原”就犹如被遗忘和丢弃的传统及根、祖先和历史,就是在归属和认同时所持的“通行证”。
自省小说对草原的亲近,还因为草原的明静、新鲜、清纯及广阔、博大,是城市狭窄、拥护、嘈杂、物欲横流的反证。因此,草原又成为对那种简单的人际关系,自由不羁的生活方式和渴望抛开强加于人的各种戒律等等的象征。在《血缘》中,风景描写是独立于作品的情节之外,以“图画”的形式出现的。这就尤为痛切地表现出城市蒙古人在城市中处在一种边际化的生存状态的飘零和没有根基的那种悬浮的恐惧——故乡、民族只能是以远远眺望着的图画而成为当下存在的东西。这更说明民族、传统、祖先是一种与自己肉体并不相连的外在物,这种感觉是非常痛苦和可怕的。自省小说中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有种忧郁、凄凉的调子,也正源于此。
艺术意味着某种存在的延展和扩充。《血缘》中对于“草原”的追寻,就是小说主人公无根的现实生存的延展和扩充,她的生存的状态和意义,由城市而扩展到了图画里的那个草原即民族的根的所在处。在所有的自省小说中对自然风景的描写,也都同样地成为着作者现实生存的延展和扩充。“象征”并不单纯是指示出一种意义,而是使意义出现,它本身就体现着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自省小说所描写的草原就是民族、就是故乡、就是传统,就是自己的根。
标签:风景论文; 文学论文; 蒙古族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草原风格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艺术论文; 民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