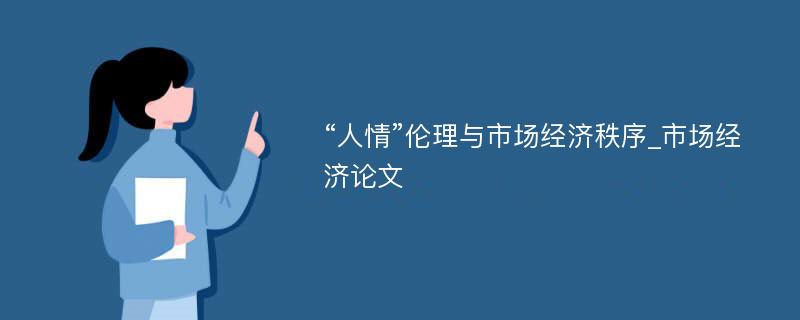
“人情”伦理与市场经济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情论文,伦理论文,经济秩序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重视“人情”的国度,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如何处理好“人情”关系是日常交往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建立在“人情”关系基础上的“人情”伦理,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世俗伦理文化的特质。由于复杂的“人情”伦理关系网络的存在,在今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渗透于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人情”伦理,对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日常交往生活中的“人情”伦理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情”所蕴涵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同样是言说“人情”,在不同的具体境遇下,它的“所指”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人情”大致包含有以下三层意义:(1 )“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这是指在人与人交往中为增进情感和友谊而实施的相互性应酬和馈赠行为,在中国的部分地区,“人情”还被当作礼物和金钱的代名词,送“人情”就是送礼物(包括金钱)之意。《礼记》中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一句是对“人情”这一层意义的最好说明。(2)“人之常情”。它带有被公众所认同的、 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日常交往行为准则的特性。如我们说“这种做法合乎人情”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3)“情面和恩惠”。 这是指人与人之间基于“人情”的某种关怀和帮助。如我们常常所说的“托人情”,就是希望对方“看在情面的份上”给自己以帮助,而对方也可能碍于“情面”自愿或不自愿地给予“关照”,施以“恩惠”,这是送“人情”的另一种表现,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得非常广泛。
对生活于“人情”文化氛围中的中国人而言,判断不同境遇下“人情”的不同“所指”、分辨自己在“人情”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作出相互的回应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长期的“人情”文化积淀,使得中国的“人情”伦理非常发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征的人际交往伦理模式和世俗伦理文化。“人情”伦理对成人社会的日常交往生活非常重要,我们不可能摆脱“人情”伦理关系而生活,除非你与他人完全隔绝、甘愿孤独。一个人若不通“人情世故”,在世人看来就是“不成熟”的表现,而一个人处理“人情”关系的能力大小又常常成为衡量其社会活动能量和人际交往水平的标准。因此,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情”关系网络,并在“人情”伦理关系基础上形成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交往共同体,便成为我们日常交往生活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件大事。
现实生活中的“人情”关系相当复杂,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之“人情”伦理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异常丰富,但是,对我们日常交往生活至关重要的“人情”伦理,从学理上看,又显得过于宽泛和含糊,缺乏明确的限定,其伦理上的是非标准难以统一。我们只要对上述“人情”的三层主要含义稍加分析便可看出这一点。在人们相互之间的“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行为中,显然存在一个伦理上是否适度的问题,频繁的、无节制的“人情”往来势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紧张,“人情”往来变为“人情债务”便是它的负面效应。再者,何谓“人之常情”?对它的判断大抵只能诉诸日常生活经验,而经验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和不可靠的。例如,在中国世俗文化传统中,我们把“君子之交淡如水”和“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两种说法都看作是日常交往中的“人之常情”,但它们表达的伦理意义是不同的,伦理性后果亦有不同。而第三层意义上的“人情”更为复杂,因为对他人提供关怀和帮助并不一定都是符合伦理上“善”的行为。例如,拥有权力的政府官员,可能会因看重“情面”而出卖国家或公共的利益,对某人或某小团体施以特殊“恩惠”;司法人员也可能会因某种“人情”而使犯法者逃避法律的惩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情”关系一旦成为某些人“权力出租”的推动力量,用“人情”作交易,那么,它对市场经济内在秩序的破坏就不可避免。这是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如果对“人情”伦理的主要特征作一简略的归纳,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1.“人情”伦理是日常交往伦理。人们的日常交往是建立在“亲情”和“友情”基础之上的,是以情感为纽带的,因而由这种“人情”关系而发展的“人情”伦理属于私人交往的伦理层面,主要在私人交往生活领域发挥其调节功能。在本质上和调节范围上,“人情”伦理不同于公共生活伦理。
2.“人情”伦理具有亲疏性。人们的日常交往有深浅之别,“人情”伦理亦有亲疏之分。施与“人情”的对象一般是“熟识”的特殊他者,如家族成员、朋友、同学、同事和乡亲等等,而对“不相识”的陌生人则很少给予“人情”伦理的关怀,即便是与这些“熟识”的特殊他者之间的“人情”往来在程度上也存在差异,“人情”伦理的亲疏性明显可见。进一步说,“人情”伦理具有指向特定的人的基本特性,它不是立足于普遍主义立场,而是立足于特殊主义立场。
3.“人情”伦理具有扩展性。施与“人情”的特殊他者,有的相对固定,有的则会发生变动,随着个人交往生活的发展,“人情”往来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原本“不相识”的陌生人有可能进入个人的“人情”网络而成为“熟识”者,其扩展程度因人而异。与此相对的是,原先有“人情”往来的某些对象也可能渐渐疏远,被排除在“人情”网络之外,如新朋友取代老朋友等等,这是“人情”伦理的脆弱性一面。
二、“人情”伦理的非公共性
中国文化传统表明,“人情”伦理在协调人与人的日常交往关系上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人情”关系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也因为有“人情”伦理的存在而加强了彼此的亲近感,拉近了对共同体利益的认同感。在家族企业、同乡公会等共同体中,“人情”伦理在共同承担市场风险、相互协作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作用非常明显。即使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以“人情”关系为纽带、由“人情”伦理维系的利益共同体,也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西方学者在讨论东亚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时普遍认为,以感情为基础的东亚伦理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他们看来,西方人强调个人发展的权利,在经济交往中重视相互的契约伦理关系,而东亚人则看重集团或不同形式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经济交往中重“人情”伦理轻契约伦理。他们从西方人的视角,看到了中国乃至东亚伦理文化的部分特征,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把“人情”伦理等同于整体主义伦理,“人情”伦理属于私人交往伦理的范畴,它至多只能是一种特殊利益集团——亲近者共同体的伦理。
因此,“人情”伦理有其局限性,它不具有公共性特征,我们必须划清“人情”伦理的适用空间和范围。实际上,“人情”伦理拥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地盘,理想的“人情”伦理所推崇的是在私人交往领域不带功利色彩而且感情上彼此关怀和帮助的行为,“人情”伦理所期望的是充满“人情”味的温馨和谐的日常交往生活。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情”伦理所起的作用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美好,由于受到来自个人或特殊团体的利益的强大冲击,使得“人情”伦理的功利色彩相当浓重。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情”伦理的非公共性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公共生活伦理秩序的要求,而且由于“人情”伦理对公共生活的排除,使得社会的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在我国的伦理文化传统中,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大多以亲情和友情为基础,并由此建立起相互的“人情”伦理关系和调节这种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缺乏发达而有序的公共生活伦理文化。把这种从亲情或友情构成的“人情”伦理关系,再向外部推展,便是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修、齐、治、平”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可能会导致将公共生活关系演化为某种准家庭关系的“大家庭伦理”倾向,从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排除对没有“人情”关系的他人或陌生人伦理上的关切与考虑。因为没有亲情或友情关系的存在,自然也就没有与己相关的伦理关系可言。因此,“人情”伦理所关注的只是或主要是个人或特殊团体的利益。尽管我们强调“人情”伦理是日常交往伦理,但是,个人总要与公共生活领域发生联系,而这种视“人情”关系的亲疏参与公共生活交往的方式,不可能真正地融入公共生活之中,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排除公共生活的倾向,这在今天的公共生活领域表现得较为普遍和明显,并由此带来了一些妨碍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发展的问题。
“人情”伦理非公共性的突出表现是将社会公共生活私人化,即把公共生活分为有“人情”的联系和无“人情”的联系两部分。在有“人情”联系的公共生活中,把公共生活交往关系视同私人关系,首要考虑“人情”关系的亲疏,因而属于公共生活的一切事务可以因“人情”而通融或变更,公共生活的规则在这里失去效用。而在无“人情”联系的公共生活中,就可以不尊重陌生人的个人权利,对陌生人持不关心、不帮助的态度,甚至把陌生人当做可以欺诈的对象。更为糟糕的是,对此现象人们常常视之为“人之常情”而听之任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之常情”在伦理是非标准上的不确定性。“人情”伦理的非公共性可能导致经济活动中无契约、无承诺、无规则的行为大量发生,公共生活的规章、公约得不到尊重和遵守,而如果公共生活领域处于无序的或混乱的状态,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三、“人情”伦理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侵蚀
保障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公平竞争,而这恰恰是“人情”伦理的弱点。“人情”伦理并不具有公平竞争所要求的公共性特征,它不应当干预公共生活事务,但是,在公共生活伦理尚未充分发育的社会,“人情”伦理突破私人关系领域,向组成社会公共生活的政治生活、法律生活和经济生活等领域的扩展就难以遏止;而“人情”伦理向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的大举“进发”,又使得公共生活伦理的发育举步维艰,市场经济秩序受到严重侵蚀。
在政治生活领域,由“人情”伦理引发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权钱交易”。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完善的民主政治传统来支撑公共政治生活,没有形成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合理的政治生活伦理,就可能导致公职人员缺乏与其他的社会成员享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意识,从而给以“人情”关系处理公共生活事务留下可乘之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错动,公职人员的利益地位有所下降,补偿自身利益的动机就易于产生。对公职人员来说,权力是手中的一种“资源”,只要“出租”便可轻易获得经济回报。用“人情”买通权力部门的官员而取得不当利益,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公职人员的腐败常常是从被动地接受“人情”开始的,而一旦经不住利益的强烈诱惑,就可能变被动地接受“人情”为主动地发展“人情”、进而出售“人情”,由受贿而索贿,“人情”成为可交换的商品。政治生活中的“权钱交易”,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政治环境,动摇了市场经济秩序赖以生存的民主政治基石。
在法律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影响着司法的公正性。对司法公职人员而言,如果不能摆脱“人情”关系的纠缠,就难以做到秉公执法。由于“人情”伦理的根深蒂固,再加上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系统建设还存在诸多不足,在与司法机关打交道时,许多人并不相信司法的公正性,他们认定有无“人情”关系是诉讼成败之关键,因而,托“人情”和找“关系”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在此环境下,如果司法公职人员徇私枉法,以“人情”代替法律,甚至企图通过出售“人情”获得利益回报,那么在大量的“人情”关系面前,任何法律法规都可能变为一纸空文,司法的公正性将无从谈起。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正的法律环境能够有效地保障市场经济的秩序,但是,“人情”与法律常常发生冲突,“人情”伦理的强大影响力有可能遮蔽法律的公正光环,消解法律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力量。
在经济生活领域,侵吞国家财产、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等现象屡禁不止的问题也与“人情”伦理密切相关。我们以一个案例对此作简单分析:
某A从国外走私一批汽车,被海关查获, 按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规定,在正常情况下,A将被没收所有走私汽车并受法律惩治。 在此情形下,A通过与其有较深“人情”关系的某权力部门官员B,疏通与海关的关系。而B与海关人员并无直接“人情”关系, 于是B又找到好朋友C,请C打通与海关的关系。C与海关某官员D是亲戚,D原想依法办事,但又不能不顾C的“情面”,最终答应帮忙。而当D得知当地政府某官员B 也过问此事后,D考虑到日后免不了要有求于B,便主动地出谋划策,指使他人帮助A伪造相关批文, 以进口汽车散件的名义将这批走私汽车销往外地,致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扰乱了国内汽车市场的经济秩序,包庇了犯法者。
A的“人情”关系模式是发散式的,由一点向不同方向扩展, 形成“人情”连环套。依靠如此复杂的“人情”网络的连续运作,A 获得了巨额不当利润,他自然不能亏待为他帮忙的B、C、D等人, 他会很通“人情”地在事前和事后给B、C、D等人以可观的利益回报, 以答谢这些人的“人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情”关系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巨大威力,温柔的“人情”,能攻克诸多难关。为了个人或特殊共同体的利益,公共权力可以化为私有权力,成为“人情”的服务工具。
“人情”伦理对社会生活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希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社会环境下,能够拥有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日常交往生活,能够得到他人的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的广大成员普遍认同“人情”关系的功利性价值,并倾向于通过“人情”关系获取利益回报,那么,这样的“人情”伦理又会破坏社会公共生活的公正性,有悖于伦理的真义。应该说,合理的公共生活伦理秩序不仅可以有效地保障社会经济交往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可以减少经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财富的增殖。因此我们必须正确看待和对待“人情”伦理,充分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公共生活伦理,控制和削减“人情伦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