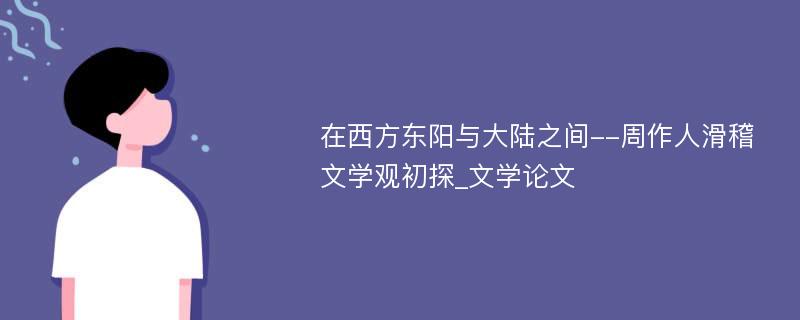
在西洋、东洋与本土之间——周作人滑稽文学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洋论文,西洋论文,滑稽论文,本土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作人,作为“五四”思想革命的闯将,封建道德的批判者,卓有成效的文学家,和大起大落命运的承受者,其人其文在经过长时期不自然的沉默以后,重新得到了应有的瞩目和关注。人们对他的文学观、妇女观、翻译理论和技巧、散文风格及其成因等等都倾注了巨大热情,并获得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成功。也许是周作人以上各方面的成就太过炫目,以至淹没了他终身不懈的另一个小小的角落,这就是他对古今中外滑稽文学的发现和倡导。他对欧洲混合着忧郁和滑稽的翻译文本的选择及对“没有意思”的滑稽儿歌的提倡,对日本文学中狂言、俳句、川柳和滑稽文本等的译介和赞赏,对中国文学中滑稽分子缺席的不满而同时又不惮其烦从明清被打入另册的文人身上及民间文艺中挖掘这一分子的举动,都明确指示出了一条虽不耀眼却一直源源不断的文学支流。这一支流跨越欧洲,日本和中国三大区域,纵横两千余年,涉及的文学体裁遍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乃至民间笑话、谜语、歌谣等。在这一片广阔的文海中,周作人以他一贯所津津乐道的知与情为衡量尺度,向世人呈献出他的儿童滑稽文学观,文人滑稽文学观和民间滑稽文学观。在将这些观念从周作人纷芜繁杂的文学活动中剥离出来,并赋予它们时代性和文学史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将注意周作人作为个人体现在其中的独特品味和审美情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周作人笔下,“滑稽”、“诙谐”、“幽默”等概念之间基本上没有大的分歧,只不过前两者更具民族特色和日本风情。
有意味的“没有意思”:儿童滑稽文学的本色
“五四”确实是一个热情而敏锐的时代,关于社会人生的所有问题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中国历史上一贯被当作“缩小的成人”或“不完全的小人”①的儿童,也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完整的“个人”的形象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和文学的舞台,它与人们对妇女和“下等人”的发现和关注一起,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和人道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鲁迅、郭沫若、叶圣陶、冰心等,或痛切指陈,或深入剖析,或满怀憧憬,或热情呼唤,掀起了一股关于儿童和儿童文学的浪潮。而周作人,以自己对本国儿歌的搜集整理、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引进介绍,特别是对儿童心理和儿童文学本质的理性阐述,无可置疑地成为这股浪潮最热心的倡导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周作人倾注了很大热情的是对欧洲卓有成效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输入引进。他将这些作家作品区分为“有意思的”和“没有意思的”两种。“有意思的”一路如安徒生、王尔德等的童话作品,人们多少能依据成人的观念在其中寻觅某些具体的意思;“没有意思的”一路有英国的利亚和加乐尔等,利亚做有“没有意思的诗”的专集,加乐尔则拥有《阿丽思漫游奇境记》②。在什么事情都追究正而大的“意思”的中国,最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没有意思”这一路儿童作品了。而在周作人看来,“没有意思”正是儿童特有的滑稽趣味,也是儿童滑稽文学的本质特征。
在从西欧引进这种新型儿童文学样式的同时,周作人更注重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给这种“没有意思”以理论上的阐述和辩明。他首先从儿童特有的心理和思维规律出发,指出:“小儿正如野蛮人,于一切不调和的思想分子,毫不介意,容易承受下去,……能很巧妙的把几种毫不相干的思想,联结在一起。”③“小儿大抵是天才的诗人,所以他们独能赏鉴这些东西。”④周作人接着引用英国政治家辟忒的话说:“你不要告诉我说一个人能够讲得有意思;各人都能够讲得有意思。但是他能够讲得没有意思么?”又引用特坤西的观点:“只是有异常才能的人,才能写没有意思的作品”⑤。可见,这里的“没有意思”是超越了有意思之后的更高意义上的一种境界,如同经过了长期的精雕细凿的工夫而终于归于平淡的化境一样。他甚至更进一步,将这种“没有意思”提到哲学的高度,指出儿童的滑稽是一种超越了主义观点的纯粹的滑稽,它产生的是一种永久的儿童的喜悦,这一永久性对于感觉到了自身限量的大人来说将产生更高层次的喜悦感。⑥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这种“没有意思”的儿童滑稽的特别提出及一再申辩和强调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五四”的时代风云将儿童推上了历史宠儿的位置,一批先驱者掀起了儿童本位主义的热潮,但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这股汹涌而起的热潮同样免不了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如出版于二十年代的《各省童谣集》,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又以一种最为传统的方式损害和歪曲了儿歌。编者或望文生义,找出意思,或附会穿凿,加上教训,强行在本来“没有意思”的各首滑稽儿歌后面加上种种道统的训词。在周作人看来,这种做法对儿童教育将产生极大危害:“中国家庭旧教育的弊病在于不能理解儿童,以为他们是矮小的成人,同成人一样的教练,其结果是一大班的‘少年老成’——早熟半僵的果子,只适于做遗少的材料。”⑦周作人在以启蒙斗士的热情积极参与掀起儿童本位主义时代大潮的同时,又以一个批评家的理性冷静地注意到了浪潮之下的沙砾。所以在众多的关于儿童文学的诸种理论之中,他特别亮出儿童的滑稽——“没有意思”这一面大旗,不仅率先揭示了儿童滑稽文学的本质特征,也给了中国社会无处不在,令人不堪负载的各种“正而大”的正统思想顺手一击。
含泪的笑——诙谐的情境——忧患的闲适:文人滑稽的表现形态及审美特性
周作人对文人滑稽的关注同样始于“五四”时期。他在与鲁迅共同进行的对欧洲新进文学的译介活动中,首次显示标志自己审美情趣的独立音符。到三十年代,周作人已远离时代的主旋律,日夜端坐于苦雨斋,仔细咂摸日本俳文的种种俳境及中国晚明新俳文闲适诙谐外貌下的忧患,在最浓厚地显露游离于时代之外的个人审美意趣和文学品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回响着周作人作为无可遁逃的时代一分子的寂寥而伤痛的微弱呼声。
“含泪”而“轻妙”的笑:“五四”主体精神笼罩之下周氏独特意趣的初步流露。
早在本世纪初,鲁迅作为中国第一代具有真正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面对积弱的祖国和冒盛的异邦,首次发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激越呼声,人道主义以它特具的品格和力量,一开始就成为这些“新声”中最为强大的一个音符。同为一代宗师,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对欧洲文学的译介活动正是自愿自觉地围绕着这一主旋律而进行的。他执着地选择东北欧及俄国等弱小民族和地区的文艺活动作为自己的译介焦点,并且明确指出:“但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有着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⑧。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对异域小说的引进工作周作人是与其兄鲁迅共同携手进行的,正如同十多年前的《域外小说集》时期一样。1922年以周作人个人名义出版的《现代小说译丛》三十篇译作中就有九篇为鲁迅所译。在共同遵从人道主义这一主体时代精神的同时,周氏兄弟还试图以自己的译介活动来影响、改造中国国民的审美情趣和情感结构。周作人曾不无偏激地指责:“中国本来绝无感情的滑稽,也缺少理性的机智,所有的只是那些感情的挑拨,叫人感到呵痒似的不愉快,这是最下等的诙谐,原来的滑稽文章大都如此。”⑨鲁迅也多次道及:“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⑩所以周氏兄弟在选择具体的文本作为自己的翻译对象时,非常注重作家体现在文中的一种中国所无的充满深厚情感的滑稽诙谐文风,他们几乎在每一篇译后记中,都不厌其烦地对这种新型文风进行了一再的强调和介绍。他们还不满足于此,而是更进一步,自己动手来进行立足于本土的创作,这就是鲁迅的中国现代第一篇新型讽刺小说《阿Q正传》及周作人的关于它的第一篇强有力的评论文章《关于〈阿Q正传〉》。
周氏兄弟的这种极具眼光的文学活动无疑地具有一种史学意义上的开拓性贡献。然而就是在这种时代总体氛围的笼罩之下,在这种对同一目标和相同风格的努力追求之中,周作人也还是和婉而坚定地初步流露出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份独特的感觉和趣味。
我们先来看周作人的几篇译后记:
事多惨苦,然文章极危诡,能用轻妙诙谐的笔,写他出来,所谓笑中有泪,正同戈果理一般。(对波兰显克微支的评价,见《点滴·〈酋长〉后记》,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8月初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因为他的真实的滑稽,优美的空想,柔和的忧郁,深厚的情感,都与自然主义不甚相合。(对芬兰哀禾的评语,见《现代小说译丛·〈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译后记》,版本同上)
但篇中的诙谐味,是他所独有的:他的小俄罗斯的温暖的滑稽与波兰的华丽的想象,合成他小说的特色……因此,便在这小说里,造成一件事实,滑稽而且严肃与悲哀。(对俄国科罗连诃的评语,见《玛加尔的梦·后记》,《新青年》第8卷第2号)。
再看同一时期鲁迅的两篇译后记:
亚勒吉阿尤有一种优美的讥讽的诙谐,用了深沉的微笑盖在物事上,而在这光中,自然能理会出悲惨来。(对芬兰亚勒吉阿的评语,见《现代小说译丛·〈父亲在亚美利加〉译后记》,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是颜色黯淡的铅一般的滑稽……(对俄国安特莱夫的评语,见《现代小说译丛·〈书籍〉译后记》。版本同上)
两相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氏兄弟在引进这种新型滑稽风格的时候,关注的是内中包裹着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感情因素:惨苦、悲哀、忧郁、笑中有泪(周作人),或曰悲惨、黯淡、铅一般的滑稽(鲁迅)。滑稽诙谐中只有掺入这些情绪因子,才不至流于轻薄和油滑。但在这一比较中我们同时注意到的还有周氏兄弟迥然相异的一面——周作人在“滑稽”和“悲哀”前面刻意加上这样一些修饰语:轻妙、柔和、温暖,而鲁迅的修饰语则是:讥讽的、深沉的、颜色黯淡的铅一般的。“轻妙”等词显示的是一种暖色调的感情,它们对冷色调的“悲哀”起着缓冲作用。这种调和两极情感的努力使我们第一次窥见了日后周作人“中和之美”审美理想的最初端倪。而鲁迅的修饰词则明显地要加强“悲哀”的份量。
周氏兄弟的这种相同及相异在他们对《阿Q正传》的创作和评价中,又一次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出来。
周作人首先指出《阿Q正传》的笔法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但又经过了鲁迅的明确取舍:“其结果是,对于斯拉夫民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11)。在这里,周作人持的是理性与情感的双重标准,从启蒙主义立场出发,周作人认为《阿Q正传》中那种缺乏和婉的一味沉重对于当时的中国现实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笑中的泪”和“俳味”分子的缺席,对周作人滑稽、悲哀、轻妙三位一体的审美趣味而言,又是一种情感上的缺憾。
情境:文化无用论中周作人咀嚼出的日本俳谐文的独特风味。
周作人对日本有着一种奇特的类乎故土的感情,他对日本的从衣食住行到文艺美术无不怀有透彻的了解和诚挚的依恋。二十年代中后期,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大地上的日益跋扈,周作人也曾凭着自己博治的知识和犀利的文笔,给予痛快淋漓的一击,但这种激情只是“五四”精神的最后闪光。闭户读书后的周作人将文化从现实生活中拉回到他的书斋,持一种悲观消极的“文化无用”论调:文化“好的方面未必能救国,坏的方面也不至卖国”(12)。在这一论调支撑下,周作人终于心安理得埋头于日本文化研究。而俳文,作为日本一种脱胎于中国却富有独特的岛国情调的文学样式,得到了周作人最大程度的赏识和迷恋。
在烽火连天的1937年,周作人相继推出了研究日本俳文和中国新旧两派俳文的文章《谈俳文》和《再谈俳文》(均收入《药味集》)。中国旧派俳文虽在先秦时代就随宫廷俳优的出现而产生,但在延续到清朝的漫长的发展路途中,它却一直作为文人的一种戏作而存在,其俳谐味的产生也主要是由一种文字上的游戏而来。在周作人眼里,这种双重的游戏导致了中国俳文生命力的永远丧失。而在日本,初始时同为游戏的俳文则田松尾芭蕉“从模拟与游戏中间救了出来,变成一种自然与人生的文艺”(13)。这种摆脱了单纯的文字游戏性质的“自然与人生的文艺”的最大特色,就是在诙谐滑稽之余,拥有一种留有余味的人生的情境,即周作人所说的“俳境”或“趣味”。(14)
“意境”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其基本含义即“境生于象外”,根据“象”及“象”外空间的不同,周作人将日本俳文区分为三种情境:“一是高远清雅的俳境,二是谐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15)。
所谓高远清雅,是一种“闲寂自然与惮悦相通”(16)的人生境界。而这种惮,又不是完全的不食人间烟火,它仍带着世俗气。若用一幅人生的情境来具体描述,便是:“譬如高门之士,扮作草笠道袍花下凭几,而成串团子终不下手”(17)。所以在周作人眼里,“高远清雅”是一种混合了“正”(高门之士)、“俗”(成串团子)、“雅”(花下凭几、终不下手)三种成份的俳境。
“蕴藉而诙诡”体现出的是另一种风致,那是介于平民的滑稽与士人雅博的趣味之间的一种中间的姿态。对此,周作人同样用一幅人生的情境作出了形象说明:“花下凭几,随手抓成串的团子吃,却仍不失其高致,庶几得之”(18)。这种恰到好处地调节雅和俗的“中间的姿态”在周作人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蕴藉而诙诡,这是一种既收且放的俳文笔调和丰腴而有节制的生活的艺术。
至于日本俳文中的“谐谑讽刺”一类,承续的是文字游戏的老传统,很难形成“象”外的空间,它基本上不在周作人的赏析之列。
诙谐闲适掩映下的忧生悯乱:苟活于乱世之中的周作人揣摸到的中国变音。
中国旧派俳文虽延续到清朝而毫无起色,但在晚明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俳文样式。这就是以张岱和王思任的小品文为代表的新俳文(19)。
明末既是王纲解纽、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异族入侵、家国将亡的乱世,这种双重因素在导致中国俳文脱离传统的游戏观念而获得全新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一种特殊的色彩。周作人通过分析晚明小品作家的心态和作品,仔细辨明了这一特殊色彩的深层含义:应付乱世的闲适诙谐及内中包裹着的忧惧、愤懑和反抗情绪。这是周作人继西洋和东洋之后,在本土体味到的文人滑稽的又一表现形态。
周作人首先剖析了闲适、诙谐、忧患之间的等同和包容关系。
清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十二闲适语一则有云:“秦观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王铚《默记》以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净土,其论甚可憎也。……盖流连光景,人情所不能无,其托言不知,意更深曲耳。”此段话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文载道文抄〉序》等文中几次引用,以为闲适辩护。但在周氏眼中,秦观的这种醉卧只是一种“安乐时的闲适”(20)或曰“小闲适”(21),这是人情所不能无的,但却并不是周作人钟情的对象,他所瞩目的是乱世中的闲适,他称之为“忧患时的闲适”(22)或“大闲适”(23)。所谓“忧患时的闲适”,周作人解释道:“这里边有的是出于黍离之感,有的也还不是,但总之是在一个不很好的境地,感到泽水在后面,对于目前光景自然深至流连,此与劫馀梦想者不同,而其情绪之迫切或者有过无不及,也是可有的事。”(24)至于“大闲适”,是在“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时应付世事的一种态度:“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25)就这样,周作人将应付乱世的闲适态度等同于一种幽默滑稽的情怀,并凸现了其中无可避免地包容着的忧患情结。
生活于明末乱世的王思任和张岱,其小品文章充满着戏谑和闲适的表层分子。王思任一生以谑为业,至晚年还改号谑庵,周作人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天性如此,一方面也有社会的背景在里面,特别是他违反“谑而不虐”传统的“谑不避虐”,更是与外界的刺激直接相关。周作人这样总结王思任文风的变迁:“他的谑其初是戏笑,继以讥刺,终为怒骂,及至末期,不谑不笑骂,只是平凡的叹息,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26)。相比之下,张宗子的诙谐则比王谑庵要闲静得多,然而这种闲静也仍然不是轻松,它包裹着张岱国破家亡的沉痛情怀:“你当他作俳谐文去看,然而内容还是正经的,而且又夹着悲哀”,“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梦寻》《梦忆》二书皆宗子记其国破家亡之痛之作,而文特诙诡”。乱世文人不免于忧生悯乱,不管他们披着怎样的闲适戏谑的外衣。
周作人怀着一种同为乱世人的感伤心态,对明末俳文的体味是细腻、真切而深入的,这种深入其境、亲临其中的心理感受使周作人再也无法像“五四”时代一样占据一个制高点,以理性批判的精神来俯视晚明文学,他只能以情感共鸣替代理性考察,在为世人理出中国乱世特有的包裹着忧患而出之以闲适的俳谐文风貌的同时,自己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甚至在闲适一路较晚明文学走得更远。
“于杂糅中见调和”:周作人诸种文人滑稽文学观中流露出的共同的审美趋势。
周作人在纷芜繁杂的文学活动中显示出的诸种文人滑稽文学观,不论是关于“五四”时期具有启蒙和改造意义的欧洲滑稽文风,还是三十年代具有自娱、自赏和自感、自辩性质的日本俳文和中国晚明新俳文,都呈现出一种趋于一致的审美风格,那是一种糅合了多种分子、包容了多种滋味,而又以调和的面目出现的富有余味、耐人咀嚼的文章境界。周作人一贯指责中国旧有滑稽浅薄无聊,多是为了滑稽而滑稽,缺乏深厚的情感内涵。而“深厚”一词在周作人眼里又不是指朝一种情感方向的极度倾斜和深入,它不是一种单向的深度,而是一种由多重层次感造成的内蕴的丰腴厚实。“五四”时期,在引进东北欧深深夹裹着悲哀的滑稽文风的时候,周作人特别提出“轻妙”一词,以作情绪的调节剂,使悲哀呈现的“悲”和滑稽呈现的“喜”达到适度而微妙的平衡。三十年代,在介绍日本俳文的三种情境时,周作人最为认同的是恰到好处地协调市井滑稽的俗趣和高门之士的雅趣的那种“中间的姿态”。而晚明新俳文的诙谐之中,原是因为杂糅了忧患、愤懑、闲适、隐逸等相互冲突的矛盾分子而获得了更为深远的内蕴。
很多论者都已论及,周作人在希腊文化中,发现了一种灵肉高度统一所达到的审美理想极境:原始、和谐、均衡,具有童话般的魅力;在英人蔼理斯那里,他又接受了其“微妙地混合取舍”的禁欲与纵欲、自由与节制的二合原则。这些与我们上文展开的周作人文人滑稽文学观一样,都指向中国原始儒家最高的一种化境:中和之美。中和之美,这正是周作人由二十年代的感性领悟到三十年代的苦心经营而成就的一片天地。这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的艺术观。这种和谐的现世之美本应存在于太平盛世,周作人却用作了剧烈动荡,毫不容情的时代避风的港湾。它在形成人们于太平盛世才能最广泛地感悟到的周作人散文艺术永久魅力的同时,也给当时的周作人造成了一片极大的人生误区。
从粗俗壮健到纯朴有情:周作人民间滑稽的二重层次
1926年周作人在《两个鬼》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他的著名的关于绅士鬼和流氓鬼的论断,事实上,人们习惯于认为“闭户读书”后的周作人身上绅士鬼已压倒流氓鬼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于是他玩字墨、抄古书、写草目虫鱼,但即便如此,周作人身上与绅士气一样根深蒂固的流氓气息和叛逆精神也仍在不绝如缕地流淌着,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他以明晰的理智和现代科学常识为本,站在传统观念和假道学的对立面,为民间滑稽趣味鄙陋粗俗的内容和言词而作出的诸种辩护。在此基础上,周作人更进一步,在对日本川柳、滑稽本及狂言等民间文学的赏析中,提出了民间滑稽艺术作为有价值的文学样式的更高层次的标准。
粗俗而壮健:现代理性精神烛照下民间滑稽趣味的原色
作为人民生活和思想直接反应的民间文学,一方面因其内容的鲜活充实、形式的自由随意而受到历代有识文人的推崇和赞赏,一方面又因其面目的粗俗不雅、思想的高下混杂而一直被排斥在正统文坛之外。在封建道统思想最为顽固的中国,作为民间文学重要一支的民间滑稽文学,更是一直没能得到正常健康地生存发展的空间。仅存的一些不甚理想的品种,如民间笑话,其命运也只是随着道学的兴衰而浮沉。加上民间笑话自身无可避免的粗俗成分,使得它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评判。周作人以现代理性精神和科学常识为武器,对作为中国民间笑话两大组成部分的“猥亵”和“挖苦”成份进行了全新的辨明和更正,特别指出这种种粗俗不雅之中所呈现出的民间特有的“壮健”特色,从而重新确立了笑话在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意义。
蔼理斯在其《随感录》中曾解释“猥亵”一词道:“我说猥亵这个词是用在没有色彩的,学术的意思上,表示人生的平常看不见的那一面,所谓幕后的一面,并不含有什么一定不好的意味”(27)。周作人对传统意识更正的第一步,正是将“猥亵”从旧有道德的阴暗角落中拉出来,放到“没有色彩的、学术的意思上”,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了“猥亵”分子在笑话中大量存在的原因。周作人引用英人蔼理斯和德人格卢斯的研究成果,认为性的娱乐原与呵痒相似,猥亵的笑话中关于性的暗示正使人产生呵痒的感觉,从而使性的兴奋爆发而为笑乐,为人们心中念念不忘却又不可能随时实现的欲望找到了一条简便的宣泄口(28)。这种对西方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引用使得“不是秘密沉默的被珍重,便是高声的被反对与骂詈”(29)的“猥亵”这一分子进入到学术高大公正的殿堂,获得了自己正当生存的一份权力。
对于笑话中的“挖苦”分子,周作人首先亦从一般大众心理的角度作出了说明:“吸了人家的愚蠢谬误,能够辨别,显出智力的优胜,见了人家的残废失败,反映出自己的幸运,这大抵是使人喜乐的原因。”(30)虽然从道德方面来看,这些本不足为训,然而这又正是老百姓思想的原质和特色:“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31)。
周作人在推翻已有成见,对民间滑稽文学的粗俗鄙陋进行重新观照的同时,另行设立了一条价值评判的新标准——“壮健”。所谓壮健,就是真诚、坦率地表露自己的一切生活,不管是高雅的幕前的,还是猥亵的幕后的。壮健是周作人评判一切民间滑稽文学的最基本的标准,只要是壮健的,不管它怎样的粗俗不雅,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轻荡不同,……这是我所以觉得还有价值的地方”。(32)“如果执守着向来的雅俗的意见,我们也要觉得川柳的文句太粗俗了……但这决不是他的缺点,他的那种对于一切人事的直率坦荡的态度倒还是它的好处,他的所以胜于法利赛文学的地方。”(33)
我们前文已提及,“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对中国旧有滑稽表示了一种很强烈的不满,称之为感情的“挑拨”,这与他为中国民间笑话所作的诸种辨白和更正似有矛盾抵触之处。其实不然,这正表明了周作人在民间滑稽趣味上的二重标准,其一为民俗学标准,其二为文学标准,文学标准包含民俗学标准而具有更高层次的要求。周作人为笑话所作的辩护是针对伪道学“道学书下面藏着《金瓶梅》”的“病的轻荡”而发,在打击旧观念的同时,以“壮健”为旗帜,为民间笑话确立了新的价值观念,然而这种新价值的显现主要是在民俗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文学的意义上:“笑话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而尤为直接透彻,此正是民俗学中第三类的好资料也。……笑话也而有苦辣的讽刺小说的风味,……但是,我的意思还是重在当作民俗学的资料。”(34)——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民间笑话能选择安排得恰到好处,可入著作之林者极不易得;不仅笑话如此,中国“世俗大多数的滑稽都是感觉的,没有文学的价值了”(35)。
那么,周作人心目中不仅仅是粗俗壮健,具有民俗学的意义,而更是真正具有文学意味的民间滑稽文学究竟是怎样的呢?
纯朴有情:民间滑稽趣味的高级形态
三十年代前期,曾为“语丝”派骁将的林语堂改弦易辙另组《论语》,大肆倡导西洋幽默,引进了英梅瑞狄斯关于喜剧的一个重要概念:thoughtful laught(“会意的笑”或“有深意的笑”)。所谓“会意的笑”,说到底也就是体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情感在读者方面引起的一种牵连自身的共鸣。中国旧有滑稽之所以很难具有艺术的价值,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平淡而能牵引人心的“情”的分子的永远缺席。这种含情的民间滑稽文学的最典型的代表,周作人是在他所深爱的日本文学中发现的,并终其一生都保持了对它的赏析和爱好。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江户时代,平民文学各种式样都非常兴盛,这其中就有被称为“狂句”或“川柳”的民间讽刺诗和被称为“落语小说”或“滑稽本”的长篇滑稽小说。周作人“五四”时期除了在《论小诗》《日本的诗歌》等文中首次涉及介绍川柳外,又于1923年写有一篇专论川柳的文章《日本的讽刺诗》,中云:“川柳揭穿人情之机微,根本上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们看了那里所写的世相,不禁点头微笑,但一面因了这此人情弱点,或者反觉得人间之更为可爱”。1944年,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又一次提及:“(川柳)上者体察物理人情,直写出来,令人看了破颜一笑,有时或者还感到淡淡的哀愁,此所谓有情滑稽,最是高品”。在日本特有的落语小说中,周作人同样感受到了这种魅力,他称颂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等滑稽小说“平凡的述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并因此而认为“在滑稽这点上日本小说自有造就”,“可以值得注意”。(36)
周作人虽然用理知精神为“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的“力即是理”的民众原始思想进行过辩护,从他自身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准则出发,他偏爱的显然是这种既讥讽又同情的,能将读者牵入其中的“情即是理”的世俗温暖的滑稽,他认为这是一种更为健全的民众滑稽趣味。
“有情”而外,“纯朴淡白”是周作人衡量民间滑稽文学品味高下的又一准则。“纯朴淡白”作为民间趣味一种最本质的面目和作为文学作品高层次的一种风格要求的双重身份,周作人是在日本中古小喜剧——“狂言”的身上最深入地领悟到的。1926年周作人译著《狂言十番》由北新书局出版,每篇译著后面均附有译后记,它们在与中国旧有滑稽的比较中,反复地凸现了日本狂言滑稽趣味的风格和品味:“狂言是高尚的平民文学之一种,用了当时的口语,描写社会的乖谬与愚钝,但其滑稽趣味很是纯朴而且淡白,所以没有那些恶俗的回味”(《〈骨皮〉附记》);“唯因滑稽之轻妙,言辞之古朴……与中国的小丑戏迥乎不同”(《〈花姑娘〉附记》);“它的好处在能把威严的雷公写得滑稽可笑,却是古朴纯厚,没有一点恶俗气,这正是中国人所不能及的了”(《〈雷公〉附记》)。时至1955年,周作人在其另一译作《〈日本狂言选〉引言》中,还高度地赞赏它是“正当的民间文学”的“一个很好的例”。
周作人的儿童滑稽文学观、文人滑稽文学观和民间滑稽文学观,虽说不上形成了严密的体系,却都拥有自己清晰的内涵和明确的审美特征;它们遵循的是知与情,或曰理性与艺术的双重准则;随着周作人的闭户读书和逐渐疏离社会,体现在它们当中的启蒙和改造国民审美结构的较为外在和急功近利的色彩逐渐减弱,充分显示周作人自身审美情趣和艺术品味的成份逐渐增强,而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巨大的背景,那就是在中国绵亘几千年的文化生活中,无论是“没有意思”的儿童滑稽、“杂糅中见调和”的文人滑稽,还是“纯朴有情”的民间滑稽都非常缺乏。这是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民族文化生活。正是在这一背景映衬下,周作人的滑稽文学观获得了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二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4月第一版。以下注中未标明编者及版本的,均与此同。
②④⑤参见周作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③周作人《王尔德童话》,《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⑥参见周作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所引麦格那思《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论》中的话语,《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⑦周作人《读〈各省童谣集〉》,《周作人散文》第一集。
⑧周作人《〈空大鼓〉序》,《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⑨周作人《读〈笑〉第三期》,《晨报副刊》1922年10月13日。
⑩《准风月谈·“滑稽”例解》。
(11)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附录一《关于〈阿Q正传〉》。
(12)周作人《谈日本文化书》,《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13)(14)(15)(16)(17)(18)周作人《药味集·谈俳文》。
(19)周作人《再谈俳文》,同上。
(20)(22)(24)周作人《〈文载道文抄〉序》,《周作人散文》第二集。
(21)(23)(25)周作人《自己的文章》,《周作人散文》第二集。
(26)周作人《风雨后谈·序》,《周作人散文》第二集。
(27)转引自周作人《猥亵论》,《周作人散文》第二集。
(28)参见周作人《猥亵的歌谣》,《猥亵论》等文,《周作人散文》第二集。
(29)周作人《猥亵论》,《周作人散文》第二集。
(30)(34)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选·序》,《周作人散文》第二集。
(31)(32)周作人《徐文长的故事·说明》,《晨报副刊》194年7月10日。
(33)周作人《日本的讽刺诗》,《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35)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周作人散文》第二集。
(36)周作人《谈日本文化书》,《周作人散文》第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