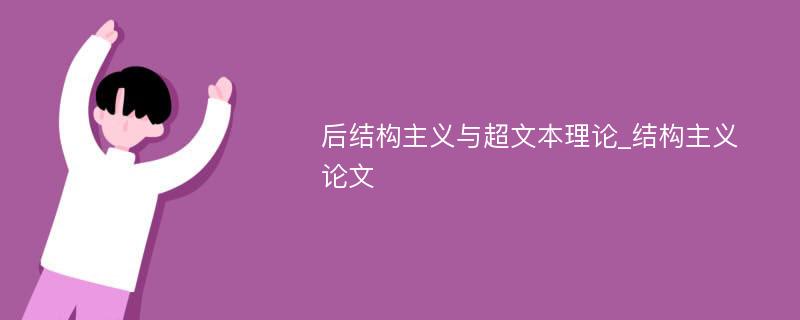
后结构主义与超文本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超文本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4-0053-06
由于电子出版物和万维网(WWW)的普及,超文本的应用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超文本开发者在各个文本单位之间加以明确的链接。这些链接开辟了新的文本空间,并深化了人们对语言符号相互关系的认识。超文本与后结构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批评家何为:超文本时代的批评理论》一文中,著名的超文本理论家兰道指出:超文本与晚近文本及批评理论颇多共同之处。例如,正像巴特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最近的著作那样,超文本重新设想了关于作者、读者及他们所阅读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设;为超文本提供了标志性特点之一的电子链接,也将朱丽亚·克里丝蒂娃关于互文性、巴赫金对多声部的强调、福柯关于权力网络、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达里关于根茎的“游牧民思想”的观念具体化了。超文本的观念成型与后现代主义发展几乎同时,但它们的会聚并非仅属偶然,因为二者都源于对印刷书籍和层系思想这类相关现象的不满。[1](P1)正如波斯特所指出的,“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2](P113)本文着重论述德里达、巴特和福柯的思想与超文本理念的相通之处。
一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是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于1966年所发表的演讲《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奠基石。199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讨论是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巴里·斯密斯等一些教授致信伦敦《时报》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里达先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哲学家,而他的写作也的确带有这个学科的某些写作标记。然而其作品的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几乎完全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例如,在电影研究、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系科里。……德里达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看来就是把类似于达达主义者(Dadaist)或具体派诗人(Concrete poets)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3](P232-233)这些人的非议是事出有因的。德里达颠覆文学从属于哲学的观念,难怪其作品在文学界的影响超过哲学;他所热衷的解构,带有鲜明的文字游戏性质,难怪学术界视之为某种“恶作剧”或“鬼把戏”。尽管如此,德里达在20世纪下半叶所曾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超文本理念的先驱之一。
德里达以对西方从柏拉图以来重语音轻文字传统的批判,树起了迥异于索绪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旗帜。他不仅着力避免在赋予“所谓时间上的语音实体”以特权的同时排斥“空间上的书写实体”,而且将赋意过程看成一种差异的形式游戏。他说:“差异游戏必须先假定综合和参照,它们在任何时刻或任何意义上,都禁止这样一种单一的要素(自身在场并且仅仅指涉自身)。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号链上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3](P76)德里达作为前提加以肯定的综合和参照,并非发生于文本内部,而是发生在文本之间。作为阅读对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场的,但它的意义不能由自身指涉获得,而只能在与不在场的其它要素的联系中赋予。如果不是着眼于单一的文本,而是瞩目于多个作为要素的文本或者由这些要素组成的系统,那么,在场与不在场的划分便失去了严格的界限(因为二者可以轻易转化)。
德里达发明了“延异”(differance)一词来概括文字以在场和不在场这一对立为基础的运动。在法语里,它的发音和“差异”(difference)一词相同,只是写法上第七个字母有a和e之分。这个新词是听不到的(被读音相同的difference所遮蔽),只有在书写中才能辨认,因此恰好可用来概括文本的特点。根据德里达的解说,延异是差异、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这一解释完全可以移用来说明超文本的特性。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这些文本单位因为彼此之间存在间隔(不构成连续文本),才得以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间隔是积极的,是联想生成的空间。当然,间隔使得这些文本单位彼此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意义”的在场与否成为一种悬念,当我们点击链接、在经历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来的是浏览器上“此页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体验到间隔本身的消极性(这是阅读连续文本时体验不到的)。构成文本单位之联系的链接因为这些单位之间的差异而得以延续(从一个页面指向另一个页面);反过来,链接本身又因为上述延续而产生变异(页1与页2的链接并非页2与页3的链接)。这种因异而延、因延而异的运动正是超文本所固有的。诚如德里达所言,“作为文字的间隔是主体退席的过程,是主体成为无意识的过程。”[4](P97)因为有间隔,链接才成为必要;因为有链接,间隔才不是纯然无物的空白,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字。间隔出现时,原有的阅读或写作中断,主体从而退席;但是,这种退席与其说是撒手而去,还不如说是新的出场的准备。间隔也促成了用户心理由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化,这种转化不过是相反的心理运动的前导。在等待原有的文本退场、新的文本出场之际,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用户尽可抓紧时间从事其它活动(如打开另一个浏览器窗口,喝茶等)。因此,间隔增加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干扰。但是,这段时间亦可被用户作为反思之用,有助于从新的内心视点审察先前浏览的文本,因此,间隔又增强了信息接受过程中的理性精神。这就是超文本的间隔所包含的辩证法。
德里达所铸造的“延异”一词,表明了后结构主义与自己的前身的差别。结构主义看重共时性而非历时性,认为结构的各种要素是同时出现的。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注意到要素在时间上的差异。“延异”之延,正是时间性的;“延异”之异,才是空间性的。因此,“延异”恰好是时空的统一。理解“延异”这一概念对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种路径可以通过地图等形式在空间中展示出来,但是,对于这些路径却不能同时加以探寻。因此,超文本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当用户选中某一种路径时,其它路径在空间上便由在场转化为不在场,对它们的探寻相应也就被延缓下来。当然,这种延缓并不是结构的破坏,而是超文本的结构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寻之外总是存在新的探寻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转,奥妙无穷。德里达所谓“延异”实际上是将结构理解成为无限开放的“意指链”(a chain of 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则使这种意指链从观念转化为物理存在,从而创造了新的文本空间。
德里达还使用“播撒”来表达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义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达看来,意义就像播种时四处分撒的种子一样,没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断变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结构,而是曲径通幽的解构世界。不存在所谓终极意义,那么,表意活动的游戏就拥有了无限的境地。这个隐喻同样可以移用来概括写作与阅读超文本时意义的变化。如果说线性文本强调文本的内部关系、因而强调意义的会聚性(所谓“主题”正是这种会聚性的概括)的话,那么,超文本则更为重视文本的外部关系,因而使意义的发散性显得相当重要。漫游于电子超文本网络之中,我们从一个页面进入另一个页面,也就是从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语境,这种运动是随着我们的兴趣而延续的,通过阅读所把握的意义随着上述运动而“播撒”,无所谓中心,也无所谓终极。即使上网时心存中心(例如搜寻特定主题的资料),这种中心也会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网作为一种活动存在为用户的时间和支付能力所间断,但这种间断并不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对终极意义的领悟,不过是新的漫游的准备。
我国古代治学传统中,早就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分别。德里达眼里的读者,同样有着重主观与重客观的分野。重主观的读者自以为有权力随便增添什么东西,重客观的读者则拘谨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东西。德里达认为这两类人都不懂得阅读,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进行解构阅读。解构阅读是文本自身解构而造成的意义播撒(dissemination of meaning),依赖于文本而又不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达的连贯性,也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阐释或说明。它强调互文性,企图抹去学科界线,这在精神上与超文本相通。
德里达认为解构是“写作和提出另一个文本的一种方式。”[3](P19)超文本的阅读同时也是写作。网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众所周知,解构阅读和传统阅读的最大区别在于‘可写’和‘可读’,传统阅读是重复性的可读,解构阅读是批判性的可写。……网络上面的联手小说,正是这么一种解构阅读产生的怪胎:没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线索,没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类的群众伦理诉求。每个续写者都只是他对于原来的文章进行解构阅读后的主观观察和本体理解,他没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着在公认价值体系下的统一所指,在网络联手的过程中,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联手者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环境。”作者参预发起的网络联手小说《守门》(http://eway.963.net)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角色参加进去。“角色扮演类型的《守门》让每个人保留的独自的视觉,任何场景和事件都是个体的感受,与他人所知无关,这是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人精神的张扬。在这样的网络联手小说中,道德、价值观念、文笔、风格都成为了段落性的个别东西,整个情节发展只有能指,没有所指。重复的只是某一个具体生命由于其经历和所思所感在一次叙述中的表露,那不是历史道德的积累,也不需要反映狭隘区域利益的法规。在传统媒体社会中,个体生命感觉的文化表达总是很难拥有最大传播范围的可能,而网络角色扮演小说让这种个人自由叙事伦理得到一个最广阔的相容空间,网络社会环境确实是解构主义的一个最大最好的舞台。”[5]
二
在20世纪思想家中,法国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又译巴尔特,1915-1980)对超文本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这位富于原创性的学者,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预言了理想化的文本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后来通过电子超文本网络得以实现。
后现代主义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来是个结构主义者,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之后倒戈,对结构主义的美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加以批判,从而转向后结构主义。巴特反对结构主义试图从一个故事中抽取模型、从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再将这一结构应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张将“本文”与“作品”加以区别。根据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与所指相互统一,存在固定的、对应的象征意义,存在作为最终探索目标的所指或意义的结构。阅读的意义就在于探寻这种结构。“本文”的概念则是巴特新创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与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间发生了自由的、无目的的意指,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任何意义都是随时生灭的,没有中心、没有连贯。对“作品”的阅读仅仅是一种理解、一种文化消费,而对本文的阅读则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游戏。巴特的《S/Z》一书,既为后结构主义树立了阅读范例,又为超文本阅读开创了先河。这本书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切成561个阅读单元,逐一进行讨论,然后以令人惊讶的错综复杂的方式将这些讨论组织成交叉参考,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出篇幅远过于原作的文本来。巴特的书自身就有可读性。读者无须知道巴尔扎克的原作就可阅读《S/Z》,当然,要想阅读《萨拉辛》,也无须先读过巴特的大作。不过,一旦读过了《S/Z》,谁还能再独立地阅读巴尔扎克的这篇小说呢?
巴特的“本文”观包含了某种网络的观念。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某个语词之存在,都以其它语词的存在为条件,语词的意义是由其它语词所组成的无形词典所规定的;其二,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也以其它文本的存在为条件,文本的意义同样是由其它文本所组成的无形网络所规定的。巴特心目中的理想文本,是一种链接众多、彼此交互的网络,是一个能指的星系,没有所指的结构,没有开头,可以颠倒。读者可从几个不同入口访问它,没有一个入口可以由作者宣布为主要的。这一理想正为万维网所实现。在万维网上,任何一个作者都可以将自己所写的超文本文件链接于其它任何文件,如果这种可能性被所有的作者都加以探索的话,那么,每个文件就将链接到其它所有的文件,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可能的文本。通过链接,文本分了支,这种分支近于无限,远非任何个别作者或个别读者所能穷尽。万维网既无开端,又无结尾,只是呈现为一个不断膨胀的中部。在理想的超文本中,没有一个节点具备相对于其它节点的优先权,各个要素的顺序可以任意跳跃。
罗兰·巴特的文本观导源于对“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的传统观念的反拨。[6](P51)他将“文”区分为两类,即“能引人写作者”(le scriptible)与“能引人阅读者”(le lisible)。前者是“有可能写作的东西”,后者是“不再可能写作的东西”。罗兰·巴特认为能引人写作者是价值所在,“因为文学工作(将文学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相比之下,能引人阅读者充其量仅具有相反的价值,即能够让人阅读,无法引人写作。他将能引人阅读者称为“古典之文”,因它在传统的文学体制下获得肯定。其时,读者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不与对象交合,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快感,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6](P56)他所向往的文学体制,自然是与传统文学体制背道而驰的。它为读者从事写作、实现角色转换提供了高度的自由。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因此完全丧失了君临读者的权利。很明显,电子超文本就是这种“能引人写作者”,它将作者和读者变成了“合-作者”(co-writer)。
罗兰·巴特所谓“能引人写作之文”与“能引人阅读之文”,存在一条重要区别:前者是生产,后者是产品。在传统时代,是产品(亦即“能引人阅读之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本体。然而,理想之文不应是产品,而应是生产,亦即“正写作着的我们”,或者说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说到底是随意所之。“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6](P62)据作者自述,《S/Z》一书乃因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与1969这两个学年的研讨班而形成的工作印迹。其时,电子超文本尚在酝酿之中。但是,罗兰·巴特论“理想之文”的一段话(见上引)已经接触到了电子超文本在交互参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电子超文本自身是网络(内部有节点与链接),同时又和其它超文本相互联系,既无中心,又无边缘,更无所谓等级。其二,电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银河系”,即后人所说的“文本宇宙”。其三,作为网络的电子超文本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任何一个网页都可以被设定为首页。其四,电子超文本的运作是可逆的,目前许多超文本浏览器都有“前进”、“后退”的功能。其五,电子超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呈分布式存在,一方面“门道纵横,随处可入”,另一方面没有哪一种算得上传统意义上的“大门”(常言之“门户站点”就有许多家)。其六,对于链接的追踪凭联想而定,与其说遵循既定法则,还不如说是随心所欲。其七,电子超文本网络所能包容的文本数量,在诸网互联条件下,事实上是无止境的。
在罗兰·巴特看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种是“将一切文置于归纳和演绎兼具的往复运动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学目光,对它们一视同仁,从归纳的方向,强使它们重返总摹本(la Copie),而后一切文都将从这总摹本演绎生发出来”;另一种是“把每篇文都放回到运作过程中”,看它如何无休止地“穿行于无穷无尽的文、群体语言(languages)及系统而呈现出来”。罗兰·巴特显然是倾向于第二种角度的。这种角度事实上就是强调文本的动态过程而非其稳态特征(所谓“独特性”)。[6](P55-56)
罗兰·巴特的上述观点,实在相当精彩,为后来的超文本理论家所服膺。他所说的“能引人写作之文”的特点,也就是超文本所具备的交互性、交叉性与动态性。他所写的《符号帝国》(1970)一书,将符号学理论糅入自己所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文化现象中,蕴含着某种超文本的旨趣,诚如夫子自道:“本文和影象交织在一起,力图使身体、面孔、书写这些施指符号得以循环互换;我们可从中阅读到符号的撤退。”[7](P1)
三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以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思想史学家著称于世,其影响身后犹存。虽然人们不止一次将他的理论归入结构主义之列,但福柯本人却从未认可,虽然他与德里达有师生之谊,但两人早已在学术成了论敌,因此福柯也和解构主义拉开了距离。尽管如此,在对于超文本理念的影响方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同样重要。
福柯之所以被某些超文本理论家引以为同济,与他所创立的“知识考古学”的宗旨不无关系。其一,福柯认为:“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在今天,历史则将文献转变为重大遗迹。”这就是说: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关注的是流传下来的文本所述及的外部事实,而知识考古学则力图着手从内部研究它们、将对这些文本加以审视与描述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与此相类似,线性文本理念建立在自身是对于某种客观事实的记载、描绘或反映的基础上,而超文本理念则以创造一种相对独立的媒体世界为宗旨、诱导人们关注文本宇宙。其二,福柯认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与此相类似,在对于线性文本的写作与阅读中,人们重视和追求连续性,意脉贯通、一气呵成、起承转合、首尾呼应,都是基于连续性的要求。但是,超文本却将不连续性作为自己的标志,主张峰回路转、化整为零、歧义并见、随机跳跃。其三,福柯主张以“总体历史”代替“整体历史”。二者的差别在于:“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8](P7-12)如果说线性文本所需要的是与整体历史相似的辐辏思维的话,超文本所需要的则是与总体历史相似的发散思维。线性文本力求建构某种集约的空间(围绕某一主题加以组织),而超文本则力求展开为“扩散的空间”。
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话语理论”,因为它将历史看成是话语的构造。就话语而言,福柯的以下观点值得注意:
其一,在考察各个时代断层中作为“碎片”的话语时,不应埋头寻找其作者,而应致力于研究话语与人的其它实践产品的关系。“不是重建某些‘推理链’(正像人们经常在科学史或者哲学史中所作的那样),也不是制作‘差异表’(像语言学家们那样),而是描述散布的系统。”[8](P57)他所著的《疯癫与文明》(1961)、《规训与惩罚》(1975)可作为这种描述的注脚。在与《知识考古学》大约同时问世的论文《作者是什么?》(1969)中,福柯将作者界定为话语的功能(而非话语的主体),认为“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9](P451)正如福柯所说,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就曾经有过无须考究文本的作者是谁的时代。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将某一文本置于上述网络,而且标示出该文本的每一观点、每一用语的来源的话,那么,表面上这一文本获得了高度重视,实际上却是被消解了,因为它在人们的心头唤起的是“不过尔尔”的感觉。当这个文本彻底消融在网络时,即使它在传统意义上是大师的作品,也丧失了原有的灵光。通过网络化的途径取消文本的自治性,尼采的著作可能被扩展到等同于洗衣店的单子,这是“杀死作者”的方法之一。对此,超文本理论家兰道已经言之凿凿。[10](P93)事实上,目前网络的应用已经显示出了淡化文本作者的倾向。
其二,与其它后结构主义者相类似,福柯从互文的角度把握话语的作用。他主张区别书的物质单位和书所支撑的话语单位,认为前者和后者相比显得既无力又次要,因作为物质单位的书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书的界线从来模糊不清,从未被严格地划分。在书的题目,开头和最后一个句号之外,在书的内部轮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书还被置于一个参照其它书籍、其它文本和其它句子的系统中,成为网络的核心。”[8](P26)这段话颇为超文本理论家兰道所看重。兰道在阐释超文本之由来时特别引用了它。[10](P3)
其三,他希望打通学科界限来开展研究,“考古学的领域可以像贯穿科学的本文那样,贯穿‘文学’的本文或者‘哲学’的本文。知识不只是被界限在论证中,它还可以被界限在故事、思考、叙述、行政制度和政治决策中。”[8](P238)他认为:人文科学是由于人在西方文化构成有待构想和有待认识的对象时出现的,时值19世纪。但是,也正是从19世纪起,认识论领域变得破碎零散,甚至四分五裂。人文科学将完整的人分割为碎片,使之变成不同学科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人文科学在发明“人”的时候也在消灭“人”。“人是晚近的一种发明。而且这一发明也许即将终结。”[11](P35)在我们看来,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建设,有助于整合各个学科对于“人”的认识,虽然这里所谓“人”已经不再处于世界中心(网络化生存本无所谓中心)。
福柯以“权力思想家”著称。在《权力/知识》(布拉埃登1980年版)一书中,他否认权力是个人或阶级的资产,强调它具备网络的特征,其线头四处伸展。他认为权力并非放射自某一中心源泉(如君主或国家),而是呈现为分布式状态。权力在社会机体中无处不在。作为权力之对立面的抵抗点也无处不在。权力关系因此是无数对抗或不稳定之点。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如果承认福柯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围绕国家机器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便失去了意义,社会变革也无法靠自觉、统一的阶级力量来推动。不过,福柯关于权力网络的某些观点对于文本网络的研究还是有启发的。第一,超文本本质上就是文本网络。已经建造成功并付诸实用的万维网正在迅速扩展,早晚超文本在社会生活中将无处不在。在超文本的每个链接上,我们都看到了某种权力——对链接的设定就是权力的表现,它要求用户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走,不许越链接一步(尽管路径是多重的)。有权力就有抵抗,当用户觉得页面上的链接不合自己的心意时,尽可以关闭上述页面。第二,福柯认为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权力总是与知识联手,利用知识来推行社会控制。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关系的。这启发我们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作为一个课题引入超文本研究。从理论上说,电子超文本网络应当成为人类共享信息资源、实现知识创新的空间。但是,在网络中仍然存在对于信息资源的封锁,这种封锁自然是依赖于权力才实现的。有封锁就有反封锁,黑客的活动正由此产生。黑客利用了他们关于计算机和网络的高深知识来打破封锁,反过来了又增进了计算机专家对于网络安全的认识。第三,福柯所关注的不仅是文本的网络、话语的权力。在追踪“监狱的诞生”时,他所作的考察就遍及“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12](P353)这提醒我们:电子超文本网络仍存在于文化大网络之中。前者目前无疑是后者当中与高科技联系最为密切、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成分,但是,其发展仍然为文化大网络所左右。例如,体现在文化大网络的价值观必定会浸染电子超文本网络的氛围,甚至决定电子超文本网络是作为自由天地而开拓还是接受规训而纳入传统媒体的轨道。
西方18世纪有所谓全景式监狱或敞视式监狱(panopticon),其特点是以中心了望塔监视设在环形建筑中的众多囚室。英国监狱改革的提倡者边沁(1748-1832)认为这种建筑可应用于监视犯人以外的场合,福柯进而创造出新词“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他引述朱利尤(Julius)的话来阐释全景敞视原则:这里包含的东西不只是建筑学上的创新,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古代社会曾经是一个讲究宏伟场面的文明。“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这是庙宇、剧场和竞技场的建筑所面临的问题。现代社会则提出了相反的问题,即“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这是为了适应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其对社会的一切细节和一切关系的日益深入的干预的需要。[12](P242-243)在电子传播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上述两个问题的表现:如果说电视作为媒体“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的话,那么,计算机网络作为媒体则倾向于“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对于网管员来说,用户其实没有多少隐私可言,至少,电子邮件比起书面信件来说要透明得多。不仅如此,“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Superpanopticon),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数据库的话语,即超级全景监狱,是在后现代、后工业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2](P127-132)当然,计算机网络也提供了“让一大群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多点对多点通讯)等可能性,因此给人以宽松的印象;同时,网上的信息流动看起来似乎不易监督,因此又给人自由的印象。其实,网络本身是实行全景敞视主义的适宜场所。正由于如此,有人呼吁:“全景式监狱虽然可以看到一切,不过只是在它所了解的地域内。当国家和资本的全景监视力量起作用时,抵抗战士要创造新的领土并行动起来。”[13]如何评价所谓“抵抗战士”的所作所为自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德里达、巴特、福柯等思想家虽然已经逝世,电子超文本却正凭借人类有史有来所曾建造的最大机器——Internet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电子超文本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代表了一种理念。只有弄清这种理念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看待电子超文本所蕴含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潜能。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进行后结构主义等社会思潮与电子超文本理念之关系的研究。
标签:结构主义论文; 德里达论文; 超文本标记语言论文; 超文本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网络结构论文; 文学论文; 福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