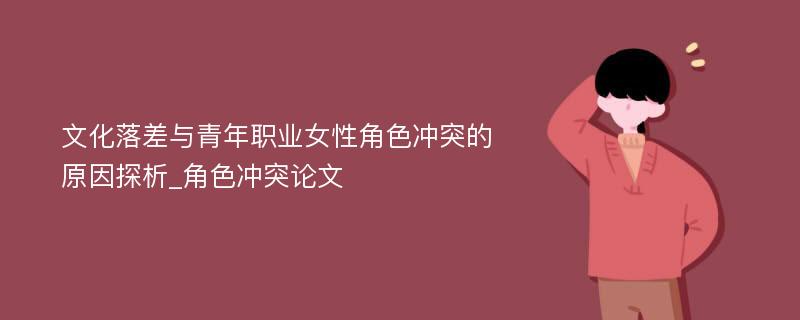
文化堕距与青年职业女性角色冲突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职业女性论文,冲突论文,角色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1]。当扮演者的行为符合了社会的要求与期待,其所扮演的角色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反之,不但不为社会所认可,反而会遭受种种质疑与责难,引发角色冲突,给角色扮演者自身带来压力与焦虑。
当下女性的角色冲突主要是表现为其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的冲突。青年职业女性要经历“孕期、产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所面临的角色冲突问题更为突出。
近年来,这一问题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对于引发女性角色冲突的社会根源,学者们大多归结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对女性的不同定位与要求及其二者之间的“不兼容”,而对于二者之间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针对女性的作用机制则缺少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究与剖析。
美国社会学家J·罗斯·埃什尔曼于1985年出版的《家庭导论》一书中曾经提出:“文化因素的力量在我们理解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社会化时占有压倒的优势。”他的这一洞见为本文性别角色的分析指引了总体的方向,而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对文化内部结构的剖析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视角。
奥格本认为文化各个组成部分的变迁速度是不同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一般来说,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民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这样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2]他将此现象称作文化堕距。
正是由于文化堕距现象的存在,人们的生活无形中被置于不同的话语空间。在职场中,制度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它从正式制度的角度表达着对于女性的职业角色期待;而民德、民俗等传统价值观念则更多地渗透于繁琐细致的日常生活,并通过更为密集的非正式制度传达着社会对于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与定位。因此,追本溯源,历时性地考察制度话语与日常话语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明确地感知当下女性角色冲突的深层原因,更为清晰地体认青年职业女性面临的困惑及其产生的社会因由。
一、传统社会:制度话语与日常话语的互构与女性角色的家庭定位
现有的考古发现表明,母系氏族时家庭与社会组织是合而为一的,男女之间是平等的。西周时随着父权制的建立,男尊女卑的社会定位、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及其活动的不同领域才有了明确的制度性的严格划分。男人活动的主要领域在外,是被称为公领域的社会大舞台,而女人活动的主要领域在内,是被称为私领域的家庭小舞台。“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至四方之事,顶冠束带,谓之丈夫,出将入相,无所不为;女子主一室之事,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日之计,只不过饔飧井臼,终生之计,只不过生男育女。”[3]
男女根据社会的不同定位,在不同领域内扮演着完全不同的社会角色。相比于家庭小舞台,社会大舞台上的角色更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是更有价值的角色。这样,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秩序得以建构和确立。这一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性别制度为以后长达三千年的后世设置了性别制度的基调[5]。考察中国三千年的性别秩序,尽管制度话语在不同时期对女性的要求存在具体条文上的差异,(如:从强调社会普适道德标准的“三纲五常”到专对妇女群体的“三从四德”,再到对妇女贞操节烈的大力颂扬等等。)但其制约女性、凸显男尊女卑的精神内核一以贯之。不仅如此,从制度设置的总体发展脉络来看,其历经累积与整合,内容相互映照,日趋系统化。虽然,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时段,也有过男女平等的呼声,但这声音大多淹没在主流话语的强大声势里。在我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下,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家与国高度一体化。制度话语中有关男女角色的这一定位,借助伦理观念、道德激励、审美诱导等途径,在日常生活中积累、构建为一套有关性别的规则及常识性知识体系:男人是天,女人是地;男人天生强大有力,女人天生温柔顺从;男人象征权威命令,女人应当听命服从;妻妾成群是男人的特权,女人只有贞洁专一才可能得到尊重……
日常话语中的性别规范如此细致缜密地规定着女性的进退行止,宰制着女性的生活世界,并与制度话语遥相呼应,相互强化。性别的制度规范因日常话语的配合而内化为隐含于生活细节中的巨大力量,而日常话语也因为与制度话语的契合获得了更为顽强的延续力。制度话语与日常话语在这一过程中相互转化并相互强化,在二者这一互动互构的过程中,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得以生产、再生产。制度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的这一互动模式长久地将女性角色定位于家庭,职场之于女性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二、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制度话语对日常话语的遮蔽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凸显
制度话语与日常话语互构、契合的历史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出现了急剧变化。
建国后,女性尤其是女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享受着史无前例的优先待遇。这一时期有关女性地位的制度话语强调“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5]。与此呼应,一系列体现男女平等的具体政策法规纷纷出台,主张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选举与参政等等。女性的角色扮演从家庭小舞台迅速扩展到社会大舞台。
然而,改革前的“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往往局限于所谓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即使在国家全能的时代,传统话语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家庭这种国家话语相对忽略的领域,两性关系的平等在实践中受到很大的限制。”[6]这一时期的妇女在与男性一样承担国家建设者角色的同时,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职业女性,即便是承担生育、哺育重任的年轻职业女性也并没有遭遇严重的角色冲突问题,这与这一时期制度话语、传统话语二者的特定关系模式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制度话语的快速转换使其与相对稳定的、由传统文化主导的日常话语之间拉开了距离,呈现出奥格本所描述的“堕距”现象。不过,二者间的不同步并非各自为政的简单二元分立模式,由于特定社会环境下二者在话语主体、表达手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声势浩大、果敢威严的制度话语一时间遮蔽了细致缜密、经久绵延的日常话语。有学者称这一时期的社会为“整体性社会”[7],政府为全能主义政府。在整体性社会里,资源通过国家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与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相配套的是国家政府严密的社会管理体制,它以行政化的单位体制为依托,自上而下实施对人的全方位的控制,其中包括对个人生活领域的介入与干预。这一管理体制使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一时期妇女社会地位、角色的变化正是国家这种强大动员能力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借助意识形态的倡导、系统的制度安排再加上宣传部门的配套支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
具体而言,国家通过单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男女同工同酬,使妇女在制度的庇护下能够与男性获得一样的福利待遇;有关妇女生育的单位保险制度,也使妇女不会因生育而利益受损;“单位办社会”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单位内部幼儿园、食堂等后勤服务设施的普遍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青年职业女性的家务重负,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更为具体的家庭问题上,女性也能通过单位从组织上寻求到来自制度话语的有效庇护。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性别制度话语的建构是与“革命”、“解放”等政治话语紧密联系的,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展开的扫除封建残余的社会运动,是否参与这一社会运动或对待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往往被视为“进步”与“落后”的分界线。因此,在国家制度话语营造的社会氛围里,即便“在家庭这种国家话语相对忽略的领域,”男性基于传统观念对女性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
基于以上原因,尽管这一时期的女性同时担当“国家人”与家庭人的角色,同时活跃于社会与家庭舞台,但国家正式制度对妇女社会角色的凸显及相应的妇女保护政策的实施使女性并未遭遇工作与家庭角色的严重冲突。
借助特定年代的资源配置方式,制度话语彰显出巨大威力,一时间遮蔽了生活中经久延续的传统话语。然而,遮蔽不同于消解,被遮蔽者并未消失,一旦这种遮盖力量消失或减弱,它便会重新彰显其本真面目。因此,随着商品大潮席卷而来,昔日的资源配置方式发生改变,被遮蔽的日常话语又重新显现它的威力,女性尤其是青年职业女性被置于双重语境之下。
三、社会转型期:双重话语的疏离与青年职业女性角色冲突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国家力量的向上收缩,行政力量逐渐撤离人们的私生活领域,国家与社会日渐分离,曾被强大的制度话语遮蔽的传统性别规范与性别秩序重又现身。不仅如此,历经制度话语的长期遮蔽,挣脱约束之后的日常话语积聚已久的能量以更为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于是,在传统话语占主导地位的生活世界里,女性再一次被明确要求要会穿衣打扮、要懂养颜之道、要擅长打理家务,要知道如何做个贤妻良母,一句话,要做个有“女人味”的女人。
如果说传统社会在性别秩序上强调的是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并将女性角色限定于贤妻良母的话,那么,在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女性家庭角色的内涵除了贤妻良母、相夫教子这些传统内容外,融入了更多特定时期的新元素。波德里亚称这个社会为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作为特殊消费品,女人味、女性美的商业价值被前所未有地关注与开发,年轻美丽的女性形象充斥媒体,成为女性的理想版本,保持青春靓丽成了女性共同的繁重功课。女性美的标准已细化到可以操作的多重指标:胸部要丰满、体形要苗条、皮肤要白皙、头发要飘逸,女人的身体为适应苛刻的审美需求被分解为各有衡量标准的部件,最终,美发、丰胸、减肥、护肤,……女性身体被“作为一个具有无数分支的新型市场来进行投资……”[8]。在这样的消费氛围里,容貌、女人味与女性婚姻之间建构起如下内在关联——有女人味、漂亮的女人才配有人爱、才能有人爱,换言之,男人若因为身材、容貌、年龄等原因,冷落或者抛弃女人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对女人而言,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是通过美容产品改变自己,而不是通过舆论导向对男人的观念进行引导与修正。显然,这种暗示将男性摆放在了一个更为主动的位置,而女性则只能顺应男性的要求改变自身。年轻、漂亮成了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应尽义务,既要“下得厨房”更要“出得厅堂”,才学、智慧与能力或可锦上添花但很难成为漂亮的替代品,于是,形塑自身,做个有“女人味”的女人成为女人不容置疑的选择,“女人味”转化为一种针对女性的话语霸权与软暴力。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制度话语中,男女平等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但与前一时期国家对妇女的政策性保护策略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与女性自身素质紧密联系起来,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精神被着重倡导,女性自身能力成为区别个体身份与衡量个体价值的重要标准,“个体由过去被动的国家保护对象转变为现在更加自主的市场选择主体”[9]。这一转变固然为女性自身发展提供了明确制度导向与更大自主空间,但男女平等的制度话语,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一般规则,使得千百年沉积下来的传统规范对女性造成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常常被忽略,女性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与阻碍,往往被归结为女性自身的因素。
制度的快速变迁与传统价值观念变迁的相对迟缓,导致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与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价值理念间的不对称,从而出现制度话语与日常话语相互疏离的局面:制度话语设定了“男女平等”的格局,强调女性通过自身素质的提升实现“自强”,在职场作出无逊于男性的业绩;日常话语基于传统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双重特征,不仅在“男女有别”的前提下对女性家庭角色提出了完全有异于男性的传统要求,而且又增加了青春、美丽等消费社会的特别要求。由于成家、立业、抚育幼子等重要活动多集中于青年时期,既要在职业舞台上扮演成功职业人的角色,又要在家庭中扮演美丽主妇的角色,青年职业女性在角色扮演方面陷入严重的角色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