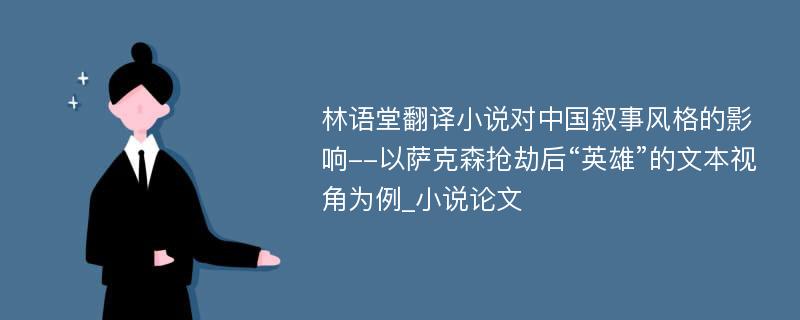
林译小说对中国叙事文体的影响——以《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文本视角特点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撒克逊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文体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10)01-0058-06
林译小说是指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1852-1924)在清末民初翻译的各类西洋小说。林纾不通西文,与友人合作翻译了160多种西洋小说,为晚清社会开启了一个“开眼望世界”的窗口;不仅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西方小说所体现的思想意识和人文精神,而且还引入了西方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作家,如周氏兄弟、郭沫若、钱钟书、郑振铎、沈雁冰等。
在中国小说形态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林译小说是重要的一环,林译小说以其独特的话语结构和叙事方式推进了中国小说现代性的发生,这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同。①然而,中西小说的发展历程迥然不同、中西小说的叙事模式、话语结构完全不同,林译小说如何在中西小说传统的鸿沟上架起沟通的桥梁,林纾以什么方式在晚清坚固的传统文化堡垒中开启一扇引入西方异质文学形式的窗口?林译小说对中国叙事形态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但却尚未真正展开的研究领域:因为直至今日,对林译小说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文本外部,着意于从宏观角度审视林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而对林译小说文学价值的评判,尚停留在对具有普遍文学意义的文本特征的泛陈概说,忽略了翻译评论须对勘原著对文本进行内面分析这一事实。但徘徊于文本外部的翻译研究难以解答林译小说的根本问题:林译小说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形式对西方叙事文本进行再叙述,进而对中国的小说传统产生独特的影响?只有通过对勘原著、对林译小说进行抽丝剥蚕的解析,从艺术层面探讨林译小说的形式特点所在,才能发现那些尘封的美学信息、感悟林译小说这一独特翻译文学现象的魅力,理解林纾在中国翻译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
文体分析是文本解读的一种方法,英国文体学家Paul Simpson认为:“文体学是把语言放在首要位置的文本阐释方法。”②Micheal Toolan也把文体学界定为一种文本解读方式:“文体学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阅读方式,其导向是对文本语言进行系统的分析。”③对文体学的这种宽泛定义,都指向文体学方法对于文本的潜在解释力。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小说作者通过语言来构建虚拟世界,对小说文本形式和建构方法的解析,有助于我们解读文本可能或者已经生成的审美蕴涵。
Paul Simpson在其《语言、意识形态和视角》一书中,根据Boris Uspensky和Roger Fowler的观点,对叙事文本的视角进行了四种分类:空间视角Spatial point of view,时间视角Temporal point of view,心理视角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又称为知觉视角perceptional point of view)以及观念视角Ideological point of view。④时间和空间视角提供了人们观察或呈现对象世界时所依循的时空角度及位置,包括时空的起点和移动的顺序。心理视角(知觉视角)实际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视角。观念视角蕴涵着说话者的价值判断,文本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信仰。在小说文本中,小说家往往通过一些特定的观察角度对小说中的事件进程、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进行调控,引导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观照、进入小说的虚拟世界。本文的宗旨就是以叙事文本的这四类视角为切入点,通过把林纾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和其原著——英国作家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历史小说Ivanhoe进行对勘,解读林译小说的文本特点,从中管窥林译小说对中国叙事话语转变所产生的影响。
一、《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时间视角
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林纾对小说章节的组织完全遵从原著的编排:原著Ivanhoe共44章,译本的各个章节和原著一一对应;原著各章没有标题,林译本各章也基本不设标题,但有一章例外:那就是第18章。第18章实际上是倒装叙述,是对第12章所叙比武场情节的回叙;林纾为这一章添加了标题“回叙战场中事”。透过林译本的这一处理,可以感悟中西小说传统的不同和林纾的翻译理念:中国传统小说由于深受史传影响,情节故事叙述时间基本以线性展开,“到20世纪初接触西洋小说之前,中国小说基本上采用连贯叙述方法”⑤。而“倒叙”打乱了“常规”的叙事时间顺序,偏离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这种对叙事时间的切割,虽然能产生很强的艺术效果,但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读者却是十分陌生的。因此,林纾通过在译本中添加标题“回叙战场中事”,既保存了原著的倒叙风格,又为读者理顺了因为叙事时间倒置而可能产生的误读。小说原著中的第21章实际上也是倒叙,在译本里,林纾通过在章首添加说明性句子向读者呈示该章的“倒叙”性质:“吾书叙洛克司列部署讫矣,今且回叙被劫之众。”⑥
按照原著的叙事时间顺序处理译本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当时却并非如此。1894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的政治小说《百年一觉》在上海出版,为了适应中国大众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他把该小说中的叙事时间一一理顺,原著中层次复杂的倒叙都被改造成了线性展开的叙述。⑦这是因为中国古典小说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个不同文类,两者语言文体不同,文学起源不同,读者对象也不同:白话小说情节性强,反映民间生活,接近民众的欣赏口味;而文言小说则继承了史传传统—中国因为没有史诗,“叙事”成了史书的专利,《史记》成为文人小说的宗源。在叙事时间上,这两种不同文类的小说也有不同的特点,根据陈平原先生的研究:“在文言小说中,倒装叙述并不十分稀奇。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薛伟》,先写薛病愈,再由薛倒叙梦中化鱼事;……”⑧而在通俗的白话小说中,倒叙却不是常见的叙事策略,古典白话小说的情节基本上都是按时间先后的连贯叙述。林纾翻译西洋小说,用的是文言,其目标读者是文人而非粗通文墨的民众,译本参照的标准也当然是文人小说,即文言小说;因此林纾注重保留原著的时间视角。
在翻译中,林纾以中国的文言家法对应西洋小说文体,他从西洋小说中读到了史传笔法,认为:西洋小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在“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以为大类吾古文家言”,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在叙述时间的运用方面,超越了《史记》、《汉书》,认为司各特的Ivanhoe“可侪吾国之史迁”。⑨
林纾对西洋叙事文体的这种解读,有学者认为是一种误读,⑩但林纾对西洋小说和中国史传文体进行的这种类比性阐释并非牵强附会,中国文言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和史传颇有相通之处。法国学者浦安迪认为:“中国叙事文的‘神话-史文-明清奇书文体’发展途径,与西方epic-romance -novel的演变线路,无疑能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对比。”中国历史上,“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和“虚构叙事”(fictional narrative)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西方文学理论家一般认为,历史讲事实(fact)小说讲虚构(fiction)。中国古代批评家则强调,‘历史中有小说,小说中有历史’,‘叙事’既包括细说也包括历史,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所谓‘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或‘三分事实七分虚构’,说的便是这个意思。从中国文化的叙事审美角度来看,‘实’与‘虚’并非简单地处于对立状态,二者常有互补成分。”(11)
中国文言小说继承了史传的笔法,林纾用文言翻译西洋小说,也在西洋小说中感受到了与中国史书相通的文气。对于西方叙事文本时间视角的“用笔之不同”,林纾不作大的改动,而只是“微将前后移易”或者宁可“故仍其文”,用评注的手法加以说明。
也正因为采用了文言小说的笔法,林纾没有沿用当时盛行的白话章回小说中常有的对偶回目。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的体裁,实从他而始打破——虽然现在还有人在做这种小说,然其势力已经大衰……什么‘话说’、‘却说’,什么‘且听下回分解’等等的格式在他的小说里已绝迹不见了。”(12)这是作为文言家的林纾,坚持用文言传统对应西洋小说的必然结果,他在中西叙事的不同界域里找到了中西小说美学上的契合点,使他在异域文学的空间里得到了与中国文言小说相似的审美体验。中西文学作品中具有普遍性的那些特征使他跨越了不同文化精神、不同文学体系的域界,在文学“共性”上找到了中西融合的节点。
二、《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空间视角
小说中叙述者的观察视点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根据小说叙事的需要不断变化的。有时,小说叙述者视角的移动就好像电影里的连续跟踪拍摄,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从一个细节到另一个细节,Uspensky称之为“连续透视”(sequential survey)。(13)
原著Ivanhoe开头展示的空间视角与晚清中国传统小说的空间构建完全不同。原著开头用的是一般现在时,以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的眼光向读者呈示了历史事件发生背景的一幅鸟瞰图:叙述的空间视角从英格兰北部谢菲尔德到唐开斯特之间流淌的一条河流以及两岸茂密的森林开始,接着是对历史上发生在这一地区的主要事件的回顾和对当时社会背景的说明。原著在这一段叙述中,一般现在时的使用和第一人称全知叙事者的视角特别值得关注: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以回顾历史的姿态,用居高临下的空间视角展示了故事的大背景,体现了历史小说叙事规模宏大的气势。而小说开头一般现在时的使用,又将叙事者置于小说所要描述的历史事件之外,使叙事者和小说陈述的事件之间暂时产生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这样小说开头对该段历史事件背景的评说就显得更为冷静和客观。紧接着,原著的时态和叙事视角都发生了变化:小说转而使用过去时态引入历史事件;同时继续使用第一人称全知视角,将叙事视角又拉回故事开头那片森林中的一个空间场景,聚焦于森林中两个人物的外貌特征,但此时,这两个人物尚无名无姓,叙事者直到后文才对他们的姓名和身份进行介绍;接着又以这两个人物的视角引入他们所看到的一群过路人,小说叙事由此展开。
可见,小说原著开篇的场景呈示采用了“连续透视”的技巧,仿佛电影中的长镜头,先展示一个大全境,然后把镜头逐渐推近,最后聚焦于对人物外貌的近镜特写。这种空间场景的推进和切换,由宏观到微观,把读者引入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体现了历史小说场景恢宏的特点。
小说文本所呈示的场景、场景之间的转换以及种种叙事细节都有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对构建小说的审美内涵起着关键作用,小说的艺术魅力也正源于此。在译本中,林纾依照原著的信息传递顺序,以和原著相同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呈示了小说的开头;并基本保留了原著开头的全部信息,对故事发生的背景作了详尽交代。林纾的这种翻译方法对于晚清小说艺术形式来说,是一种超越传统的大胆引进。因为:直至五四,中国传统小说中场景的描绘和展示往往是通过内在于作品中某个人物的眼光来展现的,而这种通过外在于作品的全知叙述者来透视小说场景的写法在当时主要是西洋小说的特点。另一方面,这种在小说开头对背景的详细描写、对故事氛围的刻意渲染,在中国小说传统中是十分稀有的笔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洋小说开始译入中国时,译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作品开头的背景、自然环境描写删掉,而代之以‘话说’、‘却说’,随之即进入故事情节的描写”(14)。《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对小说原著开头连续透视叙事视角的传译,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本空间体验,感受到异质文学作品的审美特点。
三、《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心理视角
原著Ivanhoe的整体叙述视角是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且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时而闯入文本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说。原著全知叙事者的视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叙事者以全知的姿态对小说中的叙事场景进行自如切换,对小说人物的心理进行详细的呈示;(2)在原著的不少章节中,全知叙事者直接“闯入”文本,插入评注性语言,对小说情节发展进行评论性干预;(3)原著每章开头的章首引语也表明全知叙事者的存在。
在译本中,林纾基本保留了原著的全知视角,这通过前文的分析也可以洞见;从译本第2章中的“今余书当转叙此骑士矣”第10章中的“余书此时,将别叙淑杞城外一精丽之屋,此屋即以撒及其女之居停家也。”等例子中均可看出,林纾在译本中保留了原著叙事者在文本中的闯入性评介,同时也保留了原著的叙事视角。尽管如此,林译本中的叙事视角也有不少地方与原著的视角不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原著中每章开头都有章首引语,这些引语大多源于欧洲经典文学如荷马、席勒、乔叟、莎士比亚等的作品,且这些引文的体裁丰富多彩:既有语言朴素的民谣,也有辞藻高雅、音韵讲究的诗歌、戏剧独白等。从文体上看,这些章首引语是小说高雅格调的表征,体现了小说在英国作为主流文学的品味,也展示了作者的博学和才艺。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这些章首引语不仅体现了全知叙述者的视角,而且起着奠定小说基调的作用,启引读者对各章主要内容的领悟:它们可能是对各章内容直截了当的阐释和总结,也可能提供一种类比、暗喻、幽默、或反讽等等。但对于中国小说传统,“章首引语”无疑是一种陌生的文体手段,林译本删除了所有的章首引语,使小说全知叙事视角的表征减少了一种途径,也删除了原作者贯通古今的历史视野,削弱了历史小说的恢宏气势;同时还从某种程度上部分删除了小说中暗喻、幽默、或反讽的语气,使小说在文体风格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在译本中,林纾通过增补的方式,插入了不少对当时英国历史背景的解释,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这使译文小说结构在原有的全知叙事和叙述者闯入性评论的层次上,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即译者的评论。如第3章中对“宵禁”的解释:
原文:Oswald the cupbearer modestly suggested,“that it was scarce an hour since the tolling of the curfew;” an ill-chosen apology,since it turned upon a topic so harsh to Saxon ears.(15)
林译文:侍酒者为沃司华,进曰:“为时未晚,灭灯钟初动逾时耳。”灭灯钟,脑门豆虐政也,为撒克逊人所不愿闻。(16)
“灭灯钟,脑门豆虐政也”显然是林纾根据原著的历史背景,为译文读者进行的增补性解释。又如第41章中译者的插入性评介也显而易见:
原文:“King of Outlaws,”he said,“ have you no refreshment to offer to your brother sovereign? for these dead knaves have found me both in exercise and appetite.”
“In troth,”replied the Outlaw,“ for I scorn to lie to your Grace,our larder is chiefly supplied with——”He stopped,and was somewhat embarrassed.
“With venison,I suppose?” said Richard,gaily; “better food at need there can be none——and truly,if a king will not remain at home and slay his own game,methinks he should not brawl too loud if he finds it killed to his hand.”(17)
林译文:“汝真盗中之王,不审将饵与否,可出与王之兄弟共之。盖王饥,向盗乞食也。”骆宾荷德曰:“臣每行,辄囊鹿脯。”语时甚愧,盖国制非贵阀有采地者,不能飨有鹿脯。骆宾荷德之脯,盗脯耳。李却曰:“鹿脯大佳,汝杀而食之,省我自射矣。”(18)
译文中的这些删减和增补,使读者感知到译者在文本中的介入。林纾对小说视角的这种操纵,如果站在原著的立场上看,无疑是林译小说“失”的一面,它使译本心理视角有悖于原著;但如果站在译本的立场上看,这种删减和闯入性注释无疑给当时刚刚“开眼望世界”的中国读者解读西洋小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便利,应该说这也是林译小说在当时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四、《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观念视角
文学语篇是一种社会交往,文学形态不能游离于它赖以生成的社会文化气候和思想意识形态。小说文本的语言背后隐含着大量的意识形态信息,通过对原著和译著观念视角的分析,可以看到原作者和译者在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下的价值取向特点,看到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结构差异。在林纾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在很多方面都相互冲突。在当时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以林纾为代表的旧式文人开始怀着新奇的眼光“开眼望世界”,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观念,既有无意的误读和曲解,也有有意识的操纵。他们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坚守本土文化的立场,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应对西方文化观念,在译介西方小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用本土文化的意识形态来解读西方的思想观念,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文化操纵。
在译本中,林纾使用了大量的归化策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对应西方的意识形态。这从林纾对原著中几个比喻的译法可以看出:
原文:“Come on,Jack Priest,” said Locksley,“and be silent; thou art as noisy as a whole convent on a holy eve,when the Father Abbot has gone to bed……"(19)
林译文:洛克司列曰:“汝呶呶何为?譬之老僧入定,小沙弥翻跌几案矣……”(20)
在林纾所处的时代,基督教已传入中国,但并没有像佛教那样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相融合。对原著中众多的基督教词语,林纾虽然予以了部分保留并遵从约定俗成的译法,如“天主摩西”、“亚伯拉罕”、“亚伦”等,但更多的是采用了归化的译法,把基督教特有的概念归化为具有道教、佛教色彩的表达。小说中多次出现的sir被归化为“老子”,咒语By St.Dunstan归化为“天乎”,hermit归化为“道人”,chapel归化为“小庵”,pilgrim归化为“进香客”,convent归化为“庙”,为死者的祷告则归化为“念经为亡灵超度”等。这些都体现了中西神灵观念、人的自我意识、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认识差异。归化方法的使用使译文更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充分体现了林纾的读者意识。
小说第11章中的一段译文颇能体现译文与原著在观念视角上的差异性:
原文:The Disinherited Knight was filled with astonishment,no less at the generosity of Rebecca,by which,however,he resolved he would not profit,than that of the robbers,to whose profession such a quality seemed totally foreign ….and the faithful Gurth,extending his hardy limbs upon a bear - skin which formed a sort of carpet to the pavilion,laid himself across the opening of the tent,so that no one could enter without awakening him.(21)
林译文:“无家英雄闻之,大诧,以为吕贝珈美人之身,任侠如是,余英伦男子奈何受之;且绿林之盗,惟财是耽,胡以得此巨金,乃仗义释我奴子。……哥斯则犬卧于亭上熊廊中,以备不虞。”(22)
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人们意识中依然保留着封建礼教和等级观念,父子、君臣、长幼、主仆之间恪守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及行为准则,这种意识在林译文中时有体现。就以上述这段译文来说,原著中的Gurth虽然是骑士的忠实仆人,但原著上下文中始终以名字Gurth出现,而林纾译文中的“奴子”反映的是中国封建体制下主仆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原文描述了仆人伸直四肢仰躺在门口承担警卫职责,其行文信息很显然是着意于仆人的忠心和警惕,而林译文中的“犬卧于”所隐含的“奴才”、“奴性”喻义是不言而喻的。
又如在小说第35章,译文和原文的观念视角差异也显而易见:
原文:They passed each other,if they chanced to meet,with a slow,solemn,and mute greeting; for such was the rule of their Order,quoting thereupon the holy texts,“In many words thou shalt not avoid sin,” and “Life and death are in the power of the tongue.”(23)
林译文:“二人相遇,初不交言,点首而过。寺中戒律,谓多言多戾,百凡之祸,均自口出(此语甚类宋儒之言)。”(24)
原文中的“Life and death are in the power of the tongue.”出自《圣经·旧约》“箴言”第18章:“Death and life are in the power of the tongue,and those who love it will eat its fruit.”(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子)这句话体现了基督教为人处世的思想。人们的话语可以为生命带来祝福,也可以带来诅咒,因此人们要谨慎自己所说的话,对他人要多说充满爱心和美好祝福的话语,因为有一天将会收成自己话语造成的结果。《圣经》中有多处经文均指向这一观点:“A wholesome tongue is a tree of life,but perverseness in it breaks the spirit.”(温良的舌是生命的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Pleasant words are like a honeycomb,sweetness to the soul and health to the bones.”(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Let no evil talk come out of your mouths,but only such as is useful for building up,as there is need,so that your words may give grace to those who hear.”(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I tell you,on the day of judgment you will have to give an account for every careless word you utter.For by your words you will be justified,and by your words you will be condemned.”(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25)
可见,原文中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多言于赎罪无补”强调的是言辞的力量、言辞对于自己和他人生命可能造成的危害,体现了中世纪圣殿骑士依照基督教教义苦行修炼的严格纪律。而林译文“百凡之祸,均自口出”,虽然也强调言必谨慎,但其观念指向、文化内涵和原文是截然不同的。它说的是在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人们没有话语表达的权力,言辞不当或不慎可能导致杀身之祸,故而从趋利避祸的角度告诫人们要言语谨慎。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来解读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林纾,在译文后采用了夹注的形式,将原文所述内容与中国文化中孔子的“慎言”观进行类比:“此语甚类宋儒之言。”
小说是对社会文化的一种虚构,是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而不谙西文和西方文化的林纾译介西洋小说则是对西方社会的一种双重虚构。林纾的译本向读者展示了他的西方想象,这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流,在这中国传统遗绪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对话中,体现了陈旧传统下新思想的躁动,也体现了新旧思想的交锋。
对勘原著Ivanhoe,分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在空间视角、时间视角、心理视角和观念视角四个方面的叙事文体特点,可以管窥林译小说如何跨越中西迥然不同的叙事形态,使西洋小说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并对后来的一代作者产生影响。清末民初社会文化巨变背景下的林纾,凭借其古文修养,用中国经验对应西洋小说文体、用史传眼光阐释西方小说话语结构,其本意难免有削足适屐之嫌,但结果却在中西叙事的不同界域里找到了美学上的契合点,使他在异域文学的空间里得到了相似的审美体验。因此,林纾在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和小说叙事成规的框架内,赋予西洋小说一种全新的文本形态。林译小说既保留了中国文言小说的文体特征,也吸纳了西洋小说的话语特征,使译本在文本结构和话语方式上具有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林译小说的价值也正在于:他把小说翻译置于本土读者的尺度之下,同时又向本土读者示范了西洋叙事形式。
在翻译过程中,译本通过其形式再度产生新的文本意义,影响读者的审美品位,影响译入语国家的文学形态。西洋小说形态通过林纾的译介对中国传统小说艺术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林译小说从主题内容到文本形式两个方面推进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变革,催化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注释:
①见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李欧梵:《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Simpson,P,Stylistics:A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4,p.2.
③Toolan,Micheal,The Stylistics of Fic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0,p.28.
④(13)Simpson,Paul,Language,Ideology and Point of View,London:Routledge,1993,pp.11-12,60.
⑤⑦⑧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版社,2003年,第39,49,38页。
⑥⑨(16)(18)(19)(22)(24)[英]司各特(Scott,W):《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9,1,18,214,177,61,179页。
⑩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11)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31页。
(12)(14)郭延礼:《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158页。
(15)(17)(20)(21)(23)Scott,Walter,Ivanhoe,New York:Bantam Books,Bantam Classic Edition,1988,pp.25,392,98,105,324.
(25)《圣经》简化汉字现代标点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Proverbs 18:21,Proverbs 15:4,16:24,Ephesians 4:29,Matthew 12: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