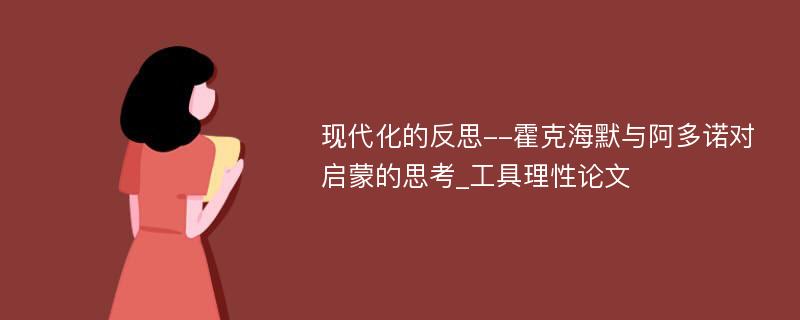
反思现代性——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论启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道尔论文,霍克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启蒙开启现代性。启蒙即对现代性的追求,是生成和导向现代性的教化性环节与精神。启蒙方舟将人摆渡到工业文明的此岸,人必因身陷工业文明的沼泽而迁怒启蒙。在这里,历史哲学关于进步代价或者历史必然性的说明和解释,丝毫不能减轻人们的愤怒。对启蒙进行反思与批判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思想界的一道引人注目的理论风景线。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就是这道风景线中的一处独特景观。
一
《启蒙辩证法》一开卷就将一个天启式的悖论置放在我们面前:启蒙总是致力于将人们从恐惧中拯救出来并建立理性的权威,然而,为什么经过启蒙的地球无处不散发着得意洋洋的灾难?人类被启蒙了,为什么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自拔?为什么人类并没有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的状态,反倒沉沦于一种新的野蛮状态中呢?换个问法可表达为,人类追求进步自由的理想何以变成了一场现代性噩梦?
以此为线索,《启蒙辩证法》率先从启蒙自我逆变角度审查了启蒙理性。
全部启蒙传统始终贯穿着去魅化努力,意在把人从一直压迫与控制他的神秘物那里解放出来。那种压迫与控制人的魔力无穷的神秘物就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界。启蒙的目的就在于去除自然界的魔力,用理性指挥失去魔力的自然界。开蒙的先哲,如被马克思称之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英国哲学家培根,为此而勾画的“剔除魔力”的纲领(启蒙的纲领),就是依靠知识使世界摆脱魔法。因为,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眼里,知识就是人进行统治的力量,“知识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页。)知识的真正的目的、 范围和本质就在于更好地支持并帮助人的生活。因此,理所当然地可以引申出这样的判断:技术就是知识的本质。一切像实体和质、活动和痛苦、存在和生成这样的概念都因其超验属性,而被驱逐出科学的领域;一切不符合计算规则和实用规则的东西都被归入想象的逻辑,从而与知识分道扬镳。因此,在启蒙的知识定义下,知识鄙视观念和思想。知识就是实用的方法,就是技能。“人们在研究新时代的科学时放弃了思维。人们用公式来代替概念,用规则和偶然性来代替原因。”(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页。)结果, 工具理性——它以定量定性、数学化、标准化、操作主义和整体控制的“科学态度”判断并榨取一切,规划并合理安排人类的日常社会生活——特立独行,成为神控世界的世俗化版本。经此转折,理性变成工具化、技能化了的理性,启蒙变成了蒙蔽,工具理性高视阔步,价值理性悄然引退。也就是说,理性已经严重消蚀,尽管它自以为自己以合理的逻辑分析超越了神话时代的混乱,但启蒙却使它再一次成为一种新神话的牺牲品。人们极为惊异地发现,在进步幻想支配下,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这种转化的内在制约而转到了它自己的反面。启蒙走上了自我摧残之路。
原本意义上的启蒙精神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真正确立主体地位的存在方式,它的根本意旨在于,使人类世界从巫术的、奇魅的或传统的束缚中觉醒出来,“解除世界的魔咒”,在经过启蒙的洗礼之后,人类得以自由地控制自然,地球遍燃自由的火炬,飘扬正义的旗帜,人类社会建立起合理的秩序。所以说,迈向理性启蒙的进步过程,就是人类征服自然,获得自由幸福的过程。本着这种天真而又稚嫩的幻想,近代思想家们将启蒙理性广义地理解为西方文明合理化的最高命令,把人之外的世界当做一个为了人的利益而可以任意加以盘剥的对象,进而挺立起科技理性,人一步一步走向对外在自然的恣意践踏,稳定地移向宇宙的中心。神话、宗教早先在大众意识里所占据的显赫地位逐渐为各种以人为主角的科学所取代,世界不再是人的“家”,只是人用来变化的材料。科学也不过是人类剥削自然的工具,人类要从自然学习的东西,就是如何控制、支配自然,以便役使自然。霍克海默、阿道尔诺一针见血地指出:“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象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独裁者只是在能操纵人们时才知道人们。科学家只是在能制造事物时才知道事物。只有这时,科学家才知道事物本身。科学家在运用事物的过程中,总是把事物的实质看成为他所掌握的实体。这种等同性构成了自然界的统一性。”(注: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 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7页。)又说:“启蒙的实质, 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人们总是要进行选择,要么使自然界受自己的支配,要么使自己从属于自然界。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的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8页。)
“新的野蛮状态的种子”导致的更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启蒙从对自然的统治必然衍生出对人的统治。因为,对自然界不断加强的统治意味着人同自然的异化,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对自身控制方式的变化。启蒙理性在提高了人对自然界的统治能力同时,也增强了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力量。“好事善行都变成了罪恶,统治和压迫则变成了美德。”(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6页。)结果,“对于统治者来说,人们变成了资料,正像整个自然界对于社会来说都变成了资料一样。”(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80页。)启蒙并没有给人们以一个自由、平等的合理的社会秩序,启蒙思想家所憧憬的理性王国在现实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被击碎,原本是为了解放人的启蒙理性现在却变成了人类主体奴役自然和自我奴役的工具。通过启蒙,人的灵魂脱离了蒙昧,然而却又可悲地置身于工具理性宰制之下,物欲的大众宁愿以精神的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因而丧失了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于是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进步的向往变成人们对权威和暴政的温顺服从,以致高度发达的理性技术管理被用来实现最大规模的、最无人道的非理性目的。这样,清醒的人们看到,“技术世界的理想、废除自然,即彻底控制自然又反馈到人的身上:全面的剥削作为‘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在被规定为是必然永恒的自然的剥削中只能坚持剥削的本性,‘即虚假的绝对,盲目的统治的原则’,并发展为一切社会形式的统治工艺学。”(注: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89页。)也就是说,启蒙造就了一种新的统治工艺学, 并且使这种统治的工艺学排除了一切法则。新的控制,支配方式不服从理性,它嘲笑任何爱恋真理的思想,启蒙理性因此彻底放逐了解放的可能性。启蒙后的人类从一个黑暗走向另一个更大的黑暗。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指出:“冷酷无情的社会借助这种带有麻醉剂的田园生活,使受奴役的阶层承担起他们不能忍受的苦难,而不再有维持自我生存的理性。实际上,这种田园生活仅仅是一种幸福的假象,让人麻木不仁地度过困苦的生活,象动物一样地存在着。”(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56—57页。)
一旦完成这种转折,启蒙就戏剧性地回到它出发的原点:启蒙做着“去魅化”努力,它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而粉墨登场的。然而,它本身却又成为一种新的神话,或者,更明确地说,神话与启蒙理性同源,都是人惧怕自然的产物。因此,启蒙理性的最终归宿只能是神话意象。就两者表达的观念本质而言,启蒙理性和神话的区别,人在这两种话语系统中位置的差异,等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只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和控制自然及人,并在摧毁旧的直接统治权的同时,又在新的联系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所以,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说:“在启蒙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有一定的理论观点受到毁灭性的批判,而只存下来一种信念,直到精神的概念、真理的概念,甚至启蒙精神的概念变成了泛灵论的巫术。神话中的英雄毁灭,从寓言中编造出来的逻辑结论所遵循的命中注定的必然性的原理,不仅支配着一切,成为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规则,西方哲学的各种理性主义的体系,而且本身也决定各种以神的等级制度开始,并通过神的朦胧怒斥真实的弊端,作为同一内容的体系的结论。正如神话已经进行了启蒙,启蒙精神也随着神话学的前进,越来越深地与神话学交织在一起。”(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页。)
历史就是这样使没有神性(尽管人们时时渴盼拥有一种神性)的人类再一次陷入难堪,而刚刚在某种自信中昂起头的人又在这种难堪中品尝到失望的苦涩。人类辛勤造出的“现代性骏马”却在一种可怕的魔法操纵下向着相反的方向迅跑。在这种底色下,映照出来的只能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及悲观的图画:“今天,恐惧和厌恶,被嘲弄和厌恶的特征,可以看成人类发展过程中强大进步的标记。从厌恶粪便和人肉,到蔑视迷信狂热、懒惰、精神上的贫困和物质上的贫困,推行着一条变成真正的和必然的恐惧的行动方式的路线。每一步都是一个进步,都是启蒙精神的一个阶段。但是,一切早期变化,从早期泛神论到神话,从母系制度文化到父系制度文化,从奴隶主的多神论到天主教的教权等级制度,用新的、即被启蒙的神话学代替了旧的神话学,用一大群神代替了母系制度的女首领,用对羔羊的尊敬代替了对死者的尊敬,在具有启蒙精神的理性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客观的、在事实中有论据的赋予,都成了神话学式的。”(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启蒙自身不倦的自我摧毁,已迫使思想放弃对习惯的时代精神倾向最后的轻信。启蒙已将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暴露给世人。
二
按照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的分析,人类在现代性计划的初期面对着两种启蒙精神:一是致力于改变人类受奴役状态的人文理性;一是用以度量并驯服自然的工具理性。“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同时要求天赋人权和科学进步。在他们那里,自由、理性、社会公正和自然秩序和谐一致,基本上是一码事。然而工业文明的发达打破了这种和谐一致。自由主义短暂的、相对平衡的统治不得不让位给一种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它以定量定性、数学化标准化、操作主义和整体控制的‘科学态度’判断并榨取一切,扬言它能以精确有效的手段研究并处理人类一应事务,从个人生活,社会福利,国际争端到种族优化。这种‘启蒙意识形态’不顾一切地推进,‘将其遇到的每一种精神抵抗都转化为自身的力量。’当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与科技发展过程中赢得压倒性统治地位后,就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中‘技术统治及操纵它的社会群体便能以极大的优势去管理人口的其它部分。’”(注:赵一凡:《美国文化批评集》,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6页。)于是,工具的、主观的、操纵的理性堂而皇之地成为工业化社会发展新的行为方式的智慧之根,而理性自身原初的内容却被劫掠一空。
当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理性的工具属性转成终极目的时,完整的启蒙精神就因属人的感性价值对同样属人的理性价值的遮蔽而发生分裂,或者说,启蒙精神中价值资源、人文理想就必然要失落,启蒙理性就只能堕落成为一种“合作协调的智力”。它失去了崇高,它的价值由对人和自然界的操纵来衡量,它的活动的合理性就仅仅取决于它是否为某一目的(商业的,保健的,娱乐的等等),它的任务就是提出一种计划或一种行动框架,它不寻求那种与生命和自然的和睦相处的方式,它更不会提出一个“真理的”和谐世界的可能谋划,因此,它只是把世界当做工具,用来上演自己征服其的史剧,而这幕史剧只关心实用的目的,一切以‘导演’这幕史剧的人的用途为转移,所以,在这幕史剧中,事实与价值是分离着的,重要的是如何去做,而不是应做什么。于是,工具理性以及它的功用在由启蒙所肇始的现代文明进程中,成为“压倒一切要考虑的事情”,成为实现对自然和对人进行控制的思维构架。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启蒙之走上自我摧毁不归之途,启蒙精神之发生奇诡的“魔法下的倒退”,启蒙之打上与自然相疏离的原罪痕迹,全部症结在于,启蒙精神发生了裂变,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手段—工具性行为被作为目的提高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是更高层次上的自我异化,它成为隔离天堂语言和其人间副本的栅栏。
法兰克福学派十分看重对工具理性的揭露,这是他们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石,是他们进行现代性反思所发现的充满忧患亟须颠覆重建的地方。因为,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病象都可以说是工具理性渗透的结果,是工具理性增长所带来的副产品。从反思启蒙角度看:
——人与自然的分化根源于工具理性。启蒙的意志是“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启蒙思想所追求的是一种统治和奴役的关系。启蒙打倒了统治世界的上帝,解放了人。但是,它又使人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人类的理性一步一步走向对外在自然界的剥夺。处于工具理性支配下的人类已不再能够和自然界做获益匪浅的对话,只能对被自己肢解的“资源库”发出一种无意义的独白。
——新控制逻辑或新统治逻辑根源于工具理性。西方现代性计划实际上崇尚一种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工具理性,它完全荡涤了天赋人权和自由理想,而代之以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和整体化,结果,社会在不断增长的技术积累中再生产自身,生存斗争和人对自然的开发变得更加科学、合理,更高的生活标准逐步得到实现。于是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产生了。人们情愿以内在精神的沉沦来换取外在物质生活的丰裕。结果,“技术创造的缓和条件愈多,人的精神肉体就愈受严格控制。”人放弃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而在权威和暴政面前变得温顺起来。正像霍克海默所说:“……当技术知识扩展了人的思想和活动的范围时,作为一个人的人的自主性,人的抵制日益发展的大规模支配的机构的能力,人的想象力,人的独立判断也显得缩小了。启蒙精神在技术工具方面的发展,伴随着一个失却人性的过程。这样,进步就有要取消它应实现的真正目标——人的思想的危险。”(注:Horkheimer,Eclipse of Reason,New York,1974,P.V—Vi.)据此, 社会在稳定进步的动态外表下强化了它静止不动的控制调节系统。
启蒙中死去的和行将死去的,已十分清楚。只要启蒙话语仍然拒绝使用“神性语言”,听任数学化的思维程序操纵现实,那么,我们面对的就只能是扰乱而不是慰藉。启蒙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智慧就只能是一种“忧郁的智慧”,而决不会是“快乐的智慧”。
三
现在,我们已十分清楚,启蒙原本以消除蒙昧,传播知识,在地上建立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为己任,它是一种力求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和确立人之主体地位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为启蒙所奋力推出的新观念无非是(工具)理性、进步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启蒙思想家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完全笼罩在这些观念的阴影之中,“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注: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透视启蒙,人们经常看到的是,科学毫不留情地将神学宗教从学问之至上王位上拉下来,自己欣然为自己加冕,将学问之至尊的称谓授给自己。现在,科学不仅许诺要给人类一个美好的世界,而且对精神归宿亦加以承诺。原本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凸现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新世界观的合理性,它因此保持着对一切自称是权威的东西的激进批判态度。然而,现在它却因为给自己加上太多的重负而被限制起来。它失去了批判的锐气,并因此没有了精神。它所剩下的唯一功能就是为启蒙幻想提供“宏伟叙事”和“合法性证明”。用近代大哲培根的话说就是,科学进行着一种与宗教相同的努力,即补偿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所受到的伤害。人由于堕落而失去了清白和对创造物的统治,不过失去的这两方面都可以部分得到恢复,依靠技艺和科学,人就能在上帝隐退之后君临世间。人乃万物之灵,虽然每个个体是注定要死亡的,但人类作为一个类却是永恒的,而且是宇宙间唯一的主体,居于宇宙的价值中心。英国著名科学家秦斯(J.Jeans )所说的下面一席话最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启蒙式的天语:
“我们不再相信人类命运是善或恶的精神或玩弄阴谋的恶魔的玩偶。没有什么能阻碍我们再次将地球建成天堂——除非我们自己(阻碍我们自己)。科学时代的黎明业已到来,我们已发现人类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是他灵魂之舟的船长。他可以掌握这船的航向。当然,他可以自由地驾驶着她驶入安全水域,也可以驶入险恶的地方,甚至撞上礁石。”(注:参见《场与有》第四辑,第32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然而,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曾阐述的那样,“20世纪将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打得粉碎。”(注: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人们早已看到,“在繁华、富裕以及政治权力的后面,西方社会经历着一个衰败及人性堕落的过程。”(弗洛姆语)于是,一部分人因为愤恨而转向野蛮,仿佛沉湎在怀旧情绪中诅咒科技理性就能够取消亚当和夏娃的罪孽;而另一部分人则因为警醒而走入沉思,他们的救世热情全部化为殚精毕思,别出机杼以拯救“达摩克利斯剑”下的人类。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显然属于后一类人。表面上看,他们对启蒙理性的分析并没有远离从罗斯金、卡莱尔那里延绵下来的对工业化社会或资本主义非人化倾向进行浪漫批判的传统。这一传统直到艾略特那里,仍表现为一种现代保守文化观,即认为整个西方文明正以资本主义价值观为楷模,实现自己世俗而功力至上的“资产阶级化”。但是,从骨子里看,问题却不那么简单。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拒斥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进步,承认它们的发展为建立一个更为公正自由的社会创造了宽阔的远景。对人类的进步持“前资本主义文化怀旧病者”的立场显然是不足取的。用这种话语解读社会批判理论,就可以看出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对启蒙的批判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在一个时代处于精神迷惘情态下,对支配时代的精神病症从建设性角度进行了诊断。法兰克福学派所极力争辩并要引起人们警觉的是启蒙精神内在的蒙骗和危险性质,即“人能将他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用来完全控制自然及其他人”;或者在启蒙过程中“将人的灵魂从愚昧中解脱出来却置于新的奴役之下”。
人们不难从工具理性、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启蒙的核心观念中导出宰制自然的思想。但是,从控制自然中发现对人的控制却是霍克海默的惊人之作。马尔库塞的学生,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W.莱斯(W.Leiss)在他的著作《自然的控制》中对此有过令人信服的剖析。 在莱斯看来,霍克海默论证了理性对外部自然的控制与它对内部自然的控制有着内在的联系。人追求控制自然进行得越主动,个人所得到的报偿就越被动;人获得控制的能力越强大,个人的力量与压倒一切的社会现实相比就更弱小。沿着这个思路,霍克海默把人类历史的三个特征即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和社会冲突联结在一起,并把社会冲突看作是连结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的因素。从冲突角度看,“由于企图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进行的斗争趋向于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范围转变。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开始经历一种特殊的冲突即普遍的全世界范围的冲突;一些远离权力中心地方的显然很小的事件都以它对全球利益平衡的可能的影响来解释。地球似乎成了人类进行巨大的自我竞技的舞台,人们为了实行对自然力的有力控制而投入了激烈的纷争,这似乎确证了黑格尔的历史是一个杀人场这句格言的真理性。”(注:W.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在这种情势下,非理性的机巧必然报复人,在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人成了自己造物的奴朴,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转化成对人的政治控制。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这历史发展中逻辑地汇聚在同一地平线,人成为控制的真正对象。启蒙理性终以非理性的超凡魁力而告终,知识与权力以控制为目标而得以整合,伴随着机械技能的日趋完善,社会终将一切归结为数量功利概念,并将整个知识文化系统简缩至一个共同的尺度。秩序的权威由此确立,它将用高度发达的理性管理和技术效率实现不容理性合理思考的非理性的目的。启蒙理性终于走向了一条与自己纲领相逆反的道路,它在自己所崇尚的理性设计的诱惑下,逐步暴露自己蒙骗的本性和奴役的本质,彻底瓦解了自己的合法性。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由此圈定启蒙所设计的现代化纲领为资本主义文化陷入精神分裂的标志,它所建立的“宏伟叙事”和“合法性神话”也因此俱告破灭。一时间,西方人被驱赶到一个真空地带,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在思想中憧憬理想主义和超验前景的权利,也在现实中丧失了捍卫或反抗任何攻击性学说的理论基础,人类陷入深深的人为的“天谴之灾”的恐惧之中。这是世纪初就蕴酿发端的危机警示的社会学深化,是展开新一轮人类自我拯救之前的思想审视。在这种审视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尽情展现着“天启圣哲”的魅力,宣告一场反抗新的控制形式或奴役形式的观念战争已经开始,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拯救所谓的“拯救者”,即对启蒙进行再启蒙。
标签:工具理性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霍克海默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现代性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神话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