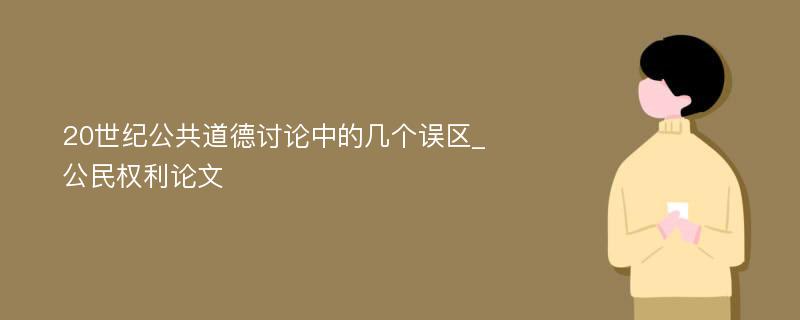
20世纪公德问题探讨中的几个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公德论文,误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8)02-0053-06 [收稿日期]2007-10-16
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起飞与社会的发展,公德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公德对于社会发展之重要以及国人公德意识之薄弱,似乎也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一致看法。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梁启超等人就已经揭示了国人公德意识薄弱的现状和现实。但是,对于国人公德意识为什么薄弱以及如何才能有效地建构社会所急需的公民道德问题,中国思想界却似乎是一再地走入误区,并且由一个误区走进另一个误区。这是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的,因为只有深入展开对其薄弱之真正原因的探讨,才能够有效地确立建构社会公德的基本前提。
一、在中西横向比较背景下对道德的二重分划
公德与私德的概念及其划分都起源于梁启超,他在20世纪初开始谈论公德时,实际上是在中西横向对比的大视野下从日本引进了公德概念。因为从传统的角度看,道德是无所谓公私的;只有引进了公德概念并且以之作为社会需要和发展的标准之后,传统的道德才被冠以私德的称谓。
1902年,梁启超首先从“我国民所最缺者”的角度提出了公德一说。在《论公德》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1](P553)。显然,就问题的提出而言,梁启超当时确实是从国家振兴与民族崛起之急需的角度提出公德概念的。
但梁启超的公德概念又是从中西横向比较的角度提出的,并且也是由此来说明公德与私德的差别以及东西方不同的道德概况的。他分析说:“道德之本体一也,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1](P554)。由于梁启超是在中西比较的背景下形成对道德之二重分划的,所以,他也就反过来从公私道德之不同标准的角度来说明东西方的道德状况:
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
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
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微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1](P554)。
在梁启超关于道德的二重分划中,其急于建立公德之目的自然不待言说,但这一划分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从公德概念的提出到对道德问题的二重分划,其实都是在中西对比的大前提下作出的。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横向比较固然有其不可避免性,但
这一比较同时也开启了一个负面的先例,这就是以西方的公德为标准,并且坚持以西律中;而在他对道德形成公私二重划分的同时,他又明确地以“新伦理”和“旧伦理”指谓东西方的道德,由于西方长于公德,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学习、效法的榜样;而中国则只有“旧伦理”且又长于私德,因而也就成为反衬和被批评的对象。其次,由于西方以公德见长,因而与之对应的东方,其所谓道德也就只能成为个体私人之德了。对 20世纪的中国来说,这一开端也就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一方面,在整个20世纪,“公德殆阙如”往往成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言以蔽之”;另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民族厄运,似乎也都可以从其“重私德而轻公德”的角度作出说明了。
当然,在梁启超的视野中,其所谓中西、新旧以及公德、私德其实并不带有明显的价值褒贬意味,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中性的划分。所以,在《论公德》一文中,他同时就明确指出:“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即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1](P554)。这说明,梁启超虽然对应于时代之所需而提倡公德,但他并不轻视私德。一年后,他又专门作了《论私德》一文,认为“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公德者,私德之推也”[1](P622)。凡此都说明,梁启超虽然提倡公德,但却绝非藐视私德,他甚至还认为,“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因为在他看来,“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欠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1](P622)。这些看法说明,梁启超不仅不轻视私德,而且对私德之于公德的前提基础地位也是认识得非常清楚、非常到位的。
但是,由于梁启超的研究是在中西横向比较的背景下展开的,而且他对中西道德之“新旧、公私”的划分也必然含有一定的价值评价意味,这就开启了一个具有明显的负面意义的先例。如果说“中西”本身并不带有褒贬意味,那么“新旧”、“公私”这些称谓却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当时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在经过《天演论》的传播,社会进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对传统道德之“旧”与“私”的定位也就必然使其成为需要唾弃的对象了。加之其同时又以“新”冠名公德,所以虽然其本意是为了探讨“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但由于他同时又以“知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1](P556)为号召,如此一来,中国传统的旧道德,作为一种已经过时的私德,也就只能成为唾弃的对象了。
梁启超的这一开端,当时就遭到了他的长辈学人——《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的明确批评。对于梁启超的一系列“维新”言论,严复当时就不无嘲讽地说:“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2](P645-646)。而在梁启超的鼓动下,人人以喊口号、搞破坏为能事,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至挽近中国士大夫,其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奉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2](P648)。显然,这就是从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国人的精神状况,至于其对道德问题的认知,自然也就含括其中了。
正因为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在“五四”前夕,蔡元培恰恰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成立了“进德会”,这等于是在当时万众瞩目的“德”、“赛”“两先生”之外明确地提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莫姑娘”的问题。当然,对于“进德会”的具体主张,人们也尽可以从新道德——即所谓公德的角度作出诠释,比如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吸烟甚至不食肉,等等,但问题在于,当蔡元培创立“进德会”时,恰恰是从被人们所遗忘、所忽视的“旧道德”之“私德”的角度入手的。所以,在创会缘起中,蔡元培就明确写到:“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曾不足措意,是误会也。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疫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3];至于其章程中的所谓“三戒”、“五戒”乃至“八戒”,也无一不是从“私德”入手的。这说明,正因为梁启超是从所谓“新旧”、“公私”的角度划分中西方道德的,因而虽然其本人并没有轻视私德的思想,但在那个急风暴雨的年代,却无疑带来了轻视甚或唾弃私德的影响;不然的话,就无法解释蔡元培创立的“进德会”一事。这同时也说明,在中西横向比较的背景下,以“新旧”、“公私”的方式划分中西方道德,其实就是20世纪国人关于公德探讨的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二、在古今、公私对立背景下的“文化革命”
“五四”以后,随着激进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对公德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也就演变为对“私德”的讨伐了;而所谓的“旧道德”、“私德”等等,实际上也就成为全民争相唾弃的历史垃圾了。这一点又以“文化大革命”为典型表现,因为当时奉行所谓“不破不立”的逻辑,认为“破字当头,立字也就在其中”,
因而当时所谓的“立”,主要也就集中在“破”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列举“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个典型口号就足以说明了。其中第一个口号就是所谓“与一切旧的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这其实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理由,而其间从“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直到“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等等,所坚持的方向也就是与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彻底决裂”,或者说是完全“对着干”的方向;而其中一个具有明显的负面意义的称谓,就是所谓“历史垃圾堆”的说法。言下之意,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统统要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并且也要从根本上断绝其能够存在的任何理由。第二个口号叫做“斗私批修”,其具体落实就是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如果说“彻底决裂”本身就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那么“斗私批修”则标志着对这一方向的具体落实,至于“狠斗私字一闪念”,则是当时任何一个个体“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日常功课——当时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其实就是要求将一切带有传统性质的所谓“旧”和带有个人性质的所谓“私”连根拔掉。关于这一段经历,亲历者自然耳熟能详。笔者之所以要列举这一段经历,绝不是对我们民族所经历的这一段苦难耿耿于怀,而是因为直到今天,为我们制造这种种苦难的思想逻辑并没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又将“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口号归结为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和王阳明的“一念发动出,便即是行了”,于是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又一轮讨伐运动,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而其典型表现就是当时的《河殇》,其指向就是要将传统文化——所谓“黄色文明”连根拔掉。实际上,将“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归结为宋明理学的影响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赖账”说法。因为宋明理学既不“极左”,也不排斥个体位格,反而处处强调个体精神的挺立与担当;其所谓“禁欲”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天理对人欲的驾驭和疏导,以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的意思,这正是沿着提升道德的进路前进的——准确地说,也就是沿着所谓“私德”的进路前进的。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沿着破坏和摧毁道德的进路来运用这些口号的,这怎能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呢?而从十年“文化大革命”到80年代的“文化热”,谁又敢讲道德呢?在“文化大革命”中,讲道德(私德)就必然要面临阶级的“专政”;而在“文化热”中,讲个人道德则只能被视为保守而又虚伪的“伪道学”。
最为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国人的个体位格,所以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不再说“我”,而只会说“我们”;即使是谋求“个人”利益,也一定要打着“我们”的旗号进行。这样,国人一方面变成了绝对依赖外在“形式”的所谓纯“质料”——没有也不允许有任何内在的依据和主宰,从而完全听命于长官意志;但另一方面,在追求个人利益——真正私我的利益方面,则又处处表现出精心算计、无孔不入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钻营精神。自然,这就完全是以负面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了。这既是“文化大革命”留给国人的重要“遗产”,同是又是国人缺乏最起码的责任、义务包括所谓公德意识的思想文化根源。
除此之外,“文化大革命”的另一项重要“遗产”就是所谓“不破不立”,从而又衍生了所谓以“破”为“立”的“对着干”逻辑,这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一切“激进”、极左思潮的渊薮。比如说,在梁启超关于道德之新旧与公私的二重划分中,其本身不仅不具有相互对立的性质,而且从根本上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却一再地将对旧道德或所谓“私德”的讨伐作为建设公德的必要前提,这就成为梁启超所批评的“蔑私德而谬托公德”了。
再从整个民族精神的角度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所谓“古今、公私”之辨,实际上又已经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坐标了。所谓“古今之辨”正是“文化大革命”中“评法批儒”的理论标准,而所谓“历史垃圾堆”包括后来所谓“蓝色文明必将取代黄色文明”之类的说法,也都由此而来;至于“公私之辨”中的“私”,则正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遭到横扫、砸烂的所谓“封、资、修”所永远卸不掉的铁帽子。实际上,这也是贯穿20世纪国人思考问题的基本坐标,直到今天,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标准,实际上仍然是在继续沿用这种经过歪曲的“公私之辨”和“古今之辨”而进行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直接批评“私德”的现象——这并不是说“私德”不值得批评,而是因为在当时,只要带有“私”字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称“德”的资格,而只能成为无条件砸烂的对象,所以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根本就没有所谓“私德”之类的说法了。明白了这个道理,同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要从解放思想做起,而安徽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甚至就因为沾有“私”的形式,所以不仅要私下里偷偷地进行,甚至相互还都一定要按上手印,做好蹲大狱的心理准备。所有这些都说明,“古今之辨”中的“古”和“公私之辨”中的“私”在当时已经成为人神共愤的对象了。所以,在那一时期,虽然并没有对所谓“私德”进行批判,但实际上,每一个批判对象都和它有关;而且每一个批判口号也都可以置它于死地。
三、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
公德意识讨论中的盲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腾飞之势,社会也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是建立经济秩序的需要,同时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一定的公德作为精神基础。这时候,人们似乎一下子发现了整个国民道德素养的匮乏和道德滑坡现象,尤其是经常见诸报端的报道:某个人要跳楼自杀,而成百上千的人却在那里无所事事地围观甚或幸灾乐祸地观望;同时,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官场上的腐败又像流感一样四处蔓延;更让人感到大丢面子的是,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出国考察者,还常常受到所到地区各种各样诸如讲究卫生、不要喧哗之类特别提醒的“优待”。所以,历来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华民族,无论是对内还是在外,一下子成了一个没有道德、没有教养、缺乏基本礼仪文明的民族。这时候,人们又开始重新认识道德的巨大作用,于是也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国民道德素养的讨论。
但人们的思考坐标却并没有得到必要的澄清,甚至也没有弄清到底什么叫做公德,却依然沿着过去所谓“古今、公私”的坐标来讨论公德问题,于是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奇怪现象。比如,通过继续讨伐传统的私德以促进公德的建设,或者将国人公德的匮乏完全归罪于传统的私德,或者认为正是传统的“重私德而轻公德”妨碍了现代公德的建设,等等。而在这些批评中,关于传统道德的批评则具有特别典型的意义。
比如说,对于经济领域的犯罪现象——所谓腐败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法律制度问题,但我们的思想精英却将经济犯罪的原因直接追溯到儒家传统的血缘亲情,认为正是儒家对血缘亲情的过分重视而又没有倡导大义灭亲,所以才导致了大量的腐败现象;而被儒家尊为圣人的舜,其本人就是一个利用权力包庇其杀人的父亲从而陷于权力腐败的“始作俑者”。这等于是说,儒家传统的亲情道德——所谓“私德”本来就应当为现代的腐败负责;所谓研究也就是要对这种腐败现象认祖归宗,以说明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其来有自的。同时,这种理论还蕴涵了这样一种逻辑,由于儒学本身就带有腐败基因,因而只要儒学根除不了,那么腐败也就是无法根除的。显然,这是继续在“古今之辨”的背景下讨论公德问题;而传统的道德,既是现代的批判对象,同时又要永远为现实的罪恶负责。
还有一种探讨,即认为由于儒家的仁爱本来就是以差等之爱为前提的,而这又正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不平等并进而导致腐败的思想根源。所以,只有来自基督的“神爱”才真正表现着普天同一之爱,因而也只有建立在“神爱”基础上的“本相伦理学”才代表着真正平等的道德,所以,中国的出路以及公德的建设也就只能通过信仰上帝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进而也才能获得真正的普世道德。除此之外,这种观点还有另一种表达,这就是既然儒家传统的亲情道德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所有罪恶的根源,而这种根源又以父子兄弟关系为核心,所以我们就必须先将儒家所重视的父子兄弟变成“路人”、将其关系变成“路人”关系,然后再通过所谓利益的大小和力量的强弱之间的对比、权衡与服从原理,如此就能形成我们所需要的公民道德。显然,这又是在“中西之辨”的背景下讨论公德问题。
再下来的探讨就几乎说不上探讨了,只不过是高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标准,并从这种标准出发,不断地对各种不道德现象表示强烈的道德义愤。而这种义愤,除了表示论者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并且也绝不混同于“缺乏公德”的芸芸众生之外,并不具有更多的实质意义。这又是所谓“公私之辨”的标准。因为这种标准实际上是先将一种绝对的大公无私视为每一个个体得以存在的先在前提,然后再以之裁定每一个个体的具体行为。大体说来,这几种说法基本上可以代表新世纪以来思想界对公德问题探讨的大致思路。
其实所有这些探讨,除了继续演绎梁启超的“中西”、“古今”和“公私”之辨外,并不具有更多的实质意义。而这些探讨的一个共同逻辑,就是以西律中,以今裁古,并绝对地崇公贬私。就其人文关怀指向而言,也许本身并无错误,但要害则在于其“不破不立”的逻辑,并且以对私德的“破”作为公德之“立”的前提和具体表现。如此一来,这三组“对子”中的“中”、“古”、“私”将再次成为被唾弃的对象;而在我们的文化精英看来,只有彻底唾弃了这些可以称之为“中”、“古”、“私”的东西,才是公德真正得以建立的前提。
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逻辑,并且还将彻底砸碎自己的脚作为自己真正能够站起来的前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理论,既不了解公德的性质,也不真正了解国人。从公德的角度看,它本质上只是一种对待、对等性的道德,其存在也主要表现于社会个体的“相互”关系中。对于这样一种道德,其性质诚如孟子所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4](《离娄下》)。那么,在这种“相互”和“对待”的关系中,究竟有没有底线呢?而其底线究竟又由谁来提供呢?这就只能是决定着人之为人的私德。因为正是人之为人的私德才能为群之为群的公德提供坚实的支撑,所以,梁启超当年说:“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矣”[1](P622)。因而,蔡元培明确批评那种“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曾不足措意”的看法是一种十足的“误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想通过讨伐私德、砸烂私德的方式建立公德,不正是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举吗?
再从中国历史来看,自从有王权以来,国人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自秦王朝以来,“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又成为历代帝王的基本国策,也是亿万臣民不得不遵从的人臣之道,如此一来,老百姓也就真正成为“草民”了。这种情形,诚如徐复观所言,“于是皇帝的崇高不可测度的地位,更由臣民的微末渺小而愈益在对比中彰著”[5]P(81)。而在皇权被无限拔高的过程中,臣下、草民也就愈益成为绝对依赖皇权的所谓纯“质料”了。在这种条件下,当国人根本就没有成为公民,并且也根本缺乏作为公民的自觉时,对国人责以公民道德的要求,不正是孟子所谓的“不教而诛”吗?
具体到社会秩序而言,公德显然属于权利与义务对等性的范畴,在公民的权利意识还没有得到普及之前,一味要求国民担负道德义务也正像根本就没有投入却期待产出一样不现实。在这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恰恰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在极左思潮横行、一切都听命于长官意志的年代里,老百姓食不果腹,面有菜色;但一当改革开放,真正赋予国民以经济自主权,整个国家的经济——从工农业生产到科学技术不就一下子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阶段吗?所以说,国民的公德意识、义务意识必然是随着其权利意识的觉醒而觉醒,并且也是随着其权利的提升而不断发展的。上述关于公德的探讨之所以陷于南辕北辙的境地,关键就在于所有这些探讨实际上都是脱离公民的权利意识来单方面责成公民的道德义务的。
四、公民的社会性地位:建构公德的真正基础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奋斗之后,为什么我们又回到了梁启超当年呼唤公德的出发点呢?当年梁启超呼唤公德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又呈现为“一盘散沙”、从而陷于任人宰割局面的时候,所以,梁启超才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的角度呼唤公德,在他看来,“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1](P556)但梁启超同时也已经看到,“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1](P554)。所以,在他看来,与其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公德,不如说首先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私德本身就已经堕落了;而私德堕落的根本原因,首先又是由于几千年专制皇权压迫的结果——正是专制皇权的压迫,既导致了私德的堕落,同时也就自然消解了公德得以建立的真正基础。
但在这一问题上,梁启超的认识与我们现代精英的思路却几乎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国民私德堕落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专制政体“陶铸”的结果,他引孟德斯鸠的观点说:“苟在上者多行不义,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贵族专尚诈虞,而平民独崇廉耻,则下民将益为官长所欺诈所鱼肉矣。故专制之国,无论上下贵贱,一皆以变诈倾巧相遇,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1](P623)。其实,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意思。这当然是私德堕落的一个原因。而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专制皇权是根本不容许其臣民真正拥有私德的,因为真正拥有私德的人也是绝对不会满足于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因为这是与其私德精神根本不相容的。但我们的现代精英却一致认为,正是儒家对私德的过分重视才挤压了公德的培养,所以要建立公民道德,首先就必须彻底摧毁私德。这简直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帮闲”理论。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皇权独占一切的时代,只有血缘亲情才为草民赢得了一息生存的空间;如果连血缘亲情也连根拔掉,这无疑是将所有的草民像沙土一样直陈于皇权的烈日之下,这也等于是以草民为纯粹的“质料”,从而将所有的能动性、主宰性拱手送于皇权。所以,虽然我们的现代精英继承了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说,但实际上却是反用其意的,甚至不惜以同室操戈的方式,将对私德的讨伐视为建立公民道德的必要前提。即使站在梁启超的角度看,这也完全是一种南辕北辙之举。
需要指出的是,在梁启超关于公德与私德的讨论中,他虽然正确地看到了公德的重要性,但他却将公德视为“新民”所由以出的前提,这就将这一问题及其关系给搞颠倒了。因为所谓“新民”(即公民)与公德的关系,总体而言当然可以说是相互生成的,但从根本上说,即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角度看,则必须是先有以权利意识唤醒公民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自觉,然后
才能形成对社会义务的担当;如果根本就没有权利的赋予却首先要求义务的担当,这除了继续败坏社会的义务之外,也根本不会有其他可能。也就是说,必须先有公民,然后才能有公德;或者进一步说,必须先有公民的权利,然后才能有公民的义务。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现代精英却一再表现了自己过人的“聪明”,他们一方面以对公德的呼唤为自己建构道德的高地,同时又以公德作为“炸弹”对草民进行居高临下式的轰炸。这就完全成为一种弱者谴责策略了。正因为是谴责弱者,所以既不会有任何风险,同时又可以表现自己的道德优势。但对于真正的公德建设来说,则只能成为孟子所嘲笑的缘木求鱼之举。
两千多年前,孟子关于“牛山之木”所以“濯濯”的分析正可以适合于我们今天对公德问题的讨论,所以,笔者特意引出这段话,以作为儒学研究者对20世纪国人公德意识薄弱之原因的看法: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4](《告子上》)?
在这里,牛山“濯濯”正可以代表国人公德意识薄弱的现实,但“濯濯”是否就是牛山之本性呢?在孟子看来,牛山其实正像所有的山林一样,“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但由于“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而孟子对“牛山”所以“濯濯”之原因的分析,其实也正相当于我们今天对国人公德意识匮乏的讨论。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反思我们一个世纪的“斧斤伐之”、“牛羊又从而牧之”在摧毁道德方面的负面作用,而只是一味地指责国人公德意识匮乏,这就像一味地以“斧斤伐之”、“牛羊又从而牧之”来对待牛山,然后又反过来以此谴责“牛山”之“濯濯”一样荒唐。而这种对公德薄弱的感慨、对传统道德的批判和对国人的指责,也就真成了所谓砍尽“牛山”叹“濯濯”了。
所以,对于当前的公德讨论与公德建设,笔者的结论只在于以下三点:首先,有私德然后才能有公德,因为传统的私德正代表着现代公德建设的文化根源和思想基础。其次,就具体的建设而言,则又必须坚持先有公民的个体人格,然后才能有公民对道德和义务的担当,因为个体人格正是所有的道德和义务得以落实的主体基础。最后,只有实现真正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的普及,才能真正形成公民自觉担当的义务和自觉遵守的公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