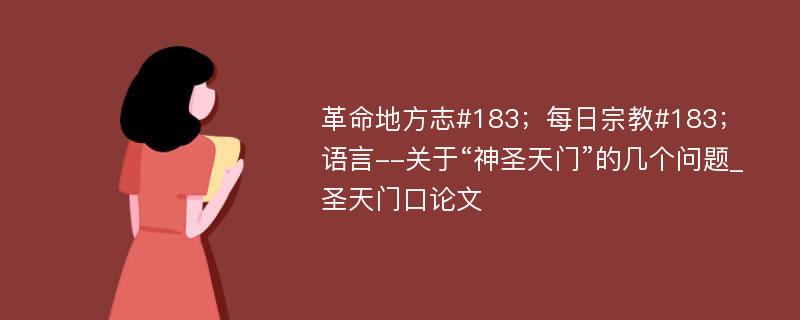
革命地方志#183;日常性宗教#183;语言——关于《圣天门口》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门论文,地方志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宗教论文,日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文学体裁的角度看,各种文学体裁在承载民族的生态和心态可能抵达的深广度上应该说是有区别的。19世纪之后,长篇小说作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体裁样态,在展现一个民族生存史和心灵史方面的长度和宽度、巨大和宏富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长篇小说从不掩饰它的史诗品格和历史意识。而且无论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还是福克纳、马尔克斯,凡是创作出史诗性长篇小说的作家都有着深刻的思想甚至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他们往往有一种长篇小说写作所独有的人格自觉,强调自己对人类和民族的担当。类似的自觉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有明显体现,像《白鹿原》、《尘埃落定》、《空山》号称民族秘史,《秦腔》说是给故乡树“碑子”。文学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现实,参与到广泛的历史建构。在这一系列的“史诗性”书写中,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无疑是一部有着自己信仰,并且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写作提供了新经验的代表之作。
《圣天门口》反思了辛亥革命到“文革”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塑造了傅朗西、董重里、杭九枫等革命者形象,它引起研究界的广泛关注。这中间,一些研究者从消解与重构的角度去阐读《圣天门口》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书写[1]。事实上,当刘醒龙面对20世纪中国历史去想象和书写时,自然存在着文学参与历史建构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像一些研究者所理解的,在作家对历史进行想象性重构之前一定存在着对历史的“消解”和“颠覆”。
这个问题,从1980年代乔良创作《灵旗》后就被提出来,到了后来的“新历史小说”,“解构”的历史观似乎成了一个很流行的看法。人们习惯认为,既然称为“解构”,称为“新历史小说”,当然就有一个“消解”和“颠覆”的对象,就有一个“旧历史小说”。而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因为频繁地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学书写,而常常在一些研究者的视野里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假想之“旧”。确实,《圣天门口》,还有《白鹿原》、《旧址》、《银城故事》、《花腔》、《笨花》、《第九个寡妇》、《生死疲劳》等,虽然它们都没有强调“重述”,但如果把它们放在整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上来看,它们又是各有母本的。这些小说“重述”的是已经被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像《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反复“述”过的中国近现代史。那么这些“述”和“重述”中间哪个又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
必须承认“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建构与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互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角度的历史建构是基于:“在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有着多少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但是这一切,对于当今一代的青年,并不是很熟悉的。因此,他们要求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不怕任何艰险,勇于克服困难,无限忠诚于人民的革命事业。”[2](p3)而文学书写之所以关注这段历史,往往也是因为“广大青少年对革命先烈斗争事迹的反映是那么强烈”[3](p29),“在文学领域内把他们(烈士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下一代。”[4](p7)只要稍作辨析,就能发现这里隐藏的历史逻辑,这里所强调的是历史在当代叙述的合法性,其实和“新历史小说”书写有着差不多的起点。这就提醒我们,当标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述”开道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建构也是它所处时代的“当代史”。它与更靠前的《蚀》、《死水微澜》相比,所提供的历史观同样是崭新的。如果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还会对当下“新历史小说”所抱持的历史观这么有信心吗?而且针对“十七年”文学历史建构的“重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并不是始于1980年代之后的所谓“新历史小说”。以《红旗谱》为例,早在1970年代初,就被批判为“‘谱’的是叛徒王明错误路线的黑旗”[4](p238)。因此,如果不看到这中间因时而易,变动不居的历史观就很难解释“述”和“重述”之间的错位问题。正因为如此,今天研究《圣天门口》这样的小说恐怕也不能简单地从“消解”和“颠覆”历史之“旧”的二元对立的角度去识别它的新经验。所以有人认为:“从《白鹿原》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程,如果说这不是一个解构的问题,也不是对原来历史进行颠覆的问题,而是一个建构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些年建构了什么?现在回头来看,80年代至90年代的主流文坛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可以称作一种‘文学意识形态’。这种‘文学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界对现实和历史的认识大不一样,文学的‘文学性’在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浸泡中彰显出来;用这种‘文学意识形态’对历史进行解释就形成了从《白鹿原》到《圣天门口》这样的一系列作品。这样的对历史的解释与我们原来对历史的解释有不一样的地方。与当代社会各界对历史的解释也很不一样。它主要的地方不是在解构,恐怕是在建构。建构了一种‘文学性’想象的人道主义为主导的历史意识形态。”[5]这里,“文学意识形态”是独立和自足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十七年”文学同样也有着它的“文学意识形态”,只不过许多时候“文学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重合而已。因此,当一些研究者指认《圣天门口》在反思20世纪中国政治现实,比如“肃反”、“大跃进”、“文革”时所体现出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勇敢和良知,我倒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是非臧否,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其实早已经明确作出回答。问题的关键是,文学不仅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简单的是或非的判断,更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是与非予以自主性立场的“文学性”表达,建构出审美性、艺术性的文学世界。
《圣天门口》涉及现代革命如何进入中国乡村。应该说,用古典时代“成王败寇”的历史观,或者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来解答,这个命题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十七年”文学回答这一历史命题就是把政治意识形态的解答作为自己的解答。那么,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这个业已普适化的命题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性和区别性?在世界革命格局中,中国革命具有中国特色;在中国革命格局中,参与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地方”,有没有和“地方性”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特色呢?而每一个革命“地方”的个人,有没有他们进入革命的个别性呢?《圣天门口》是一种仿“地方志”的书写,相较于正史,“地方志”的历史建构本身就体现着个别性和边缘性。这使得《圣天门口》能够摆脱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抗中的“非文学”因素的缠绕,回到革命的“地方”,书写革命的“地方志”。因此,虽然写了革命和后革命时代,但我倾向把《圣天门口》作为20世纪中国的乡村志、“百科全书”来阅读。它不仅仅书写20世纪中国乡村的“战事”,而且还有和“战事”同样重要的中国乡村的人事、物事、农事、情事、性事。《圣天门口》的革命图景中摇曳着风花雪月和乡俚村俗。革命和欲望荷尔蒙的叙事,这个“革命加恋爱”小说前辈们开创的主题因为《圣天门口》的傅朗西、董重里、阿彩、杭九枫等革命者而有了一个乡村版和“游击”版。
应该说,从文化碰撞的角度看,现代革命不是最早进入中国传统乡村的“他者”。天门口不过是中国乡村的样本。在这里,“多年以前,三个蓝眼睛的法国传教士来到天门口,用自己的钱盖了一座溜尖的美其名曰教堂的房子,诚心诚意地住在里面。多少年过去了,蓝眼睛的法国传教士百般勤奋地传教,仍旧不能让天门口人信他们的教,进他们的堂。”而后来的革命者却能够意识到,“处在雪杭两家矛盾之中的天门口民众急切需要正确的引导”。傅朗西、董重里的革命实践正是建基在对地方性经验的发现和充分把握之上。和法国传教士的宗教一样,同样是舶来品的革命,在天门口却如杭九枫所说:“我人不暴动卵子还要暴动哩!”《圣天门口》其实也是一种撤退的叙事。撤回到革命的“地方”,作为革命方志的《圣天门口》,对农民朴素的革命想象给予了充分的尊重。那些革命的神圣化叙事中淡出的江湖和淘掉的渣滓,重新回到“文学”。雪狐皮大衣、旗袍、雪家的女人、独立大队……革命不仅是精神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一个叫“天门口”的“地方”的翻天覆地、河东河西。
《圣天门口》审视革命和后革命时代“乡土”、“民间”的变动不居,书写乡土中国在“常”与“变”、“赓续”与“断裂”中的流逝与存留。在乡土中国的民间社会,每一个人都意味着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而且这样的世界与世界之间又交织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在乡土人物志式的书写中,《圣天门口》无疑绘制了一幅乡土中国的全景图。天门口虽小,但它是整个20世纪中国的具体而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对天门口上流社会的雪家之外那个暧昧不明的广阔底层的关注。在讨论中国社会的层次时,殷海光指出:“中国的社会层级在广大的农民底下的有不务正业的无赖群体。这一层次的人素来是中国一般‘正人君子’所瞧不起的。可是这一层次的人素来不乏奇才异能之士。”[6](p106)现代中国文学中对乡村人物的书写也有分层,但其分层相当单一,因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作家在书写乡村人物时往往把他们纳入预设的框架之中,因此,现代小说的乡村人物也逐渐被类型化。杭天甲、杭九枫、常守义、段三国、林大雨、余鬼鱼……麻木和觉悟、落后和进步已经不能够区分他们了。《圣天门口》的意义在于将这些在现代书写中被压抑、隐而不彰的乡村人物解放出来,回归到他们生息的乡土,书写他们丰富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从这个角度上看,革命和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只是乡村芸芸众生的布景。说得直白一点,《圣天门口》其实就想写出革命进入中国传统乡村之后引发的物质和心灵的“暴动”,写出在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的人和人性的卑琐和高贵、妥协和矜持。这样,《圣天门口》的革命地方志自然也有了一种心灵史的意义了。
应该说说《圣天门口》的“圣”。在革命和宗教实践中从来伴随着崇“圣”欲望,考察中外历史上的革命,和宗教结缘的很多。就精神气质而言,革命和宗教也极其相似,“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希冀、欲望、起诉的记录”,在宗教式微的时代,宗教“表达理想的功能”在革命中得以存续。“人在历史的前进过程中抛弃着宗教,虽然抛弃却留下了印记。部分宗教信仰所保留下来和保持着活力的冲动和欲望,已去除掉它限制性的宗教形式,在社会实践中成为创造性的力量。”[7](p125-127)而且,在回答什么样的人能够超凡入圣这一核心问题时,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强调成圣之路上对个人情欲的抑制。革命和宗教的圣者常常是禁欲主义者。
如果从纯粹革命和宗教的两面观之,当傅朗西和梅外婆先后抵达天门口,“天门口”似乎都有可能成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心目中的“圣地”。但刘醒龙将“圣”置于天门口这个偏野之地前,似乎并不是对一个行将湮没的“圣地”的追认或者命名。在《圣天门口》中,“圣”成为一种人性和德性的精神高度。如他所说:“优雅是一种圣,高贵是一种圣,尊严也是一种圣。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对圣的发现,不只让这部小说拨云见日,更是使其挺起人在历史中的风骨,哪怕是马鹞子这一类的命运,也不再被历史抛弃。身为书写者,如果没有小说中日益彰显的优雅、高贵与尊严时刻相伴,信息时代的六年沉默,就会形同六年苦役。年复一年不与外界接触的写作,因为有了圣,才不枯燥,才有写小说二十几年来,最为光彩幸福的体验。”因此,阅读《圣天门口》,我总会想起周毅和刘醒龙通信中的那句话,“分享一下你小说中的人物吧”[8]。从我们的阅读经验看,不是所有作品中的人物都可以和读者分享。分享是一种和感恩相关的馈赠。
“圣”是心灵的自我清洁和对世界卑污的涤洗。小说的第九章“一耳一口一个王”有一段王参议与傅朗西的对话:“雪家女人心里想的却是不让人使诡计,耍手段,昧良心,犯凶残。这四样事我做过的,你哩一定也做过。从今日开始,往后我们说不定还得这样做。你想推翻国民政府,我想保卫国民政府,梅外婆和雪柠却想将你我的思想放进白云里用雨雪擦洗一遍,这非得有登天的本领呀!”在天门口,梅外婆是受难者,她和雪柠荫被雪家恩泽的余晖,散尽家财,仍然要背负着乡人对雪家的仇恨;她救人困厄,却惨遭蹂躏,“同样受了二三十个日本人的糟蹋,做丫鬟的杨桃都选择了死,梅老太婆竟然还有脸活在世上。我要对大家说,因为在天门口,所有该死的人从来都没有办法活着,轮到我该死时却死不了,这种结果能使大家用敬畏之心看待身边的平常事、平常人,哪怕活得再窝囊,我也心甘情愿”;她沉静、化解着天门口无所不在的仇恨,甚至以德报怨,虽然不能相视一笑泯恩仇,但仇恨的心如“起了波澜的水,平静就没事”。“善心善意来看人是不会枉费心机的。”正是因为梅外婆源于心灵的爱与宽宥,悲天悯人,天门口才不至于坠入畜界和地狱界。在一个理想主义被普遍冷落的时代,刘醒龙以良善之心在梅外婆的身上灌注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在由宗教渴望而有意识的社会实践的过渡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可以被揭露然而无法取消的幻象。它就是对完美的正义的想象。”[7](p125-127)梅外婆的“宗教渴望”一定意义上是作家刘醒龙“对完美的正义的想象”。梅外婆有“宗教渴望”却没有过渡到“有意识的社会实践”。因为,她意识到以一己之力救赎世界的限度。在她临死前留给雪柠的信中说:“你梅外公活着时,总想以一己之力来救赎一国,结果没有成功不说,连命都搭进去了。轮到你梅外婆,自觉力量不够,才来天门口,想以一己之力来救赎一方,看来也不成功。所以你梅外婆觉得,如果你这一生也想学梅外公和梅外婆,不如用一己之力来救赎某一个人。”如果《圣天门口》的“圣”是一种宗教情怀,那应该是和我们生命休戚相关的日常的俗世的宗教,一种爱人、渡人、活人的宗教。所以当雪柠把亲人的尸体扔给驴子狼的时候,才能体味到“只要能救活人,死人也会乐意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情欲在《圣天门口》也被充分的释放和宽容。
刘醒龙固执地以一部百万字的小说书写人何以能够高贵、优雅和尊严的活着。如果真的有个圣、人、魔的三界,马鹞子,至少小岛北肯定位于魔界一席,但残忍、鲁莽如马鹞子,也有着朗诵《扫荡报》《六十无名烈士传》的悲壮,有着拍打大钟学着董重里说书的慷慨。而制造毁灭和死亡的侵华日军团长小岛北也在日记里写下“天门口是妹妹的,做哥哥不能夺走属于妹妹的东西”,“使他不忍用大炮与火焰将顽强地阻碍其前进步伐的小小山镇碾得粉碎”。如果《圣天门口》是关于宗教的。那么这样的宗教不是某一种教义和仪式,而是日常生活的信仰和道德尺度。其实,整个中国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就一直徘徊在道德的压抑与放纵、毁弃与重建的摆动中。19世纪中期,“西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在传统的道德废墟上重构“伦理觉悟”的新道德。但20世纪上半期的历史语境没有给他们提供充分展开道德重构的机会。即便到了20世纪中叶,建立在集体和共产主义“公”德想象的社会主义道德又使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重构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这个半拉子工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有了一种重建的可能。但这样的重建显然纠缠着复杂的传统道德资源。而80年代知识分子也没有意识到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和机会已经很少,当他们的道德重建还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时,商业社会大潮汹涌而来,于是从19世纪开始的道德重建成为仍被延宕的“未完成”。如何在传统东西方道德资源、当代社会主义道德资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未完成道德想象”中间,“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来获得当下的创造性的道德转换,常常让当代知识分子失陷迷途。《圣天门口》中朴素的乡村日常性的宗教却有着度人和向善的理想。世界如此卑污和粗鄙,我们却头顶着一个灿烂的星空。但这样的理想如果放置在我们描述的现实之下,是不是迹近幻象呢?梅外婆、雪柠、雪蓝和雪荭那地母般辽阔、深厚的宽宥,真的可以消弭大地上的卑污、幽昧、仇恨吗?其实,无须绕这么多的弯子,小说的最后,革命和宗教的抱持者开始靠近,他们都对自己的理想发出了质疑。于傅朗西是:“这么多年,自己实在是错误地运用着理想,错误地编织着梦想,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紫玉离家之前说的那一番话真是太好了,革命可以是做文章、可以雅致、可以温良恭俭让,可以不用采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按照这样的逻辑,傅朗西正一步步靠近梅外婆。而梅外婆的福音是不是真的福音呢?雪柠给出的答案是“当年梅外婆没教,我也是才明白的,福音之福不是幸福,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睁大眼睛做出来的黄粱美梦。”雪柠和杭九枫“肩并肩走到同样设在河滩的会场,先到的那些人中,大部分还不晓得雪杭两家在人口几乎死光时彻底和好了”。他们可以窥破历史上谁第一个被杀,却不能终结被杀的历史。阿彩、小岛和子、林大雨、杭九枫的觉悟,并没有阻绝仇恨的绵延,谁能终结被杀的历史,悲天悯人如梅外婆不能,尚能期待何人?刘醒龙就这样从理想主义者腾身一变,成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最后说说语言问题。《圣天门口》有着语言的自觉。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比如在叙述性的散文中,夹杂着韵文的“黑暗传”,刘醒龙沉潜到中国小说传统丰饶的沃土中。关于小说的语言,我们往往忽视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韵散错糅的杂语体特点。这种或韵或散的小说语体,在文言文失去合法性地位的新文学时代,只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还残留着一些痕迹。现在,《圣天门口》以说书人的腔调公然复活韵散错糅的中国小说传统,为中国小说的语言运用提供了一个实验的样本。还有方言,这个被普通话遮蔽的世界,刘醒龙说:“写小说时,我有一道心理防线,从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语为主要因素的各种粗鄙的流行用语。无论它如何甚嚣尘上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强烈亲近感和时髦相。我还会喋喋不休地诘问,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华既有的民间人文精髓本来就是大错,那些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就应该挨天堂里老祖宗的鞭挞了。不记得是谁写的,只记得那本书名《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义吧,起码对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评价说,我在《圣天门口》启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其实不然,常用的方言词汇也就二十来个:汰衣服/掇东西/啸水/阊风/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后日/嘎白/晓得/吊诡/嗍几口,如此等等。这些较为典型的鄂东方言,与当下常用的同义语对比,明显具备高出一筹的优雅。这种特质犹如定海神针,一旦出现,就会让人觉得无所不在。仰仗民间人文底蕴的长篇小说,不可以视流行俗语为至宝。”[9 ]刘醒龙夹带着韵文的私货,擦亮了方言的蒙垢,回到语言的“外省”,看来他是准备书写一部和自己心灵相关的小说了。它关于革命的“地方”,关于俗世的富有宗教渴望的日常生活。“在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学或者说广大中国的文学知识分子正应该重新调整文学与现实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在对文学自主性的捍卫与追求之中,自主性地介入政治、介入历史。正是在这种自主性的介入之中,文学才能获得自己的力量与尊严。对于现代以来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紧相纠缠并且在晚近时期充满问题的中国文学,这正是一次新的机会。”[9]从这种意义上,《圣天门口》提供了文学以自主性的意识形态方式介入政治、介入历史的书写样本。还不只是《圣天门口》,《白鹿原》、《旧址》、《银城故事》、《花腔》、《笨花》、《第九个寡妇》、《启蒙时代》、《平原》、《赤脚医生万泉和》、《生死疲劳》、《刺猬歌》、《致一九七五》……近现代中国政治的文学性历史就这样被建构着。
标签:圣天门口论文; 文学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宗教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小说论文; 白鹿原论文; 读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刘醒龙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