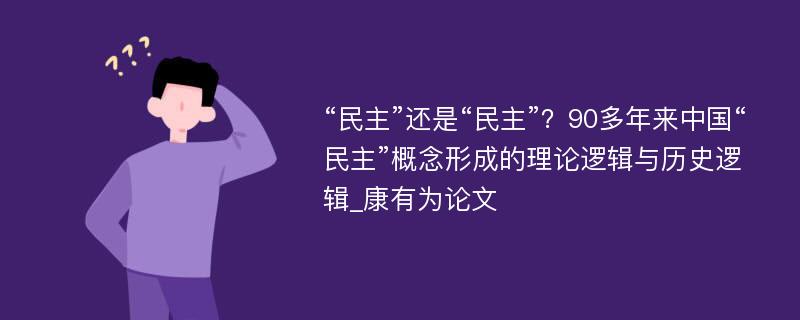
“民主”还是“民主主义”?——九十年来中国“民主”观念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逻辑论文,民主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十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3-0011-10
“民主还是民主主义”在英文里似乎应该说成“Democracy or Democratism”——不过,现在的英文 词典里还没有“Democratism”这个词。而我之所以做这个发明,是因为现在人们一看到“Democracy”,想到的就是“民主”而不是“民主主义”。但在九十年前的“五四”时期,中国人对不带“-ism”尾巴却表达一种系统的主义、价值和信仰的性质看得很清楚,而且极力加以标榜。当时“Democracy”的译法,除了“德谟克拉西”一类的音译之外,其他如“惟民主义”、“庸民主义”(张东荪)、“庶民主义”(陈启修)、“平民主义”(李大钊)、“民治主义”(胡适)、“民本主义”、“民权主义”等等,无不拖着“主义”的尾巴。而据陈启修的研究,在所有译法中,又尤以“民主主义”“通行最广且久”——尽管他本人甚不以为然。①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五四”时期最流行且最能表明国人对“Democracy”热爱的,却不是“民主主义”或“德谟克拉西”,而是“德先生”。似乎只要“德先生”大驾光临,不仅政治经济将为之丕变,而且“美术也,文学也,习俗也,乃至衣服等等,(亦)罔不着其色彩”。② 惟其如此,陈独秀也才敢对不满于《新青年》主张的人发出战书:“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③ 陈独秀并不是真以为天下人都没有胆量反对“德先生”、“赛先生”,而是认准了没人愿否认它们对中国的重要性。“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九十余年,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民主与科学”形成了中国人对于“什么是现代”的最根本的理解。近年来,一些思想史开始关注“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思想开展的严重制约④,但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现代性方面的制约却无人提及。实际上,正是因为将现代政治化约为客观、透明、形式化的科学问题,“民主”才成为那种“以经济生产为原则”就可裁决的问题⑤,才是所谓的“日常经验”(如胡适的“民主是幼稚园政治”⑥),才是“生活常识”、“客观事实”(比如,“已经证明……”),并以“感觉化”、“身体化”——所谓“直观”——的方式进行传播。由此看来,考察中国“民主”观念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势在必行。
一
2006年秋,《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⑦ 一书出版后风靡学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大实话”口吻和似乎业已无可置疑的、简明的、常识的面孔(类似“科学真理”)。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民主”长期以来都名声不好。因为在许多大思想家看来,民主不仅不是个“好东西”,而且可能是个“坏东西”。这就要从“民主的故乡”雅典说起了。
今人说到的“Democracy”,最早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⑧ 一书。在希腊文里,“民主”由“demos”和“kratos”两个词构成。前一个词即今人所说的“人民”;后一个词是“统治”的意思。但这个解释过于简单。“demos”本来是指希腊时期雅典城外的“乡村”和居住在那里的“庶民”。公元前5世纪,一个叫克勒思叙尼(Cleisthenes)的平民领袖赶走了以前的僭主,把城乡混编成一个个叫“德谟”(demos)的组织,编属其中的人叫“德谟特”(demotos);作为城邦的新成员,他们可以选举“德谟”的首领。⑨ 后世就把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体称为“demokratia”,即我们通常说的“Democracy”。
不过,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政体评价很低,是其大著《政治学》书中三种坏的“政体”(regime)之一。亚氏把所有的政体区分为好、坏对应的三类六种。第一类是“一人统治”:好的称之为“Monarchy”(君主制),坏的称之为“Tyranny”——比较时髦的译法是“僭主制”,但其实是指暴君统治。第二类是“少数人统治”:好的形式称为“Aristocracy”(贵族制),坏的是“Oligarchy”——一般译作“寡头制”,但“寡”在中文里有时指“一个人”,如“孤家寡人”,既容易与“暴君制”混淆,又不容易传达少数人统治的意思,不如径译为“X头制”好些。第三类是“多数人统治”:好的形式是“Polity”,坏的才是“Democracy”。“Polity”在《政治学》书中有时指一般性的“政体”,但此处无疑特指一种“混合政体”,一般译为“共和制”。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1915—)创造了一个新词“Polyarchky”(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后来又写出以此为题的名著,不少人译为“多元民主”,但不如译成“多头政体”更恰当一些。⑩ 至于“Democracy”这个今天人见人爱的宠儿,则被亚里士多德贬损为简直“不是一种政体”,在中国被译成“庸民制”或“暴民制”也并不少见。(11)
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对“Democracy”的恶评,倒不是因为厌恶乡下人的土和穷。雅典的城乡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些理论家至今念念不忘的城乡共同体典范;亚里士多德本人对农民的纯朴、自足也相当欣赏。不过,他对“民主”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其一,政治是一项专门技艺,就像航海一样需要长久历练和专门的技艺,而“德谟特”们缺乏研究政治的余暇,经验不足。其二,他们共同体意识淡漠:或则过于积极,如“商人”和“鞋匠”;或则不感兴趣,如“农民”;而只知道关心自己的私利。当然,漠视公共利益,是所有政体被败坏的共同原因。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德谟特”们常常不依法办事而靠点人头和“抽签”——这不是比方,而是雅典民主的主要方式。(12) 所以,亚里士多德虽不像柏拉图那样蔑视大众,而力图吸收“民主”政治的优长如热爱“平等”、“自由”等,但在他看来,“民主主义”实在是一种“多数”的“专制”,与“暴君制”相似,算不得一种像样的政体。
“民主”在“故乡”雅典的坏名声,当然不是从亚里士多德才开始的。臭名昭著的“苏格拉底审判”(公元前399年)即来自民主的判决,是大多数人决定应处死伟大的贤哲苏格拉底。柏拉图早期支持少数贵族的统治——不过并不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政体——晚期则致力于“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协调,虽一度玄思“哲人王”的统治,但思考的中心始终在“城邦”(Republic)正义的实现,对雅典的民主遗产不屑一顾(《法律篇》)。修昔底德严守“史家纪律”,不轻着一辞,但其所著《波罗奔尼撒战争史》对雅典民主泛滥与败坏留下的大量记录,足以使人们不懂春秋笔法也知其用心所在。而后来另一位希腊政治史家波利比阿(Polybius)赴罗马做人质十七年,在目睹了雅典的衰落和罗马的崛起之后指出,罗马人成功的关键,在于摒弃了任何形式的单一政体,而以“混合政体”的形式使君主、贵族和人民三种力量,既相互制约、平衡,又各得其所,充分发挥自己的优长。
而随着希腊城邦的衰落,“Democracy”这个词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消失了。(13) 在漫长的中世纪,人们谈论的是另一个词“res publica”。“res publica”本意为“公共事物”,用西塞罗《论共和国》中的语言来说,“公共事务(res publica)乃人民之事务(res populi)。而“人民”,不是指那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基于一致性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集合起来的。换言之,“res publica”指的是人们因理性和利益结成的共同体——人们称之为“共和国”,并将这种结合方式称之为“共和政体”。(14)
有人认为,“人民”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一波利比阿类型的、现代共和观念的出现。(15) 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发展出以“人民”为核心的、现代共和观念的是马基雅维利,尤其是卢梭。实际上,也正是卢梭逆转了“民主”的坏名声,使它变成了一个人人争取的“好东西”。
简要地说,卢梭把此前作为“政体”(regime)概念的“民主制”,变成了一切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来源;而将此前作为各阶层或政团力量均衡配置的“共和制”,变成了一种“依法统治”的原则。以《社会契约论》为例:首先,卢梭通过“general will”(“公意”、“普遍意志”)把“大众”(multitude)凝铸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民”(people),并将其置于政治领域的绝对位置,即“主权者”。其次,卢梭把“结社活动”(act of association)——“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共同体”(16) ——作为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因而将普遍意志形成的法律作为一切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对卢梭来说,只要“依法统治”的都可视为共和制——他的原话是:“Tout gouvernement légitime est républicain”(“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的”)——很显然,“共和”在这里的含义又回到了西塞罗对“公共事务”的论述。最后,既然任何一种政制“不管是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其统治的合法性都只源自于“公意”,政府就不过是共同体中一个独特的中介,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就只不过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而只有“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决定,才是最后的裁决。那么,人民就有必要而且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直接转变为执政者。这就是“人民主权”的原则。
所以,在卢梭之后,“民主”成为一切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而共和价值在被“民主”吸收后,则成为一个附属性的原则——在罗马时期则正好相反——尽管有关“general will”如何产生,人民能否以及如何依据“general will”行使主权者的权利,民主与“法制”的矛盾,民主与个人权利、个体自由的冲突一直聚讼不断,但“民主共和”却开始成为最常见的搭配,似乎民主的一定是共和的,共和的也一定是民主的。而且,这也最终导致了“民主自由”的流行,而罔顾“liberty”和“de mocracy”的相互冲突——用当下欧洲新锐政治哲学家墨菲(Chantal Mouffe)的话说,即“paradox of liberal democracy”(“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吊诡”)。(17)
二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之后(18),因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其“人民主权”观念更随之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的核心想象——“人民做主”。然而,“民主”概念本取自中国典籍《尚书》,中外的当事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惜“权变利用”,并作有意无意的误解,实已到了不能再将错就错而不得不正本清源的地步。例如,《尚书·多方》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显休命于成汤”;同书《洛诰》篇云,“天命文王,使为民主”;《昭明文选》亦有:“肇命民主,五德始终。”以上“民主”指的都是“民之主”,即“人民的主人”;而我们现在使用的“民主”,指的却是“人民当家作主”。从构词法上看,古代汉语中的“民主”属于偏正结构,而迄今为我们所用的“民主”则属于主谓结构。
根据意大利语言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考证,这一主谓结构的“民主”出现得非常之晚,实属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翻译《万国公法》时的“创造”。(19) 不过,更令人吃惊的是,《万国公法》中的“民主”对译的是“republic”,而不是“democracy”。按照马西尼的看法,这实在只能算作“误译”!也有学者不同意此观点,因为他们发现丁韪良翻译中的“民主”并不每次都和“republic”相对,有时也有用来翻译“democratic republic”(丁译为“民主之国”)或“democratic character”(丁译为“民主主权”)。(20) 不过从丁韪良将“democratic republic”译成“民主之国”——而最基本的要求也应译为“民主共和国”——来看,他对“republic的漫不经心、不以为然,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是,丁韪良为什么故意忽视“共和”与“民主”的区别,对“民主”情有独钟而对“共和”不理不睬呢?
已有很多研究者注意到,晚清各种报刊、译述中将“President”称为“民主”的用法,如1874年12月《万国公报》有关次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报道:
美国民主,曰伯理玺天德(,)自华盛顿为始已百年矣,例以四年换举,或者在位深得民望者(,)再行接位四年(,)亦曾见过;即现今之美皇古难得(,)亦已续接四年,是两次也。而古君在位惠及民(,)兹逢更举之期,民照又欲再举古君四年为美主,据云(,)古君已力辞不受矣。
从字面上看,这里的“民主”、“美皇”、“美主”,与文言中旧有的“民主”——即“君主”——的用法,并无区别,但通过对“四年换举”、“续接”不得超过“两届”以及由人民推举等制度设计的强调,民选总统与旧式君主的区别可谓一望可知。那么,传教士们为什么仍要用它来翻译一个“与其意义正完全相反的”对象呢?按照金观涛、刘青峰的解释,是“翻译的困难”;并称这一做法“显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认识西方的机制。这就是,从一开始就把包括现代政治制度在内的西洋事物,视为和中国传统文化、制度完全相反的新奇事物”。(21) 这未免令人不解。为什么这不属于巧妙的对比策略(以从效果上强化了两者的对立)而是翻译的困难?为什么这不是一种传教士的认识逻辑而是中国文化的机制?我以为,正是出于对“民主”与“君主”的绝对对立的强调,丁韪良才会甘冒丧失“头号中国通”的危险,无视“republic”与“democracy”的区别,一味扬“民主”而抑“共和”的。在他们看来,“君主”(制度)自古以来就是与“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近年来,有人对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有关“东方专制主义”论述在日本的传播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接受进行过考证,发现无论是“儒教、专制政体、官僚政治、家族主义还是特别的种族特性,都可以溯源至欧美东方学的描述”。而传播这种殖民意识的,除了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也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人和海外华人。他们“将西方对东方的表述,如中国专制之类,译成中文,引入中文世界,并变成自己的表述加以传播,进而重新塑造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记忆”。其结果是,“表面看来由中国人自己作出的论述,用的是中国的‘语言’……骨子里则是欧美东方学对中国漫画式认识的重复、再现与拓展”。(22) 这种貌似从广阔的比较史视野中产生的“新史学”,实则严重地阻断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不过,复杂的是,“这种舶来的论断”之所以能让“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意无意地“替西方人宣传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治史的戒律,而在于清末以来“革命”的政治实践这一内在的自我需要——我们试想,既然秦以来的“君主”(制度)都是“专制主义”的,而“专制统治”不过是东方特有的、外在于世界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地方性制度安排,那么,清王朝的统治者即使不是“蛮夷”,而同为华夏苗裔(如康有为、梁启超所论的那样),难道不也是逆当世“民主主义”潮流而动、必须根除的顽逆吗?翻读《民报》与《新民丛报》当年的论战,这样的论证触目皆是。
而从这个角度观察“republic”的翻译,则很易明白,其主要的考虑仍是与“专制”字义上的对立和对“民主”新意的模仿。现已清楚,“共和”一词,源自日本学者大槻盘溪对“周召共和”旧典的挪用(23) ——“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24) 在古代汉语中,“共和”是“共同/协作”的意思,而这恰好与“专制”(个人独立制裁—以“制衣”、“裁剪”为喻——或决断)相对反。而对“周召共和”旧典中“君主”缺位状态的挪用,则无疑有助于在强调“republic”之非君主统治状态共同性的同时,拉近与“民主”之间的距离,为与“民主、共和”的联用、互用创造条件。
与“民主/共和”在联用、互用中相互加强的效果形成对比的是,“君主”与“专制”的联用和互换不断压缩着自己的空间,最终被“民主共和”这一新的组合完全否定。这里举一个例子。在与梁启超有关民主、共和的辩论中,汪精卫竟悍然说:“共和与民主,意义范围不同,然论者所谓共和,即指民主。故此文亦往往用共和二字,当解为狭义的共和即民主也。”(25) 共和即是民主,民主即是共和!在专务吹毛求疵的辩论中尚且如此,一般情形下就更可想而知了!
有人经过统计指出,1895年前,“共和”极少被使用;1895—1901年,“共和”的使用虽然开始增加,但仍不及“民主”;其后在1903、1906、1913和1915年,则大大超过“民主”。(26) 但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同时也是“共和”概念使用开始急剧衰减的年份——到1918年到达最低点——实际上,除了个别阶段,“共和”概念的使用一直处于一种极不对称的劣势。但以晚清君主立宪的失败以及1912年“中华民国”(英译为“中华共和国”)的成立来解释,认为自斯以往,“共和”不再合乎时宜,“民主”才是首要的选择,则是不够充分的。必须注意到,当中国人接受“republic”的时候,“democracy”在西方特别是所谓在美国的成功(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读),已使之获得了极大的示范效应;而与之相应,“共和”则完全失去了独立的意义,或者只有在“民主”的意义下才能获得理解。所以,在晚清以降的文献中,“民主”与“共和”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互换使用的。这甚至包括那些坚持共和主义信念、抨击民主主义的“反动(保守)分子”,他们多谓“共和”亦无不意在“民主”,而这也正是中国共和主义政治实践所面临的最深层的困境。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与“戊戌”时代的思想领袖康有为之间展开的一场论战看,论述虽仍集中在“观念”的冲突上,但观念已不仅仅是某种所谓的修辞,而是那些激荡历史的意念的凝聚。
三
学术界很少有人注意到康有为与“五四”的关系,注意到的也不过是因为陈独秀的驳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和《驳康有为〈共和评议〉》——连带注意到康有为的《致总统总理书》(原题《致黎元洪段祺瑞书》)和《共和评议》。但实际上,康有为与“五四”的关系可谓不浅。(27) 就其大者而言,五四运动爆发两天后,康有为立即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并《请犬养毅转达日本内阁撤兵交还(青岛)电》。相关的文本,可以参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陈独秀的著作则可参看《独秀文存》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至于陈、康之间的对话关系更是鲜有人论及。故这里从一篇至今尚未被纳入到辩论范围的文章讲起。文章的篇目是《袁世凯复活》。
翻阅当时的报纸,传言袁世凯未死的并不少见;但像陈独秀那样确信袁世凯活着的则不多见。他说,自己每天都看到袁的宣言、袁的行事……怎么大家都糊涂了,竟然认为袁世凯死了呢?当然,我们会觉得,这不过是陈独秀比喻性的说法,是“文学”修辞,“袁世凯”不过是个代名词——确实,他也两次引用了蔡元培的说法,把袁当作“旧官僚、旧学究、旧方士”等三种“旧社会”势力的“混合物”。但他却说,令他“悲从中来”的并不是所谓“精神之袁世凯”仍活着,而是“肉体之袁世凯,亦已复活”!“其人之相貌,思想,言论,言论,行为,无一非袁世凯,或谓为‘袁世凯二世’”。这显然是说,他坚信,像袁世凯称帝那样颠覆共和的事情,必然发生!作为一个政论家,这无疑是在显示自己的政治判断,岂可与无聊的文人调侃同日而语?!
那么,陈独秀口中的“袁世凯二世”(秦二世?)究竟是谁呢?
袁世凯二世酷肖袁世凯一世之点甚多:其身矮而胖也同。其口多髭须也同。其眸子不正,表示其心术也同。其风姿气味,完全一市侩,无丝毫清明之气也同。其自命为圣王,雄才大略也同。其贪财好色,老而不戒也同。其欲祭天尊孔以愚民也同。其爱冕旒喜拜跪也同。其尊信文武圣人,求神,治鬼,烧香,算命,卜卦,看相也同。其主张复古,提倡礼教国粹也同。其左袒官僚,仇视民党也同。其重尊卑阶级,疾视平等人权平民政治也同。……其主张小学读经,以维持旧思想也同。其怂恿军人,摇旗呐喊,通电拥护旧政教,排斥新人物也同。其口称德义,而负友辜恩也同。自居为中国第一老资格,而国人亦以第一老资格目之也同……
这不正是康有为吗?!这倒不是说陈独秀的描写如何“写照传神”,关键是文中所列“行状”要集中在一人身上则非康有为莫属。更为令人惊异的是,陈独秀的预感半年后竟然应验了!刊布陈独秀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16年12月,半年后(1917年7月)“辫帅”张勋就将废帝溥仪重新拥上了大清的金銮殿!尽管在史称的“丁巳复辟”中,康有为一直靠边站,但在时人心目中,没有康有为这个“后台老板”(28),一介武夫的张勋是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来的。
但陈独秀不可能不明白,康有为不是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后,康有为的讨袁檄文哄传天下,且以康有为的尊君,岂会有袁世凯的“自为”之举?那么,“袁世凯二世”的恶谥所为何来?
陈独秀少年时以康党自居,此时却丑诋康有为“不仅代表过去之袁世凯,且制造未来无数袁世凯”,真正的原因实在于康的屡屡为“孔教”张目与抨击“共和”。对陈来说,孔教乃“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与之相比,袁世凯的复辟也不过“枝节”和“恶果”。所以,康有为才成了他必须要辩驳的对象。陈独秀所撰写的《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时局与杂感》等文,都涉及与康有为的辩论。陈独秀反复声张:“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可以说,围绕“孔教与共和”,陈与康形成了极端的对立。
不过,在对这一命题进行分析之前必须指出,这里的“共和”指的是“民主主义”。所谓“孔教与共和”,即“孔教与民主主义”。但是,如果说孔教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因而与民主主义对立的话,那么民主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为何必然与孔教对立呢?遍寻陈独秀的论述,除了有关形式逻辑上的“归谬”,如孔学非教——吾人本无国教——信教乃个人自由——入宪即为强制(这大半是对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模仿)等外,主要针对的是“孔教”与“专制”的联系。
按照陈独秀的分析,既然“孔教”是“封建专制(主义)”(29) 的基础,故对孔教的批判就不仅只有“文化批判”的意义,而直接指向其政治后果。他说,孔教之本在于三纲之教,三纲之本在别尊卑、明贵贱,绳人以“忠、孝、节”;然而,一旦以君(父、夫)为臣(子、妻)纲,则不仅“民(子、妻)于君(父、夫)为附属品,无独立自主之人格”,且“率天下之男女,则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30) 既然如此,孔子之道,就只能是“封建”之道、“君主”之道、“专制”之道了,只要用孔子之道来治国,那么就一定会有君——“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复辟与尊孔》)——有君就只能是“君”主。而在“民”主国体之下,断断不可能有“君”主的位置,那么,孔子之道就只能是必须废除的“封建专制时代之道”,尊孔护教也就只能是倒行逆施、居心叵测、对“共和政治”——“民主”——的根本威胁!因此,陈独秀敢于断言,尊孔的论调不除,复辟永不可止,帝制永不可绝,共和永不可固!也正因为如此,在陈独秀看来,康有为的坚持孔教,力主“虚君共和”,除了表明自己的不能与时俱进、“反动”倒退外,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留恋帝制罢了。是故,在《驳共和评议》里,陈独秀说,你要坚持帝制就直接讲帝制好了,不要把帝制与共和制夹杂起来讲,自相矛盾——因为一边是“君”主,一边是“民”主——这样只会让年青一代看不起你。
但现在看来,这一辩驳与推理未免过于武断了。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力持君主立宪,冀望速成,“三年而规模成,十年而本末举,二十年而为政于地球,三十年而道化成”(31),故倚重君主的“乾纲独断”,有知恩图报之心,确为事实;但是,在光绪皇帝病逝后,康提出“虚君共和”,是否仍欲为光绪的后人留出一个位置呢?显然不是。
实际上,民国甫建,康有为就已说过,“满洲归化,实同灭亡。天所废之,谁能兴之”(《共和政体论》)。只是在《不忍》杂志刊出时,这句话才被删掉,现在我们查阅《康有为全集》却是可以看到的。既然清人之亡等于“天灭”,这表明他实际上已割断了由光绪皇帝的私人情谊而致的对清王朝的责任,转向对民国的认同。袁世凯宣布称帝,康有为即多加声讨,力促其下台,可见他的立场。即使最为人诟病的“丁巳复辟”,查其《丁巳代拟诏书》除“访遗老”、“表忠烈”等旧式节目,“免拜跪”、“免避讳”、“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改新律”、“召集国会”等内容,都表明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帝制无涉。其《拟帝国国会议院法》更从国会的召集及会期开始,对两议院的关系及职能分布、议长议员的津贴、委员会的设置、会议的章程等,详加论列,“愿用英国君民同治之政”并非虚语。对康的误解,实际上集中在“君主立宪”的“君主”上。但“民主”是否就是无君?“民主”就一定是与君主绝对不能兼容的吗?那么,又如何理解作为“大地宪政之母”的英国所采用的“君主立宪”呢?
四
当然,康有为之所以为世人诟病,除了“君主”论外,他的屡屡抨击“共和”与“民主”也是一大因由。
康有为抨击“共和”、“民主”,是因为康并不认同“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二分,力持“共和”、“立宪”、“专制”的三分法。简单地说,康将“民主”视为太平、大同之世之法,认为当时之务在摆脱“剧乱之世”的“君主专制”,采用“君民共主”以入“升平之世”。所以,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在于立宪——有宪政则国为公有,有没有君主并不重要,就如英国一样,有君主而无害其为民主国;无宪政则国为私有,如墨西哥虽无君主,但其比专制有过之而不及。(32) 从初期倚重君主“乾纲独断”的“君主立宪”,到后来的“虚君共和”,康的关怀都在如何促成宪政的实现。
康有为反对“民主”的另一个理由,指向的是晚清革命派所心驰神往的“美国民主”。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八十一年中,九次变乱,三次复辟;南美(如巴拿马、秘鲁、危地马拉)的动乱尤其是墨西哥的三百年大乱,最后只有借墨西哥总统迪亚斯的专制才安宁了三十年,其教训即在于他们对美国民主特别是民选总统制的盲目模仿。康有为认为,总统制在美国实行,与美国的特殊国情有关——开国国父是清教徒,为公众服务之心重,争权夺利之念轻;十三个洲皆有议会而无君主;原本都是英国人,接受英宪,自治已成;开国之时,人口稀少;处于太平洋、大西洋之间,四无强邻,国不设兵;新地初辟,民易谋生,等等。所有这些,都与中国的情形截然相反,如果贸然效仿,必致大乱,刀枪相向,失地亡国。(33)
今日真正了解美国的人,虽不一定认同康有为对美国的评价,但至少会同意他对美国“特殊性”(“特因”)的观察——康是否受到过“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康的特殊国情论,却被革命派仅仅视为对“专制”的辩护。在他们看来,时间、地点的限制,史无前例等等,都不是理由,而且正好是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提高的条件,最重要的是要采取最先进的方法:“火车要靠火车头”。而美国的民选总统制——“民主”,与联邦自制——“共和”,正是这样的榜样。
康有为的宪政理想不是美国民主,而在英国君宪。康有为研究英宪有年,于君主对现代政治的作用印象深刻,留下了大量的论述,可用“虚君”论来概括。康有为认为,一种“木偶式的虚君”,既可以避免因总统更迭造成的纷争,而以内阁行政元首依法行政,君主不负实际责任,又转可避免因内阁更迭引发整个国家混乱。
然而,康有为的“虚君”论也留下了大量的困难:一是时势。一度赞同君宪、批评美国民主的梁启超曾质疑,君主“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譬诸范雕土木偶……投诸溷牏,经旬无朕,虽复升取以重入殿笼,而其灵则已渺矣”(《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认为被推翻了的帝制,就如同丢入粪坑的木偶,怎么会再有神力呢?二是来自于对君主立宪制如何运行的不解。陈独秀即追问,如果大家明白了权力在内阁不在虚君,为什么就不会剑指内阁?或者,为什么内阁首相不会倒过来挟持虚君以增加自己的力量呢?三是“虚君”的出身问题,似乎只有皇室,才能满足康有为的“独此一家”、天下人无法与之争衡的绝对性。四是“虚君”论会不会仅仅是出自对英宪有关皇室设置的亦步亦趋呢?钱穆即怀疑康有为因过尊西俗,故事事规模。(34) 然而,康有为看到的是,两千年来“帝者最尊”的习俗对被目为物质文明冠于全球的现代大英帝国子民的影响:
英国虽为国会万能,民权至盛,而保守其纪纲礼俗、道揆法守,以成其整齐严肃、博大昌明之政俗美化,良矣!比于法之腼纲错纪、恣睢自由者,其政俗皆远过之。所以然者,英为虚君共和之治故也。天下皆称英之善法,然其义旨深远,非常识所易识。然共和国人,不可不深思也。(35)
实际上,不管是所谓的帝王之家还是“孔子世家”,通过家庭教育和自我修养所获致的“淑行懿德”、“良言美形”以身垂范,其在公共生活中的示范作用及其对人的潜移默化是毋庸小视的。
以孔教为国教的“尊孔”主张,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康有为尊孔主张的出现相当之早(见《孔子改制考》、《康子内外篇》),而所以终生坚持不动者,确在于对自然的、既成的习惯势力的尊重和善加利用的认识。康有为在《与孙洪伊、范源濂书》中说,尊孔之礼在中国行之两千余年,信从者众,与清廷并无特别的关系,因对满人的愤恨而一朝弃尽,打孔铲教,已为不当;当此国势衰微、外人横行之际,自弃其教,更非“所以为人心风俗之计也”。
几十年来,人们大都以康有为在《致黎元洪段祺瑞书》(即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有“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执拜跪明令……”,以为康有为要重回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老路,更进而联想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陈独秀因而下结论道:在一个民主国家主张祭祀孔子,“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推尊孔教者而计及抵触民国与否”?(36)
然而,也许令陈独秀完全不能设想的是,被自己奉为民主之神的卢梭对“公民宗教”的论述却与康有为极为相似。卢梭在论证以人民的普遍意志作为一切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依法统治”——之后,却马上意识到,人民自身并不足以应付像立法这样重大而困难的事业,而必须依赖一个伟大的“创制者”(“立法者”)。因为,首先,立法者必须是客观的与公正的——
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如果说由于他的天才应该如此的话,那么由于他的职务更应如此。……它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间世界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号令人的人(“行政者”)如果不应该号令法律的话,那么号令法律的人(“立法者”)也就更不应该号令人;否则,他的法律受他的感情所支配,便只能经常地贯彻他自己的不公正……(37)
其次,立法者所立的法必须为民众所理解,而这就不能不用“俗人的语言来向俗人说法”,“可是,有千百种观念是不能翻译成通俗语言的”,那么,为了使一个民族能够从健全的政治原则中受益,尤其是为了“使人民遵守国家法也像遵守自然法一样”,“能够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服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就必须“托之于神道设教”,“让神圣的权威来感化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38) 这种“神圣的权威”,就是“公民宗教”。当然,“公民宗教”与一般的宗教不同:
(公民宗教)是写在某一个国家的典册之内的,它规定这个国家自己的神、这个国家特有的守护者。它有自己的教义、教仪、自己法定的崇拜表现。……它把对神明的崇拜与对法律的热爱结合在一起;而且由于它能使祖国成为公民崇拜的对象,从而教导了他们:效忠国家也就是效忠于国家的守护神。(39)
卢梭当然知道,“公民宗教”有愚弄大众的危险,但却坚持,每个公民都应该信一个宗教,只要它的条款由人民确定、简明扼要即可。
很显然,卢梭的论述与康有为把对孔子视为中华民族的创制者和百代“素王”、“万世教主”的论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孔教会序》一、二)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为了论述的简洁起见,这里只征引民国成立后,康有为的《孔教会序》中有关设孔教为国教的正面论述,而不牵扯人们常常批判的那些从自然的习俗(“数千年奉为国教”)和横向格义(“今则各国皆有教而我独为无教之国”)层面给出的消极理由:
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即国大安宁,已大乱于内,况复国乱靡定乎?恐教亡而国从之。(40)
这些话尽管与他同时代那些言必称卢梭的民主主义者相背驰,却可谓是《民约论》后半部(第三、四卷)的真正知音。
但是,康有为的困境在于,由于“民主主义”对“共和主义”的吞噬,使他不得不将“共和”概念也出让给“民主主义”,最终使自己被笼罩在“专制主义”的阴影里无从解脱。从汉语的本意看,康有为所坚持的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力主“君民共治”,才是“共和”的真实表达。当然,其思想是否可以归为古典共和主义的范畴另当别论。然而,在康有为的论述里,几乎所有的“共和”都是“民主”的意思,都是康有为要抨击的对象!虽然这与“民主主义”的在卢梭之后的横肆是完全一致的,却仍令人对观念的宰制强力不寒而栗。
五
按照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看法,迄今为止,“德先生”(“民主”)的宏大工程在西方也未完成。(41) 从近百年中国政治现代性的进程来看,“民主”也属于不断接近的目标。其所以历经坎坷和曲折,对“民主”的误解以致膜拜是关键所在。
历史地看,康有为以君主立宪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实已包含了民主政治的要求,只不过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势力(所谓“后党”)却完全看不到妥协与权力让渡的必要性,所以,当这个有着明显英式共和主义宪政温和诉求的改革被血腥中断后,清政府也就此丧失了最后的自救的机会。自此以后,清政府的任何政治主张,包括“行宪”,就再未被信任过,而且,一有机会人们就要除之而后快了——为“行宪”成立的各省议会,正是如此成为清廷的掘墓人的。后人常将辛亥革命的胜利简化为所谓“武昌一呼,楚人一炬”,而实际上,各省议会的共同议决——“联省自治”——与军事革命在那一瞬间形成的合力,才是清王朝瞬间崩解的原因。
共和垂成的艰难,使人们对“民主”问题格外敏感。首先是“君主”政体被悬为“厉禁”:袁世凯为出任总统曾向南京临时政府一再承诺,“……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其“总统誓词”中也保证“当共和宣布之日,即今通告天下,为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其次则取法“民主先进”,将权力集中在议会与内阁,试图以之来全面控制国家。然而,事与愿违,由于对“民主通则”理解的各取所需,结果不仅形成了此后长期“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的渊薮,频繁的党争与政争也使袁世凯铤而走险,企图以帝制来恢复国家运转的基本秩序。众所周知,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结果除了自速其死,极大地加深了民主政体岌岌可危的印象(特别是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丁巳复辟”事件)外,也使得对“民主”的反思几乎不再可能,且有被视为居心叵测、卖身投靠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共和”危机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才表现出一种更加迫切的“民主”要求,其锋芒所向自然是直指那些据说与“(封建专制)君主”统治血肉相关的思想、文化与历史的根源——这当然只能是儒家,是“孔教”、“儒教”、“礼教”了。然而,把中国传统政治笼统归结为“封建(‘专制’)主义”,在传统文化(如“孔教”)与现代政治(如“共和”)之间“存其一必废其一”,显然是一种简单的推理——笔者无意否定五四运动的历史贡献——事实上,许多民主理论家,如托克维尔、韦伯,包括前述的卢梭,对民主与宗教的内在关系都有极其肯定的论述。(42)
九十年来,因为中国政治始终不能符合一些人理想中的“美国民主”模式—“民选总统”、“联邦自治”、“三权分立”——从而不断遭致否定和自我否定。然而,这种对美国民主的理解,乃是非常浅表化的。简要地说,“美国民主”乃是基于美国宪法的,而按罗伯特·达尔等人的看法,美国宪法是非民主的或反民主的,“共和主义”才是美国宪法的绳墨所在。(43) 那种以为只需要自由作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尽管个人自由的实现有赖于自由的人身关系,但自由的人身关系(自由伦理)却无法保障“自由”道德的实现,更无法保证如何塑造良好的政治公民。
九十年来,不断有人从各种角度反思“五四”,但对“民主主义”的信仰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愿本文的反思不会再一次被视为“反民主”的陂辞,就如当年的“君主立宪”主义所一再指向的“民主”认同被论战者视为狡饰。这也乃是本文执意于区分“民主”与“民主主义”这个几乎不可能的区分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 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上篇),载《北京大学月刊》1卷1号,1919-01。以上各译法,亦同参此文。
② 守常(李大钊):《Panthe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载《太平洋》,第1卷,第10号,1918-07-15。有关“五四”时期“民主”观念的流行,可参阅朱志敏:《五四民主观念研究》之第一章、第六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对“民主”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过程,可参阅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可以理解的是,两人对“民主”之为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主义话语,并无觉察。
③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0。
④ 参见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汪晖:《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上、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赵寻:《中国当代思想转折与汪晖的现代性论述》,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7)。
⑤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见《陈独秀著作选》,第232—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⑥ 胡适:《一年来对民主与独裁问题的讨论》,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卷,第5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⑦ 阎健编:《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⑧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397—398页,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⑨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15页注1,第129页注6,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⑩ Robert 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达尔的意图也许不一定是要恢复共和政治的理念,但是毫无疑问,其对立面是一人统治的王政。中译本见谭君久、刘惠荣译:《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 朱执信:《暴民政治者何?》,见《朱执信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朱文所述情形,并不只出现在“五四”之前,在民国期间此类说法同样十分常见。
(12) 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第一讲“民主从何而来”第6—8页的论述,第7页所附“雅典的抽签石盘”照片尤可一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3) Richard Wollheim,“Democrac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April,1958)19,pp.225—242; reprinted in Anthony de Crespigny and Jeremy Cronin,eds.,Ideologies of Politics,pp.109—13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4)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第39页,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5) 萧高彦:《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见《共和、社群与公民》,第10—1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6)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9页,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本文将其“集体”改译为“共同体”;下同。
(17) Chantal Mouffe,The Democratic Paradox.London:Verso Press,2000.
(18) 该书先后被译为《民约通义》(中江笃介译,上海,同文书局,1898)、《民约论》(杨廷栋译,《译书汇编》,1900.12—1901.12)、《卢骚民约论》(马君武译,上海,中华书局,1918)。
(19) [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第54页,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20)(21)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第255、25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2)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载《近代历史研究》,2008(4)。甘怀真的《皇帝制度是否为专制?》,见《钱穆先生纪念馆观刊》(四),1996-09。
(23) Tsuyoshi Saito,Meiji on Kotoba:Higashi kara nishi e no kakehashi,Tokyo:Kodansha,1977.([日]斋藤毅:《明治新词:从西到东的桥梁》)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第267页。
(24)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
(25)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九号,1906-11-15。
(26)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第254页。
(27) [日]竹内弘行:《后期康有为论:亡命 辛亥 复辟 五四》,日本,京都,同朋社,1987。
(28)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第498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
(29) 陈独秀是这一说法的创造者。但是,从“专制”推导出“帝制”、“封建”(时代),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0)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1)(32)(33) 《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9页;第10集,第39页;第11集,第49、56—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780—7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5)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0页。
(36)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10。
(37)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53页。
(38)(39)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54、174页。
(40) 康有为:《孔教会序一》,见《康有为全集》,第9集,第341页。
(41)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态度可以其著名演说《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目标》为代表。对他而言,现代性的目标也即是欧洲启蒙运动所揭橥的理性、民主和解放等现代价值;其所以“仍未完成”而不是已然失败,在于人们通过“交往理性”达成相互理解和彼此协调的潜能仍未充分实现([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与民主法制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2) 韦伯对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外,《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如果不是更值得关注,也同样值得重视。俱见《韦伯作品集》(12),康乐、简惠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对美国宗教与美国政治关系的考察,是托克维尔美国之行的重点之一,在其所著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n)一书中多见论述。此处仅举一例:“在美国,宗教从来不会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39页,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3) [美]罗伯特·达尔:《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s),佟德志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标签:康有为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袁世凯论文; 陈独秀论文; 君主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