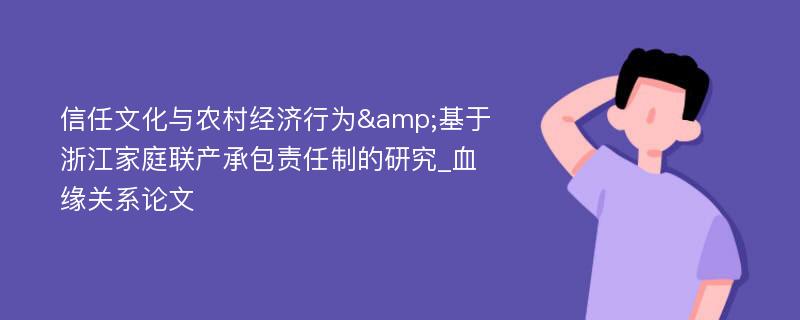
信任文化与农村经济行为——基于浙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承包责任制论文,农村经济论文,浙江论文,文化与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包括浙江人在内的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和准亲缘式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可以使人们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亲缘关系及其扩展形式如朋友、师生、邻里、熟人等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它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多线的、具有持久特征的社会关系。相互之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确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或明确的规章制度建立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也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来保证,而是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和保证的。”① 这种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和保证的、建立在亲缘或亲缘式个人关系基础上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社会功能,它给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方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这一方面,浙江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下面拟以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绩效为例,对此进行论述。
一
信任是人们对交换规则的共同理解,是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它支撑着广泛的经济关系和社会过程,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润滑剂,依赖于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如卢曼所说,信任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概括出一种行为期待,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匮乏。“信任并未消除风险,只是使之少些。它只是起了跳板的作用,帮助跳进不确定性。”② 信任强化现有的认识和简化复杂的能力,强化与复杂的未来相对应的现在的状态。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正因如此,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信任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③ 正因如此,从信任文化的视角切入,有助于对当代浙江区域经济现象有更全面的理解。
像全国一样,1978年以来的浙江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也是从农业领域起步的。在全国农村改革全面铺开的宏观背景下,1983年春,浙江全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迅速地达到了占总队数的94.7%。由不联产到联产,由联产到组到联产到户,极大地提高了浙江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迅猛地发展。1984年与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全省农业总产值从85.84亿元增加到125.22亿元,增长45.9%(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粮食生产取得了突破性的增长,总产量从1467.20万吨增加到1817.15万吨,增长23.9%,创历史最高水平;农民家庭平均收入从165元提高到446.37元,增长1.71倍。④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何以能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Lardy认为,始于大跃进时期的粮食自给政策(命令),使地方政府别无选择,只有迫使各生产集体在气候、土壤状况更适合栽种其他农作物的地区栽种粮食。直到农村改革开始之前,这项政策一直没有放宽。因此,粮食自给政策的实施及随后的放松,直接对应于利用地区比较优势的可能性的下降和增加。基于上述分析,Lardy提出了一个假设:正是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显著变化。Putterman,Dong和Dow,以及其他学者也持有与Lardy相类似的观点。⑤ 林毅夫则提供了另一个解释视野。他认为,在人民公社以及生产队制度下,农业生产率之所以显著下降,主要是因为努力和报酬之间联系不紧密造成的。在生产队劳动中,每个成员的预期收入既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程度,也取决于整个生产队的净产出。由于农业劳动中对每个成员的劳动实施监督的成本和对其劳动投入及其产出进行计量的成本都是相当高的,因此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努力与应得报酬取得一致。在无法实施有效激励和监督的情况下,具有经济理性的生产队成员,必然具有强烈的“搭便车”倾向,这决定了生产队的制度安排必然是低效率的。然而,“在家庭责任制下,监督的困难总的来讲得到了克服。根据定义,家庭制下的监督是完全的,因为一个劳动者能够确切地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劳动,且监督费用为零,因为它已不需要使用为执行劳动计量所花费的资源。其结果,一个在家庭责任制下的劳动者劳动的激励最高,这不仅是因为他获取了他努力的边际报酬的全部份额,而且还因为他节约了监督费用。”⑥ Lardy和林毅夫等人的解释,虽然从不同角度出发,但无疑都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他们的分析主要借助的是一种政策学和经济学的视角,但是,对上述问题更全面的解答,还需进一步诉诸于文化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视角。
二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全国农业生产效率之所以迅速提高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特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就此而言,浙江区域尤显典型性。因此,分析浙江现象,也就可以为理解中国现象提供一把钥匙。
在历史上,浙江是一个受血缘家族文化及其扩展形式影响较深的区域。据钱杭、承载的研究,历史上的浙东是强宗林立之地,“宗族之‘强’不仅表现在它外有雄踞乡里的经济实力和来自朝廷奥援的政治实力,还表现在它对本宗族内部秩序有效的管理。这两者在大部分场合下可能是统一的,尤其是浙东,这种统一在17世纪就已实现,并且程度也要较其他地区为高。”⑦ 周晓虹的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因诸种因素的影响,宗族血缘关系弱化从苏南到浙北、再到浙南呈递减状态。换言之,一直到1949年为止,温州一带对宗族血缘关系的重视,仍要强于浙北,尤其要强于苏南。⑧ 虽然,江苏与浙江农村中血缘关系的弱化在1840年西方列强打入中国之后已有相当的表现,但宗族血缘共同体的松懈程度以苏南为最,浙北次之,浙南再次之。比如,在苏南的昆山周庄农村,基本上一无公田,二无祠堂,而这种现象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十分普遍,所以陶煦在光绪六年(1880年)撰写《周庄镇志》时就说:“宗祠为近地所鲜。”⑨ 在周庄,起码自19世纪中叶起就已经不存在同族共聚祠堂祭祀祖先的现象、而家祭虽然供奉着“自始祖以下之主”的牌位,但大多数只涉及父母和祖父母两代。周庄所在的苏南一带的大多数地区很早就没有族长了,而浙南有些地方虽至20世纪30、40年代仍设有族长,尽管除了调解家庭内部或家庭之间的矛盾外,族长对族内成员的约束力已大为减低。⑩
浙北杭嘉湖平原一带可以看作苏南和浙南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与苏南类似,近现代以来浙北宗族血缘关系虽然仍然存在,但也有逐步趋于松懈的迹象,只是在松懈程度上较苏南弱,较浙南强。据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的研究,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浙北乡村到处散布着“家庭组合”式村落。这种村落内部的宗族组织已经解体,宗族血缘纽带已大大松弛,宗族意识已相当淡漠,家庭个体化、独立化已近完成,村落成为各独立家庭的集居地,村落的地缘关系高于血缘关系。宗族活动大多限于婚丧大事,家庭生产和生活的互助大多限于直系亲属和姻亲属及邻里的小范围之内。据当地老人回忆,在20世纪30、40年代,多数宗族并无族谱,少数保留族谱的“大宗富族”,其最晚的延修时间是清末民国初年。而在浙中的嵊县,1949年前,一些宗族,一般相隔30年修一次宗谱。家谱修成后要造祭谱酒,有的村还演谢谱戏。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嵊县所存历代宗谱,大多因破“四旧”而毁,但1985年,经初步查访,县内尚存王、张等96姓的家谱520部,其中明代1部,清代142部,民国197部,年代未详180部。此外,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浙北乡村,“绝大多数宗族并无族产,即令少数拥有族产的宗族,其数量也微不足道,其祠田收益或仅够每年一度的共同祭祀,或需各户分摊祭祀费用,或由经商致富者资助。”(11) 与浙北宗族文化的外在组织形貌的松懈形成鲜明对照,在浙南温州的虹桥,一直到1949年土改前夕,全镇仍然有宗族公田1078.41亩,占镇内8044.51亩土地的13.4%,并且宗祠也随处可见。(12) 而在浙东南的台州地区天台县,一直到1949年以前乃至于改革开放以前,全县乡镇多同姓聚族而居,连县城内也分族姓各居一处,如东门陈姓、溪头姜姓、桥上王姓、后司街曹姓。乡间则由几户、几十户,乃至几百户、上千户组成自然村落。绝大部分村庄是同一个宗族,也有大的宗族分居两个以上村庄,或一个村庄居住两个以上宗族的。聚族而居的村镇必有祠堂。祠又分大宗、小宗。全县最古老的祠堂是县城东门哲山的陈氏祠堂;最宏敞的祠堂是县城袁氏祠堂。民国《天台县志稿》称:“天台人,多聚族而居,重宗谊,善团结”,有“好勇斗狠之风,往往因雀角细故,而约期械斗”。若宗族中人有为外姓(族)所侮,则合族群起与外姓(族)争。或争执公山公地而族斗,或因几个人的事闹成斗殴;或因大族欺小族,小族起而反抗;或大族与大族之间各逞其雄而械斗。宗族械斗大多是由一些小问题引起的。
三
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效率之所以迅速提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隐含着承包责任制可以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而有力地借重于传统家庭亲缘关系的力量,从而有效地利用传统的信任资源。如前所述,这一点在全国受儒家文化浸润的地区都概莫能外,但可以从深受血缘家族文化及其扩展形式影响的浙江区域实践中得以充分地阐明。按照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传统人际关系是以血缘为序列,以父子为经、以兄弟为纬的立体关系网,几乎所有相识的人都可以被纳入这架网中,但不同人之间的关系却是不同的。这架立体网上不同的网结间,既具有远近亲疏的差别,也具有程度不同的信任关系。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像全国一样,浙江各地的传统社区、家族认同被取消,原来的家族和聚落被改造为以“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形式而存在的统一管理的生产和工作单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血缘为原则的聚落内部一体化与互助原则,创造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在“大队”和“生产小队”制度下,农民之间更多地是以邻里、朋友、生产合作伙伴等关系而进行交往的,家庭血缘关系则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但是,“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13) 按照“差序格局”理论,在特殊主义文化的信任背景下,邻里、朋友、生产合作伙伴等关系与血缘关系在立体关系网上的远近亲疏和信任程度是不一样的。王飞雪和山岸通过使用有关特殊信任的问卷进行调查(14),对于“下列几种人,你认为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这一问题的回答所得的结果表明,在特殊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所信任的其他人仍以与自己具有血缘家族关系的家庭成员和各类亲属为主,其中家庭成员得到的信任程度最大。虽然在“可以较多信任的一类”中,包括有不具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密朋友在内,但仅是一般性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其他人如同事、邻居、熟人等得到的信任,则介于“说不准”和“可以信任”之间。信任程度最低的则是不具有稳定社会关系的其他人。据此,按照信任程度的高低大小,可以将各类信任对象较清晰地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可以较多信任的一类,难以确定信任与否的一类和不可以过于信任的一类。
在人民公社以及“大队”、“生产小队”制度下,既然农民之间更多地是以邻里、朋友、生产合作伙伴等关系而进行交往的,因此,与家庭血缘关系相比,显然存在“信任不足”的问题。而如果人们在交易活动中缺乏信任,他们就必须花费大量资源在度量和监督方面,以防自己受骗上当。但是,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有效监督的费用必然是非常昂贵的,或者甚至也可以说,有效监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信任不足”问题,显然是人民公社制度下农业生产低效率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
与此形成对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借重的是家庭血缘关系的力量,而在特殊主义信任序列中,或者说,在“差序格局”中,家庭处于“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通路上离“己”最切近的位置。毋庸置疑,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信任程度是最高的。“‘己’实体不是独立的个体、个人或自己,而是被‘家族和血缘’裹着,是从属于家庭的社会个体。”“这样的‘己’,不同于西方的‘自己’,可以描述为‘家我’(family oriented self),它的内外群体界限是相对的。”(15) 因此,“以已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具有排他性。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家族血缘关系“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接纳,也就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信任的人际关系。
正因如此,1982年上半年,在浙江,凡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春粮、早稻都获得了普遍的增产,农村干部、群众普遍反映“联产比不联产好,包产到户比包产到组好。”(16) 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判断。
彼得·布劳认为,特殊主义具有区别集体的特殊属性,同时也把每个集体的成员联合起来,还在不具有特殊主义的人们之间起到分割的作用。“特殊主义的价值在副结构中创造社会团结的整合纽带,但同时也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副结构之间创造隔离性的界线”。(17) 所谓“副结构”,其实就是前述的“圈子”,特殊主义在一个社会中划分出了许多“副结构”或“圈子”。“这就提出了特殊主义标准的适用范围的问题——它们的联合性力量的范围有多广。作为一个事实,一个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主义的标准经常在它的副结构中变成普遍主义的标准。……与此相反,某种社会结构中的普遍主义价值可能在它的副结构中变成特殊主义取向的基础。”(18) 也就是说,“副结构”或“圈子”有大有小,相互套结。如果将彼得·布劳的分析框架略加引申,就可以看到,在生产交往活动单位中,与“生产队”相比,“生产组”显然是一个“副结构”或“圈子”,农民在“生产组”中,比“生产队”更易于建立亲密的或拟亲缘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也便具有更大程度的信任。但是,与“生产组”相比,家庭又是一个“副结构”或“圈子”,人们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经营活动中,相互之间无疑又具有比“生产组”更高程度的信任。由“亲”而信的人际关系模式即亲缘关系,实际上起到了一种信任的担保作用。家庭经济中存在着科尔内所说的保护性“父爱主义”。在家庭资源配置中,主要不是依靠供求关系、法律制度或行政命令,而是依靠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伦理规范等因素的作用,其中家庭伦理、亲情人情等规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家庭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被固定在由家庭和亲属联结的关系网络上,“人们基本的行为模式是相互依赖,即在亲属关系网络中,别人依赖他,他也同样依赖别人。每个人都十分明确对被赋予的东西要回报(尽管回报的时间或许很迟)”。(19) 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互利”在家庭经济中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正像“追求利润”在市场上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那样重要。(20) 在市场上,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在进行竞争,追求自身利益,而在家庭经济中,家庭成员对外竞争,对内采取互惠互利的利他主义原则,追求共同的利益。因此,在家庭成员之间,甚至在其他的亲属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个相互信任的、互惠互利的“保护性”网络。(21) 在家庭这一基于血缘的特殊关系的交换和组织中,成员之间具有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有了这种信任关系,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减少组织内部的“搭便车”行为,花费在度量和监督方面的资源就可以大大节省,讨价还价和扯皮的成本就可以大大地降低。这虽然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较高生产效率的唯一原因,但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① 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② Niklas lumann 1979 Trust and Power.John Weley & Sons Chichester,New York.33.
③ 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④(16)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当代浙江研究所编:《当代浙江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325页。
⑤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⑥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5页。
⑦ 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⑧⑩(12)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130、129页。
⑨ 光绪《周庄镇志》。
(11)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500页。
(13) 卢作孚:《中国的建设与人的训练》,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14)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载《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196页。
(15) 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6)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当代浙江研究所编:《当代浙江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17)(18) [美]彼得·布劳;孙非、张黎勤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页。
(19) [美]许烺光;薛刚译:《宗族、种性、俱乐部》,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20) 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21) 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