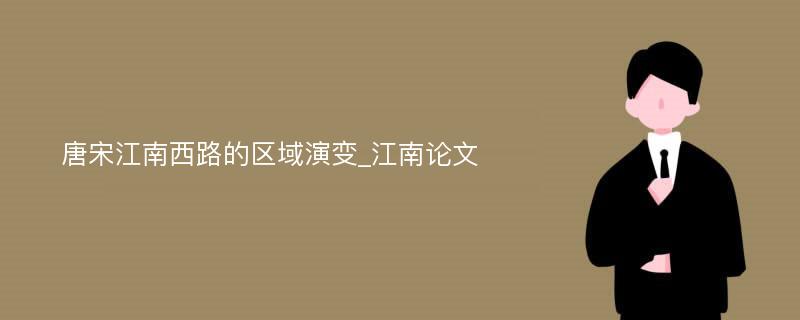
唐宋時期“江南西道”的地域演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唐宋论文,地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唐近三百年间,江南西道析分演变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唐貞觀元年(627),因“關河近便”,分天下爲十道,今長江以南與五嶺間劃爲江南道,其範圍,“東臨海,西抵蜀,南極嶺,北帶江”①,地域範圍過大。至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爲十五道,原江南道一分爲三:東部爲江南東道,西部置黔中道,中部地區爲江南西道。江南西道的範圍,約當今長江中下游以南、五嶺以北、雪峰山以東、天目山和武夷山以西地區,地域仍舊十分廣闊。肅宗至德(756-758)以後,爲對付安史之亂,唐廷將全國析劃爲四十多個方鎮。節度使方鎮與道逐漸趨同,形成了道(方鎮)、府州及縣的實際上的三級政區運作方式。其中,開元江南西道被拆分成湖南、江西、鄂岳及宣歙等四個觀察使轄區②,西北一隅的朗(治今湖南常德市)、澧(治今湖南澧縣)二州則北屬荆南節度。 綜觀唐代前中期的“江南道”,即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的地域演變,最值得注意的是,江南東、西二道的分界,並不是以今湘、贛二省間的羅霄、武功、萬洋等山爲界,而是大體以今江西東段省界爲限。這種地緣政治區劃的分割,在唐以前是從没有過的,唐以後也没再出現過。漢、晋、南朝數朝對“江南”地域的劃分,幾乎都是以中間的羅霄、武功、萬洋等山爲界,將長江以南一分爲二,西面劃歸荆州,東面劃屬揚州,直至唐代纔産生這種新的区劃方案。而且,開元江南西道的轄境遠遠大於江南東道。唐廷最初的劃分,必定有其合理的一面,後來的再次析置,又是出於對新形勢的考慮,隱藏著新的誘因。 由此可見,唐開元末的“江南西道”的劃分可謂空前絶後,唐代是長江中游以南、五嶺以北地域分化與整合史上的關鍵階段,宋代則是這種新分化發展及初步定型的時期。宋代的“路”制表面上看是對李唐“道”制的一個揚弃,實則體現了繼承與發展。並且,以“貞觀十道”爲代表的唐“道”的地域劃分,後世特別是五代及宋,依舊盛行。③然則以“道”的地理範圍討論該地域在唐宋時期的演變,能够更好地把握其內在動因與影響。本文的討論即以開元末的“江南西道”的空間範圍爲限定,討論該地域在唐宋數百年間的演化進程。 一、“山川形便”與“關河近便”:貞觀十道 唐《通典·州郡典》載:“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貞觀初,並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爲十道:一曰關內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東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隴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劍南道,十曰嶺南道。”④對於貞觀十道,史無异說。而道的劃分原則,兩《唐書·地理志》與《通典》略同。《唐會要》則謂:“貞觀元年(627)三月十日,並省州縣。始因關河近便,分爲十道。”⑤細玩二文,貞觀十道的劃分原則,《通典》等書謂“山河形便”,《唐會要》則曰“關河近便”,一字之差,初看無甚差別,實際則別有內涵。 史念海先生在《論唐代貞觀十道和開元十五道》一文中論述關內道時,說:“這樣的山川形便,以之拱衛關內道,自然極爲有利。不過當時似還感到未能就此有恃無恐。唐初爲了配合各方軍事活動.在各地設關置守,以補山川形便的不足。”⑥這一觀點爲我們理解《唐會要》的記載提供了綫索。據《唐六典》:“司門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諸門及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凡關二十有六,而爲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爲上關;餘關有驛道及四面關無驛道者,爲中關;他皆爲下關焉。”⑦山川之間往往未必完全密合,而且,兩山之間的隘口,或者山川之間的交接處,常成爲交通驛道的必經之處。在此設關,關與山河相結,恰好形成一個密閉的完整區域,可以方便的進行對外守禦和對內管理,如關內道就設有潼、散、藍田、子午等關,關與山川緊密結合,“有了這樣一些設施,作爲都城長安所在的關內道,就可能因若金湯,不虞外來的侵擾和攻擊了”⑧,正所謂:“所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止暴者也。”⑨由此可見,對於貞觀十道的劃分原則,《唐會要》言“關河近便”更爲貼切。 十道的具體範圍,《唐六典》對貞觀十道的劃分有明確的記載: 郎中員外郎,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爲貢賦之差,分十道以總之。一曰關內道……東拒河,西抵隴阪,南據終南之山,北邊沙漠……二曰河南道……東盡於海,西距函谷,南瀕於淮,北薄於河……三曰河東道……東距恒山,西據河,南抵首陽、太行,北邊匈奴……四曰河北道……東併於海,南迫於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關、薊門……五曰山南道……東接荆楚,西抵隴蜀,南控大江,北據商華之山……六曰隴右道……東接秦州,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朔漠……七曰淮南道……東臨海,西抵漢,南據江,北距淮……八曰江南道……東臨海,西抵蜀,南極嶺,北帶江……九曰劍南道……東連牂牱,西界吐蕃,南接群蠻,北通劍閣……十曰嶺南道……東、南際海,西極群蠻,北據五嶺。⑩ 因“關河近便”所劃分的區域,朝廷的官員在地方巡察時,不至於跋高山涉深水。這種主要依照自然區界劃定的地域範圍,不僅使地理範圍本身,亦使十道之名稱成爲一種固定的地理概念,對當時及後世産生了重大影響。 貞觀十道,既無固定治所,亦無穩定建制,只是大體劃分了道的區劃、範圍和境內的州數量,並非實際的高層政區。朝廷雖然因實際需要,會派遣使者分道執行某些政務,但都是臨時措置,事畢即罷。儘管如此,這種大的自然區域劃分,看起來十分方便快捷,但在實際運作中,卻存在重大缺陷,即:地域範圍過大,以及由此帶來的行政效率低下。貞觀十道時期,平均每道管州三十左右,尤其是劍南、江南、嶺南諸道,管州都在四十以上,甚至更多。每道的管理幅度太大,朝廷若遣使巡察這幾個道,往往很難走完全程,勢必影響行政效率。(11)《唐會要》記曰: 萬歲通天元年(696),鳳閣舍人李嶠上疏曰:“陛下創置左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否,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疏,法令宜簡,簡則事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686),諸道巡察使科目,凡四十四件,至於別作格敕令訪察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之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委積,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尚一千已下,皆須品量纔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皆所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12) 因此,出於實際行政能力的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唐廷開始將一些較大的道進行拆分,道的數量開始突破十個。如山南道,“景雲二年(711)五月,出使者以山南控帶江山,疆界闊遠,於是分爲山南東、西兩道;又自黄河已西,分爲河西道”。(13) 二、開元“江南西道” 至開元二十一年(733),唐廷正式分天下爲十五道,並於每道置采訪使以檢察非法,同時規定確立了十五道的治所,常設不撤。據《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京畿,理西京城內;都畿,理東都;關內,多以京官遙領;河南,理陳留郡;河東,理河東郡;河北,理魏郡;隴右,理西平郡;山南東,理襄陽郡;山南西,理漢中郡;劍南,理蜀郡;淮南,理廣陵郡;江南東,理吳郡;江南西,理豫章郡;黔中,理黔中郡;嶺南,理南海郡。”(14)兩《唐書·地理志》略同。但是,嚴耕望先生據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的《唐六典》及《册府元龜》考證,此時十五道中尚無黔中道(治今重慶彭水縣)而有河西道,《通典》所記不確。(15)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三○“黔州”:“開元二十六年,又於黔中置采訪處置使,以(黔中)都督渾瑊爲使。”(16)至此,唐代的道制已增爲十六道。對於江南道析置爲東、西二道,嚴耕望先生在《景雲十道與開元十六道》一文中也作了詳細考證。他認爲,江南道析置東、西二道,亦不在開元二十一年,而在與山南道分東西的同一年,即景雲二年(711)(17),此說甚是。然則江南西道的出現,不至晚到開元二十一年,在此之前,早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 實際上,對於貞觀十道至開元二十一年的十五道,我們不妨可以這樣理解,即開元二十一年的十五道並非一次驟然完成,而應是根據實際需要逐漸劃分出來的。這一點由開元二十六年,黔中道從江南西道中分離出來可得一旁證。因此,所謂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應是唐廷對這種既成事實的一種官方正式肯定而已。正因爲如此,此事意義極大,以至在時人的腦海中形成一種意識,開元十五道遂成爲一種潜在觀念。後人修書時不審,故出此紕漏。(18)由貞觀十道至開元十五道,道的範圍變小,境內州數減少,平均每道內有州二十左右,大大方便了官員的巡察。 貞觀十道的劃分原則爲“關河近便”,十五道主要由十道分置而來,其劃分原則也大體若是。如山南東道與山南西道的分界綫,北段上部沿著漢中盆地的西側,中段則以大巴山爲界,基本上是今天川、陝、鄂省的省界,南側則以成都平原西側山脉爲界;江南東道與江南西道的分界綫,北段以天目山、懷玉山東側爲界;南段以武夷山爲界,基本與今天閩贛省的省界相似。 尚有值得注意者,前引諸書記“山川形便”與《唐會要》“關河近便”中的“便”字的涵義。這裏是否還可以這樣理解,即除依照山川的自然區來分界外,道的劃分,在細節上還要考慮到朝廷官員出行的距離遠近及便利與否,也就是交通的優勢問題?尤其開元以後,巡察使多由地方刺史兼任,因此巡察路途遠近及便利與否勢必作爲考慮的因素之一。這種例子有很多,如虢州(治今河南靈寶市)原屬河南道,“開元初,以巡按所便,屬河東道”(19),時河東道按察使多由蒲州(治今山西永濟市西南蒲州)都督兼任,蒲州南下由風陵津渡黄河即是虢州(20),路程很近;與此相比,當時河南道按察使多由汴州(治今河南開封市)刺史兼任,由汴州至虢州,距離就較爲迂遠,這樣虢州改屬河東道就打破了單純依照自然區劃的原則。江南西道內部也有較爲典型的,如南部所轄連州(治今廣東連州市)跨過五嶺,延伸到嶺南地區;東北角的宣州(治今安徽宣城市)一直延伸到江南東道內部。特別是宣州,在江南道初分東、西二道時,甚至“統江南之西”,以宣州來巡察包括譚、衡等十六州在內的江南西道。(21)宣州能够“統江南之西”,是與優越的交通區位分不開的。 開元二十六年(733),江南西道析置出黔中道後,江南道已被一分爲三:江南東、西與黔中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黔中道理黔州。江南西道簡稱江西道。江南西道采訪使的理事範圍,《唐六典》、《舊唐書》與《新唐書》的記載不同。 成書於開元年間的《唐六典》,記“江南道”: 江南道。古揚州之南境。今潤、常、蘇、湖、杭、歙、睦、衢、越、婺、臺、温、明、括、建、福、泉、汀、宣、饒、撫、處、洪、吉、郴、袁、江、鄂、岳、潭、衡、永、道、邵、澧、朗、辰、叙、錦、施、南、溪、思、黔、費、業、巫、夷、播、溱、珍,凡五十有一州焉。(22) 李林甫注《唐六典》,於“汀”之後注“已上東道”,但後面三十三州再未出注。史念海先生以《新唐書》所記,認爲此處注文可能有脫漏,後面三十三州應分屬江南西與黔中道,這個觀點十分恰當。然此三十三州究竟如何分屬又是一個問題。考“叙州”,《新唐書·地理志》載:“本巫州,貞觀八年(634)以辰州之龍標縣置,天授二年(691)曰沅州,開元十三年(725)以‘沅’‘原’聲相近,復爲巫州,大曆五年更名。”(23)“叙州”雖出現於唐初,但天授年間即改它名,至大曆五年(770)纔又恢復原名,而《唐六典》爲開元年間張九齡等人撰,成於開元二十六年(733),李林甫隨後奉敕作注,次年完成。(24)林甫卒於天寶十一載(752),知《唐六典》成書之時,尚無叙州之名,該書此處不僅注文脫漏,三十三州正文亦極有問題,是《唐六典》不能作爲開元末江南西道轄境的依據。 兩《唐書·地理志》對勘,又有問題。《舊唐書》記歙州歸江南東道,而《新唐書》則記在江南西道下。《唐六典》所記江南東道有歙州,與《舊唐書》合,開元時歙州當屬江南東道。至此,開元江南西道所含州目,可以得知,即: 宣州(治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 饒州(治鄱陽,今江西省鄱陽縣) 洪州(治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 虔州(治贛縣,今江西省贛州市) 撫州(治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西北) 吉州(治廬陵,今江西省吉安市) 江州(治潯陽,今江西省九江市) 袁州(治宜春,今江西省宜春市) 鄂州(治江夏,今湖北省武漢市) 岳州(治巴陵,今湖南省岳陽市) 潭州(治長沙,今湖南省長沙市) 衡州(治衡陽,今湖南省衡陽市) 澧州(治澧陽,今湖南省澧縣東南) 朗州(治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 永州(治零陵,今湖南省零陵市) 道州(治營道,今湖南省道縣西) 郴州(治郴縣,今湖南省郴州市) 邵州(治邵陽,今湖南省邵陽市) 連州(治桂陽,今廣東省連州市) 總計十九州。相其地理範圍,約當今江西省全境,湖南雪峰山以東地區,湖北省東南部的鄂州、黄石、咸寧全境及武漢市的部份地區,安徽省的宣城、池州、銅陵及馬鞍山市境以及江蘇省南京市的部份地區。 三、從“江南西道”到“江南西路” 唐中期於邊境置節度使,設置軍事區域,加强對邊境的軍事防務。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後,中原連年戰亂,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等名稱。要衝大州,都設立節度使。這些節度使管的州多,有兵權、財權,往往擁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與朝廷對抗的局面。在藩鎮割據形勢轉趨緩和以後,節度使多半改爲觀察使。江南西道整體上一分爲四,略述於後: 1.湖南觀察使。至德二載(757),“置衡州防禦使,領衡、涪、岳、潭、郴、邵、永、道八州,治衡州(治今湖南衡陽市)。”廣德二年(764),“置湖南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治衡州,領衡、潭、邵、永、道五州,治衡州”。至“大曆四年(769)湖南觀察使徙治潭州(治今湖南長沙市)”。(25) 2.江南西道觀察使。乾元元年(758),“置洪吉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使,兼莫徭軍使,領洪、吉、虔、撫、袁五州,治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上元元年(760)“洪吉觀察使增領信州(治今江西上饒市)”。廣德二年(764)“洪吉都防禦團練使觀察使,更號江南西道”。貞元四年(788),“江南西道觀察使增領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26) 3.宣歙觀察使。乾元元年(758),“置宣歙饒觀察使,治宣州”。二年,“廢宣歙饒觀察使”,宣州併入浙江西道。至大曆元年(766),“浙江西道觀察使罷領宣、歙二州。復置宣、歙、池等州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兼采石軍使”。(27) 4.鄂岳觀察使。乾元二年(759),“置鄂、岳、沔三州都團練守捉使,治鄂州(治今湖北武漢市)”。上元元年(760),“岳州(治今湖南岳陽市)隸荆南節度”。永泰元年(765),“升鄂州都團練使爲觀察使,增領岳、蘄、黄三州”。(28) 這樣,江南西道被調整爲宣歙、江西、湖南以及鄂岳四個觀察使轄區,朗、澧二州則北屬荆南節度。這其中,江西觀察使已經和今天的江西省境基本一致,是一塊完整的自然地理區域;湖南觀察使則對應於湘、資二水流域;宣歙則將今安徽南部山區與長江南岸沿江平原包括在內;鄂岳觀察使則轄洞庭湖周圍以及幕阜山與長江之間的地帶。 宋人歐陽修說:“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録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没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29)五代時期出現了以軍的名號代替州名的區劃,並統轄數縣。在某地建立“軍”或改某州爲“軍”,表示對該地的重視,這種措置,一直延續至宋代。 北宋初曾因循唐代的道制,太平興國四年(979)曾分天下爲十三道,其中有江南西道。而十三道中轉運使所領道,又被稱爲路(30),江南西路此時開始出現。同唐代的道相似,宋代的轉運使路制的演變也相當頻繁,但宋廷亦有明確統一分路的規定。太平興國四年,宋分全國爲二十一路,此後歷經變化,到了至道三年(997),始定天下爲十五路。唐開元末的江南西道的主體部份,被劃爲江南西路、荆湖北路,原宣、歙、池等州屬江南東路,鄂、岳二州則歸荆湖北路。此後路制變化頻繁,但該地區的分屬,除個別州、軍外,變化並不大。至道三年以後,從這十五路中又陸續分出一些新的路。天禧四年(1020),之前短暫合併成的江南路,復分江南爲東、西二路,於是共爲十八路。 宋初,太祖、太宗兩朝爲防範西、北二敵,爲維護漕運河道等交通命脉,加强對廣大南方地區的控制,先後於川峽、河北、河東、陝西及京東、江南、淮南、福建等地設置了四十餘軍,以控扼衝要之地。這一時期的軍大多有屬邑,少則一、二縣,多則三、四縣,軍治所在地原有的縣,基本不撤銷。開元末江南西道在宋代所含統縣政區,除州以外,也有軍、監等特殊政區出現。軍有南安、南康及武岡等七個;監則僅桂陽一個,但南宋時升爲軍。北宋政和元年(1111),總計開元末江南西道所含統縣政區,除朗州更名鼎州外(31),還有以下十二個: 池州(治貴池,今安徽池州市) 太平州(治當塗,今安徽當塗縣) 信州(治上饒,今江西上饒市) 南康軍(治星子,今江西星子縣) 筠州(治高安,今江西高安市) 興國軍(治永興,今湖北陽新縣) 建昌軍(治南城,今江西南城縣) 南安軍(治大庾,今江西大餘縣) 臨江軍(治清江,今江西樟樹市西南臨江鎮) 全州(治清湘,今廣西全州縣) 桂陽監(治平陽,今湖南桂陽縣) 武岡軍(治武岡,今湖南武岡市) 降至南宋,統縣政區的數目較爲穩定,其變化主要體現在名號上。例如將一些州更名爲府:洪州更名隆興府、鼎州更名常德府等等。此外,虔州於紹興二十三年(1153)更名爲贛州。(32) 較之李唐,宋代是中央集權高度發展的朝代,中央政府顯然有意識地使作爲高層政區的某些路的轄境,偏離“山川形便”的原則,以利於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宋代的江南西路並不和唐後期自成一地理區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東北一隅的南康軍、江、饒及信三州,並在西北邊越過幕阜山而領有興國軍(今湖北省的東南部)。江州、饒州、信州、南康軍等四州軍屬江南東路,與長江南岸的江寧府(今南京市)、宣州、歙州、池州、太平州、廣德軍等共爲一個大行政單位。這樣一來,江南西路就不再是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域了。“江南西道”地域統縣政區,由唐代的“關河近便”到宋代的“犬牙交錯”的演變,體現了兩個中央集權王朝對地方管理的思路的轉變。 四、對唐代“道”制的再思考 “道”的作爲行政區劃概念的使用可以溯源至漢,“凡縣,主蠻夷曰道”(33),當時是一種設於少數民族居住區的、與縣同級的管理單位。至唐貞觀元年(627),以“關河近便”,分天下爲十道,重新劃分全國的疆域。長江以南地區被整合爲一個面積廣袤的江南道。這種區域劃分並非地方行政區劃,嚴耕望先生甚至認爲:“彼時十道僅爲地更名稱,至於施政無大關係。”(34)十道劃分以後又有分道巡察之舉,這種分道巡察並非唐代首創,應是效仿了漢代分天下爲十三州部刺史巡察天下的辦法。可是,以十道巡察不久,巡察官便紛紛因“疆界闊遠”而“力不及”,在規定的時間內無法完成巡察任務。於是十道得以再分,其中江南道最初被一分三:江南東、西及黔中。 三道相比,江南西道的特點有二:一是幅員最廣,二是中間被縱向的高山隔斷。如果說對監察區而言,這個幅員尚可以接受,中間的隔斷可以憑藉山間孔道及長江航道連通的話,隨著生産的發展,地域間主要是東、西部亞區之間的差异,開始變得明顯。在江南西道逐步演變爲統縣政區的過程中,加之幅員太廣與高山阻隔,使其有再被劃分的可能。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後,出於內部軍事的需要,江南西道終於被分離。安史之亂以後,唐廷對地方的管理,“道一級建制的管理區劃在戰時調整中變小,但道作爲一級中間權力機構、行政管理單位實體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加强,並通過與節度使制的結合,增加了軍事管理方面的功能。隨著道的實體化發展過程的完成,唐廷的地方行政管理逐漸形成了中央—四十餘道—三百餘州、府—一千四百餘縣的三級制體制。”(35) 不過,反過來考慮,江南西道的最初整合又有其內在的合理因素。除幅員仍較爲廣闊,卻適合官員巡察外,交通便利與軍事需要又都促成其整合爲一體的重要原因。交通的便利,主要體現在過嶺交通這一南北交通大動脉上,對這一問題將在後面的章節中詳細論述,此不贅述。軍事控守的客觀要求,並非安史之亂以後,主要出於加强今湘贛地域內部控制的需要,而是江南西道對唐代控制嶺南地區的重要作用。這個作用可以從江南西道一分爲四後,逢五嶺有事,唐廷的作法反證。唐懿宗咸通年間(860-874),南詔兵亂,“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36)又“征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澪渠,並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湘、澪溯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37)糧運爲湖南、江西兩路並進,“以饋行營諸軍”,說明軍隊也是如此行進。秦漢時期對嶺南用兵,同樣需要在湖南、江西兩路並進來完成,開元末的江南西道,正是將這兩路納入一個巡察體系之中。這種措置至宋代亦常常用到。宋皇祐時(1049-1054)嶺南儂智高反,孫沔以“廣,天下寶貨之儲,而蕃舶之家,常以億萬計”,被任命爲“江南西路荆湖南路安撫使”,統一征討,後又加“安撫池江饒太平四州”。(38)孫沔安撫的地區,與開元末的江南西道相差無幾。但是,嶺南地區畢竟不是唐宋的軍事重心所在,特別是宋代,其外部壓力主要來自北方,兩路並舉的的措置只有嶺南有大亂時纔會用到,基於前述原因,開元“江南西道”被析置以後,再没有整合在一起實是勢所必然。 唐代的十道與十五道的影響都較爲深遠。唐元和年間成書的《元和郡縣圖志》,五代、北宋修撰的舊、新《唐書·地理志》,都以十道爲綱,分全國爲十個大區,再以十五道爲目對統縣政區分別記載。十道與十五道,十五道應是對十道的細化,是區域內部差异的表現之一,江南道分爲江南東、西及黔中道是最好的證明。史念海先生甚至認爲:“這十五道區劃的沿用時期,遠較十道區劃爲長久。”(39) 唐代江南西道是中央重要的財賦來源,宣州及鄂、岳二州則是東南貢賦北運的重要通道。元和二年(807)李吉甫上國計簿稱:“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40)杜牧曾上書言:“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賊耳。”“濠、亳、徐、泗、汴、宋州賊多劫江南、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光州賊多劫荆襄鄂岳等道。”(41) 開元末年的江南西道中,僅占據沅水流域的下游地區,其上游則歸黔中道屬。江西道與黔中道以雪峰山爲分水嶺。安史之亂以後,由江南西道析置出湖南觀察使,僅據有湘、資二水流域,“湖南”卻逐漸成爲約定的稱謂。至宋代在該地區設荆湖南路,簡稱“湖南”,仍舊只有湘、資兩個流域,沅水及其北面的澧水流域歸荆湖北路管轄,這種情况延續到清代纔得到改變。 唐宋六百多年間,即便除去中間的五代分裂割據數十年,在唐宋兩個大一統的王朝中,開元“江南西道”地域的演變依然是十分劇烈的。由最初面積廣袤的江南道,到初分的江南西道(含後來的黔中道),再到開元末的江南西道,今湖南江西地域的分化演變已經歷了一百多年。不過這種分化的趨勢並没有結束,安史之亂以後,江南西道一分爲四,經過五代十國的分裂到宋代也再没有重新整合。不過,宋代該地域的行政區劃與前代又大有不同,反映出在經歷唐末方鎮割據及五代十國割據之後,宋廷對於經營該地區的新思路。宋代還在該地區設置了多個統縣軍,對於這些統縣軍逐一進行分析其特點,並從整體上把握軍的空間分布,可以加深對軍的認識,從而更好地理解該地域在宋代的發展,此有待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①李林甫:《唐六典》卷三“戶部郎中”,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70頁。 ②據《唐六典》及《舊唐書·地理志》,開元江南西道不包括歙州,考慮到宣、歙兩州後整合爲一個觀察使轄區,故放在一起討論。 ③王溥《五代會要》卷二○《選事》載:“後唐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吏部三銓下省南曹廢置、甲庫格式、流外銓等司公事,並係《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等格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58頁)王應麟《玉海》卷一四《景德重修十道圖》載:“淳化四年,分天下爲十道。景德四年八月己酉,命知制誥孫僅、龍圖閣待制戚綸重修十道圖。祥符六年十月戊子,判吏部真從吉言,格式司用《十道圖》,考郡縣上下緊望,以定俸給法,官亦以定刑,而戶口歲有登耗,請校定新本。”(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307頁)宋淳化四年(993)曾一度分天下爲十道,又《十道圖》本爲唐修,不僅有十道域分之圖,且包含大量銓選、定賦、土貢等方面的文字材料,應該是類似圖經一類的總志書,不管怎樣,《十道圖》以“道”爲綱並爲五代及宋沿用是没有問題的,後文還有論及。 ④杜佑:《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478頁。 ⑤王溥:《唐會要》卷七○《州縣分望道》,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231頁。 ⑥史念海:《論唐代貞觀十道和開元十五道》,《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36頁。 ⑦《唐六典》卷六“司門郎中員外郎”條,第195頁。二十六關詳參同條唐人李林甫注。惟二十六關無一在江南西道境內,故不展開論述。 ⑧《論唐代貞觀十道和開元十五道》,《唐代歷史地理研究》,第37頁。 ⑨《唐六典》卷六“司門郎中員外郎”條,第196頁。 ⑩同上,卷三“戶部郎中員外郎”條,第64~72頁。 (11)郭峰:《唐代道制改革與三級制地方行政體制的形成》,《歷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1頁。 (12)《唐會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撫等使》,第1414頁。 (13)同上,卷七○《州縣分望道》,第1233頁。 (14)《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第4479頁。 (15)嚴耕望:《景雲十三道與開元十六道》,《史語所集刊》第三十六本,1964年,又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第195頁。 (16)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江南道》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36頁。 (17)《景雲十三道與開元十六道》,《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第195~196頁。嚴氏認爲,開元分十五道在二十二年,而非《通典》、兩《唐書·地理志》所記二十一年,拙見不敢苟同,仍暫取二十一年,待考。 (18)此事仍有探討的餘地,惟此處不在討論這種觀念,俟以後再論。 (19)劉昫:《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29頁。 (20)《元和郡縣圖志》卷二《關內道》二:“潼關,在縣(華州華陰縣)東北三十九里……河之北岸則風陵津。”河即黄河。第35頁。 (21)陳簡甫:《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文苑英華》卷八三○,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4380頁。 (22)《唐六典》卷三“戶部郎中員外郎”條,第64頁。 (23)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074頁。 (24)永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九《史部》三十五,萬有文庫排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第16頁。 (25)《新唐書》卷六九《方鎮表》六,第1938頁。按涪州(治今重慶市涪陵區),《元和郡縣圖志》卷三○《江南道》六涪州:“元和三年(808),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奏曰:‘涪州去黔府三百里,輸納往返,不逾一旬。去江陵一千七百餘里,途經三峽,風波没溺,頗極艱危。自隸江陵近四十年,衆知非便,疆理之制,遠近未均,望依舊屬黔府。’”涪州與湖南道相距甚遠,疑有誤,待考。 (26)《新唐書》卷六八《方鎮表》五,第1910頁。按由此以下二道引文出處同,不一一出注。莫徭,《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澧陽、衡山、熙平皆同焉。”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898頁。 (27)《新唐書》卷六八《方鎮表》五,第1905頁。 (28)同上。 (29)歐陽修:《新五代史》卷六十《職方考》,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45頁。 (30)此外又有淳化四年(993)分天下爲兩京十道,翌年即罷。見《玉海》卷一八六、《宋史》卷一六二《職官志》。宋初分道及歷朝諸路,詳張家駒《宋代分路考》,《禹貢》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1935年,第25~44頁。 (31)脱脱等:《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常德府”:“鼎州……本朗州,大中祥符五年(1012)改今名”,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194頁。 (32)據《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及校勘記,第2189頁。 (33)司馬彪:《續漢書》志二八《百官志》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623頁。 (34)《景雲十三道與開元十六道》,《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第193頁。 (35)《唐代道制改革與三級制地方行政體制的形成》,第103頁。 (36)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五○《唐懿宗咸通四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8104、8105頁。 (37)《唐會要》卷八七《漕運》,第1599頁。 (38)滕甫(元發):《孫威敏征南録》,《全宋筆記》第一編八,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5頁。 (39)《論唐代貞觀十道和開元十五道》,《唐代歷史地理研究》,1998年,第32頁。 (40)《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唐憲宗元和二年》,第7647頁。 (41)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全唐文》卷七五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7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