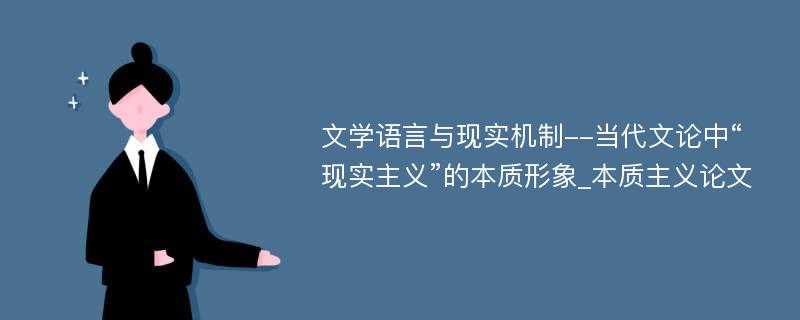
文学语言与现实机制——当代文论中“现实主义”的本质主义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语言论文,文论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本质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1)04-0119-04
“文学反映现实”涉及“语言”和“现实”、“形式”和“内容”的等级关系,即现实高于语言,语言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一创作方法坚持词语和现实的亲和关系,以此强调人民改造世界的力量以及世界的可知性。“文学反映现实”在后来的文学反思中被作为文学本质化的具体表现,特殊的政治规定塑造了文学的僵化形象。“二十七年文学”的“创作方法”伤害了现实本身,因为这种创作方法严格遴选有限的“现实”景象,只有光明的国家现实才是最终的真实。形式主义包含的个人意愿往往被视为败坏国家精神的流毒,“精神”和“意志”等带有集体感和光明气质的词汇更容易让人接受。在这一特定时期,人们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实际上集中于它通过语言的机巧表现出的没落、反动现实,可以说,这仍旧是内容层面的反感。宏大政治掏空了“现实”的丰富特质,这才是后来人批判“文学政治化”根本缘由。
借助于“现实”政治性和集体色彩的详细规定,“语言反映现实”就成了对现实的唱盛,“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在这里是不合法的。“哲学上的现实主义的总体特征是批判性的、反传统的、革新的:它的方法是由个体考察者对经验的详细情况予以研究,而考察者至少在观念上应该不为旧时的假想和传统的信念的本体影响:它还使语义哲学,即词语与现实之间一致性的本质的命题真有特殊重要的意义。”①这段话暗示着一下几个层次的意思:第一,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相互关联;第二,个人化视角是文学批判性的重要支撑。“二十七年文学”关于“现实”的政治表述恰恰去除了个人性和批判性,这是文学本质化的具体表现。“集体性”并非一无是处,纯粹的个人性也将导致文学的本质主义,集体性和个人性的整合才是文学去本质化的上策。此外,在有些人看来,“政治化现实”“这种框架隐秘地表现着一种规范性的看法,即把物质基础作为真正的现实存在。因而,在政治上就低估了非物质力量,尤其是个体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力量,以及它们的政治功能。”②马尔库塞将丧失个性意识的文学病归罪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论过分强调物质基础的重要性,从而束缚了“非物质力量”的反作用。然而,这种说法完全否认了“现实”的意义,同时也回避了个体意识的外在现实基础,从而取消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这和“二十七年文学”的境况并不一样。不可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支撑着“二十七年文学”国家叙事的一整套文学规律,在此基础上文学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魅力,这并没有改变机械决定论人为地规定何谓“真实”的文学事实。“二十七年文学”的问题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决定论的僵化。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真正“现实”的严格规定,就会面临逻辑怪圈:资产阶级的“现实”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来是伪现实,那么是否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永远不能塑造出现实的真理?这种缺失是否意味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限度?逻辑的矛盾显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级性“现实”本质规定的某种尴尬。
在“二十七年文学”教科书语法中,关于“真实是什么”的确切表达并没有妨碍“什么是真实”的语义游击,和政治挂钩的“现实主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万能术语。“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赞同的文学清规戒律,其本质的规则体系一直以来都是笼统的、貌似简单的,这实在是有意而为之。因为表述的笼统、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可以为自己留有余地,保证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下能够机动回旋。”③文学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中获取模糊美学的真谛,但所指的流动性却无法改变“现实主义”本质倾向。因为这种形式的语义添加不是文学历史性的表现,而是政治的时期表达在文学中的强制表现,是现实的政治学逻辑对文学的规约。这样,不断膨胀的“现实主义”也被冠以“机会主义”的帽子。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国语境中的相互对立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的内涵融合感到不解。“现实主义”不断截取“自然主义”的原有内涵,却又始终将“自然主义”作为对立面,这说明对立的始终是作为阶级招牌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拥有了真理的确定性,那么自然主义等就自然而然成为现实主义的剩余物,它们以非现实主义的形象出现。“现实”在这里决不是现象学上客观存在,而是一种革命政治理念。阶级观念的文学表达和政治学逻辑合力造成了“现实主义”本质化和概念模糊之间的矛盾,当然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肯定党性原则,即对党不断变化的姿态保持忠诚,是文学理论和美学问题的基石。”④
新时期文论观念强调外在世界描写的主观性,在文学实践中则表现为动用具体的文学技巧以彰显语言的力量。纯文学直指主观性和个体性,这仍旧顺延了“二十七年文学”的文论逻辑,因为它把“个体主观性和形式主义”与“集体性和现实主义”截然划分开来。其实,在“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上,纯文学和“现实主义”也没有太大的分歧。纯文学以远离现实主义为己任,通过主观变形达到陌生化效果。“纯文学”并不排斥他们自身所处的当下现实,它反思的对象是“二十七年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现实,这种现实被符号化为“缺乏想象力的统治政令”。具体地说,纯文学时代并没有反驳“文学反映现实”,只不过人们提倡曲折地反映现实。语言变形记实际上并没有取消“现实”的地位,世界仍旧可知,纯文学的审美立足于原本就是在启蒙的总体氛围中证明人的主体性。因此,“纯文学”所持的“语言反映现实”的观念和具体文学实践中回避现实的倾向存在落差,纯文学的实践者们还没有从之前政治文学的威压中解脱出来,积极介入当下现实的书写,以至于造成自身“反现实”的假象。⑤“纯文学”顾虑的是以怎样的文学方式表现的现实。不可否认,过度的形式实验使纯文学的具体文本晦涩难懂,因此也大大冲淡了文学介入现实的功能。纯文学的本质倾向是因为它极端热衷某种表现现实的文学手法,而不是文学和现实割裂以及由此引起的历史性的消失。虽然师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理念,但是在“语言和现实”关系上,纯文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现实”被全然妖魔化,“真实”和主观性建立了复杂关联,这样语言在极端自恋中建构了和现时世界全然脱钩的主观现实。“艺术的批判功能,艺术为自由而奋争所作出的奉献,存留于审美形式中。一件艺术作品的真诚或真实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即是否‘正确地’表现了社会环境),也不取决于它的纯粹形式,而是取决于它业已成为形式的内容。”⑥语言是自足的,它无须和现实建立联系,尽管“真实”这个概念在他们这里仍旧重要,但“真实”已经转而指向以审美的方式讨论世界的可能性。
纯文学让“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划清关系,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却宣布了二者的联盟,“无边”的空间形象宣告了现实主义强大的涵盖力。在加洛蒂看来,“主观的真实”消泯了“阶级”带给文学的政治禁忌,“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原理演变为一则精神寓言:“一、世界在我之前就存在,在没有我之后也将存在。二、这个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变革的过程中。三、我们每一个人对这种变革都负有责任。”⑦在此,现实主义实际上指对现实的历史性发现。世界是客观的,但对世界的发现是主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强调人的主观性,强调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实实在在的主观审视。“无边的现实主义”现实先强调了主观性后才论述技巧问题,而“纯文学”则是通过形式的审美试验证明人的主体性,这种先后次序微妙地体现了主观和技巧的不同地位。问题是,融合了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之后,原来存在于二者身上的本质主义倾向在“无边的现实主义”这里是否就此消失?“无边的现实主义”如何看待“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众所周知,现实主义是一个流派的关键词,即用现实主义‘文学’取代‘纯虚构’,也即糟糕的虚构。这也意味着为一般文学所下的定义:一切文学都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再现一种现实,当它给现实以外在于直观感知、日常生活和普通经验的一种形象时尤为如此。现实的‘岸边’可以无限延伸。而现实主义思想却不是虚构的对立面,它几乎与虚构没有什么不同。”⑧主观现实主义的“真实”源自主体的真诚,“无边的现实主义”早已不是一种具体的美学风格,在强调“技巧并非判断‘现实主义’的标准”的同时,“主观真实”被前所未有地拔高。“再现现实”依然是“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终极目标,只是这种再现更强调主观,而非技巧。当然,由于判断这种“现实主义”更多基于道德标准和心理学标准,而缺少文字技术层面的借鉴,“现实主义”面临着内爆,当“主观现实主义”无所不包,它就成了新科“本质主义”。将现实主义创作背后的主观情绪具体化,或许能够制止“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危险倾向。“无边的现实主义”只能是一种历史性书写的精神原则,“主观性”意味着人们必须回到每一具体文本和切实的历史现场。“我们所以相信现实主义的持久魅力,乃是因为我们将持久地感受着人物与社会、平民化情绪与理性精神的吸引。”⑨“持久”恰恰源自文学个案对“无边的现实主义”总体精神的印证。
正如前文所说,纯文学、“无边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二十七年文学”在现实主义某个层面上相互冲突,却都存在本质主义的弊病,“语言和现实”等级秩序是三者共同命题,“真实”和外在的客观世界密切相关,当然这并非是本质主义的来源。那么,当话语理论阶段“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发生逆转,“现实主义的幻象”又是如何反本质主义的?它又是如何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的?和强调主观精神性的现实主义不同,“现实主义幻象”关注语言对于“现实主义”真实感的直接塑造,这就完全颠覆了真实的客观意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成为叙事的产物,“语言反映现实”此刻变成了语言塑造现实。“小说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表现的是什么生活,而在于它用什么方法来表现生活。”⑩伊恩·瓦特虽然仍旧强调小说对于“现时”社会运作逻辑的迎合,他所强调的方式也不是形式主义意义上“陌生化”形式实验,而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小说手法。虽然瓦特仍旧强调小说叙事对于社会现实的必要参考,但他“语言能够塑造一种真实感”的观点却隐含了话语理论的典型因素。表现生活的具体方法提供了作者对于世界真实的个性化理解,也就是说,话语理论阶段强调的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创造现实主义,此时“方法”拒绝定于一尊,“现实主义”也成为开始了话语时代的漫游。“对于不同的潮流,比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分源自于两种因素之间的结合。这两种因素都是以极大的自由度构成的,即一方面是对可进行多重阐释的文本和事件的阐释,而另一方面则是诸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这些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而非武断构想出来的概括性概念。试图对文学思潮进行区分的各种各样的尝试导致了对大量在某些历史、地理、社会学领域之内正确合理的成规的描述。”(11)也就是说,主义间的区分不是出于辨析真假、确定亘古不变之本质的需要。这种区分说明了人们阐释世界所选择的话语规范,人们重新将具体的社会因素引入话语分析当中,这实际上转译了共时和历时的辩证关系。个体话语规范选择和“无边的现实主义”的主观性不能等而视之,后者缺少前者自觉强调的话语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的“真实”是由社会成员的文化规范具体决定的,“文学学者知道修辞学,知道似乎是真的东西将取决于所用的语言与听众的期待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学研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今天字面的客观真理不过是昨天的隐喻的尸体。”(12)“真理”的历史性消除了绝对的真理霸权,随着真理的改弦更张,“现实主义”真实体现为不断发展的叙事规范。“(形式现实主义)之所以是形式上的,是因为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在此并不涉及任何特定的文学教条或目的,而是仅仅与一套传统叙事方法有关,这套传统作法在小说中如此常见,而在其他文学样式中如此罕见,以至它可能会被认为是这种形式本身的象征。”(13)“手法”加重了文学创作匠气十足的技巧形象,作家的精神世界退居次要位置。“真实”更多时候不是因为文学描述切合外在客观世界,而是其符合一定历史语境的观念规范。在当下的叙事理论中,人们开始梳理全知视角和有限世界的意识形态区别,全知世界代表着万能知识的恐怖景象,叙事层面的视角选择强调了“现实主义”事实表述的话语策略。
挖掘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大显“关系主义”的魅力,语境化的意识形态只是话语理论的一面。在另一方面,话语理论中的语言学色彩使其大有取消主体的趋势。结构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谱系学都编织了“语言说人”的新牢笼,这是典型的语言中心主义。但福柯并没有说明这些历史性结构是借助何种力量得以变迁的,至于人对历史可能的主动性则只字不提,而强调人的主体功能的历史才能最终实现历史的永恒批判。话语理论的历史往往只是断章,它将历史变化的动力神秘化,绕过了将历史普遍主义的陷阱,话语理论的硬伤在于将一个个局部的历史本质主义化。话语理论的另一个本质危险还是术语操劳过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现实主义仅仅是社会话语规范的结果,那么是否意味着在极端的意义上人人都可以拥有自身的现实?它和“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内涵内爆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现实主义”概念的个体多样性,后者则立足于现实主义本身内涵的无限开放性。话语现实主义原本想突破客观真理的一元本质,但现实主义的无限表述确实造成了新型的思想惰性,人人都怀揣着自己的“现实主义”,构造了狭小的思想安乐窝——即使这些危险很多时候只是理论的构想,实际的生活中的情况往往要好得多。话语时代“术语狂欢”抑或“术语消费”的结果产生了话语时代的本质主义,它源于“怎么都行”的消费型虚无心态。
注释:
①⑩(13)[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均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3、27页。
②⑥[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196页。
③④[荷兰]杜威·W.佛克马:《清规戒律与苏联影响——一九五六—一九六○年中国文学概观》,聂友军、季进译,《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第134页。
⑤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被视为扭转了先锋文学的避世情结,但它们仍旧延续了之前人们关于“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惯有的文学印象。当下文论界提出“底层文学”和“纯文学”的必要关联就是对这一印象的反拨。
⑦[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⑧[法]埃蒂安纳·巴利巴尔、皮埃尔·马歇雷:《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⑨南帆:《现实主义:涵义、范围与突破》,《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第7页。
(11)[荷兰]佛克马、[荷兰]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12)[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标签:本质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纯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形式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