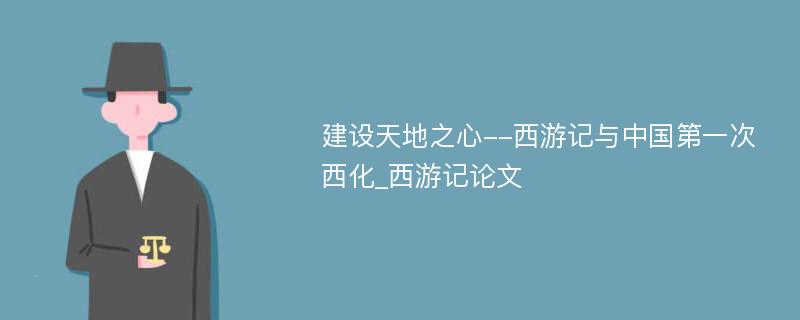
为天地立心——《西游记》与中国的第一次“西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游记论文,中国论文,天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紧箍咒与头痛病
近些日子老是头疼得厉害。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疼痛是一种信号,一种警告。如果不是感冒或别的什么疾病,那这头疼八成就是用脑过度。你把脑袋用过分了,脑袋自然就要警告警告你。你若是再不听,脑袋就要生病,你就要完蛋。
唐僧为什么要念动定心真言,叫那孙猴儿在地上打滚求饶?不也是一种警告,一个信号。
用脑过度是什么?按佛教的说法,就是识心太过。
识心是什么?识心就是念头。
某一类念头长时间集中于脑神经某一部位,此一部位脑神经负荷过重,岂有不出问题之理?欲出问题又岂有不以疼痛警而示之之理?
我们脑子里的念头大概是人类生命的最大奇观了。它一天到晚无有止歇,蹦蹦跳跳,灵动活络,攀援不定,刹那间天上地下海里,古今中外宇宙,没有不可以去的地方。
念头这模样不就是孙猴儿的模样?孙悟空实在就是人之念头,用《西游记》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心猿”。筋斗云一瞬间十万八千里,不正如我们大脑的联想功能,小不留意,开一小差,那念头便一筋斗翻到九霄云外去了。
念头或曰识心,也就是认识之心,智慧之心,主要的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识或理性的范畴。
人的认识之心,智慧之心的发蒙、反叛、成熟正是人成长的必经之途,我以为,《西游记》要写的实在就是这人的认识之心,智慧之心的发育故事。当然,不仅是个体的,也是人类的。
人们曾将这孙猴儿说成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或是大自在的精神英雄,甚至是说书人与小说家于玩笑、游戏中戏拟出来的一个供人取乐的玩偶,虽然也稍带有一些儿哲理味。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孙悟空,怎么读都不碍事,只是我呢,横竖读来,却总觉得这书实在写的只是一个“心”字。
唐僧肉与立地成佛
小时读西游,唐僧最是谜。
所以是谜,其一:如此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干吗非要服那窝囊无用的唐僧管束?其二,皮松肉软的唐僧肉怎么吃了便可成佛,以至那么多妖魔都不避艰险,非将那唐僧肉吃上嘴不可?
唐僧其人,说来真个是不可理喻。他既无谋略,又无武功,更不识善恶好歹,实可谓百无一用!
然无用是无用,可爱却也有可爱之处。他面目端庄,气度清如止水,总能面带微笑,常怀静气平心。虽不才,却虔诚,无欲无念,一心西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向佛之心未曾有丝毫更改……
倘将唐僧此一特点与那孙猴儿两相比较,你很容易想起当年老人家的一句话: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唐僧);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悟空)。
人生的这场战争,真的也就需要这样一个两极。
倘说人有孙猴儿的一面,有识心,念头活,智慧争天,理智夺地,以至于成为万物之灵,甚而要人定胜天,做它个“齐天大圣”,然人这东西再聪明再智慧,也还是自然之子,它果然能违了自然吗?不能,丝毫不能。所以,人除了识心外,还得有个比识心更为根本的“本心”。
唐僧就是本心。西游里说得再清楚不过。
佛教里,除了讲识心外,还讲个本心。何为本心,宗教上自然有他们一大套的说法,然依我看,其实也简单,本心就是向佛之心,或者说,就是佛心,甚至就是佛本身。
佛是什么,佛就是自然,道法自然,佛亦法自然。东方精神的根蒂就在这“自然”二字。
宗教家当然要笑我。我于宗教全然外行。释道两教,典籍无数,更有那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神秘所在,然,既然直指人心,既然我佛即我心,我心以为佛就是自然,大概也总是不错的。
所以,本心就是自然之心。闭上眼睛,只觉清清静静虚虚无无坦坦荡荡,无我无他,无人无天,一无挂碍,混沌一片,纯然自然,那就是本心。
本心当然是无用之心。
但尼采老先生说,黄金是最无用的,然黄金也是最尊贵的。
本心正是黄金这样一种无用之心。向来佛家都讲,本心看似容易修来难,真修到本心,则成正果,也就是成佛,乃可齐天比地。
不想下功夫修行,而又想成佛长生的人,总想走捷径,如何走,将别人的本心窃来,如何窃,吃唐僧肉呗。唐僧肉之所以好吃,俱因为那唐僧便是本心,吃了唐僧肉,也就是得了本心,就可以成佛。不过,唐僧肉绝没有一个妖魔吃到了嘴,本心这东西并非技术机密,偷是偷不来的。
也正因为唐僧乃本心,那猴儿倘要乱来,识心太过,违了自然,本心当然要念动定心真言,叫你头疼,以示警告。
一部《西游记》,其实要说的,关键就是这人之本、识二心的关系,要演的就是这本、识二心的矛盾以及由此矛盾而生的故事。
“唐孙大军”与五位一体
“文化革命”时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个“千钧棒战斗队”。
然从西游看,这类队伍本应叫做“唐僧战斗队”才是。因为唐僧才是这支西行取经队伍的主帅。
只是毕竟,那一路西行中,斗妖除魔,披荆斩棘,做一切实事的都只是孙悟空的首功,所以,想来那队伍叫做个“唐孙大军”似更为恰当。
唐僧做政委,孙悟空当司令员。
或曰,唐僧是精神领袖,悟空为行政长官。
事实也确如此,唐僧实在乃是我们心中终极关怀的象征,而悟空乃是我们人生中现实关怀,或事实关怀的体现。人之一身,这两方面总不可或缺。
如此说来,那八戒、沙僧呢?
八戒最是鲜明,当然是人的食性大欲,好色贪吃,名扬四海,无须细说。
沙僧乃是人之形体的符号,是“唐孙大军”的手和足。瞧他一路西行中,只是老老实实挑着担,最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试想想我们一身中,最听我们意志调遣的不就是我们的手和足么?我们的心跳、血流、血压、各种新陈代谢,循环系统等等等等,我们实在没一样指挥得动的,甚而至于大小便,我们也拿它莫可奈何。至于脑中的念头等大脑活动,我们已说过,也绝不是可以随便领导的。
再就是白马了。这白马按说在此书中本应是与那孙猴儿差不多重要的角色,且从书中各回题目来看,一再地提到“意马”二字,意马与心猿相连互依,结果却并没有个平起平坐的份儿,甚至连八戒沙僧,也即欲和形的重要性还不如。
此角儿实在本该比现在这样重要得多,因为它乃是人之情感的表征。
这龙宫太子,一开始就是因为情爱上的失落而犯了天条;变了取经的脚力后,见那前妻与九头虫勾结窃宝做坏事,还要义愤填膺,挣脱缰绳,奔下海去助战一番,方解得心头之恨。
情感这玩意儿,在人心中,本也是个极难对付的东西,所以,要给它套上辔头,拴上缰绳,由唐僧(本心)牵着,骑着,驯服着,又还要有悟空(识心,理智)在一旁看管着。
西游注中说,弼马温就是“避马瘟”,民间传说,猴子可以防止马群发瘟病。所以,那孙猴儿本就是安来管马的。
只是这书中猴子管马的故事实在太少也太不出色,以至于我们现在感觉起来,仿佛情感这玩意儿,在这书中是太老实,太委屈了点。我总觉得这是作者的才力有限,也表明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人之情感其实是很不放在心上的。
本心(唐僧)牵制识心(悟空),并驾驭情感(白马),识心(悟空)管束情感(白马),同时一并治理欲望(八戒)和形体(沙僧)——这便是“唐孙西行大军”的建制。
终极关怀—认识或智慧—情感—欲望—形体,五位一体,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
一部《西游记》,要讲的正是一个人在修行或人生修养中,如何处理好人之一身五种关系,相互谐调,共同克服人生之途上种种困难,最终拥有一个理想人格的这样一个故事。至少,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这样来读它,把它读成一个有相当系统的哲学的寓言。
齐天大圣与人定胜天
人类发育史与个体发育史是同构的。人一开始也是自然的乖孩子来的,他信天命,信鬼神,信图腾,或信老天的代用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什么的,后来,少年期来了,人对大自然的信仰发生了危机,理性摆到桌面上来了,任什么都要通过人类理性来辨识斟酌,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天平上重新衡量,一如孩子大了便要用自己的脑瓜子想一想了。人类开始用理性的科学向大自然宣战,并且也的确取得了可观的战绩。于是,人定胜天的旗帜在人类的世界里树了起来。
远远看去,这“人定胜天”的旗帜与那孙猴儿花果山上“齐天大圣”的旗帜是不是颇有些相似处?
完全是一码事!
大闹天宫闹什么,不就是向大自然宣战么?
玉帝是什么?玉帝便是老天,即大自然的总代表,天宫众臣,不都是些大自然景观么?从和事老太白金星到将那猴儿押上斩妖台的掌刑官南斗星及属下火部众神、雷部众神;从参加蟠桃盛宴的天上各极,地下各海各山神仙到上天告状的龙王、阎罗,孙大圣要战的几乎是全部大自然!
人类要战的,不也是全部大自然么?包括阎罗,医学的高度发达,不就是向阎罗宣战?
人的识心,理智或智慧,也确是不简单,万物之灵嘛,不就灵在这一点上。所以,自然也便很有些退避三舍的味道,好吧,承认你确可齐天,给你做个齐天大圣府,设上安静司、宁神司,让你呆着,别识心太过,别任意胡来,搅乱了自然次序,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招安纳降给以虚名,依然安不了这颗了不得的人心,它依然地要胡作非为,只好又来高压政策,太上老君的丹炉正是高压之一法。
做过周天功夫的人都知道,放松宁神,呼气时将注意力放在小腹中一点,即丹田处,渐渐地,那地方就会发热,热到一定时,则须将注意力稍稍放开,使之保留一点微温,即以文火煨之,日久,丹田处,自会产气,有时甚至果有一气球感,然后,这气将循经运动,且据说,如此就可以祛病延年。
这套道家智慧,表面上看起来是为着养身,骨子里实乃是为着修心。长生是人之大欲,从此入手,将人的那颗活蹦乱跳的识心拘在丹田处,不许胡来,久而久之,识心自然驯服。所以,西游中太上老君的丹炉,其实就是人之丹田,即小腹中一点,将那孙猴儿放进炉里煅烧,也就是意守丹田,把识心拘住。
这法子于识心果然有用么?很难说,我以为,于身体健康是的确有些效的,然于修心,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不信你试试,将注意力放在丹田处,要不了几秒钟,念头又不知去向了何方!那景象恰似悟空在丹炉里炼了一阵,踢倒丹炉,逃之夭夭也。且由于在那丹炉中呆过一阵,注意力也算是得到过一种训练,反而是变得更为敏锐,更为活跃。
招安逢迎不行,压制堵塞也不行,如何办,大自然拿出最后一招:放!尽你的马跑,看你能跑多远。
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居然会跑不出如来的手掌心,奇怪吗?一点不奇怪。如来的手掌心就是大自然本身,你跑吧,跳吧,滚吧,飞吧!人的脑袋里那一点点聪明智慧,还能跑得出大自然本身的手掌心?今日人类自以为了不起,创造了多么令人神奇的文明,然环境污染,核威胁,植物和生物灭绝到无以复加,不可再行远的最后限度了,这岂不是正如孙大圣一个筋斗云翻到了天边,在那里撒了泡猴尿,污染了环境,却还在大自然的手掌心里!
为天地立心
一部西游,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荒诞不经,然而却实在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严肃,极重大,极深刻的大问题:人类究竟如何看待它的认识和智慧?
在蒙昧时代,如原始社会和血缘或类血缘性的奴隶制、封建制等时期,人们曾长久地生活在大自然的重压下,生活在由自然的血缘关系衍生而来的社会结构和宗教制度的重压下,那时人们的认识与智慧虽然也已发挥了非凡的功用,然却并没有被挑明,被正视,被真正看作人类的伟大之所在,天命高于一切,上帝高于一切,智慧和知识乃是奴仆,人,作为拥有认识和智慧的个体的人,也就只能是天命或社会的奴仆。
及至这一个千年内的十四五世纪,启蒙时代的来临忽然向我们揭示了一种奇异的可能性,我们发现了于我们身内孕藏着的伟力:理性,我们醒觉了,人类长心了,自立了!原来,我们无须臣服大自然、上帝或者天命,我们只要拿出理性,就可以肢解并窥探大自然的奥秘,并将其战而胜之,以为己用:我们只要拿出我们每一个人头脑中的理性,我们也就可以为我们自己作出一切重要的判断,进行一切于我们有利的行动。
这一醒觉,无论东西方,起步都是基本同时的。
《西游记》的成书年代是我国明代中叶,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风起云涌,中世纪土崩瓦解,新兴资本主义微露曙光之时,而我国亦是商潮初涌,市场因素迅速滋长,很快蔓延,社会动荡,人心极是活跃之时。
孙悟空这个文学形象的出现,正是当时我国知识界、思想界探讨将人的精神从传统文明的桎梏里解放出来,并重新为天地立心的一个颇为成功的战例。在西方,人们说,是笛卡尔首先阐明了人之“认识”;在中国,我以为,是孙悟空鲜明地显现了人之“认识”。
无用唐僧与神通悟空的极鲜明极有趣的对比,正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本心,亦即信仰之心的怀疑和批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神圣至崇高的所在,不管是玉帝还是佛祖,人的识心,即理智之心和智慧之心,都可以去摸一摸他们的老虎屁股,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玉帝老儿那儿自然不肯躬身下拜,即使面对将它压了五百年的如来,那泼猴也绝无一点卑怯之意,如来有错儿,他照样敢找上门去与之算账。
虔诚的信仰之心不见得值几文钱,有多大用,倒是现实的认识之心和智慧之心才真是救苦救难,昌盛人世,发达人类的可靠保证。不再迷信,不再盲从,不再做信仰的奴隶,个人依自己的理性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人类亦自己的理性创造理想世界。掀翻至高至上的神殿圣座,长了心,有了头脑的人类从此敢想敢干敢当!这是中世纪以后人类精神的基本态势。
《西游记》当然并没有这种彻底。那猴儿毕竟还是只能被戴上金箍儿,与唐僧等其他四众一道完成他们的修心之旅,人生之程。且在那书中一切都是佛祖事先安排设计好的,天命与宿命依然是那书中人物的根本境况。
这当然是局限,致命的局限。这说明在此书的世界里,尽管理性开始醒觉,然天命与宿命的古屋并未动摇;这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界、思想界,虽然也在呼唤个人理性,并开始意识到人自身的伟力,想为天地重新立心,但他们囿于现实,还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对整个传统信仰的观念体系发动进攻,他们所做的还只是一种关系的调整,调整旧精神大厦与新兴的理性意识的关系,突出个人理性的作用。这里也便可以见出近世中国精神的悲剧之所在了,科学的难以发达,民主的难以实现,个性的难以张扬,其深在的原因就在这旧的精神大厦的稳固,古老东方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的定势太强。
不过,尽管局限深刻,此书中本、识二心之力量与意义的有趣逆转,已然将认识之心的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已然是对个人理性精神的一种极有力的高扬,已然展现了一种新文化精神的萌芽,这在中国精神史上,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有着极具革命意义的变化了。
而且,若从整个人类精神史的长河看,近现代文明中的理性至上主义虽然是人类自觉的一个伟大阶段,然也不是没有任何危险和局限的。二十世纪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纵深发展,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非理性思潮在更高一层次上的回归,使人们意识到,人类在后理性时代,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理性与终极关怀等诸种关系。在这一意义上,《西游记》隐藏在天命与宿命一类糟粕后面的,那样一种纯哲学意味上的心的本、识二元结构,那样一种轻本而不失本,重用而不妄用的独特的精神辩证关系,很可能是东方思维能向未来人类提供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正果与奇果
唐僧五众成了正果,《西游记》则成了奇果。所谓奇,首先自然在作为艺术奇观而百世流传;然还有一奇却在,此书的日后遭遇总让人觉得有些儿怪。
围绕着《西游记》,有两个奇怪的悖论。
悖论之一:《西游记》显然是一部“全盘西化”之作,然国人却从不介意,反倒是一直地引以为豪,列作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皇冠上的明珠之一。
西游的结尾处佛祖如来在解说为什么要设下取经一事时,大大咧咧地指斥我们中国这边是蛮荒之邦,多贪多杀,罪孽深重,虽有孔丘立下仁义之说也无济于事,所以他老人家要送经以拯救之……这样的话拿到今天的小说家的笔下来,也是危险得紧的言论呀!
中国的第一次“西化”,即向紧邻印度佛教学习,按胡适的话来说,是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予消化,消化成了“中国本位”的东西。但依我看,一千年时间消化下来的东西,可说已是国粹,但却不可说是“中国本位”的东西。我们那第一次“西化”的硕果,我想大致有三项,其一是禅宗,这是宗教方面的果实;其二是心学,这是哲学方面的果实;其三便是《西游记》了,这乃是文学方面的果实。三项果实中,至少有两项,让人看起来,是“西”学本位的。
看来,关键的还只在一个“化”字,管它东化西还是西化东,你化我还是我化你,但食而化之,于己有营养便足矣。中外东西的名目之争,实在无多大意思。倘说真有个本位与否的区别,则只在文明的进程上,文明先进,则可作本位,地域民族之别,之特性,当只应为文明的进展服务。
悖论之二:《西游记》实在是一部惊世骇俗,极具精神革命意义的伟大思想小说,寓言文学作品,但国人几百年来,何以只把它当作儿童读物,嬉笑之作,虽有些个学人也在探其深意,但其思想上的革命意义却始终未得认可。
我总觉得,若纵比,《西游记》的思想价值当与《庄子》同,它融通释道儒,然又并非单是谈禅释道的简单宗教文学,而是特立独行地提出了个人理性这一现代文明的头号主题,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反信仰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倾向。
若横比,它当可以与英人的《天路历程》比。《天路历程》在西方,被视为基督教著作中除《圣经》之外最重要的作品,且公认为提出了一种精神个人主义的价值主张。《天路历程》的故事在西方也可算作优秀的儿童文学,而思想价值却并未被看轻。
我们的《西游记》却绝没有这种幸运。《西游记》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吴承恩老先生今日九泉之下不知作何认定。
究竟是吴承恩本人的失误,过于杰出的艺术层面,以至于遮蔽了它的思想层面,影响了它的意义价值的实现;还是中国文化的惰性,国人观念的僵化,老不开窍,以至于视而不见这宝藏深处的灿烂光辉呢?
好在那孙猴儿所张扬的个人理性主义精神,即使没有在理性层面上,也在感性层面上濡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且它的心的本、识二元结构及其独特的相互关系思想,亦定会对又一次处于社会转型,文明裂变关口,亟待重建精神规则,重为国人乃至人类立心的我们今天,作出极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