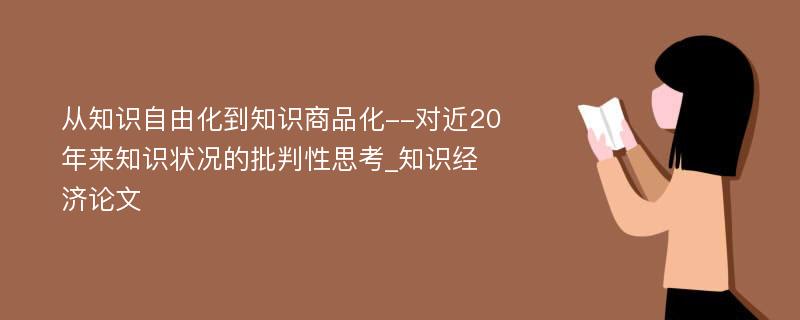
从知识的自由化到知识的商品化——对20年知识状况的批判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前,围绕“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讨论。它推翻了两个“凡是”,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真理说到底是个知识的问题,并以话语的形式来显示自身。如今,知识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以往的变化作简要的批判反思是本文的宗旨。批判,是指“辨别”和“鉴定”,即对认识/实践之能力的再审视。反思的对象,既有作为客观的知识,更包括了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反思者自身。
一
在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真理”的讨论是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方式提出。它试图避开强加于人的政治运动,将讨论转入理性化的学术轨道。由于毛泽东掌握了真理的解释权和社会实践的主导权,讨论注定流产。此后的十年实践,将真理的追求者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与此同时,作为整体的知识界也以“真理”的名义参与了全民性造神运动。知识和学术被迫沦为当下政治实践的奴仆,专制主义打着“革命群众实践”的旗帜践踏真理和知识的主体。知识的自由化是“反革命”的同义语。
第二次关于“真理”的讨论成功了。它是一次水到渠成的政治事件,其争论本身却并不具备学术的品格。为什么?众所周知,知识是概念的运用,而概念体系又决定了知识的性质和运思的模式。20年前的那场讨论是在文革话语形态的阴影下展开的,言说者无法超越身处的文本。因此,它采纳了既定的主导型概念“实践”,却不能在“文革”思想架构之外来界定何谓“实践”,亦不敢区分性质不同的“实践”。(“大跃进”和“文革”难道不是实践?要不要彻底否定?)同样道理,它也不可能将实践者的创造性或者破坏性活动及其缘由纳入批判的视域。(群众运动是否如毛泽东认定的那样“天然合理”?)它尤其回避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谁在主导实践的方向并对实践的性质和后果做出权威性价值判断?离开了人和人的认识/判断,“实践”本身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检验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焕发出巨大的建构性物质力量,拉开另一种性质的实践运动之序幕,原因不在其哲学层面的那颇成问题的“直接意指”(字面义),而在它政治符号学意义上的“含蓄意指”。后者在特定历史上下文中,以非人格化的“实践”来取代人格化的“一句顶一万句”,矛头直指两个“凡是”,体现了民心所向。顺乎民心的政治家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打响了拨乱反正的第一排重炮。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当年第二代领导者的政治智慧,而不是秀才们的哲学贫困。这就是我们今天反思往事的一个起点。起点不能歪。如果歪了,即继续陶醉于当年的话语贫血症,以泛泛而论的“实践”和从来就不存在的“唯一”来充当对未来理论开拓的承诺,乃至以毫无新意的宣传来取代学术的批判反思,那么其结果只能是重蹈“文革”话语之覆辙:假,大,空。
二
推倒两个“凡是”,就是宣告“文革”话语霸权的终结。它标志着旧话语形态的断裂和知识状况的嬗变。其划时代意义当然不单单是为平反冤假错案扫除了最大的直接障碍。站在今天看过去,那场讨论是在一个有三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政治文化氛围中,第一次以官方和学界通力合作的方式向全国人民宣告:个人或少数人垄断真理解释权的时代结束了。
任何对真理的陈述都是一种解释;没有解释也就无所谓“真”或“理”。作为一切专制形式之基础的思想专制。其成功之道是以“神性”代言者身份牢牢控制住知识界对真理的各种陈述。千年中世纪智性恐怖的根源不是《圣经》,而是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将基督教机构化为一个庞大的释义金字塔组织,从上到下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并通过此垄断来控制一切有关知识的陈述和建立在知识之上的个人/群体实践行为。新教改革最伟大的功绩是使个人的灵魂有权直接面对上帝,从而在基督教欧洲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知识自由化运动和思想大解放,为后来的启蒙运动和西方物质文明之腾飞铲除了思想障碍。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显学的国度,当理论经典的解释权从神性“作者”及其钦定的“接班人”之手转归“读者”时,首先获得解放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信仰者。但是,它又不可避免地推动了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界认识/实践能力之重建。其认识论层面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樊篱。20年前的那场讨论,在共和国打开了思想自由的“潘朵拉之盒”。它将作为一次伟大的政治事件和知识自由化运动的里程碑而载入中国思想史册。
三
“摸着石头过河”以通俗的隐喻为讨论做了一个指向未来的总结。这是被称为“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论基石。它告诉我们:知识或真理,是在没有先入之定论的前提下,在群体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显示自身;谁如果还没有下河,就声称知道有唯一正确的过河之道,谁如果还没有过河,就以理论权威自居来规定河那边“是什么”,谁就是企图再次垄断真理的解释权。
整个80年代知识的状况就是围绕如何“过河”的问题来展示自己的特征。冲突的实质是垄断和反垄断。当年曾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且做出一定贡献的某些人,就像新教徒不能容忍世俗启蒙运动一样,以一种类似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对抗知识的自由化。他们继承“凡是派”衣钵,企图以自己认可的知识来控制现代化实践运动。他们的战略目标是阻止市场经济进入中国,战术方针是关闭“潘朵拉之盒”,具体策略是用“文革”式“大批判”来对付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者。这就是针对知识和知识界的“反自由化”之实质所在。
在这样的经济/政治环境中,知识界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知识和知识的主体高度统一,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展开了一场长达10年的新启蒙运动,以瓦解“新凡是派”扼杀知识/思想自由的企图。为寻找新的理论武器,知识分子再次转向西方,遂促成了中西沟通史上规模最大、涉及学科最多的一次西学东渐,同时也对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引介和应用作了一次见仁见智的批判反思。其结果,就不仅仅是为反垄断提供了多元杂居的论证手段,不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30年闭关锁国而延误的知识进程,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结构及其话语形态。10年较量的结果,双方的分歧从经济/政治追求方面的一般性观念之别,扩展到概念体系之异,即知识的性质和运思的模式问题。这已不是泛泛的文化隔膜,而是知识范式的对立。10年争论是一个知识更新的大课堂;“以不变应万变”者将自己放逐到当代知识和学术之外。另一方面,知识精英虽然不断受挫,却没有失去知识和学术的主导权。知识界内部的分歧始终是次要的,因为在80年代大家都服从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体现,民众的启蒙人,其当下的首要任务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确立,以便为民主政治创造必要条件。因此,反垄断的另一个结果是相对独立的、现代性意义上的共和国知识分子共同体之形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屈辱被“牛虻”的自信取代。就知识的状况而言,更重要的成果是官方和学界话语都采纳了“多元化”的关键概念,这一成果至少在理论上否认了一元化的简单独断。知识的自由化成为新的“宏伟叙事”。
四
80年代知识和知识主体的独立亦付出了不可忽略的智性代价,必须认真批判反思。代价之一是冷落了作为人类重要的且无法替代的理论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撇开个人政治品德不议,从当年的王明到如今,各类“凡是派”的共同特征是用自己认定的准宗教信仰教条来捆绑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拉大旗充虎皮,推行智性恐怖主义,控制一切有关真理的陈述。在中国语境中,他们代表了一种世俗化的“加尔文教义”。80年代初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的讨论以不平等的方式草草收场后,知识界的策略似乎是“惹不起,总躲得起”,提出“淡化意识形态”的口号。这就将经典文本的阐发、开拓权拱手相让,使之成为“新凡是派”用来对付“自由化”的“专利”。此段时期内成长的青年一代,不少人不仅缺少马克思主义的ABC, 而且有一种非理性的逆反心理,他们误认为“‘新凡是派’=马克思主义”。代价之二是通过张扬一直被冷落的欧洲启蒙理性传统,将另一种意识形态置于统帅的地位,在反对“新凡是派”一元化简单独断论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暗暗树立另一种一元化简单独断论。“高调民主”、“积极自由”、“科学主义”、“看不见的手”等等理念与各种现代专制主义之间的逻辑/现实的关联,均落到批判者视域之外。就知识和知识的主体而言,知识几乎成了客观真理本身,中国式“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的主体意识空前膨胀。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揭示各种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维度,质疑知识主体的先在性和自律性,正是80年代西方学术的哲学主题。共和国新时期的10年西学东渐为实用功利的动机左右,拿来就用,没时间亦无条件从事深入的研究消化。其学术水准,似乎并没有超过本世纪初“五四”先辈留下的成果。
五
1989年春夏之后,争论戛然而止,知识界陷入短暂的沉寂。其间,“学术性”和“思想性”之争的小打小闹,具有暂避现实和自我反思的双重动因。表面原因是因为权威性行政指令“不要争论”。实际效果却是戏剧性的:面对大是大非问题,“不要争论”的指令使最希望展开争论且控制了舆论工具的“新凡是派”丧失了最佳亦是最后一次垄断真理解释权的机会。此后的“南巡”使形势急转,标志着市场经济的合法化和“新凡是派”话语权力的边缘化。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在80年代的社会心理效应主要在于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帅位,以“科学”和“技术”的名义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实践中的主体作用;那么,90年代初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和高新技术被全社会认同,知识和知识的主体便逐渐分离,知识本身亦日益凸显出作为又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问题的性质从知识的自由化向知识的商品化过渡,现代性难题终于被现代化实践运动推至表层。
六
1979年12月31日,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巴黎正式出版。作者认为知识的状况已发生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科学的含义被市场锁定在高技术的位置,遂成为主要生产力且从知识拥有者处分离出来,转化为商品。知识的创造和传播都要服从系统的优化性操作原则:知识必须电子化数字化,即能转译为电子信息方能进入传播渠道,否则就会被淘汰;新的研究课题,必须保证其成果可以转化为机器语言,否则就无法进入学术商业市场,也得不到资助。知识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值而被消费。人作为主体(无论是知识的提供者还是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承受了生产者/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青年马克思早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就指出:由人创造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反过来成为控制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理论在原东方阵营的解释者们未能解决这个问题,都企图以思想专制和“计划经济”来推行乌托邦理想,结果使得经济崩溃,阵营解体。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发现的问题不存在了。)不同之处在于如今异化或物化的深度和广度:信息学和高技术媒体与市场经济联手,已成为塑造社会生活方式和知识生产/消费模式的主要力量。人的主体性失落,知识由自由化变成商品化而沦为市场的工具。
如果知识的商品化在70~80年代的中国还属海外奇谈,那么在90年代的今天已是毋需争辩的事实。它有一个雅号:知识经济。按照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有关文件中的界定,这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这也就是新形式的利润生产、分配和使用。因此,知识产权是保护知识经济的不可少的法律手段。利奥塔曾预言知识经济将进一步拉大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20年来,经济年增长率一直高居世界首位的中国当然不甘落后,1998年9月27日, 在北京召开了“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研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发言要求强化“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迅速“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他进一步树立了知识经济作为新“宏伟叙事”的地位:“要求社会管理方式、企业组织方式、产品流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法律体系、伦理道德体系等等与之相适应”。这实际上是将知识经济当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规范/调节力量。利奥塔20年前的预言,在中国成为现实。
七
其实,知识商品化最初的身体力行者并不是政府和科学家,而是有“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称的作家、艺术家乃至哲学家。“下海”是第一个信号,不仅人“下海”,知识也“下海”。这些年文学“流派”像走马灯似地出场和消遁,实质上是创意性商业炒作,不可与80年代初发自精神深处的“伤痕文学”相提并论。评论家为炒作推波助澜,也为自己在学术市场定了身价。画家们最关心的是作品能否进入艺术市场和以什么价格进入。戏剧和影视界导演“专制”一去不复返,投资者的意愿是最高原则,此意愿将“灵魂工程师”的美学理想置于观众的喜好之下,而观众喜好的唯一量度是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在西方,文化工业和精英文艺泾渭分明;在中国,精英文艺成了文化工业的中坚。没有技能可卖的大学人文学科不甘寂寞清贫,于是纷纷挂羊头,卖狗肉:哲学系开办“企业管理”专业,历史系推出“旅游”专业,中文系标出“秘书”专业,外语系课程表上冒出只能唬唬外行的“商务英语”和“旅游英语”等不伦不类的玩意儿。几年前,学界曾喧嚣一时的“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讨论,如果不是不自量力,拿鸡蛋碰石头,也只能是“天鹅的绝唱”。“上帝”死了,知识当然就要投入金钱的怀抱。思想和知识的自由化是一场悲壮的短剧,演完了。
与“上帝”共舞的人文学术研究又如何呢?它面临市场经济和当下政治的双重挤压。要么放下学术独立的架子,为显学宣传服务或者互相利用;要么抛弃学术清高,面向文化消费市场。最近一哄而起的各类学术“丛书”和“以书代刊”,说到底是为适应市场情趣而设计的商业包装或炒作。笔者撰写的这篇文章,缘于“牛虻”丛书的一位编者朋友之邀,旨在反思知识状况之变迁。“牛虻”是指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和知识主体的“独立人格”。而笔者不得不面对的反讽性现实却是:“独立人格”和对它的反思,得由消费市场来决定其命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时代又回来了,只不过换了一层皮罢了。至于说那些为极少数专家乃至未来的人撰写的至少1000年内无法转化为生产力的纯学术文本,又如何呢?要等出版商赚足了利润,再拨出一点点零头来资助,以便为知识的商品化裹上一层薄薄的知识自由化和学术化的外饰。
从知识的自由化到知识的商品化,西方走了几百年,在中国浓缩为20年。这是中国智慧的本领和希望,同时也是它的问题和麻烦。
八
知识商品化并不可怕,何况有些知识本来就应该商品化,否则就会在市场经济这个大文本中白白浪费资源。将文学艺术技能转化为生产力再拿去换钞票,亦无可非议,只要不再自命为“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并将求利的产品当作“精神文明”的样板来搞营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对当前知识状况的性质或麻木不仁,或执着于80年代的理念——以知识自由化的名义为知识的商品化吹喇叭,抬轿子。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政府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来临”的口号,可以理解,也有必要。搞哲学、历史学、文艺批评理论、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精神科学”的人,也带着他自己领域的知识热情地投入“知识经济”这个新“宏伟叙事”的怀抱,轻则不务正业,重则将沦为更新一代的“凡是派”——市场经济“凡是派”!
知识界有责任向官方和民间强调一个简单的事实: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技术是生产力;科学却不是。科学和上述“精神科学”一样,属于上层建筑。科学从来不保密,其价值却无法用金钱来度量;技术要保密,转让要付钱。通俗地讲,爱因斯坦或陈景润无法申请专利,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的独创是知识而不是知识经济。“科学种田”和“科学管理”是不科学的表述方式,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区别。如果全社会都以知识经济来认可知识,以生产力来界定知识,如果政府宣传部门和大众传媒也以此为尺度来弘扬“精神文明”,那将是华夏文明的灾难。
知识界还应该向官方和民间强调,科学和“精神科学”是跟着问题走,而不考虑当下的物质生产的需要。它的首要任务是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而不是为问题提供一个优化的可操作的解答方案。这是广义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区别,也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根本区别。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总面临一个永恒的尴尬:任何时代和任何制度下的公共权威部门都本能地希望天下太平,没有问题;发现了问题,不要大喊大叫,悄悄地呈报上级同时附上可行的解决办法。遗憾得很,科学从不提供一劳永逸的办法,却不断地提出令固步自封者恼火的问题。这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进程。以直言不讳著称的撒切尔夫人在位时曾对牛津大学的精神科学家们说:“要么赚钱,要么滚蛋!”这是西方技术官僚专制主义的写照。她不是用斯大林式的“古拉格”集中营,而是企图以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斧,来砍杀知识的自由化。好在英国纳税人毕竟懂得,若没有问题的提出,哪来问题的解决,并懂得将两者严格区别开来。无情的事实是:铁夫人下台了,科学家们仍执着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中国智慧将如何处理已经出现的类似尴尬呢?笔者愿以谨慎的乐观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