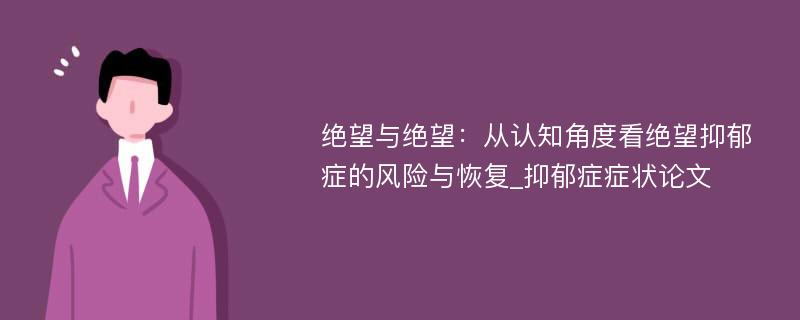
无望与希望:从认知方式看无望抑郁的风险和恢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抑郁论文,风险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Abramson,Mctalsky和Alloy(1989)在抑郁无助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望理论,认为无望对个体抑郁的形成有直接和充分的作用,并将无望感所直接导致的一系列症候群命名为无望抑郁。无望理论提出消极认知方式(认知易感)和消极生活事件(压力)是导致个体无望的重要贡献因素,该理论也被称为抑郁的认知理论。因视角和侧重点的差异,无望抑郁认知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病因学研究和恢复研究两大取向。病因学研究与无望抑郁存在互证的关系,受到了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广泛关注。历经20多年的积累该研究取向有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的研究成果增加了人们对无望抑郁危险因素的理解,提高了人们对高风险人群的辨识能力(Haeffel & Grigorenko,2007)。受诸多原因的影响,有关无望抑郁恢复的系统研究还非常少。目前,这两大研究取向基本上是独立进行,交叉研究极少,相互之间的促进作用还未凸显出来,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2 无望:以认知易感-压力模型为核心的无望抑郁病因学研究 2.1 无望、认知易感-压力模型与无望抑郁风险 无望包含了消极的结果和无助的期待,即心仪的结果不出现而厌恶的结果很可能会发生,个体对此却无能为力。无望是无望抑郁病因链上最近端、充分的原因。在无测量误差的理想情况下,无望与无望抑郁之间的相关等于1(Alloy,Abramson,Metalsky,& Hartlage,1988)。无望必然会导致无望抑郁症状的发展(Abramson et al.,1989)。 无望理论用认知易感-压力模型解释个体无望的重要成因。Abramson等(1989)在无望理论中指出个体的认知易感包含:(1)对消极生活事件的原因作稳定的、总体的归因和/或(2)推论消极事件会带来很多灾难化的后果和/或(3)从消极的事件中推论出消极的自我价值。当个体知觉到压力生活事件发生时,这些消极的认知方式/推理方式会增加其无望的风险,进而导致无望抑郁症状的发展。从无望理论的特异性层面来看,无望抑郁认知假设是指认知易感能预测事件特定(event specific)的消极推理、增加个体的无望感,而无望是认知易感与抑郁之间的中介因素。“无望”一词概括了无望抑郁的核心特点(Alloy et al.,1988),也概括了病因学研究的指向。 2.2 以认知易感-压力模型为核心的无望抑郁病因学研究 认知易感和压力是增加个体无望的重要影响因素/贡献因素,也是病因学研究的焦点。大量前瞻性研究发现认知易感与消极生活事件相互作用能预测抑郁症状的发展(即使控制被试抑郁症状的基线水平)。如,认知易感与消极生活事件相互作用能预测几天(Abela,2002;Gibb,Beevers,Andover,& Holleran,2006;Hankin,Fraley,& Abela,2005),几个星期(Abela,Parkinsona,Stolowa,& Starrsa,2009;Abela et al.,2011;Brozina & Abela,2006;Haeffel et al.,2007;Haeffel,2010;Hankin,2008a;Lee,Hankin,& Mermelstein,2010),半年(Steca et al.,2014),甚至几年后(Abela & McGirr,2007;Cole et al.,2008)抑郁症状的变化。这些研究涉及的被试有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主要是大学生)。最近有研究发现无望抑郁的认知假设在老年群体中也适用。64个老年被试(59~97岁)参加跨时6周的前瞻性研究,回归分析表明当控制其他危险因素时被试的认知方式与压力相互作用能预测抑郁症状的变化(Meyer,Gudgeon,Thomas,& Collerton,2010)。也有研究部分证实了无望抑郁的认知假设,如有研究在低龄儿童(平均年龄8.47岁,标准差为0.56岁)样本中发现对自我价值的抑郁质推理方式与消极事件相互作用能预测抑郁症状的变化,但对原因的抑郁质推理方式与消极事件相互作用不能预测抑郁症状的变化(Cohen,Young,& Abela,2012)。 在临床研究方面,研究者在大学生被试中发现认知高风险被试比低风险被试有更高的重性抑郁(Alloy et al.,2000;Hankin,Abramson,Miller,& Haeffel,2004)和无望抑郁发病率(Alloy,Abramson,Whitehouse,et al.,2006)。消极生活事件会导致认知易感高风险被试抑郁症状增加(Bohon,Stice,Burton,Fudell,& Nolen-Hoeksema,2008)和临床抑郁发作的风险(Alloy,Abramson,Walshaw,& Neeren,2006;Fresco,Alloy,& Reilly-Harrington,2006;Bohon et al.,2008)。此外,研究者在青少年样本中发现,压力事件与消极归因方式和功能失调性态度相互作用可以预测1年后重性抑郁发作(Lewinsohn,Joiner,& Rohde,2001)。 从无望抑郁认知理论的特异性层面来看,认知易感与消极生活事件相互作用能预测事件特定的消极推理(Haeffel,2011;Hankin et al.,2005;Hong,Gwee,& Karia,2006;Panzarella,Alloy,& Whitehouse,2006),认知易感与无望显著相关(Haeffel,Abramson,Brazy,& Shah,2008;Hong et al.,2006;Panzarella et al.,2006),无望在认知易感与抑郁之间有中介作用(Feng & Yi,2012)。也有研究发现,将消极事件归因为内部原因是抑郁青少年是否会无望的预测指标之一(Becker-Weidman et al.,2009)。消极认知方式和冗思与青少年早期的抑郁症状显著相关(Young,LaMontagne,Dietrich,& Wells,2011)。与冗思和功能失调性态度比较,消极认知方式是更稳定的抑郁认知易感因素(Hankin,2008b)。这些研究结果为无望抑郁认知假设提供了更有力的实证支持。 关于无望抑郁认知易感的发展特点,有研究认为抑郁认知易感在儿童早期出现,是特质性的,与抑郁的关系较为稳定,童年早期表现出的抑郁认知易感能有效预测儿童的抑郁风险(Hayden et al.,2013)。但抑郁认知易感也并非是不可改变的,如同伴可能会影响个体抑郁认知易感的变化(Haeffel & Hames,2014)。此外,Cole等(2008)对2~9年级的儿童和青少年追踪4年,发现被试的认知易感总体水平有一定稳定性,但其结构可能会因年龄而发生变化。消极生活事件方面,不少研究者认为人际事件与无望抑郁症状有密切联系(如,Rehman,Gollan,& Mortimer,2008;Haeffel & Mathew,2010)。 病因学研究还存在不少分歧,尤其是以儿童为被试的研究。如,有本土研究发现儿童认知易感与无望抑郁之间的关系不支持无望理论的抑郁认知假设(吴文峰,卢永彪,杨娟,谭芙蓉,姚树桥,2011)。认知易感操作化方法(周丽华,陈健,苏林雁,2012;Haeffel,2010)、研究设计以及被试(Bohon et al.,2008;Hyde,Mezulis,& Abramson,2008;Reilly,Ciesla,Felton,Weitlauf,& Anderson,2012)等因素可能对这些分歧的产生有影响。总的来说,消极的认知方式与消极生活事件是无望抑郁潜在的风险因素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 3 希望:以恢复模型为核心的无望抑郁恢复研究 3.1 希望、恢复模型与抑郁恢复 病因学研究最终是为了回答:“人们怎样才能从抑郁中恢复?”研究者用两种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是建立更合适的认知方式,改善抑郁症状。既然无望是病因链上最近端、充分的原因,直接破坏无望或改善病因链上增加无望风险的因素都是无望抑郁潜在的恢复途径(Abramson et al.,1989)。如,改善消极的认知方式和改善环境都有助于个体抑郁的恢复。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是达成这一愿景的较佳选择。CBT改善抑郁症状效果显著已被许多研究者认可。近年来,CBT还发展了电话(Furukawa et al.,2012)、网络(Andrews,Cuijpers,Craske,McEvoy,& Titov,2010;Cuijpers et al.,2011;Glozier et al.,2013;Ruwaard,Lange,Schrieken,Dolan,& Emmelkamp,2012)等新形式。但CBT对训练者专业素养要求高、参与者训练时间长和费用大的特点限制了受益群体。针对这种局限性,Koster,Fox和MacLeod(2009)等采用认知偏向修正方法(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CBM)以及针对注意(attention)偏向的CBM-A,通过电脑任务反复训练被试更多地注意中性词语,帮助被试纠正导致心理病理的认知偏向(如,对消极刺激的注意偏向)。有研究者认为CBM或CBM-A能有效减少抑郁症状(Wells & Beevers,2010;Haeffel,Rozek,Hames,& Technow,2012),也有研究者认为它可能还会增加抑郁症状(Baert,De Raedt,Schacht,& Koster,2010)。尽管存在这些争议,CBM因易传播、操作简单可能会成为一个有潜力的干预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Haeffel et al.,2012)。无论是CBT还是CBM或是CBM-A,研究者都是在抑郁的大范围内研究其有效性,对无望抑郁的特殊症状以及特定的认知假设的影响还未见有研究报告。 二是重获希望,促进无望抑郁恢复。希望代表了积极的情感和对未来积极的期待,期待积极的结果会出现或是消极的结果会被改变。事实上,不少抑郁个体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Beck,1967)。这促使研究者思考个体内部是否存在促进抑郁缓解/恢复的积极素质。无望抑郁的恢复模型正是在这一思路上提出的,Needles和Abramson(1990)提出提升的认知方式(enhancing cognitive style)(也有研究者称其为积极认知方式)与积极生活事件相互作用有助于抑郁个体重获希望,促进抑郁恢复。从逻辑上看,恢复模型是期待通过与认知易感素质-压力模型相对应的因素和路径获得对应的结果。与消极认知方式对应提升认知方式被定义为:(1)归因积极事件为内部的、稳定的、总体的原因;(2)认为积极事情很可能会带来其他积极的结果;(3)根据积极事件推论自己在某些方面是特殊的。与CBT比较,恢复模型绕开了无望抑郁的危险因素,直接关注抑郁恢复的保护性因素对个体重获希望、缓解无望抑郁症状的影响。从恢复模型的视角来看,未来的干预研究也可以挖掘个体潜在的积极素质/保护性因素促进个体健康发展,而不仅仅是改善认知易感或是修正不适应的认知方式。 3.2 以恢复模型为核心的无望抑郁恢复研究 根据无望是无望抑郁最近端、充分的原因,Needles和Abramson(1990)推论无望感的持续决定了无望抑郁症状的持续,并由此提出无望抑郁恢复最近端充分的原因——重获希望。重获希望的影响因素包括了经历积极生活事件,并对积极生活事件作提升的归因方式。而提升认知方式缺失的个体在调节情绪时难以从积极事件中获益。在实证研究中,Edelman,Ahrens和Haaga(1994)发现,积极生活事件与稳定的、总体的原因归因可以预测希望的发展和心境抑郁的恢复。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Needles和Abramson在恢复模型中也曾论述“消极生活事件及其归因方式可以预测无望抑郁的发作,而积极生活事件及其归因方式可以预测无望的抵消,从而促进个体从抑郁中恢复”。或许受这一思维的影响,尽管恢复模型强调希望是无望抑郁恢复最近端、充分的原因,大部分相关研究还是使用Beck无望量表测量被试无望水平的变化,并没有直接测量希望水平,潜在的逻辑是无望水平降低则希望水平提高。如,Needles和Abramson对42个抑郁大学生(BDI分数达16分及以上且对条目2做非0反应,条目2非0反应表示存在无望感)进行追踪调查发现,有提升认知方式且经历积极生活事件的被试无望水平显著降低、抑郁症状减轻,而提升认知方式缺失的个体难以从积极事件中获益,并以此结果来论证无望抑郁的恢复模型。研究者在门诊抑郁被试中也发现提升的认知方式与积极事件相互作用能预测无望与抑郁症状的变化(Johnson,Crofton,& Feinstein,1996;Johnson,Han,Douglas,Johannet,& Russel,1998)。但希望和无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望水平低的个体并不代表着可以归为无望一类,无望水平低的个体也并非可以推论为希望水平高(Stoddard,Henly,Sieving,& Bolland,2011),无望与希望两者非一维两极对立。 此外,Vines和Nixon(2009)在儿童被试中发现,提升的认知方式调节消极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且提升的认知方式对积极事件和抑郁症状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也有人认为提升的认知方式是通过减少压力生活事件来降低抑郁风险(Kleiman,Liu,& Riskind,2013)。Needle和Abramson(1990)也曾发现积极事件增加与消极事件的减少有类似的功能,消极事件减少且有提升归因方式的被试无望水平也有降低,并推论提升归因方式或许既影响个体对积极事件的反应,也会促进生活环境总体的改善。研究者在儿童被试中还发现积极事件的数量对消极事件与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作用虽不显著但有积极影响(Vines & Nixon,2009)。 无望抑郁恢复研究的结果也存在不少分歧。Needles和Abramson(1990)认为,独有积极事件或提升认知方式不足以使被试重获希望,两者兼有才能促进被试抑郁症状的缓解。Haeffel和Vargas(2011)在大学生被试中发现,提升认知方式和积极生活事件都能缓冲消极事件给认知易感个体带来的抑郁风险,认知易感和生活压力水平低同时提升认知方式水平高、积极生活事件多的个体有最大的抑郁恢复弹性。该研究认为,提升的认知方式、积极事件对抑郁个体都有独立的保护作用,这与抑郁恢复模型的观点不一致。 总的来说,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积极事件和提升认知方式单独或相互作用,能培养认知易感个体在面对逆境时的认知弹性,调节压力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具有保护性作用。具体表现为有提升认知方式且经历较多积极生活事件(或消极生活事件减少)的个体比其他抑郁个体弹性恢复的可能性更大。 4 小结与展望 综合已有研究,从认知角度来看无望抑郁研究基本可以分为病因学研究和恢复研究两个取向。病因学研究取向以无望理论为基础,以认知易感-压力模型为核心,着力无望抑郁的认知风险因素。由于针对无望抑郁的临床认知行为干预、治疗研究未见报告,无望抑郁恢复研究仍以探索无望抑郁认知保护因素为主。该取向以无望理论为基础,以恢复模型为核心,探索个体内在的积极认知素质激发情绪弹性、缓冲抑郁症状的作用。目前两个取向的交叉研究极少,综合考察个体无望抑郁的风险、评估个体无望抑郁的弹性恢复,整合病因学和恢复研究这两大取向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Haeffel和Vargas(2011)提出应该综合考察积极和消极两类生活事件及其认知方式,Haeffel和Grigorenko(2007)也从病因学的角度提出抑郁的风险因素和弹性因素是相互影响的,但都没有明确提出应该整合两个研究取向的意见,也没有就整合的途径、整合的意义做出详细的说明与论证。回顾已有研究,整合两个研究取向前,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思索。已经有研究者详细讨论了无望抑郁认知易感相关研究的研究设计(Alloy et al.,1988;Bohon et al.,2008)以及认知方式测量等问题(Haeffel,Gibb,et al.,2008)。本文不重复谈及这些方面,只分析两个取向的研究现状以及整合两个取向的基础和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4.1 对无望抑郁恢复研究关注不足还是关注点转移? 与无望抑郁的病因学研究比较,研究者认为无望抑郁的恢复研究关注不足(Haeffel & Vargas,2011)。从谷歌(Google)的学术搜索引擎中可以看到,至该文成稿之日,Abramson等(1989)提出无望理论的文章被引用2666次,Needle和Abramson(1990)提出抑郁恢复模型的论文被引用253次。这个数据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病因学研究和恢复研究两个取向被关注的差异。本文认为,分析后者关注不足的原因或许还不能局限于无望抑郁研究领域,应扩展视野从更广的相关领域来分析。 研究者对恢复模型的关注或许已经超越无望抑郁研究领域。恢复模型认为提升认知方式是促进抑郁个体恢复的积极素质,这与积极心理学提出的关注个体积极品质的观点很接近。如提升认知方式与积极心理学提出的乐观、希望等概念很接近。Seligman从归因风格的角度解释乐观,认为一个人是乐观还是悲观取决于解释问题的方式。乐观的人将积极事件归因为持久的、普遍的和内在的原因,将消极事件归因为短暂的、具体的和外在的原因,悲观的人则相反(Snyder & Lopez,2002)。且乐观(以及习得乐观)、希望的研究涉及成就、个体主观幸福等诸多领域。而无望抑郁恢复模型强调心理疾病的痊愈,是一种免除疾病的观点。或许这是恢复模型虽然横跨了传统心理治愈与积极心理学两大研究取向但仍然显得关注不足的重要原因,又或者说无望抑郁恢复模型提出的积极素质——提升认知方式正在其他的领域被人们以其他方式关注。 4.2 积极事件归因方式与消极事件归因方式之间相互独立? 恢复模型指出积极事件的归因方式与消极事件的归因方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Needles & Abramson,1990)。研究者在非临床儿童被试(Conley,Haines,Hilt,& Metalsky,2001)和青少年临床抑郁被试(Curry & Craighead,1990)中发现了支持这个观点的结果。Macleod和Moore(2000)也反对将积极和消极归因看作是单一维度的对立两极,认为将积极事件的归因方式和消极事件的归因方式看作两个独立操作的系统或许更合适。但最近有研究者在儿童被试中发现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归因方式中等相关(Vines & Nixon,2009)。目前的研究都是采用自陈问卷的方式考察积极与消极两类生活事件及其归因方式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有无其他因素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有句古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比喻坏事可能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能引出坏的结果。这不仅仅是指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之间会存在一定的联系,祸福之念其实也是指对事件的归因带来的情感体验。如果积极、消极事件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个体对这些事件的归因方式会是完全独立?还是既独立又相互联系?或是其他?两者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文化差异?本土研究还未涉及这些问题。积极事件的归因方式与消极事件的归因方式之间相互独立的观点,还有待商榷,值得进一步研究。 4.3 不同生活事件及其认知方式对抑郁的影响具有一贯性还是双面性? 消极生活事件及消极认知方式对抑郁发展有消极作用,积极生活事件和提升认知方式对抑郁恢复有积极作用已经被许多研究者认可。已有研究通常报告有无验证这种影响,是否证实了认知易感-压力模型或恢复模型的适用性。即,研究者潜在地认为这些认知方式和生活事件对抑郁病程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具有一贯性。是否消极认知方式对个体发展也会有积极影响,提升的认知方式可能会有消极影响,不得而知。其他研究领域的一些结果提示我们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Norem和Cantor(1986)提出防御性悲观(包含消极期望和反思两个基本成分),认为并非所有的悲观都是适应不良的表现,消极思维也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防御性悲观能在失败时保护个体,促使个体为取得好成绩更加努力,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苏彦丽,张进辅,2008)。“抑郁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则认为抑郁个体对于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对于现实的风险与损失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是因为一般人群的自我认知过于积极(积极自我偏见)才衬托了抑郁个体认知方式的消极。或者这种消极认知偏向只存在于严重抑郁患者中,轻度抑郁患者是“现实主义”的(Haaga & Beck,1995)。相对地,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乐观易损的观点,认为当外部环境非常不利时,对未来的乐观期待可能不利于个体的适应。在较低的压力下,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适应得更好,但在持续的压力下,乐观主义者的抑郁风险更大(Chang & Sanna,2003)。双相抑郁研究也表明“好事情”不能过头(Francis-Raniere,Alloy,& Abramson,2006;Lex & Meyer,2009),其原因可能是当经历积极事件时,积极归因的个体可能会变得有希望、兴奋,从而发展轻躁狂或躁狂症状(Alloy,Abramson,Walshaw,et al.,2006)。这些研究提示我们应了解消极认知方式的积极作用,警惕提升认知方式可能带来的风险。 消极事件和积极事件对抑郁的影响或许也不是一贯的或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基础。消极生活事件对个体发展也会有积极影响,如消极生活事件让人变得更明智、更成熟、能更好应对其他的生活危机(Thomas,DiGiulio,& Sheehan,1991),当这些消极生活事件与高水平的社会支持相结合时,会对个体的情绪(Caspi,Bolger,& Eckenrode,1987)和心理成长(Park,Cohen,& Murch,1996)有积极的影响。同时,尽管许多研究表明积极事件有助于抑郁恢复(Haeffel & Vargas,2011;Needles & Abramson,1990),积极事件缺乏是抑郁质的(depressogenic)(Haeffel & Vargas,2011)。但也有研究认为积极事件可能会因为导致生活改变而成为压力事件(Brown & McGill,1989),增加抑郁风险(Davidson,Shahar,Lawless,Sells,& Tondora,2006)。积极事件对个体的情绪可能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积极事件可能因为其积极的效价保护个体免受情绪压力,但也可能因为其新异性和不确定性来带来压力(Shahar,Elad-Strenger,& Henrich,2012)。 4.4 整合两大研究取向的意义与可行性 Needle和Abramson(1990)曾指出,消极事件及其消极归因方式是影响抑郁发作的重要因素,积极事件及其提升归因方式是促进抑郁恢复的重要因素。大部分研究也证实积极事件的归因方式与消极事件的归因方式是两个可以同时存在但相互独立的系统。Abramson等(1989)指出压力生活事件的发生或积极生活事件的不发生会促使无望抑郁因果链启动,相对应地Needle和Abramson(1990)认为积极事件的发生和消极事件不发生会促进抑郁恢复模型的启动,但对于没发生的事件是难以在研究中辨析其影响的。这可能是许多研究者独立思考抑郁的病因和恢复的原因。Haeffel和Vargas(2011)认为人为地将两种生活事件分离对研究是有害无益的。对“无望抑郁恢复取向关注不足”等上述问题的思考,其实也揭示两个研究取向是有诸多的内在联系的,整合这两个研究取向是可行的且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视域。 整合能更好地综合评估个体抑郁的风险和预后。如,有研究者提出积极事件与消极事件数量比至少达到2.9∶1(也称为罗莎达比率,Losada Ratio)才能缓冲消极事件对抑郁的影响,发挥积极事件的最佳缓冲力(Losada & Heaphy,2004;Riskind,Kleiman,& Schafer,2013)。Voelz,Haeffel,Joiner和Dineen(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消极认知方式和提升的认知方式水平都很低的个体是最有弹性的,他们的抑郁风险水平与没有消极认知方式的个体相当。与此不同,Haeffel和Vargas(2011)则发现消极认知方式水平低且提升认知方式水平高或积极生活事件多的个体抑郁恢复的弹性最大。综合这些研究结果,或许可以认为个体的生活环境和认知易感性都是动态变化的,全面考察这些因素才能更准确地评估个体的抑郁风险和弹性恢复,也有利于理解以往研究结果中存在的分歧。 两个研究取向整合也是切实可行的。除实证研究基础外,无望抑郁的病因学和恢复研究其实质都是源于无望理论的认知易感-压力模型。Needle和Abramson(1990)认为恢复模型与无望抑郁的认知易感-压力模型是相容的。两个因果链的要素构成结构以及逻辑都相对应,积极事件与消极事件启动因果链的方式一致。而从整合的视角来看,与其说恢复模型是一个独立的模型,不如说恢复模型是认知易感-压力模型的补充,即两个研究取向具有整合的可公约性基础。 尽管无望抑郁认知研究历经20多年的积累,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对精神疾病的诊断产生的影响还非常小,DSM-IV和DSM-5诊断手册并无该抑郁亚型。未来的研究应拓展视域,整合两个研究取向对无望抑郁的认知风险和弹性恢复作出更准确的评估,加强临床研究为治疗和干预提供更可靠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以整合的视域研究易感个体如何从易感性中弹性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