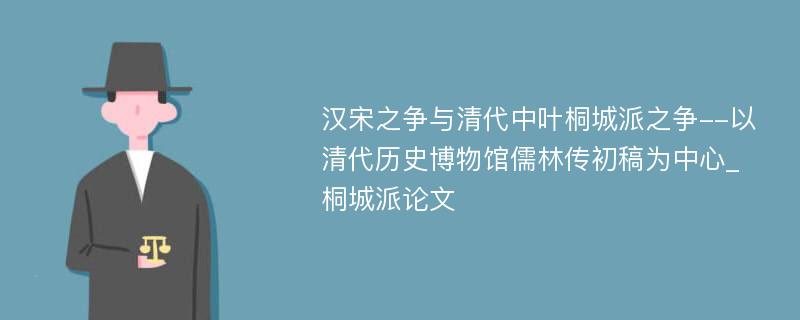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国史馆论文,儒林论文,初稿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10)04-0078-06
汉、宋之争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四库馆臣曾认为:“自汉京以后,学凡六变,……要其归宿,不过汉宋两家,互为胜负。”① 将二千余年的儒学发展史,归纳为汉、宋二派互相争胜的过程。有清一代,学者埋首董理群籍,成就蔚为大观,后人述及清代学术,亦常以“汉学”代称。然而,尽管汉学在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处于执学界牛耳的地位,但由于清朝官方始终将宋学悬为功令,宋学学问并未完全消亡,有清一代,关于汉宋学问的争论仍所在多有,学者基于各自或汉或宋的学术宗尚,著书立说,扬己抑人,构成了学术史上颇具特色的景观。
今人对清代汉宋之争的研究颇多,其中关于二家争论的核心,已有观点主要有两种:1、考据学和义理学两种不同为学方法之间的争执。这种观点产生较早,也是长期以来学界的一般看法。2、清代汉学发展出来的新义理与宋明理学旧义理之间的冲突。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张寿安、张丽珠等台湾学者为代表。她们反对传统以训诂称汉学、以义理称宋学的“二分法”,认为“礼理争议”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核心。“汉宋之争,应是义理学内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汉宋歧见;而不是考据学与义理学两种不同形态的学术路线之争。”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循的观点:“清代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官方,其实就是君主一人驾驭臣民的统治之‘术’。因此,一方面要迎合‘术’守住意识形态,一方面要通过客观历史的研究来突破义理、致用等意识形态的规范,来为‘学’争取些许的自由,这两种取向的冲突,即是所谓‘汉宋之争’的核心含义。”③
这些关于“汉宋之争”实质的不同看法,其实道出了这个问题的不同面向。其中,考据学与义理学的争论应是汉宋之争最主要的方面。近年的研究表明,清代理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信奉并从事理学研究的学者所在多有,既非前辈学者所形容的“竭而无余华”,也不简单只是帝王驭下的统治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④。而“以礼代理”固然是一种新义理,但那是汉学家经由考据这一汉学为学方式,由汉学学术生发出来的。所以“礼理争议”是由汉、宋两种不同为学路径导致的争论,本质上仍不脱汉、宋学术之争的大范围。
其实,清人基于各自学术宗尚对汉宋学术优劣的陟抑,在指出对方学问的缺略处之外,也蕴含着各以本方学问为周秦以来孔学正统的想法。“这种一方面否定他人,一方面肯定自己的目的,显然是在恢复千余年前的两汉儒学旧传统,以取代自南宋以来六百年间理学家所建立的新儒学传统,藉以加强汉学家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⑤
通过编修学术史、描绘学脉,将彼方学问打成异统,是学者为己方学问争取正统时常采取的手段,清代之前已是如此。南宋朱熹撰《伊洛渊源录》,其职志即是为以二程为代表的道学争取儒学正统地位⑥。清初学者排击陆王,亦通过学术史的编写阐发意见⑦。而在清代中叶,汉学学者抑宋扬汉,为汉学争取正统的活动,则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清国史《儒林传》初稿的编修过程上。
一、清国史《儒林传》初稿之体例
清国史《儒林传》是清朝官方修史机构国史馆编纂的一部当代学者类传,该传自嘉庆中开始编纂,前后删订续修多次,直至清末宣统年间仍有编辑,也是一部清人自撰的清代学术史⑧。该传初稿的编修,主要是在阮元的主导下进行,编纂体例则主要受到清初《明史》编纂的影响。
在关于《明史》体例的最初设计中,“道学”一传也包括在内。彭孙遹曾有《明史立道学忠义二传奏》,较早提出设立《道学传》。康熙二十一年徐乾学补《明史》总裁,二十三年与徐元文撰成《修史条议》,亦主张为理学(道学)家设类传,但遭到朱彝尊、黄宗羲等的激烈反对,史馆最终采纳多数学者的意见,未立《道学传》。
在这场争论中,始终蕴含着关于汉宋学术,何者才是儒学正统的不同意见。彭孙遹认为宋儒直接孔孟心传,其学醇、其功巨,有不得不特为表彰者。他要求将明儒中与程朱合者(理学家),和有功于传注的学者(汉学家)区分开来,将后者与那些“学未大醇”者入之《儒林传》,认为这样才不会使大道混淆,显示出其以宋学为学术正统的倾向:“窃惟历代之史,凡儒学诸臣皆载《儒林列传》,独《宋史》于《儒林传》之前复立《道学列传》一篇,专以记大儒程颢、程颐、朱子为主,其及门弟子悉为编载。盖以道学之统自尧舜至于孔孟代相授受,孔盂殁后,千有余年,而得程子、朱子发明六经之蕴,远契列圣之心,其学至醇,其功甚巨,故特立此传以衍孔孟之真传,明正学于天下,诚非无见也。……自今纂修《明史》,合无照《宋史》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合者编为《道学传》,其他有功传注及学未大醇者仍入之《儒林传》中,则大道不致混淆而圣谟独高于今古矣。”⑨ 徐乾学则意识到载入理学传者未必皆胜儒林,并云“《宋史》程朱门人亦多有不如象山者”,但仍然坚持“学术源流,宜归一是”⑩。
反对设《道学传》之学者的观点正好相反。朱彝尊注意到《宋史》将言经术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别之为道学,又以同乎洛闽者进之道学,异者置之儒林的做法,蕴含着以程朱义理为正统的观点,“其意若以经术为麓而性理为密,朱子为正学而杨陆为歧途,默寓轩轾进退予夺之权,比于《春秋》之意”(11)。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的正统:“然六经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尧舜之术,不外是焉,学者从而修明之,传心之要、会及之理、范围曲成之道未尝不备,故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12) 汤斌更认为经书之外无道学:“《宋史》道学、儒学厘为二传。盖以周、程、张、朱继往开来,其师友渊源不可与诸儒等耳,而道学经学自此分矣。夫所谓道学者,六经四书之旨体验于心,躬行而有得之谓也,非经书之外,更有不传之道学也。”(13)
这些围绕着《明史》编修问题的儒学正统之争,特别是《明史》最终只立儒林传,不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做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汉学逐渐兴起,并渐渐开始占据主流的学术发展时态。众所周知,“儒林列传”最早见于《史记》,所叙次者皆为“传经之儒”。后世史书仿而效之,在各自《儒林传》小序中,所描绘的也多为“经学历史”。经学占据了儒学的主导地位。元修《宋史》,首度标举道学传,又加诸儒林传之上,传经之儒的地位有所下降,失去了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清初学者借由讨论《明史》编修问题所实欲争取的,正是传经之儒(汉学)在儒学中的正统,所采用的手段,则是取消为程朱理学家立传的道学传,而以为汉学家立传的儒林传囊而括之。因此,清初学者对《宋史》道学传的看法,并不是从纯粹的史书编纂学方面出发讨论后的结果,也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甚至也不一定是最合理的)看法。乾嘉之际的史学家章学诚就深以《宋史·道学传》之设为是:“宋史为元人所撰,疵病甚多。以史家法度而言,等于自郐无讥矣。然有特笔创例可为万世法者。……又《道学》、《儒林》分为二传,前人多訾议之。以谓吾道一贯,德行文学,何非夫子所许?而分门别户以启争端。此说非是。史家法度,自学《春秋》,据事直书,枝指不可断而兀足不可伸,期于适如其事而已矣。儒术至宋而盛,儒学亦至宋而歧。《道学》诸传人物,实与《儒林》诸公迥然分别,自不得不如当日途辙分歧之实迹以载之。……如云吾道一贯,不当分别门户,则德行文学之外,岂无言语政事?然则滑稽、循吏亦可合于儒林传乎?”(14)
清初因修《明史》而引发的“道学”与“儒林”之争,特别是《明史》最终仅设儒林传,不再单独为理学家立传的做法,对嘉庆中清国史馆之修《儒林传》有重要影响。阮元主导编纂的初稿,《凡例》开篇即盛赞《明史》将“道学”融会于“儒林”的做法:“《史》、《汉》始记儒林,《宋史》别出道学,其实讲经者岂可不立品行,讲学者岂可不治经史,强为分别,殊为偏狭。国朝修《明史》,混而一之,总名儒林,诚为盛轨。”(15) 并批评《宋史》的二传分立:“《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也。”(16) 但和清初学者明确喊出的“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足以统儒林”的口号所不同的是,清国史《儒林传》的编者似乎还强调汉、宋持平的态度:“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迳也。门迳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实未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也矣。”(17)
尽管编者做出了如此明显的调和汉宋的表态,历来学者皆认为是传仍以汉学为重。侯外庐曾分析《拟国史儒林传序》,认为其在重视汉学的前提下,叙述中有意歪曲了清朝之前的儒学发展史。“他在文字上尽其委婉曲折之能事,首述学术之流变,对于汉儒,‘复兴六经’,推崇备至,对于魏晋玄学,认为‘儒道衰弱’,对于宋儒轻轻叙过,不加抑扬,对于明儒,认为‘不出朱陆,空疏甚矣’,对于清朝学者谓‘卓然不惑,求是辨诬’,‘精研古义,诂释圣言’,‘好古敏求,各造其域’,……按照他的这样述学,无论如何得不出‘两汉名教得儒林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为什么他做出这样的矛盾文章?实在是由于他所云:‘我朝列圣,道德俱备,包涵千古,崇宋儒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一句文化政策。所以,这篇文章是官样格式,不是他的内心话。”(18) 德明则认为:“从选择传主的标准来看,史书《儒林》一向是学行并重,而由阮元选择者来看,却偏重于学,尤重汉学。如毛奇龄、阎若璩等在清儒心目中德行品评不高者,因有考据著述,亦被选入。”(19)
清学以汉学为主要特色,但在清代历史的不同阶段,汉、宋学术的具体面貌则非常丰富。以清初为例,虽然就后来汉学大盛的事实上溯,基本可认定这一时期,儒学主流正处于由理学向考据学转变的过程中,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理学仍然比较兴盛。学术史的编写,应该如实反映这一时期“儒林”与“道学”并存的汉、宋学术现实。但阮元主持的初稿,虽制定了汉宋持平的写作方针,却在叙述儒学史时特别突出汉学的地位,在入传人物方面又将汉学家作为叙次的主要对象,为汉学争取正统地位。这种扬汉抑宋的取向,在处理关于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的入传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作家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20)。百余年来,学界研究成果颇丰(21)。但这些已有研究,大多数仍将桐城学者主要视作文学家,将其作品归类为文学作品,较少注意到桐城学者在清代儒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事实上,桐城学者在经学等方面亦有造诣。嘉庆中,清国史馆纂修《儒林传》初稿时,部分桐城学者被认为可以入传,但由于主事者崇尚汉学,他们的经学成就因其理学的学术宗尚而被轻视,加之他们在辞章方面亦颇有成就,所以被史馆列入《文苑传》中。因为后者较为时人所轻视,被列入《文苑传》中类似被打入另册,所以引发了桐城学人的不满。他们或致书史馆争之,或在私人信件中进行讨论。这些文字,既体现了当时学界对国史馆这部当代学术史应如何编纂的不同意见,也反映出清代中叶汉宋二学相互争论的学术时态,这些都是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内容。以下即以桐城学者的言论为切入点,分析该传所折射出的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
二、桐城学者主张宋学的学术取向
清中叶汉学大盛,流风所及,学者不仅多治考订之学,更多讥诋宋儒、宋学者,标榜汉学、诋毁宋学俨然成为时尚(22)。但同时仍有一批学者深知汉学之弊,注意对义理的阐发,姚鼐及经其所发扬光大的桐城学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姚鼐论学,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义理尤为其所强调者。在他的笔下,被清代汉学家认为“去古未远,独得圣人真意”的汉儒,其学“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授,侪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后虽有通儒渐出,贯穿群经,然“其弊也杂之以谶纬,乱之以怪辟猥碎,世又讥之。”只有到了宋代,“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而“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仄”,此皆“其宋儒论学之效哉!”因此,他认为:“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蔸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23) 姚鼐所授之徒亦多承师说,主张宋学,形成了桐城学派表彰宋学的学术取向。他们重视义理,反对《明史》取消道学传而以儒林传囊而括之的做法,要求恢复道学传在史书中的原有地位,陈用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陈用光,字硕士,江西新城人,“从(姚)鼐最久,师说尤为笃信”(24)。他对《明史》废道学传深为不满,认为当时主张废道学传的朱彝尊“纂修《明史》时所上总裁七书言多中史法,独第五书言儒林道学不宜分传,则于司马、班氏所立义例及宋元明儒之源流派别皆有考之不详者。”(25) 在他看来,宋代的理学大师远胜汉代的传经之士,“夫通天地人之为儒,称此名者,非周程张朱莫属也,彼京刘之属曷足云。”只不过因《史记》、《汉书》所创之“儒林传”所传者乃在于经学,故“京刘之属有不可没者”(26)。陈用光的这一看法颇足玩味,他既以只有周程张朱等理学家才配得上“儒”的称号,实际上就将研治章句训诂的汉学家排斥在外,这种观点较之清初修《明史》时学者试图以儒林统摄道学的做法,实际上走得更远,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的传经之士根本配不上儒的称号,这无疑从根本上把汉学家打翻在地。
道光间,陈用光出任福建学政,正好赶上《福建通志》的编纂,他极力主张在其中设立道学传以表彰宗尚理学的闽籍学者,特别是身为福建人的理学宗师朱熹。但当时主持修纂的汉学家陈寿祺并不同意,“道学之名,创自元人,古无是称,不可以为典要,且道外无儒,儒外无道,道与之儒,将何分辨?……夫圣门四科,游、夏列于文学,孔子语子夏以为君子儒,语子游以学道,舍儒何以为道,舍学何以为儒。紫阳大贤,百世尊仰,然平心而论,正与游、夏伯仲,使紫阳而在,亦未敢自谓驾二贤而上之也。必欲因仍《宋史》之旧,道学、儒林歧而为二,乖违旧章,失所依据,欲崇道学,转蹈不经,恐徒供人窃笑耳。”(27) 坚持不为理学家立专传,以致梁章钜说他:“墨守汉学,排挤宋儒是其故智。”陈寿祺去世后,陈用光联合地方部分意见和己相近的学者,持续施压,迫使陈寿祺的继任者,同样主张不为道学立专传的高澍然辞职,并使这部志稿的刊刻被迫延迟并险些遗失,在后来对该志所进行的修改中,道学最终立有专传(28)。
在这个问题上,桐城派其他学者也多持此说,主张不可以儒林传代替道学传,方东树以《汉学商兑》一书激烈批判汉学时,更认为清初学者对于《宋史》设理学家类传的批评,其实出于“深妒”(29)。一往一还之间,体现出学术史编纂背后的汉、宋争论。
史书中登载的文字,必定不可能是对时代巨细靡遗的全貌写真,它只是著作者对自己所观察(包括亲身经历和发掘文献)到的历史情况的描写。换句话说,后人经阅读史书所感触到的历史,乃是经史家过滤后的历史,并非也无法是历史事实的全部本真面目。而那些有幸存留在史书上的人和事,必定是被史家所认为特别重要者,因为后人乃是借由史书的记载以了解过去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古代读书人都希望身后能在史书上留有一篇佳传,赵翼曾云,“男儿生坠地,例须一篇传”。桐城学人强调恢复道学传在史书中的原有地位,也就是表彰理学的一种方式。
三、桐城派的无奈
由于《儒林传》出自官方修史机构,对于入传者来说,被收录其中也等于其学受到官方表彰,所以学者之门生汲汲为师谋入传者,所在多有,并将此当作表彰师说的手段。但提倡宋学的桐城学者虽多方奔走,却难以谋得一席之地。
桐城学者对该传的编修一直非常关注,姚门弟子利用在史馆任职的有利条件,经常向乃师通报相关情况。姚莹曾写信给姚鼐汇报凌廷堪入传情况,引起姚鼐强烈不满,“所言近时诸公于学问邪正之辨不明,其所品论殊非公当,诚然。吾昨得凌仲子集阅之,其所论多谬漫无所取,而当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宁足以信后世哉!吾家自当力为其所当为者,书成以待天下后世之公论,何必竞之此一时哉!”(30)
这是一封写给姚莹的家书。在信中姚鼐说:“吾家自当力为其所当为者,书成以待天下后世之公论。何必竞之此一时哉!”这勉励侄孙的一句话,表面看来,似乎表达了这位桐城掌门对后世关于桐城学者可能的评论拥有充分自信,实际却显示了他对当下学界以《儒林传》形式扬汉抑宋,轻视讲求宋学的桐城派之做法的深深无奈,即既然此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只能寄望后世“公论”。
姚门弟子不满国史馆《儒林传》侧重汉学,积极为本方学者谋取入传,但这些努力多以失败告终,在整个学术界如日中天的汉学氛围下,提倡宋学的他们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这更加深了他们的无奈感。姚门弟子曾试图将姚范入传,此事先由在史馆任职的姚元之致信姚范曾孙姚莹。姚元之因“史馆修儒林文苑二传,阐发幽隐”,命姚莹以姚范之家集上呈史馆,以备采择。姚莹虽“因子孙不敢议其先祖之义而未明言请入何传”,但他强调姚范“病近代诸公或竞谈考据,以攻抵宋儒为能,谓此人心之弊”的论学大旨(31),认为“仅若以诗文入传,是以精深之学转为辞章掩矣”(32),足见其寄望姚范能入《儒林传》的想法。但就史馆所成之稿来看,姚范后来所入为《文苑传》,可见他虽于宋学有所成就,终难符合史官眼中的儒林标准,这次努力以失败告终。之后姚门弟子的目光又集中在乃师姚鼐身上。嘉庆二十年九月,姚鼐刚刚去世,陈用光就以为乃师谋入史传为己任。他写信给姚莹,请后者为姚鼐撰写行状,预备上呈史馆,作为日后撰写传记的准备,“吾师以德行文章为后世师表者四十余年,所当上之史馆其生平出处言行之大缀而状之,弟子之责也”(33)。尽管陈用光官至礼部侍郎,地位不可谓不高,影响不可谓不大,也没能改变史馆主张汉学诸官将其师归入《文苑传》的结果,这次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当年姚鼐面对史馆主事者利用《儒林传》抑制宋学的情况时,虽感无奈,尚能喊出“吾家自当力为其所当为者,书成以待天下后世之公论。何必竞之此一时哉!”的口号以激励后辈,但在他的弟子那里,由于连番请将本方学人入传的活动均以失败告终,甚至连未来“天下后世之公论”也不寄望了。嘉庆二十一年,姚莹路过姚鼐曾讲学的钟山书院时,写了一首诗给陈用光,将姚门后学那种无可奈何,又带着一点绝望的心情体现的淋漓尽致:“千秋学术太纷夸,谁识渊源尚一家。常恐时贤从末俗,妄持史论乞京华。韩欧有道皆知重,汉宋门户祗自夸。文苑儒林君莫问,大江东去日西斜。”(34)
当代学者曾认为:“任职史馆的姚门弟子,在修史时,对桐城一系的学人,不能不有所偏重。”(35) 此语诚然。但同时也要注意到,由于姚门弟子之汲汲为本方学者谋入《儒林传》的活动并未成功,所以他们虽任职史馆,但对是传的实际影响力可能相当有限。
桐城学者之所以积极谋入《儒林传》,深以入《文苑传》为耻,主要是和时人重儒林、轻文苑的观念有关。清国史馆的学者传记,除《儒林传》外,还有《文苑传》。尽管当时人已认识到“经生非不娴辞赋,文士或亦有经训”(36),但文人和学士在时人心目中似乎更是不可兼得、彼此对立的两个称呼,并且在清人的观念中,学者的地位在文人之上。比如桂馥就认为“读书莫要于治经”,否则即是虚度此生,“今之才人,好词章者,好击辨者,……皆无当于治经,胸中无主,误用其才也。诚能持之以愚,敛之以虚,刊落世好,笃信师说,以彼经证此经,以训诂定文字,贯穿注疏,甄综秘要,终老不辍,发为心光,则其才尽于经而不为虚生矣。”(37) 他又附和顾炎武“一号为文人,则无足观矣”的说法,称“一号为才人,将不得为学人矣”,表示“与其崔、蔡宏丽,无宁马、郑饾饤”(38)。
因此,清人看重儒林传,轻视文苑传,甚有恐为文苑传中人者(39)。并且出现了部分学者本入文苑,后又改归儒林的情况。这是时人轻视文苑传,子孙惧其先人不得佳名,多方奔走后的结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汪中,他曾被阮元列入《儒林传》中,史馆在修订中拟将其改入《文苑传》,这一消息于嘉庆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被时在史馆任职的朱士彦写信传递给了汪中子汪喜孙,十二月九日,后者写信给王念孙,请求王念孙寄书阮元,说服史馆诸官将汪中由《文苑传》改入《儒林传》(40)。汪喜孙从朱士彦致书到写信给王念孙,前后不过二十日,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反应可谓迅速。不仅如此,汪喜孙还特别搜集当时学界对其父学问的评价为《汪氏学行记》一书,其中有相当部分为汪中当入《儒林传》的言论,如焦循:“去年史馆中,下问《儒林》、《文苑》两传,当入何人?循以尊公之名,宜征实列入《儒林》,未识能依否?然亦公论也。”(41) 这显然是企图以民间“公论”来影响“国史”的书写,汪喜孙的种种举动,皆说明时人对于二传高下的看法。
由此即可了解清国史馆将某些桐城学者列入《文苑传》这一事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从表面上看,这些学者因其辞章之学而厕身国史中之《文苑》,亦得垂名于后世,但由于时人对《儒林》、《文苑》二传高下的认定,只有进入《儒林传》者才被视为学者,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这些桐城学者的经学成就,不承认他们对经典的义理阐发也是对这些典籍的一种研究。应该说,国史馆《儒林传》初稿将大部分桐城学者打入《文苑传》,虽然并不符合这些学者的自我定位,但却对后来的学术史研究有着深远影响,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这和清代中叶国史馆纂修《儒林传》时候所形成的看法不无关系,桐城学者当日百计不得跻身《儒林传》,无奈之下只有寄望后世公论,但就其后的历史事实来看,他们的希望并未实现。
四、结论
作为一部清人自撰的当代学术史,清国史馆《儒林传》本身就是清代学术发展变化的产物。本文通过对该传初稿编修体例的分析,认为这部由阮元主导编修的传稿,在体例的拟定中效仿《明史》,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在入传人物的确定中则偏向汉学家。通过对桐城学者的学术主张和言论的分析,本文认为,清国史馆忽视这些学者的经学成就,而将其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反映了汉学学者利用学术史编修以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注释: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② 张丽珠:《清代新义理学——传统与现代的交会》,里仁书局2003年版,第149页。
③ 张循:《十九世纪清代的汉宋之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0—21页。
④ 参见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⑤ 王家俭:《清代“汉宋之争”的再检讨——试论汉学派的目的与极限》,载氏著《清代研究论薮》,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⑥ 陈祖武:《中国学案史》,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4页。
⑦ 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⑧ 关于清代国史馆编辑《儒林传》的具体过程,参见拙文:《清国史馆儒林传纂修活动考述》,《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25卷,第3期,2008年春。
⑨ (清)彭孙遹:《明史立道学忠义二传奏》,载氏著《松桂堂全集》卷3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⑩ (清)徐乾学:《修史条议》,载氏著《儋园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12) (清)朱彝尊:《史馆上总裁书》,载氏著《曝书亭集》卷32,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6、277页。
(13) (清)汤斌:《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载范志亭、范哲辑校:《汤斌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14) (清)章学诚著、冯惠民点校:《丙辰札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2页。
(15) 《儒林传稿·凡例》,载《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8页。
(16)(17) (清)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载氏著《擘经室集》一集,卷2,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页。
(18) 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三友书店1944年版,第538页。
(19) 德明:《阮元史学撰著述评》,《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20) 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1) 江小角、方宁胜:《桐城派研究百年回顾》,《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
(22) 据张循研究:“大量的读书人……无论对‘汉学’还是‘宋学’,他们往往并没有很高的修养,乃至根本就是不入流的门外汉。”因此,“汉宋之争并非只是少数专业学人书斋里严肃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广泛传播于读书阶层的时髦话题”。见张循:《论十九世纪清代的汉宋之争》,第22—23页。
(23) (清)姚鼐:《赠钱献之序》,载氏著《惜抱轩文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册,第56页。
(24) 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60页。按,当代学者曾认为,“(陈用光)能实事求是地对当时的学术,特别是考据之学作出客观评价,与姚门其他弟子狭隘的师门观念不同。”(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事实上,对汉学有肯定言论的并非陈氏一人,姚门其他弟子也有类似言论,但他们之肯定汉学,不过是要以汉学补宋学之罅漏,其表彰的核心仍在宋学。在崇尚宋学,排击汉学上,陈用光和姚门其他弟子并无显著不同。
(25)(26) (清)陈用光:《朱锡鬯史馆上总裁第五书书后》,载氏著《太乙舟文集》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493册,第387、388页。
(27) (清)陈寿祺:《答陈石士阁学书》,载氏著《左海文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第228页。
(28) 陈忠纯:《学风转变与地方志的编纂——道光〈福建通志〉体例纠纷新探》,《福建论坛》2007年第2期。
(29) (清)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30) (清)姚鼐:《与石甫侄孙莹》,姚鼐著、陈用光编:《姚惜抱先生尺牍》卷8,宣统元年刊本,第14页。
(31) (清)姚莹:《援鹑堂集后叙》,载氏著《东溟文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512册,第383页。
(32) (清)姚莹:《与张阮林论家学书》,载氏著《东溟文集》卷3,第395页。
(33) (清)姚莹:《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载氏著《东溟文集》卷6,第428页。
(34) (清)姚莹:《丙子过钟山书院有作寄陈石士编修用光律原刑部》,载氏著《后湘二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513册,第38页。
(35)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36) (清)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载氏著《雕菰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第183页。
(37) (清)桂馥:《惜才论》,载氏著《晚学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458册,第648页。
(38) (清)桂馥:《上阮学使书》,载氏著《晚学集》卷6,第694页。
(39) 据说,姜宸英自少年起就“常恐为文苑传中人”。见(清)方苞:《记姜西溟遗言》,载氏著《方苞集·集外文》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5页。
(40) (清)汪喜孙:《致王念孙书二》,载赖贵三:《昭代经师手简笺释——清儒致高邮二王论学书》,里仁书局1999年版。按,关于此信的撰写时间,赖氏书中认为是嘉庆十二年,而王章涛则系于嘉庆十七年(见氏著《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92页),此处从王说。因为嘉庆十二年阮元尚在浙江为巡抚,并未来京纂修《儒林传》,喜孙何以辗转请其将汪中由《文苑》改入《儒林》?
(41) (清)焦循:《焦里堂与喜孙书》,载(清)汪喜孙编:《汪氏学行记》卷3,收入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下册,“中研院”文哲所2003年版,第9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