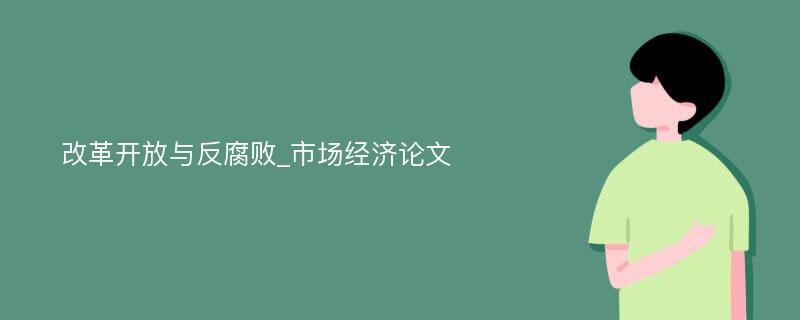
改革开放与反腐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化与腐败关系辨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卓有成效地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政策,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市场机制的逐步引入,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目前我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能忠实地代表国家、民族及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号召力、组织力和管理力,故而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无比信赖和强有力的支持。这是任何人或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客观现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党和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内部,确有不少人丢掉了共产党人的本色,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运用党组织及人民赋予的权力,大肆地进行索贿受贿、损公肥私、滥用职权、敲诈勒索等肮脏活动。特别是近几年来,极少数变质变节分子以权力为资本,以谋利为动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使得权钱交易为根本特征的权力腐败现象,已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些人不仅对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视而不见,而且认为腐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是现代化的“必然伴侣”,有的甚至主张保留权力腐败滋生的土壤及其生存空间。因为在他们看来,权力腐败既不是经济发展的羁绊,也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桎梏,而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催化剂”或“第一级火箭”(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理论动态》,第813期。)。 其实这些观点和主张并不新鲜。众所周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 ·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就曾断言:不发达国家业已存在的政治腐败现象能起到冲击其僵硬的行政体制并为经济发展“松绑”的作用(注: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权力腐败能“帮助这些国家轻松愉快地踏上现代化道路的征程”,因而是“值得欢迎的润滑剂”。(注:塞缪尔·P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可见上述观点的本质和中心内容是一致的,那就是权力腐败有百益而无一弊。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举步维艰,多多少少与其盛行的腐败之风有关。有些国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秩序井然,一般地说,均与该国较为完备的法制及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历史的经验还昭示我们,在我国,凡注重加强廉政建设,注重惩治腐败工作并力图使之法制化、制度化、常规化、经常化,生产力就发展,社会就稳定,人民就安居乐业。而对此略有松懈和怠慢,或对惩治腐败采取“运动式”的办法,而不运用法制、制度来扼制和惩治,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停滞,社会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人民群众就会不满不安,并压抑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必须指出的是,权力腐败对现代化建设丝毫起不到积极作用。这是因为腐败削弱了党和政府的权威,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会控制不住”(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就会天下大乱,权力腐败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新秩序难以形成。公共权力私有化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根基,污染了社会风气,妨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剧了干群关系的矛盾,削弱了人民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总而言之,权力腐败是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的大敌,是亡党亡国的潜在性危机因子(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巨大阻力和破坏力。既然如此,我们必须从思想和认识上端正态度,决不能对腐败分子及其行为听之任之,甚至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
二、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新形势下的权力腐败现象为何滋生并蔓延,分析其产生的根源是扼制与根除腐败的基本前提。
1.封建残余和小生产意识的影响,是产生腐败的历史根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又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它的重要表现就是可以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类型和社会存在不同步。因此,两千年的封建残余观念和小农意识能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少数党员、国家公职人员中发生的腐败现象均可找到封建主义和小农意识的印证。例如,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同现在的“官贵民贱”的思想,封建主义的宗法观念同现在存在着的“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的裙带政治或家族政治现象,封建的特权思想同一些人把公共权力私有化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封建社会的官利一体、官财一家、官本位至上的无官不贪的官风、政风同现在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的腐败行为,封建官僚控制的“官工”、“官商”同现在的官倒官商合污现象,小生产自私性意识与现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及“最后捞一把”心理,小生产的散漫性与现在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违法乱纪行为等等,可谓是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2.落后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消极作用,是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
第一,落后的生产力与腐败产生有一定的联系。这是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使物质财富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有些产品供不应求,造成市场短缺,物质的匮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使得人们想尽办法拼命追求富裕。当采取正常或一般的手段达不到目的时,便有可能使某些掌权者采取不正当行为为自己谋取私利,从而走向腐败。
第二,生产关系的不完善,会给腐败的产生提供某种物质条件。生产力水平低,不平衡的多层次、多结构的形式并存,表明了公有制还很不完善,多种经济物质实体的利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在市场无序、竞争不公平不合理的条件下,就可能使一些国有企业或私有企业的某些人运用金钱、美色、物质财富去收买、拉拢、腐蚀或贿赂拥有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一旦后者利欲熏心,就会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于是权钱、权色、权利交易等怪胎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三,腐败现象的产生与市场经济不成熟及其负面影响有着很直接的关系。我国的市场经济实际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很不成熟,要达到市场经济法制化、规范化、民主化、公平化和合理化的程度,还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过程中,而市场运行机制不正常,市场经营规则不健全,特别是价格体系中不合理的比价存在,物资的国家供应和市场供应之间,国有企业的经营业务与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经营业务之间,都存在较大的“断层”与“间隙”,这就给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提供了诱因和条件。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联的一种经济体制,因此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及最终目的和目标上都有本质区别。但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然有与西方市场经济相类似之处,也有其天然存在的负面因素。比如一旦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扭曲变形后引入政治领域,就会使一些人陷入损公肥私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又比如,市场经济下货币职能的充分显现,会激发一些意志薄弱者和丧失免疫力的掌权者的资产阶级“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膨胀。在他们眼里,货币或金钱已到了万能的地步,把党的最高政治理想抛到了一边,一个心眼向钱看,所谓“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则想”就是这些腐败分子阴暗面的真实写照。在“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心理支持下,一些党员干部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改革政策不配套,政策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是腐败产生并蔓延的现实根源。
其一,我国原存的旧体制中存在着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弊端,在转型期还没有得到根除,国家公职人员(尤其以行政部门最为突出)直接介入经济过程,担任生产经营主体和行政长官双重角色,这为以权谋私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由于我们在管理上、制度上的政策很不完善和配套,从而造成了局部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约束和控制的态势,这就给腐败创造了更为现实的条件。
其二,现行的双轨制为权钱兑换提供了诱因和机会。
其三,法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基本上进入了“有法可依”的轨道,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存在。立法体制、司法体制及具体制度,仍然不能完全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许多法律,特别是有关惩治腐败的法律还没有完备的量刑标准,可操作性差,而随意性又多于规则性。诸如有“从严”、“从重”、“不得”、“禁止”等等,但往往“禁”而又不“止”。究其原因,不在于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原则,而在于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实施中走了形,变了样。事实告诉我们:腐败之所以有禁不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在一些地方在惩治腐败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过程中,以言代法,以罚代法或重罪轻判、轻罪不判及死罪不毙的现象很严重,这无形中助长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反腐败斗争的必由之路:综合治理
由于腐败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有着各种极其复杂的原因,这就决定了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为此必须把反腐败斗争贯穿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并且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对策,进行综合治理,以达到扼制和铲除腐败的根本目的。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市场经济建设,铲除产生腐败的经济基础。大力培育以市场为主体的自我调节、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生产力或经营主体与国家政治权力的适当分离,最大限度地割断金钱与政治权力的联系。
第二,加强行政体制建设,铲除产生腐败的政治前提。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机构改革,使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割断政府与企业的“母子”关系,克服政企不分、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的弊端,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权力运行体制,以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的良性发展。
第三,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与腐败行为作斗争,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彻底铲除腐败现象的关键性条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其民主权力不仅仅在于拥有管理国家和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权利,而且还在于负有责任感、正义感、使命感,敢于和一切危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仅仅指望名目繁多的“文山会海”夸夸其谈的说教来铲除腐败只能是一种奢望。
第四,加强廉政制度建设,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没有制度,好人也可以变坏;有了制度,不能说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为所欲为。这是非常精辟的结论。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其一,可以防止惩治腐败的斗争“运动化”,并使之经常化、常规化和制度化;其二,对权力有效地进行监督和制约。失控或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政治权力不是导致专制就是导致腐败和黑暗,基于此,廉政制度的建设重点应放在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督制约体系基础之上。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我国监督的网络系统(党的监督、国家机关的监督及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等),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健全和完善监督的具体制度及措施。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必须充分重视对廉政制度建设的实际评估问题,否则就不能真正地、全面地了解廉政制度建设是否彻底有效。因此,认真总结反腐败斗争制度化的经验与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第五,加强道德和法制建设,举起“德治”和“法治”这两把“双刃剑”。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铲除腐败。腐败之所以产生和蔓延,必定与道德水平下降或沦丧及法制不严、不健全有关。因此反腐败斗争客观上要求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建设。这势必要积极开展德育教育,提高廉政意识,树立无产阶级政治道德观,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为政者道德修养提高了,对于扼制和铲除腐败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要加强法制建设,严惩腐败。其一,加强立法工作,应尽快制定或颁布惩治腐败的专项法律,如《为政道德法》、《惩治腐败法》等。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健全的法律,惩治腐败很难奏效。其二,严格执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否则,一旦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必然会使腐败分子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藐视党纪国法并助长其腐败行为的蔓延和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