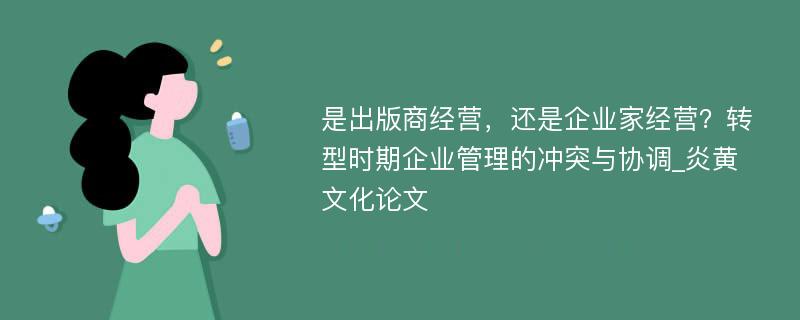
出版人经营,还是企业家经营?——改制过渡期的企业管理冲突与协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渡期论文,企业家论文,冲突论文,企业管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出版人,非指一般从事出版工作的人,而是指在改制前出版单位从事企业管理与企业制度设计的社长或总编辑。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出版社的经营风格、企业文化及其经营业绩,都深深地打上了出版人烙印。从某种程度上说,近30年中国出版成就的取得,是政通人和、文化学术繁荣的大环境下全体从业人员努力的结果,当中一批卓越的出版人则扮演了领导者角色。
在绝大多数非公益性出版社进入市场化运作后,出版企业经营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①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需要进行的公司管理架构设计较改制前有很大的不同;②公司的经营范围日益多元,从单一的图书内容经营发展到企业整体资产的经营;③评价公司经营绩效的对象由原来的主管机关、大众读者拓展至更多的利益攸关方,如债权人、投资者等。
企业顺利转制带来的是企业管理及决策方式的变化。企业需要稳健运营、文化发展天然存在的继承性使原有的绝大部分出版人顺利进入公司高管位置,这也使得改制成本最小化。企业的资产经营属性如何兼容内容出版的属性?站在企业决策与管理的角度,这个命题等同于,现代出版企业究竟是由出版人经营还是由企业家经营。本文尝试用更多的篇幅描述出版企业改制后新型管理冲突的客观存在,在呼吁业界关注的同时,提出若干弥合分歧与解决冲突的方法,制度创新更是不可回避。
一、卓越出版人:书业发展中的一个出版符号
中外书业发展史上,卓越出版人总是同其经营的出版机构共享美誉。贝内特·瑟夫(Bennet Cerf,1898-1971)是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兰登书屋的创始人,也是美国出版界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①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张元济(1866-1959)和他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一起载入中国出版史册。②在中国出版企业改制并部分上市之前,区区五六百家出版社,能够在规模甚至两个效益走在业内前列的无一例外具有一个鲜明特征——出版社社长或总编辑具有强烈的个性,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学术偏好和研究方向,开拓自己最擅长的图书领域,在“两个效益兼顾,社会效益优先”的大背景下,他们更乐于在学术出版领域里建立起自己的职业声望。他们也愿意结交有一致学术偏好的作者圈层,渴望取得与学界平起平坐的对话能力。在出版社内部,出版人重用和提拔那些认同自己出版观的编辑、发行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领导具有职位上的固化特征,因而他有时间和精力用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来实现某个出版产品愿景。特别是,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总有几件标志性的图书产品具有全国性影响。尽管出版社的资产百分百属于主管部门(比如大学出版社资产属于高校),但“核心图书产品—卓越出版人—品牌出版社”三位一体的出版特征已呈现在读者面前,“出版人及其出版的核心图书产品”作为一个符号反映一家出版社的社会地位。如资深出版人巢峰和他的《辞海》之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意义,资深出版人“金黎组合”和他们打造的系列畅销书之于湖北长江文艺社的意义。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间或某个出版人跳槽到了一家新的出版社,他仍然会凭借积累起的业内资历,比如“优秀出版人”、“韬奋奖”等个人头衔迅速对新进入出版社进行改造。而改造的结果往往是成功的。更有趣的是,个性化的出版人在经营图书的同时,他们也擅长利用超越图书媒体的方式发表自己的出版见解和主张,以期引导大众引导行业。在流行文化多元、媒体庸俗表达泛滥的年代,他们以审慎和忧虑的视角关注当下过分市场取向的书业态势,他们的声音彰显了一种社会责任担当,且经常以怀旧的方式表达自我肯定。
二、过渡期的管理冲突诱因
转制过渡期的企业管理冲突是改制前出版单位未曾遇见的。对出版人、对企业家、对上级主管部门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1.企业经营的多元
随着出版社转制任务完成、特别是部分出版企业上市后,企业的整体经营范围呈现多元。如安徽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出版企业有安徽人民出版社、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安徽美术出版社、黄山书社、安徽电子音像出版社、安徽画报社。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湖北人民、长江文艺、湖北教育、湖北少儿、湖北科技、湖北美术、湖北辞书、九通电子音像等出版企业,这些出版社在按单位原有特色发展的同时,上市集团公司一方面可以将许多成本内部化,另一方面可以整合资源,将经营范围进行实质性拓展,企业边界获得延伸。在《公司法》及企业章程范围内,企业原先以“内容”为形式的单一图书经营,转化为资产经营,“内容”产品只是整体资产中的一部分。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收购兼并以及跨地区经营、跨媒体甚至跨行业经营活动日益频繁。2011年,中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华为公司合作重组天闻数据公司,进入数字出版新领域;并购上海凯基印刷公司,成功介入商业印刷短版领域,实现异地印刷业务扩张。时代出版传媒则在波兰及东欧设立出版物销售、印刷与复制单位,投资5000万元参拍由冯小宁导演的《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公司利用闲置资金参股贵州商业银行及东方证券、华安证券等。③
2.企业评价主体的多元
在改制前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模式下,评价出版单位的主体主要来自市场读者(专家)和上级主管部门。出版单位只有依靠长期经营和优质图书产品积累才能获得社会肯定,风格化的出版人也多半在这样的出版单位诞生。出版社走向市场特别部分成为上市公司后,出版企业的利益关联方增多,投资者上升为企业的最主要利益攸关方。企业的经营目标要满足作为公司最高的权力机构股东大会的要求,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及集团下属出版社管理层必须服从集团公司利益,关注投资方(股东和债权人)的介入对传统出版风格及管理决策的影响。
投资者与读者的诉求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企业的投资者、企业图书产品的读者身份无法完全重合。在读者看来,出版人人格力量、图书产品与企业品牌已经形成读者广泛认知,企业上市意味着企业有更强的资金实力、更自由和更开放的市场,读者对企业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有更大胆的期待。另一方面,在独立纯粹的投资者眼里,他们需要“赚钱”能力强的企业家,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票红利是他们评价公司的尺度。他们希望职业经理人懂书,更要懂市场,能够持续可靠地给公司创造价值。在公司多元化经营年代,投资者关心企业资产的整合能力甚至超越图书的赢利能力,他们有理由相信,职业经理人(未必是出版人)才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具前景的企业资源整合价值,比如,重组收益、参股及其他对外投资形式取得的分红收益等。
3.基于新建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下的市场困惑
出版企业以上市公司名义进入公众视野时,在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下,企业多重的利益攸关方在公司内部都有其权利代言人,大股东的表决权地位以及中小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用手”或“用脚”投票机制。故投资者会关注企业的决策与经营权究竟是赋予惯性存在的“以书为本”的出版人,还是应该赋予新型的“以创造价值为主”的企业家?
类似于像《辞海》这样的标杆性大型图书,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元老级人物几十年磨一剑的成果。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下,中小投资者要求的投资回报通常不能超过5年。传媒出版类的上市公司股东如果被赋予真实投票权的话,这个图书选题方案可能会被废掉(那时似乎还没有政策性基金支持)。
传媒出版公司与一般工业企业产品形成最大的差异在于:出版公司中每一个产品都是一个独立的形态,一本书可以带来超额利润(类似于《哈利·波特》等)。而工业企业比如海尔,其产品多以规格化的形态批量出现,边际利润贡献不大,其经营爆发式增长经营不依赖于一件产品,而是某条生产线上系列产品。现行的传媒出版类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很难完全代替传统出版单位的选题委员会从事产品经营决策。传统出版单位里,“一个出版人可以做大一个出版社,一个出版人可以风格化企业品牌”,但在上市公司中,经理人很容易走向两面,或绕过董事会,按个人文化兴趣或者价值偏好从事公司经营;或者,掣肘于董事会的权力制约,摒弃文化的价值创造,而将传媒出版企业的经营等同于综合类上市公司。
此外,出版集团化,特别是一些大型传媒出版企业陆续上市后,原有定位于出版社、其固有的以“出版社品牌+出版人”为特征的出版企业形象已经被上市公司取代。企业上市的目的,除了获取直接融资、以外部力量促进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等以外,企业上市无疑放大公司的市场广告效应,股价的波动促使投资者关注影响股价的所有公司信息,进而作出短、中、长线的投资抉择。现在的出版上市公司通常是重建全新的集团品牌走向市场,如“时代出版”(安徽)、“中南传媒”(湖南)、“长江传媒”(湖北)、“出版传媒”(辽宁)等,集团下属原有的“社品牌”和“社风格”存在着被弱化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原有出版人继续因“做书而成名”、因“傍社而成名”的难度。
实际上,围绕上市公司董事会作为的某些企业经营决策,社会各界一直争议不断。2011年安徽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则委托放贷的公告就产生了相当大的争议。④
三、出版人与企业家的角色融合
短期来看,出版人转型为出版企业家,需要技能、经验与战略思维的全面转变。在图书产品作为企业资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交由职业经理人管理时,改制后的出版人很难顺理成章地在出版社上市后找到自己的位置。弥合管理冲突,实现角色融合,既要靠出版人与企业家在职业技能以及道德层面进行自我修炼,也需要基于企业共同愿景的设计,制度创新更不可停步。
1.企业家兼具出版人气质符合文化企业的禀性
文化企业共享一般企业属性,企业投资者及各利益攸关方的诉求长期来看是一致的,因而存在经营目标上的趋同;但文化企业仍要坚守其文化特质,其核心产品、其主营业务仍然是基于内容产业,出版企业能够在读者文化追求与投资者财富需要之间寻找到交集。出版人向企业家过渡是学管理的过程,企业家不具备文化品格也很容易被市场定义为“农民企业家”。出版企业家的文化品格提升靠自身修养,靠团队智囊,且在企业成长中获取。同时,企业的多元经营活动,比如企业的纵向、横向收购及兼并更多关注能否同现有主业——图书产品——有更大的协同,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中应嵌入更多的“内容”因素,基于“内容”进行文化创造,塑造大传媒概念。
2.企业发展中的共同愿景设计
一方面,以企业共同愿景,旨在向市场传达中长期的发展目标以及基于以“文化”为内核的企业价值观符合各利益攸关方利益,这对培育百年文化老店意义重大。同时,基于共同愿景的企业目标建立,客观上也可调和出版人主观偏好和特色专长与公司发展的关系,从而将出版社的发展建立在主业特色鲜明,同时又有助于分散企业风险的多元化路径上。在笔者看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含义有二,一是优秀经典作品的产出规模与产出效率提高,包括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二是文化能够彰显其表达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特征。出版企业上市吻合这一战略诉求。一方面,投资者拥有自由买卖股票的选择权,从而折射出文化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出版企业上市客观上具有丰富文化产品、创造受大众满意(投资者)的产品动因。出版人向出版企业家过渡进程当中,可以将自己的偏好表述在企业长期发展的共同愿景当中,二者可以在出版企业的平台上实现目标的统一。
3.公司治理架构中的特色制度设计
出版社在成功转制后,董事会成员较多地引入了外部力量。公司高管中的角色分配体现企业经营两种不同的运营观,新高管偏重于短期经营业绩,以赢得较高的社会满意度,但易将企业偏离轨道;原出版人按既定思维从事企业经营而易被人们诟病为改制不彻底。上市传媒出版企业的高管组成则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职业经理人由原先的出版企业社长或总编辑顺位取得,而董事长过去的职业经历比较复杂。这正如前所述,出版企业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应能平衡以下两个关系,关注单件图书产品对公司业绩的支撑以及据此产生的社会效益对公司品牌的意义;同时,妥善谋求基于内容产业的综合价值链开发及公司经营的多元化。特别应指出的是,出版企业业已存在的选题委员会制度曾经是双效图书推出、出版人品格与出版社品牌建立的重要制度保证;现有公司治理架构下应确保选题委员会在产品开发上的独立性、长期性,且选题委员会成员应在董事会中占据应有的席位。
在出版人与出版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表明,张元济既是杰出的出版人也是优秀的出版企业家,他把国家的发展和民智的进步与出版社的发展关联起来,制定了一系列的出书计划,进行了一系列的企业生产活动,最终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出版界的巨擘和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化机构,其影响力历久不衰。中国出版企业真正进入市场才刚刚开始,人们期待涌现杰出的出版人,也期待涌现真正的出版企业家,过渡期的管理冲突协调及隔阂弥合中,制度创新任重而道远。
①贝内特·瑟夫著,彭伦译.我与兰登书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②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③以上资料来自沪深上市公司时代出版、长江传媒、中南传媒2011年公司年报。
④时代出版(600551)8月30日公告:公司用6000万元委托交通银行安徽分行放贷,年利率达到了24.5%!这一动议在投资者那里得到普遍肯定,因为这一收益水平远远超过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2011年为9.85%)。但在某些出版人看来,公司被指责为“不务正业”、“高利贷者”。——散见期间相关报刊及网络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