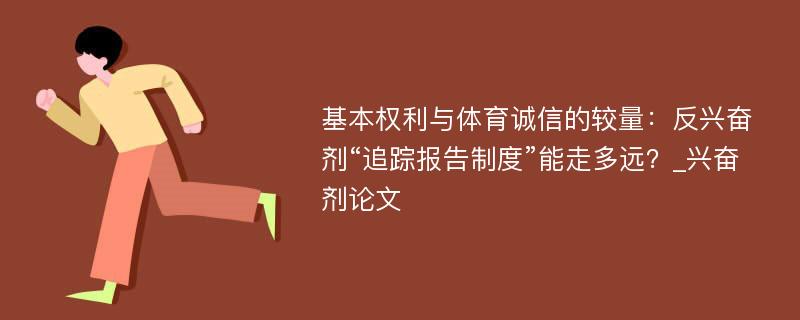
基本权利与体育诚信的较量:反兴奋剂“行踪报告制度”还能走多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权利论文,还能论文,行踪论文,走多远论文,诚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13)06-0008-06
CLC number:G80-05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13)06-0008-06
兴奋剂问题几乎是与竞技体育相随而生的,但随着体育的全球化和兴奋剂制造技术的发展,新型兴奋剂检测的难度不断提高,从而使国际反兴奋剂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反兴奋剂规则便日趋严格。但运动员作为普遍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正在这场斗争中不断受到侵蚀。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是优先维护体育的诚信,还是保护运动员的基本权利,二者的利益冲突和博弈将成为未来反兴奋剂斗争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其发展前景值得关注。
1 行踪报告制度的演变
随着兴奋剂制造技术的发展,很多禁用物质和方法只能在运动员体内存在一段有限的时间,经过这段时间后则再无法检测出阳性结果,然而,却能在比赛期间提高运动员的成绩。进行这种检测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了解运动员的行踪,在作弊者最可能使用禁用物质和方法时进行检测才最有效。因此,从2003年版的WADA《反兴奋剂条例》开始,就借鉴了许多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已经采用了的报告行踪做法,引入了运动员行踪报告制度。
1.1 2003版的行踪规则
根据2003版《反兴奋剂条例》,运动员的行踪要求受第2.4条调整,即“运动员赛外检测可及性适用要求的违反”。它规定运动员有义务接受赛外检验的适用规定,包括没有提供必要的行踪信息和错过根据合理规则宣布的检测。在对该条的注释中,指明运动员“有责任提供和更新他们的行踪信息以便能够在那里可以不经事先通知就进行赛外兴奋剂检查。”但如何报告,报告频次,如何处罚等都没有规定,这就为各体育联合会或者国内反兴奋剂机构自由采取规则留下了很大空间,即围绕行踪信息的专门规则和特定细节由各个国际体育联合会和国内反兴奋剂机构制定。
1.2 2009版的行踪规则
面临各体育联合会、各国内反兴奋剂机构所执行的各式各样的标准,WADA认为有必要统一建立起一致的行踪报告制度。经过各方谈判磋商,2009版的《反兴奋剂条例》最后确定了比较具体、严格的行踪报告规则。其第2.4条规定:凡在18个月内累计3次错过兴奋剂检查和(或)因未提供准确行踪信息而无法完成样品采集的运动员,应被认定构成一次违犯反兴奋剂规则。行踪报告制度主要针对高水平运动员,为此要求各个国际、国家体育联合会建立本项目的运动员兴奋剂检查注册登记库,凡纳入注册库的运动员应及时(提前3个月)报告自己的行踪信息,以便兴奋剂检查工作人员能随时随地地顺利执行事先不通知的赛外检查。
2 行踪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彰显着体育的公平和正直
2.1 行踪规则是反兴奋剂斗争的客观需要,它体现了体育的公平和正直
公平竞赛和正直价值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所在。因此,自1928年国际田联制定世界第一个反兴奋剂条例起,反兴奋剂规则就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自行车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所导致的赛中系列猝死事件终于让国际奥委会在1967开始对兴奋剂问题痛下杀手,此后反对体育中使用兴奋剂被确认为体育的固有规则。而行踪规则的引入则是为了应对提高比赛成绩的违禁物质平时服用而在比赛期间无法检测出来而设计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通过强调为了抓住那些作弊者不经事先通知而检测这样严格的行踪规则是反兴奋剂斗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正如WADA秘书长David Howman所坚持的,赛外检测是有效的反兴奋剂政策的基石,而且行踪规则是实现其目标、阻止作弊的最佳途径。[1]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指出,“今天的体育不得不为嫌疑人士的存在付出一定代价。”[2]英国体育组织、英国反兴奋剂组织对WADA的新规则也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认为“如果不知道运动员在哪里的话,药检计划的运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3]
2.2 行踪规则已经考虑了消除体育中的兴奋剂目标与保护运动员私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支持者认为,新的行踪规则与原规则相比已经有了一些人性化的改进。一个WADA媒体坚持新规则与各体育组织的规则相比“是一种改进,让运动员的生活变得更轻松而不应成为昼夜不停的兴奋剂监控的牺牲品。”[4]Howman指出,WADA特别关注避免让新措施太过分,而且规则实际上将监控从以前很多国内反兴奋剂机构的“7天24小时”的要求减少到了1天只有1小时临检。他相信该规则只是要求运动员提供计划和承担责任,他公开宣称更新一个运动员的行踪信息是很容易的、很快的,“不像发射火箭技术那么复杂。”[3]国际田联也支持WADA新的赛外检测政策,宣布这一制度对于有效地与体育中的兴奋剂现象作斗争而言还是“比例公平的”、“绝对具有强制性的”。尽管国际田联也承认这些要求给运动员增加了很重的负担,但国际田联相信,新的行踪规则在需要定位作弊者的存在以及实现清白运动员的权利之间达到了适当的平衡。[5]该组织理事长Andy Parkinson相信,新规则对于“维护清洁体育……清除体育中的作弊者是一种较少的代价。”[6]
一些运动员也表达了对新规则的理解。如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Paula Radcliffe就说:“我们都承诺让我们的体育变得纯洁。那就意味着纯洁运动员也要作出牺牲,但我们知道,那些负责运行兴奋剂规则者明白我们是人,会帮助我们解决任何新问题。我们在哪里都需要真正的国际公平检测。”[7]奥运会男子链球奖牌获得者Koji Murofushi说:“我们每天接受检查的烦扰是为了实现纯洁的体育世界。我想检测官员努力的结果就是为了保护体育。逐渐习惯于这种检查可能还有点困难,但一旦你习惯了你也就不再觉得有什么困难。”[8]
3 行踪制度引发的反对浪潮:其合法性受到质疑
就在2009新条例通过后一个月,其行踪规则就点燃了反对的风暴,很多世界高水平运动员和著名体育组织都纷纷对行踪规则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批评之声可谓此起彼伏。这些批评和指责的依据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3.1 新行踪规则侵犯了运动员的隐私权
在诸多人权保护的国际文件和多数民主国家的国内法中都把隐私权或私生活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加以保护,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7条、《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美洲人权公约》第11条等。权利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私生活安宁权、通信和个人信息不被泄露等。仅以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对《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的解释为例,隐私权就包括了个人身体、住所、人身监控、私人生活、通讯信息、个人肖像、私人信息和资料、姓名、家庭生活、性取向和性行为、受孕和堕胎等诸多方面。[9]由于行踪规则要求高水平运动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其行踪信息并保证在指定的一段时间内随时接受药物检查,因此,运动员的住所、通讯信息、私人信息和资料等必然需要透露给反兴奋剂机构。甚至在运动员享受家庭欢乐时光或者度假时也会因药检官员的随时光临而使其家庭生活、私人生活大受影响。为此,不少运动员都抱怨行踪规则成为他们焦虑的来源,降低了他们享受体育所带来的愉悦。例如Nadal就表示,规则对运动员的隐私缺乏必要的尊重,它实际上把运动员与罪犯同等对待,他强调说:“我们是人,我们不应当感觉像罪犯,因为我们只是些从事体育的人。”(Independent,28,January,2009)
3.2 新行踪规则侵犯了运动员的休息权
欧洲有学者提出,在法律上攻击WADA新行踪规则的最佳根据可能是《欧盟工作时间指令》,它规定了欧共体工人最低的安全要求、健康法规以及休息时间。特别是运动员可以根据指令第5条,即“每周休息时间”和第7条“年度休假”来挑战“行踪”规则。第5条规定,每个工人有权每周最低享有不受中断的2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第7条规定每位工人有权享受每年至少4周的带薪年休假或者度假时间(Council Directive 90/104,art.3,1993 O.J.(L 307)18(EU),arts.5,7)。据此,WADA的新行踪规则不得干涉一个运动员的每周休息时间和带薪休假的权利。如果有规则侵犯了这些权利,那么欧洲职业运动员们就有资格根据并入上述条款的《欧共体条约》提起诉讼。[10]
根据行踪规则,在一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中要有1小时,运动员要接受可能的不经事先通知的药检。由于运动员要提供他在1小时的时间里在哪里的信息,运动员实质上在每天要随叫随到。这样,根据第5条运动员享有的不受中断的24小时休息放松的权利在时间上可能就无法保证了。运动员无论如何必须在“指定的时间里”出现在“指定的地方”。WADA的新行踪规则要求每天都要得到遵守,这显然妨碍了运动员每周休息时间的权利。
而就第7条的休假权来说,行踪规则让运动员每天有1小时要固定于某个特定地方,运动员就不能随时自由地去他想去的地方,必须待在“指定的地方”1小时。假期时间通常被认为是运动员自由地可去任何地方,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不应有任何工作责任限制或阻碍他的活动。而根据WADA的行踪规则,一个运动员将会丧失这种自由。这些要求甚至让运动员假期里一天都不得安宁,更不用说享受指令第7条所保证的4周休假了。
3.3 行踪规则有损运动员的人格尊严
挪威奥斯陆体育学院教授Ivan Waddington曾从社会学视角对行踪制度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就行踪制度给运动员所给予的待遇来看甚至都不及缓刑或假释的罪犯的待遇,因为即使是在英国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恋童癖罪犯在假释期间受到警察部门的监控,也只在其改变了姓名和永久住所、或者离家7天以上,或者打算出境旅行时才要求其报告行踪,而并不要求报告每天的行踪。但那些被要求报告行踪的运动员们还都是些体育界的精英,往往是享有崇高的名望和社会声誉的人,却竟享受如此“礼遇”![11]此外,该学者还进一步研究了陌生的兴奋剂检查官员随时临检给运动员心理上造成的羞耻感。正如欧洲精英运动员协会(EEAA)所主张的,“被要求取尿样时还要被人观察着,这显然是很具有侵扰性的。”[12]前国际网球运动员,现为体育记者的Mathen Syed最近也提及,“在匿名的检验员的注视之下把尿尿到一个杯子里是有伤尊严的。”[13]Waddingto特别指出,兴奋剂检查官窥视运动员的身体不同于医学检查,因为医务工作者是经过了严格的医学教育的,他们已经养成了神圣的职业伦理,而兴奋剂检查官一般并没有经过那样的专业训练和伦理教育。因此,他建议WADA以及各国反兴奋剂机构都应对兴奋剂检验员进行医师职业伦理同样的教育。
3.4 行踪规则缺乏民主性,并不能代表运动员的普遍意志
争议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运动员通过参加比赛的协议而接受行踪规则是否是其真实意愿?二是WADA条例制定过程中所谓运动员委员会的参与是否实际代表了全体运动员的意愿?
就第一个问题,反对者认为,虽然运动员在比赛前都通过与其所属的单项体育联合会通过协议约定受WADA条例的约束,但这事实上并非运动员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这种协议是“要么同意,要么退出”的协议,运动员并没有其他选择权。虽然形式上是出于当事人的自愿,但对于年轻的或刚出道的运动员来说,或许还有是否选择从事体育的机会,但对于已经有所成就的运动员,或者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他们个人的全部财力、精力甚至家庭都长期投入了他/她所钟爱的体育事业,他们的成绩源于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而取得,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显然不可能仅仅因为对行踪规则有异议而轻易放弃他所赖以生存的体育职业和运动员资格。因此,运动员同意受行踪规则约束是被迫接受的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愿。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反对者同样认为WADA条例制定中的运动员委员会并不能代表全体运动员的意志。且不说代表的人数十分有限,就是这些人的代表资格也并不是全世界的运动员选出来的,而是由WADA的官员们指定的。他们在参与制定反兴奋剂条例的过程中也并没有广泛征集运动员的意愿。因此,他们的同意只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而已,并不能代表全球运动员的意志。比如欧洲精英运动员协会就不承认运动员委员会的12名委员代表了所有运动员(EEAA2008)。
4 行踪规则对运动员权利的限制具有正当性吗?
那么,面对上述众多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从法律角度来说,行踪规则对运动员隐私权、休息权、自由权和人格尊严这些基本权利的干涉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呢?这需要从人权受到限制的条件分析入手。
4.1 可以限制基本权利的条件
根据国际人权法原理,人的基本权利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受到限制:一是权利的克减;二是权利的限制。前者是指国家生存陷入危机或者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暂停或中止履行其承担的与某项人权有关的国际法律义务,它属于一种非常限制。后者是指国家对个人和群体行使人权的范围、方式和程度所施加的限制或约束,它属于一般性限制。[14]187行踪规则对运动员基本权利的限制显然属于后者。
对于一般限制,国际法确立了4项限制权利适用的条件:一是应具有合法的限制根据,即只能受到“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二是应符合合法的限制范围,像迁徙和择居、公开审理、宗教或信仰的表示、思想或意见的发表、集会结社等权利一般是不得限制的;三是应基于合法的限制理由,如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道德、公共卫生、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普遍福利等;四是应符合合法的限制程度,如不得超过民主社会所必需、是绝对必要的、相称的,即符合相称性原则。在相称性的判断上各国拥有一定的裁量余地。[14]188-191
从法律上说,人权法上限制和克减权利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而WADA作为一个国际民间组织显然没有这种权力,但由于各国普遍核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反兴奋剂公约》,而该公约则采纳了WADA《反兴奋剂条例》的基本原则,因此,WADA限制运动员的权利也就具有了合法的根据。对照上述条件,维护体育的公平和正直对于全球体育健康发展来说构成一种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因此,对运动员人权进行限制的正当性上就主要落脚于是否符合相称性要求上了。
4.2 行踪报告制度减损基本权利的合理性
一般说来,限制一个运动员的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是否合理主要是看这种限制与其所追求的目标是否是相称的。如果相称那么这种限制才是正当的。相称性原则不仅适用于特殊的兴奋剂案件,也是任何纪律处罚机关施加制裁的一般法律原则。要实现相称性原则还需要考虑两个要件:第一,任何限制必须适合于实现它要追求的目的,即阻止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第二,必要性要求。这意味着实现这种目的所要进行的限制不能有太多侵略性,即只要能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足矣,不能过分。[15]就此而言,尽管根除兴奋剂无疑是一种正当目的,但所使用的方法,限制的方式是否相称则是一个复杂的利益衡量问题。这取决于诸多复杂的衡量因素:如不同国家的运动员的权利意识存在差异,对反兴奋剂重要性的认识是否充分、不同国家的文化因素的干扰等等,都会影响运动员和体育组织对行踪规则的态度。从表面上看,行踪规则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似乎表明它已经突破了运动员和体育组织对于其权利侵害所能容忍的底线,他们普遍地内心确信所谓反兴奋剂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权利的受尊重之间的权重是不平衡的。但就实质而言,理论上的争论仍将会继续,要判决行踪规则是不是反兴奋剂所必需的、是无可替代的措施,能否推翻它最终还要取决于司法上的考量,这就需要对司法判例加以考察。
就目前已有的涉及行踪规则的判例来看,行踪规则的实体正当性和合法性并没有被撼动。
4.2.1 Ohuruogu v.UK Athletics Limited案(资料来源:CAS 2006/A/165(Apr.3,2007))
2006年8月6日,比利时田径名将,世界和奥运会400米冠军Christine Ohuruogu因违反了反兴奋剂行踪规则而被UK Athletics Limited(UKA)禁赛1年。事实是,她虽然向UKA提交了行程计划但对3次计划的修改没有告知UKA,从而导致了18个月内错过3次检查而受到处罚,但她对UKA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向CAS(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请仲裁。她主张国际田联的行踪规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运动员的限制性解释,即只能在运动员获得通知对这三次违反进行了评估以后才能确定违反兴奋剂规定。此外,Ohuruogu还提出,鉴于她的情况,一年的禁赛是不相称的惩罚。CAS仲裁庭没有认同Ohuruogu的观点,而是支持了国际田联的处罚决定,指出“赛外检查是有效反兴奋剂计划的核心。”CAS仲裁庭支持国际田联的行踪规则,宣布如果运动员没有提供足够的行踪信息,或者在18个月内三次没能出席兴奋剂检测就违反了反兴奋剂规则。另外,CAS认为,根据国际田联的规则,一年的禁赛也是正当和对称的,因为这属于WADA规定的范围,并认为WADA规则对于这些违反来说是“反兴奋剂运动的神谕”。最重要的是,CAS强调了行踪报告规则对于不经通知进行药检的重要性,对于那些未提供准确行踪信息的运动员需要给予有效的惩罚。仲裁庭的结论是:“运动员有义务提供充分和最新的行踪信息。这无疑是一项麻烦的工作,但反兴奋剂规则对于要抓住那些使用药物进行欺诈的运动员来说是必要的,因此,这些规则有时产生了很多人可能认为不公平的后果。这种情况应当是对所有运动员的一种警告,相关机构之所以采用如此严厉的行踪信息的规定,是因为它们对于持续地开展与体育中的药物滥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Ohuruogu,CAS 2006/A/1165 at 23.)
在Ohuruogu v.UK Athletics Limited案中,虽然CAS支持的是国际田联旧的“行踪”政策,但这一政策非常类似于现在的WADA行踪要求。这一裁决实质上导致了如下结论:任何向CAS挑战“行踪”规则的行为都可能不会成功。[3]
4.2.2 Subirats v.FINA案(资料来源:CAS 2011/A/2499(Aug.24,2011))
此案于2011年8月作出裁决。自2006年以来,委内瑞拉游泳运动员Albert Subirats 一直都向委内瑞拉泳联提交行踪信息表,然后由委内瑞拉泳联转交国际泳联。然而,在2010年和2011年间,委内瑞拉泳联3次没有把Subirats的行踪表转交给国际泳联。这三次中,每次国际泳联都通过向委内瑞拉泳联发函试图通知Subirats没有提交表格,但委内瑞拉泳联都没有转告。在第三次没有提交后不久,国际泳联指控Subirats违反了兴奋剂规则,并给予禁赛一年的处罚。Subirats不服上诉至CAS,主张他并没有违反任何兴奋剂规则。在上诉中,CAS裁决,运动员有责任通知国际泳联其行踪信息,不管其是否已将这种责任转让给了第三方。因此,如果第三方没有向国际泳联提供运动员的行踪信息,他自己最终依然负有责任。不过,由于国际泳联从来也没有直接通知过Subirats没有提交其行踪表,Subirats并不知道没有提交,因此,他并不存在违反兴奋剂规则的行为,对Subirats的制裁最终被推翻。
Subirats案表明了CAS的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它仍然肯定了行踪规则的约束力,指出即使实践中运动员通过约定或者事实上将提交行踪报告表的责任转移给了体育组织,但并不能免除运动员的违规责任。但另一方面,裁决实际上又以运动员没有过错而豁免了其责任。与之前的Ohuruogu案相比,这似乎意味着CAS在适用反兴奋剂行踪规则上的一种松动迹象:开始考虑各方在违规过程中的过错了。这是否体现了CAS对于反对声音的一种妥协亦未可知,但此案至少证明,CAS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正式否定行踪规则,否定它所体现的体育利益。也就是说,CAS仍未考虑过直接向WADA的行踪规则提出挑战,对于纯体育规则不加审查的信条依然在得到奉守。
5 行踪规则的未来走向
虽然从法律上看,目前行踪规则依然得到了顽强的遵守,但这并不影响实践中人们对它的实施能力及问题品头论足。例如,随着不赞成WADA新的行踪规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些运动员建议在运动员手机中安装全球定位系统跟踪设备以即时提供运动员的行踪信息。[16]然而,这种做法也并非完美,因为这一措施可以知悉运动员的即时位置,但却无法掌握其随后的行踪信息,让检测员无所适从。
总之,虽然“行踪”规则有侵犯运动员的隐私权、休息权之嫌,妨碍了他们自由活动的能力,并让他们受制于不断监视之下。然而,WADA认为需要应用严格的新的检测标准,这对于阻止体育中的兴奋剂滥用、维护体育的正直、维护国际比赛和奥运会的荣誉,同时也为保护运动员自身身体健康所必需。WADA的强硬立场让运动员、体育组织虽然不满但也无力改变,甚至CAS都不得不继续成为WADA规则的“卫道士”。正如James Halt所预言的,由于有效的反兴奋剂政策所产生的引人注目的利益,任何根据欧盟法在欧洲法院对行踪规则的挑战都可能遭到WADA的顽强阻击。虽然完全有可能根据欧盟法宣布行踪规则是违法的,但诉讼可能代价高昂,耗时费力。最终,那些挑战行踪规则,捍卫其隐私权的运动员所能采取的最佳道路也不过是在“公共舆论的法院”中踯躅前行。[17]换言之,在兴奋剂检测技术不能提供可替代的可靠措施之前,行踪报告制度仍将继续存在,这不是多少反对意见所能决定的,而是体育的公共利益所系。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运动员的基本权利可以任意践踏。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运动员Ian Thorpe的机密遭到反兴奋剂机构泄露的事件,这引发了反兴奋剂机构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如果运动员违反行踪报告制度要受到严厉处罚而反兴奋剂机构人员违反国际或国内隐私法却不受任何制裁,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WADA也开始引入新的保护运动员信息的国际标准,并规定在涉及由于实施行踪规则而侵犯了运动员隐私的案件中国内法优先的原则。同时规定,运动员的姓名除非符合隐私法否则不得对外宣布,运动员的信息使用必须获得必要的通知,反兴奋剂机构持有运动员信息不能超过必要的时间长度,授予运动员越来越多的权利对反兴奋剂机构持有其信息提出要求等等(WADA 2009第4.1、7.1、7.2、10.1、11.2款)。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和规定,来体现对运动员权利的维护,从而实现反兴奋剂与保护运动员个人权利之间的适当平衡。我们相信,未来的行踪规则也仍将会在此方向上得到继续发展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