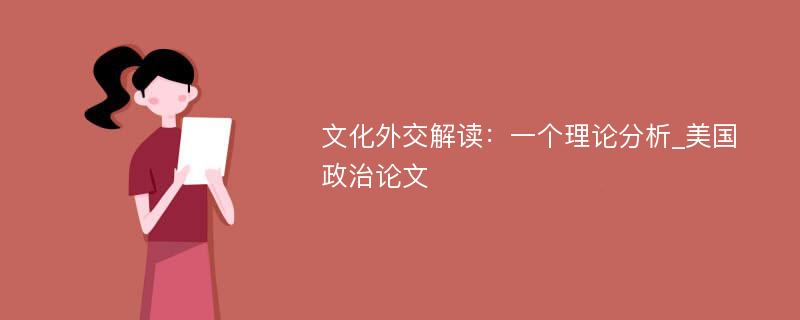
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外交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3-0050-09
冷战结束后,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在各国尤其是美国外交领域和学术界曾一度沉寂。但“9·11”事件后,文化外交率先在美国成为新的热门话题。美国政府力图从组织和战略两个方面恢复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外交的辉煌,以应对来自恐怖主义和新的“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对其国家利益可能造成的威胁,文化外交也再度成为美国紧握的思想武器(weapon of idea)。同时,其学术界和外交圈也不断关注法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文化外交。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关于文化外交研究则起步比较晚,研究成果也不太多。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亦开始讨论和研究文化外交,包括从思想理论、实践特色和国别的角度进行研究,国别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日本。但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文化外交究竟为何物并没有系统的理论论证,对其研究现状、定义、属性和特征也缺乏深度透析。① 本文试图对文化外交进行一次学理分析,以便人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文化外交的内涵、理解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一、西方学界对文化外交的研究现状
文化外交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已有一定的历史和较好的基础。1947年,美国国务院退休外交官鲁斯·麦科姆雷(Ruth Emily McMurry)和穆纳·李(Muna Lee)两人合写了《文化方式:国际关系中的另一种途径》(The Cultural Approach:Another wa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64年,美国前负责对外教育与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库姆兹(Philip Coombs)撰写了《对外政策的第四层面:教育与文化事务》(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这两部书较早地对文化外交的历史与功能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探讨。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著名外交史学家弗兰克A·宁柯维奇(Frank A.Ninkovich)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时专门对美国在1938—1950年期间的外交政策和文化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于1981年出版了专著《思想外交:美国对外政策与文化关系,1938-1945》(The Diplomacy of Ideas: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1938-1950)。该书认为美国文化政策起源于私人组织的慈善活动,后因战事需要改变了这个传统,美国政府开展文化外交是从1938年开始的,该书还论述了1938-1950年间美国政府对外文化关系的早期发展史。1996年美国外交政策协会(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出版了弗兰克A·宁柯维奇另外一部研究美国文化外交的专著《美国信息政策和文化外交》(U.S.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该书重点分析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遏制苏联的需要,全面展开了信息战,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成为美国政府炙手可热的宠儿,而文化外交却被冷落,为公共外交所同化,尤其体现在美国对文化与信息机构的重组上,以及政府在对外信息与文化项目经费投入的不对称上。
从80年代开始,西方其他国家也有学者开始从国家间文化关系角度探讨文化外交。曾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中从事文化外交的英国外交官J.M·米切尔(J.M.Mitchell),于1986年出版了专著《国际文化关系》(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该书是文化关系领域中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著作,从概念入手分析了文化外交与文化关系、文化宣传之间的异同,通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以及日本所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该书全面阐述了文化关系的缘起、发展、组织机构的演变、目标与手段以及作用与效果,是文化关系与文化外交研究的理论入门书。199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平野健一郎出版了其长期研究的文化关系成果《国际文化理论》,该书提出了系统的国际文化理论,包括文化基础论、文化摩擦论、文化交流理论、涵化理论等,他指出,所谓国际文化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2.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侧面;3.国际性的文化关系;4.国际文化。② 平野试图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探索国际关系新视角,构筑起一套有关国际文化理论的体系。他对国际文化关系的研究视角独特,对文化外交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不少美国学者反思美国政府对伊斯兰国家文化外交的失败,呼吁政府要高度重视对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外交工作,因此文化外交时下又成为热门话题,人们甚至开始怀念冷战时期的文化外交。③ 其中美国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所作的文化外交研究课题最有代表性。该中心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的组织,一家致力于检视文化政策中的关键性问题以及拓宽和深化全国性文化问题对话与研究的独立思想库。该中心1994年成立后便启动了一个名为“艺术、文化和国家行动计划”(Art,Culture and the National Agenda)的研究活动,受到了不少基金会的慷慨支持,共发布了5篇研究报告,分别为:“文化外交和美国政府:一项全面考察”(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A Survey)、“国际文化关系:多国情况比较”(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A Multi-Country Comparison)、“美国国务院支持文化外交的最近趋势:1993至2002年”(Recent Trends in Department of State Support for Cultural Diplomacy:1993-2002)、“有效的外交:文化外交中最成功的范例”(Diplomacy That Works:' Best Practices' in Cultural Diplomacy)、“慈善事业的一个新方向?美国基金会为国际艺术交流提供资助”(A New Mandate for Philanthropy? U.S.Foundation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Arts Exchanges)。这5篇文章是近年来研究美国文化外交最有影响的系列文章。④ 美国文化外交研究的最新成果是理查德T.安特(Richard T.Arndt)撰写的《国王的第一手段:20世纪美国文化外交》(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y Century,Potomac Books,Inc.Washington,D.C.,2006),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它是目前为止研究美国文化外交史最为全面的专著。⑤
同时,一些国际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政府高官也参与到这场讨论。2002年8月29至9月1日,彼特·J·卡赞斯坦在美国政治学年会(波士顿)发表了题为“开放的地区主义:欧洲和亚洲的文化外交与流行文化”(Open Regionalism:Cultural Diplomacy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urope and Asian" 的长篇学术论文。当看到中国在世界上推广“孔子学院”后,日本也加大了在海外建设日语学习中心的力度,外相麻生太郎于2006年4月28日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文化外交的新思想”的演讲,重点探讨日本的漫画外交,试图运用动画片和漫画书向世界推广日本文化。⑥ 2006年5月15日,法国外交部长杜斯特—布拉齐宣布,法国外交部与文化部将联合成立“法国文化署”,以促进法国对外文化交流,增加法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可读性”,每年将投入3000万欧元。⑦ 中国前驻法国大使、现任国际展览局主席吴建民、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等也先后就文化外交的意义和中国文化外交的建设提出了不少观点。⑧
尽管文化外交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正成为热点研究对象,但是文化外交是否具有自身的理论依据甚至理论体系、是否能成为外交学中的分支学科仍无权威定论和有效论证,它在外交领域的定位是否位列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支柱还是政治、经济、军事之后的第四方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可以说文化外交存在着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间。
二、文化外交的定义辨析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与国际关系一样古老,它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外交。美国前新闻署高级官员兼学者理查德T·安特(Richard T.Arndt)博士以研究富布赖特项目而著名,他在最新的著作中提出,至少三千多年前,文化外交便成为国王们的首要外交手段,从有文字记载来看,铜器时代文化外交已成为人类要求文明进步的一种规范。⑨ 在古代,罗马和波斯都曾将文化作为他们战争的一部分。罗马文明在语言、学识、秩序、繁荣和娱乐等方面的优势都是罗马征服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地区强有力的工具。⑩ 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较普遍地将文化作为外交关系的一部分。法国是第一个通过官方途径广泛进行宗教传播、教育输出、慈善事业等文化项目的国家,其目标主要针对近东和远东地区。随着1934年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创立,英国也正式进入文化外交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将文化作为战争工具,在拉美地区发动文化攻势(Cultural Offensive)。前苏联曾努力创建苏联文化和生活,在共产主义阵营大规模开展文化外交。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文化外交大国,尤以“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闻名于世。冷战时期文化外交发展到顶峰。冷战结束后,首先在美国出现了“鸟尽弓藏”的现象,国际社会似乎将文化外交打入了冷宫。(11)
以历史视角看文化外交,它是国家和民族间文化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治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外交活动迈向成熟的标志。而从根本上看,文化外交又是外交的基础和内核,一般来说,外交活动离不开文化外交因素。(12) 因此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赋予文化外交不尽相同的内涵。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政治学和人文学教授柯文·墨尔凯西(Kevin V.Mulcahy)对文化外交两面性的本质进行了阐述:就传统而言,在推动地缘政治的优势和保护国家安全利益方面,政策制定者认为文化外交“更加现实”(more realistic)、更加“强硬”(more tough-minded);相比之下,在促进相互理解而与种族优越主义和墨守成规作斗争时,人们认为文化活动无疑更加“理想化”(more idealistic)、更“注重质量”(more qualitative),这种两面性成为文化外交定义混乱和长期争议的诱因。(13) 英国比较早重视文化外交,1935年3月20日,伦敦泰晤士时报(The Times)刊登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成立公告时,曾对文化外交的功能进行了阐述:“致力于推进海外世界对英国语言、文学、艺术、音乐、科学,教育体制和我们国民生活其他方面的了解,从而增进海外世界对英国的好感、保持彼此之间密切的关系。”(14) 英国前退休外交官J·M·米切尔(J.M.Mitchell)将文化外交定义为文化在国际协议中的介入,是文化对国家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的直接支持。(15) 按照J·M·米切尔的定义,他所谓的文化外交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为许可、促进或者限制文化交流而与其他国家协商签订多边或双边的协定,例如:政府间召开的会议、协商洽谈文化协定、交流项目等;二是有关国家机构执行、实施文化协定及其所从事的文化关系方面的活动。(16) 英国与美国在文化外交定义上的区别在于英国特别突出政府的角色,没有给非政府组织以适当角色。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对文化外交的定义为: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公关活动。他指出,某项活动是否属于文化外交的范畴,可以用四条标准衡量:一、是否具有明确的外交目的;二、实施主体是否是官方或受其支持与鼓励;三、是否在特殊的时间针对特殊的对象;四、是否通过文化表现形式开展的公关活动。(17)
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政治价值观的作用下,对文化外交的定义会有所差异,因此,目前国际学术界尚没有一个权威定义。要全面理解文化外交的内涵,还需要从其行为主体和表现形式的分析入手。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不同,它的实施者既可以是职业外交官、也可以是非职业人员,例如学者、艺术家、跨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文化教育雇员等。作为文化外交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指的是主权国家,但从现代意义上理解,既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国际政治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区域组织、跨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如基金会、教育文化的学术团体和文化教育产业公司等)。从文化外交一元行为体的角度理解,它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是主权国家重要的外交形式之一。(18) 而从文化外交二元行为体的角度理解,它则是由政府或者充当公共机构契约协作者(Contractual cosponsor)的非政府组织向别国国民描绘本国情况的活动,其描绘目的是使对方国的人民提高对本国的了解与同情,从而提升本国的声望,支持其对外政治经济关系,或者加强生活在海外的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度。(19) 笔者比较认同这一定义。从文化外交从业者的素质来看,它是指,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学习和传播彼此文化以推进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活动;因此,依据罗伯特·罗索(Robert Rossow)观点,(20) 外交官,尤其是从事文化外交的人员,在文化交流与诠释方面的能力特别重要。鉴于文化外交官与知识界、艺术界和学术团体之间有非常重要的联系,以及对公众意见有重要影响,美国文化外交学者曾要求政府给从业人员学习对象国的语言、熟悉对象国的文学、历史、科学和音乐的机会,同时建议文化外交官应该掌握有关美国的广阔知识,以胜任与别国人们和自己同胞交流美国文化意义的职责需要。(21)
就如文化本身,文化外交也具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美国著名外交史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通过解释文化定义来分析文化外交的表现形式,这种分析值得借鉴。他把文化定义为,“包括记忆、意识形态、感情、生活方式、学术和艺术作品和其他符号”,同时,他认为文化外交是“通过思想和人员的交流、学术合作或者其他达到国家间相互理解的努力,来承担国与国和人民与人民互相联系的各种任务,称为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22) 文化国际主义是文化外交的理论依据之一。依据该理论的理解,世界应该建立在文化秩序而不是建立在权力秩序基础上,因为以政府形式出现的权力无法摆脱那种误解、憎恨和战争的循环,而文化则可以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建立一个更加有序和更为和平的世界。从文化国际主义的定义可以较好地了解文化外交的表现形式,即语言、文学、艺术、意识形态等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以语言教育、文学作品交换、艺术表演、人员交流、科学技术交流、广播电视的文化教育讲座、各种各样的文化作品展览以及为文化教育交流提供的信息服务都是文化关系的内容,同时也可以充当文化外交的形式。著名美中关系学者兰普顿(David Lampton)教授还提出:“美国之音的英语教育栏目和文化产业领域中的交流和合作以及文化产品的贸易,也可算文化外交。”(23) 李智博士认为,文化外交既可以通过国家双边开展文化交流项目的形式,向海外输出本国的文化“产品”(期刊、外文图书、音像资料、文化艺术作品)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鼓励国民在外国从事商业、宗教、教育和其他活动的方式进行。(24) 故广义上理解,文化外交行为主体和表现形式比较多样,内涵也就显得特别丰富。
通过对中外学者就文化外交定义进行辨析,笔者认为,要全面准确定义文化外交,必须包括外交的主体与客体、目标与意义以及手段与途径。那么文化外交可以定义为:是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通过教育文化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为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是外交领域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支柱。
三、文化外交的属性透视
美国著名的文化外交学者弗兰克·宁可维奇(Frank Ninkovich)从目标、动机、组织机构和理念几个方面,对美国新闻署所辖的信息政策(information policy)、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它们的不同是内在的、固有的(inherent),它们向世界显示两个不同的界面(two faces),即文化界面与信息界面。(25) 本文认为宁可维奇所谓文化外交与它们之间区别是内在和固有的论述,实际就是一种对文化外交属性的探究。在宁可维奇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力图深化对此问题的探讨。这些属性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相互性(mutuality)、长期性(long-term orientation)与诚实性(integrity)。
第一,相互性。文化外交犹如一条双向车道(a two-way street),通过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通过学术合作或者其他努力,来促进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而单向(one way)的信息传输本质上并非文化外交行为。美国1961年通过的《教育与文化相互交流法案》(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 of 1961),就文化外交的宗旨和目标,其表述为:“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26) 1975年由全美红字会主席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任主席的“国际信息、教育和文化关系专题研究小组”发布了斯坦顿报告,特别论述了文化外交的相互性问题:“面对我们共同的问题,如果美国领导层选择合作型的解决方式,那么新的文化外交项目必须真正做到对等互惠(reciprocal)。今天,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在教导别人的同时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合作型领导不仅需要有说服力的讲述也需要良好的倾听,在美国文化外交新领导风格需要注重外交双方的对话(dialogue),要将重点放在建立相互理解中的‘相互性’方面(mutual side)”。(27) 正因为这种相互性的存在,使文化外交成为促使人民之间彻底地相互了解,从而推进政府间的相互理解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28) 1963年,美国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顾问委员会对政府执行的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开展成效评估,评估报告总结表明: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这个项目推进了相互理解,有些受访者特别强调项目的相互性和交流的双向效果。(29)
文化外交的相互性首先表现在外交双方都主动参与、互相合作与协作,期望双方通过这种外交形式能够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这一客观要求尤其体现在官方项目中。通常在双方政府的推动下,一个国家的学者、学生、艺术家等在政府资助下到另一国家进行教育文化活动,同样另一国家相对应人员也会到对方进行类似的活动。中国与法国、俄罗斯政府就曾签订协议先后在对方举办“中国文化年”与“法国文化年”、“中国俄罗斯文化年”与“俄罗斯中国文化年”。又如,美国政府开展的富布赖特项目就明确要求合作方与其成立两国双边委员会(Binational Fulbright Commissions)、共同支付项目经费和开展项目管理。
相互性另一种体现是文化外交使者需要肩负双重任务。一方面以自己在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身份到海外执行外交任务;另一方面,获得机会向自己的同胞解释外国的情况。如此一来,大多数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文化外交活动的人都会遇到重新思考自己国家的机会。前富布赖特学者罗诺德·约翰逊(Ronald Johnson)认为:“回国后的富布赖特学者常常更客观看待美国的文化、重新思考美国社会的实质部分……把美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同时要将世界的故事讲给美国听(telling America' s story to the world and telling the world' s story to America)。”(30) 建国之初,新中国就很重视文化外交相互性的原则。1954年7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接受柏林胡包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致答谢辞时说:“我们相信各国人民对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学习将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促进共同的进步”。(31)
但作为文化外交大国,美国在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简称USIA)管理时期就只将美国的故事告诉世界,却做不到将世界的故事告诉美国,严重偏离了文化外交的相互性属性。事实上,在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愈来愈高的今天,一个国家培养学习它国文化的兴趣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人们不仅学会容忍他们的邻居,同时学会理解彼此间的差异,从而有助于相互理解的建立。
第二,长期性。文化外交的使命主要是推动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长期信任,以维护国家长远利益。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外交便是实现这一目的最有效方式。美国前驻也门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威廉·卢夫(William A.Rugh)对此认识很深刻,他说对外交流的开支是我们对未来的投资,数量少,但回报确实巨大的、长期的。(32) 理解文化外交的长期性应包括以下4个方面:一是外交目标的长远性;二是实现目标所运用的手段或者方法具有常规性;三是对文化外交的物质支持具有稳定性;四是国际协议或者国内法规须确保文化外交项目的可持续性。
教育和文化项目需要人们对本国和对象国的文化有一个深刻和全面的了解,需要客观真实地描述和自由平等的对话和互动,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生活和观察(办学校、建医院和图书馆以及留学、讲学)等。它们不能依赖像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所使用的“电台广播”、“心理战”、“宣传片”等手段去实现其长期的外交目标。1904年英国罗兹信托公司(Britain' s Rhodes Trust)设立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向美国青年才俊提供奖学金以推动美国知识精英更深入地了解英国。该项目已运作一个世纪,至今仍是最受美国大学生追捧的海外奖学金之一。20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雅礼协会、哈佛-燕京学社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内地开展了一些有名的文化项目,尽管经历了30年的中断,一旦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项目的组织机构力图迅速恢复与中国的合作。(33) 可以说,历史上成功的文化外交常见于具有长期性的交流项目。而交流项目能够确保长期性与其背后的财力支持分不开。没有稳固的经费保证,任何文化项目只会昙花一现。除了出于纯粹的政治目的,如二战时的文化攻势和冷战期间的文化冷战外,(34) 其他时期文化教育项目都能保持长期性。美国的富布赖特项目、德国的DAAD项目、英国文化委员会项目、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项目都有稳固的政府拨款,而非政府组织开展文化项目也都需要雄厚的财力才能维持。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创办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从1916年筹建到1947年基金会所做的预算(涵盖了后两年的开支)的32年间,共拨款总数为4465.25万美元。(35)
为了保持文化外交活动经常性开展,政府之间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还常常以协议(合同)的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目的、意义、经费来源以及合作的周期等。例如中美两国政府1979年1月签订的政府间文化协议至今近30年,期间几度续签,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中美官方文化外交活动的法律基础。2004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时与美国政府再次续签了该协议。美国先后出台了“富布赖特法案”(1946年)、“史密斯蒙特法案”(1948年)、“富布赖特-海斯法案”(1961年)等法律,确保国会每年拨款支持国际文化教育项目,从而维持美国文化外交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正如1996年美国公共外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坦承那样:相对信息时代的公共外交来说,文化和教育交流所包含的内在的长期价值极为重要。
第三,诚实性。诚实性是文化外交的灵魂,它反映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品质。理想主义者推动文化外交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教育、文化项目的诚实性来取信于双方的人们,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诚实是信任的基础,只有相互信任,才能达到相互理解。罗伯特·塞尔(Robert Thayer)于1959年8月10日在缅因大学发表有关文化外交的演讲时,其标题就是“文化外交:眼见为实”(Cultural Diplomacy:Seeing Is Believing),因此他特别强调通过与一国人民的直接、成功的交流,从而达到对一个国家人们的生活和文化彻底的理解。(36) 文化外交依据直接交流而不是道听途说来传递真实的信息。对口若悬河的文化外交使者,人们不免怀疑其传递信息的诚实性,更希望看到真切的文化交流活动。正如斯坦顿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今天文化外交特别需要诚信(credibility),以便使别国人民相信由美国政府运作的文化外交项目所展示的是美国社会真实和客观的一面。(37)
尽管诚实性是文化外交的基本属性和客观需要,但现实中文化外交的诚实性并没有成为外交主体普遍追求的准则。本文将之归纳为文化外交三大属性之一,是从历史反思与理想追求的维度来探讨,并非现实属性的总结。政府主导的文化外交项目常常伴有明显的政治性和现实目的性,因此不可避免会带有不诚实的一面。20世纪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以文化外交的名义展开全面文化冷战对世人的欺骗,至今在善良的人们心里仍余悸未消。20世纪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西柏林成立“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它的宗旨就是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该组织的文化活动特征是“如果欺骗可以用来推广真理,那么即使使用欺骗也无妨”。(38) 于是不少理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出于对政府组织的不信任,不断要求非政府组织加大对文化外交的参与度。诚实性考验从业者的正义和良知,但现实的功利驱动和政策压力,使得外交使者实难做到这一点。因此,诚实性应成为未来文化外交长期追求的目标。
无论是从实然还是因然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外交的三种属性已经明确了其基本内涵,但在现实运作中,文化外交还是容易与公共外交和文化关系混淆。然而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区别也凸显出文化外交的特征。包括新闻传播、对外宣传在内的公共外交,其重点是向别国公众解释本国政府的政策以实现政府的短期目标,常使用“心理方式”(the psychological approach)、“劝诱”(persuasion)手段,因而公共外交的功利性强,注重价值取向灌输,追求对他国民众全方位、彻底的心理和思想上的控制;而文化外交突出“合作”、“相互理解”和“互惠”(reciprocal),注意对方的需要和期望,注重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来实现促进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致力于长期目标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效应。至于文化外交与文化关系之间,则是文化关系早于文化外交,没有文化外交的国家之间可能会有文化关系,而文化关系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文化外交源于文化关系,但同时又高于文化关系。文化外交具有化解误解、增进互信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战略意图和政治动机,因此文化外交具有“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价值。文化外交客观上要求组织者、实施者从战略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制定政策、实施项目和评估效果。所以文化外交的政治价值高于文化关系,它注重政治导向、政府决策地位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者对政府的服从和协助。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文化外交更加突出政府行为主体在对外文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四、结语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过多关注国家间的权力关系而忽视了国家间的文化关系,这种局面应该随着人们对软实力、文化外交认识的不断提高而改变。正如文化国际主义倡导者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所言:“文化外交研究应该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尤其是全球化程度的提高,文化外交应该是全球化的一部分,NGO以及私人组织都将更加重视对文化外交的介入和投入。我们的学术界要高度重视和加大研究。”(39) 笔者认为,中国学界未来对文化外交的研究应该着重于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外交的理论体系建构,用理论回答文化外交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文化外交行主体为何多元化和影响文化外交开展的关键因素为何等,通过与公共外交、对外宣传、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来进一步定义、定位文化外交;通过研究文化外交与主权国家本身的文化特征、尤其是政治文化特征的紧密关系,讨论文化外交的思想基础和原动力,以此深化对文化多样化、文明对话与共融的理论意义的认识;第二,文化外交的现实意义研究,如文化力量与国际新秩序建构的关系,文化外交在建构和谐世界中的作用,文化外交与意识形态输出和平演变的关系,非政府组织在文化外交的特殊作用,文化外交中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和大众文化(世俗文化)的关系,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国家的文化外交实践特征的研究以及文化外交项目的个案研究等;第三,中国文化外交研究,包括中国文化外交的思想基础与历史经验、中国与大国及周边国家间文化外交的现状与走向、中国文化外交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模式、中国文化外交的战略设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外交项目建设、中国和平发展理论中的文化外交等。
随着现实需要和研究的深化,国际社会可能将进入一个文化外交的竞争环境。但是,对冷战期间文化外交的怀念情节,必须清醒地审视。冷战期间,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开展的文化外交轻视相互性、缺乏诚实性,最终丧失长期性,而沦为文化冷战工具。文化外交的基本属性被扭曲后,其原有正面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今天开展文化外交,应该摒弃冷战期间的手法,固守其本质,即坚持文化项目流向的相互性、政策与目标的长期性、活动内容的诚实性。如此,才能步入文化外交正轨,真正实现通过文化外交达到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让文化外交成为建构和谐世界的一种路径。
注释:
①国内学界的著作主要有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共外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论文主要有李智:《论文化外交对国家国际威望树立的作用》,《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李智:《试论美国的文化外交:软力量的作用》,《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李新华:《美国文化外交浅析》,《形势与政策》,2004年第11期;金元浦:《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及其特点》,《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4期;张清敏:《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外交》,《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杨友孙:《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周永生:《冷战后的日本文化外交》,《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丁兆中:《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胡文涛:《美国早期文化外交机制的建构:过程、动因与启示》,《国际论坛》,2005年第4期;胡文涛:《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等。这些著作和文章既有从理论角度,如传播学、软实力、国际威望、全球化等来探讨文化外交的理论内涵,也有从实践层面,如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文化外交战略与政策、历史演变和机制建构,以及具体项目如美国富布赖特项目、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等,来探讨文化外交的实际内容、实践特征以及现实意义等。
②转引自李廷江:《探索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平野健一郎和他的国际文化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页。
③美国前负责教育与文化代理助理国务卿海林娜·费尹(Helena K.Finn)200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为文化外交辩护:激发外国观众的兴趣》,详见Helena K.Finn," The Case for Cultural Diplomacy:Engaging Foreign Audiences," Foreign Affairs,Vol.82,No.6(November/December,2003);美国学者阿兰·雷丁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重启我们冷战时期的文化外交》,详见Alan Riding," Rerun Our Cold War Cultural Diplomacy," New York Times,Oct 27,2005,E.10。这两篇文章都给与美国文化外交在冷战中的作为以高度评价,同时对美国当前的国际声望深表忧虑,呼吁政府重新重视文化外交的运用。
④以上五篇报告请参看http://www.culturalpolicy.org/,另外该课题组成员还发表两篇有影响的论文:Juliet Antunes Sablosky的论文" Reinvention,Reorganization,Retreat: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at Century' End,1978-1998" ,和Kevin V.Mulcahy的论文"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Exchange Programs:1938-1978" ,发表在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s,and Society,Vol.29,No.1( Spring,1999) .
⑤在香港港美中心主任夏龙(Glenn Shive)博士的引荐下,笔者与该书作者已取得联系,并获得该书部分内容,正在研读。
⑥可参见http://news.163.com/06/0430/02/2FU48JV70001121M.html。
⑦《法国推出新“文化外交”策略》,新华网巴黎2006年5月15日电。
⑧郑园园、刘水明:《文化部长孙家正谈今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人民日报》,2004年12月20日,第七版;孙家正:《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求是》,2004年第24期,第8页;曲力秋:《“别把观念停留在文化就是文化”吴建民解析法国文化观》,《新民周刊》,2004年10月18日等。
⑨Richard T.Arndt,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y Century( Potomac Books,Inc.Washington,D.C.,2006) ,p.1.
⑩Kevin V.Mulcahy,"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Exchange Programs:1938-1978,"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s,and Society,Vol.29,No.1( Spring,1999) ,p.8.
(11)1993美国国会消减文化外交的经费预算的30%,减少外交服务人员30%,减少海外项目20%;1999年美国新闻署(USIA)的撤销是其被打入冷宫的标志。
(12)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3)Kevin V.Mulcahy,"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Int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s,and Society,Vol.29,No.1( Spring,1999) ,p.3.
(14)这个公告并没有直接定义文化外交,但其论述文化外交机构建立的宗旨时隐含了英国对文化外交使命的理解。
(15)J.M.Mitchell,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Boston:Allen & Unwin,1986) ,p.81.这是目前比较早对文化外交进行定义的学术著作。
(16)转引自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共外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17)孟晓驷:《锦上添花:“文化外交”的使命》,《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1日,第7版。
(18)Kevin V.Mulcahy,"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Exchange Programs:1938-1978,"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s,and Society,Vol.29,No.1( Spring,1999) ,p.8.
(19)Oliver Schmidt," Small Atlantic World:U.S.Philanthropy and the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s after 1945," Jessica C.E.Gienow-Hecht and Frank Schumacher eds.,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3) ,p.127.
(20)罗索认为,外交人员对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贡献来自他在两种文化间的诠释技能,他从两个方向运用这种技能:在外国文化背景下为自己的政府解释和评估当前形势与发展态势,同时也为其政府追求在海外的政策目标时充当辩护人。参见Robert Rossow,"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New Diplomacy," World Politics,Vol.14,No.4( July,1962) ,p.565.
(21)Kevin V.Mulcahy,"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Int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s,and Society,Vol.29,No.1( Spring,1999) ,p.5.
(22)Akira Iriye,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Baltimore,Marylan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p.3.
(23)2004年6月29日下午3点笔者到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兰普顿先生时,他对笔者提问的问答。
(24)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25)Frank Ninchovich,U.S.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Headline Series No.308( Ithaca,NY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1996) ,p.3.
(26)PUBLIC LAW,87-256-SEPT.21,1961,p.527,p.527.也可参见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22/usc_sup_01_22_10_33.html。
(27)Pane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Education,and Cultural Relations,1975,p.12.该报告没有公开出版,此件系笔者复印自美国埃默里(Emory University)大学图书馆。
(28)Robert Thayer," Cultural Diplomacy:Seeing is Believing,"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August 10,1959,p.740.
(29)" A Beacon of hope:The Exchange-of-Persons Program:A Report from the U.S.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April,1963,p.16.
(30)Juliet Antunes Sablosky," Reinvention,Reorganization,Retreat: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at Century' End,1978-1998,"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s,and Society,Vol.29,No.1( Spring,1999) ,p.32.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32)William Rugh," If Saddam had been a Fulbright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Vol.87,Issue.237,p.19.
(33)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eng Institute)创立于1928年1月4日,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成立于1901年,两者在1949年前曾致力于在中国开展教育、学术合作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与中国方面的合作关系。洛克菲勒基金会1921年在北京创建了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在中国培养大批精通西医的医学人才,中美关系正常化,迅速与中国恢复了文化交流关系,后来重点是资助中国的农业、生物技术和高等教育等。
(34)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是指在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国之间运用文化交流的手段(即艺术成为准军事资产,文化名流成为宣传工具)来赢得人心与思想(to win heart and mind),它是冷战的重要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冷战国际组织就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策划在西柏林创立的“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该组织被认为是文化北大西洋组织。英国人费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历时八年查阅大量资料,以文献记录的形式写出著名的美国文化冷战史著作,参见Frances Stonor Saunders,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New Press:Distributed by W.W.Norton & Co.,2000) 。
(35)资中筠:《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
(36)Robert Thayer," Cultural Diplomacy:Seeing is Believing,"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August 10,1959,p.740.
(37)Pane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Education,and Cultural Relations,Serial 20155670,1975,p.12.该报告没有公开出版,此件系笔者复印自美国埃默里(Emory University)大学图书馆。
(38)[英]弗兰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05页。
(39)2004年9月23日笔者在哈佛大学历史系采访了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他对笔者问题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