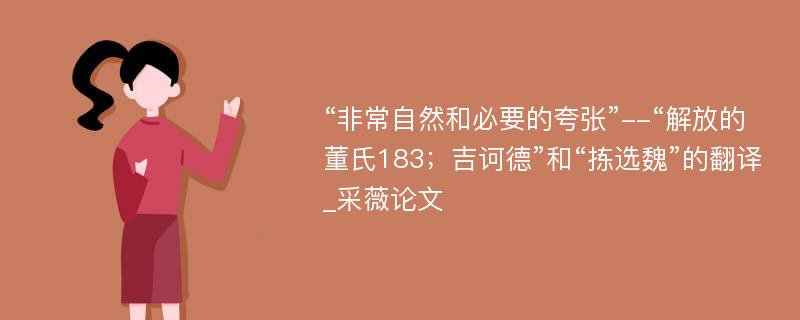
“极自然而必要的夸张”——《解放了的董#183;吉诃德》的翻译与《采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夸张论文,吉诃德论文,采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翻译过程
《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是卢那察尔斯基根据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经典人物和情节所改写的讽喻现实的戏剧作品,1922年在苏联印行。剧本最早在中国由鲁迅翻译,根据德、日译本译成。在《北斗》(1931年11月20日)上发表了第一场。后来因为鲁迅发现了德、日译本的删节问题,又找到了俄文原本。于是由易嘉(瞿秋白)接下来翻译了第三、四场,仍旧发表在《北斗》上。后来《北斗》被禁(1932年7月20日第三四期合刊止)瞿秋白则继续将之翻译完成。1933年10月28日,鲁迅曾经在单行本译出之后,在其出版的后记中谈到这部作品能够完整的翻译,让他“不可以言语形容”的高兴。他说:“和我的旧译颇不同,而且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并且感叹说“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可庆幸的”①。加之,此时,距离卢那察尔斯基病逝不到两个月,他的亲近的“战友”瞿秋白,也在被国民党通缉之中,这部作品的出版,对鲁迅来说可谓弥足珍贵。
鲁迅在这本书的开头介绍了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Vasilievich Lunacharski)的生平。这篇介绍译自日本翻译家尾濑敬止1926年作,原为1930年出版的剧本《浮士德与城》②的作者小传。据说1926年“《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在日本舞台上演,且是“苏联戏剧首次在日本公演”③。通过本序文可以知道,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戏剧作品出自他的《戏曲集》。这部集子中,还有不少根据17世纪的历史题材所改编的戏剧作品④。尾濑敬止指出:
但在这里,有应当注意的事,是他的思想,每系于取现代为中心的中世纪以至辽远的未来的。而那思索的线索,所以常采于中世纪者,就因为他太通晓了意大利和法兰西的缘故。
卢那卡尔斯基寻求着无产者艺术。然而单是描写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的东西,是不行的。必须是更其内面底,悲剧底,而且未来底的,才好。而这样的艺术,则一定是象征底(Symbolic)的东西。……卢那卡尔斯基说,却是在最高限度上的规则底,急进底的。⑤
卢那察尔斯基的这部戏剧集,有一大部分是通过历史,或者古典文献中的人物为范本。这种写作方式是因他熟悉文献的缘故;同时,在作品的思想性上,这位革命艺术家认为这种依照古典形式所造就的“象征性”的作品,可谓是最高限度的激进的典范,是能书写革命的俄罗斯这样“非常哲学底而又象征底的诗的黄金时代”的。
从《浮士德与城》的鲁迅译本序言⑥中可知,一直到后来,中国文坛1930年代对卢那察尔斯基的翻译,更多的是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而对于文学作品,到《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一共也就这么两部。尽管如此,鲁迅认为他的理论和创作之间也构成了“印证”的关系。且这两部剧作都是根据古典文学文献中的典型人物演绎出来的。它们密切地结合作者本人所焦灼的社会政治问题,同时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尽管如此,因为二者分别发表在1916、1922年,所以在前后的思想变化和风格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在鲁迅所选录的序言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
其次是《浮士德与城》,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终在1916年改定,初稿则成于1908年。……于是他试着写历史剧Oliver Cromwell和Thomas Campanella;然后又回到喜剧去,1921年成《宰相和铜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后一种是1916年开手的……⑦
与《浮士德与城》不同,“《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带有喜剧的性质。因为历史剧的尝试之后才写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另外,《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是根据俄文本翻译的。注重文献和原始材料的鲁迅想必十分重视这一点。《浮士德与城》与“《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具有诗剧上的严肃性,而同时“《被解放的堂·吉诃德》”中所延续的创作风格则是喜剧。或许,恰如果戈理的作品那样:《巡按使》、《两个伊凡》以及《死魂灵》。这对晚年鲁迅来说更具有吸引力。最后,在卢氏的所有创作中,鲁迅只亲自动手翻译了“《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的偏重。
有意思的是,鲁迅在《浮士德与城》这部作品的前后序记中,分别采用了尾濑敬止和英译者的评价。尾濑敬止的评价是站在“卢那卡尔斯基”对于象征性悲剧的理解和他的天赋创作上。虽然是写旧的崩坏,但都表明了真正的现实。这种象征性的、悲剧的、有方向性的对于过去的崩坏的告别,也同时是现实中革命的俄国。而英译者则倾向于认为“卢那卡尔斯基”是“复古”的,鲁迅认为这种看法是忽视了“卢那卡尔斯基”所认为的继往开来的前后关系。与“世纪末的颓唐人”相区别的是,“卢那卡尔斯基”的作品有明确的方向,不是落入经验主义的、有列入未来新阶级的倾向。
而卢那察尔斯基是以写作哲学论文起家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哲理性,加之后来的革命经验,他的革命文学作品中包含了某种强烈的思辨性。这点与一直不愿意被单一理论所固封的鲁迅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浮士德与城》与其后来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都选材于经典作品。《浮士德与城》用作者的话说是被“Faust的第二部的长篇所启发出来的”。而通过阅读《堂吉诃德》可知,《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是根据上部第22章——“堂吉诃德释放了一伙倒霉人,正被押送到不愿去的地方去”⑧。只是在此基础上,将人物关系修改,置放到更为贴近当前现实革命反叛的情景下。在人物结构上,有着“恶的深思的外貌”的梅菲斯讬也很像《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中的那个极端恶的化身谟尔却;浮士德的女儿浮士蒂娜的形象也类似像国公的女儿斯德拉。它们都在讲述:过往的历史的遗踪在时间的变革和演进中所发展的角色和他们的命运。初步了解了卢那察尔斯基戏剧的创作脉络,也许能更深一层拎出笔调较为轻松的喜剧作品的质地来。
二、以喜剧传达:吉诃德与伯夷、叔齐兄弟
就《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本身而言,这部作品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讽刺剧。它展现了卢那察尔斯基除了为人所熟知的文艺批评造诣之外精湛的文学修养和语言才能。正如高尔基所说:“作为一位语言艺术家,您能驾驭语言,只要您愿意这样做”⑨。作品仍然是以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两个主人公为主线,但充实在他们周围的显然是一群现代人。这群人大致可以分为“革命者”和“反革命者”。这些在鲁迅所翻译的第一场中也能看到。(相较瞿秋白的接续作品,鲁迅的翻译泼辣、轻熟、简练、有力)为有助于对这部戏剧作品的理解,笔者根据《解放了的董·吉诃德》译本,将内容归纳如下:
第一场:写四个士兵押送三个革命者去行刑,路上碰到了董·吉诃德和他的随从山嘉。董·吉诃德以善和正义的名义在他们当中搅和了一通,放掉了三个革命者,而吉诃德和随从挨了打,驴子也被流浪汉骑走了。另外四个士兵只好打算押送这一对“历史人物”去给国公交差。
第二场:董·吉诃德会见了国公和他的宠男谟尔却,后者嘲笑董·吉诃德的天真可笑,吉诃德则讲述了神的旨意以及他出于对正直和善良的倾慕,保存了三个犯人。于是国公和谟尔却打算:留下来继续玩弄这个“道学家”“傻瓜的圣人”。
第三、四场:黑人亚菲利坚的挑战。吉诃德被打败。后者获得国公善良的侄女斯德拉的同情。吉诃德被逮捕。
第五场:山嘉与狱卒的谈话。董·吉诃德在狱中沉睡做梦。斯德拉提了篮子来看他,给了他吻,使他的情欲复苏。城内发生了骚乱,革命者推翻国公的统治。
第六场:吉诃德与争取平民自由的革命者、工人阶级的代表德里戈的对话。董·吉诃德认为革命者是在以暴制暴。“因为现在你们,你们,你们是强暴的人,而他们是被压迫者了。”
第七场:国公与谟尔却等人被捕。吉诃德接受斯德拉的请求,试图营救国公及其随从。
第八场:国公与谟尔却等人在监狱里寻求逃脱办法的对话。国公企图通过诉说祖辈和自己的罪过来赎回生命,结果遭到了谟尔却和国公夫人的嘲笑。斯德拉与董·吉诃德按照计划来到监狱解救他们,给谟尔却吃了昏死三天的药。
第九场:董·吉诃德、斯德拉、山嘉三人到坟墓去解救。国公诸人被医生救走,把董·吉诃德留在坟墓边。山嘉告发之后带来大兵,结果抓到的只有吉诃德。
尾声:谟尔却的荒淫和暴政,连同斯德拉也成了他的玩弄对象和牺牲品。吉诃德和革命领袖的对话、告别。山嘉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随从本分,跟从吉诃德而去。
从革命者的被捕到董·吉诃德的出现,显然有一种穿越历史的镜面,其中对话幽默风趣,行文亦符合经典中的人物性格。读来并不感到突兀,反而具有某种合乎情理的现代性质。
众所周知,鲁迅当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因为对革命文学性质冷静深邃的批判把握,被李初梨称之为“中国文坛上的老骑士”,对他的“无视斗争的重要性及其实践性”的“人道主义”进行讥讽⑩,这些都多少使人想起《解放了的董·吉诃德》里面栩栩如生的情节。
1928年4月,鲁迅在《语丝》上公开发表给一个受其文字的“革命性”影响甚深的青年的信中就说:
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11)
并且,他指出,很多的“革命者”“问目的不问手段”,这是许多人用来谋生的口实,他说:“苏俄的学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尔斯基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里,将这手段使一个公爵使用,可见也是贵族的东西,堂皇冠冕。”(12)这封信写得极为真诚,像是在剖析自己的文字之路如何与社会政治的革命发生关系,从政治的意义上,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革命的流血牺牲是他所不忍的;再次,就是对于自身,他认为应该走渐进的“顺手的改革”、“无论大小”的道路,然这条道路要建立在自我谋生的基础之上;最后,他告诫这位青年,那些“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之类的界定,多半基于文字,文字是不可靠的。
一方面不认为自己是政治上的革命家,另一方面,国民进步的内在渴求,又要求鲁迅主张在文人谋生的基础上“顺手的改革”,这都说明了鲁迅对于身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警惕和敏感。
两个月后,新出版的《奔流》第一卷第一期第一篇文章即发表了郁达夫从德语译的屠格涅夫(I.Turgenjew)的《Hamlet和Don Quichotte》。该文从作品出发,十分细腻地比读了两大世界文学人物身上人性的和哲学的层面,很显然,作者对堂吉诃德身上“轻快明朗,质朴而多感”的人性成分也给予了赞扬(13)。这些都或可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当时所身置的“堂吉诃德”文学接受氛围。
1929年鲁迅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批评(14)时,似乎更加深化了这一思考,他开始将目光投射到作者似乎有所揶揄的吉诃德身上:
那么,在也可以看作这演说的戏曲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里,作者虽在揶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吉诃德老爷,却决不怀着恶意的。作者以可怜的人道主义的侠客堂·吉诃德为革命的魔障,然而并不想杀了他来祭革命的军旗。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卢那卡尔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宽大。(15)
鲁迅在本刊编校后记中说,中国尚未有完整的《堂吉诃德》的翻译,而对于书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含义也是道听途说。在屠格涅夫的观念里,“堂吉诃德”是“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他与“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Hamlet相对照。他说,“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什么‘Don Quixote’了,但因为实在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16)。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之对于国人舶来西方文学概念而不加认真阅读理解的厌恶。也算是对两个月前的“有人”的回应。
而鲁迅之支持瞿秋白翻译这个剧本,是同情堂吉诃德还是通过对“堂吉诃德”的批判实现对自身的反省?或二者兼而有之?在1928年4月与李初梨《文化批判》同期发表的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则从“奥伏赫变”(Aufheben)辞义的追溯讥讽鲁迅在革命理论上的“无知”。这篇文章论证充足,想必对鲁迅有所触动。即便当时的中国并非一定有“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般革命的民众也在急迫的要求”(17)的革命情势,也会使鲁迅对自己一直以来的革命理论的无视表示自省,这大约也是后来鲁迅逐渐开始系统翻译革命文学理论著作的重要原因。
对于鲁迅的“革命文学”论争到1930年代以左联为核心所展开的论争的前后变化,一直是研究者热爱讨论的问题。很显然,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的观点与后期他的反对派有某种相似之处。鲁迅的思想变动也并非随意趋时,他必须对其有拣择和消化,这种态度决定于他的独立精神以及与外界一直从未隔绝的开放态度。这两个时期,他都有一个底线,那就是文学作品的品质。前期是批判革命文学的不“文学”;后期则是批判革命文学的不“革命”,这些,都基于他对文学随着时代变化所给予的质疑和修缮。
鲁迅是知道当时的欧洲作家是如何非难苏联的。在翻译作品的后记中他说道:
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Merzhkovsky),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Einstein)。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18)
接着鲁迅历数“革命者”罪行的新闻和言论,指出他们和董·吉诃德似的文人十分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正是“谟尔却”之流的体现。也就是说,鲁迅在得知这种非难的情形之下,还是坚信苏联的革命的正确性。这剧本,用鲁迅的话说,是针对当时的知识阶级对于苏联的“专制压迫”不满引发的。鲁迅认为“董·吉诃德”似的知识分子,一开始赞成正义的革命,为之作出牺牲,后来当革命者夺得政权之后,他又认为是一种变相的压迫,丝毫无差,这是一种保守,温和的人道主义立场。在《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第九场中董·吉诃德的梦境恰体现了这种思考:
我那次做梦,仿佛我在红云堆里,站在一个光华耀眼的审判官眼前。雷声轰隆轰隆的响着,那人的威严的声音给我讲着:“你敢自己以为是正直的吗?你没有了解你的时代责任,你那种腐败的正直——他正是这样说的,——你那种腐败的正直,只会产生死灭——正是当代伟大的幸福的创造者的死灭。”
鲁迅这篇翻译后记写于1933年10月,恰可以看出与1928年前后的态度变化。1928年1月,在他对于十多年来的政治生活极其警惕的境地之下,他的那篇鞭辟入里的演讲稿《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就曾经对“人道主义”境地下的托尔斯泰表示理解和同情,他认为文艺家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永远要求变革和进步,因而也往往处于被政治当局和革命者利用和压制的处境之中。这篇文章更多地采用自身多年的所见所体验,加之裹入论争的漩涡,思想可谓沉重。
然而,尽管有如此的前后变化,鲁迅仍认为董·吉诃德的抱打不平是合理的。但是,他的手段不行,而且那些旁观者的嘲讽也是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革命者给予吉诃德的也是同情和拥抱。在《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中亦能发现作品对于这种态度上的纠结。第六场中吉诃德对争取平民自由的革命者德里戈说:
我赞成你们,也反对你们,我是不是拥护国公和他的专制呢?我是不是认为富人的统治是老天爷决定的,是不能够动摇的呢?假使这种坏的秩序,值得肃清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地球,也的确要肃清一下,因此要推翻这种秩序,那么,我自然只会高兴;可是,有一个条件,即是这种秩序不要推翻到了地狱里去,而要把它的地位让给天堂。(19)
结尾处“先进阶级”的革命者与董·吉诃德的对话:
巴勒塔萨:唉,董·吉诃德,你不够做饥荒的流血的共和国的国民;这种共和国的领导者,要求民众的怒潮无论怎样也要得到胜利,他们要领导着民众,经过赤尔谟海,经过大沙漠,经过残酷的战斗,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可是,等到我们到了目的地,我们就要脱掉染着血腥的盔甲,那时候,我们来叫你,可怜的董·吉诃德,那时候我们给你说:走进我们争得的蓬帐里来罢,来帮助我们的建设。那时候,你胸口呼吸起来要多么舒畅;四周围的情形,叫你看起来,又是多么自然呵。噢咿,那时候,你才是真正解放的董·吉诃德。可是,那时候,你想必还要皱着眉头,记起经过的事情,记起许多恐怖的事实,虽则这种事实,你是没有经过的。唉,你不能够了解我们是在出着代价——不出这种代价是不能够跑进那样世界的,而只有那样的世界里,真正解放的董·吉诃德才可以找着和谐和光明。
吉诃德:我是这样想的:他们跑进了伟大的事业的海洋里去游泳了。那是很容易迷路的,很容易使自己和别人都在痛苦里面沉醉着,因为我知道:就是做着好事,最直接的好事,人也会种下极大的恶的种子。你们的信仰,和我的是不同,可是我们人本来又能够做什么呢?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真正成了瞎子了。(20)
吉诃德:不要,我走好了。我不能够答应你说:我明天就一定不把你们的牺牲品藏在我的床底下。而我又怎么能够知道,这不是第二个谟尔却呢?(21)
到这里,作品将革命者和吉诃德的真诚思想都鲜明地表述出来了。并且,对于吉诃德而言,许多革命流血的事实是他所“没有经过的”。这种被平民的自由的革命者所指摘的特点,恰能够返照鲁迅对于革命的态度来。首先,他曾经不无无奈地自我界定为作为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向往革命和时代的进步又是他所期许的。在以上二者的对话之中,也许能够找到鲁迅对于自身经验的反省和对于革命者的同情和理解。这种真诚的文学描述给鲁迅带来的不仅是经典重读的审美愉悦,也许更多的是个中的思想的冲击。用他自己1933年的话说,是“又滑稽,又深刻”(22)。
再从这翻译去观察鲁迅的作品,我们很容易想到卢那察尔斯基戏仿的堂吉诃德,与鲁迅1935年12月所戏仿的伯夷、叔齐,以及他们同样悲惨的命运,似乎有着某种奇妙的关系。
在经历了从1928年以来的革命文学论战之后,鲁迅不断地裹挟在文人的论争之中,同时,他不忘记做自我的思考和剖析。到了1935年末,鲁迅在着力翻译俄国讽刺文学的同时,又联接着自己的命运和苏联文学中这个带有现代意味的文学典型——堂吉诃德。对他来说,《采薇》可谓是这许多年来对于自己和他者的批判所引发的外界反应的一个清算。这场清算,甚至没有让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任何一个参与历史的现代人逃脱。
大致说来,堂吉诃德和伯夷、叔齐二兄弟,在文学作品中,都表现出了一种纯粹者在历史现实面前的困境和遭遇。这种悲剧引起人们的同情、悲悯,也给人们带来了思考。章太炎在1925年考察这二位历史人物,将其作为“自释迦以前,未有过于”(23)的强大的民族自立的模范,鲁迅在处理对于伯夷、叔齐的情感之时,也带有十分复杂的意味。无论是堂吉诃德式的被驱逐的“人道主义”者,还是如他们这二位没落的贵族伦理的坚守者,都内蕴着对于自性的思考。
鲁迅在《采薇》中并没有就此指证伯夷、叔齐二兄弟为失败者,周王朝才是合理的王朝。对此,鲁迅曾在1934年3月他的杂文中很尖刻地看出了新王朝与旧王朝之间绝然对立的理论破绽来,他说: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们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24)
虽然吉诃德和山嘉并没有死掉,只是离开,但仍然摆脱不了伯夷、叔齐二兄弟般悲剧的命运。他们的无用和死亡,带来了腐朽的贵族道德的悲剧的力量。与《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一样,两部发源于古典题材的现代作品共同构筑了讽刺文学中的某种特色:在具象中超越,实现多重意义;从历史之中开脱,走向本质的荒芜。如果作品仅止于对革命家的讴歌或者僵化儒学的讽刺,都难以解开作品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面纱。在这一点上,《采薇》和《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一样,表现出了文学对于具体世俗意义该有的大度和宽容。
三、敞开的结尾
在这里稍微追溯一下堂吉诃德在鲁迅的文学视野中的作用。我们也可以通过钱理群勾勒式的作品《丰富的痛苦》看到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在欧洲的传播和东渐。通过近代日本大量书籍的译介传播,鲁迅曾经得到过德语译作以及他所青睐的翻译家、评论家片上伸等人的日语译本乃至插图单印本(25)。这都显示了鲁迅一直以来对于堂吉诃德这个人物的偏爱。周作人自1917年4月任教北大时所编《欧洲文学史》讲稿,据说鲁迅就曾为其修改过。或可见其对堂吉诃德的评价:
Cervantes故以此书为刺,即示人以旧思想难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不啻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世俗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26)
钱理群还谈到了鲁迅在和瞿秋白翻译《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时候的评析和态度。他认为鲁迅之强调董·吉诃德的人道主义态度的软弱性恰是特定时代的要求。
而鲁迅的《采薇》中,武王伐纣,这样一个“其命维新”的历史事件给了一向反对武力、希望依靠仁政的二兄弟以沉重的打击。
桑丘朋友,你该知道,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我恢复金子的时代,一般人所谓黄金时代。各种奇事险遇、丰功伟绩,都是特地留给我的。(《堂吉诃德》)(27)
在百静中,不提防叔齐却拖着伯夷直扑上去,钻过几个马头,拉住了周王的马嚼子,直着脖子嚷起来道:“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采薇》)(28)
于是他们也像是那个传说中的堂吉诃德和他的随从桑丘一样,开始了漫游的生活。在这其中,他们遇见了各色人。在时代的变化面前,二位虽然非常敏感,但还是对新的变革充满了恐惧和怀疑。正如堂吉诃德一样,他们依靠一种似乎亘古不变的伦理来践行他们的残生。于是,这也注定了二兄弟的悲剧人生。鲁迅的这一戏仿精神与卢那察尔斯基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并没有像卢那察尔斯基一样,给他们太多的言行。这言行包括大量的说理和宗教虔诚,以及武力上的征服,而是两个可怜巴巴的手无缚鸡之力,胃口不好、怕冷的,已经住在养老堂里饱食终日却为伦理所迫的老汉。在漫游中,现实和历史,逐渐把他们两个视信仰如同性命的人逼到了死角。更其显示出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悲凉感来。鲁迅在《采薇》中也借用昏昏噩噩的御用文人小丙君的嘲讽,来写二兄弟的“过错”:二兄弟为信仰殉难之后,首阳村的人们开始请有“文化”的小丙君来写墓碑,遭到小丙君的拒绝:
“他们不配我来写”,他说。“都是昏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
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你瞧,这是什么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我不写!……”(《采薇》)(29)
正如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结尾,董·吉诃德并没有屈服于革命者的言论而是选择了离开一样,《采薇》也有着这样因信念而决绝,从而让人读来伤心甚至感动的结尾。尽管这暗喻了一种悲剧,但是这种悲剧的力量,似乎给了作品一种敞开的结尾。到底是谁胜利了?革命或维新后的时代是走向了“好的秩序”还是走进了“地狱”?
19世纪俄国很多大作家都注意到了堂吉诃德这一文学形象的不朽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引介和评价方面包括普希金、别林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等等。高尔基称堂吉诃德是“真实事实的极自然而必要的夸张”。(30)而卢那察尔斯基本人曾经在《西欧文学史》(31)中讲述过他对于堂吉诃德的看法也许能够多少说明这个典型在文学境遇上深意:
……西万提斯,具有异常高贵性格的一个人,实在地,他本身就是一位唐吉诃德,他认为一个人必须能为人类牺牲自己才当得起人的名称,他是他那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最好代表之一,表现着种种反抗精神与脱出那没有公理正义的恶势力怀抱中的挣扎,但是这爱自由与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匍匐在旧时代的理想前,他赞赏它,他想去仿效它,他希望这是皆能成为唐吉诃德脑中所想像的那样,不幸得很,世界压根儿就不是那样。西万提斯同情他小说中的账房老板及商店掌柜吗?绝对不会的,很明显的,在他看来,现实的世界是充满了愚蠢,欺骗及狂暴的,将唐吉诃德和以那样残酷的愚蠢的态度来嘲弄讥笑他的充满了丑儒弄臣的公廷来相较,他显得多么无限的高贵呀!(32)
……在这种世界内那看来是可笑的,被蛮荒的法律所统治着的这个世界内是没有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余地的。……唐吉诃德和桑曹潘撤必须继续在这世界内窒息着,直到开始将社会主义付诸实行的时候。当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许多热心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堂吉诃德们,梦想家们都可以得到机会将他们的英雄浪漫主义用于革命工作上;他们将不再是幻想的骑士,而将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正有用的劳动者……(33)
卢那察尔斯基显然认为堂吉诃德代表了旧的阶级(资产阶级),他们的那一套令人赞赏的伦理和道德标准不适应于当前的时代需要。即便是如此,他们仍然与那些嘲笑他的人相比显得“无限的高贵”,卢那察尔斯基给被时代中的堂吉诃德的建议则是,将这种“英雄浪漫主义”用于革命,当社会主义付诸实现的时候,这些奇思妙想将不再是空想,反有利于“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正有用的劳动者”。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一看法似乎也和他所创作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在对堂吉诃德的态度上构成了思想上的某种互文关系。
四、反封建还是反虚伪:阿金与《采薇》
从1931年11月开始登载,一直到1933年10月写完后记为止,《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翻译,一共历时两年左右的时间。想必鲁迅也像是为其他的左翼小说如《铁流》、《毁灭》一样,为此剧作耗去不少的心力。而这一项庞大的左翼文学的翻译事业,不能不说对鲁迅最后看起来十分微薄的小说创作——《故事新编》,在文体乃至思想内核上产生或多或少的创作上的共鸣。
同时,在这两年当中,鲁迅曾发表一篇杂文《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櫬”,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34)
以堂吉诃德为主题,直接批判当时,申明中国只有一些半途而废、沦落变质乃至虚假的堂吉诃德。仔细理解《采薇》中的深意,大概可以看到这篇杂文可算是这篇小说的注脚之一。鲁迅讽刺胡适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不具备像堂吉诃德那样的理想主义色调的战斗品质的所谓“中庸主义”者。鲁迅之对于胡适也始终并非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对一些虚伪、做作,表面柔和而实际上不下关键性判断与作为的抨击。在这种急迫性中,对外界敏感、责任感深厚的鲁迅自然会以自己作为一个文学者的职责来约束和要求自己。在这个方面,鲁迅似乎比1930年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深刻痛苦地把握着。
而我们在当时的左翼文艺批评家胡风身上看到的是另一番解释,据他晚年回忆,为“悼念”瞿秋白而作的对于《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批评,其中区分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和董·吉诃德“糊涂的人道主义”(35),这篇文章便是1934年7月15日发表在《中华日报·星期专论》上的《董·吉诃德的解放》。这篇文章十分鲜明地指出了革命的紧迫性,认为伟大的不是“良心”,而是“‘良心’世界的实现的行动”,知识分子必须“为着自由的王国”“与大众合流”,“得到最高的融合”。很显然,胡风在明晰的论述线条之中,站在代表着“大众”和“斗争力”的革命的工人阶级一边(36)。作为一篇纪念文章,胡风似乎另有深意。这种建设意义上的解释,即对于堂吉诃德这样一个人物经过人道主义而进入无产阶级的合流之中,显然与1933年的鲁迅在译作后记中说的类似,然而鲁迅并没有继续推进、建设,使之成为一个阶级的文学参照,这应该是他和当时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如胡风)间的差异。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中这样写道:
尽管堂吉诃德本人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甚至有几分虔诚;作者的叙述语调还算平静,但读者却能感觉到一种调侃、戏谑的味道。就在这或严肃或平淡或戏谑的模仿中,骑士小说自身的荒诞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都暴露无余、不攻自破了。(37)
这一看法,似乎也直可印照鲁迅关于《采薇》中这对拿儒家贵族伦理武装的“真吉诃德”兄弟漫游作品的文学机理。塞万提斯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曾经试图让堂吉诃德和他的忠实随从奔到中国这个古老而遥远的国家(38),虽然没能达成心愿,但是却由卢那察尔斯基将他们置身于革命氛围浓郁的俄罗斯的土地上,他严格地按照两人的人格逻辑将故事铺展开来,好像是《堂吉诃德》本身的续作一般。虽然中国的革命文学家们并没有将这一典型嫁接到本国的文学环境之中,然而,鲁迅对中国贵族文化典型的深刻把握应该是从卢那察尔斯基的这部作品中找到的某种启示和共鸣。
谈及贵族文化典型,在1930年代以降的人文语境里,它和人们对于“封建”的看法总是密不可分。竹内实在《阿金考》中结合鲁迅晚期杂文《阿金》(1935年3月),以及《采薇》中的阿金形象,认为鲁迅语言中的这个“阿金”是发生了变化的。《采薇》中的阿金是从“鲁迅最讨厌”《阿金》到后来的“给予了肯定的、带有反封建色彩的阿金”。(39)因为,阿金在小说《采薇》之中起到了直接促使他们死亡,以及在他们死后散播吃鹿肉而死的谣言的作用。竹内实的这种论述,前提是伯夷、叔齐兄弟首先是革命思想的反面,即所谓“封建”。
《采薇》中食鹿肉的片段并非鲁迅全部杜撰,典故出于刘向《列士传》:
时有王糜子往难之,曰:“虽不食我周粟,而食我周木,何也?”伯夷兄弟遂绝食。七日,天遣白鹿乳之。经由数日,叔齐腹中私曰:“得此鹿完啖之,岂不快哉!”于是鹿知其心,不复来下。伯夷兄弟俱饿死也。(40)
鲁迅对此种说法作了修改,在小说中将之放置在阿金这个他晚年专门撰文将其漫画化(41)的文学人物的传言身教上,可见鲁迅对伯夷、叔齐二兄弟的态度。因此,很难说,阿金是完全带有肯定色彩的角色。竹内实将这个问题简单化的根源,应是他太想坐实《故事新编》和左翼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了。
顺便提及,在尼采的作品《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就曾经描述过二王逃离自己的国家到旷野的细节,逃离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自己的国家“那里的一切(“礼仪”,“好社会”,“高贵”——笔者加)虚伪而腐烂”(42),“一切都是污秽的闯入的狗,他们镀饰了棕叶”。(43)与《采薇》中的二兄弟相比,前者不过是用逃离而反其腐朽,后者不过是用腐朽的固执而反其崩坏罢了。二者其实都在着眼于至纯的道德。
五、余论
至于1935年末创作这部作品时,鲁迅到底想要表达些什么,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我们只能够从以上的脉络中找到些微的联系。但从其自身的境遇和对于整个国家急迫性的危机之中,可以看到他或者一反1928年前后革命文学论战时期的不信任不合作,而抱着一种与“群众”(44)合流的殷切愿望。
就这两部作品而言,它们都将一个纯粹的个体放入复杂的现代环境之中,遭受非议与磨难,体会更多的存在意义上的困境。相较于卢那察尔斯基,鲁迅似乎在文本中更多面对的是主人公生存或生活的困境,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他和作为文学者和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卢那察尔斯基之间的一个分疏:有意无意地淡化后者所倚重的意识形态上的评判与建设。
鲁迅对卢那察尔斯基充满好感的原因,很可能是后者的文字并无僵化之感。卢那察尔斯基将自己的生命、文化体验投注到对于理想社会的希冀之上,因而其文学的范本也是多层次的。作为一个敏锐的文学者,鲁迅对于异国苏联的想象应该首先在于它的文学世界。当然,归根结底,应该是基于他自身对于国民改革的必要性的认知基础之上,他通过这种内在的驱力去寻求范本和动力,然后通过信任好友瞿秋白及其翻译的文学与理论世界,来信任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及其政体的世界。
但对于己国,鲁迅的文字里似乎有一种更坚决的东西,忍不住让其死灭,并赋予其一种在世俗批判中的无意义。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中,卢那察尔斯基则将堂吉诃德剔除到了对立的阶级社会群体之外,而鲁迅让兄弟二人死于各阶层的喧闹之中,不给出路。这一方面是文学历史典型的内涵所成;另一方面,这个结尾别具匠心,正如《理水》的结尾让大禹走向了日常的君主做派,他比卢那察尔斯基更为亲近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后者着力于思想的论辩和观念的清理,一面,总是将虚假的理想之路、完美之境扼杀,另一面,却又同样显示着宽大的同情之心。
1928年到1934年鲁迅对堂吉诃德看法的前后变化,说明了他对“群众”的洪流本身从未看作是一种理想的手段抑或状态,而是对其保有足够的警惕和距离感。而《采薇》正是在此历练的基础之上清醒的世象的描绘图景。
然而,当这种“群众”的洪流成为一种希望的幻象之后,鲁迅眼前所见的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仅看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虚伪和投机,而且对此加以抨击和嘲讽,反而因此,对那些旧道德的追殉者(人道主义、封建结构)给予了尊敬和同情。他常这样反诘:你们虚伪投机成那样,还配谈别的?他要他们揭掉自身的面具,爽然登上他的解剖台。他许多文字的基调都是这样,即不去描写将来的“黄金世界”,而是钟情于目下渐进的可能的“改造”。
作为文学家,鲁迅和卢那察尔斯基都面临政治世界的干扰,但是他们在处理文学问题时,自觉地践行其文学者身份(或者文学形式),这促使他们走向除政治视野之外的另一面(或者更广大的一面)。身处复杂的文化环境中,鲁迅在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面前,深刻认识到以上两种典型身上的尴尬;但是一进入到文学世界,他又把这种角色的力量放大,竭力地铺染他们的生活和语言。在文学和政治乃至道德的多重“真”与“力”的要求之下,《采薇》表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嘲讽、揶揄、同情等复杂的感受。也许正是在这种复杂性书写上,《采薇》与《被解放的堂·吉诃德》一起,折射出了各自作者所属的国家复杂而交错的时代中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
注释:
①鲁迅:《后记》,[苏]卢那察尔斯基著、易嘉(瞿秋白)译:《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上海联华书局1934年版,第160-163页。
②(44)[苏]卢那察尔斯基著、柔石译:《浮士德与城》,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1930年9月。
③[苏]卢那察尔斯基著、郭家申译:《艺术及其最新形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05页。
④如《王的理发师》,是“用十七世纪封建时代的一个王叫作克柳惠尔来做主角的七幕诗剧”。[日]尾濑敬止:《〈浮士德与城〉作者小传》,见《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第430页。
⑤[日]尾濑敬止:《〈浮士德与城〉作者小传》,《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431、433页。
⑥“Lunacharski的文字,在中国,翻译要算比较地多的了。《艺术论》(并包括《实证美学的基础》大江书铺版)之外,有《艺术的社会的基础》(雪峰,水沫书店版)有《文艺与批评》(鲁迅译,水沫书店版)有《霍善斯坦因论》(鲁迅译,光华书局版)其中所说,可作含在这《浮士德与城》里的思想的印证之处。”鲁迅:《后记》,卢那卡尔斯基著、柔石译:《浮士德与城》,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231页。
⑦鲁迅:《后记》,卢那卡尔斯基:《浮士德与城》,柔石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228页。
⑧(27)[西]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144页。
⑨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论文学》《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32页。
⑩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武器的艺术’也就成为变成Don鲁迅醉眼朦胧中的敌人了”。《文化批判》,1928年4月,第4号。
(11)(12)在1928年4月《语丝》刊物上发表的《通信》(并Y来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98、100页。
(13)《Hamlet和Don Quichotte》:“我们想到‘堂克蓄德’这几个字的时候,只会想到一位滑稽家的身上去——‘堂克蓄德’当成普通名词Don-Quichotterie用的时候,我们只作‘荒唐愚钝’的意思解释,殊不知真正的意思,我们却应该当作一个高尚的自己牺牲的象征(Ein Symbol hochere Selbstaufopferung)”。《奔流》第1卷第1期(1928年6月20日),第2-3页。
(14)卢那察尔斯基:《托尔斯泰与马克思》,《文艺与批评》,《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
(15)《〈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1929年10月1日),《鲁迅全集》第10卷,第301页。
(16)(17)《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一)》,《鲁迅全集》第7卷,第157-158页。
(18)(19)(20)(21)《译后记》,卢那察尔斯基著、易嘉(瞿秋白)译:《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上海联华书局1934年版,第160-161、98、152、153页。
(22)《〈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鲁迅全集》第7卷,第460页。
(23)章太炎:《文录续编》卷一,《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24)《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10页。
(25)1908年,鲁迅购于东京日本桥的丸善书店。从德国邮寄过来的文学书籍,即德国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的《堂吉诃德》德译本(64开平装本)。鲁迅一直珍藏着这个版本。而且二、三十年代还搜集了日本岛村抱月、片上伸合译,大正四年东京植株书院再版的《堂吉诃德》精装本(二册),以及法国著名画家陀莱的插图单印本《机敏高贵的曼却人堂吉诃德生平事迹画集》(共120幅,1925年德国慕尼黑约瑟夫·米勒出版社出版)并且同时收藏了塞万提斯另一部长篇小说《埃斯特拉马杜拉的嫉妒的卡里扎莱斯》。姚锡佩:《周氏兄弟的堂吉诃德观:源流及变异——关于理想和人道的思考之一》,《鲁迅研究资料》第2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325页。
(26)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28页。
(28)(29)《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第397、411页。
(30)(32)(33)李嘉译述:《俄国作家论莎士比亚及西万提斯》,《文学月报》,第3卷,第2、3合期(1941年12月10日),第100、99、100页。
(31)发表时间当为十月革命之后,写作《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之前。根据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论文学·译后记》:“十月革命胜利……列宁立即任命卢那察尔斯基为人民委员会所属十二个部门之中的教育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部长)……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个重要岗位上连续战斗了十二年,……此外又亲自在高等院校讲授本国和西欧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630页。
(34)《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53页。
(35)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36)胡风:《堂吉诃德的解放》,《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6页。
(37)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的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38)《献辞》:“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个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西]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9)(40)孟广来、韩日新编:《〈故事新编〉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43-544、105页。
(41)据鲁迅本人说,《阿金》本是写给《漫画生活》的。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213页。
(42)(43)尼采著、楚图南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306页。
标签:采薇论文; 堂吉诃德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塞万提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