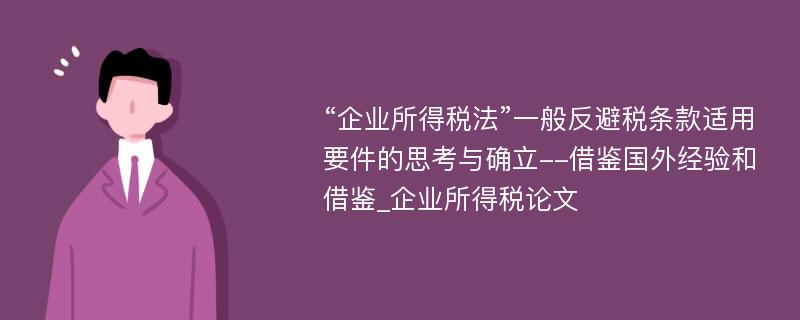
《企业所得税法》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要件的审思与确立——基于国外的经验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件论文,所得税法论文,条款论文,国外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4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5.17
文章编号:1001-2397(2012)05-0162-10
近年以来,各种形式的避税行为在我国层出不穷,引起了巨额的税收流失。以2005年为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全国税务机关对70家外资企业进行反避税调查,调整的税款高达4亿元人民币[1]。为应对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的避税活动,200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专章对特别纳税调整予以规定,除具体规定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等特别反避税条款外,其第47条引入了“一般反避税条款”,为税务机关遏制税法尚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新型避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尽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以及随后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第10章对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具体适用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却并未对其中诸如“合理商业目的”、“实质”、“形式”等基本概念予以明确,导致该条款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极大的随意性。为此,本文对一般反避税条款在适用中所存在的模糊与争议予以剖析,并探求其应对的方法。
一、《企业所得税法》一般反避税制度的规则冲突
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的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加以调整。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规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93条的规定,若企业存在滥用税收优惠、滥用税收协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利用避税港避税以及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税务机关可以依据上述规定对其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审核企业是否存在避税安排,并要求税务机关考虑安排的形式和实质、安排订立的时间和执行期间、安排实现的方式、安排各个步骤或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安排涉及各方财务状况的变化以及安排的税收结果等因素。
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引入对我国反避税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它避免了以特殊反避税条款应对形式多样的避税行为所造成的税法的庞杂性,有利于实现税法的简化[2];另一方面,作为认定避税行为的一般标准,能够有效地避免因税法的滞后而对新型避税行为应对不能的困境,增加了税务机关应对全新避税行为的可能性,并以此作为协调各个特别反避税条款的法律基础。与其他采用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国家①一样,由于采用模糊的、统一的标准认定一项行为是否构成避税行为,一般反避税条款的适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不仅如此,我国对于一般反避税条款的规定更存在其独有的问题。
一般反避税条款以概括方式抽象出对所有避税安排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定,力图通过要件的描述,涵盖违反立法意图的所有税收规避行为。因此,一般反避税条款采用更为抽象和模糊的用语,以保证其条文的包容性与涵盖性,如“合理商业目的”、“实质重于形式”等。这种模糊的用语固然增加了条文适用的灵活性,但税法的可预测性与确定性也随之大为削弱,使得税务机关获得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以此为法律基础判断是否存在避税交易,导致纳税人无法从税法的规定直接判定其从事的经济交易是否构成避税行为。这种状况在当前高度简化的立法模式下更趋恶化。除《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的规定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共有7个法律条文对一般反避税调查的启动、认定标准、考虑因素、法律后果、实施程序作出规定。规则简化的结果必然是:高度抽象与概括的一般反避税条款仍无法获得配套法规的支撑,何谓“商业目的”、如何判定是否“合理”、是否构成“主要目的”、如何认定“经济实质”等问题,在相应的配套规则中均无明晰的规定。含糊的用语无法以具体规则的形式获得更为确定的内含与外延,更无法提高其可操作性。
当前立法更大的问题在于,一般反避税条款及其配套规定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之处。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的规定,企业实施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所得额的,为避税安排。因此,只有造成“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后果的交易,才能被认定为避税安排。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那么,一项以“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的交易,如果并未造成减少应纳税所得额的后果,是否为避税交易的问题,则显然会存在争议。再如,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93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应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审查企业是否存在避税安排,然而,第95条则要求纳税人就其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承担举证责任,而交易是否存在经济实质、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是否一致,则由税务机关予以确认,纳税人并无权予以证明。这便可能产生纳税人即使可以证明其合理商业目的的存在,仍可能由于税务机关对其经济实质的认定而构成避税交易。
一项避税安排的一般构成要件在当前的立法中同样是不清晰的。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的规定,如果一项安排“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则税务机关就可以进行调整。依照这一规定,是否存在合理商业目的是认定避税行为的基本要件,只要满足这一要件,税务机关可以作相应的调整。然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93条则规定,税务机关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审核是否存在避税安排,根据这一规定,“经济实质”将决定一项交易是否构成避税安排。那么,对于“合理商业目的标准”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而言,何者将确定一项避税安排的存在?两者同属一个标准或是两个独立的标准?答案并不明确。从法律位阶上看,“合理商业目的标准”由全国人大所制定的《企业所得税法》予以规定,其法律位阶明显高于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也明确规定,该办法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而制定。②那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似乎应当是“合理商业目的标准”的内含要件,是判断是否存在合理商业目的的标准,是“合理商业目的标准”的下位概念。如果单纯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即可以认定避税安排,显然违背了“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基本法理。如果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一项交易只要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无论是否存在经济实质或发生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的背离,都应当构成避税安排,即“商业目的”的存在将最终决定一项交易的属性及其税收负担。然而,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92条的规定,实质上却将“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作为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的前提要件,而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作为审查交易是否为避税安排的核心标准。同时,根据该办法第75条的规定,企业与关联企业所签署的成本分摊协议自行分摊的成本不得税前扣除,其要件之一为“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如果按照上述规定,似乎可以认为“经济实质”与“商业目的”应当是分别予以认定的两个标准,两者并不存在相互包含的关系。这意味着必须独立判断一项交易是否存在商业目的或经济实质。那么,所产生的问题在于,一项不具有商业目的的交易,能否主张具备经济实质,从而避免被认定为避税行为?
因此,当前企业所得税一般反避税条款的相关规定存在不明确、相互矛盾与冲突之处,决定了有必要对一般反避税条款实施的要件予以进一步厘清。
二、作为认定避税安排构成要件的合理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
(一)合理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一个要件还是两个要件
如前所述,《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93条分别规定了判断避税安排的商业目的标准与经济实质标准。为确立避税安排的构成要件,首先应当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标准还是存在包容关系的一个标准。
从各国立法中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及实施实践来看,商业目的或经济实质是否作为避税交易的构成要件,各国的规定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加拿大采用商业目的这一单一要件。根据加拿大《所得税法》第245条第2款③对一般反避税条款的规定,目的要件是区分不可接受的避税与税收筹划的基础[3]。除非该项交易可以被合理地认为主要是为了取得税收利益以外的其他善意目的而发生或安排,一项交易或作为系列交易的组成部分的交易,若直接或间接导致税收利益,将构成避税交易。瑞典《反避税法案》④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只规定了以取得税收利益为目的这一要件,并未将经济实质作为认定避税交易的要件之一[4]。在同时采用经济实质和商业目的作为判定标准的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德国《税收通则法》第42条规定了实质课税原则,但依该法制定的《反滥用与技术性修正法案》规定,认定一项法律形式滥用安排的3个要件中包括经济目的的要求[6]。根据这一规定,商业目的应当为认定交易是否具备经济实质的要件之一,是实质课税原则的下位要件。尽管澳大利亚《所得税法》第177D条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并未直接采用经济实质或商业目的的用语,但如根据交易的方式、形式与实质、当事人与其他相关利害关系人的经济地位的改变以及其他后果能够推定纳税人以取得税收利益为目的,则构成避税交易。⑤根据这一规定,经济实质的存在是纳税人是否以税收利益为目的的认定要件。
在未明确规定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国家,尤其是普通法系国家,在其司法实践中形成的避税活动的一般认定标准中,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标准。但两者构成单一标准还是双重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同样差异巨大。以美国为例,大多数法院在审理避税交易的案件时,往往将商业目的标准和经济实质标准作为两个独立的要件,对案件事实分别予以认定。但也有少数法院认为,“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不过是相关的事实,都与虚假交易的调查相关”,“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区别”,“仅仅表明立法机关要求透过活动的形式揭示其实质”,因此,两者并不构成“严格的双重要件的分析”。⑥但在美国最近将经济实质原则成文化的立法草案中,却要求必须同时满足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两个要件。⑦
关于是否将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作为判定构成避税安排的要件,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存在差异,一方面表明两者是判定避税安排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与相互印证的关系。从逻辑角度看,经济实质标准与商业目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商业目的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纳税人的思想状态与交易意图的判定,然而,“思想状态”显然是无法直接“阅读”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客观的、外在的行为,此即判断一项交易的“实质”。两者分别从主观与客观方面对交易是否构成避税安排予以判断,但无论如何,合理商业目的是一项主观而非客观的标准,只要求纳税人具有从事合法商业活动的意图,却不要求其承担任何独有的经济风险,显然无法包容经济实质的判断[6]。从实践来看,避税安排存在两种具体的形式⑧:第一类避税安排是纯粹的税收利益套利工具,如果无税收利益,纳税人不会从事该项安排。对于此类避税安排,既然不具有除税收套利以外的其他目的,交易安排也是“虚假”或“虚拟”的,确定其不具有商业目的的同时,也可以认定其不具有经济实质。第二类避税安排之目的在于从事真正的商业交易,但选择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交易,以满足税法的技术性要求,并因此而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此类交易显然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但却可能存在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之间的背离[7]。实质与形式之间是否脱节,并不能否定交易本身的合理商业目的。随着避税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避税安排采取这种模式。如果仅以商业目的或仅以经济实质推断交易是否真实,显然无法将此类避税安排纳入规范的领域。经济实质的确认往往基于客观的经济事实,并不考虑纳税人从事交易的动机、目的和意图,交易目的的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证明纳税人并不存在利用税法漏洞、违背立法机关立法意图的违法性,同样是认定避税交易的重要判断要素。因此,经济实质标准与商业目的标准无法相互替代、相互包容,从而共同构成认定是否存在避税安排的双重要件。
因此,我国在立法中肯定经济实质与商业目的作为避税安排的要件,应当是值得肯定的。但确认两项要件之法律渊源的立法位阶差异却表明,难以将二者作为同等适用的构成要件。为此,应当有必要对《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进行修改,将“不具有经济实质”同样作为避税安排的构成要件之一。
(二)合理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择一要件还是并存要件
在确立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作为认定避税安排的同一层级的构成要件之后,两者为择一要件或是并存要件的问题应有必要予以进一步探讨。如为择一要件,只要交易缺乏经济实质或缺乏商业目的,即应被认定为避税安排。反之,如为并存要件,一项交易只有同时缺乏经济实质和合理商业目的,才会构成避税安排。关于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为避税安排的择一要件还是并存要件,美国各个法院在具体适用中存在巨大的差异。根据美国学者对近年来涉及避税案件判决的统计[8],第二、六、八、九、十巡回上诉法院、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倾向于采用择一要件,认为即使是具备合理商业目的的交易,如缺乏善意的经济实质,也将构成避税安排,反之亦然。⑨第二、三、四巡回上诉法院则认为,必须同时证明该项交易缺乏经济实质且无合理的商业目的,该交易才会构成避税安排。⑩第一和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则尚无明确的倾向性。
美国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将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作为避税安排的择一要件或是并存要件缺乏确定性的适用,被认为是当前美国打击避税行为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从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将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作为避税安排的择一要件或是并存要件,在实体上直接关系到一项交易被认定为避税安排进而决定纳税人最终承担的纳税义务和国库收入的取得,在程序上将决定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证明程度。因此,在择一要件与并存要件之间进行选择,首先应当以“有利于纳税人”或是“有利于国家”作为判定基准。其次,在程序方面,应当考虑与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之间的衔接。
与并存要件相比,将经济实质和商业目的作为认定避税交易的择一要件,将使纳税人在认定避税安排时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从纳税人的角度而言,只要不存在真正的经济实质或者不具备合理商业目的,该交易即构成避税安排,与并存要件相比,依据择一要件所认定的避税安排的范围要宽泛得多。这固然更有利于税务机关防止因避税交易而发生国家税款的流失,保证税法获得公平的实施,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更多的经济交易被纳入反避税调查的范围,更多的纳税人为此不得不承担繁杂的资料提供义务、面临由于反避税调查所引发的税收成本不确定的风险。税收征管成本也将因反避税调查的广泛性而大幅增加。更为重要的是,一项交易如果被认定为避税安排,税务机关即有权“按照经济实质对企业的避税安排重新定性,取消企业从避税安排中获得的税收利益”,其结果远高于预期的纳税义务、滞纳金、利息和罚款等额外费用,交易的整体成本也随之增加,交易的盈利性可能因此丧失。纳税人不得不选择在税收方面更为保守的交易形式,甚至不惜以其本可依法享受的税收优惠为代价,税收将因此成为扼杀新型交易形式创造力的元凶,税收激励的政策效应也将因此无法达成。
从程序方面来说,择一要件与并存要件对证明责任的范围要求各不相同。我国对于避税交易的举证责任分配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95条的规定(11),纳税人似乎应当对交易的合理商业目的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12)由纳税人承担举证责任,如适用择一要件,纳税人必须同时证明交易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和真实的经济实质,才能认定交易的有效性,其证明责任的范围相对较广。在并存要件的场合,纳税人只需证明其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或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之间的一致性,即可免予被认定为避税交易。根据举证责任的规则,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举证不能或举证不明,必须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不利税收后果。举证责任范围越广,发生举证不能或举证不明的可能性越大。将经济实质和商业目的作为认定避税安排的择一要件,纳税人更可能因举证不能而面临反避税调整的后果。
避税安排构成要件的设置应当在国库收入的保护与纳税人权利之间实现适度的平衡,否则,将可能因为过于宽泛的反避税调查而使税源减少和税收管理成本增加,并因此而使由一般反避税管理而增加的国库收入消泯殆尽。从总体上说,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作为认定避税安排的择一要件,将使纳税人在反避税调查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相比较而言,将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作为认定避税安排必须同时满足的要件,更能实现一般反避税条款的价值追求。
三、合理商业目的要件的判定与适用
合理商业目的要件探求的是纳税人从事交易的主观意图,该要件强调纳税人必须具备除税收目的以外的、有效的商业或经济目的。但何谓“合理商业目的”,我国立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仅规定了“不合理的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亦即如以获得税收利益作为从事交易的主要目的,则不应被视为主观要件的满足。但这一概念显然过于宽泛,可能导致任何以税收作为考量因素的所有交易(包括以取得税法所规定的优惠税收待遇为目的的交易安排)均被包括在内。既然要求纳税人必须提供资料证明其“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就有必要探求何为非税的“合理商业目的”。
(一)“商业目的”的判定
由于“商业目的”的判断包含了对纳税人从事交易的主观思想状态的判断,一直是税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各国极少在立法中直接对何谓“商业目的”作出规定,而是在税收征管或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判断的因素和标准。在英国,法院一般基于案件事实而以一般常识对交易是否具备商业目的进行判断。在美国,法院所认定的商业目的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一种为文本形式上的商业目的,即要求纳税人采用交易形式的商业目的应当与条文所规定的目的一致;另一种则是纯粹的主观商业目的判断,只要具有非税的目的,均认为构成商业目的[9]。
一般而言,商业目的必须根据特定的经济行业与特定商业活动的属性、实施交易时的经济环境等因素予以判断,必须考虑纳税人的动机和交易是否服务于有用的经济目的。目的并不意味着纳税人头脑中的主观动机或意图,而是交易的客观结果(13),能够基于纳税人的行为等外部表征予以支持,且必须对纳税人经济地位的改变或未来存续而言是有用的[10]。商业目的可以根据纳税人在交易安排中的权利与义务予以衡量,权利义务的属性越接近纳税人的商业惯例及其持续经营,商业目的要件越能得到满足[9]。作为一种主观的思想状态,商业目的应当根据纳税人所实施的行为等外部事实予以客观评价,如交易是否具有盈利的可能性、是否真正将资金投入交易中、各个交易步骤是否真正发生、交易所涉及的主体是否相互独立且在交易前后从事合法的商业活动,等等。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证明交易存在“商业目的”,最为重要的是证明“非税目的”的存在。一般而言,作为交易主体,基于经济理性人的考虑,无论公司或个人,交易能否实现“利润最大化”无疑是首要的考量。因此,交易是否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商业目的”。如果纳税人能够证明在交易时是以实现自身利益追求为目的,以实现一定的利润为目标而作出交易决策,具有“真正且诚实的利润目标”,应当可以成立“非税目的”。但利润动机并非惟一的“非税目的”,以实现利润以外的其他商业利益为目的,同样可以构成“商业目的”。在TIFD III-E inc.案(14)中,纳税人“缔结合伙协议以筹集资金,且更重要的是,向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和其高级管理人员证明其可以筹集资金”,被法院认为构成“商业目的”。“履行除纳税义务以外的其他法定义务”可以被认定为“非税的商业目的”,如美国法院在Frank Lyon Co.案中认为,满足监管义务应该构成一项商业目的。(15)此外,以利益最大化为考量因素的其他商业动机,如反敌意收购、风险管理、股价的增值、有限责任的承担、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和经营架构的调整等,也可以构成“商业目的”。
但应当强调的是,“商业目的”要件并不意味着交易不应包括任何税收的考量。对公司而言,税收是一项成本,与工资、租金或利益并无实质的区别[11]。在公司作出商业决策时,如何减轻其税收负担也是其发生交易及选择交易形式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例如,由于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税收待遇的差异而选择进行债务融资、基于工资的加计扣除考虑而雇用残疾人员等,即使此时减轻税负是其作出商业决策的主要甚至惟一目的,也不应当认为不构成“商业目的”。要求交易具有“商业目的”,并不能将税收排除于商业考量的范围。为此,应当将税收利益的追求与交易可预期的商业利益进行权衡比较。但取得税收利益也可以是善意的商业目的。(16)税收目的是否构成“善意的商业目的”,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判断:其一,该税收目的是否符合税法条文的立法意图,实施交易的目的是否在于实施税法所欲鼓励的行为;其二,该税收目的是否指向善意的、追求利润的商业活动。只要满足上述要件,即使税收是其发生交易及其形式选择的主要目的,仍应当认为具备“商业目的”。
(二)何谓“合理”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的规定,构成税法上有效的经济交易,不仅应当具有“商业目的”,该目的还应当具有合理性。在法律领域中,合理性的判断一直是最模糊的领地。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对商业目的的“合理性判断”更加困难。在我国,到目前为止,税务机关仍是适用一般反避税条款最主要的主体。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显然并非经营活动的专家。商业活动所欲达成的目标往往是在复杂且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下形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营者当时的直觉与判断。在交易完成后,再由税务机关对该目的的合理性进行事后评价,对企业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税务机关并非公司经营成果的裁决者,其交易目的追求的合理性更应当由市场进行评价。税务机关不能也无须过多地承担商业目的合理性判断的任务。税法是以评价经济负担能力为基础的,这也决定了税务机关只需判断交易目的的实现在促进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能力”方面是否具有合理性。税务机关对商业目的的合理性判断,应当是最低标准的判断,即如果交易同行或处于类似状况中的经济理性人在同一情况和环境下也认为该商业目的的实施不利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显然与实现企业未来财产价值的增加或提供可获得利益的机会无关,才能据此认为该商业目的不具有合理性。为此,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交易发生时的宏观市场环境、行业的商业惯例、企业的一般经营策略等进行判断。
商业目的的合理性判断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商业目的的合理性是基于交易整体还是以交易各个部分或步骤进行的判断。有学者认为,只要交易整体上的商业目的具有合理性,即使交易的某个方面或步骤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仍应当认为其满足商业目的要件[7]。但在普通法系国家中,则认为应当分别审查交易的各个步骤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组成交易的若干步骤欠缺合理性,则该步骤将被忽视,即“阶段交易原则”(Step Transaction Doctrine)。纳税人固然可能采用迂回、复杂得多环节交易方式创造避税机会,但各个步骤本身是交易整体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并不具有完全独立于交易的商业目的,因而难以进行合理性的判断。如果单纯由于其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而否认该环节的税法意义,将在一定程度上剥夺纳税人实现整体商业目的在经济形式方面的选择权。从经济角度来看,商业目的之合理性应当是立足于交易整体判断的合理性,而非各个阶段或步骤的分别探讨。如果根据所在行业的商业实践,某个环节或步骤为实践交易的整体目的所必要、服务于交易最终利益的实现,即使该环节本身并无独立的商业目的,仍应当认为其满足合理性的要求。
四、经济实质要件的基本判断
如何判断交易是否存在真实的经济实质或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是否一致,各国的作法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尽管与商业目的要件相比,经济实质要件是对交易的经济效果进行的客观评价,但透过“法律形式”的实质探求,对交易的不同事实与环境的把握同样可能产生不同的实质属性结论。因此,如何以客观的甚至足以量化的标准判断经济实质的存在,也成为各国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的又一难题。在当前各国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中,确定经济实质的方法主要包括商业利益法、可比交易法、经济地位改变法等。少数国家的司法机关也采用机会成本法。
基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市场主体在从事真实的经济交易时,必须关注取得税前收益的可能性,因此,商业利益法被认为是确定交易是否存在经济实质的重要方法之一。根据商业利益法,如果一项交易产生经济回报,即应当被认为具有真实的经济实质,为此,纳税人必须证明交易预期产生的经济回报将足以弥补所发生的交易成本。考虑到市场的风险因素,并不要求交易产生真正的经济回报,只要求在缔结交易时,根据交易条件和经济环境可以预期交易的结果将产生合理的收益。但对经济回报的认定,则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方式。有些法院认为,只要为纳税人带来经济收益,无论该收益是否能够量化,都能满足该要件。(17)有些法院则认为,交易具有客观经济实质,不仅要存在可预期的经济收益,该收益还必须是能够量化的经营利润。(18)但商业利益法备受诟病之处在于“合理的收益”之确定,即多大数额的商业利益足以使交易产生经济实质?在美国早期的司法判决中,只要产生积极的经济回报,即认为满足该要件。(19)但这意味着,即使非常微小的回报也足以使交易具有经济实质,相反,非常微小的损失却将导致交易缺乏经济实质[12]。随后,法院采取了最低税前回报率的方法判定经济回报是否合理。在Carol W.Hilton案中,法院强调交易只有取得超过6%的回报,才足以认定交易具有经济实质。但由于本案判决并未具体说明6%回报率的确定方式,使得具备经济实质要件需要达到的最低税前回报率的确定似乎是随意而主观的。有学者则认为,如果系争交易不能预期可以产生高于无风险或低风险投资的潜在收益,纳税人只需从事无风险的投资,因此,应当以低风险或无风险投资回报率作为判断的标准[13]。无风险或低风险的投资回报率实际上只是代表了货币本身固有的时间价值,即使取得相当于无风险投资的回报,仍不能意味着纳税人因交易而取得额外的经济机会,并因此而增加自有财产的价值。因此,如果要求交易必须取得最低税前回报率才具备经济实质,将可能产生如下两种不利后果:一方面,对于缔结交易而无法预期最低利润数额或可能产生潜在损失的纳税人是不公平的。尽管一项交易(如避险交易)本身可能发生亏损,却可能为纳税人创造新的交易机会,或对改变相关财产的价值有着直接且实质的关系[14]。单纯因发生亏损的预期而否认其经济价值的存在,显然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最低回报水平的设定也可能导致纳税人为保证交易的回报满足最低收益预期的要求而无效率地承担额外的风险[15]。此外,商业利益法无法对以非正常方式取得显著税收利益但同时实现真正盈利的交易予以真正的评价[7]。
由于商业利益法所存在的问题,可比交易法逐渐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采用。所谓可比交易法,即将系争交易与在善意商业环境下本应发生的交易进行比较。(20)具有经济理性的纳税人不会利用避税工具获得与经济上相当的市场交易相同的收益,尤其是在考虑了税务诉讼风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9]。因此,如果系争交易所产生的税后回报与可比交易实质相当,则该交易具有经济实质。反之,如系争交易所产生的税后回报明显高于可比交易,则不认为具有经济实质。但适用可比交易法的逻辑前提在于,该项交易已取得积极的税后回报,同样无法避免商业利益法的上述困境:无法评价存在亏损预期或无盈利但取得税收利益的交易。加上可比交易法是基于实际发生的税后收益的比较,所取得的收益不仅决定于交易条件,更受到复杂的市场因素的影响。可比交易法对相似环境下相似交易的依赖同样也将大大弱化其结果的客观性。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完全相同甚至类似的交易实际上是很难取得的,即使一定的非决定性因素的调整可能保证其可比性,但在实际交易中,微小的合约条件差异可能从根本上决定纳税人经济地位的差异。(21)因此,可比交易法不仅无法解决商业利益法中存在的问题,反而使得本应是客观事实判断的经济实质要件具有更强的主观色彩。
商业利益法与可比交易法都以完备市场假设为前提,即在不存在任何市场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对交易实质予以判断。在现实的不完备市场中,市场存在各种摩擦力,任何企业从事任何经营活动和交易,都将面临不同程度的风险。财产价值在一项真实的交易中不可避免地将面临价值增加或减损的不确定性。因此,经济收益机会与价值减损的风险成为任何一项交易的一体两翼,缺一不可。两者之间更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关系,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金融工具的价格更是直接决定于其未来收益与损失风险的预期。如果纳税人愿意承担与预期收益相当的风险暴露,意味着纳税人以未来财产价值减损的可能性换取收益的取得,则交易具有经济实质[6]。一项只有预期收益而缺乏任何经济风险或收益的取得与所承担经济风险之间显失比例的交易,是违背市场基本规律的,必然是虚假的或人为创造的结果,不具有真实的经济实质。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市场主体从事经济交易都必须以利润的追求作为最终目标,但这一最终目标并不直接体现在其所从事的任何交易中。市场主体可能从事一项并不产生直接收益而是间接服务于未来收益机会增加或风险减弱的交易,如表决权或控制权的取得、反收购、购买保险计划、竞争地位的改善,等等。这些交易的发生并无量化的利润产生,甚至仅仅造成资源的耗费,但对企业未来的市场发展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经济效果,其经济实质仍不容否定。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未来收益预期、风险的承担或消除风险的努力、法律权利的取得与义务承担以及非货币商业利益等,将在不同程度上实质性地改变或影响纳税人在交易前后的经济地位,代表着纳税人未来直接收益或潜在收益机会的取得或财产风险的减损,将使纳税人财产价值发生或将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因此,一项交易是否足以实质性地改变纳税人交易前后的经济地位,应当成为判定交易是否具备经济实质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包括商业利益在内的广义标准,更能够对复杂商业环境下形式各异的交易之经济成果予以正确评价,其涵盖面显然比商业利益法或可比交易法更广,对交易的经济实质判定也更具有科学性。根据这一标准,只要纳税人以任何方法实质性地改变交易前后的经济地位,即应当认为交易具有经济实质。虽然是一项产生税收利益的交易,但如果可以预期纳税人交易前后的经济地位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该交易就不具有经济实质。例如,一项投资活动的完成使纳税人所处经济地位与资金留存于银行并无任何差异,该交易就不具有经济实质。
五、结语
一般反避税条款在《企业所得税法》中得到采用,被认为是该法的制度创新之一,是以一般标准应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复杂且形式更加多样化的避税交易的重要制度。一般反避税条款成为纳税人头上时刻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避税行为的阻吓作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在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不明的情况下,纳税人将不得不慎之又慎地作出经营策略,以免面临不确定的税负成本和高昂的调查成本。在当前高度简化的立法背景下,税务机关适用一般反避税条款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不难预见大量的税务争议将由此产生。因此,如何将一般反避税条款所确立的“标准”具体化和明晰化,将是未来税收立法与实践的重要任务之一。ML
注释:
①当前规定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新西兰、葡萄牙、新加坡、西班牙、瑞典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②参见:《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1条。
③Section 245,Income Tax Act(Canada).
④The Tax Avoidance Act(Sweden),1998.但该条同时要求交易的形式不能与税收立法的目的存在冲突。
⑤Section 177D,Income Tax Act(Australia) 1997.
⑥ACM Partnership,157 F.3d at 247.
⑦H.R,2520,107th Cong.(1st Sess.,July 17,2001); America Competitiveness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02,H.R.5095,107th Cong.(2d Sess.2002); 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rength(JOBS) Act.S.1637,108th Cong.(1st Sess.,Nov.7,2003); S.Rep.No.108-192 (2003) (Reporting on JOBS Act).
⑧有学者认为,避税安排还包括另一种形式,即从总体上看具有盈利性的交易,但如税收从一般投资活动中分离出来,则不具有商业目的或经济实质,但同时认为,这种类型的避税安排实质上与纯粹的套利工具相同。
⑨Generally ASA Investerings,201 F.3d at 513; Saba P' ship,271 F.3d 1135.
⑩Rice's Toyota World v.Corona'r,752 F.2d 89,92-95(4th Cir.1985); ACM P' ship v.Comm'r,F.3d at 231(3d Cir.1988).
(11)我国《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95条规定:“税务机关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时,应按照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向企业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企业应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提供资料证明其安排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资料,或提供资料不能证明安排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税务机关可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实施纳税调整,并向企业送达《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
(12)在涉及避税安排认定的案件中,由纳税人承担举证责任,其合法性与合理性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这已超出本文探讨的内容范围。
(13)Smith's Potato Estates Ltd v.Bolland HL 1948 30 TC 267(1948) AC 508(UK); IRC v.Brebner(1967) 2 AC 182(UK).
(14)TIFD III-E inc.,342 F.Supp.2d at 109.
(15)Frank Lyon Co.,435 U.S.at 583-584.
(16)IRC v.Plummer(1979) STC 793(UK).
(17)Bail Bonds by Marvin Nelson,Inc.,820 F.2d at 1549; Winn-Dixie Stores,Inc.,113 T.C.at 285.
(18)Ohnson v.United States,32 Fed.C1.709,716-717(1995).
(19)Goldstein v.Commissioner 66-2 USTC 9561,364 F.2d 734(CA-2); Barnett v.Commissioner,66-2 USTC 9563,F.2d 742(CA-2),aff'g CCH Dec.27,414,44 TC 261(1965); Rothschild v.United States 69-169-1 USTC 9224,407 F.2d 404(Ct.Ci.).
(20)Merryman v.Comm'r,873 F.2d 879,881(5th Cir.1999); CM Holding,Inc.,254 B.R.at 600; CM Holding,F.3d at 108; Andanteeh L.L.C.v.Comm'r,83 T.C.M.(CCH)1476,1505(2002).
(21)例如,ASA Investerings Partnership v.Commissioner案、Saba Partnership v.Commissioner案以及Boca Investerings Partnership v.Uinited States案中的CINS交易,在具体交易条件上存在细微的差异,仍可能导致其经济实质上的差异。(参见:ASA Investerings Partnership v.Commissioner.201 F.3d 505(D.C.Cir.2000);Saba Partnership v.Commissioner,273 F.3d 1135(D.C.Cir.2001);Boca Investerings Partnership v.Uinited States,314 F.3d 625(D.C.Cir.2003);Jason Quinn.Being Punished for Obeying the Rules:Corporate Tax Planning and the Overly Broad Economic Substance Doctrine[J].George Mason Law Review,2008,(15):1054-1059.)
标签:企业所得税论文; 税收法定原则论文; 合理避税论文; 税法论文; 反避税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企业税务论文; 纳税人论文; 法律论文; 经济学论文; 税收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