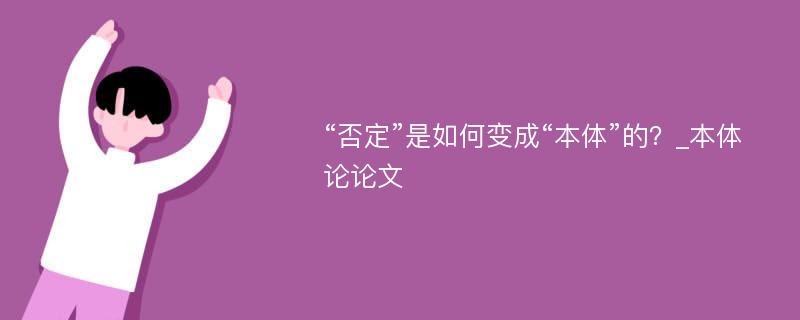
“否定”何以成为“本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否定”成为“本体”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我所说的“本体性否定”,必须能够“离开”或“穿越”过于人为化的当代性物欲追求,使“人为”之潜能发挥在任何确立自己的存在价值上——这样一个“离开——建构”的新型“人为性源流”之价值努力,我称之为“本体性否定”。其中,“离开”意味着否定主义哲学对既定现实特定的“局限分析”,而“建构”则意味着对既定事物建立独特的“个体化理解”。这种理解的最高境界是哲学性理解。因此,“本体性否定”是对“人为性”的一种价值限定。
首先,“本体性否定”与其他本体范畴(如实践、自由、创造、符号、道)相比究竟有什么区别?“本体性否定”产生的历史依据是什么?
所以,在我看来,“实践”主要强调的是“本体性否定”的“结果形态”,而一切“结果形态”都主要是现实的形态。“自由”和“道”又正好相反——“自由”在萨特那里是一个“潜意识”或“非理性”状态,并不包含自由的结果;而“道”在老庄哲学这里虽然作为“源”通向“流”(现实事物),但道作为本根的非现实性意味则是明显的。这样,“实践”、“我思”和“自由”、“道”便都将作为整体的“本体”割裂了。比较起来,只有“创造”最为接近“本体性否定”,最为接近“本体性否定的结果”。但“创造”只是人最根本的价值冲动的一部分,而不是最根本的冲动的全部(而且对“创造”的理解哲学界也有分歧)。最根本的、原初的冲动应该是人对现实的“不满足于”的情绪和意识。人因为意识到现实的问题和局限,才会有“不满足于”的批判冲动,才会有创造的行为与实践。而且在创造中,还必须批判地对待现实事物,创造才成为可能。因此,批判与创造,本来就是一个本体之中相辅相成的内容——这个内容,我就称之为“本体性否定”。
这种“不满足于——开始另一种”的张力,就是“本体性否定”冲动产生的时候。这种冲动首先是无形的,所以,一切有形的人类文化均不能说明这个冲动,但可以推测这种冲动。也就是思维、劳动、工具等有形的人类文化,并不对立于这个冲动,正好相反,以上符号正是这个冲动完成的标志。所以,我们看见的文明符号作为“流”,是“本体性否定冲动”这种“源”的产物。
其次,“本体性否定”之所以有“不同而并立”的思想,来自于我对以下现实经验的分析和甄别:当代人对欲望与快乐之所以有“不满足”与“不满足于”之别,就在于“不满足”依然可能是在欲望世界中挣扎,即不满足一种欲望,可能是在追寻另一种欲望。但否定主义美学不同于西方“超越欲望、超越世俗”的地方,在于我并不认为“否定结果”是比“否定对象”优越和进步,而是“不同、并立”之意。所谓“不同”,意味着“否定者”是对“否定对象”的“腻味”和“局限”的发现,而不是因否定对象整体上具有“落后性”而否定之。“腻味感”是因自然性重复和循环产生的感受,被“可能成为人”(在人产生之后,“成为人”便是成为“创造性之人”的意思)的动物意识到,才产生了对自然性生存的“不满足于”。“不满足于”不是说“否定对象”“不好”,而是说“否定对象”“不够”。既然是“不够”,人就离不开自然性的生活,而是不能光靠自然世界生活。人从此便成为兼具“自然性”和“人为性”两个世界的特殊体。两个世界不同而并立,只不过说明各自可以互补对方之局限罢了。因此,在“本体性否定”的观念中,不是两个世界各有高低,而是两个世界因性质不同而被人同时需要。
当然,这也不是说,作为否定对象的自然界,与作为否定结果的人类世界价值等同,而是说,人的自然界多为生存快乐和难受的体验,人的文化性世界,多为心灵依托和自我实现的体验;生存快乐的体验是自然而然的、循环的、群体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心灵依托之体验是人为努力的、难以重复的、个体性的、或然性的。这样,人否定自然界和自身的自然世界,只不过是将心灵价值依托安放在文化世界,而将自然性世界作为另一个不同世界予以尊重而已。
再次,“否定”作为“本体”还意味着:“否定结果”因其性质上的独特存在,可以作为否定者全部生活内容的价值支点来对待。
这就是说,“本体性否定”还是一种“价值本体论”。这种“本体性价值”不仅区别于自然性生存价值,而且还区别于一般的人为性价值。我在说“区别”一词时,已经先验地命定了自然性生存价值的有价值性。因此,说“本体性价值”,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替代其他价值,或比其他价值更具有优先性,而是说“本体性价值”和“非本体性价值”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同。
下篇:“否定”成为“本体”的理论推演
为什么“本体论”应该做“人本本体论”而不是“自然本体论”解?为什么“本体性否定”所说的“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是对“人本本体论”的一种价值限定?并因此区别既定的人本主义哲学?“本体性否定”的内在结构如何?它如何在避免“以人为中心”的思维的同时又与对人的相对主义理解有所区别?
首先,“本体”从“上帝”、“自然”、“实体”、“客观规律”这些物质或精神实体,向“人的思之功能”、“人的实践”、“人的筹划和自由”的转换,应该是西方古代本体论和现代本体论的分水岭。
其次,“本体性否定”之所以区别于讲主体功能(我思)、人的存在(自由与筹划)等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西方现代本体论哲学,将“什么人为”的问题作为对中国当代本体论建设的思维方式,是因为:第一,当人仅仅作为区别于自然的一种存在时,“我思”、“自由”、“筹划”乃至包括“实践”,只能揭示人的“类存在”特性或人区别自然的普遍的、一般的特性,而不能真正揭示“个体”在自己的“类存在”面前的“再存在”之意义和方法。而如果我们不能在根本上揭示个体与群体的区别,也就解释不好人类与自然的真正区别是在哪里——假如动物的“筹划”或“自由”就是原始地选择自身的生存方式呢?这就必然提出一个“什么筹划、自由、实践”,“如何筹划、自由、实践”的新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统一的哲学命题。第二,“本体性否定”之所以以“批判与创造的统一”作为对“自由”、“筹划”、“实践”的价值限定,并以此作为对“什么人为”的中国化解答,是因为否定主义美学认为人的“筹划”的本体只能是“批判与创造”,而“批判与创造”的实质是建立对“世界”的“个体化理解”。这意思是说:对“世界”的“个体化理解”不等于对“事物”的“个性化理解”。前者是哲学性的,后者则只是一般理性的;前者是本体论的,后者则是认识论的。所以,“本体性否定”对每个人来说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这种或然的、创造的“否定”,是对“筹划”、“自由”、“实践”的具体规定,并因此可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成为人是自身的或然性对自身的创造性的揭示,而不是必然性和筹划性的结果。
再次,这就涉及到对“本体性否定”的内在结构的分析了。“本体性否定”之所以以“批判与创造”为自己的规定性,是因为它将萨特所说的“自在”和海德格尔所说的“沉沦”作为否定者离开的“对象”,从此不再对“自在”或“沉沦”说三道四。因为“自在”和“沉沦”不能安放人的存在性而只能获得快乐性,所以这是不同于萨特、海氏将“自在与自为”、“沉沦与澄明”作为“自由”和“在”的内在结构的——人不是原始的、本能的选择“自在”和“沉沦”而也具有存在性,而是在“离开”它们的时候审美意义上的存在性才开始出场。这样,“本体性否定”只是在萨特的“自为”领域和海氏的“澄明”领域中去开拓自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