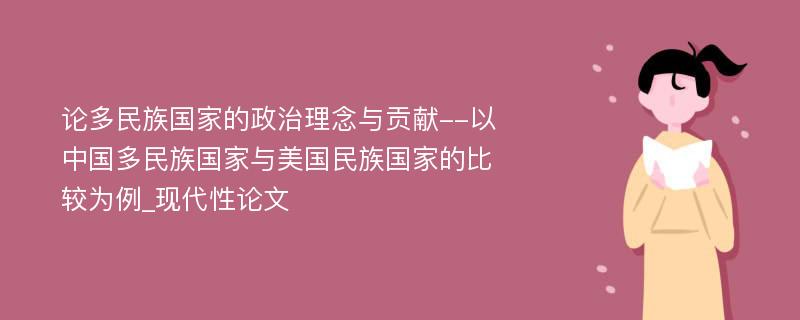
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及其贡献——以中国多民族国家与美国民族—国家的比较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民族国家论文,为例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多民族国家政治理念的来源
起源于欧洲的民族(nat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均是具有现代性(modernity)的概念。所谓的现代性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之一,其典型的思维方式是把历史割裂开来,划分为二元对立的两个时代:黑暗的中世纪和光明的现代。中世纪是与宗教、封建制、农业经济等相联系的,现代则与科学、民主制、工业经济等相联系。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几乎都承认这样一个“现在”与“过去”的截然对立。这不仅是一种时段划分,而且是一种价值判断:现在的就是好的,而过去的就是不好的;人类历史以科学、理性、民主等武器而不断走向光明的未来。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理论正是现代性统治下的极具局限性的理论形态。
西方学者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组成的国际体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了这个问题:“是什么使得民族——国家成为19世纪初至今的一种无可抗拒的政治形式呢?”他认为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及其运作原则起源于欧洲,并随着三种因素的推动而扩展到全球,即:工业力量与军事力量的结合,国家行政力量的急剧膨胀,以及“一系列偶然的历史发展过程”①。与马克思主义所建构的进化论式的连续性社会形态演进方案不同,吉登斯却是要提出一种对“现代史的非连贯性解释”,而“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乃是现代史断裂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②。这种断裂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traditional states)的断裂。起源于欧洲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取代其它地方的各种形式的“传统社会”,也就是可以接受而且必须接受的过程了。显然,吉登斯是在建构现代性,而非瓦解现代性。
吉登斯虽然声明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民族——国家的发源地亦即“西方”,但他也讨论了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并承认在当今世界各国家之间存在民族——国家的“变异”。那么,这种“变异”到了何种程度?是不是在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体系中还存在有非民族——国家的政治形态呢?人类学家王铭铭在对中国闽南美法村的个案研究中对吉登斯所代表的现代性表示了质疑,因为王铭铭看到的不是历史的“断裂”,而是历史的“绵延和回归”。他指出:现代性只是一种“理想模式”,而非“社会现实”,吉登斯、盖尔纳等人“片面强调‘现代性’对传统取代的有效性,忽视了乡土传统的持续性”③。吉登斯所强调的民族——国家的“内部绥靖”,即行政力量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表达了民族——国家对同质性(homogeneity)的追求,这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使然。但意识形态要求的“理想模式”与“社会现实”是有差异的,吉登斯建构的国际社会中并不存在完全符合其理想型的“民族——国家”。
不仅如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如果“民族——国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模式”的话,也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追求这样一种理想模式。诚然,在近代史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把欧美式的民族——国家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型,但其结果是未能在理论、实践中完全实现与中国传统的对接而以失败告终。1949年以后的中国,则从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民族——国家”,反而在意识形态上将“民族主义”列为自己的反面。新中国倡导的“多民族国家”模式事实上已经是另一种“理想模式”,并且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获得了成功。新中国为什么选择了一种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呢?笔者认为,这里涉及三种主要的理论资源及其交叉影响,即:中国传统的族类概念和民族政治,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话语系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国家观念。
1.中国传统的族类概念和民族政治.
中国传统的“族类”概念,包括“民”、“族”、“人”、“种”、“类”、“部”几个单字及其不同的组合。作为一种分类体系,中国传统的族类概念基本上遵循的是“血统论+文化论”的原则。“族”这个字的本义是“矢锋也,束之族族也”,指的是一个共同对外的群体,在中国,这样的基本群体单位当然是作为血缘组织的家族、氏族、宗族,在血缘维度之外再加上一个文化的维度,就扩大到“族类”概念。如《国语·晋语》所言:“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姓”是血缘维度,“异德”是文化维度,“异类”就是、“种类”、“族类”的差异,这种分类是一个由生物学意义扩展到文化学意义的分类体系。如果说这种“族类”概念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族观的话,则“天下观”就是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并由此引出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政治”,即民族问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
“族类”的民族分类体系与“天下论”的世界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因为中国古代追求的国家模式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以“民族”为其内容和支撑的“国家”,而是“家天下”的“皇朝”。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多种“族类”的多元化的“天下”正是古代中国所追求的、符合“天理”和“道”的民族政治模式,即“浦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天下观。以“五服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关于“亲疏远近”的想像的空间秩序观,正是族类分类体系与天下一统观念的契合。因此,可以认为,中国传统的“族类”概念和民族政治引出的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亦即多民族的国家模式。
2.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话语系统
与中国传统的族类概念相比较,欧洲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概念则有极大的不同。“民族(nation)”本质上并不涉及一个分类体系,而是一种主观的意识形态建构。“民族主义”并不关心世界上有多少族类,而关心“我”与“他”的二元划分,强调以地理国界界定的本群体的内聚意识和排他意识。这种意识最强烈的表达就是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诉求:“民族”要求的不是一个“天下”,而是属于“自己”的独立领土和主权,也就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因此,“民族”(nation)所要求的必然是一个要求内部高度同质化、对外则强烈排斥的国家模式。
中国传统的族类与西方舶来的“民族(nation)”所导致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政治理念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卡尔·波普尔提出了“封闭性社会”和“开放性社会”的概念,其本质区别在于是坚持价值判断的一元决定论还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二元决定论④。在古希腊哲学那里,已经开启了这个二元论的思路:人与物的分离,应然与实然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最终造就了哲学上“我”与“它”的对待之局(Co-ordination),“意识到了人生活于实然与应然这两个世界夹缝中的尴尬处境”⑤。而儒家哲学是一种“无它”哲学,“由于有‘我’无‘它’,儒家难以建构一个事实判断系统,只能向着价值判断的单一向度片面发展,无限扩张,造成了一个独木支撑的‘千年至仁之人极’”⑥。如此看来,中国古代的族类观与天下观是服从于价值判断的“应然”的系统,而西方的“民族”(nation)则是服从于事实判断的“实然”系统的。两种不同的民族观的出现实际上是一元论和二元论哲学的不同造成的。
起源于欧洲的具有强烈现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近代史上输入中国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渠道是通过与中国传统的“族类”观念的结合,实现了不同形式的中国化。1840年以后,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开始输入中国社会,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理论即是其中之一。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来看,呈现一种多重架构:既有排满的种族民族主义,也有反帝的国家民族主义;既有文化民族主义,也有经济民族主义;既有保守的民族主义,也有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著名的理论家和代表人物则包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等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把欧美式的民族——国家作为自己追求的国家模式,使得民族主义成为1949年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正是民族主义的舶来使得汉语“民族”概念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和学术上的主角之一。
3.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国家观念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民族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划分是横向的、以地理国界和文化传统为标志的“民族(nation)”之间的区分,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是纵向的、以经济地位为标志的“阶级”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民族主义运动的时候,要看其是否符合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反对那些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殖民主义和沙文主义,支持那些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超越民族——国家壁垒的各族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国家观念上,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持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大国”的原则。这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而这更容易与中国传统的族类概念和民族政治契合。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苏俄模式的影响,近代中国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又一次发生了较大的转型:从追求欧美式的民族——国家的“国族主义”转变为追求苏俄式的“自由联合的”多民族国家。与此相联系的是:与国民党化“民族”为“宗族”的同化主义论调不同,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国内的少数民族。国民党的取向是熔国内诸族为惟一的“国族(nation)”,因而是一个归纳式的思维模式;共产党的取向是挖掘各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是一个演绎式的思维模式。结果,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多民族国家模式不感兴趣,而共产党却进一步在中国划分了 56个民族[1]。
综上所述,以上三种理论资源在近代史上发生了交叉和融合。在中国近代史上,古代中国想像的“天下”已经被压缩成为现实中的“万国之一”。欧洲式的“民族(nation)”概念也舶来中国并风行一时,“民族主义”被各派思想奉为富国强民的“法宝”。但这个外来的概念与本土的思想之间必然要发生一系列的碰撞、融合。1949年前影响最大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经历了由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向西方式的“国族主义”的转变,并在此过程中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资源。但是国民党完全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诉求还是遭到了挫败,因为“民族——国家”这件紧绷绷的外衣很难覆盖中国庞大的躯体,亦即舶来的“民族”话语还要适应中国的语境而做出改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引进了另一种思路,真正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 1949年后,“民族”概念在综合中国传统、西方“民族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等诸种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化,在此基础上,一个中国化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也逐渐形成了。
二、中国与美国: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的若干比较
在经历了百年近代史上的挣扎和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成功,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多民族国家模式与欧美式的民族——国家模式有什么不同?这个多民族国家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什么贡献?笔者将以中国与美国的比较为为例,探讨多民族国家政治理念的特点。
(一)中国VS美国:国家政治制度
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模式与欧美的民族——国家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是社会主义中国选择了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所谓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笔者将把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堪称欧美民族——国家代表的美国做对比。
1.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就是国家的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也是在国家机构体系内纵向配置国家权力行使权并规范其运用程序的制度模式⑦。一般认为,国家结构形式分为单一制、复合制两种,复合制又主要分为邦联制和联邦制两种。各国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取决于该国的具体国情。
新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又有着独特的特点,即:从最早主张自由联邦制逐渐转变为实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在法理上,单一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央,地方的权力具有中央授权性。中国的单一制下存在三种行政区域类型:普通行政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别行政区,从而形成三种类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类型,使中国的单一制在解决民族问题、国家统一问题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⑧。可见,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中就有关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机制的设计,也可以说,是国内民族问题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最终样式。这一点正是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最显著特点之一。
美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经历了从邦联制到联邦制的转变。1776-1787年的美国为邦联制国家,主要权力分散于各州,中央权力十分脆弱,这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巩固。1787年宪法改邦联制为联邦制,但各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联邦中央权力的集中是美国变得强大的重要因素之一⑨。可见,决定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重要因素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而没有民族因素的作用。可以说,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其中考虑了民族因素。
2.政权组织形式
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反映国家的国体(阶级本质)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前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多为民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两种形式,而社会主义国家均为民主共和制。中国和美国都是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但其具体内容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制度的原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保证了全国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可见,新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建立在保证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取向之上的,而这之中必然要考虑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建立特定机构、实行特殊措施确保少数民族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这是新中国政权组织形式必然要考虑的内容。下面关于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的讨论中,将进一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美国则是共和制下的总统制,即总统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政体形式。总统制肇始于美国。总统由选民选举,独立于议会之外,向选民负责而不向议会负责。美国总统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如总统可对国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但如果国会再以2/3多数通过则可不经总统批准成为法律;总统同时也受国会制约,国会可弹劾总统。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有目共睹,甚至被称为“帝王”般的总统,这直接削弱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原则。美国式的政权组织形式已被证明为是“富人的国会,富人的统治,为富人谋福利”⑩,人民,尤其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在这里不会成为重要内容。
3.国家权力的实现形式
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都宣称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机关和行政元首由选举产生。如上所述,新中国和美国虽然都是民主共和制国家,但其政权组织形式不同,因而导致了国家权力实现的形式不同。
新中国实行的是起源于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制度,即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从属于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即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设置中处于最高地位,是人民的代表机关,其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新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只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为体现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特别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并设立专门的民族委员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区域自治,该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则是自治机关。为了贯彻落实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和实现平等权利,新中国实行了民族识别,正式确认了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以便在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时适当分配名额。
美国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制度,即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三个机关独立行使、相互制衡的制度。人民行使权力的主要形式是参与议会与总统的选举,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美国的立法机构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国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统则是间接选举。但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竞选是世界闻名的“金钱之战”,并且逐年升级。1994年4月的统计,美国参议院中有1/4以上(28名)议员是百万富翁。2004年,小布什与克尔的新一轮总统竞选又创造了美国总统竞选史上金钱花费的新高。这些都表明,美国政治的金钱本质使其不可能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在美国的政治中,基本上没有少数民族的位置。
(二)中国VS美国:“民族”政治
新中国与美国国家政治制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国“民族”政治的差异:在中国,民族问题是国内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家政治特意给予关注并提出了相关措施的对象;在美国,民族/种族问题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在国家政治中没有给予特殊的关注。
1.对“民族”的不同界定模式
汉语“民族”一词的译名问题一直存在,它与西方语言中的同类概念无法完全对等。这种差异实际上还反映了不同国家政治、不同文化背景中对“民族”的不同界定模式。
在新中国,是以政治性的民族识别确定民族划分和公民个体的民族身份。中国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基本上每十年都会爆发一次,政治意识形态直接介入对“民族”的界定,这是因为“民族”标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通过把“民族”固定化,通过定义“民族”的客观特征,以便在现实生活中使得“民族”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变量。例如:国家法律确定了56个民族,使这些民族群体获得参与国家政治的合法身份;通过把“民族”身份标注在公民身份证上,使得“民族”标签成为衡量公民个人身份的一个固定变量。在学术领域,中国的民族研究就表现为强调每一个民族单独的历史和文化体系,倾向于非关系性的研究。
在美国,则把民族身份(ethnicity)归诸私人化、非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致力于强调基于国家认同的“美利坚民族”(the American Nation)。美国没有官方的“民族”定义,也不会去进行民族识别,在现实中交替使用“民族”(nation)、“族群”(ethnic group)、“种族”(racial group)、“少数民族”(minority group)等词汇,在各类统计中使用的民族分类也不尽相同。西方族群理论强调的是“族群”的主观认同,族群具有主观、模糊、变动不居等特点,与中国式的“民族”理论强调民族的客观、清晰、固定等特征相反。美国的民族研究则主要存在于社会学领域,强调关系性研究。
2.民族关系的社会目标
马戎指出,西方从事族群、民族、种族研究的社会学学者“注重对一个国家内部族群关系的现实状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总结该国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而制定该国国内族际关系的社会目标(the social goal),以及研究在一个多族群(多民族)国家中,族群关系应当如何发展的远景,政府和社会应当如何引导和创造条件来实现这一远景目标”(11)。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关于民族关系的社会目标。
新中国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产物。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族类观描绘了一个多元民族和文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一直主张建立“统一的大国”的原则;二者的结合必然导引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模式。因此,新中国从国民党时期倡导的同化论的“国族论”发展到多元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并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社会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具体落实在国家的各种民族政策之中,其中最基本的是作为中国三大根本性民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据1990年1月的统计,美国人口为2.48亿人,其中欧裔白人1.9亿多人,占全国人口的78%以上;非洲裔黑人3025万人,约占12%;拉美裔居民近2200万人,约占9%;亚裔和太平洋诸岛国裔居民近700万人,约占3%;原住民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约200万人,占 0.8%(12)。显然,美国在事实上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美国民族关系的社会目标一直是锻造一个具有统一认同的美利坚“民族”(nation),强调国家认同而淡化族群认同,具有明显的同化论色彩。美国学者戈登(Milton M.Gordon)认为美国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3):第一是“盎格鲁—撒克逊化”(Anglo-conformity)阶段,自英国向北美移民开始直至20世纪初。其政治和文化导向是明确以强化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传统文化为中心,是“单向”的“同化主义政策”。第二是“熔炉”(Melting-pot)阶段,自20世纪初直至50-60年代。其理论是“美国是上帝的坩埚,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个种族在这里得到冶炼和重铸”(14),结果是大家都变成“美国人”(American)。这是一种“相互融合型”的“同化主义”政策。第三是“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阶段,自20世纪50-60年代至今,主张承认并容忍“亚文化族群”的存在。宁骚认为,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与熔炉论相对的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从未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美国政府也没有公开申明接受多元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仅仅是对传统的同化政策的一种补充”(15)。
3.民族参与政治的途径
由对“民族”的不同界定和对不同的民族关系社会目标的追求,引出了“民族”参与政治的不同途径问题,亦即:在国家政治中,“民族”符号是否具有重要性?是以何种方式被表达出来?笔者认为,在中国,“民族”是以群体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而在美国,公民只以个体身份参与国家政治。这种“群体—个体”的不同取向,正是“民族”参与政治的不同途径。
在中国,民族既是一种被赋予的个人身份,也是一种法定的群体身份。首先,个人的民族成分是由他的血统确定从而是他无法选择的,这是一种被“赋予”的而非主动取得的“身份”,建立在“客观条件”而非“主观认同”的基础上。其次,“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国所有关于“民族”的法律条款,基本上其指向对象都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民族”,而非公民个体;当然,法律条款的落实往往还是要落在具体的公民个体身上。但在中国的政治中,一个公民个体 (尤其是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政治的时候,不仅作为他个人,更多的是作为他所属的“民族”的代表而出现的。这在新中国的民族干部政策中表现最为明显:民族干部配置不是个体性行为,而是个体背后的“民族”群体之间的资源配置问题。新中国在机构设置上也专门配备有民族工作部门,负责协调、组织国家和地方的少数民族工作,更好地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中国各少数民族群体实现其政治权利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
在美国,公民只以个体身份参与国家政治,而不带有“民族”背景。“在美国,民族特性不容许成为享有领土主权或政治上单独享有任何管辖权的一种手段。不容许它变成政治组织的排他性手段(即不容许成立以民族原则为基础的政党——引者)。政治权利属于个人而非民族群体。”(16)这样,美国式的平等是属于各个族体的公民个人的平等,而不是各个族体的平等。例如,“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的组成上,都不实行民族配额制或民族代表制,这样就能够使在各个方面都拥有优势的种族和民族群体近于垄断性地占有各级政府的职位”(17)。这样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显然是不公正的。美国也有若干与民族工作相关的机构设置,如党派中的民族委员会,参议院中的印第安人委员会,众议院中的资源委员会(管理土著人事务),联邦政府中的公民平等权利委员会,内政部的土著人事务局,教育部双语教育办公室和印第安人教育办公室,卫生部印第安人健康福利司等(18)。但各机构之间没有统一的行动原则和协调机制,其工作范围也没有涉及所有的弱势族群。
三、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及其贡献
综上所述,新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前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多民族国家不仅表现为一种社会现实,而且也表现为一套系统的政治理念。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总结多民族国家相对于民族——国家而言的特殊之处。
1.多元与二元:世界观的差异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的“天下”是一个民族与文化多元论的世界观,一个多种族类的多元化的“天下”正是古代中国所追求的、符合“天理”和“道”的政治模式。这种传统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的契合所引出的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亦即多民族的国家模式。而这种多元模式与当今世界强调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是一致的,与国际社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多元主义”也是一致的。民族与文化的多元论才能达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境界。
欧洲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强调“我”与“他”的二元划分。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必然导致“民族”要求的是属于“自己”的独立领土和主权,也就是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民族——国家”。强烈的二元化观念则将导致每一个民族都具有咄咄逼人的态势,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2.多民族与同质化:国家理想型的差异
世界观的差异导致了国家理想型的差异。事实上,“民族——国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模式”,这种理想模式是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即追求与“民族”(nation)与“国家” (state)界限的完全吻合,企图在国家界限内铸造一个完全同质化(homogeneity)的“民族”(na tion)。二战时的纳粹德国强调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和血统纯洁性,从而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到极致的一种恶果。在现实世界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纯粹的民族——国家类型。
新中国倡导的“多民族国家”模式是另一种“理想模式”,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关系,即:在统一的大国之内,承认各民族的差异及其平等权利。这种模式是一个“一体多元”模式:政治上的一体(国家)和文化上的多元(民族)。这实际上更为符合当前世界民族与国家的现实存在状况。
3.群体与个体:民族参与政治的途径的差异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是否承认“民族”的政治性。在中国模式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明确承认“民族”群体的政治合法性及其以群体身份参与政治的必要性。既然“民族”表现为一个“群体”,那“民族问题”就应该表现为“群体行为”或在“群体”层次上得以解决。新中国的“民族”政治就是让各民族都能够在国家政治里获得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代表和发言权。
在美国模式中,是否认“民族”的政治性,把“民族”推向私人化、非政治化领域。公民只能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不能出现民族化的政党。这实际上是牺牲了弱势族群的利益,助长了强势族群的政治垄断性。
如果说承认民族的政治性、民族以群体身份参与国家政治有可能会给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因素,甚至像前苏联那样导致国家的解体的话;则否认民族的政治性或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结果只能是牺牲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利益。任何选择都是有其弱点的,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关键是在明了自己的弱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有效地防止不良倾向的发生。
在今天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话语霸权和垄断局面,展现了另外一种国家模式的可能性。今天,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已经承认完全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只能是一个神话;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就像是“捆绑式销售”的商品,这种“不可分割性”是人为的建构而非唯一的选择。王柯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民族思想中,“不以国家为尺寸限制民族的构成,而是按民族的构成及其变化量体裁衣,制定和变换王朝国家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这种主从关系的设定,与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思想,以及国民国家的理论都迥然不同”(19)。这种传统资源在经历了近代以来与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观念、欧美式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理论的磨合以后,诞生了新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对世界“民族”与“国家”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注释:
①②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05-306页,第38页。
③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0。
④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⑤⑥朱学勤:《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新儒家政治哲学评析》[A],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C],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255-285页。
⑦⑧杨小云:《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⑨李德志:《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及联邦中央权力集中的特点》[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3)。
⑩[美]《华盛顿邮报》1994年4月17日;转引自戴德铮主编:《当代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11)(13)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第181-185页。
(12)(14)(15)(17)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2页,第555页,第563页,第549页。
(16)迈克尔·诺瓦克:《多元个性》[A];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549-550页。
(18)王铁志:《美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机构》[J],《民族工作研究》,1998(1)。
(19)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
标签:现代性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国家结构形式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