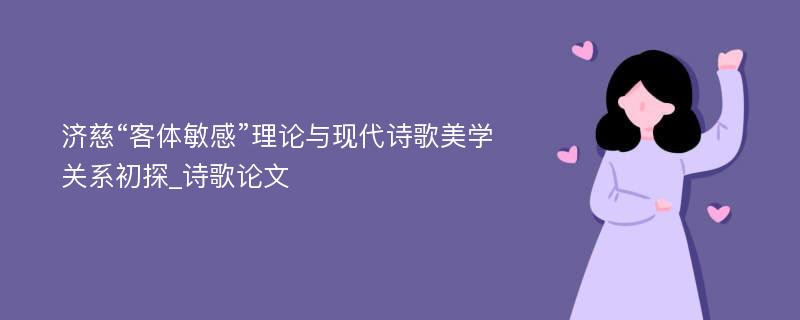
济慈的“客体感受力”说与现代诗歌美学的关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济慈论文,感受力论文,客体论文,美学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约翰·济慈(1795~1821)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一位重要诗人。然而,与其他浪漫主义大诗人有所不同的是,济慈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上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王佐良教授指出:“他们(其他浪漫主义诗人——引者)在吸取前人精华和影响后人诗艺上,作用都不及济慈。……他一方面是浪漫主义众多特点的体现者,有明显的十九世纪色彩;另一方面,由于他所面对的环境和他所要解决的思想和创作问题(经验的复杂与内含的矛盾,诗人的处境,诗艺的多面性,语言的限制力与可能性,等等)都是属于现代世界的。他又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注: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他认为工业化对当时英国田园式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济慈所思考的诗歌经验、诗艺、语言等问题使得诗人的作品具有现代特色,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特别是济慈在他的书信中提出的关于诗歌艺术的理论思想与现代诗歌精神与美学似乎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济慈的诗歌艺术理论中,有一个“后来的文论家无不注意的”“客体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说。许多评论家对这一思想都进行了分析。这里简单介绍两种:“1.济慈关心的是当时的美学核心问题:区分人们所说的‘客体’诗人与‘主体’或‘感伤’诗人。‘客体’诗人朴素地、并非个人化地表现事物,‘主体’或‘感伤’诗人按照诗人个人的兴趣、信仰、情感来表现事物显示出的样子。具有‘客体感受力’的诗人是‘客体’诗人。2.一首诗中,主体事物只要在诉之于‘美感’的艺术形式中展现就够了,它与脱离了诗歌去判断事物的真与假无关。”(注:《诺顿英国文学选集》(Ⅱ),诺顿出版公司1986年第5版,第863页。)我国的翻译家对这一术语有多种译文,以我寡闻,它们包括“消极感受力”、“消极能力”、“消极的才能”、“客体感受力”,等等。这些不同的译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对这个Negative Capability有着各自的理解。应该说,各种译文和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如何理解诗人提出的主客观关系?如何认识美与真的关系及其深刻涵义?这一思想与现代诗歌艺术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对“客体感受力”这一思想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下面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思想提出一些看法。
一、主体与客体相交融的新境界
济慈在写给弟妹的信(1817年12月21日)中谈到“客体感受力”时这样讲:“我和戴尔克讨论了一些问题,没有争辩,有好几样东西在我的思想里忽然合拢了,使我立即感到是什么品质能使人有所成就,特别是在文学上,莎士比亚多的就是这种品质。我指的是‘反而感受力’(引者按:即‘客体感受力’),即有能力经得起不安、迷惘、怀疑而不是烦躁地要去弄清事实,找出道理。……对一个诗人来说,美感超过其他一切考虑,或者说消灭了其它一切考虑。”(注:转引自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3版,第316页。)这段话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有能力经得起不安、迷惘、怀疑。这包含着诗人应该体验外部客观世界的动荡在诗人心中唤起的复杂、多层、不安的感受这样一层意思。这种感受并非诗人的主观臆想,而是与客观外界相交融的结果。第二,不是烦躁地要去弄清事实,找出道理。这里,重要的不在于用理智去分析,去判断,而在于感受,在于体验。第三,美感超过其他一切考虑。美感是最为重要的。“真”是通过美感来体现的。
首先,从济慈的诗歌作品与他的其它书信来分析,我认为济慈在这里所说的不安、迷惘、怀疑并不是诗人主观的想象或凭空产生的感觉,而是客观外界作用在他心灵上产生的结果。这里就有一个客观外界与诗人主观世界的互相关系问题。济慈认为,诗人应该深入到客体事物的内部去体验,去感受。济慈在其它书信中多次表露过这样的观点,即诗人没有“自我”(identity)。如他说“关于诗才本身……我要说它没有个本身——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它没有特性——它喜爱光明与黑暗;……诗人在生活中最无诗意,因为他没有一个自我,他总在不断提供内情,充实别人。太阳、月亮、大海、有感情的男人女人都是有诗意的,都是有不变的特点的——诗人可没有,没有个自我——他确是上帝创造的最没有诗意的动物。”(注:转引自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3版,第317页。)如果没有认识到济慈对诗人深入到客体事物中去感受这一点极为重视的话,理解他的“诗人没有自我”是困难的。济慈在这里强调诗人隐去自我,将自我融入客体当中,这表现了一种新型的物我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相溶合的关系。“他曾说他可以深入到一只麻雀的性格中去,同样‘在瓦砾中啄食’”(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一方面,他认为诗人不应该与外界事物相隔离,让自我的情感无限制地膨胀,使自我最终失去依托,成为空洞的、狭隘的自我。另一方面,他也否认诗中的物与诗人毫无关系,是绝对外在于诗人的客体。任何客体,都是诗人眼中的客体,是诗人内心中所认识所体验到的客体。这样,诗人的自我就是与外在的客体世界相通的。诗人的情感通过客体这个媒介来表现,来抒发,而这个客体无不感染上诗人的情感和灵魂。不安、迷惘、怀疑便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发生的。
济慈的六首颂诗(包括《秋颂》)都很好地体现了诗人的主观与外在的客观的交融。有评论家说:“他的五大颂诗探索了济慈不断增长的信念,即他必须在想象中成为他所沉思的事物。”(注:玛格丽特·斯多尼克(Margaret Stonyk):《19世纪英国文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在《夜莺颂》中,他幻想与那鸟儿一同飞离现实世界的同时,自己也化作了夜莺。在《秋颂》中,他深入到有生命的秋天中去,用秋天的眼睛来看大自然。《希腊古瓮颂》更是极好地体现了这种物我交融的关系。诗人歌咏了绘在一只希腊古瓮上的画。这一幅幅画面在诗中五彩缤纷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十分迷人。然而,这些画面既是被客观地描绘在古瓮上面,又是诗人眼中、心中的画面,诗人在每一幅画中都倾注了自己的思考、情感和想象。如,诗中的第二节是这样的:“听见的乐曲是悦耳,听不见的旋律/更甜美;风笛啊,你该继续吹奏;/不是对耳朵,而是对心灵奏出/无声的乐曲,送上更多的温柔;/树下的美少年,你永远不停止歌唱,/那些树木也永远不可能凋枯;/大胆的情郎,你永远得不到一吻,/虽然接近了目标——你可别悲伤,/她永远不衰老,尽管摘不到幸福,/你永远在爱着,她永远美丽动人!”(注:此处所引及下面两处所引诗均为屠岸译文。)画中的少年在吹奏风笛,这乐曲是听不见的。但在诗人看来,这听不见的乐曲比能够听见的更美妙,更动听,因为这乐曲是对心灵吹奏出的永恒的乐音。只有心灵能够领会,只有心灵能够理解,只有心灵能够感悟。这里,诗人是在通过描述画面来抒发蕴藏在心底的强烈情感。他对无声的旋律的认识甚至带有某种哲学意味:少年的永恒的歌唱,树木的永远青葱,少女的永不衰老的美丽,情人的永不消失的爱情……这一切都同时记述了画面的动人场景,又表达了诗人的深刻的哲学思考和难于抑制的对永恒的美的赞叹和追求的愿望。希腊古瓮是客观的物,古瓮上的画面也是客观的物,而此时客观的物已不再是客观的,它是诗人心中的“客观物”,主观已经化入了自然的物中。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的物我交融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济慈之前,也有通过咏物来抒发诗人情感的诗歌作品。但是,济慈是首先在理论上认识到应该将自我沉入客观物中,物我应该交融,并在创作实践中尽力做到这点的诗人。一般传统诗歌作品要么重物,即采取写实的或记叙的手法,很少加进诗人个人的情感色彩;要么重我,即以抒发诗人的个人情感为主。多数浪漫主义诗歌作品就是重我的。然而,现代派诗歌作品却比较注重物我之间的融合关系。比如意象派诗歌就直接把诗人的“我”的感受与物的表象重叠起来,构成一个新颖别致的意象。郑敏教授在谈及意象派诗歌中的主客观问题时说道:“在20世纪初,首先由意象派用意象的理论来打破物我的割裂,企图将我与物在意象里有机的结合起来。……一个意象既非单纯的主观内心经历,又非单纯的客观真理。它是二者突然合拍,结合在一起的复合体”(注:郑敏:《英美诗歌戏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现代派诗歌从意象派开始,一直到当代诗歌作品,有很多都注重诗人个人的内心情感与外在客观世界的交融,有时甚至是重合。二者的融合在一些作品中表现得如此紧密,以致沟通它们之间的连接线也被砍断,使得读者有时难以辨别诗人究竟是在描绘外在的客观世界,还是在表述诗人自己的情感。这也是现当代诗有时较为费解的原因之一。然而,物我之间的交融毕竟是诗歌创作中的较高境界。“物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不容割裂。‘我’的形成由空白到充满思想感情是由于‘物’的影响,‘物’或客观世界的存在也经常由于‘我’对它的改造、干扰、影响而发展、变化。因此,在物中有‘我’的思想感情,在‘我’中有‘物’的力量和影响。纯我、纯物是不存在的,主客观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两者相矛盾而又相依存。”(注:郑敏:《英美诗歌戏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济慈所提出的,将诗人自身融入客体去认识、体验、感悟的思想,与现代诗人提倡和实践的主体钻入客体世界去感悟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他的思想对后来的意象派诗歌是有过影响的。
其次,济慈强调诗人应有能力经受得起不安、迷惘、怀疑,这也就是说,外部客观世界唤起诗人内心的感受往往不是纯粹或单纯的,它是复杂的,多层的,困惑的,怀疑的。“济慈认为最丰富的人性在于能够体验强烈而冲突的情感的能力。”(注:玛格丽特·斯多尼克:《19世纪英国文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在他的一些诗歌作品中,他提出,真正的人应该能够感受矛盾的情绪。从浪漫主义诗歌的总体来看,复杂多层的情感其实在一些大诗人的作品中并不少见,但济慈在他的诗论中明确提出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表现了伟大诗人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感受力。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少都饱含着一种多层的和复杂及怀疑的意蕴。特别是在《夜莺颂》和《忧郁颂》中,这样的情绪体现得十分突出,他在快乐中寻找忧郁,在痛苦中寻求欢乐。即使是在歌咏永恒之美的《希腊古瓮颂》中也表现了一种内心的不安或不和谐的颤音,诗中以一连串的发问构成的第五节便是这样:“这些前来祭祀的都是什么人?/神秘的祭司,你的牛向上天哀唤,/让花环挂满在她那光柔的腰身,/你要牵她去哪一座青葱的祭坛?/这是哪一座小城,河边的,海边的,/还是靠山的,筑一座护卫的城砦——/居民们倾城而出,赶清早去敬神?/小城呵,你的大街小巷永远地/寂静无声,没一个灵魂会回来/说明你何以从此变成了荒城。”面对古瓮上的画面,诗人感到某种困惑:这些是什么人?他们在哪里?他们要去哪里?小城为何从此变得荒凉?等等。人群中还夹杂着牛发出的哀鸣。这一切都与整首诗的调子形成某种对比和反差,是一种不和谐的调子。然而,这种不安的情绪并没有破坏全诗的美感,反而使美感更加强了浓度和深度,使得这种美感更加丰富厚重了。
济慈所强调的诗人内心应有能力经受不安、迷惘、怀疑的观点,在现代派诗歌中得到普遍的承认。早在20年代,艾略特就指出:“诗人须变得越来越具有包容性,暗示性和非直接性”(注:T.S.艾略特:《玄学派诗人》,见《诺顿英国文学选集》(Ⅱ),诺顿出版公司1986年第5版,第2219页。)。这里包容性指诗人的思维和感受应该是多层的,复合的,有肯定,有怀疑,而非单一的,直线的,完全透明的。暗示性指诗人在创作中用独特的语言来提供读者自己去体会和想象的余地。20世纪的诗歌作品中不安、怀疑和否定的情绪几乎处处可见。这些情绪似乎是20世纪诗歌一个共有的特色。然而,不安或怀疑并非一种绝对的消极情绪,在不安和怀疑中必有所寻觅,有所追求,这也是一种充满生命的美感。20世纪的美学原则肯定艺术作品中的不安和怀疑因素。在这点上,济慈的思想洞察到了一种他去世百年以后的现代气息。
二、感性与理性的交融
济慈提出,诗人要有能力经得起不安、迷惘、怀疑,而不是要烦躁地弄清事实,找出道理。王佐良在解释这段话时这样说,其“主旨是清楚的,即诗人要经受一切,深入万物,细致体会,而不要企图靠逻辑推理匆忙作出结论。”(注: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3版,第316页。)这里诗人提出了逻辑与理性的问题。济慈所说的弄清事实,找出道理,就是要用某种依赖于理性和逻辑性的思维方法去对待诗歌创作。济慈主张诗人应该注重感性体验,注重联想,注重想象力,应该通过想象力、感觉和感情来写诗,而不是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写诗,他说道:“我深知心灵中真情的神圣性和想象力的真理性”,“我一向不能通过逐步推理来知道哪件事是真实的。”“要能够靠感觉而不是靠思想来过活,那够多好!”(注:周珏良译:《济慈论诗书信集》,见《外国诗》(第一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等等。诗人要靠近感觉,而非通过推理,来写出好的诗歌作品,而且,这种感觉是深入到客体内部去感受而得来的感觉,这是济慈“客体感受力”的另一方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济慈认为在诗歌创作中只要有了这种感觉就可以不要深刻的思想了。有些评论家认为济慈的诗歌作品多强调感官快感,是放纵感觉的产物,而忽视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深刻思想,如有些人认为“济慈没有心智”,“诗人似乎是无意识和无意志的工具,被各种偶然的印象驾驶着”(注:奚晏平:《济慈及其‘夜莺颂’的美学魅力》,《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事实上,在济慈看来,深刻的思想正体现在诗人的感性体验中。只有一方面抓住了想象力、感情和感觉,另一方面抓住了思想,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诗歌作品。他讲道:“我认为诗之能动人在于美好充实而不在于出奇立异。要使读者觉得是说出他自己的最崇高的思想。”“我指的是一方面具有想象力而同时又能仔细控制想象力的产物的那类性格。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既靠感觉也靠思想生活,年龄渐长,他们就需要具有好深思的心情。”(注:周珏良译:《济慈论诗书信集》,见《外国诗》(第一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5页。)从这些话当中,我们可以感到济慈所追求的是那种将感觉融入到思想中,而将思想化为感觉的艺术境界,感到他的“感官永远伴着抽象”。
他的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感觉与思想交融的例子。还是以《希腊古瓮颂》为例:“你——‘宁静’的保持着童贞的新娘,/‘沉默’和漫长的‘时间’领养的少女,/山林的历史家,你如此美妙地叙讲/如花的故事,胜过我们的诗句;/绿叶镶边的传说在你的身上缠,/讲的可是神,或人,或神人在一道,/活跃在滕陂,或者阿卡狄谷地?/什么人?什么神?什么样姑娘不情愿?/怎样疯狂的追求?竭力的脱逃?/什么笛,铃鼓?怎样忘情的狂喜?”诗一开始,诗人就通过他具体的感受和想象来暗示读者:艺术是永恒的,是不朽的,艺术经过时间的考验和磨难,始终展示着它的纯美,它的光亮。这个思想并非理智的推演或判断。这里,并没有出现永恒、不朽这样的词句,但读者通过体验诗人的心灵感觉可领悟到这一思想。诗人一边在观看这只古瓮,一边任凭想象力飞驰,进行一系列的猜想——并非靠推理,而是靠感情的位移,先是新娘被暗指艺术品,她属于“宁静”,保持着童贞,然后艺术品被诗人想象为历史学家。古希腊的许多历史恐怕有不少是由这些“历史学家”唤醒的。一连串的发问一方面体现了诗人的思绪在跳跃式地面对古瓮飞腾,一方面也体现了时间的跨度在这里已经消失了。想象力的自由驰骋说明时间的跨度已经被永恒的美所征服。这个深刻的思想是与诗人的想象、猜测与思考溶合在一起的。《夜莺颂》体现了他对丑恶现实社会的批判。《忧郁颂》中丰富的意象与大胆的思想交融在一起,表现了一种对强烈的矛盾感情的体验。济慈曾表示,“他早期把感觉体验放在理性思考之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认识到他需要思想与哲理,并在感觉中研习哲学思想。罗伯特·希里奇斯指出,济慈并非沉溺于美感当中,他的头脑中充满了“神秘的重担”,关心着人类的痛苦与人的生活。他的这种理性的思考是与他的感官印象分不开的。
20世纪的诗歌从理论到实践都重视感觉与思想的交融。艾略特曾说,玄学派诗人能够“从思想中直接产生出一种感觉的领悟,或把思想重造为感情。”这里,感觉或感性认识与抽象的理性思想是分不开的。诗人在他的敏锐而细腻的感觉中注入了深刻了思想和巧妙的思辨。诗人的思想不是概念化的,或者理性化的,它们都是经过了感觉所催化的产物,是感觉化的思想。艾略特推崇玄学派诗人的这种“把概念变成感觉”,或“把观感所及变成思想状态”的诗歌艺术。他提出要让思想拥有玫瑰花的香味。艾略特的诗歌主张及诗歌创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现代派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不少现代和当代诗歌中渗透着理性与感性的交融。尽管艾略特批评弥尔顿以后的诗歌直到20世纪为止越来越趋于“感受力的涣散”,但我们在济慈的诗歌作品中,以及他的关于“客体感受力”的思想中,不难感受到一种与现代诗歌艺术相通的精神,即感觉与抽象理性思想的融合。济慈提出诗人没有自我,同时又认为诗歌必须在诗人的感性体验中表现诗人的抽象理性思想,这些想法看似矛盾,其实,这恰恰体现了济慈对诗歌艺术进行思考的深度。他提出诗歌中诗人要隐去自我,并不意味着诗歌要完全客观地描述或反映外在世界。恰恰相反,隐去自我的目的是要在物我交融的状态下捕捉诗人的感觉体验,而这种感觉体验正是某种理性思想的具体体现,这样,这个感觉或感受也升华为感悟或顿悟。
三、关于美与真
济慈的“客体感受力”所涉及的第三个问题是美与真的问题。在《希腊古瓮颂》中,他提出“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一著名的带有哲学思考的论断。不少批评家受到这一诗句的感染和启发,纷纷对此进行分析和阐述。然而,济慈在这里所提出的美究竟是什么?真又是什么?美与真的统一其意义何在?这仍需要我们进行一番探讨。
“美即是真”中的美是否仅指感官所体验到的美?是否仅指一种古典式的和谐统一的外在美?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些评论家认为济慈的作品沉醉于感官快感及由此带来的美感。这似乎不够全面。济慈所提出的美应该包括他的感性的美和对现实世界痛苦的沉思所产生的美。现实世界给人更多的是痛苦与失望,然而他此时能够将痛苦转化为美学意义上的美,悲剧意义的美。比如。《夜莺颂》中就有对丑恶的现实生活的描述,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痛苦中的悲剧美。罗伯特·布里奇斯说:济慈的诗歌并非崇拜通过味觉、触觉、视觉和听觉可感知的外在美,他的目光落在悲痛与欢乐的美感上,这是有关道德与精神的美。这里,道德与精神的美可以指济慈对现实世界的忧患意识,对矛盾与复杂情感的审美体验,等等。这种美的观念超出了古典美学追求和谐一致的外在美的局限。不少人认为济慈是古典美学的追随者,信奉古典美学原则。这恐怕只是问题的一面。实际上,他在追随的过程中,也在突破。现代美学承认美学意义上的矛盾与丑,甚至恶。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便是例证。虽然济慈的美学观与此有距离,但我们从中亦可见到某些现代美学最初的影子。
这种美在一定意义上规定着他所说的真。济慈在讲到“客体感受力”时曾说过:“对一个诗人来说,美感超过了其它一切考虑,或者说消灭了其它一切考虑。”“客体感受力”的内容之一就是诗人所体验到的美感可以涵盖一切。在他看来,美似乎比真更为重要,只要抓住了美,似乎就抓住了真。
济慈十分重视想象力创造的美。他曾说:“想象力捕捉到的美的也就是真的。”(注:转引自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3版,第264页。)他的想象力捕捉到的美更侧重于幻觉中或直觉中产生的美的意境。这种美更贴近心灵的感应,潜意识中的感悟,具有超越现实的、超越意识表层的审美境界。这种美所规定、所体现出来的真更强调心灵的真实,感受的真实,是心灵在与外界碰撞中产生的想象的真实,也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它不同于仅仅反映客观,认识客观,而是某种真诚的心灵碰撞之后的感悟或升华。“真即是美”的论断在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会发出奇异的光彩。
古希腊以来的美学与哲学都是以模仿、再现或者表现客观事物的实在性为其根本的。古典美学提倡的形式美、和谐美、单韵美等等,都是为了体现这种客观实在性,客观实在性就是唯一的真。现代美学观与古典美学观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现代美学观突破了艺术应单纯反映客观实在的功能。浪漫派美学注重抒发诗人的个人情感,而不注重反映客观。现代美学则将美学意义上的美与真的概念大大延伸。丑的东西可以被转化为美学意义上的美,这在现代美学中是很典型的。古典美学认为不美的,例如那种不和谐、不对称、追求反差效果、突起突落效果、或运动变化效果的艺术,在现代美学看来则是美的。真也不仅仅指客观真实。一个变形的现代雕塑并不能反映客观真实,但它所蕴含的力量,美感,或者动感中孕育的生命力使其具有艺术的真实,也使这作品充满了客观实在所没有的美。济慈的关于将痛苦与丑转化为美的美学观,以及这种美学观规定的真和想象力捕捉到的美体现出的真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这种现代美学的走向。
当然,济慈是浪漫主义诗人,他身上体现出许多浪漫主义的突出特征,关于美与真也有不少典型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如真也指自然的、天然的、不造作、朴素等意思,也有天真、返朴归真之意。他的美也包含着感官体验到的美。他的美也指最高理想,或者说他的最高理想就是美。济慈那短促的一生经历了许多人间的不幸。父母早亡,兄弟病逝,经济拮据,婚姻无望,自己的诗歌才华得不到承认,而且招来评论界的恶毒攻击和漫骂,等等。尽管如此,济慈始终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美就是他创作的最终目的,是永恒的。这些是与他的浪漫主义理想分不开的。然而,我们从他的理论中仍能看出某些与现代诗歌或艺术美学的联系,这更体现出济慈诗歌和诗论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诗人,济慈能够凭借自己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洞察到诗歌理论复杂而深刻的层面,并将这些理论观点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去,这说明济慈的理论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它对开创现代美学具有一定的意义。
标签:诗歌论文; 美学论文; 希腊古瓮颂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夜莺颂论文; 约翰·济慈论文; 英国诗史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想象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