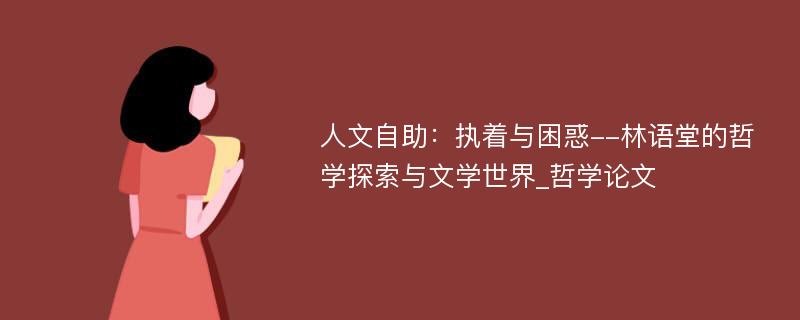
人文自救:执着与困惑——林语堂的哲学探寻与文学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惑论文,人文论文,执着论文,哲学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对于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许多中国现代作家来说,“矛盾”的体验于他们并不陌生 。在《八十自叙》里,林语堂就曾云:“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 。”这绝非矫情之语。确实,《语丝》时期的林语堂,遵从个性,未依门户加入《现代 评论》,而紧紧追随周氏兄弟,以凌厉的笔锋直指中国国民性之弊端,甚至在疗救问题 上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全盘西化之法——“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 气太重,若惰性,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 则弟以为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注:林语堂:《给玄同先生的信,林语 堂文集》第9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而当历史经过一段时间的沉 淀,尤其是当他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文明之困境(诸如物质主义的压迫,人们心灵的紧张 和压抑等),站在西方的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林氏又从儒道释互补的哲学中,从中国百 姓的日常生活中大书其文化特质之优越,用作医治西方人文困境之良方,前后文化观的 矛盾和断层是显见的。然深入文本,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矛盾,所谓的不一贯更多地 是来自话语表述的层面,在矛盾的语词下实则一直流淌着其文化哲学观的主流,那就是 建立在健全活泼的生命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哲学观。以此反观,若奴气、惰性、敷衍终非 合于健全人性,因其萎顿、虚伪而斥之,而西方的物质主义之压迫因其悖情则以中国文 化中健全的人文精神以补之,如此,一破一立,而构成了互补自足的哲学世界,体现其 素朴的世俗关怀视角。当然,其人文主义哲学观也面临着种种困惑、危机直至最后的后 拨。而经由作家的哲学探寻之轨迹,我们也就能自然地理解其文学世界(包括其小说、 散文、传记等领域)中的种种文化“情结”及其嬗变。
一、人本位的近情哲学
我们知道,在西方,人文科学的定义出现得很早,但其发展却是较为缓慢的。自古希 腊至康德,科学主义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这自然与欧洲重智、重知识的哲学传统有密 切关系。古典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是世界的本源问题,从而使经院哲学带有浓厚的本体 形而上学色彩,人性哲学始终未能构成主流而只是内在于其间。及近代,哲学家们的关 注焦点转向了认识世界,出现了以“理性万能”为主要特征的主体形而上学,而这同样 表现出对生动丰富的人性的淡漠。
对于西方这一经院哲学的传统,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显然也深深地体会 到了,但他的回应姿态却是独特的。有别于对经典,对传统的郑重其事,他一开始采取 的便是大胆的怀疑与解构。在《生活的艺术·自序》中,他发出了挑战性的话语——“ 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在他看来,我们的学问、 哲学是太过复杂和严肃了,而只有把哲学从繁复、玄虚的形而上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回 归简朴,这才是文化的最健全的理想。与此相对应,他选择了以素朴的世俗人生为其落 脚。在《谈中西文化》一文中,林以对话体的形式借人物之口说道:“常人谈文化总是 贪高鹜远,搬弄名词……如此是谈不到人生的,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剥离了 文化绚丽的外壳,文化回归到了真实的人生。而文化既关乎人生,就不能不以人情为参 照。事实上,林氏心中的人首先或根本上是取自生物学意义上的芸芸众生,这在散文《 生活的艺术》中清晰可见。在他看来,人无非都是猿猴的孙子,都不免一死,人的生活 也都受一个叫肚子的无底洞的影响。既然动物性对人生影响至深,人又何必羞于或无视 人的这一生存层面?因此,近情的人才是真实的人,也只有近情的态度才有可能产生宽 容的真正的文学。由此,在他的散文世界中,多的是对“假道学”,对“方巾气”的鄙 夷。同时,作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现了苏东坡、袁子才、郑板桥、金圣叹、李渔等 诸名士,在西方的文化资源中,发现了克罗齐的“表现学说”,作家的结论是:“文学 无新旧之分,唯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个人之真知灼见,亲诚至感,皆可传不朽。”(注 :林语堂:《论文》、《林语堂文集》,第10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204 页。)显然,这是作家的“近情”哲学观与他的“真”的文学观的互现。
而以此视角关注林语堂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很可以看出其倾情所在的。也许,林语堂 小说之最大缺陷在于作家主体的过多介入,老彭、姚思安、立夫……众多人物的背后无 不较显明地暗示着作家的人物定位和道德评价,而使其多少具有哲学代码的功能,甚至 放在其整个小说创作的背景中,显示出一定的类型化的倾向;但从另一方面看,则相当 程度上保留了其哲学和文学的互渗和互融。
不难发现,女性形象在林氏小说中的份量是很重的,然此处我尤感兴趣的是其同一小 说中的比照性女性组合。林语堂曾在《吾国吾民》一文中表示:“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 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如问他喜欢黛玉还是宝钗”,而我认为,看林氏之性情,只 要视其更倾向于木兰、牡丹还是莫愁、素馨即可。应该说,在《京华烟云》中,木兰和 莫愁都是作家所认可的女性形象,小说中的莫愁善解人意,圆融稳健,可谓传统儒家眼 中的理想女性,但事实上,在作家的心中,其理想并非莫愁而是木兰。他甚至明白地说 :“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作为妙想家,木兰更多地从其父姚思安的灵魂中感受 到了道家的仙风,洒脱自然,不拘一格。在感情上,她爱立夫,甚至以冒险的方式营救 立夫,但这并不妨碍她顺应家族和命运的安排嫁给荪亚,并共同幸福地生活;她爱荪亚 ,她也爱一切美的东西,甚至愿意为丈夫纳妾;她身为名门之女,却恬淡自如,过起居 家百姓的生活;出于天然母性,在痛失爱女后,她愿意全身避祸,但随时势之发展,她 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毅然追随政府,汇入革命的洪流。如果说以前和立夫相恋,她发 现了自我,而在抗战大潮中,她却融入社会。而无论丧失或发现,皆一派自然,顺乎内 心,顺乎成熟的历程,毫无矫情。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点上,获得了作家对这一人物的 偏爱!同样,小说《红牡丹》中,妹妹素馨也是一个善解人意,淑静内秀的女性,正如 作家所描写:“她是诲淫诲盗等章节删除之后的洁本”。但显然,林氏之兴趣在牡丹, 虽然在正统派视之,牡丹风流成性,丧失后数度追求男性——婚前情人金竹,堂兄孟嘉 ,诗人安德年,拳术家傅南涛,毫无传统女性的贤淑之美,而作家的内在情感是宽容和 认同的,甚而带有欣赏的意味。在他看来,追随内心而不压抑个性,这就是人道,而彼 此的身份是无足轻重的,牡丹最后恰恰在地位不高的傅南涛这儿找到不安灵魂的归宿, 纯属内心的召唤。在以“一男多女”为主要模式的言情类小说中,《红牡丹》是大胆率 真的,虽然由于过多地偏于人性的自然,抹去了对主人公的道德评价而失之于单薄。其 他的如丹妮,柔安等发展中的女性形象,虽皆有诸如多重恋爱、未婚先孕等历史,但同 样,作家的重心在其自然天性而给予极大的同情和认可。可以说,在林语堂的小说世界 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最为集中而深刻地蕴涵着作家的人文哲学。其中,林氏表现 出对消解完美,回归自然天性的极大热情,体现出真诚的人本位的世俗关怀走向。
二、素朴的文化自救
卡西尔在《人论》开篇指出:“在哲学史上,怀疑论往往只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的 副本而已。借着否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真实性,怀疑论者希望把人的一切思想都投 回到人本身的存在上来。”林语堂正是立足于普通人的生存层面,怀疑并消解了完美的 人和完美的哲学体系的可能。在他眼中,圣者的境界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在完美的背 后必包含着对人性的压抑,而极端的宗教和哲学也必包含着欺骗与不合情理。人生即为 人生,精彩与无奈,欢乐与痛苦,美好与丑陋共存。另一方面,面对这种不完美的人生 ,林氏并未轻易地走上悲观之路,而代之以达观的理想。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他 写道:“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 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迁人 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正是合于这种观念,林语堂在其散文 世界中大谈幽默。在他看来,幽默意味着同情和宽容,幽默意味着发现人类的愚昧偏执 而并不鄙夷它,幽默正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达观。而将此种观念在其作品中得到深透传达 的便是《苏东坡传》。事实上,传记中的苏轼更确切地说是林语堂心中的苏轼。在作品 开篇,林就直言:“我们只能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以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 我了解,是因为我喜爱他。”可以说,苏东坡一开始就作为作家的精神知己而出现。因 此,实质上,传记具有了另一方面的参照意义,那就是从中观照林氏的人生哲学。苏轼 因诗屡次遭贬,但始终保持达观的心境,思想的快乐,这是林心向往之的。苏轼精通哲 理,深究儒学,珍惜生命,热爱自然,在入世和出世之间,他总能凭理性的克己获得精 神的和谐,凭生命中健全的浩然之气抵挡住世间的风雨,真正实践了无须离开社会而保 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林语堂从苏轼身上看到了人类于社会之中实现文化自救的希望!事 实上,关于这种文化自救,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也有一段表述:“只有那种合理 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种温暖的、朝气的、情感的、直觉的思想,跟着同情混起来”“ 只有去把我们的生命发展起来,和我们的本能调和着,我们才会得救。”这和传记中透 出的理念显然是一致的。这种正视人生的不完美,致力于通过矛盾的调和,生命的复苏 ,幽默的滋润,以达观积极的态度来拯救人类的思路,跟马克思的从经济角度解决人类 困境显然是殊途的,而更多地带有内省层面的理想主义的文化论色彩。
在我看来,林语堂在文体中的这种文化自救意识,这种对达观精神的信心背后是对中 西文化中不同的人文哲学观的自然选择和整合。从传统文化的源头看,林氏更多地汲取 了孔孟的儒学(非经程朱改造后的儒学)和老庄的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当然,佛家的悲天 悯人的思想也为他所认同,但对其脱离凡尘的过于悲观虚无的一面则不取)。这里,一 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是孔子和孟子在林氏笔下都被戴上了温情的面纱,以一个普通人 而非圣人的形象来到了读者面前。在《论孔子的幽默》一文中,林称孔夫子为“一多情 人也”,首先还孔子以做普通人的权利,而孟子的“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 舜”之说更是彻底消解了圣人和常人之间人为的等级差别。既然人心类同,人性本善, 人的世俗自救则成可能。对于儒家学说,有些学者认为其缺陷在于缺少超越性,或只有 凡俗而无哲学。有些学者则肯定其化凡俗为神圣的价值,如当代学者杜维明在《现代精 神与儒家传统》一书中就认为儒家的精神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其终极关切是在凡 俗中创造精神理想,“体现的是一种内在而超越的精神价值。”对于林语堂来说,似乎 也倾向于接受并汲取儒家哲学中朴素的人文气息,希冀在社会中寻求道德理想的实现。 由此,我们视其小说中人物的成长或自救(如丹妮、素云等人物的叙写),就不难理解作 家的内在哲学关怀。
如果说儒家影响林语堂的是将世俗中自我完善的哲学观引入其文本创作,老庄学说则 更多的是神秘性和平民性兼具的天道观的影响。林不信完美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不用上 帝而依自救,但对其心中的宗教和“上帝”,林在散文《生活的艺术》中自有一番解说 ——“中国的异教徒都是信仰上帝的,……其最常见者就是造物主……他以为‘委心任 远’乃是最虔诚的态度和宗教信仰,而称之于‘生于道’”。在林语堂看来,在愈来愈 广阔的宇宙面前,人自然起敬畏之感,而明智的态度则是走广义的神秘主义,即尊重天 地之秩序,一切任其自然。同时,林深信道教的“天理循环”,而这种循环又和生物学 意义的自然循环是相通的。既然一天有日出和日落,一年有季节的更替,一个人有生长 和腐蚀的内在循环,天理也自有其彰显的时候。
顺应天理,天道循环可以说是林语堂对老庄之道,造物之道的一己理解,由此,他对 世事有了通脱达观的看法。在小说《京华烟云》中,作家借姚思安之口在故事开端就显 露了这种思想:“孩子,……物各有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永远占有一件物品 ,拿现在说,我是主人,一百年后,又轮到谁是主人呢?”既然历史都是流动的,循环 的,又何必太拘泥于眼前的得失?姚在云游前对子女说的一番话亦是这种自然之道的阐 述:“一读庄子,你们就会明白。生死、盛衰是自然之理。……虽然依照一般人情,生 死离别是难过的事,我愿你们要能承受,并且当作自然之道来接受。”在林语堂看来, 顺应了人生的节律,坦然面对荣辱盛衰,每一凡俗之人都能获得诗样的人生。同时,天 道循环的认同使作家对“恶”之消亡有一种近于天真的自信。就他所处的抗战现实和二 战现实而言,他早就断言法西斯势力的最后结局;在小说《朱门》中,杜家主人杜方陵 父子违背天道,自私残忍,林毫不心软地给以遭报应、不善终的结局。这里,显然有简 单化的倾向,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老套,但背后自有作家的哲学支撑。
汲取儒家的向善自救和道家的天道自然的汁液,林语堂初步完成了处社会之中获内在 超越的自足的哲学建构。出于这种人本位的朴素的世俗哲学,林语堂同时从西方文明中 找到了他的精神知己。当然,对于西洋哲学中的经院哲学传统,林基本上是否定的,他 所取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生命哲学。在《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中,林首先指出中西 哲学之歧在于中主直觉,西主逻辑,其着重推出的则是哲学家勃莱利和柏格森,前者重 视情感在哲学上的地位,后者独创知觉与逻辑对立之说。实质上,林之推崇两位是借这 种重生命、重感觉的哲学与其近情的人文哲学的精神类通,找到他的哲学支柱。因此, 在文学主张上,他抛弃了白璧德而借鉴了克罗齐的表现学说;在对具体作家的评价中, 多次盛赞惠特曼,认为其与人生相接近,保存了对人类平民的博爱与信心。其他被称赞 过的如Throrean,Emerson等,多为荡漾着生命激情的哲人。正是从对中西文化传统的整 合这一视角,我们不难理解,在其驳杂的文学复调中,立于人间的世俗超越成为其不断 复现的主旋律。
三、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的背后
前文已叙,林语堂自称是“一团矛盾”。确实,他的一生都在寻求内心矛盾的平衡, 寻求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归依。经过多年的探寻,林氏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西方的生命 哲学中找到了契合点,从而糅合为以普通人为本位的近情的人生哲学;同时,这种哲学 因其对宗教和经院哲学的解构而更多地带上了文化自救的积极意义。林语堂自己也承认 “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 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注:林语堂:《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林语堂文 集》第9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444~447页。)这种人文主义的色彩则强劲 地贯穿于其文学作品的叙写中。然而综观其一生的探寻,人文主义是其主旋律却非尾声 。经过了一段“性灵上充满震惊和环险的旅程”,(注: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教 徒绪言》,《林语堂文集》第10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482~486页。)林 语堂最终还是回到了基督信仰。在基督这儿,他声称:“我不再询问有没有一种能使那 受现代教育的人得到满足的宗教。我的探寻已告终结,我已回到家中了。”(注:林语 堂:《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林语堂文集》第9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年,第444~447页。)这一转变颇耐人寻味,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次心灵探险“充满了疑 惑、踌躇、叛变及渴望返航的威胁”,(注: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绪言》, 《林语堂文集》第10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482~486页。)其间的转变固 然有多重合力的作用,而更多的是林氏对人文自救哲学的困惑和这一哲学的最终败退, 实质上则寓含了这一哲学本身所隐藏的内在危机和缺憾。
这种危机感在《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一文中已大略阐明。林氏曾云:“观察20 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现在深信人文主义是不 够的”。林氏把现实的问题归为不信神所致,仍是书生之论,但他意识到人文主义是不 够的,乃是对他过去对人文主义的价值认识的纠偏,意味着过于强调通过人的修养、适 性、达观来超越现实丑恶之策略的危机。事实上,这一危机在他大力提倡幽默文学时已 悄然埋下。幽默这一概念内涵极其开阔,既可指一种文学笔调、文学观念,亦可指人生 态度、行为态度。在林语堂这儿,各个时期各篇作品所涉的幽默也各有侧重,但有一点 是基本明朗的,那就是幽默在文化自救哲学中的特殊地位。林氏曾在30年代的《论幽默 》中(上中下篇)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所借用的理论是麦烈蒂斯的《喜剧论》——“我 想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及俳调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的标准,是看他能 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此语讲的是喜剧,林氏悟的是幽默。虽有偷换概念之嫌,但足 见幽默的崇高地位。在他看来,幽默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的滋润是无论哪国的文化、 思想兴盛的必要条件,无此幽默,则天下病态丛生。同样,在《生活的艺术·论幽默感 》一文中,林氏更是大胆分析了世界不和的病根,并开出了以幽默救治的处方——“( 幽默)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 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为了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 失了帝国”,他甚至更天真地设想:“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 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任何战争依旧是可以避免 的。”然而,美则美矣,到底是一文人的乌托邦,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未因此而稍停脚步 ,林语堂对此也已有觉察吧。事实上,鲁迅对此有着更清醒更理智的认识:“只要并不 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 注:鲁迅:《一思而行》,《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 73页。)
幽默亦好,克己达观亦好,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我们毋须怀疑它们的文化价值,但前 所论,林氏的这种人文自救更多的属于内省的层面,指向心灵的内在超越,而“内省向 我们揭示的仅仅是为我们个人经验所能接触到的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它决不可能包括 人类现象的全部领域。”(注:(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 8年4月。)世界的历史进程除了文化,还有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的交互作用。对文化寄 予单向的重任,显然要遭到失望的宿命。林氏从异教徒的撤退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想与现 实的矛盾不能再度平衡的结果。
其次,林语堂的哲学观中包含着积极中的消极和狭隘。应该承认,林氏哲学从道家吸 取顺其自然,天道循环的思想,相信邪恶终不能长久,正气必有张扬时,包含着素朴的 平民化的道德乐观主义,如前文所提及的小说《朱门》中的人物命运安排。但这种素朴 的伦理哲学观从某种意义上则是一贴心灵的安慰剂,现实绝非如此简单地以循环往复、 因果报应的形式出现,更何况,人生短暂易逝,消极的等待和适应带来的只是生命的萎 顿。林氏自己在后期也认识到了这点,对现实的困惑和失望使他对乐观的人文拯救产生 了深刻的怀疑,而佛教讲求来世,道家讲求宇宙法则,这些都未曾积极地触及现实,因 此都不能从根本上解答现代人的困惑。林氏的不满从他对老子的评价中可见:“道教的 先知老子确是一位杰出教师,可是他那回复自然和拒绝进步的本质对于解决现代人的问 题不会有什么贡献。”(注:林语堂:《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林语堂文集》 第9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444~447页。)林语堂也终于正视到了现代问题 的复杂性,并最终从人文拯救的坚信转为对基督的归依。对于其宗教选择的深层原因不 在本文的探究范围,作为一种信仰,我们也不急于评价其选择的价值或意义,但从一个 侧面,我们确实可以部分地触及到林氏的人文主义哲学观的欠缺诸如狭隘性和非现实性 。毕竟,在现代社会,人文是重要的一极,但并非仅此一极。基于这种认识,来构建面 向现实,面向科学时代的人文精神,可能更具现代性和开放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林语 堂的文学世界虽极具个人风格,但仍失之于形象的相对单一和思想的厚度不足,跟其哲 学观的内在结构应不无关系吧。
标签:哲学论文; 林语堂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林姓论文; 作家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