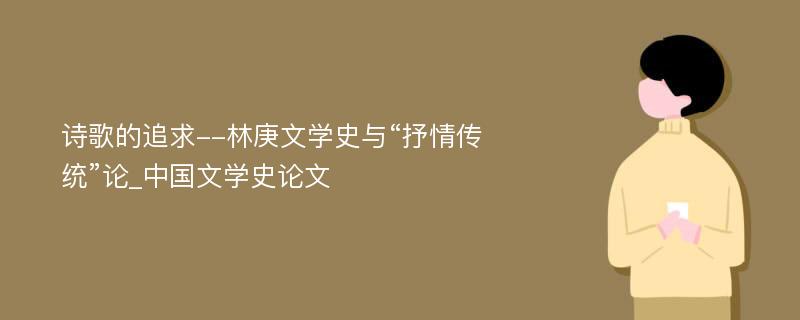
诗意的追寻——林庚文学史论述与“抒情传统”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诗意论文,抒情论文,论述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4-0143-07
一、“抒情传统”论述与林庚
最近,中国文学与“抒情传统”的研究又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去年(2009)四月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合办了“抒情文学史”研讨会,八月政治大学“百年论学”讲座举行一场由蔡英俊主持、颜昆阳和龚鹏程反思“抒情传统”论的对谈;王德威前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相关议题的系列讲座,在上海、苏州等地也作了巡回演讲,刚过去的十二月又在政治大学的“王梦鸥教授讲座”以“世变与诗心”为题讲了三场。同时,台湾大学即将出版由柯庆明和萧驰主编的《抒情传统之再发现》论文集,而我和王德威主编的《抒情之现代性》也将在短期内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本人亦在去年九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思勉人文讲座”、十月香港的“方润华学术讲座”,作过有关“抒情传统”论与中国文学研究发展史的关系的演讲。
在北京大学举行纪念林庚先生的研讨会上,我认为还是值得把这个课题的意义再作陈述;当然我的重点是林先生与这个论述的学术关联,并借此补充时论未注意的部分。
在大陆地区以外,讨论“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一说时,一般都会举出陈世骧(1912-1971)晚年发表的《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作为讨论的起点。这篇文章的英文原文“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是当年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任教的陈世骧于美国“亚洲学术年会”(1971)发表的讲话。其中译本出现以后,对台湾、香港以至于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影响极大。在内地,现今也有相当文章论及陈世骧;一般仅视之为美国汉学家的一员,以为其学说是域外汉学的一种表现。然而我想指出的是,陈世骧以及其“抒情传统”论述,其实与北京大学的学统密切相关;他和林庚先生(1910-2006)也是上世纪30年代北平文坛的同群。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陈世骧与他的老师艾克敦(Harold Acton,1904-1994)合力完成中国现代诗的第一个英译选本《中国现代诗选》(Modern Chinese Poetry),当中收入林庚先生的诗最多。①陈世骧在晚年接受访问时提及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说林先生是“我的同学”,②其实二人分别就读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陈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林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但相信二人来往甚多,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共同活动。我在《“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政治》已有交代。③以下我想就林庚先生的文学史观和陈世骧等后来发展的“抒情传统论”稍作系联辨析,以见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流向和轨迹。
首先让我简单交代相关论述产生的背景,并对“抒情传统”的概念略作勾勒,作为下文讨论的根据。
二、“中国文学传统就是一个抒情传统”
中国文学究竟有何特质?经历数千年发展的中国文学,是否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传统?打从“中国文学”成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以后,这些问题就不断被提出。当然,中国的诗词歌赋或者骈体散行诸种篇什,以至志怪演义、杂剧传奇等作品,本就纷陈于历史轨道之上;集部之学,亦古已有之。然而,以诗歌、小说、戏剧等崭新的门类重新组合排序、以“文学”作为新组合的统称,可说是现代的概念。亦只有在这个“现代”的视野下,与“西方”并置相对的此一“中国”之意义才能生成。于是“中国”的“文学传统”就在“西方文学传统”的映照下得到体认,或者说得以“建构”。从20世纪之初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认知”,或者可以用陈世骧的一句话来概括:“整体而言,中国文学传统就是一个抒情传统”(“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as a whole is a lyrical tradition”)。④如果我们以陈世骧的《中国的抒情传统》,以及此论的另一位重要旗手高友工的长篇论文《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⑤作为这个论说系统发展臻成熟的主要标志,我们大约可以归纳此一论说的基本论点如下:
(一)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具体而言,专指“抒情诗”——比其他文类占更重要的地位;在这个判断之上的进一步推衍是:“诗”甚至可以有超文类、超形式的存在,渗入其他文学体制的意蕴世界,成为中国文学以致文化精神的最高表现。于是“抒情传统”(lyrical tradition)的论述范围,就从“抒情诗”(lyric)出发,再引申到“抒情精神”(lyricism)、“抒情体现”(lyricality),从而归纳演绎出“抒情美典”(lyric aesthetics)。
(二)“抒情传统”中“抒情”一词所采是其广义,它既可包括“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言志”的主张,也可以容纳“诗缘情而绮靡”的审美态度;至于“发愤以抒情”一路的“诗可以怨”,更是其中重要的一脉。
(三)“抒情”或者“言志”,其“情”与“志”属于创作主体内在领域,“抒”与“言”则指其向外呈现的行动,行动的结果就是“诗”、“赋”等语言艺术成品。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也就是以创作主体的“情”与“志”为重心以体认文学意义的一个传统。
(四)“抒情传统”既以“情”、“志”为重,则如何以艺术形式以寄寓、传达“情志”,也就成为其中不能轻忽的环节。提倡“抒情传统”论者,并不会忽略作品的“外在形式”,因此与重视艺术形式的理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有相类似的表现,在建立论述的过程中,也往往从这些形式理论取资;然而二者的出发点与终极关怀实有所不同。
(五)“抒情传统”论述以创作主体之内在“情志”为关注对象,易招“脱离现实”,“遁逃于个人世界”之讥。然而,正如此论源头的“发愤以抒情”、“诗以言志”等说,当中不乏现世的指涉。事实上,在这个论述系统中,由“情志”所统括的“心象”或者内在世界,处处与现实世界相关照、相呼应;“抒情传统”论者以为透过这种相互映照,更能洞悉“人与外界”的真正关系。
从以上几个根据点来检视林庚先生尤其以1947年厦门大学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文学史论述,我们认为当中具备了许多抒情论说的特征。虽则林先生并没有在《中国文学史》中明确提出“抒情传统”一说,但其一贯的文学史思考角度却是同向同质的;而林庚先生之幽怀别抱,以至其独特的表述模式,也可以在这个论述的脉络下,展示出更深刻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从“抒情传统”论述的角度讨论林庚先生的理由所在。因篇幅关系,本文先就以上最为关键的第一点,剖析林庚先生文学史论说的“抒情论”面向。其他几方面将在另文细论。
三、“诗的国度”与“抒情传统”
1940年林庚在厦门大学一次中国文学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
中国本来是一个诗的国度。⑥
同样的话又见于1943年发表的《漫话诗选课》。⑦半个世纪以后,在不同的访谈录中,还可以见到他的同一意见,如1993年见刊的一篇说:
中国文学史事实上乃是一个以诗歌为中心的文学史。⑧
2000年发表的另一篇访谈说:
中国的文学传统不是戏剧性的,而是诗意的,……中国还是诗的国度,所以我写文学史,也是拿诗为核心。⑨
这个讲法,可说是林庚一贯的主张,从1930年代到20世纪完结,他以大半个世纪的时间,成就了三个阶段的文学史论述(分别以1947、1954-1957、1995三本文学史为代表),但从没有放弃这个观点。所谓“诗的国度”,可以从两个方向去理解:一是以为中国文学虽体裁众多,但最重要的表现就在“诗”——这牵涉到诗与其他文体的比较;二是以为中国文学的起源时期缺少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史诗和悲剧,因而抒情短诗发展成为主流——这是国族文学文化现象的比较。这两个方面应该都是林庚对中国文学史的见解,其中后者更是他的思考出发点。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谜》,林庚就颇用力去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没有悲剧,早期文学中也没有长篇叙事诗和长篇小说。这一篇论文后来就浓缩为《中国文学史》的第二章《史诗时期》。他的文学史论述,也就是以这一个匮乏现象作为基础;其中最简单直接的判断是:
中国文字的起源是诗的,西方文字的起源是故事的。⑩
多年后,林庚在《漫谈中国古典诗的艺术借鉴——诗的国度与诗的语言》(1985)一文再扼要地总结这些观点,并提出“抒情传统”的观念:
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因为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产生得很晚。……就文学史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完整的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的是甚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代表的抒情传统。……
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才成其为诗的国度。(11)
这一论点,完全可以与陈世骧的重要宣言《中国的抒情传统》相连接。陈世骧说:
与欧洲文学传统——我称之为史诗的及戏剧的传统——并列时,中国的抒情传统就显得突出。我们可以证之于文学创作以至批评著述之中。人们惊异伟大的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造成希腊文学的首度全面怒放,然而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与希腊自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同时开展的中国文学创作,虽则没有任何类似史诗的作品,却也一点也不逊色。再说,非到两千年以后,中国还是没有戏剧可言。(可见)中国文学的荣耀别有所在,在其抒情诗。……
整体而言,中国文学传统就是一个抒情传统,此说或许不算夸张。(12)
说中国文学的始源阶段与西方早期文学史相异,这不过是简单的现象罗列排比。比之更为重要的,是据此作出的诠释——中国文学自此形成了其“抒情传统”,于是整个文学甚至文化的发展,都含蕴着这个“抒情传统”的特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中国文学史》时,林庚仍未正式使用“抒情传统”一词;数十年后,当他回顾自己的文学史书写时,却不期然用上这个概念。(13)我们不能证明林庚在1980年代的说法与陈世骧在1970年代发表的宣言有直接关系;然而,我们似乎也不能仅仅用“巧合”来解释这同一词汇的运用。我们注意到林庚与陈世骧早期学术训练和时代熏染的共同背景,还可以参酌属林庚和陈世骧二人的师长辈、又曾在1930年代同时任教过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闻一多的类似言论。(14)闻一多在1943年发表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也是从比较的角度去说明中国的文学传统:
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录在文字里。……印度,希腊,是在歌中讲着故事,他们那歌是比较近乎戏剧性质的,而且篇幅都很长,而中国,以色列则都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
对于中国的诗歌之成为文学传统的主脉,他还有这样的说法:
中国,……在他开宗的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所以我们的文学传统既是诗,就不但是非小说戏剧的,而且推到极端,可能还是反小说戏剧的。(15)
林庚在《中国文学史》中的论述似乎在呼应闻一多:
《诗经》这部书一向被人奉为经典;它仿佛是这民族最古的一声歌唱,便从此唤醒了人们的爱好。……这些简短的诗歌的表现,便是我们最早的文艺的特色,它同时暗示了我们将来文艺的发展。(16)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很明确的指出诗歌在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位置,以为:
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此后,在不变的主流中,文化随着时代的进行,在细节上曾多少发生过一些不同的花样。诗,它一面对主流尽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的服务。(17)
林庚在《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也说过: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历史很长,而且从没间断过,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
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因此成熟得最早,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诗简直成了生活中的凭证,语言中的根据,它无处不在,它的特征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去。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因此才真正成为诗的国度。(18)
这些观点和论述态度,在陈世骧及以后的“抒情传统”论者的著述中,都有所继承。
在陈世骧来说,中国文学到处洋溢着“抒情精神”(lyricism)。不但“赋”与“乐府”受此影响,即使后来的“戏曲”和“小说”,也备受“抒情精神”的支配、渗透,或者颠覆(“lyricism continued to dominate,infiltrate,or…subvert[drama and narrative art of the novel]”),因此陈世骧认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本质(essence),就是这种“抒情精神”。(19)后来高友工更细致地论述中国文化史上不同艺术表现(包括音乐、诗、画、书法等)的“抒情传统”。(20)这种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诠释,其精神无疑可以溯源至闻一多所说的“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又或者林庚所说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因此才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当我们将闻一多、林庚的论说,与陈世骧或者高友工等对“抒情传统”的讨论并置,实在不难见到其中思维与认知的同质与同向。
四、诗外寻诗意
在《中国文学史》中,林庚当然奉行一己的宗旨:“拿诗为核心”以写文学史。他对诗歌的发展,尤其诗的语言形式与艺术的关系,特别究心,并且时有精彩的考析和论断。但我们不应忽略林庚对诗以外诸种文体的讨论,因为这是他的“诗歌传统”说——或可称为林庚式“抒情传统”说——文学史诠释能力的展现,从中我们可以见到林庚的敏慧睿智,见解独到。例如他谈到先秦散文中的《老子》和《庄子》,先说:
中国文字的起源是诗的。……诗是最后的语言,一切以此为归宿。
再指出:
(老子以为)万有都归于无,……又以为“有”是变动的事物,而无才是永恒的主人。这归宿的要求,便是老子不完全唯物,而富有诗意的缘故。(21)
他又表示庄子散文:
富有文艺趣味,正因为他追求绝对,而成为心灵的归宿。……散文到了这个地步,它一方面完成了自己,一方面却更近于诗;散文的高潮乃重新又走向诗去。(22)
讲到魏晋风流,便说:
一些快意的人物,一些超然的行径,乃成为时尚的追求。然而这一个诗的国度,既追求着一切的归宿,它的人物乃永远就完成在刹那的风度上;这一个艺术的形式,使得中国后来的字画美术,都发展在这同一的领域,这是东方特有的形式,它似乎倾向于智慧,而又要求着感情上的自由。(23)
这些评断虽然看来恍惝迷离,但其指向并不难掌握。林庚主要以诗的理想境界、结合中国的思想及其形式载体,融汇而为观察的凭借;于是,以此可以诠释散文,也可以诠释人物风采;甚至如下文的诠释中国文学史上发展较迟的叙事体——林庚和闻一多一样,称之为“故事”(24):
从诗的爱好走向故事,也必仍带有诗的情调。诗是生活的指点,在刹那间完成;刹那以后,我们仍然落在生活中,不过觉得心地更不同罢了。它虽然是完整的,却并不就是生活的结束,它与欧洲以整个生命,去换取一个意义的形式不同,中国故事所以从来缺少悲剧的结构,这对于生活经验日增的文艺恰好成为一个说明。(25)
所谓“从诗的爱好走向故事”,是林庚对中国文学史自宋元以后小说戏曲为文坛的主角的承认;(26)然而,在林庚眼中,中国的叙事文学仍然不脱“诗的情调”。于此林庚以其感悟式的观察,对诗歌的存在意义,或者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作出极为精到的判断。他视诗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存在:文学虽然从生活而来,但两者并不完全对等。人生布满多向庞杂、不同层次的各种经验;文学却在它的结构中有一个完整的表现。这个完整的经验可以给予人生无穷的启示。当作者或者读者经历一次完整的文学经验以后,回到生活,就得到许多的“指点”。这个观察与1970年代后期高友工的几篇“抒情美典”的基础理论文章的见解相同。(27)林庚之论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如何把这个观察所得延伸到“故事”结构的讨论,他以为欧洲文学的“悲剧结构”是“以整个生命去换取一个意义的形式”。换句话说,西方的叙事文学与生命同构。然而,中国叙事文学则是生活之外的一个驰想园地,林庚更以“梦”作为中国故事结构的比喻:
梦的写作一方面是想象的自由,一方面是避免悲剧的结果。因为梦中的事最多不过是一场梦罢了。东方的故事所以始终是一个诗意的欣赏。(28)
东方式的生活正是一种欣赏的生活,一切都持一种静观的态度,诗如此,故事亦如此,庄子的蝴蝶梦便首先适应这一个趣味而成为东方典型的故事。(29)
西方“悲剧结构”指向一种身陷其中、不能自拔的命运;中国“梦的结构”则是置身局外的、抽离的“静观”和“欣赏”,好比庄周对“蝴蝶梦”的凝想冥思。由此而言,人世的生活经验可以“梦”为镜像作映照,然而镜像之自成结构毕竟又与生活不同。林庚从存有“诗意”的角度对中国叙事文学作出诠解。于是,中国文学作为“诗的国度”并没有因为小说戏曲的出现以至兴盛而有本质的变化,仍然不离“诗的传统”或者“抒情传统”。
五、结语
“抒情传统”的概念在近时有相当炽热的讨论,但多只聚焦于陈世骧、高友工等海外学者身上,罕有对这个论述系统的源起作出探察。本文以林庚先生的文学史论述为中心,说明此说其来有自;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评论界,相关的思想和论述已经出现。我们在评定这个论说系统的意义时,有必要同时审视其学术背景与文化脉络,以了解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从而鉴往知来、拓展学术的前路。
另一方面,针对陈世骧等的“抒情传统”说,部分批评者往往举出中国文学在“诗歌”以外还有不同文体的表现,又或者以为中国文学在诗词的“抒情”元素以外不乏史传等“叙事”元素。这些评论其实都没有真正明白,“抒情传统”论是一个诠释问题多于一个史实考订的问题。本文以上的讨论,也希望说明我们面对这个论述应有的态度;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一论述系统的文学史解释能力,而不是据现今文学史后出转精的研究积累,去指摘主张“抒情传统”论的学者在某些个别文学史判断的不准确。以林庚先生的论述为例,我们以为其成效是显著的,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学史的不少现象,都有帮助。对于前辈的贡献,我们更应珍视和尊敬。
注释:
①全书选录15人共96首,其中林庚入选最多,凡19首;见Modern Chinese Poetry(London:Duckworth,1936)。
②1971年陈世骧接受谢朝枢的访问,谈到《离骚》时说:“我同意我的旧同学林庚的说法”,见谢朝枢《断竹·续竹·飞土·逐宍——陈世骧教授谈:诗经·海外·楚辞·台港文学》,《明报月刊》,第68期(1971年8月),第28页。
③陈国球:《“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政治》,《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3辑。
④Chen Shih-hsiang,"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Tamkang Review 2.2 & 3.1(1971-1972):20.本文有杨铭塗译本《中国的抒情传统》,载《纯文学》10:1(1972):4—9;后来经杨牧删订,收入《陈世骧文存》(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版),第31—37页。杨牧本是这篇重要文章最通行的版本。然而笔者认为两个中译本尚有不少可以改进的空间,故此处引文以及下文引述,皆为笔者在参酌两个译本后按原文重新译出。
⑤见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8版。
⑥《新诗的形式》,见《林庚诗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2卷,第91页。
⑦《漫话诗选课》,见《林庚诗文集》,第2卷,第90页。
⑧林清晖:《谈古典文学研究和新诗创作》,见《林庚诗文集》第9卷,第241页。
⑨张鸣:《谈文学史研究》,《林庚诗文集》第9卷,第276页。
⑩《中国文学史》,《林庚诗文集》,第3卷,第39页。
(11)《漫谈中国古典诗的艺术借鉴——诗的国度与诗的语言》,见《林庚诗文集》,第7卷,第171—172页。林庚又说过:“中国人是‘诗’的,西方人是‘剧’的。西方文学不是以诗歌为核心,从古希腊一直到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等等,西方的整文学发展是以戏剧为核心的。”林在勇:《我们需要“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见《林庚诗文集》第9卷,第256页。
(12)Chen Shih-hsiang,"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pp.18 & 20.
(13)林庚在1986年写成的《中国文学简史·修订后记》中再次用到“抒情传统”一词,他在文中说明这次修订补充“主要是加深描述了寒士文学的中心主题,语言诗化的曲折历程,这与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无妨说乃正是先秦至唐代文学发展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多费些笔墨。”按:这个说明是针对《简史》上卷而作,所以说“先秦至唐代”。见《中国文学史》,《林庚诗文集》第4卷,第593页。
(14)林庚在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校任助教,曾为当时任教清华的闻一多批改学生作业。
(15)孙党伯、袁謇主编:《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0卷,第16—18页。
(16)《中国文学史》,《林庚诗文集》第3卷,第29、31页。
(17)《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17页。
(18)《林庚诗文集》第7卷,第170、173、174页。
(19)Chen Shih-hsiang,"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p.20—21.
(20)参见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
(21)《中国文学史》,《林庚诗文集》第3卷,第39页。
(22)《中国文学史》,《林庚诗文集》第3卷,第47—48页。
(23)《中国文学史》,《林庚诗文集》第3卷,第112页。
(24)闻一多《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见《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31页)把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到民国六年的“第七大期”称作“故事兴趣的醒觉”,其思考的模式与林庚也很相似。
(25)《中国文学史》,见《林庚诗文集》第3卷,第318页。
(26)用他的话来说:“元曲以来,文坛已是故事的天下,诗文毫无起色。”《中国文学史》,见《林庚诗文集》第3卷,第382页。
(27)请参阅高友工《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试论“知”与“言”》(1978)、《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上):美感经验的定义与结构》(1979)、《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下):经验材料的意义与解释》(1979)等文;均见《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
(28)《中国文学史》,见《林庚诗文集》第3卷,第324页。
(29)《中国文学史》,见《林庚诗文集》第3卷,第319页。
标签: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论文; 林庚论文; 闻一多全集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陈世骧论文; 闻一多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