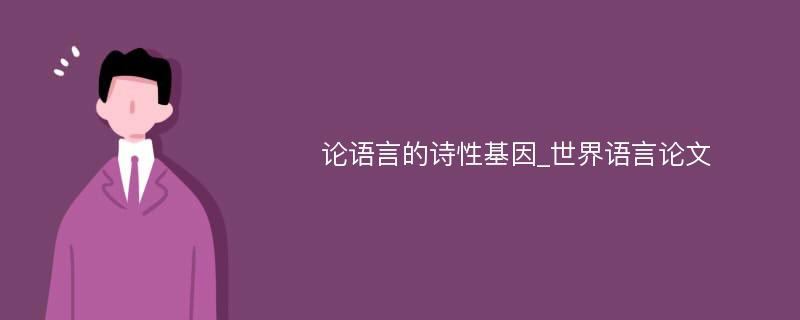
论语言的诗化基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的诗论文,基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诗化是语言的原初本性,它构成了语言发生与创造的一系列内在法则,当语言演化为逻辑推理符号后;诗化依然在语言的深层结构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决定着语言符号转化为艺术符号的可能性,是艺术语言存在的客观基础和前提。艺术创造中的任何主观努力,一方面是语言诗化基因的释放,一方面又受其内在规律与法则的制约。为此,文章具体分析了诗化基因的发生,内在运动法则及其主要表现形态。
关键词 诗化基因 相似律 隐喻律 想象律 情感表现 意象建构 语义生成
语言与艺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类型,语言是理智的逻辑系统,艺术是情感的体验系统。在符号学领域内建树颇丰的卡西尔和苏珊·朗格,其艺术符号学研究的重点:一是辩析语言与艺术两类符号不同的形式与个性;二是探讨语言符号向艺术符号转化的方法和途径。对于前者,他们的论述极有启示意义;对于后者,他们却没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苏珊·朗格虽肯定“诗歌根本不是真正的话语”,诗中语言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服务于事实的说明、意思的传达和概念的建立,“而是以推理性语言所进行的虚幻的‘经验’和虚幻的往事的创造。”〔1〕但她坦率地承认:“有关语言在诗的创造中的作用问题, 在我自己所属的学派内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
尽管语言符号的概念性、推理性与艺术符号的意象性、体验性互不对应,但问题的全部症结就在于:诗只能用语言去创造艺术,用推理性符号去营构体验性符号,用语言去言传不可言传的“内在生命”,用受到极大限制的东西去表现难以限制甚至无法限制的东西,这种困境,迫使语言符号要创造性地转化为艺术符号,推理性系统要转化为表现性系统,以形成新的符号现实。诚然,转化的发生,离不开诗人对语言创造性地组合和运用,离不开艺术家在特定语言行为中的主观努力,但转化之所以能够发生和实现,却离不开语言内在的诗化基因,简言之,任何主观的创造性努力都建基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诚如罗曼·雅各布森所说:“一个对语言的诗歌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对语言学问题毫无兴趣、对其方法也知之甚微的文学学者都同样是全然不合时宜的人。”〔3〕
一、语言诗化基因的发生学前提
最早指出语言具有诗化基因的是亚里斯多德,他认为语言中除了表示真和假(逻辑)的叙述外,还有既不表示真也不表示假的语句,比如心意和抱负,它们是心灵的所属,不是逻辑的,而是诗和修辞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他那部天才著作《新科学》中,则首次提出了“语言起源于诗”的观点,他告诫人们“要从诗的原则中‘寻找’语言的原则”。他的观点得到了诗人雪莱的热烈反响,雪莱从“诗即想象的表现”,语言的形式是隐喻,隐喻本是想象的推论出发,得出结论:“语言的本性就是诗”,诗是“来自于语言天性的本身”。〔4〕随后, 黑格尔在《美学》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诗的用语产生于一个民族的早期,当时语言还没有形成,正是要通过诗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5〕著名的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奇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语言与艺术的统一说,他的美学代表作其书名就是《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他的推论是:直觉即表现,表现即艺术,语言原本就是主观直觉的创造,是“精神最原始的表现”,所以,语言当然也就是艺术。克罗奇由此肯定:“语言活动并不是思维和逻辑的表现,而是幻想,亦即体现为形象的高度激情的表现,因此,它同诗的活动融为一体,彼此互为同义语。这里所指的就是真正、纯朴的语言,就是语言的本性,而且即使在把语言作为思维和逻辑的工具,准备用它作某种观点的符号时,语言也是要保持它的本性的。”〔6〕上述列举的种种论断归纳起来, 就是目前很多文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都认可的一个命题:语言起源于艺术,艺术符号是语言符号的母体。
其实,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累累实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许多研究者把艺术的开端确定在大约4至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有学者更提出了“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发生”的观点,把艺术起源的上限定在大约300万年前。〔7〕无论采取何种说法,艺术的起源显然早于语言,从考古发现看,无论是3 万多年前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还是2万多年前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所画奔马、野牛、 野羊、鸟头人等,形态生动,色彩明快,已经达到相当水准,而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是最近在我国湖北宜昌杨家湾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象形文字,专家们初步认定也不过6000多年,尽管语言要早于文字,但从当时原始文字的简陋形态上也可看出,它在表情达意上的水准远远落后于艺术。
这样,先在的艺术自然成为孕育并催生语言的母体。黑格尔从另一个角度上也肯定过这一点,他说:“诗,语言的艺术,是把造型艺术和音乐这两个极端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在精神内在领域本身里,结合于它本身所形成的统一整体。”〔8〕原始艺术中, 除了起源最早的舞蹈外,恐怕孕育语言的直接源头就数绘画和音乐了。原始文字其实不过是简化了的绘画。“凡是最初的民族都用象形文字来达意,这是一种共同的自然需要。”〔9〕既然“文字是绘画的产物”(布龙菲尔德), 那么,绘画的艺术精神自然会深深积淀在文字中,中国汉字尤为典型,难怪庞德对汉字这种直观的艺术表现精神赞叹不已。至于音乐,虽无考古学意义上的实绩可循,但如果把前语言的声音信号,即一些有声无义、有情无理的喊叫视为雏型中的音乐的话,那么,就不是斯宾塞所说的音乐起源于语言而应该是语言出自音乐了。维柯以为“野蛮人的最初的语言一定是在歌唱中形成的”。〔10〕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并对斯宾塞进行了反驳。曾被拉波夫誉为本世纪最出色的三位语言学伟人之一的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通过自己的潜心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语言起源于唱歌。”
语言脱胎于艺术,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迫使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最初的语言主要不是用之于认知和推理,而是用于情感的表现,它是艺术,是诗;虽然,语言后来的发展背离了这一方向,它遵循着卡西尔所谓的“综合性增补过程”不断地抽象化、逻辑化,过滤掉许许多多的个体经验,把越来越多的具体事物纳入公共概念命题当中,从而挖空了事物,使人再难用整个心灵去占有事物、体验实在,但“从发生学的观点看,我们必须将人类言语具有的这一想象的和直觉的倾向视为言语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为“在人类文化的早期,语言的这种诗意的或隐喻的特征似乎比逻辑的或推理的特征更占优势”。〔11〕至此,合理的结论是:语言虽然从艺术品格走向了逻辑品格,从与艺术的同一走向了对立,但语言的脉络中依然流淌着艺术的血液,它身上依然潜伏着诗化的深厚基因。
二、语言诗化基因的法则
语言的诗化基因是语言的创造、运用的基本法则的产物,语言脱胎于艺术这一事实表明,这些法则中最本原的并非逻辑法则而是艺术法则。虽然狄德罗当年曾断言“每逢哲学的精神愈发达,魅力和诗也就愈衰弱”,但语言与艺术深层结构的同一,却是语言诗化基因生生不已的内在源泉。
1.相似律
据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研究,原始人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物与人自身之间的一种直观的相似性,他们根据这种心理直观上的相似性而规定外物本不存在的种种神秘性质。由于语言以最为自明的形式在自身中显现了一切文化活动的“模式”,因而人类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自然也就成了语言符号的构成方式。语言作为创造和构成意义的活动,并不是孤立地为某一存在的事物命名。世界是人的世界,只有在人的感知、体验中存在才具有意义。与其说语言为事物命名,不如说语言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命名,而相似律正是人辨认环境、结识宇宙、创生意义、外化本质力量并借助外物反观自身的基本法则。
语言作为人的创世神话,一方面在人与物间多种类型的相似性中创造符号意义,为世界命名。“石头”、“树身”、“山腰”、“桌腿”不正是人与物的拟人性相似吗?“毫无结果的争论”、“这人很成熟”、“权势达到了顶峰”、“奋发向上的精神”、“思想深刻”不也是无形的观念和有形的事物间建立同构性相似吗?难怪众多语言学家都一致指出,人类的语词多半是比喻性的,语言本身就是通过取之于专门词汇的比喻而发展起来的。维柯:“一切民族语言的主体都是比喻。”索绪尔:“类比是语言创造的原则。”帕默尔:词的“意义扩展的最丰富的源泉是词的比喻性应用”。著名心理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也写道:“语言发展的历史表明,那些看上去与直接的知觉经验无关的词语,在它们刚出现时是与之有关的。看得出来,许多词语现在仍然是比喻性的。”〔12〕另一方面语言通过拟人性相似和同构性相似,构成了人对世界的一种非现实化的、超感性的体验方式。人在一个被主观内化了的世界中,创造并理解着世界对人的意义,同时,又凭借它体验并观照着自己的生命存在。语言在相似性连结的两头,展现的是互为重叠的双重影像:既是对象的自我化,又是自我的对象化;既是表层的现实图景,又是深层的情感意蕴;既是形而下的有形之喻,又是形而上的无形之本。在这幅语言的创世神话中,淋漓尽致地抒发着艺术的神韵与风采。
2.隐喻律
隐喻有三层含义:一是修辞手法,指不用喻词,甚至喻指也不出现,喻指与喻体间通过某种相似形成比喻;二是诗语言结构方式,西方结构主义诗学把隐喻和转喻视作语言的两种基本结构,布拉格学派的罗曼·雅各布森根据索绪尔的语言横组合和纵聚合的理论,提出横组合是句段的历时组合,其组合过程表现为邻近性,因而是一种转喻方式;纵聚合是联想的共时选择,其选择过程表现为相似性,因而是一种隐喻方式,二者紧密结合并互相转化。他认为诗歌的特有功能,就在于把垂直的选择轴(隐喻)投射到组合轴(转喻)上,使诗的句段组合具有隐喻特征。三是语言的基本特性,既然最初的语言是在相似性关系中互为阐释地为存在命名,那么,其符号意义就必然在表层的指称意义中隐含有深层的情感意义,说出来的意义必然暗喻着没有说出来的意义,在直接呈现的现实图景中必然重叠着与之同构的心灵图景。
这三个层次上的隐喻,相应地构成了语言活动的三个层次:表层的修辞现象,中层的结构活动和底层的语言世界观。语言隐喻法则的根基正是这种底层的语言世界观。其实质是把人当作权衡事物的标准和尺度,如果说逻辑性语言遮敝了人的存在,那么隐喻性语言的目的则是敞开存在,让物的意义向人开放。因此,当符号意义从字面义向联想义、从外延向内涵、从语言向言语滑动时,隐含的精神意蕴必然由背景而突现为前景,产生“言外之意”、“象外之旨”。
隐喻意义的生成,凭借的是相似性基础上的直觉和体验。尽管由于感觉经验在不断重复中日益被概念逻辑所替代,我们至今已很难从“日出”、“日落”、“山头”、“锯齿”等语词中感受到生命的冲动,但一旦我们从重复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陌生地面对语言所展示的人与存在的新的相似性时,就不难体验到命名活动中情感的激荡和生命的创造活力,于是命名的语词就不仅与对象相联系,同时包容了一切由命名活动带来的感觉经验和心理内涵。这种来自原始思维的物我互渗、物我同一的语言世界观,宣告了最高的艺术精神——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存在,它与理性逻辑的二元性对立,形成了人的两极精神结构:艺术和科学。
3.想象律
想象(包括联想与幻想)既是人向外投射主观意向的心理活动,又是在人与物、物与物间建构相似性的思维运演方式。亚里斯多德就曾肯定过它是与逻辑推理并列的一种思想方式,黑格尔则进一步认为,它不仅有“独立的自觉的目的”,而且完全可以构筑一个“独立自足的完整的世界”。〔13〕
想象在语言命名活动中的主要功能是建构相似性,对此,英国那批极有思辩才华的浪漫派诗人雪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都有阐述。雪莱在《诗辩》中说:“推理尊重事物之间的相异,想象尊重事物之间的相同。”华兹华斯认为想象的独特能力,就是把事物汇聚在一起,确立一些有力而统一的相互关系、相似点和连接点,它领悟并且创造整体。柯勒律治则希望想象能揭示一切事物当中的有机联系,摧毁那些由亚里斯多德式的分析在事物之间建立起来的人为的分界,他指出最理想、最完善的诗人应“散布一种统一的情调和精神,使各个部分都通过我们所特别命名为想象的这个综合神奇的力量,彼此得到调合和渗透。”〔14〕其实,稍加审视便不难发现,无论是语言符号的创造还是运用,想象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如汉字形体与指称物间的象形,靠的是想象的粘连。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索绪尔认为是任意性的,任意性可以理解为非逻辑性、非分析性,既然人们仅凭主观意愿把能指与所指结合为一体,那么想象在这种主观意愿的命名中显然占有重要地位。当“愤怒的葡萄”“生命凋谢了”,“不肯围拢的石头狂吠不已”、“太阳在你的舌根下升起来”、“那些诞生过星光的言语全被淋湿”……等感觉与经验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惊奇于事物间那种神秘的超常联系时,我们不能不将此归功于想象嫁接相似性的神奇魅力。
既然想象驱使语言不断地在人与物间发现新的相似关系,不断地运演着人的内在世界的外化和外在世界的内化,因而,语言隐喻性的实现,也就离不开想象的激发和粘连作用,一方面是语言在想象的作用下为隐喻性提供特定的语境和组合方式,另一方面想象又在特定语境与组合方式的作用下,被充分调动和激活,从而能沟通表层义与深层义的联系,如霍克斯说:“隐喻所惯用的统一不同事物以及反复强调其‘相似点’的方法,都刺激和显示着想象,继之而来的则是:想象以隐喻的形式把自己纳入人类所特有的语言机能当中。”〔15〕
三、语言诗化基因的表现
在相似律、隐喻律、想象律的作用下,语言必然表现出强烈的诗化倾向,这既是语言艺术存在之本,也是语言维系主观与客观,揭示人的内在世界的意义与价值的根基。可以说,诗化语言是人类灵魂闪烁、游荡的空间,是人类精神发育、升腾的圣殿,它以情感表现性、意象建构性、语义生成性为主要特征,在科学与艺术的两极间来回摆动,产生着持久而特殊的震荡。
1.情感表现性
语言的情感表现功能在发生上远远早于逻辑推理功能,在原始语言中它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支配性的语言倾向。在现代语言中,它虽然已从前排退居幕后,从显性表现转为隐性表现,但在特定思维的作用下,语言内在的诗化法则会重新把它推向前排,并在逻辑语言的辅助下,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对此,我们不妨从语义、语音两方面进行描述:
语义的情感表现性。语义可以被理解为语言能指与所指间的对应关系,它有两种性质:传达关系和表现关系。传达关系中的语义是人们对于现实的一种概括的、抽象的反映,集中体现了人对外在现实的理解与认知,它往往以概念的方式在语词中结晶固定下来,形成含义确定的字面义、指称义、逻辑义。表现关系中的语义是个人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心理反映和主观体验,其含义是流动的、变换的,联想义、暗示义、隐喻义等均为表现关系的产物。语义的情感表现性主要来自于表现关系,因为情感的表现只能通过体验的渠道,而唤起读者情感体验的关键,是营构意象,以吸纳并释放情感,所以即便是纯粹的情感语词,如爱、恨、愁、悲等,当处于传达关系中时,也只能起传达情感概念的作用。传达关系中的语义和表现关系中的语义,在科学文本和艺术文本中会各有所侧重,但并不是壁垒分明的,在特定思维和语境的作用下,两者能相互支撑、相互转化。按新批评文论家退特的说法,诗应当是“所有意义的统一体,从最极端的外延意义到最极端的内涵意义”。〔16〕因为“美学的信息是作为一个从一个层次过渡到另一个层次的不中断的‘多级’指示系统而发生作用的,它的外延意义不断地变成内涵,永无止境”。〔17〕
语音的情感表现性。语音源于音乐,使其情感表现性比语义更为直接和便当。“语词的声音变化本质上是属于心理的”(索绪尔),难怪黑格尔断言“音乐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谓富于意象的富丽词藻还更重要。”〔18〕立普斯说得更为明确:“诗歌的音响、仅仅是子音和母音的单纯组合,即使完全抛开了它们所传达的意义,也具有强烈的感情意蕴。”〔19〕
语音的情感表现性,首先来自于语音与情感状态的同构对应。人们在发不同的语音时,在心理上会引起不同的情绪感受,如说“飞扬”的“扬”字时,口腔是一个从低闭到高开的过程,有没有一种升扬的感觉呢?说“压抑”的“抑”字时,口腔则紧闭低压,是否给人一种压迫的感觉呢?四声的变化也如此,即所谓“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其次来自于语言的组合和配置中与情感变化对应的声、气、息。它表现单个说话人的某种特殊的生命状态和情绪状态,形成特殊的语气和情调。钱钟书评陈师道的《后山集》时说:“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闻一多在评骆宾王的“梅花如雪柳如丝,年去年来不自恃,初言别在寒偏在,何悟春来春更思”时也写道:“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因为人所发出的声音正如人的呼吸,充满了生命力和激情。”(洪堡特)
2.意象建构性
情感本身无形式,它是各种心理成分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倾斜或张力状态,在人的心理中,它附着于各种表象,在艺术中,它附着具体的感性形式。情感作为携有强大心理能量的动态性心理因素,总要求着呈现,这样,情感寻求并呼唤感性形式作为自身的载体便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所谓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苏珊·朗格),美就是将情感由无形变为有形(桑塔耶那),均是这个意思。
原始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象性,“原始语言没有抽象概念,大量使用表象词,进行形象描绘,并且极富表情声调。”〔20〕由于尚未受到抽象思维的大规模濡染,其“象”对客观的具体存在有很强的依附性,具有十分突出的个别化倾向。在南非巴文达族的语言中“每种雨都有专门的名称”,“他们对每一种土壤,对每一种石头或岩石都有专门的称呼……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什么树、灌木和植物是叫不出名字来的,甚至每种草他们也能叫出不同的名称。”克拉玛特族印第安人“有20个词表示冰,11个词表示冷,41个词表示各种形式的雪,26个动词表示上冻和解冻。”〔21〕这种个别化倾向,凝聚着命名活动中产生的十分具体生动的感受和体验,负载着丰富的感性内涵,但语言为了适应发展了的思维和交往的需要,势必趋于抽象化,突出表现就是牺牲“个别性”来换取“普遍性”,这样,在现代语言中,语词的显象功能固然存在,但已不再和具体的事物和印象相联系,成了某一类事物形的客观抽象。“个别性”的丧失意味着具体的感性内涵的抽空与剥离,如果说“命名似乎是把一个词同一件物奇妙地并合在一起”(维特根斯坦),那么,并合就是人和世界的交往,随之而来的是对发现的欣喜,对交往的兴奋、对世界与自我的赞叹,于是命名的语词就不仅和对象相联系,同时包容了一切由命名活动带来的感受与体验,因而,原始语言的“象”实为原始意象的直接传达,语象和意象完全同一。现代语言的“象”由于脱离了具体存在,只与抽象的形打交道,其语象实际上是表象的符号,“意”与“象”是分离的。我们知道,表象对艺术并没有决定意义,能够负载情感冲动的是意象,因此,在逻辑抽象性占主导地位的现代语言中,具象性只是建构意象的条件,要使语象所唤起的抽象的知觉表象转化为意象,就要通过必要的语言行为,重新使之由抽象回到具体,由“普遍”回到“个别”,否则,即便具象十足,也会由于“意”的匮乏,而与诗化无缘。因此,意象建构性的关键并非语言材料,而是起转化作用的特定的语言行为,这种语言行为,简言之,就是变“语言”为“言语”,使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传达关系转化为表现关系。
语言的知觉表象,一旦进入表现关系,一旦被重新命名的光辉所沐浴时,往往表现得更具造型性,因为知觉表象脱离具体客观所指后,就成了游荡于言语主体思维屏幕上的“视觉意念”,而不再受制于客观实在的直观制约。这样,不仅为想象扩大了驰骋的空间,为建立相似性提供了更广阔的途径,同时为构建心灵和情感的形式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因此,我们既可以在直观层次的意象中领略诗人潜隐的情怀,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也可以在非直观层次的意象中洞悉诗人心灵的震颤,如“在每条冰缝里长满大树,结满欢乐的铃铛和钟”,“我站在你瞳孔的田野里久久逗留”,“土地的每一道裂痕渐渐地蔓延到我的脸上,皱纹在额头上掀动着苦闷的波浪。”
3.语义生成性
诗化语言的要旨,不是外向指称,为人们理智地、客观地、逻辑地认知世界提供工具性的符号操作系统,而是内向言情,为个人体验自己的精神世界,感受自身的情感与心灵的价值和意义营构观照的仪式,因此,诗化语言的语义具有两个特征:一方面它不是抽象的、共义性的,而纯粹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索绪尔),总是和个人具体的感受经验、心理定势、行为动机、价值观念、人格旨趣、文化素养联系在一起,成为难以重复,也难以归纳抽象的个人变体,按索绪尔的说法,就是很难认识和研究,因为它“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22〕另一方面其语义属于能指与所指间表现关系的产物,侧重在联想义、暗示义、隐喻义,而非字面义、指称义、逻辑义。当然,这两方面的意义并非各自为阵或平分秋色地存在于语言中,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语义向表现关系倾钭,只能在语言的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
个体性和运动生成性,做为诗化语言语义的两个显著特征,促使诗化语言始终处于原初命名的状态中。“命名是灵魂的某种独特的行为”(杜夫海纳),它将具体生动的感性印象和主体体验聚合为一体,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神奇的魅力高扬生命的旗帜,并通过不断赋予世界新的形式与意义的活动,表现人的诗意存在。
对诗化语言语义生成的主要途径,可从下列方面加以描述:
其一,语言行为中的语义生成。根据索绪尔语言横组合和纵聚合的理论,任何一个语词都处于“历时”的横组合和“共时”的纵聚合的交叉点上,“历时”占优势语义偏向传达关系,“共时”占优势则偏于表现关系,诗化语言作为“共时”占优势的言语系统,按雅各布森的说法,就是要善于通过具体的语言行为把垂直的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上,使语言组合具有明显的隐喻特性。由于隐喻来自于主体心智与相象的规定性,其语义必然具有不断命名的生成性。如“绿窗”一词,放在指称性质的传达关系中仅指绿色的纱窗,而放在隐喻性质的表现关系中,便会产生家庭气氛、闺阁色彩、宁静幸福等多种含义。如“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刘方平《夜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温庭筠《菩萨蛮》)“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韦庄《菩萨蛮》)。
这种种语义的生成与特定的语言行为策略是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诗论对此有众多论述,有的倡导含而不露,富于暗示、空白的言语策略,刘勰主张“隐之为本,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司空图标举“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梅圣俞揭橥“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的主张应设法使指称虚化、模糊化,以表现独特而不可重复的经验和感受,严羽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谢榛曰:“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妙在含糊,方见作手。”王廷相曰:“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着,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
其二,语言关系中的语义生成。语词本身的意义只有在语言关系中才能得以呈现,简言之,我们不是靠孤立的语词而是靠语言的组合来传情达意的,在特定的语序、语法关系、语境中,词与词之间的意义会互相作用、互相剥夺、互相给予。例如“海”,其纯语义是“海洋”,但如果将它置于不同的语言关系中,即可转换为:海——母亲;海——愤怒的声音;海——充满诱惑和迷误的人生等等。诗化语言的语义既然主要由联想、隐喻等语言潜在意义生发而成,那么,它的基本存在前提只能是语言在特定关系中的相互作用,正如霍克斯所言:“艺术似乎是把‘信息’组合到一起的方式,目的在于产生‘文本’,在这种文本中,含混性和自我指称不断增长并‘被组织起来’……结果产生了一种‘美学的个人习语’,一种艺术作品独具的‘特殊语言’。它在观众身上引起一种不断地把它的外延转变为新的内涵的‘宇宙’感。”〔23〕
既然词与词是互相发掘和互相感生,那么其语义必然是一个不断增殖的过程;一方面是语义生成的多元性,即能指的某些复杂配置可能同时带动许多所指;一方面是语义生成的无限性,即能指与所指在语言系统中的相互转换,能指不断转变为所指,所指又不断转变为能指,这种不知所终的无穷运动已被结构主义所披露。罗兰·巴特曰:“意义并不终止于所指,意义是系列的重新排列。”〔24〕
其三,语言形式中的语义生成。“新批评”的代表人物,诗人兰色姆曾提出过著名的构架——肌质说,他认为一首诗可分为构架和肌质两部分。构架是指“诗可以意释并换成别一种说法”的部分,即可以用散文加以转述的东西,这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内容;肌质则是指作品中那些无法用散文转述的部分,它“并非内容,而是一种内容的秩序”,这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形式。在兰色姆看来,诗的魅力和美都在肌质而不是构架。这显然具有形式至上的片面性,但就它强调形式也能产生魅力和美这一点来看,却具有合理性。从心理学角度看,任何艺术作品都引导读者的情绪向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内容引起的情绪,一方面是形式引起的情绪,形式变了,由形式引起的情绪也随之消失殆尽。如用一般的语言形式改写杜诗《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结果只能得到这样一个“构架”:叛乱已平,捷报传来,又惊又喜,纵酒放歌,返家之路已无阻碍,游子归家的愿望已不难实现。这样一个干巴巴的“构架”与诗的原作是无法相比的,原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25〕改写后,则诗的意趣、生气、神韵全部丧失。
由此可见,语言形式决不是无足轻重的仅仅起呈现内容的因素,而是一种给内容以美学阐释,并使内容在艺术秩序的作用下生发新的语义的重要力量。
注释:
〔1〕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第291页。
〔2〕苏珊·朗格《艺术问题》,第142页。
〔3〕转引自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第34页。
〔4〕〔14〕〔15〕转引自泰伦斯·霍克斯《隐喻》,第65、76、 65页。
〔5〕〔8〕〔13〕〔18〕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4、11、 65、68页。
〔6〕克罗奇《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第41页。
〔7〕见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
〔9〕〔10〕维柯《新科学》,第107、197页。
〔11〕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164页。
〔12〕阿恩海姆《视觉思维》,第342页。
〔16〕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第58页。
〔17〕〔23〕泰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第146~147页。
〔19〕转引自朱先树《诗歌美学辞典》,第193页。
〔20〕杨春时《艺术符号与解释》,第20页。
〔21〕列维·斯特劳斯《原始思维》,第166页。
〔2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30页。
〔24〕转引自赵毅衡《文学符号学》,第115页。
〔25〕见仇兆鳌《枉少陵集详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