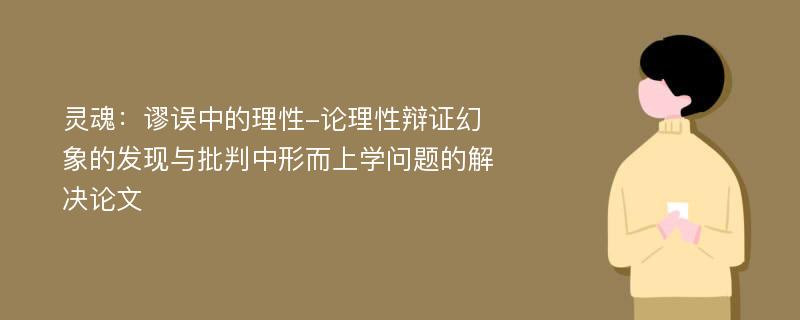
灵魂:谬误中的理性
——论理性辩证幻象的发现与批判中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
张 广
[摘 要] 对“灵魂”这一理念的辨析使得批判发现超验的“自我”不是信以为真的“本体”,而是似是而非的“谬误”。这一发现似乎表明批判只具有一个消极的功用——取消理性的超验运用。不过,因为有理性,并且“谬误”也关系着理性的实现,因此人们还是不会放弃理性,并主张其超验的运用。可见,“谬误”之所以要破除,有比表面出现的“幻象”更根本的内在的问题。另外,“幻象”的发现也会提醒人们:出离“谬误”,在理性能够满足的地方寻求理性的满足。并且,区分“概念”和“直观”也使得“批判”不仅能提供人们破除“幻象”进而消除理性内在问题的可能,也提供了人们重返“概念”在理性自身之上实现理性自我满足的契机。
[关键词 ] 直观 统觉 灵魂 谬误 批判
“灵魂” (Seele )①这一理念可谓批判研究的鸡肋——虽然不得不提及,但鲜有能深入的。② Ameriks总结了三个原因:首先,这并非批判哲学的中心;其次,这一部分少有争议;最后,这一部分说明繁难,结果消极。本文则更强调此部分的过渡性,即说明“灵魂”这一理念本原地提出了理性,开启了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重建。K. Ameriks, Kant’s Theory of Mind—An Analysis of the Paralogisms of the Pure Reason , Oxford:Clarendon Press, p.1.因为,一方面,不同于“分析论”之中的诸“范畴”,它们被展示为知识得以可能的建构性的“规范”(Kanon),③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S. A 61/B 85.处在“辩证论”之中的它被指出作为“本体”(Substanz)不过是推理之中的“谬误”(Paralogism),④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S. B 410.是混淆了“概念”为“直观”而产生的似是而非的“幻象”(Schein)。⑤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S. A 293/B 349.甚至,就是在“辩证论”之中,它也既不像“自由”(Freiheit)那样提供了“总体”(Totalität )⑥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S. A 407/B 434.的可能,也不像“上帝”(Gott)那样架构了理性普遍可能的“理想”(Ideal)。⑦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S. A 574/B 602.于是,涉及理性的认知功能和自我的实在性,人们会退回到“分析论”中的“统觉”(Apperzeption )⑧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S. A 98/B 132.来谈论。⑨ 在这个方面Ameriks援引Strawson观点说明了这一趋势(同②)。相对这一倒退,本文强调“谬误推理是对批判的推进的。同样的总结见O. Höffe,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Die Grundlegung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 München: C.H. Beck, 2003, S.224-229,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还把康德的观点与笛卡尔的观点做了对比(O. Höffe,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Die Grundlegung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 S.230-338)。而作为理性建构与主体性得以可能的一个“前提”(Postulat),①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Hamburg: Meiner, 2003, S. V 121-146.人们又会倾向于进一步地联系“自由”和“上帝”来探讨。② 在这个方面上,正如这里的引用所表明的那样,它多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实践理性批判》等这些涉及道德前设的地方被探讨。不过,也与Ameriks 援引的Strawson的观点所表明的那样,它与康德理论理性相关,并且本文还要突出这一理论的讨论为开启一个实践的认知做了准备。
1)使用画板图解的教学过程是动态灵活的,教师绘制直线,画出文字过程最为困难,要在备课时反复练习鼠标的绘制方法;
中国减贫的历史和事实,向世界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雄辩地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可以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摆脱贫困,实现国家的振兴。
然而,前者忽略了在批判之中“分析论”还是个知性概念的解析,是到了“辩证论”才对理性进行了本原的讨论。同样,后者也忽略了理性运用的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因为辩证而产生“谬误”,因而它需要一个消除“幻象”的“辩证论” 才能达到对自己问题的认识,进而提供实现自己的可能。③ 对于“谬误推理”的研究Horstmann也做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总结。应该说他的总结也照应了本文这里的总结。但是,至于“谬误”所具有的批判意义,也还没有充分的说明。R. Horstmann,“Kants Paralogismen”,Kant-Studien , 1983,pp.408-425.并且,通过区分“直观”和“概念”来发现一个“谬误”,批判不仅否定了理性的实在性,而且否定了在“直观”之上去寻求形而上学实现的可能。与此同时,就像形而上学本来所昭示的那样,它也指引我们回到我们作为主体自身的规定,回到我们自身的理性之上,来认识和修正形而上学。④ 因为对这一意图的认识不足,许多重要的研究者因为康德没有提供一个概念的体系(D. Henrich, ”Systemform und Abschlußgedanke— Methode und Metaphysik als Problem in Kants Denken“,Gerhardt , 2001, Bd.I, S.94-113)和批判否定了理性的实在性而给了理性建构以否定性的评判(K.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 London: N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 2003, p.579; P. Guyer, Kant and die Claims of Knowle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与此同时,尽管批判实践的意图已经被提及(O. Höffe, ”Architektonik und Geschichte der reinen Vernunft“,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Hrs. v. Morl, G. und M. Willaschek, Akademie Verlag, 1998, S.634-636;P.Manchester,“Kant’s Conception of Architectonic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 Volume 41,2003, pp.187-207;“Kant’s Conception of Architectonic in Its Philosophical Context”,Kant-Studien , 2008, pp.133-151),并且在这个目的上也确实能发现理性建构的可能(H.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 New York, 1990, pp.22-28),但是缺乏对批判方法,即区分直观和概念的详尽领会,也让批判的这一成就没有得到基础性的阐明。如此,批判才迎来了它化解形而上学辩证问题进而成就形而上学理性建构的契机。
一、 直观:表象的理性
尽管出现在了解构主观的“概念”被错认为客观的“直观”的“辩证论”之中,并且借助“谬误推理”的发现也被指出,支撑它的“理性心理学”(rationale Seelenlehre)⑤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342/B 400.就是这一错认所发展出来的“幻象”,但是“灵魂”这一理念以及与之对应的理性的综合在批判之中却并非只有这一消极的意涵。因为,对于最终要呈现“先验综合判断”(Synthetische Urteile a priori)⑥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B 19.何以可能,从而最终要给出形而上学的可能的批判而言,这一消极的否定无疑只是它的一个方面,以至于是它说明一个积极的建构的一个环节。或者,就是因此认定了理性综合的空虚,但是仅止于此也只是道出了理性综合的外在限制,而没有否定理性自身就有成就自己的可能,因而人们也还是会继续主张形而上学,主张理性超验的运用。更不要说,“谬误”也对应着“正当”,对错认的认识也启发正当的发现。可见,一个具有解构性的理念也关联着一个建构性的设想。并且,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理性,还可能是开启它积极建构的“导引”(Propädeutik)。⑦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841/B 869.这开启了德国观念论的发展,但是观念论者却将“导引”与“科学”(Wissenschaft ebd. S. A 841/B 869)割裂开来,将批判认作是导向但是并没开启科学的“导引”,而将自身的哲学看作是实现科学的“科学”。不过,无论是知识学主观的观念论,还是精神的客观观念论,其实都可以在批判之中找到它们引以为傲的发现。当然,不能不说批判丰富的意涵也的确遮蔽了自身复杂的意图和布局(G. Zhang, Kants Architektonik der reinen Vernunft—eine Aufklärung über eine weltbürgerliche Weisheit , UB Tübingen, 2017, S.36-44)。
事实上,上述的后一种意涵不仅出现在了“方法论”,特别是在“建筑术”这一章之中,那些指出“元素论”区分“直观”和“概念”这两个认识元素就是为了提出“纯粹理性的体系”(System der reinen Vernunft )这个“科学”(Wissenschaft)的架构的总结之上,也体现在了指出存在着“幻象”的“辩证论”的“分析论”中对构成知性前提的“范畴”和“原理”的演绎和分析;不仅早就出现在了“感性论”对“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直观形式的说明之中,也出现在了否定了理性的“辩证论”之中。并且,一个消极的否定也确是一个积极的建构的“导引”。批判在指出纯粹“概念”不能为客观的“直观”的同时,也展示了理性可以架构我们的“直观”为体系。因为,批判修正理性推理的“幻象”及其由此所产生的形而上学问题不是通过别的就是借由“元素论”中的“直观”和“概念”来完成的。这么一来,它不仅指出了“概念”不同于“直观”,也说明了“概念”会综合“直观”为“体系”。
在批判之中,知识这一理性的建构首先被区分为“直观”(Anschauung)和“概念”(Begriffe)①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50/B 74.两个元素。接着,在“感性论”之中利用“空间”和“时间”的演绎,“直观”被指向了一个主观的综合,因而指向了“概念”。继而,在“分析论”之中借助对“范畴”的演绎和说明,“概念”又被指出是主体的一个系统性的建构。最后,通过对“理念”的辨析也说明了“概念”如何架构了“体系”(System)。②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474/B 502.如此一来,首先在“感性论”之中,批判就将“直观”与经验的“感觉”(Emp fi ndung)③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20/B 34.区分开来,从而将其与普遍的主观认识形式关联了起来。接着,在“分析论”之中,上述形式又被推究到了“统觉”(Apperzeption )④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98/B 132.这个提供了知性系统架构的自我意识之上。最后,在“辩证论”上述自我意识也在推理的形式上说明它如何发展出一个知识的“体系”。由此可见,批判确实不仅是一个“谬误”的发现、一个“幻象”的否定,也是一个自我建构的启蒙。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提供了“纯粹理性建筑术”的理性的知识论批判之中,作为主体的自身的规定,理性及其系统化的建构不是在“灵魂”这一理念出现之后才被说明如何得以建立,而是早在此之前就已经作为一个系统性的主观建构被提出。甚至,它不仅出现在了提出了“统觉”这个自我意识的“分析论”的“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⑤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B 131-136.之中,而且早就出现在了“感性论”之中的“空间”概念的形而上学演绎⑥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22-24/B 37-39.之中。更不要说,它不仅在“分析论”之中的“原理论”部分被最终归结到了一个主观的“体系”之上,而且在“感性论”之中就借由“时间”概念的“先验演绎”使作为主体自身的能力被提了出来。这么一来,不仅是知性的概念,而且“范畴”,也就是表象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直观形式,都被追溯到了理性这个我们自身的普遍规定及其系统化的建构之上。 因此,不仅是“范畴”,就是“直观”也都是理性的一个功能和运用。
然而,“直观”不仅呈现“概念”,也惑乱“概念”。借由“直观”和“概念”的区分及其各自的先验演绎,批判清楚地表明了理性与“直观”相关,“直观”也是理性的表象和实现。但是,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的是,不同于“概念”,“直观”同时也是一个被动的表象,而不完全是一个主动的意识。并且,作为普遍的规定,“概念”也只有区别于具体的“直观”,才能在知识之中得到本原的认识。更不要说不能区分这两者,就像“灵魂”这一“谬误”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无法认识到一个主观的理性综合,还会因为发现一个混淆了“概念”为“直观”的“幻象”,从而不仅会让理性的实现落空,进而还会否定理性运用的可能。因此,为了排除这一辩证,为了认识和确认理性的综合,有必要在知识之中剥离出“直观”,进入“概念”,在主体自身的规定和综合之上来说明理性的综合和建构。不然,就是没有碰到惑乱理性的“幻象”,我们得到的也可能只是表象的“直观”,而不是呈现主体自身系统性综合的“概念”。
但是,与此同时,同样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与“直观”分离了之后又被与“范畴”区分了开来,批判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自我”或者理性不是客观的“直观”,而只是纯粹的“概念”。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它曾经不仅在“范畴”之中被说明为整合“直观”的知性概念,也在“直观”之中被指出是表象的形式。由此可见,在批判之中,理性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概念”,也是一个“直观”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它不仅要和“直观”相结合,被阐述为表象的普遍形式,也需要正如诸“范畴”所表明的那样,展示自己是对“直观”的一个系统性的建构。并且,正如批判区分了“直观”和“概念”,又区分了“范畴”和“理念”所表明的那样,作为知识普遍的规定和架构,理性及其建构既不能在“直观”之中,也不能在“范畴”这个“直观”的“概念”之中被找到,只能回到“理念”这个理性自身的规定和建构之上才能被本原地说明。在这些诉求之上,人们也不能停留于“灵魂”这个纯粹的“概念”之上,而应该进一步地结合“直观”,在理性自身之上说明理性是如何建构起了一个认识的“系统”。
二、 统觉:知觉的理性
当然,对“谬误推理”的处理批判也没有局限在只是揭示一个“谬误”、一个“幻象”。与此同时,它也将理性与“直观”的辩证指向了它所带来的我们不得不修正的后果(Übergang),③ vg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B 428-431.即打破了上述使人沉溺于其中的“迷梦”(Schlummer)的“二律背反”(Antinomie)。④ vg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407/B 434.并且,“二律背反”之所以必须解决,不仅仅在于它表明了理性在其客观的运用之中出现了自我否定的矛盾,也在于这种矛盾否定了理性最终要将一切知识纳入一个“体系”因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普遍的客观法则的“理想”(Ideal der reinen Vernunft)⑤ vg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574/B 602.的可能。因此,辩证之所以必须认识,不仅在于发生了“谬误”,因而带来了自我的欺骗让理性失去了它追求的客观性,也在于辩证导致了矛盾,让“直观”这一本应展开和实现理性的经验的领地成了取消和否定理性及其建构的形而上学的“战场”。⑥ 为解决二律背反,批判引入了先验的自由(Freiheit ebd. S. B 566-570),使得在自然之下不可能的理性获得了可能。不过,至此,应该说批判也只是处理了理性可能性的问题,而没有真正地触及二律背反,即没有消除我们理性自身的主观性。在这个基础上,它还应该再说明,这种解决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理性要成为普遍的法则。并且,只有理性变成普遍的法则,二律背反才真正地解决。这个意涵,笔者会专门撰文加以论述。
不过,尽管区别于“直观”,诸范畴体现为存在于“概念”之中的主体自身的规定,并且它们还将主体的综合指向了一个系统性的建构,但是因为存在于认识对象的知性之中,它们首先是一个客体意识,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主体自身的综合和建构。因此,与“直观”一样,它们也要与对象相符合,因而它们依然扣留在具体的感知和表象之中,而不能直接呈现自己为主体自身的综合和建构。与之相反,作为普遍的规定,不同于作为表象客体的“直观”,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它们引以为基础的综合只能在“概念”纯粹的主观规定之上才能加以认识。这样一来,要原本地认识理性,也就需要像批判进一步地划分出“辩证论”和“分析论”所做的那样,再进一步地在“概念”之中将“理念”这个理性的概念与“范畴”这个知性的概念区别开来,在“自我”这个主体自身的规定之上来说明“概念”和理性的规定和建构。否则,我们得到的就只是一个知性认识能力及其对“直观”的不同综合,而不是一个唯一的理性及其系统化的建构。
与之相应,批判不仅区分了“直观”和“概念”,还进一步在“概念”之下区分了知性的“范畴”和理性的“理念”。这么一来,它就不仅将理性联系到了“直观”这一感知活动之上,继而在“范畴”之上展示了理性对“直观”的系统综合,最后还在“理念”之上说明了这一综合何以可能。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它不是最终在“理念”之上,甚至不是在“范畴”之上,而是早在“直观”之上就提出了理性的综合。因为,无论是“范畴”,还是“直观”,它都进行了“形而上学演绎”和“先验演绎”。这样,它不仅将它们与理性联系了起来,还将它们归结在了理性的综合之上,以至于以此展示了理性系统性综合的功能和建构。然而,为了本原地认识理性,在区分了“直观”和“概念”之后,批判也还是有必要再进一步地在“概念”之下将“理念”和“范畴”区别开来,进而在理性自身的综合之上来说明我们自身的“概念”。否则,我们得到的就不过是理性的不同的认知功能,而不是理性自身的规定及其建构。① 上述提到的德国观念论将批判仅看作未开启科学本质的导引,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在逻辑论中相对于辩证论只在分析论中将理性展示为知性的统觉,却没有正面展示这一自我意识,即演绎出一个范畴的体系。不过,批判体系并不是一个范畴的体系,而是概念之中所具有的体系性,并且这个体系虽然是涉及幻象的,辩证论中也以理性的理想展示了出来。以此来看,批判已到达科学,并且为未来的形而上学发展出了到达科学的方法,也就是直观和概念的区分 (O. Höffe,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Die Grundlegung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 15 f)。
更不要说,理性之所以会产生“幻象”、带来辩证,以至于造成对自己的否定,不是在别的地方,就像已经提到的那样,就在于与直观的关联之上,在于它的直观的综合,因而在于它作为“范畴”的运用和建构之上。因为,恰是与直观的结合,让它与直观成为一个整体,才造成了人们不再区分它与直观的差别,以至于将其与直观混为一谈,将本只是主观的概念的理性错认为客观的直观,使得人们发现它并不具有它被认为应当具有的客观性,认定其为“幻象”,从而否定其客观运用的可能。然而,事实上,“幻象”否定的只是理性不存在于纯粹的直观之中,而不是否定了理性自身及其建构的可能。它只是带来了一个对理性运用的限制,即应当限制在直观之上,而不是否定了理性自身综合的可能。为了破除辩证和主张理性的运用,因此也就需要不仅将“概念”与“直观”区别开来,还要进一步地将其与“直观”的综合区别开来,也就是与“范畴”这个知性的概念区别开来。
并且,作为我们的认识之中的普遍规定的理性,不仅会超出有限的“直观”,也会超出具体“范畴”,而要求体现为自己主体自身的规定。因为,在区分“现象”(Sinnenwesen/Phaenomena)②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248f/B 306.和“本体”(Verstandeswesen/Noumena)③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249/B 306.的情况下,“范畴”与“直观”一样作为有条件的感知,总是联系于一个前在的条件,因而体现为非本身的意识。然而,与之相反,理性作为普遍的规定,它指向作为自身原因的主体的规定,而体现为“自我”这一“灵魂”理念所表达的主体自身的规定。④ 在这一点之上,我们可以看到批判提供给我们的自我意识并不像Sellars、Kitcher、Powell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认知功能的解释,它也牵带认识一起进入实践的领域,即主体自身的规定也是我们的认识对象。当然,局限在限制理性认识范围的目的之下,批判将理性的运用限制在了可能经验的范围,并且它的这种知识论限制也的确没有直接谈论这一实践意涵。 这么一来,这个“自我”意识和规定不仅不会局限于“直观”这个有限的表象形式,也不能存在于“范畴”这个有限的“直观”的综合概念之中,而只能也必须在“概念”这个我们自身的意识之中主张和说明。因此,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理性关联和运用到“直观”之上的同时,为了认识和确认它的运用和实现的可能,我们必须回到“概念”自身之上,回到主体自身的规定之上,来对其加以说明。
三、 灵魂:本原的理性
不过,即使将理性追溯到“灵魂”这一“理念”,批判也还是没有进一步说明它如何架构了我们的“直观”,因而也还是没有让主观的“概念”展示为客观的原则,并因此澄清它是赋予我们整个存在以系统性架构的基础和可能。因为,至此,它还只是一个“理念”,一个纯粹的“概念”。这就是说,一方面,它还没有联系到具体的“直观”,让自己成为一个综合了“直观”的“概念”;另一方面,它也没有联系到自身的建构,进而表明如何为“直观”提供了一个系统性框架。易言之,将“概念”与“直观”区别开来,进而在“概念”之中将“理念”与“范畴”区别开来,再在“灵魂”这一理念之上说明理性,这只是说明理性及其建构的开始。因为,一方面,这一做法的确在认识这个结合了“直观”的理性运用之中,将理性与“直观”和它对于“直观”的综合区分了开来,并且本原地展现了“自我”和理性的所在。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做法也将“概念”剥离了它与“直观”的结合,让理性不再是一个体现在“直观”之中的法则,而成了单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一个意识的规定。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理性赢得了“自我”,也失去了能够赋予其存在因而体现其功用的“直观”。① G.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Werke . Band 3, Frankfurt: Meiner, 1970, S.13.
水力压裂技术的原理实质上就是在透气性比较差的煤层中利用水作为动力,然后使煤层之间的空间畅通,进而使煤层在开采过程中能够产生流体动力,让煤层空间能够得到膨胀,增强煤层之间的透气性,另外使煤层破解之后的缝隙能够相互联通,形成透气性良好的网络结构,提高煤层之间的交联,增加煤层与抽采部位之间的联通能力。
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批判将理性与我们的感知联系了起来。对它而言,理性不是纯粹的“概念”,而是与“直观”结合起来的认识能力。为此,甚至它不仅降身为知性的“范畴”,表现为综合“直观”的认识活动,还要沉降到“直观”,成为对象的表象。但是,也同样如批判先行区分了“直观”和“概念”,继而又在“概念”之下区分了“范畴”和“理念”所表明的那样,首先不同于“直观”,理性不是被动的对象表象,而是主动的自我意识。同时,也不同于“范畴”,作为普遍的“理念”,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意识,而是一个普遍的自我意识,因而只能在我们自身之上、只能在我们的理性之上才能得到本原的说明。因此,尽管它与“直观”相关,且它不仅体现为“直观”的综合,也体现为“直观”这一表象,但是为了本原地说明它,必须像批判所做的那样,将它不仅与“直观”这一表象能力,也与“范畴”这一“直观”综合概念区别开来,在我们自身的理性之上来说明它的规定和建构。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元素论”的划分中所表明的那样,批判地完成了对理性及其建构的说明。② 就“谬误推理”这一章节集中在说明“理性心理学”的谬误,也就是理性的辩证幻象,而没有澄清“灵魂”这一理念也包含着说明以自身为原则的主体性而言,揭示理性乃是主体自身规定这样的作用体现的并不明显,甚至遮蔽在了因为避免“幻象”而对“理性心理学”、对理性的否定中。相反地,这一部分涉及的“行为”(Handlung)的理论倒是提供了这一思考方向(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B413-415)。
但是,出现在表明存在着“混淆”(Amphibolie)⑦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270/B 326.的“辩证论”之中,并且也以“谬误推理”被指出错认了纯粹主观的“概念”为客观的“直观”,“灵魂”这个自我的规定不仅在“概念”之中区别于“范畴”被本原地追溯到了“理念”这一理性自身的规定之上,与此同时它也被发现,作为认识这一理性建构的“本体”,它并非现实的“真理”,而是混淆了纯粹主观的“概念”为客观的“直观”而产生的“幻象”。这样,它也就表明了作为超验规定的理性为主体自身的一个规定,因而本原地呈现了自我这一意识的所在。与此同时,它也让我们发现了理性不同于客观的“直观”,不过是一个纯粹主观的“概念”。这么一来,在以主体性来建构客体性的形而上学之中,理性似乎不仅无法提供“直观”以普遍的形式,反而还会妨碍我们真实地认识事物,让我们陷入脱离“直观”的“幻象”。于是,这不仅会否认理性自身的客观性,也会让人否认理性自身运用的合法性。这么一来,似乎“幻象”的发现不是什么使理性的运用归于正当并促成理性的建构的“规训”,反而是应当排除对理性运用的怀疑和否定了。
当然,批判并没有要停留在一个只是剥夺了理性客观性的“纯粹理性的规训”(Disziplin)②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709/B 737之上。事实上,正如“辩证论”接下来所展示的那样,在一个“纯粹理性的规训”之中,它也发展出了一个“纯粹理性的建筑术”(Architektonik)。③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832/B 860.因为,在这一部分之中,寻着理性的三个“理念”和与之相对应的三个推理形式,它不仅借由与“灵魂”对应的“定言推理”(kategorischer Vernunftschlusse),④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335/B 392.首先本原地指出了“自我”的规定为纯粹的“概念”,为我们的理性自身;进而,也利用与“自由”这一理念相对应的“假言推理”(hypothetischer)⑤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335/B 392.使得主观的理性展示为一个客观的“总体”;最后,它还利用与“上帝”这一理念相对应的“选言推理”(disjunktiver),⑥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335 f/B 392 f.将上述“总体”展示为我们理性整合其自身的原则而建构起来的一个“体系”。这么一来,最终,批判的确在“辩证论”部分不仅发展出了一个否定主观的“理念”为客观的“直观”的“规训”,也提供了说明理性如何架构“直观”为“体系”的“建筑术”。并且,这个“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不仅体现为发展一个客观法则的综合,也展示自身为一个主体对自身的整合和建构。
张华军:当我们把关注点放到“关系”上时,我们可能就要打破新手教师和成熟教师的界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新手教师对课堂非常艺术的处理,他能自觉地在一个不断生成的课堂允许很高质量的创造发生,而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在一个经验丰富的成熟教师身上发生。我们不能完全把它归结为天赋,它一定是与一个人的思维品质和他对教育的深层次理解有关,也与教师是否愿意探究课堂教学技术层面之外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有关。
四、 谬误:辩证的理性
通过区分“直观”和“概念”,批判表明了感知和理性是如此不同的认识能力,人们不仅能够也会将它们完全地分开,从而避免辩证及其带来的对理性的否定,进而维护理性的客观运用。然而,就是这个知识元素的区分也同样传达了我们对理性的认知难免陷入“谬误”,难免造成对理性的否定。因为,一个为“现象”,一个为“本体”,在知识这个理性的综合之中,“直观”和“概念”结合为了一个合二为一的“体系”。因此,即使二者存在着差异,人们也不免将它们错认,从而陷入辩证的“幻象”。当然,尽管结合“直观”,尽管以“直观”来显现,但是作为超验的规定,理性必然超出具体的“直观”而要求自己体现为普遍的“概念”。与此同时,作为“无限的量”,①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25/B40, A32/B48.“直观”也同样不能被看作一个普遍的“概念”,尽管它作为“现象”植根于“概念”这一“本体”。不然,不仅“概念”会成为“幻象”,“直观”也会失去它的“真理”。
不过,也正如批判也意识到的那样,仅仅是存在着“幻象”并不足以警戒人们去发现一个“谬误”,因而更不要说让人们去发现理性的正当运用了。与之相反,“幻象”不仅否定理性超验的认知,也会使人将理性的综合归之于无用。同时,因为提供了虚假的满足,它还会使人沉溺其中,而不去发现什么“谬误”。正如已经说明的那样,在“科学”这一理性的“体系”之中,理性也被视为“直观”这一“现象”的“本体”。这么一来,尽管有限的“直观”不足以使人认识超验的“本体”,因而后者只能是纯粹的“概念”的而不能是什么客观的“直观”。但是,二者的结合使人不免会将二者混淆,并且也会因为客观“直观”是主观“概念”的运用和实现而沉溺于“谬误”。② 休谟对理性纯主观的认定,即认为理性不过是我们的习惯,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例子。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放弃了理性具有规范我们感性的能力才得到的一个片面的认识。当然,这一拒绝形而上学的姿态批判并没有接受。相反地,将主观的规则看作是客观的法则,就是批判所针对的建立在辩证幻象之上的理性独断的运用(vg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713/B741)。当然,这样的满足也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似是而非。它不是现实的“真理”,而是辩证所导致的“幻象”。但是,因为还是有理性,就是发现有“幻象”,人们也还是会主张超验的规定并寻求它的实现。
为了本质地说明“直观”,为了本原地说明“概念”,需要进一步地批判在“分析论”之中解析了“范畴”这一“直观”综合的概念,并由此将“概念”指向了主体自身的一个系统性建构。不同于“直观”,“概念”则表明了知识之所以可能,有赖于主体自身的一个综合,有赖于我们“统觉”的发动和运用。并且,这个“统觉”的运用不仅能将“直观”综合起来,还能将其纳入一个主体的系统性建构。因为,正如“分析论”所表明的那样,一方面,作为综合“直观”的规则“范畴”体现着综合“直观”的普遍能力,也就是“统觉”。另一方面,“范畴表”也将“概念”指向了一个系统性的主观建构。因为,一个普遍的规定不可能存在于具体的“直观”之中,而知识却有普遍的元素,那么它也就只能存在于唯一赋予其可能的“概念”之中。① 关于物自身怎么与主体关联起来,在批判的表述中虽然有明确指向,即物自身对应主体自身,但却没有明确地说明。应该说,批判的先验的演绎可以让我们将理性追溯到主体自身的规定,但是批判现象和本体的区分也仍然需要进一步说明,对于批判哲学而言客体对应的是有限的经验,而主体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事物体现自身为自己的原则 (参见 G. Prauss,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Dinge an sich , Bonn, 1974;M. Willaschek, ”Phaenomena/Noumena und die Amphibolie der Re fl exionsbegriffe“,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Hrs. v. Morl, G. und M. Willaschek, 1998,Akademie Verlag, 1998, S.325-351)。
显然,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问题,不仅意味着出现了“谬误”,出现了外在的限制和否定,也意味着它陷入了自我否定以至于取消了自我建构的可能。将纯粹主观的“概念”与客观的“直观”相混淆,不仅会让人发现信以为真的“本体”不过是似是而非的“幻象”,同时也会遮蔽理性作为纯粹“概念”的主观性,从而会因被错认为“直观”而为其主张“独断”的运用。这么一来,就会造成理性自身不同观点的对立,以至于会取消其普遍运用的可能。这样,“谬误”之所以要认识,辩证之所以要消除,也就不仅在于它混淆让我们的理性的目的成了不具有现实性的“幻象”,因而否定了理性实现的可能;也在于它颠覆了理性,让实现理性自我主张成了理性的自我否定。也因此,欲成就理性及其形而上学的建构,就不仅要消除辩证,发现区别于具体客观“直观”作为“本体”的“灵魂”不过是纯粹主观的“概念”,也要消除它内在可能的冲突,使其成为自身的一个普遍的“立法”(Gesetzgebung)。⑦ Kan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S. A 839/B 867.
①《汉语大词典》将隐身解释为:1.不露身份;2.犹隐居,隐而不出;3.遮蔽身体;4.隐匿身形。将隐形解释为:隐没形体。
微小RNA含有18~25个核苷酸,是真核生物细胞内一类高度保守的内源性非编码单链RNA,能与靶基因mRNA3′非编码区特异性结合,在细胞增殖、分化及凋亡等生理生化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7]。Leung等[8]发现,miR-135a在恶性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组织中表达上调。体外实验表明,miR-135a可诱导子宫颈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能力,miR-135a过表达可促进Hela细胞在体内成瘤作用。表明miRNAs在子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抑癌或致癌功能,可作为生物标志物或治疗靶点应用于临床治疗,然而miR-145在子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尚不清楚。
对于这个任务而言,将“灵魂”作为“谬误”来阐明,应该看到,一方面,批判确实指出了它的空洞,指出了纯粹“概念”作为单纯主观的规定,自身不具有认识对象的能力。因此,批判就确实发展了一个消极的“规训”,否定了理性的超验认识的可能,将理性的运用限制在了“直观”的综合这一可能经验的领域之内。另一方面,区别于“直观”,它也指出了存在着主观的“概念”,因而为以“概念”为基础说明理性的普遍建构提供了可能。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地,它不仅能指出理性在形而上学之中何以出现自我否定的所在,还能为消除这一否定,转向理性正当的建构说明其必要和可能。因为,作为纯粹主观的规定,它不仅可以提出相对的因而自我矛盾的主张,还可以将对立的观点都综合在一个主观的、无所不包的系统之中。当然,这一意涵在“谬误推理”这一部分还没有触及。不过为此,它已经做好了铺垫。
五、结论
兼具感知和理智的我们虽可以运用普遍的后者来建构我们的本质,但是这一建构也同样受制于我们有限的前者。不过,尽管如此,这却并不意味着不同于可以带来客观真实的前者,后者的建构就只是主观的空想。的确,不同于具有客观性的前者,作为普遍规定的后者只是意识自身的原则。但是,前者只是限制了而不是否定了后者的运用。就前者缺乏普遍的规定而后者可以提供普遍的整合而言,我们始终有运用后者整合前者的必要。并且,后者的运用也不必然就导致与前者的辩证,从而带来后者的落空。正是后者运用到了前者之上,后者才得到了实现和满足。明确了两者的差异之后,就不仅可以免于辩证及其造成的对后者的否定,还能在后者之上发现整合前者的可能以至于给出落实后者的可能和建构。
与之相应,区分了“直观”和“概念”,还在“概念”之中又进一步地区分了“范畴”和“理念”,使得批判一方面可以排除“理念”被当作实在的存在而混淆了主观的“概念”和客观的“直观”的辩证,另一方面它也能够解释在“理念”之上说明“范畴”这一“直观”综合的必要和可能。当然,辩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足以意识到应该离开“直观”,返回“概念”,在“理念”之上把握理性的综合,因为,“直观”只是外在地限制了而没有否定了理性的运用。同时,“直观”不仅是限制,也是理性的运用和实现。再者,“幻象”就来自于上述运用,因而不仅容易出现,还会令人沉溺。因此,在“灵魂”这一理念之上发现存在“谬误”之后,“批判”也仍有必要再深入地指出“幻象”会导致理性自身的“背驰”,从而会取消它建构自身普遍运用的“理想”。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得到结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由于其仅仅是一种具有导向性的保护法,相关儿童健康权保护问题,尚缺乏倾斜性的责任条款予以规制。也是这一软法属性以及上述政策的导向性,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健康权保障力度是明显不足的。以《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五条为例,儿童健康权一旦受到不法侵害,应当如何维权,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暂无倾斜性的特殊保护,而唯有主管部门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加以更为强有力的行政处罚甚至于刑事处罚,才能更好的保护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权利。因此,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健康权,我们仍需要参考我国其他法律,加以综合梳理。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11-0024-08
*本文系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8wkpy6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 广,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275)。
a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Hamburg: Meiner 1998, S. A 342/B 400(按研究习惯标注A/B版页码)。
责任编辑:罗 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