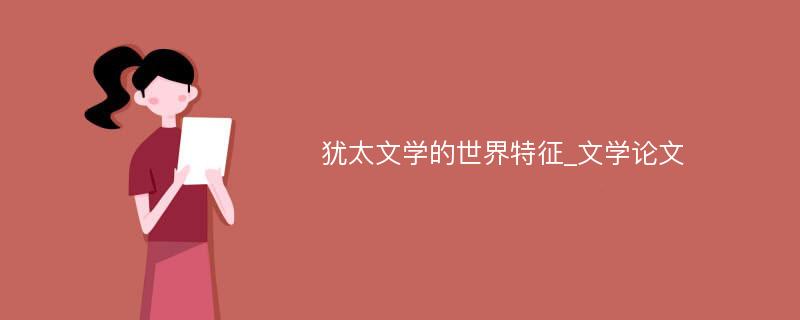
犹太文学的世界化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论文,品性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特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机制,犹太文学呈现出独特的世界化品性,这不仅对文学史的编写,也对一般的文学原理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犹太文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学—文化范畴,所以我们将由犹太人创作的并显示了一定犹太性的文学现象都纳入“犹太文学”之中。虽然有些作品对犹太要素的运用和对犹太性的表现相当含混与隐晦,但犹太文学(文化)的特质和力量有时恰恰就隐藏在这种含混与隐晦之中,就像卡夫卡(1883—1934)那样,尽管在其全部作品中几乎从未出现“犹太”的字眼,也未摹写过一目了然的犹太人的细节,然而“他对犹太人各方面的描述,其内容远远超过了一百篇科学论文。”〔1〕从苏联流亡到美国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 )的情形亦十分类似,他的作品已成为美国大学《现代经典犹太作品》课的必读书目。我们在此将卡夫卡、阿格农(1888—1970)、贝克特(1906—1989)、贝娄(1915—)、马拉默德(1914—1986)、布罗茨基等著名犹太裔作家的作品都归入“犹太文学”的整体视野之内,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陈述一个被人忽略的文学事实,而且也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批评框架,以寻求若干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普遍规则。
一
犹太文学的世界化品性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无国籍的文学”,文学发生和成长在广袤的空间范围,在文学整体上显现出散存的结构特征。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原是古代闪族的一支,约在公元前2000左右越过幼发拉底河进入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区,后因饥荒进入埃及,时值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时期(约前1710—前1580)。由于埃及法老兰塞二世(约前1617—前1580)的迫害屠戮,希伯来人被迫“出埃及”重返迦南。约在公元前1028年扫罗被立为王,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建立,但在公元前933年王国分裂,形成相互对峙的北朝以色列和南朝犹大。 公元前722年北朝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 族人被掳和流散各地以至不知去向,史称“失踪的以色列氏族”。公元前597年和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两次攻陷圣城耶路撒冷,数万犹太精英和民众被掳至巴比伦,即所谓“巴比伦之囚”,“犹太人”(Jew)便是其时希腊、 罗马人对沦陷后的犹大人的蔑称,后贬义色彩消失,成为对希伯来人后裔的通常称谓。此后,波斯帝国、马其顿、塞琉古王朝和罗马帝国等先后统治迦南地区,犹太人虽间或起义抗争,但在反抗罗马人的两次“犹太战争”(公元66年,公元132年)失败后,犹太人被迫离开迦南, 开始了历史性的“走家串户”。到公元7世纪时, 犹太人的足迹几乎遍及欧洲各国,19世纪中叶以后,美洲则成为犹太人的重要聚居地,据美国犹太年鉴统计,1790年美国的犹太人为1500人,到1900年猛增到100多万, 二战时则达到500多万人。〔2〕目前全世界约有犹太人1600 万, 仅美国就有600多万,有300多万人生活在以色列,其余多散布在东欧、西欧、美洲、非洲特别是前苏联地区。
犹太文学是伴随着犹太人散居世界的足迹而出现的。近代以前,犹太文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中东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邻近地区,上古希伯来《圣经》的文学传统得到较好延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塔木德》文学〔3〕, 在南欧则涌现了著名犹太诗人萨姆伊尔·哈·纳格德(公元933—1056年)、伊玛努伊尔·利姆斯基(1268—1330)等。 18世纪德国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倡导的哈斯卡拉(Haskala,意为“启蒙”)运动在欧洲犹太人中发生了重大影响, 它促使封闭的犹太生活走向世俗与开放,以此为标界,欧洲犹太人逐渐开始与西方全面接触。在此背景下,欧洲犹太文学获得迅速发展,到现代已成为欧洲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有戈·埃·莱辛的好友摩西·门德尔松、融学者和诗人于一身的纳夫塔利·赫茨·纳利泽(1725—1805)、著名诗人海涅(1797—1856)、诗人和评论家阿尔诺德·茨威涅(1887—1967);在奥地利,有著名作家施尼茨勒(1862—1931)、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在北欧则有丹麦的勃兰克斯(1842—1927)、196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籍女作家奈利·萨克斯(1891—1970);在东欧,有生活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的卡夫卡,俄国著名小说家伊格·爱伦堡(1891—1967)、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匈牙利艺批评家乔治·卢卡契(1885—1971);在西欧, 则有意识流小说大师马·普鲁斯特(1871 —1922)、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艾利亚斯·卡内蒂(1905—)等等。美国犹太文学起步虽晚,却有后来居上之势,较重要的作家有埃玛·拉扎勒斯(1849—1897)、玛丽·安汀(1881—1949)、亚伯拉罕·卡恩(1860—1951)、迈克尔·高尔德(1894—1967)、霍华德·法斯特(1914—)、辛格(1904—)、贝娄、马拉默德、布罗茨基、约瑟夫·海勒(1923—)、诺曼·梅勒(1923—)等等。非洲曾是犹太人的主要居住地之一,世世代代生活在非洲的犹太人在体质、气质上业已发生较大变化,遗憾的是这些具有东方人气质的非洲犹太人未能在文学上留下惊人之作,倒是一些后来的犹太移民及其后代在文学上建立了卓著业绩,他们的代表是199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籍女作家纳丁·戈迪默(1923—)和被称为南非小说的先驱者之一的丹·雅各布森(1929—), 后者曾荣获萨姆塞特·毛姆小说奖和《犹太纪事报》H·H·温盖特奖。在以色列, 从欧洲返回巴勒斯坦的作家与土生土长的作家相呼应,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66年诺贝尔奖得主阿格农,以及海姆·哈扎斯(1898—1973)和被称为“以色列最著名的在世诗人”的耶胡杰·阿米凯(1924—)。在世界其它地区,犹太文学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
二
值得强调的是,犹太文学的这种散存结构不仅是文学的存在方式,同时也蕴涵着特定的文化语义,即呈现了犹太文学在文化属性上的散化特征。一般而言,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无可避免地处于同所居住地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关系之中,文化冲突体现了犹太人对文化传统的固守取向,而文化融合则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变迁。因此,不同文化缝隙中的犹太文化及文化群体便形成了若干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差异的犹太文化单元,因而可以说犹太文化的主流是由各种犹太文化支流汇聚而成的。各犹太文化单元及作为文化载体的犹太人,在以各种方式呈现出一定的犹太特质的同时,也打上了鲜明的居住地文化特征,就像美国犹太人那样既是犹太人,也是美国人,但同时不同于俄国犹太人,也不同于德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本土的犹太人。犹太文学的多样性及犹太人的多重文化特征,决定了犹太文学在文化属性上的独特的散化性质,即散存于世界各地的犹太文学既属于居住地文化,也存在于犹太文化的整体之中。应该指出的是,文化属性的散化并不意味着文化意义的减少,相反它表明了文化内涵的增加和拓展,并显示出一定的世界化趋向。
南非籍犹太女作家纳丁·戈迪默被誉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士,她的主要作品《六英尺土地》(1956)、《伯格的女儿》(1979)、《我的儿子的故事》(1990)等都包含着对南非当局种族歧视政策的抗议,她的一些作品曾因此而遭到查禁。作为一位犹太作家,她的种族平等思想和对黑人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犹太民族的历史遭遇紧密相联的,正因为如此,她能克服种族界限,自我感觉到“和黑人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事实上,她对种族问题的探讨不仅是针对南非的,也是针对整个世界的。
但评论界在评论散居各地的犹太作家时,往往只强调了他们的居住地文化特点而忽略了深层的犹太要素。这与散居各地的犹太作家的国籍、作品中强烈的非犹太文化特征有关,也与文学作品中犹太性的隐晦和模糊有关。犹太性作为犹太作家对犹太文化要素的消解、运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民族性品质,在具体作品中往往有着方式、程度上的巨大差异。一部分作家惯以写实的态度,直接运用犹太生活素材,以极鲜明的方式来表现犹太移民的生活和思想,辛格和马拉默德主要关注东欧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的历史遭遇、现实困境,萨克斯则将个人被驱逐、被迫害的经历与欧洲犹太人的共同命运相联系,表现出突出的民族意识和历史感,她的名剧《伊莱》(1943)就是在听到纳粹分子对东欧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后,用几天时间赶写的一出反映欧洲犹太人的遭遇和心理的名剧。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作家大多不是直接具象化地把犹太生活作为文学的客体对象和表现重心,而是意象化地运用犹太生活,将犹太要素消解为文学的潜在媒质,以犹太民族特定的历史、境遇、宗教、观念等方面的个别因素作为文学的某种构因,从而生发出特定的象征、隐喻、暗示意义,既表现了深厚的和超越犹太的文学意味,也暗含和焕发了一定的犹太特性,卡夫卡、普鲁斯特、贝克特、贝娄、罗斯等都是这样,如果不了解他们与犹太要素的内在联系,便不可能理喻他们的创作资源及其深刻的文化蕴涵。卡夫卡生前唯一的好友、学者马克斯·布洛德在谈到《城堡》中的K时说:“他是陌生人,他碰巧来到村子里。 那里,陌生人满腹狐疑地注视着他——这就是犹太人特有的感觉……卡夫卡这种描写的基础,是他的犹太人的思想。”〔4 〕菲力浦·罗斯在他的《再见,哥仑布》(1959)、《鬼作家》(1979)等作品中,讽刺、嘲弄了犹太人的传统生活,为此他曾遭到犹太组织的激烈抨击,但他对犹太传统的背离同样是对犹太要素的一种运用,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了罗斯的犹太性。
三
犹太文学的世界化品性还突出地体现在犹太文学的语言构成上。在这时,如果试图以某种语言来作为犹太文学的标识,就像以日语作为日本文学的标识那样,那就很难行得通了。犹太文化在其历史沿革中,曾创造和使用了两种犹太性语言,即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希伯来语属闪族语系的一支,在形成过程中吸取了迦南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等的要素。在“巴比伦之囚”至纪元前后这段时间,犹太人深受巴比伦人使用的亚兰文的影响,希伯来语的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流散时期开始特别在中世纪以后,希伯来语逐渐成为犹太民族专门性的宗教用语,往往只在规范的书面写作和宗教生活中才被运用。随着现代哈斯卡拉运动和锡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回归巴勒斯坦的俄国犹太人埃利泽·本·耶胡达(1858—1922)的倡导下,“死去”近千年的希伯来语才重新得以复活,这被认为是世界语言史的一大奇迹。意第绪语是欧洲犹太人在长期的流散生活中将希伯来语与德语、斯拉夫语等欧洲语言混合后创造的一种犹太性语言,形成较晚,它仅流行于欧洲及从欧洲移至美洲、以色列等地的犹太人当中。使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创作的文学,文学史上分别冠以希伯来文学和意第绪文学的称谓,被视作犹太文学的基本部分。“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默海德·哈伦·金斯伯格(1796—1846)、金斯伯格的朋友、 诗人多夫·亚伯拉罕·哈科恩·莱温佐思(1794 —1897)、近代希伯来小说的创始者亚伯拉罕·玛普(1808—1867,著有《锡安山之爱》)、什约·阿布拉莫维茨(1836—1918,即“书贩子门德勒”,《父与子》的作者)以及撒·约·阿格农等都是使用希伯来语创作的著名作家。意第绪文学在13—16世纪时主要成就集中在德国、意大利,19世纪末以后重心逐渐转移到东欧、苏联和美国,最著名的则是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巴·辛格,他坚持以意第绪语创作,是贝娄等人把他的作品转译为英语的。
除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以外,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直接采用借居住地的语言来进行创作,在现当代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许多作家还能掌握和使用两种以上的西方语言。运用外族语言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犹太人的一种传统,甚至在希伯来《圣经》中的某些章节(如《但以理书》、《以斯拉记》)也曾间或使用过亚兰文,犹太文化的其它经典性著作(如《次经》、《伪经》等)都曾直接使用希腊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等异族文字。所以现当代犹太作家对非犹太语言的大量采用是与其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相联系的。1966年使用希伯来语创作(亦有少量意第绪语作品)的以色列作家阿格农和使用德语创作的瑞典犹太人萨克斯被同时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在授奖辞中曾特别指出:“本奖金由他们两位合领确实具有其特殊原因:表彰这两位作家,是由于他们虽然以不同的文字进行创作,但他们出于同一种精神,并在继承犹太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相辅相成。共同的创作灵感正是他们两人不可缺少的力量。”〔5 〕瑞典学院的这一评价对于许多使用非犹太语言创作的犹太作家是同样适用的,并符合他们的实际情况。
四
犹太文学的主题复杂多样,有代表性的倾向是努力追求文学主题的恒定性和形而上性,不仅揭示犹太民族千百年历史上的一贯难题,而且显示出超越时空、种族、国界的普遍意义,尤其是那些“使用西方语言的犹太作家还将犹太问题、思想风格、情感方式引入其他文学: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特别是英语文学。 ”〔6〕
犹太民族长期生活在异族文化的夹缝中间,犹太人的普遍困惑往往首先集中体现在自我身份的困惑上,这种对身份的自觉在文学作品中常常体现为强烈的局外感、边缘感乃至非我的异化感。索尔·贝娄在他的《挂起来的人》(1944)、《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雨王汉德森》(1959)、《赫索格》(1964)、《洪堡的礼物》(1976)、《忧思更伤人》(1987)等作品中,系统地塑造了现代的流浪汉和精神流浪汉,他们为寻找自我、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建筑精神家园而四处漫游,但始终无结果,成为被“挂起来的人”。贝娄成功地将犹太人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与当代西方人的自我危机结合在一起,这体现出了他的深刻的洞察力。犹太作家在演化犹太民族的身份困惑时,往往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从而显示出各自的文学个性。美国犹太剧作家阿瑟·米勒在名剧《推销员之死》(1949)中所生发出的那种关于人际关系和人类社会中的“推销现象”和“市场原理”,里面就隐暗含着犹太民族几千年来在世界各地的“推销”经验;卡夫卡作为寓言大师,则以极度的夸张在《变形记》(1915)中叙述了萨姆莎由人变成甲虫的故事,这个荒诞名篇的构思,可以在卡夫卡的最后一个作品《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1924)中找到其中的犹太索隐,在这部作品中,卡夫卡将异化的犹太人比作耗子:“我们这个民族几乎总是在忙碌活动,经常目的不很明确地到处奔波。”〔7〕所以在卡夫卡的“耗子”、 “甲虫”之类的变形形象中,无不包含着他对犹太民族境遇的感悟及其与现代人类普遍命运的某种契合。艾蕴·施泰恩堡在分析卡夫卡的《在流放地》(1919)时说过,读者如果没有犹太教的知识便不可能透彻理解这篇小说的细节和思想,同样,忽略了犹太作家的文化背景,也就很难把握其文学作品的发生、结构和蕴涵。
犹太文学还以其特有的历史意识发掘和升华了犹太文化中的各种悖论因素,进而对人类现实命运中不可摆脱的矛盾作了集中探讨。在犹太文化的观念世界中,犹太民族是受上帝特殊眷顾的“选民”,上帝的光芒首先普照到犹太人身上,然后才折射到其他民族。但在犹太人的经验世界里,犹太人却极其敏锐地感觉到了人类的种种苦难和不幸。诸如此类的深刻悖论存在于犹太文化的方方面面,以致于敏锐的犹太作家都不约而同地以“悖论”的镜像来观照现世生活,西方社会中人的种种矛盾与两难在犹太作家笔下得到了极为充分的揭示,并在一定程度上由此诱导了整个西方文学对悖论问题的关注。卡夫卡的《城堡》呈现了多重性的意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揭示了一个类似西叙弗斯般的困境:目标(城堡)虽有,道路却无,更难以企及,只能周而复始地徘徊于希望与失望的魔圈。卡夫卡在《皇帝的御使》中更为集中地揭示了这种困境,在接到皇帝派遣的谕旨后,“使者便立刻出发了……如果是在空旷原野上,使者就快步如飞,不久你就会听到他响亮的敲门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力气白花了。他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里的殿堂,但他怎么也通不过去。即使他通过去了,那也是白费力气。因为在下台阶时,他还得经过一番努力,如果下去了,仍然是无济于事。他还必须走遍所有的庭院。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层宫阙。紧接着的又是石阶和庭院,往前走又是一层宫殿。就这样,宫阙和庭院重复着出现,循环往复,无穷无尽,几千年也走不完。”〔8〕
类似的魔圈还有著名美国犹太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3)等等。诺曼·梅勒在他的《一场美国梦》(1965)中强调了主人公自身的悖论和分裂:斯蒂芬·理查兹·罗杰克因痛苦万分而盼望得到拯救,但他摆脱痛苦的途径却是凶杀和放任情欲,显然,他只能步步走向难以自救的深渊。在当代犹太文学中,事与愿违的失败者(《雨王汉德森》)、追求爱情却又为爱情所困的倒霉蛋(贝娄《赫索格》、《忧思更伤人》、马拉默德《杜宾的传记》)之类的形象屡见不鲜。
五
作为一个文学整体,犹太文学最突出的艺术精神就是它的整合意识。犹太民族在长期的流散生活中,形成了典型的文化兼融心理,就像文化心理学家S.阿瑞提所说:“‘接受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刺激’尤其适用于犹太人。古老的希伯来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影响相结合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对立……对于无论来自多数人还是来自少数人的不同意见都一概予以容纳,这一直是犹太人当中流行的态度……作为一个在其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民族来说,他们高度重视容纳态度所具的价值。”〔9 〕这种容纳态度在犹太文学的艺术精神上亦得到了充分体现。犹太文学的整合精神体现在不同的层次和方面,从犹太与非犹太的文化背景,到抽象与具象的艺术思维,乃至到文学文本的营造、文学技巧的运用等等,许多悖逆的因素在这里都得到了奇妙的结合。辛格、马拉默德等写实型作家在其作品中曾程度不同地运用了象征、虚幻等非实的现代性手法;罗斯、海勒、梅勒等所谓现代派作家也将表象的荒诞与本质的真实、抽象与具象等等因素统纳为一体。关于索尔·贝娄究竟属于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前些年曾有一场小小的争论,今天看来,简单地以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或两者的结合来界定贝娄,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贝娄的整合既体现在创作思潮上,也体现在文本构建和技巧的各个方面,比如在小说模式上,贝娄融合了流浪汉与精神流浪汉两种类型,在小说视角上同时运用了单一视角和复合视角,在人物构建上,将人物的心态与性格、自身与替身等因素相结合。〔10〕同时,犹太作家的整合精神也不是一般的“相加性”综合,而是在各悖逆的因素之间建立互补的有机联系,并从中获取超越性的升华,就像萨特所说,“全体大于且不等于各部分之总和。”〔11〕综观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整合已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走向。当然,犹太文学的整合精神只是就其一般情形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都以等量的方式实现着这一精神,否则,也就抹煞了文学的自律特性和作家的创造个性,这是无需赘述的。
犹太文学的世界化品性是犹太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和表征,犹太文学中的犹太性与世界性是一组对立统一的范畴,因为犹太性的本身便包涵了一定的世界性意义,而世界性的实现则又进一步丰富、充实了犹太性的内涵。这也是犹太文学何以在现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据突出地位、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之所在。在近90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中,犹太裔作家就有10位,即柏格森(1927)、帕斯捷尔纳克(1958)、阿格农(1966)、萨克斯(1966)、贝克特(1969)、贝娄(1976 )、 辛格(1978)、卡奈蒂(1981)、布罗茨基(1989)、戈迪默(1991),而且在西方诸多现代文学潮流中,往往都有犹太作家走在前头,比如卡夫卡之于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之于意识流,贝克特之于荒诞派,约瑟夫·海勒之于黑色幽默、后现代主义,金斯堡之于垮掉的一代,等等。
歌德曾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也认为中国、印度、以色列(希伯来)、希腊四个文化“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但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12〕在“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3〕的现代社会里,犹太文学的世界化品性已经并将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它对世界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性意义。
注释:
〔1〕〔4〕〔8〕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周建明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69、254页。
〔2〕阿瑟·A·戈瑞《美国犹太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3〕《塔木德》(Talmud)——犹太人的口传律法总集, 被认为是仅次于希伯来《圣经》的第二经典。
〔5〕《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毛信德等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06—507页。
〔6〕罗伯特·M·塞尔特泽《犹太人民,犹太思想:犹太的历史经验》,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0年,第715页。
〔7〕孙坤荣选编《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7年,第344页。
〔9〕S.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430页。
〔10〕参见拙文《心态与性格,自身与替身——贝娄小说的人物构建》,见《求是学刊》1991年第6期。
〔11〕萨特《反犹太者的画像》,见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2页。
〔12〕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第20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345页。
标签:文学论文; 犹太民族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卡夫卡论文; 作家论文; 贝克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