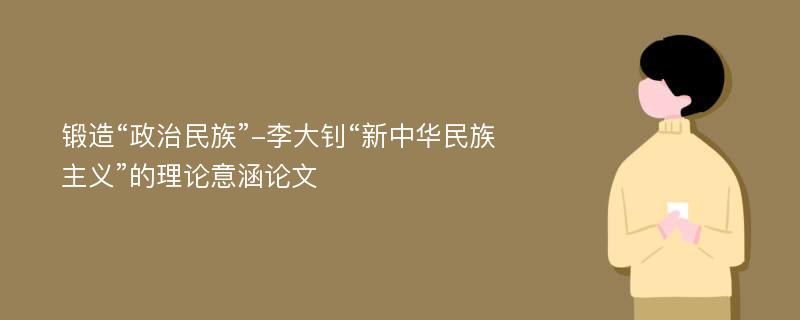
锻造“政治民族”——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
王 锐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李大钊颇致力于阐述“新中华民族主义”。在他看来,“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即强调此主义之“新”,在于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文化上、风俗上、语言上的区隔,在参与新政权的过程当中形成坚实稳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政治民族”。此外他相信,实践“新中华民族主义”是对全球不平等支配体系的冲击,如果中国的革命者能和周边地区的革命者充分合作,那么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新亚细亚主义”,将提供想象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让李大钊得以更为直接且犀利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矛盾,让他能够从全球革命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说,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日趋清晰透彻。
[关键词]李大钊 新中华民族主义 新亚细亚主义 马克思主义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首要任务在于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的领土版图,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进行各方面的现代化基础建设,让中国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国富民强。许多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促进了这一过程,才能具备基本的合法性。它“作为一种政治纲领,一种理论体系,一股社会思潮,绵延不断而又高潮迭起,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①可以说,近代许多政治势力、社会组织、文化团体、思想流派,都曾对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实践方法展开分析与讨论,并以此作为表达自身政治与文化主张的不证自明之基本前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伴随着国内爱国者的民族屈辱感与海外留学人士的巨大改革热情,民族主义思潮更是风行一时。②尽管五四运动的思想言说中具有一面宣扬民族主义、一面憧憬世界主义的“两歧性”,③但正如论者所言,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民族主义仍是理解他们言行的重要概念工具”,即便曾设想世界主义的未来图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或应说是潜藏而不是丧失”。④因此,“今天对五四思想的再认,不要太受民族主义观点的牢笼”⑤固然十分重要,但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民族主义主张,较之力图用世界主义来稀释其意义与影响,或许更应深入具体文本,仔细解读其中的思想内核与理论意涵,以求更为深入地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特色,分析为何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民族主义论述者中,李大钊无疑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代表人物。不同于陈独秀一度质疑国家的存在有无合法性,李大钊不但强调救亡图存的重要性,而且在1917年2月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具体宣扬其民族主义主张。甚至有论者认为,李大钊“生活在有浓厚民族主义气氛的环境中,并且以直率的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倾向著称”,同时认为“民族主义是促使李大钊响应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因素”。⑦本文即以李大钊所提倡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为切入点,分析他的民族主义主张之思想特色与理论意涵,并且探讨其民族主义思想与他的其他思想主张之间的复杂关系。⑧
一、“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思想基调
自从参与政治论争开始,李大钊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唤起广大民众的“自觉心”,通过共同的努力来改造中国政治,让中国走出动乱与衰败的颓势。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宣称“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就这一点而言,“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因此实难让人心生爱戴之情。⑨他甚至认为“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⑩针对此论,李大钊强调:
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是故自古无不亡之国,国苟未亡,亦无不可爱之国,必谓有国如英、法、俄、美而后可爱,则若而国者,初非与宇宙并起,纯由天赐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凭其国民之爱国心,发挥而光大之,底于有成也。⑪
可见,李大钊固然承认中国当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弊病,但这并非抛弃国家观念的理由。他强调“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因此每一个国民能否产生祛除弊病、建设良好国家的“自觉”,实乃能否出现“可爱之国家”的关键。⑫在这里,李大钊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之良莠建立在国民是否有“自觉心”上面,呼吁充分唤起广大民众对于改造国家的情感与能力,在这一参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锻造国民对于国家的基本政治认同。⑬
晚清以降,民族主义思潮涌入中国。按照时人的理解,“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⑭此处所言的“风俗”“历史”“语言文字”,意在强调民族主义思潮与过去延续的传统之间具有不可或缺的关联。也正因为如此,晚清许多历史论著,都强调如何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培育爱国思想。⑮而这种从公民性与政治性着眼来强调“历史”与“传统”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之所以能盛行的重要文化因素。⑯
与之不同,李大钊认为国民热爱国家的“自觉心”,不能主要依靠历史与传统的因素,而应唤起人们对建设新的政治与文化之热情。他认为“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因此,有志于从事救国事业者,必须“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⑰基于此,李大钊认为今世最能担当更新中国、再造国家之任者非青年莫属。他坚信“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所以“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⑱很明显,李大钊强调的个人突破旧因素的网罗,呈现出青春的各种样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形塑新的政治实践主体,使其能够以新的理想与诉求投入到改造中国的事业当中。⑲
[24]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说起近代中国对“青年”和“少年”抱有一种新的政治期待,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按照黄遵宪的说法,梁启超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参见黄遵宪:《致饮冰主人书》,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8页。作为自清末就开始思考中国现实政治的青年才俊,李大钊应该十分熟悉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当他对民初政局感到不满,希望有新的政治力量来改变时局时,极有可能会借助梁启超式的思考方式,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
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调之上展开论述的。他强调:
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龂龂辩证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23]
突出青年的重要性,是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内容。[24]而他这里所言的民族问题乃当时世界的主要问题,可以放在一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战局的观察这一背景下来理解。正如汪晖所指出的,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东方杂志》的作者们多聚焦于战争与民族国家体制的关系。他们多认为在这一体制下,民族认同超越种族认同,导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激烈的战争。为了避免被殃及甚至瓜分的命运,必须唤起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与民族自觉。[25]或许可以认为,李大钊竖起“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旗帜,也和这一言说氛围息息相关。[26]
在李大钊看来,“十九世纪以还,欧洲大陆茁生于拿翁铁骑之下者,实为国民的精神”。[27]在民族主义思潮的鼓动之下,欧洲许多小国从过去的帝国当中独立,旧有的政治合法性论述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左支右绌。霍布斯鲍姆认为,在19世纪欧洲,“一旦国家能顺利将民族主义融入到爱国主义当中,能够使民族主义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情感,那么,它将成为政府最强有力的武器”。[28]对此李大钊亦十分清楚。他认为在近代,“发扬蹈厉以树国民的精神,亿辛万苦,卒能有成者,则德意志帝国之建立、意大利之统一,其最著矣”。[29]在此风潮之下,“国民的精神既已勃兴,而民族的运动遂继之以起”。[30]李大钊注意到当时许多国家都在倡导具有本国特性的民族主义,如德国的“大日耳曼主义”、俄罗斯的“大斯拉夫主义”、英国的“大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甚至他把美国的“门罗主义”与印度的独立运动都视为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虽然他并未辨析这些政治口号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帝国主义借民族主义来进行全球扩张与殖民地国家运用民族主义口号展开独立运动之间决然不同的性质,但通过审视这一全球局势,李大钊认为如何建立中国的民族主义纲领,已然成为迫在眉睫的时代主题。
李大钊指出:“民族主义云者,乃同一之人种,如磁石之相引,不问国境、国籍之如何,而遥相呼应、互为联络之倾向也。”因此在具体的政治实践里,就有可能出现“或同一国内之各种民族有崩离之势,或殊异国中之同一民族有联系之情”的现象。[31]那么“新中华民族主义”能够实现的政治与文化基础为何?这更是李大钊必须要充分考虑的问题。
作为19世纪著名的民族主义阐释者,勒南认为民族精神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集体拥有的丰富回忆,其次是当下在一起生活的愿望。[32]某种程度上李大钊对“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论述也体现出类似的思路。在他看来,“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33]可见,李大钊认为中国各民族之间长久的交往与联系、中国文化里“高远博大”的政治传统是构成“新中华民族”的历史基础。而他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也基本继承了清末梁启超、杨度等人提倡的整合各民族于一体的“大民族主义”理论。[34]这一点显示出晚清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具体而微的影响。
不过李大钊在论述“新中华民族主义”时,除了显示“中华”代表因“高远博大之精神”而形成的各地人民“畛域不分、血统全泯”这一历史与文化遗产,更为重视的是在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语境里,各民族所可能产生的休戚与共感:
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属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35]
很明显,李大钊认为各民族在辛亥革命之后共处于“共和国体”之下,是“新中华民族”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在中国出现,为“新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共同致力于“共和国体”的奠基与建设,是“新中华民族”能够形成稳固认同的情感与心理基础。借用韦伯的观点来理解,“这种政治命运的共同体,即生死与共的政治斗争共同体,会在各个群体当中产生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往往比单纯的文化、语言或人种共同体的纽带具有更深远的影响”。[36]如果说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确立起由人人自主而奠定的民族主权”,进而锻造一个“政治民族”,[37]那么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即强调此主义之“新”,正在于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文化上、风俗上、语言上的区隔,不再将民族主义内涵单纯地借助于符号式的、本质主义式的“文化”,让在中国国土内生活的各族人民,在参与新政权的过程当中形成坚实稳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政治民族”。[38]
二、“新中华民族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还强调:
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兹其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主义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的自觉尚矣。[39]
传统媒体的盈利主要在于收视率和广告宣传,新媒体融合形势下,要善于整合不同的营销渠道,包括广告的宣传模式、相关产品的推介等,都要采用全新的模式。目前,微信的广告宣传采用植入软广告的方式,宣传内容设置专门的文章,有很强的代入情境。借助网红的个人影响力,对媒体的宣传形成名流效应。对于营销策略的整合,还在于与多家媒体的通力合作,双方信息的共享,降低信息获得的成本,促进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借助互联网技术,不断更新媒体传播方式,促进传媒业的变革。
无可否认,李大钊在这里对中国面积之大与影响之广的具体描述,或许有溢出历史实相之处,[40]但他强调在审视亚洲问题之时,中国的地位至关重要,中国在历史上曾极大地影响周边地区的政治与文化形态,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显示出李大钊在论述“新中华民族主义”时,并非停留在中国内部展开思考,而是设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化会给周边地区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因此,李大钊提倡“新中华民族主义”,必须面对当时另一种由日本所描述的亚洲政治图景——“亚细亚主义”。作为近代日本在面对西方势力东渐的危急时刻,围绕着“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特定的亚洲观及其政治思想与实践诉求,[41]“亚细亚主义”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在此基础上应形成怎样的对华策略。随着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海外扩张的野心日益增强,古典亚细亚主义中的那种认同东方文化,把亚洲视为一个整体并力求振兴亚洲的思想因素日趋衰亡,通过侵略中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获取自身利益,维护日本政治与经济霸权的扩张型亚细亚主义尘嚣直上,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42]对此,一战爆发之后,杜亚泉、章锡琛等人在《东方杂志》上频繁专文讨论这一思潮,一方面介绍日本舆论界对“亚细亚主义”的论述,另一方面批评这一主张在学理上有不少缺陷,在实践上只能导致亚洲局势越发扑朔迷离、危机四伏。[43]
依李大钊之见,提倡一种区域联合的政治口号在当时实属必要,但其内容实质必须区别于日本为对外扩张张目的“亚细亚主义”。[45]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口号之下唤起广大民众参与改造中国,能够给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设想新的区域联合之可能性:
以吾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其宏阔,族众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夸,亦实举世所公认。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45]
⑪ 李大钊:《厌世心与爱国心》,载《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51页。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批评日本式的“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49]它采取的是帝国主义的逻辑,根本无助于亚洲的区域和平与平等。他指出:“日本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倘或有外来之势力横加凌制,不惟不可助虐,且宜念同洲同种之谊以相扶持相援助,维护世界真正之道义,保障世界确实之和平。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50]在另一篇文章当中,李大钊更是直言:“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倡的,不是为怕欧美人用势力来压迫亚洲民族而倡的。我们因为受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压迫,我们才要揭起新亚细亚主义的大旗,为亚洲民族解放的运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51]
近藤邦康曾以民众作为帝制时期被统治的客体,如何经由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论述而逐步转化为革命主体为线索,来分析李大钊与晚清思想的内在联系。[52]其实李大钊在分析“新中华民族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之关系时,也延续并发扬了晚清思想中的相关议题。章太炎在1907年曾发起创办“亚洲和亲会”,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而中国在其中的意义,便是作为一个亚洲的大国,“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十数邻封,因是得无受陵暴”。[53]换言之,章太炎所构想的亚洲区域体系,是要在各殖民地与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摆脱这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并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全新的、平等的政治格局。章太炎希望中国的反清革命在其中能起到示范作用,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反帝运动。此外,他认为“中华民国”的“中华”,代表了特定疆域内创建各种政治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以及不断实践与完善这套制度的人,“中华”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承认与概括。正是拥有了数千年丰富的生产、交往与组织经验,“历史民族”才有可能成为具有自觉政治意识的“政治民族”。[54]可以说,李大钊关于“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论述,进一步继承、延续了章太炎对“中华民国”的性质与意义的分析,深化了清末革命的时代主题。[55]
前文谈到,李大钊认为践行“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力量是中国的青年,“新中华民族主义”逐步实现的过程,也正是新的政治主体诞生、成熟的过程,这也是“新中华民族主义”之所以“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设想中国青年在从事更新中华的事业的同时,也应成为“新亚细亚主义”的重要参与者:
亚细亚的青年,就该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打出一道光明,使我们亲爱的兄弟们,在真实的光辉之下,开诚心,布公道,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运动,断不可再受那些特权阶级的愚弄、挑拨、隔阂、遮蔽。中华的青年应该和全亚细亚的青年联成一大同盟,本着全亚改造的方针,发起一联合大运动。[56]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强调:
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57]
梁启超认为:“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是即所谓天下也。换言之,则我中国人之思想,谓政治之为物,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5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之际,严复就预测:“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59]当时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都期待一战能一扫19世纪列强争霸之惨状,为缔造全球大同式的世界主义制造条件。[60]与很多人一样,李大钊在当时也对世界主义心向往之。他呼吁:“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61]这一点表面上确实呈现出与“新中华民族主义”之间的“两歧性”。但如果分析“新中华民族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即二者都旨在打破旧有的、不合理的束缚与压迫,突破不平等的内外体系,向往通过新的政治主体来实现新的联合形式,那么我们便可看到,从中国自身的视角出发,“新中华民族主义”堪称塑造一个新世界的起点,可以“打出一道光明”,提供了想象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可能性,而非苦恼于一厢情愿地把西方当成“世界”,但后者却并未把中国视为其中一员,因此只能沦为中西之间边缘人的窘境。[62]因此,李大钊思想中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具有不少共通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的。
三、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在比较中日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时,丸山真男认为中国在晚清未能通过改组统治阶层的内部结构来实现现代化,因此遭受了列强的长期侵蚀与渗透。但也正由于这样,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为了能够最终反抗帝国主义,必须完成从根本上改革旧社会与旧政治体制的时代任务,所以民族主义与革命运动具有内在结合之特点。[63]回到历史现场,辛亥革命之后,列宁从全球革命形势变化的角度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因此,“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64]在这样的视野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全球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以此为切入点,我们也可以理解李大钊从提倡“新中华民族主义”到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
[34]关于晚清思想论争中的“大民族主义”观念之详情,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60—65页。
[28][英]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21页。
“五四”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将“中国的民族革命理解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革命”。[76]这意味着在他们的政治视野里,中国自身的解放与改造离不开世界其他地区革命所带来的全球政经体系的变化。李大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他指出:“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所以,“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77]此处所谓的“世界革命”,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民族主义固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但其结果并不仅是让中国国内的境况有所改观,而且是以此为出发点,让中国革命具有世界意义,成为突破19世纪东西方列强所形塑的世界体系的重要起点。总之,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国家、资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方法,李大钊的民族主义始终是在一种国际视野之下呈现出来的。
当User1发布一条消息m,m会发送到标注模块进行词性标注和语义分析得到m0,并存储在在线社交应用中。然后,User2向访问控制模块提交访问m的请求,访问控制模块对该请求进行评估,并评定经过词性标注的消息m0的敏感度。最后,根据User2亲密程度的不同运用相应的隐私规则得到新的消息m1,发送给User2。
在这里,李大钊将“弱小民族”与“无产阶级”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受到政治与经济上不平等支配的受害者。1924年他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演讲“人种问题”,便从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系入手,分析晚近以来的全球局势,以及中国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他指出,欧洲人秉持“文明论”的观念,认为白人支配全球理所应当,其余国家及其人民,“只有退化,只有堕落”。他们认为:
就这个问题而言,从访谈和观察中可以看出,他们中客观存在毕业前已恋爱和未恋爱两类人群,两类人群绝大部分对婚恋问题持积极态度,认为随着社会接纳度的提高,婚恋问题会有所好转。但事实上,已恋爱和未恋爱的人都对这个问题心存忧虑。
白人在世界上居于引导文化的先驱,视异色人种为低下阶级而自居于高上的地位,因此人种问题在世界上也成为阶级的问题,于是世界上就形成了相对的阶级。人种的斗争于将来必定发生,这是可以断定的。而且这斗争或许为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战争而与“阶级斗争”并行哩![78]
COAR拥有遍布全球的3000多个机构知识库,这些机构知识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学术传播模式的转型。以前由图书馆或学术机构建立的机构知识库往往各自为政,今后要通过集体管理与合作,将传统的由图书馆或学术机构购买资源转变为由图书馆或学术机构储存并与外界公平分享本地资源。在技术层面上,过去图书馆把重心放在元数据上,认为只要做好元数据管理就可以了,资源放在哪里无所谓,而忽略了对资源的管理。“下一代机构知识库”要求图书馆关注两者,将元数据和资源都放在一个可共享的开放平台上。
李大钊的这段话,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被理解成“对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给予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辩护”,[79]但如果将眼光放到整个19世纪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全球殖民主义的兴起这一时代背景中,特别是亚洲与非洲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日渐被帝国主义国家所瓜分、支配、殖民,[80]那么李大钊在这里谈到的人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本质上是阶级问题的观点就自有其合理性与针对性。基于此,李大钊强调民族之成立“要更兼有主观的事实,要在相互的意识之承认及精神上认为同族之后而民族才能成立”,所以,“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同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猛力勇进,要在未来民族舞台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81]就此而言,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存在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马克思主义赋予他的,是较之先前更为广阔且有深度的分析视野,以及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政治学说。这预示着此后政治行动中的“民族特性”,已经融入了不容忽视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要实现民族独立,离不开阶级解放。革命者们必须要思考,如何将这一因素更好地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这一政治理想所要达到的目标。
四、结语
在一篇写于1923年的文章中,李大钊饱含感情地指出:“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够感觉到的。”他坚信“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82]秉持这样的态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李大钊颇致力于阐述“新中华民族主义”。在他看来,中国各民族在辛亥革命之后共处于“共和国体”之下,是“新中华民族”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在中国出现,为“新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犹有进者,李大钊在论述“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同时,还在积极设想一种不同于日本为了称霸东亚而故作标榜的“亚细亚主义”,能保证区域平等与和平的新的联合方式,他将此称之为“新亚细亚主义”。他相信,实践“新中华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对全球不平等支配体系的冲击,如果中国的革命者能和周边地区的革命者充分合作,那么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新亚细亚主义”,将提供想象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设想借由锻造新的“政治民族”,再造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实现一个平等无压迫的世界,凡此种种,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正如论者所言,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神圣诉求,总是和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正当性之声张,以及在此名义下的民众动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83]马克思主义让李大钊得以更为直接且犀利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矛盾,让他能够从全球革命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认识到广大的底层劳动者身上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在他那里,民族独立与阶级翻身,是一体之两面。可以说,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日趋清晰透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他开始走向政治行动,着手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深刻影响着下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探索、实践让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向独立富强的方法与道路。[84]
注释:
①姜义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载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所谓主观因素是行为主体能够把控的因素,是因人而异的。通过行为人自身的努力,不断提高,完全可以克服困难,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如临床知识、临床技能、临床思维、临床经验等[4]。
②[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页。
③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张灏:《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132—136页。
④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载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366页。
⑤同注③,第135页。
[27]同注23。
⑥黄兴涛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产生与流衍入手,通过耙梳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文本,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与影响,实为迄今为止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最为详实且丰富的论著。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关于笔者对此书的具体评论,参见王锐:《王锐评黄兴涛〈重塑中华〉:思考近代中国关键问题的视角与方法》,“经略网刊”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G1zupYlFAhhkLYmMDfgxg。
⑦[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⑧关于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黄兴涛曾揭示其不容忽视的思想遗产,正是受此启发,笔者开始注意李大钊的这一思想面向。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126页。此外,张三南、吕伟波曾对《新中华民族主义》进行探析,但其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文本介绍的层面,未能从思想史的角度展开讨论。参见张三南、吕伟波:《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探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51—54页。张治江通过分析李大钊的民族主义主张,探讨其对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见张治江:《李大钊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兼论民族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第108—112页。
⑨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载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897—191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⑩同上。
近代中国之所以衰微,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息息相关。中国内部状况的巨变,本身就是对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所建构的国际体系的巨大冲击,象征着突破这一极不平等国际关系的尝试。就此而言,将“中华民族之复活”视为另一种“亚细亚主义”的曙光,并非单纯建立在古代中国不容忽视的文明辐射力之上,而是象征着20世纪亚洲反侵略、反殖民运动的重要一环,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46]即“吾人但求吾民族若国家不受他人之侵略压迫,于愿已足,于责已尽,更进而出其宽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诱提亚洲之诸兄弟国,俾悉进于独立自治之域,免受他人之残虐,脱于他人之束制”。[47]正如汪晖所言,在这一分析视角里,“构成亚洲之为亚洲的不是从儒学或某种文明类型中抽绎出来的文化本质,而是亚洲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的特殊位置——这个特殊位置不是产生于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叙述,而是产生于有关亚洲社会内部的阶级构成和历史传统的动态分析”。[48]
1.1 一般资料 本院神经内科共有护士40名,均为女性,年龄21~48(28.5±3.8)岁;工作年限3~20(15.2±3.2)年;职称:护士25名,护师 12名,主管护师 2名,副主任护师 1名。所有护士均在知情同意下参与研究,并愿意积极配合完成相关调查。分别于团队管理制度实施前(2016年1~6月)及实施后(2017年1~12月)各抽取80例患者进行调查,实施前男 40例、女40例,年龄45~75(58.2±3.5)岁;实施后男 38例、女42例,年龄48~75(57.6±3.7)岁,实施前后所选患者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子宫平滑肌瘤病理基础与造影表现。子宫平滑肌瘤是一种常见的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肿瘤,大小不同,呈球形或不规则形,具有明显界限,瘤组织切面一般为灰白色。如果出现供血不足或肌瘤生长较快的情况,会出现多种继发性改变。子宫平滑肌瘤造影剂增强一般表现为肌瘤周边首先增强,出现一个半环形增强影,主要供血血管呈树枝样伸入,然后瘤体整个增强。子宫腺肌病表现为多条血管呈不规则分支状进入病灶内,整个病灶区肌层呈不均匀高增强,造影后期呈不均匀稍低增强,边界不清,无包膜感[3]。本研究中16例子宫平滑肌瘤的超声造影符合上述表现,但其常规彩超诊断符合率与超声造影诊断符合率差异无显著性。
⑫ 按照罗志田的分析,中国人的民族认同长期处于潜藏心中的状态,如不出现大的内忧外患,基本上就维持潜存的状态,一旦出现国家与民族危机,这种内心深处的认同感并不难被唤起而转化为政治力量。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版,序论第13页。由此入手,或许比较容易理解李大钊为何强调“自觉心”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⑬关于李大钊对陈独秀的回应,较为详细之分析可参见[日]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丁晓强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171页。
⑭余一:《民族主义论》,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87页。
⑮ 关于这一点,姜萌在《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一书中有较为详尽的分析。
从图1走势图可以看出,农产品价格大幅增长的同时,CPI也呈增长的趋势,但增长幅度明显小于农产品价格的增长幅度;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同时,CPI也同样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下降幅度小于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据此,从空间角度分析,农产品价格和CPI变动的方向相同;从时间的角度分析,农产品价格的变动要先于CPI的变动。但二者之间协同升降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⑯ [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114页。
⑰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87页。
⑱ 李大钊:《青春》,载《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13页。
⑲ 石川祯浩认为,李大钊对于“青春”和“青年”的重视,受到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政论家茅原华山的影响。参见[日]石川祯浩:《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145—147页。无可否认,茅原华山的观点对李大钊有所启发,但在面对中国的具体问题时,李大钊对“青年”报以极大的期待,是希望他们能不同于民初政坛的各色政客,具有良好的政治德性。
⑳ 段炼:《寻求超越: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个人价值认同》,载许纪霖、刘擎(主编):《多维视野下的个人、国家与天下认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
采用日本早稻田大学Laurence Anthony教授开发的antconc[12],对《鲁迅小说》用字和无标记分词进行字频与词频统计(结果见图1与图2),并将统计结果导入excel与北语两表进行整理比较。
[21]正如章太炎所言,中国人之“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参见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
1.5 治疗与随防 确诊CH后立即给予优甲乐(左旋甲状腺素钠)替代治疗。药物治疗2周后复查血清甲状腺功能,根据指标调整药物剂量,并定期随防。随防期间给予甲状腺B超检查、体格发育和心理发育评估等。PKU患儿给予低/无苯丙氨酸奶粉或食物治疗;BH4缺乏症补充BH4和神经递质前质(多巴和5-羟色氨),定期随访监测血中Phe浓度在理想范围,并定期评估体格发育、智能发育。其它遗传代谢病根据具体疾病给予饮食控制、左旋肉碱、维生素B12等。随防期间定期监测血中相应氨基酸谱、酯酰肉碱浓度,评估体格与智能发育。
[22][日]沟口雄三:《中国的民权思想》,载[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7页。
[23]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载《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77页。
关于这一点,有论者认为,在李大钊那里,作为个体的“小我”之价值在“大我”面前居于次席,甚至为了实现“大我”可以牺牲“小我”的利益。⑳从一种苏格兰启蒙运动式的自由主义后见之明来看,李大钊的思想或许有这样的特点,但如果从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来看,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总体而言并非处于对立状态,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在逻辑上乃一以贯之的过程,个体为构筑一个更好的群体(家族、乡里、政权)有所贡献,才能在伦理与道德上符合“公”的标准,否则便沦为“私”之体现。相应的,某一类群体(家族、乡里、政权)实为个人在社会上形成较为稳定的认同、达到心之所安的重要对象,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格。[21]也正由于这样,恰如沟口雄三所论,近代中国对民权的诉求,在推翻一个不良的、专制的政治集团同时,还要求参与者克服利己性,致力于巩固新的集团,以此实现“大众的”民权。[22]
[25]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载汪晖:《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7—58页。
[26]在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之前,李大钊写了一系列与对德外交有关的文章,探讨一战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应对德国所采取的态度。这些文章的基本着眼点是强调国家利益不可作为国内不同政治团体彼此政争的工具,对德断交乃国家意志的表现,属于“外交之曙光”。所以他在这之后,撰文系统论述“新中华民族主义”,很可能是针对当时的外交形势而言,即进一步阐明如何明确国家利益,凝聚民族意识。关于李大钊这段时间内的言行,参见朱文通(主编):《李大钊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14页。但此书作者却认为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是针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发的(参见第214页)。笔者不否认李大钊或许有此考虑,但他在同年4月专门以“亚细亚主义”为主题撰文,明确回应了日本的这一宣传。按照常理,这篇文章才应该是针锋相对之作。而“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论述,更可能是他针对之前政局,为自己提倡的各种具体主张所做的理论性、总结性的宣言。
南一环站、芜湖路站均为主体宽约13 m的岛式站台车站,两层三跨结构;覆土厚约3.2~4.1 m,底板分别位于粉细砂层和强风化泥质砂岩中。高架主桥桥墩承台高2.5 m,置于车站顶板上。水阳江路站为主体宽度为11 m的岛式站台车站,车站为双层双跨矩形框架结构;覆土厚度约3 m,底板位于黏土层,高架匝道桥桥墩置于车站顶板上。三站均位于车水马龙的城市主干道上,车站周边高楼林立,最近的高层建筑距车站基坑仅约5 m。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芜湖路站与高架桥同位合建单平面如图1所示。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认为“democracy”一词应翻译为“平民主义”,其在精神上与社会主义相一致。他指出:“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74]因此,为了让中国走出衰颓的境遇,必须铲除国内由权力、资本、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支配关系。通过向国人介绍当时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与工人运动,李大钊呼吁:“我们要知道这样大的问题,都是因为分配而起的。我们要知道,有生产才有分配,有生产的劳工才有分配的问题。像我们这种大多数人只想分配不想生产的国民,只想了抢饭不愿作工的社会,对于这种世界潮流,应该怎么样呢?那些少数拿他们辛辛苦苦终年劳作的汗血,供给大多数闲人吮括的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呢?这大多数游手好闲不作工专抢干饭的流氓,应该怎么样呢?望大家各自拿出自己的良心来想一想!”[75]
[29]同注23。
[30]同上。
[31]同上,第478页。
一是培养员工爱岗敬业精神。工作中要思想统一,为了共同的工作目标能互不拆台、互相补台,人人都以工作为重。
对两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的血糖水平控制情况及治疗效果进行统计、对比。①血糖水平控制情况包括对患者治疗前后的空腹及餐后2 h血糖水平进行检测、统计,空腹及餐后2 h血糖水平应分别控制在7.0 mmol/L及10 mmol/L范围以下;②疗效判定指标:显效:经治疗后,患者血糖水平控制较好,每日血糖波动不明显;有效:经治疗后,患者血糖水平获得一定改善,且尽在餐后出现明显血糖波动;无效:经治疗后,患者血糖水平无明显改善或加剧,且血糖水平处于较高波动状态。
[32][法]欧内斯特·勒南:《何为民族?》,载[法]欧内斯特·勒南:《法兰西知识与道德改革》,黄可以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页。
[33]同注23,第478页。
李大钊的政治生涯,最开始主要是与汤化龙、孙洪伊等进步党人关系密切,直至1917年,李大钊与高一涵还替孙洪伊起草地方自治法规。[65]章士钊则回忆,李大钊“及与余交,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当时高(即高一涵——引者注)、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胡适之曾屡道之”。[66]但是目睹民初政治与社会的各种乱象,依李大钊之见,在内忧外患并存的现实条件下,中国之再生需要克服极大的困难:“吾以老大衰朽之邦,风烛残年,始有新中华之诞育。先天遗传之病惰种子,在在皆足以沉滞新命发育之机能,甚且有流产胎殇之恐焉。故吾人于新命诞孕之中,所当尽之努力,所当忍之苦痛,尤须百倍于美、法、俄诸国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间所能竟此大任。”[67]在此焦虑下,章士钊对于现政府的支持态度,让李大钊感到不满;而李大钊经常对研究系进行攻击,章士钊也并不同意。二人之间,分歧日增。[68]因此,十月革命的成果,给予李大钊一个彻底有别于进步党式的、新的分析中国问题与世界格局的视角,让他能够以此为出发点,去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69]他在《庶民的胜利》一文里谈到,十月革命“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而“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70]既然“新中华民族主义”之“新”建立在新的政治实践者于共和政体下形成新的联合与认同,那么苏联的“庶民”作为革命的最主要参与者,他们通过打破列强所形塑的世界体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联合,这无疑给李大钊思考如何在中国推翻由官僚与武人支配的政治,摆脱列强对中国的控制,提供了绝佳的借鉴与参考。质言之,“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都成了工人”。[71]如此一来,“新中华民族主义”不再寄希望于抽象意义上的“青年”或“青春之力量”,而是思考如何与广大被压迫的、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群体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翻身解放,才是中国摆脱民族危机的关键所在。因此,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里,李大钊更是颇为激动地宣称:“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72]对李大钊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意义正在于,它借助阶级、资本、帝国主义等概念,揭示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压迫与危机,以及在这种情势之下新的政治主体应当如何形塑、动员、组织。它使李大钊认识到,中国人不再将救亡的诉求寄托在旧式的武人政客与列强资助之上,而是寄托在被动员起来的广大工人与农民,依靠严格的组织纪律与清晰的政治经济纲领,重新改造国家与社会,真正摆脱孱弱贫穷的境地,同时获得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参与感。犹可注意者,李大钊思想的这番变迁,在当时绝非个案。杜亚泉与《东方杂志》的作者们目睹当时的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也开始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与横暴,同时寄希望于“科学的劳动家”成为20世纪政治的新主人。[73]
[35]同注23,第478—479页。
[36][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8页。
[37]张志强:《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载《哲学动态》2015年第3期,第10页。本文关于“政治民族”的定义,即借用此文中的观点。
[38]黄兴涛认为,近代中国人谈论民族问题,“认可历史文化因素在民族构成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近代中国人‘民族’概念的实际运用,又没有局限在历史文化的层面,而是同时实现了超越,引入了共同体成员平等的国民和公民政治身份的内涵并将其置于基础性地位”。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372、373页。笔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彰显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中的“政治民族”的意涵,并认为此乃他针对中国近代具体历史语境而产生的思想倾向,而非试图以近代西方的历史流变为标准,审视李大钊相关见解是否符合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民族”。
[39]同注23,第478页。
[40]迈斯纳所言的“沙文主义”倾向,或许就是指此点。
[41]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页。
[42]同上,第137—143页。
[43]同注25,第65—66页。
[44]1917年4月,李大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此文主要的针对对象是日本《中央公论》4月号刊登的《何谓大亚细亚主义》。此文从东西方比较入手,强调要建设区别于充满掠夺行为之“西洋文明”的“东洋文明”。参见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54页。
[45]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55页。
[46]这里借用朗西埃对“政治”的定义,即“政治”旨在“打破界定组成部分与其份额或无分者的感知配置”,是在“重新配置用来界定组成部分、份额之有无的一系列空间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参见[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按照这一思路,中国突破帝国主义所设定的国际体系,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打破原有界定组成部分的方式,开启了重新思考全球秩序的可能性。
[47]同注45。
[48]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载汪晖:《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49]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79页。
[50]同注45。
[51]李大钊:《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载《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97页。迈斯纳认为李大钊提倡“新亚细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托洛茨基设想的“欧洲联邦”的启发。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201页。这一点从思想源流上来说或许可以成立,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具体形势,即帝国主义问题与国内新政治力量的萌芽。李大钊的倡议,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形下产生的。
[52][日]近藤邦康:《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第143—144页。
[53]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9、280页。
[54]关于章太炎的这些观点,参见王锐:《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如何建立?——〈中华民国解〉中的国名性质、疆域版图与政治选举问题》,未刊稿。
[55]因为史料有限,今天我们无法判断李大钊是否读过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与《亚洲和亲会约章》两篇文章。不过笔者关注的是,章太炎在清末所提出的观点,与李大钊在民初的论述有极强的相似性。这或许至少可以证明,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下,思考中国问题的两代知识分子之间具有共同聚焦的政治思想命题。
[56]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载《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29页。
[57]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载《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69页。
[58]梁启超:《国际同盟与中国》,载夏晓红(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3页。
[59]严复:《与熊纯如书》,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9页。
[60]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载许纪霖(编选):《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2—86页。
[61]李大钊:《我与世界》,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488页。
[62]关于这一点,笔者借用了罗志田的描述。参见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载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第361页。
[63][日]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56页。
[64]列宁:《亚洲的觉醒》,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
[65]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载人民出版社(编):《回忆李大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66]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载《章士钊全集》第8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
[67]李大钊:《此日——致〈太平洋〉杂志记者》,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55页。
[68]同注65,第165页。
[69]据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回忆,“早在东京留学时,他(指李大钊——引者注)就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了。那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守常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著作”。参见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载人民出版社(编):《回忆李大钊》,第165页。不过据今人研究,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的主要是河上肇关于经济学的论著,而非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但是,他却颇受当时在早稻田大学任教的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的影响。参见朱文通(主编):《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2—73、80页。无论具体因缘为何,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70]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58页。
[71]同上。
[72]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67页。
[73]同注25,第98—99页。
[74]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载《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7页。
[75]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404—405页。迈斯纳认为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隐含着“在中国的外部敌人面前,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消失”的假说。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205页。但根据这两段引文,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李大钊虽然强调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但并未因此忽视中国国内的阶级问题,而是把二者都视为需要有效解决的时代任务。
[76]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载许纪霖(选编):《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上卷,第70页。
[77]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载《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24页。
[78]李大钊:《人种问题——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的演讲》,载《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575页。
[79]同注⑦,第206页。
[80]关于这一历史过程,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王红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236页。
[81]同注78,第574、578页。
[82]李大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载《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87、488页。
[83]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136页。
[84]迈斯纳曾提及李大钊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但论述过于简略,关于这个问题,或许可做更为细致的分析。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责任编辑:周 慧
Cultivating A “Political Nation”: Li Dazhao’s “New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Theoretic Implication
Wang Rui
Wang Rui,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Li Dazhao was intensely devoted to expounding “New Chinese Nationalism.” In his view, what’s so “new” about “New Chinese Nationalism” is its aim to break the long-standing barriers in culture, customs and linguage and to form a rock-solid “political nation” with a common political ideal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new political power. In addition, he believed that the practice of “New China Nationalism” would constitute an impact on the global system of inequality. If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could fully cooperate with revolutionarie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from “New Chinese Nationalism” to “New Asiaticism” a new world pattern would become possible to conceive. It is on this basis that Marxism came into Li Dazhao’s mind and allowed him to analyze Chin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tradictions more directly and sharply so that he could think about China’s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revolu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from “New China Nationalism” to Marxism, Li Dazhao’s thinking on China’s problems reached a higher level of distinction and thoroughness.
Keywords: Li Dazhao, New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Asiaticism, Marxism
标签:李大钊论文; 新中华民族主义论文; 新亚细亚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