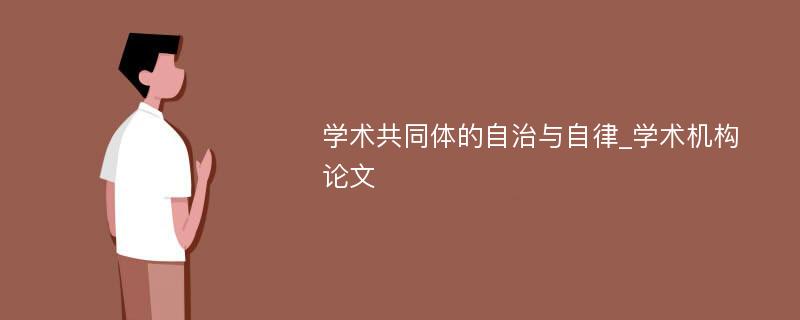
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术、学人和学术共同体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清末思想家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和重要的意义。曾经成为后世学人的追求目标,至今仍然强烈地影响和激励着中国学界和广大学人。
数年前,笔者曾经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为题写过一篇评论。我想先将其中的要点引在下面,然后做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是指一切学术成果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虽然它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生产和提供的,生产者或供给者也享有知识产权,但一旦公之于世,就要向全社会公开和开放,由社会大众享用,为社会大众服务,任何个人和集团都不能据而为私,也不能专有专营和实行垄断。不仅如此,学术成果一旦公之于世,就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评判,以定高下优劣。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只能面对社会的检验,不能也无法阻止社会的评判,虽然作者自己可以做出补充修改和进一步完善,但是无法抹去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因而,“文责自负”,即作者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其次,是指学者都是独立、平等的自由人。在学术活动中,学者是社会的代言人,其全部活动在于求实、求是、求真、求新。因而,他们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人格,不应依附于任何个人和利益集团。在真理面前,学者们人人平等,学术水平虽有高下优劣之分,但人格无高低贵贱之别;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学者的天职和良心。自由思想是学术发展之生命所系,在学术思想领域,学者享有充分的自由,做何种研究规划,取何种理论立场,学者有选择的权利,其他人无权干预。
再次,是指学术单位既非政府权力机构,也非企业盈利组织,而是一种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学在民间”,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历史和事实证明,政治权力的介入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同样,学而优则仕和学不言利都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其中包含很多迂腐的东西,与学问之事无补,当然,做学问需要物质的支撑,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增进,但由私利支配的学术活动会走到邪路上去。在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中,没有等级观念,没有组织纪律,不需要也不应下级服从上级和少数服从多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批评其他人的学术观点,学生也可以与老师辩论,初出茅庐的新手也可以向专家权威挑战,但必须以理服人。因此,学术单位是一种社会组织和公众机构。
最后,是指学术规范是公正的和公开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反。学术规范是学界的共识,也是学者和学术机构的行为准则,遵守学术规范是学术发展和知识积累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保证,也是学者和学术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不遵守甚至有意破坏学术规范,也就丧失了学者的尊严和资格,学术机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学术失范,学风必然败坏,其后果是学者的堕落和学术机构的毁灭、思想的贫乏和理论的凋敝。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学术成果是社会的公共财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任何人都无法据为己有的东西。它是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而由学者发现和提炼出来的,虽然学者的创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成为据为己有的理由。事实上,一切学术成果一旦公之于世,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和运用,专利权和著作权都是一种拟制的权利,旨在保护和促进学术的发明创造而不是限制和扼杀思想的桎梏。学者的思考和创造也离不开社会的实践,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个人的胡思乱想和胡编乱造,学者也无权这样做。任何成果都要经过社会的检验,都会发生一定的作用,正确的观点能够提升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错误的观点也是人类认识的一个片面和片段,有可能成为正确认识的先导。至于那些重复生产的学术垃圾,不仅是人类能力和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会毒化社会空气,是一种社会病态的反映。
中国自古就有“学在民间”之说。孔子办学,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与官方无涉,只有子贡后来做了大官。古代的私塾、书院,近代的燕京、辅仁,亦非官方所办,造就了多少人才,培养出多少大家,生产了多少巨著名篇,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章太炎在致王鹤鸣的信中对“学在民间”做了很好的阐述。他说,“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望”。其关键在于把中国官场上下尊卑那一套陋习照搬到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中来。在国外也是一样,西方学术最早出现于宗教活动之中,基督教曾经做过很多坏事,宗教歧视和宗教战争也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但也做过一些好事,它是中世纪教育事业唯一的组织者,也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宗教改革不仅促进民族国家摆脱教会控制,促进科学文化摆脱经院哲学,而且“宗教容忍曾是近代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
学在民间,是由学术活动的自由性质决定的。政治权力的作用在于保证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的独立自主,在于保证学者的自由探讨,因而是外在于学术的;如果政治权力渗入学术机构,左右学术活动,控制学者言说,必然造成学术的非学术化。这也意味着学术的终结。任何政治势力都可以利用学术成果为自己服务,这与学术研究活动本身无关。学者一旦将自己的学术成果用于政治和商业活动,也就成为政治家和商人。
学术共同体是一个自由人的松散联合体。在这里,只有思想上的认同和学界同仁的默许,每个人都是自由人,在法律和伦理的限度内,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可以不受其他约束,不仅进出完全自由,而且行动也充分独立,做什么,如何做,皆由自己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里没有长官意志,没有行政命令,没有组织纪律,但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规范、自己的秩序,一切以无声的约束和自觉的遵从来实施和维持。因此,学术传统是自由的传统,学术规范是自我实施的规范,学术秩序是一种自发的秩序。
正是由于学术共同体有着自由的传统,是自发的秩序,这种传统和秩序的维持,除了法律以外,全靠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不仅需要每一个学人的自觉遵从,而且需要共同体的一致行动。如果没有每个学人的自觉遵从,没有共同体的一致行动,这样的学界将不成其为学界,而是乌合之众,自然也不会创造出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
二、中国学术研究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有所进步,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虽然水平较低,但方向正确,发展迅速。然而,随着改革的停滞、倒退和转向,中国的学术研究也严重失序和失范,而且愈演愈烈,至今仍看不到收敛的迹象,其表现和原因如下。
一是学术研究的环境继续恶化。如果说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学界的脊梁,那么市场化改革的扭曲则腐蚀了学者的灵魂。对此,我们并没有做出认真的反思和真诚的检讨,也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其余毒和影响还在继续。直到现在,以言获罪之类的事情仍不断发生,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仍然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并未真正落实。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官方的思想控制不得不有所放松,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也发生了动摇,其正当性和公信力也大大下降,为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开放了一点点空间。但是,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不仅学而优则仕,官大压死人,而且官方的组织控制依然相当有效,而且无孔不入,在实践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往往要得到官方的批准,在公开和正式场合,自由的空间不大,特别是在一些所谓敏感问题上。
问题严重性在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尚未摆脱官方的掌控,又落入了金钱的奴役和驱使之中。无论是教学科研单位,还是学术出版机构,一方面受官方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听任市场的摆布,不该市场化的也市场化了。官方的方针是,只要听话,不与领导为难,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唱反调,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追求自己的经济目标。而一些商业机构和企业人士,甚至一部分官员,也看到了学界地位和学者身份的社会影响和市场价值,不是力图挤进学者的行列,就是以提供金钱支持和政治庇护为手段,直接掌控某些学术单位和笼络一部分学者,为其利益服务。也只有这样,学者们才能发点小财,过上“体面”的日子。
二是教学研究机构官僚化。我们的教学研究机构不是由教育家和学问家治理,而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僚统治,因而出现了一大批“官学”和“学官”。他们的目标不是学术水平的提升,而是官位的升迁,权力的扩大;他们并不真心支持思想理论的创新,而是通过各种控制手段,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借以维持治下的安定和得到上级的褒奖;他们也不重视学人独立人格的培养,因为这样的人有可能危及他们自己的安全。在现有教学研究机构中,有不学无术的官僚,有以势压人的学阀,有投机钻营的骗子,而正直的学者很难立足,往往被边缘化。官方的教学研究机构已经官僚化和商业化了,不是跟着意识形态的指挥棒转,就是被财神爷牵着鼻子走,非官方的学术机构则没有合法生存的余地,只能在现行制度缺陷的缝隙中勉强维持和惨淡经营。
前不久,有人提出高校去行政化,引起了一场热议。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教学研究机构都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和行政事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取消不了的。真正要去的不是行政化,而是官僚化。这才是事物的本质和问题的正确提法。
三是学人行为已经冲破了为学做人的底线。在权力的控制和金钱的引诱之下,不仅教学研究机构官僚化了,而且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也扭曲了,现有的学术管理和评价制度不仅不能有效地规范和校正学人行为,反而起到了逼良为娼的作用,不仅恶化了学术生态,而且形成了一种不思和反智的潮流。
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按照行政方式设置和管理,以宣传政策、解释文件、上镜曝光为要务,以数量指标考核为手段,以晋升当官、金钱地位为诱饵,教授往往身兼数职,既当官又做生意,一些人成为不学无术的官痞党棍,一些人成为学术上的掮客和商人,很多人都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赚钱、玩乐、拉关系上,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读书思考。
现行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走上了工厂化生产的道路,大学变成了“养鸡场”①,研究生培养办成了“包工队”,主管部门也成了发包商。处长、司长、总裁、经理也附庸风雅,要弄个硕士、博士当当。全国234个高校设有博士点,培养的博士有5万多人,与美国相当,毕业的博士一半以上去各个政府部门当了公务员,一个公务职位居然有4500多人竞争。
由于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处于强势地位,不仅混淆了政治批判和学术批评、道德评判和学术评价的界限,往往用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代替学术批评和学术讨论。研究课题由主管部门拟制和发包,研究成果以领导圈阅为上乘,成果鉴定和学术评奖不是走过场,就是搞形式,真正的学术著作很少有严肃的学术批评和讨论,而充斥报刊的大多是“广告式”和“推销式”书评,于是重复生产、重复研究,今年和去年的研究项目相同,研究课题类似。与此同时,学术出版机构既要保证政治方向正确,又要能够赚钱生财,很多变成了垃圾制造厂。
在这样的学术生态和制度结构下,绝大多数学者的理性选择是适应形势,顺应潮流,一是缺乏独立性和自主精神,叫干什么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缺乏或者不敢表示自己的主见,丧失了学者应有的人格和骨气;二是缺乏学术担当和批判精神,既没有涉足理论禁区的勇气和能力,也没有在知识生产上超越前人和外人的魄力和打算;三是缺乏深钻细研的实干精神,表现为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重数量,轻质量,好大喜功,做表面文章。这种理性选择却断送了学术的生命。
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不思和反智潮流中,炒作、起哄和跟风成为最普遍、最时髦的行为方式,除了那些快餐文化和快餐学术以外,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判和讨伐也成为热门话题。很多人把30年来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失误,特别是分配不公、贪污腐败也归罪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这不是说经济学没有局限,也不是说经济学家不能批评,而是在于这种现象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和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顺民,遇有内忧外患,不敢直指当权者的失误,又要找几个垫背的。今天,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就成了冤大头。
对于中国学界的不良风气,历来就有不少批评。当年,熊十力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人有一不良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而,于是所学,无有甘受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其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人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矝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今人对学风的批评更是充斥于报端。然而,风气已成,积重难返。
在目前的情况下,学人学品和学界学风的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抄袭之风甚烈,造假之风更甚,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很多是学生写文章,导师跟着署名,而且还要当第一作者。有的甚至连文章看也不看,就把大名签在上面。结果不是学生抄袭剽窃,老师拿来当做自己的发明创造,就是错误满篇,笑话百出,突破了做人为学的底线。
三、学术共同体如何走向自治和自律
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中国学术研究的命运多舛,前途未卜。但也不是毫无希望,这取决于中国学人能否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以使学术共同体逐步走上自治和自律的道路。
无论是学人,还是学术界,其所以缺乏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就在于我们缺乏真正的反思,而陷入了一种不思的状态之中。因为,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来自于不断进行的理论反思和实践反思。首先要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认识我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所受到的影响,既屏蔽各种外来的干预,又抵制各种潜移默化的渗透,解决社会无意识的问题。其次要反思我们的学术实践,认识我们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和影响,既消除由于无反思引起的偏见,也祛除对人、对事,特别是对自己的幻觉,解决学术无意识的问题。因为通过这种反思,我们就不会把外部环境的进步看做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也不会把研究对象的重要误认为是自己研究的重要,既不会简单地把任何外部的需求和炒作看做是科学评价的标准,也不会简单地把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担当作为混淆二者区别的理据,进而把学术批判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这样,就可以扩大自由空间,发展自觉意识,进而生产更多更好的知识。
学人要拿起批判的武器。我们的学术生态、学术环境、学术机构、学人行为和学术成果其所以如此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人放弃了自己专有的批判武器。要知道,学术生态和学术环境虽然是既予的,也是人创造的,虽然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学人绝非无能为力,也不能逆来顺受。对于政治的强权和社会的弊端不仅不能苟同,而且要明确说不。其实,政绩人人都看得到,用不着学者去捧场,而缺点和问题虽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但都害怕别人指戳。批判强权的危害和揭露社会的弊端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界的腐败和黑暗直接恶化了学界的空气,危害了学人权益,更是学人批判的对象,即使某种原因不能公开表态,至少应当洁身自好,不能同流合污。学术批判更是学人分内之事,是学术活动的正常内容,学术的发展和理论思想的繁荣,都是质疑、批评、辩驳的过程中前进的。如果没有批评和反批评,学界就是死水一潭,迟早会臭气熏天。
学人要采取一些集体行动,揭露和抵制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目前,学术界其所以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假冒伪劣充斥和风行,就在于学人未能采取必要的批判和坚决的抵制行动。在体制内的学术机构不作为,甚至支持和鼓励的情况下,民间应当独立采取相应的行动。
去年,笔者曾经写一篇评论“建立中国学术秩序的突破口——简评汪晖朱学勤涉嫌剽窃事件”,现将其中一段引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目前,几乎没有人不对中国的事情发出抱怨。但是抱怨又有什么用呢?中国的事情都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没有制衡,没有监督,而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就以反腐倡廉而论,没有了媒体的公开监督,没有了独立司法的制衡,仅靠纪检委,仅靠反贪局,只能是腐败越反越多。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须知,纪检委和反贪局也是由常人组成的,也可能出现贪污,谁来监督监督者呢?现有的反腐肃贪暗箱操作,置法律于可有可无,即使抓住的贪官再多,对法治和秩序的形成也无多大作用。
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除非发生重大事变。但这样的结果是好是坏,是前进还是后退,谁也说不清楚,更无法预知。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地改变。既然学术界是社会的良知,学者们都主张法治和宪政,主张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先在学界逐步建立起一套宪政秩序、法治规则和纠错机制,并使其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呢?这是学术界可以担当和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中国学术界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到和做不好,还遑论什么改造中国、服务世界,那真是没救了。
其实,在学术界实行民主宪政和建立法治,目前是一个最好时机。汪晖和朱学勤是学界名人,对其涉嫌抄袭剽窃进行审查,就是在学术界建立宪政秩序、法治规则和纠错机制的突破口和起步点。如果说,像拆迁条例之类恶法的立宪审查,学界只能呼吁,只能坐而议,不能起而行,那么,通过对涉嫌抄袭剽窃之类的事件进行学术审查以建立学术秩序,就不是只能而坐而议,而是可以起而行了。这也许是学术界可以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的领域之一。在体制内的学术机构不作为的情况下,体制外的学者也可以单独采取行动,对抄袭剽窃进行审查。同时,建立学术秩序和学界规矩,并不神秘,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都是学者,自然有很多共识。关键还在于学者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和担当,有没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
本文系为2011年5月8日召开的华人哈耶克年会所作。
注释:
①李零教授有“学校不是养鸡场”一文,对此有很好的描述和分析,参见《香港传真》2003年第2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