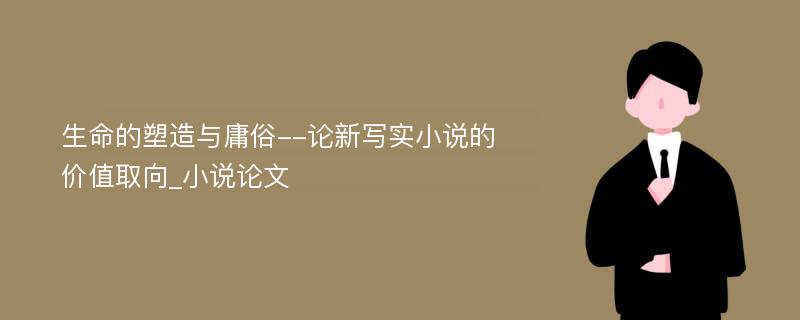
生命的写真与媚俗——试论新写实小说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写真论文,生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新写实小说严格遵从文艺创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极力摹写当今社会中人们的生存之累和精神状态,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明显的媚俗倾向。而这种媚俗倾向又是以失却信仰和理想的追求为代价的。新写实小说应该走出世俗困扰的圆囿,在提高现代人生的精神品位上有所突破。
一
一个时期以来,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等一批青年作家举起新写实主义的大旗,给疲软的文坛带来一阵清新自然的春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评论界也在一片赞扬声中对这一新的创作方法进行了热烈而模糊不清的争论。
有些评论家把新写实归纳为“新写”和“新实”是有道理的,它很敏锐地抓住了新写实的基本特征。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了“新意”,无论“新写”也好,“新实”也好,关键是作品要有“新意”。假如说作家们用大量的时间去搞所谓的“新写”的“零度叙述”、“还原原则”,去大量追求“新实”的“世俗还原、日常还原、生存还原”,那么这仅仅是在搞一种文本上的实验,我想这不是错觉就是假象。倘若新写实存在的价值仅仅是作为弥补当代文学陷入困境中无法自拔后的附属品,一种满足文化大裂变后中国人读文学的愿望,那是否太简单了?退一步说,即使是这种太简单的愿望,也起码需要有点叫国人感兴趣的“新意”存在,如果没有一种触及当代中国人精神价值的“新意”存在,我想它不会造成真正的社会反响,甚而至于连进入真正纯文学实验的独立品质都不会有。基于此,在读到一些评论文章以为新写实表现的是现实主义的“形”,吸收的是现实主义的“神”,贯穿的是寻根文学的“髓”时,就不能不让人发出疑问,新写实自身的独立品质是什么,它是当代文学的集大成者吗?
就象“文化”加“小说”不等于文化小说,“新写”加“新实”也决不等于新写实。作为一个派别,新写实首先应该有自己的艺术观念,而靠其他任何东西眩人耳目都是不行的。而许多新写实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一味也追求“新写”与“新实”,却忽略了追求独特精神取向的“新意”,以至于造成许多作品缺少一种触动人们心灵的穿透力和震撼力,甚至一些作品成为一种无现实气息的艺术花瓶,这就严重影响着新写实的发展。因此,新写实小说已经给人造成了一种走向穷途的印象。
为了新写实小说走出困境,更为了它的发展进步,我们不能不重视新写实小说的精神取向。笔者认为,新写实的含义应该是用新的文学真实观,新的创作原则来写新发生在当代生活中精神价值观上的深刻变化。仅仅注重“写”和“实”,而不注重“新”是不行的,因为只有“新”才是问题的核心和焦点。新写实小说正是针对国人当前生活状态,最终以鲜明的精神价值座标来表现、审视和参与当代中国文化与生活方式构建的。新写实小说以新的文学真实观和新的创作原则,来深入反映和表现当前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观念信仰状态。
二
人类的精神发展过程就是从生存到信仰的不断经受坎坷的历程。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出发点,而信仰则是人们的精神支柱。人不能没有观念和信仰,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历史,任何艺术品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的催化下产生的,这一普遍性艺术规律规范着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但是,在人类高度文明的今天,由于种种原因,信仰正成为当今人类茫然无极的东西,人们在理性世界纷纷踏上了返回人类的自我生存,返回人类家园的归程。生存和信仰正困惑着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在世纪末的转折点上,许多人表现出对生存与信仰的深深困倦和精神负重。
新写实小说正是在这种困惑大潮中的具体显现。新写实主义小说及时抓住当今中国人普遍的社会情绪和人民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各阶层小人物的琐碎生活,将中国目前人们的生存处境和观念处境展示于世。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写实小说就在不遗余力地高唱“真实性”、“客观性”的同时,也在为“新”不得不渗透着“主观性”的色彩,以此来展示现实人生的处境和人们的生存之累。大概也正基于此,新写实小说曾被一些人称为写“生存状态”的文学。那么,这种“生存状态”向人们所展示的价值取向或精神观念指的是什么呢?其实,“生存状态”的客观性并非是让作家抛弃自己的主观倾向。在创作中,作家的主观倾向可以深层地融化在客观的“生存状态”之中,从而以达到形成无我之境的作家精神写照。因此,在方方、刘震云、池莉、叶兆言等人的“生存状态”的客观化展示中无不渗透着一种强烈的生存之累,而这种生存之累也是当前最为普遍的国民情绪和国民状态。在方方的《风景》和刘震云的《新兵连》中所展示的生存之累还只有苗头,而到了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则充分张扬了生存之累的主调。
方方的《风景》写了七哥一家蜗居的贫民生活。七哥一家九口人拥挤在十三平方米的“河南栅子”里,七哥靠捡破烂补贴家用,平时夫妻吵闹,父子斗殴司空见惯。贫乏而无聊的生活内容使在困厄中彼此相依的一家人,又把痛苦发泄在别人身上,于是有了后来各人的逃避。最为典型的是七哥走上了不择手段向上爬的道路。这在存在主义就是被抛入的自我设计,存在不由自己,本质却可自行设计和选择。七哥要改变自己,但又不得不欺骗自己、违逆自己、甚至失去自己。作品通过七哥这个一向被家庭残酷折磨的小人物的奋斗历程,在向人们展示七哥的生存之累上写出了人生追求的失落感,也展示了灰色的市井人生风景。刘震云的《新兵连》以“文革”时期为背景,写了一群处在集训状态下的新兵的日常生活。小说的背景是十多年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政治高于一切,政治支配一切,政治渗透在文化、心理以及人的行为方式中,政治标准成了人的“集体意识”。同是来自农村的老乡们来到了新兵连,在三个月的训练中,为了政治进步,各有各的打算。志肥、元首、王滴等人为能成为班里的“骨干”,都怀着互相防备互相利用的心情,李上进为了入党进步,克尽职守,任劳任怨,无不是为了这种半功利半虚荣的政治名声。年轻的新兵竟可以不顾做人的起码德行,暗中算计、攻伐,使“新兵连”生活如同一曲狂乱无序的噪音,几乎每个乐手和听众都在不自觉中受到伤害。作者激情这个严峻的现实,把人生的某种缺失同社会生活的缺失联系起来进行艺术观照和无情的揭示,展示了中国普通人为了活下去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被以为是新写实小说力作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有着与刘震云作品相同的思想意蕴。尽管池莉的小说给人造成一种大同小异的感觉,但从中也使人体会到了一种执着的追求。池莉的小说避免了方方的《风景》写生存史的色彩和刘震云《新兵连》运用“文革”作为背景的情况。她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描写领域放在当前最近的中国人的心理时空中,她在小说中从不穿插回忆,将时间、人物、故事放在现实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池莉追求的是用最新的时间写出最新的生存状态,刻意强调当前的新生活、新心态中写世俗人生的无边烦恼。在《烦恼人生》中,印加厚对于肖晓芬的瞬间冲动,对于雅丽的刻意掩饰和对于旧日好友聂玲的刻骨铭心的眷恋等,体现着他感情世界的追求,但生存道德感的作用使他处于各种压力的氛围中,在生存的沉重负载中爆出了他对现实生活实境的厌倦和烦恼。《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则是在饱尝了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后,发出了“生活的内容要比男女之间性的内容多得多”的苍白而无奈的感慨。在池莉笔下,他们的生存负重感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虽然池莉在精神深度和挖掘上不如方方的厚重,在理性的悲剧审视上不如刘震云的凝炼,但她却地地道道地代表了新写实小说的精神,其作品更带有时代的新意。她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和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就很好地说明了新写实小说的价值取向。在池莉《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非常鲜明地昭示她对人的生存疲惫无奈的认识已转向活着就好的麻木。她的写实也转向了“典型”的写实,作品中猫见人就重复:“我们店一支体温表今天爆炸了。”然而并没有人去问为什么和施予关注,因为人都活得很累而且都想活下去,既然活着就好,体温表炸又算得了什么?问题不在于晒“爆”了体温表的高温酷暑是否是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也不在于在大街上摊成“大”字睡觉和种种亲昵、谈笑是否是一种文雅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人们在这种特殊生存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生活情态和沉重的人生滋味。人的价值在沉重的生存中受到空前的失落。同样,刘震云在《一地鸡毛》中也将笔触放在了当前的生活实境上。刘震云自己曾在《磨损与丧失》里说: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单位、家庭、上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对付保姆,还有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如何求人让孩子入托,如何将老婆调到离家近一点的单位。每一件事情,面临的每一件困难都象刀山火海令人发愁。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得与人打交道。我们怕人,于是我们被磨平了。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的,千言万语都说不清日常身边的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这些日常生活琐事锻炼着我们的毅力、耐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记得有些文人爱说,感谢生活。这比我们生活起来更加感到沉重。生活固然使我们一天天成熟,但成熟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意味着遗忘和丧失吗?这里,不仅是刘震云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理解和感受,而且是对待生活的一种观念。刘震云的这个转向大概可以透露出新写实精神的导向。作品在“面包总会有的”的自我调侃中将当代人生存的盲目性、深重感表现得一览无遗。
三
新写实小说对中国当代世俗人生的大量描写,以及强烈反映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存负重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于观念的跳跃,忽略了信仰而造成的。纵观新时期文学,不难看出,新写实小说的一大特征是排斥浪漫主义。它所强调的刻骨的真实以及客观性就是在于拒绝浪漫主义的干扰,表现在作品中对形而上学的东西一概给于坚决的悬置。事实上,新写实小说本质上没有根绝主观性,只不过是将主观性隐逸了。它反对那种直接高扬自己的观念和把表现作为最终目的的作法。同时,又赞赏旧现实主义的再现,肯定了现实主义精神这种民族共同心理,但他否定和反对再现中过分的追求典型意义而导致的故事情节的戏剧化等简单模式,尤其反对观念的直露。新写实小说也根绝了外倾的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将浪漫主义的无限憧憬化为乌有,将信仰的无限虔诚推向彻底的世俗求实。正因为如此,新写实小说彻底走向了世俗精神。表现为理想,只有现实;没有神往,只有世俗;没有永不气馁的追求,只有无可奈何的日常等待。
新写实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生存负重感,正是失却信仰支柱的世俗追求所导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新写实小说是轻视信仰的文学,正是这种现状,使新写实小说在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缺憾。这可以从新写实小说同新时期其他文学思潮的比较中看出来。
在新时期的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从初期就注重揭示当代中国的苦难意识和历史负重感。从“伤痕”、“反思”到“改革”,许多作家把文艺视野放在中国改革进程的曲折和艰难上,从不同行业、不同的角度严肃地关注和审视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值得重视的是,这些现实主义文学笔下的现实负重感,大都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信仰、追求及崇高的信仰存在。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贯穿了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承受历史重负,以英雄主义的崇高信仰去战胜一切世俗纠缠,鄙弃个人得失的精神价值追求。而新写实小说恰恰抛弃了这些。新写实小说在洞悉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后,没有去表现和追求意义的影响力,而是将世俗人生个人命运捡了起来,以彻底的归依世俗、放弃信仰为目标。它根本无力甚至也不故意成为时代的英雄,他们耽于平凡、耽于世俗、耽于自足。单从这方面来看,新写实是一种丧失自信力和丧失人生目的的文学,不得不说它夹杂着一定的媚俗倾向。
与新潮文学相比,新写实小说更迥异于新潮文学。新潮小说是强烈反对媚俗倾向的,但其反叛常常有失当之处,以至于搞得不伦不类。然而,新潮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悲剧倾向,尤其表现出当代中国负重感的牵绕,以及造成的身心疲惫和精神创伤,不管是从理性深度上,还是文化选择的苦涩上,都是新写实小说所望尘莫及的。在新潮小说中,作家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念,它所展示的疲惫和沉重,大都是形而上学的。在他们笔下,青年们所为之困惑的不是具体的生存问题,我们发现,新潮小说中人常常是世俗眼中仰慕的目标,他们虽然具备世俗人生的物质满足和地位满足,但是他们心灵上的创痛、失落、寻觅都是世俗人所无法理解的。在新写实小说中,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为之发愁的,不满足的,所期望的就是如何能够得到世俗的安身,倘若稍得满足,便会安然自得,恬然入梦。
四
新写实选择了彻底的生存与世俗是坚定的,没有余地的。那么,新写实小说的这种价值取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作用如何?其局限性以及未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新写实小说对文学所采取的生存视角,尤其注意描写世俗人生的主题,不仅仅反映了当前普遍的社会情绪和大众心态,它对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我国目前的社会无疑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新写实小说在新时期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上也有其独特性,它第一次摒弃了所有的理想观念,把人放进了没有信仰观照的普通生活中去写生存之累,这种充满世俗特征、日常特征和大众特征的倾向,使中国文学出现了空前的写真现象,使文学与生活的距离进一步拉近,更加贴近生活现实。此外,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与生活常常有实录原本状态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新写实小说并不注重要说明什么,而把重点放在表现什么上,在此创作原则下,文学在充满生命自然状态下得到了充分的本真显露。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无疑填补了当代文学中的空缺面,也必将有助于当代文学走向多维发展的互补局面。
另一方面,不能不提的是对信仰的忽视或是轻视甚至于摒弃,乃是新写实小说的巨大缺陷,这也许是甚至今不能成大气候的原因所在。的确,全然忽视生存现实而去一味张扬信仰,那是盲目的信仰,是空浮的信仰。尽管这种信仰带有虔诚的宗教色彩,但毕竟它对于世俗的“凡夫俗子”是可望不可及的。时间长了,这种信仰的存在必然会产生副作用,那样的话,它不仅不会使人类更加坚强地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而且会使人产生逃避现实的空想。从这方面讲,我们宁愿选择反映生存的文学,而不会选择反映空幻信仰的文学,因为前者更具有生命的真实性。但是,对于芸芸众生来讲,的确又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理想,不能没有希望。信仰、理想、希望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动力和活着的信心,是人类这种充满生存目的性动物的特性。因此说,新写实尽管给人的现实感很浓烈,但人性的揭示欠缺;可读性很强,但留给人的思考和回味不足。鉴于新写实小说特有的世俗精神和媚俗倾向,使其缺少一种深刻的、高度的文化审视和宏观视野,也缺乏深沉的情感力度和悲剧价值。它是在琐碎的日常人生展现中,来完成自己世俗文化的生命写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写实小说是对传统文学中很少关注生存状态的“中和”之风的超越。
其实, 新写实小说的最大遗憾是它缺乏现代人生的精神品位。 在90年代的今天,要写现代的中国人,要写正走向世界一体化的中国人,就不仅要有独特的传统生存风格,也需要具备现代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要真实地呈现出真正的生命情态,必须要在人生、社会广阔的生存现实和信仰前景上下功夫。走出灰色人生的圆囿,在精神品位上增添一些现代的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