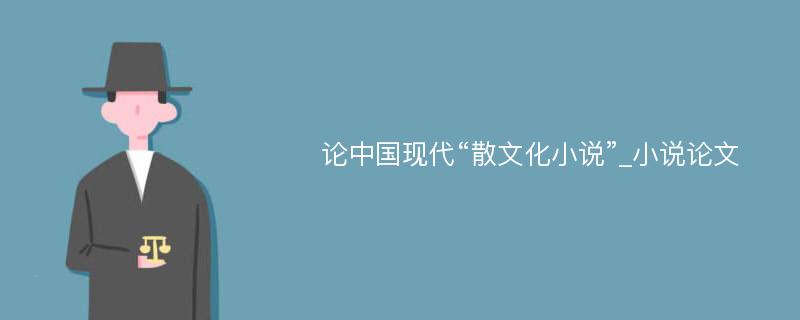
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散文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9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 —3926(2000)02—0063—05
20世纪对于中国小说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纪。当中国小说经历漫长的古典时代,跨入20世纪之门后,终于从边缘位置走向文学的中心,成为了文学舞台上的“正宗”角色。从此以后,它以一种新的姿态踏上了现代途程,也在对旧传统进行反叛、颠覆的同时走向了新的选择。较之古典时期的小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无论是思想倾向,还是艺术形式、美学追求,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单就其文体形式而言,便发生了深刻的巨变,出现了多样的、富有创造性的新形式,散文化小说便是其中之一。这种富有探索创新意义的小说形式与古典小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古典小说一向讲求故事和情节的引人入胜,讲求结构的完整,表现出极强的叙事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的作家写小说就是编故事。而在现代散文化小说中,叙事性因素被大大弱化,情节故事乃至结构不再受到重视,这与古典时期那种陈陈相因的程式化的小说形式是迥然不同的。
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的出现,既是对旧有小说传统发起挑战、反叛,进行探索、创新的结果,也是各文学体裁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渗透和影响在各文学体裁的发展过程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东、西方都没有例外。巴赫金在论及“作为一种体裁的小说”时,指出,“在走向主导地位时,小说促进所有其他体裁的更新”,造成“其他体裁的小说化”现象,同时“小说不让自己的任何一个品种保持稳定”,“小说对其他体裁(正是作为体裁)作庄谐体摹拟,剥去它们在形式和语言上的假定性,排斥一些体裁,把另一些体裁纳入自己原来的结构,并重新理解和评价它们。”[1 ]小说和其他文学体裁的这种相互吸纳的现象,必然使小说和其他文学体裁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新和独创性,从而得到不断的发展,散文化小说无疑就是一个相互吸纳的产物和小说创新的标识。
追溯小说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化小说是到了现代才出现的。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在文体结构方面颇具散文化特征的小说——《十日谈》,虽然它叙述的是故事,但在文体探索方面却显示了作者的自觉意识,米兰·昆德拉说:“在现代欧洲,这本书(《十日谈》)是最早的创造大型的叙事散文结构的尝试之一。”[ 2]可惜的是,在欧洲小说史上,由《十日谈》开创的散文化传统并未随之被重视、推进,而是长期被中断。相对而言,中国的散文化小说的出现晚了好几个世纪,但也是在中国进入现代时期后出现的,虽然中国在汉代就有了散文和小说的分野,那以后也客观地存在着小说和散文间的边缘化写作问题,比如《搜神记》、《世说新语》中的许多作品都有“散文化”的特点,但是,当时的作者并不具有自觉的小说文体意识,真正在自觉的文体意识支配之下所进行的小说“散文化”的探索与尝试,则是进入现代时期以后的事, 具体说来, 它最早见诸“五四”时期。1919年,俞平伯的小说《花匠》的面世使我们注意到了它的散文化气息:它用拟人手法对花进行心理描写,用抒情的笔调加以叙述,让人觉得它更像一篇散文而非小说。在此,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似已初显端倪。较之俞平伯,现代小说之父鲁迅更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3], 他的《故乡》无疑是现代较早的堪称“散文化小说”的作品。《故乡》通篇以抒情的笔调,渲染童年生活的美丽,既写闺土也写“我”,展现了“我”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寻梦,又终于绝望而去的心理过程,表现出显著的抒情性特征,而这恰是散文化小说的一个重要表征。在现代时期,对散文化小说进行探索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的作家,还有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承续散文化小说传统,创作上颇有收获的作家仍大有人在,主要有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可以说,从“五四”到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这条审美线索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它既显示了散文化小说的生命活力,又使得散文化小说成为一个值得留意和研究的文学对象。
今天,提起“散文化小说”,人们已不会感到陌生,然而,“散文化小说”的概念含义及其特征仍然让人一言难尽,“散文化小说”依然是一个非常宽泛、含糊,缺乏具体明确界说的概念,也许“界说”是一件极不容易也极不明智的事,因为愈是丰赡的事物,愈是难以拿几个字或几句话来界定它。人们似乎意识到了为它下定义和廓清其特征的巨大难度与危险性,所以长期以来总是避实就虚地谈说它,或随心所欲地在不同的层面使用这一概念,也有一些对小说文体感兴趣的论者,总是愿意对散文化小说创作的个案进行分析,而不愿意越过这些个案去追究“散文化小说”的特征。这些不免会造成对“散文小说”认识、理解上的混乱不清,也使得散文化小说始终如雾中之花般面目模糊。鉴于此,弄清散文化小说的状貌,廓清其特征,寻索其灵魂,确实显得既迫切又必要,拙文的写作用意正在于此。也许,这是一次艰难的探险,结果不会尽如人意,但如果能有些许发现,那同样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那么,究竟什么是散文化小说?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有何特征?这是本文无法绕开也不能绕开的问题。实际上,自现代以来,人们已经有意无意地触及到了这些问题,只不过未曾加以明晰深究罢了。30年代初,穆木天、徐懋庸等人就曾注意到当时小说创作的“散文随笔化倾向”,可惜他们只是担心它“危及小说样式之独立”[4], 而并未说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与阐释。在新时期出现的一些论著中,我也曾见到“散文化小说”就是“散文与小说两种文体互相渗透后出现的一种新文体”[5]的说法,这固然不错,但太过笼统。或许, 杨义的说法更接近“散文化小说”的实质,杨义认为,小说的“散文化”,“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6](P542)。杨义的说法对我颇有启发,在我看来, “散文化小说”就是抒情小说、非戏剧性小说,也就是说,抒情性、结构的非戏剧性是散文化小说的核心特征。虽然郁达夫、沈从文、萧红、汪曾祺、贾平凹等人的小说意味不尽相同,但人们却通常把它们统统归入“散文化小说”的行列,这说明,在这些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背后,确实还存在着某种能将他们的作品联在一起的共性特征,这种共同性特征主要就是抒情性特征和结构的非戏剧性特征。
由叙事向抒情的转变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重大变化,它意味着小说描写焦点从动作转向心理,从故事转向琐细的情感。这一转向肇始于“五四”,在“五四”时期,抒情的氛围弥漫,笼罩着小说界,无论是激情直露的郭沫若,还是冷静深沉的鲁迅,无论是苦闷的郁达夫,还是感伤的庐隐,他们的小说在字理行间都饱含着作者的情感和自我情绪,在人物内心的抒写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强度和深度,表现出显著的抒情风格和抒情性特征。
或许,“五四”小说这种总体上的抒情特征来自于作家在一个新异的时代所产生的那种强烈的抒发自我,表现自我的渴望;或许,它也与作家们在小说创作上的自觉追求不无关联。在“五四”时期,冲决罗网的兴奋,遭受挤压的痛苦,追求碰壁的压抑,诸种情绪,使人急需要渲泄与排解,而小说就是一种绝佳的情绪的出口,所以作家们纷纷以小说来表现自我、传达心声。与此同时,现代小说的尝试者、开拓者已不满足和不愿意遵奉我国传统小说既成的美学戒律,他们试图进行小说审美表达方式的创新,他们追求抒情并希望小说朝抒情化的方向发展,这在创造社作家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创造社作家从理论到实践都强调小说的主观性和抒情性,郭沫若认为,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抒情是其天生的特质,郭沫若的小说常常以主观抒情为基调,出于内心倾诉、情感展示的需要,他多选择“自叙传”和第一人称“我”的体式来写作小说,来渲泄青春的苦闷,生存的苦闷,社会的苦闷,他的小说《鼠灾》、《未央》初具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特征,《牧羊哀话》、《残春》、《喀尔美萝姑娘》则有突出的主观抒情特征。郁达夫也看重抒情,他说:“小说的表现,重在情感。”[7 ]他之所以对日记体、自叙传这种文学体式推崇备至,原因之一便在于这种小说体式便于抒发情感,这种“自叙传”抒情小说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也是“五四”小说家较喜欢采用的。郁达夫小说具有鲜明的“自叙传”抒情特征,无论是用第一人称的“我”,还是用第三人称的“他”来写,其小说大都直接取材他本人的经历、遭遇与心情,且往往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去抒写个人的情绪波动和心理的变化,较典型的如《沉沦》,它以日记的方式披露主人公“他”的内心痛苦与企求,也真实传达了作者的情感。创造社诸作家中,成仿吾的说法更具反叛性,在成仿吾看来,小说不需要强调典型的描写和故事情节,只要努力表现自我、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气质与情感,就可以“充满了更新的生命”,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认为,追求典型的小说是“失败”的,描写的艺术是“文学家的末技”,带有故事性的作品不能称之为“我们近代所谓小说”[8]。 成仿吾的观点虽不乏过激之处,但也道出了他不满既成的小说规范、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抒写的心声,除了创造社作家外,当时也有其他社团的作家写有以抒发个人苦闷和感伤情绪为主的“自我抒情小说”,比如文学研究会的庐隐,浅草——沉钟社的陈翔鹤等等。总之,在“五四”时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似乎更愿意把一个赤裸裸的“我”放到创作中来“抒情写世”[9]。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些作家们渴望自我抒发, 追求不受束缚的激情抒写,使得“五四”成为中国小说的抒情时代。
在告别“五四”时代之后,中国小说虽然走出了“抒情时代”,但其抒情传统并未断裂,抒情特征仍时隐时现,并主要在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等作家的散文化小说中得到呈现和延展,这不仅说明,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就有抒情的一脉存在,而且也足以说明,抒情正是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的共性特征之一。事实上,近观中国现代作家的散文化小说创作,是不难发现这一点的。
最早对散文化小说创作作出较大贡献的郁达夫,其小说的抒情特征人所共识,自不必多说,在他稍后,又有废名,废名的小说既钟情于乡土,又以抒情见长。他笔下的艺术世界常常由竹林茅舍、桃园菜园、柳荫菱荡、古塔木桥、修竹绿水以及慈爱的老者、清纯的少女、善良的浣衣母等等所构成,这一艺术世界不仅散发出诱人的乡土气息,也寄托着废名对“抱朴含真”的乡土田园的浓浓情思及其由衷的欣赏、赞美之情,同时,也体现了废名小说抒情方式的独特性:他不再像“五四”小说家们如郁达夫、庐隐等那样多采用“自叙传”的方式来进行主观抒情,而常常把平凡人生的描写与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景物及田园情致的描写相交融,以此来进行抒情,来吟颂自然的诗意美,人物的性灵美以及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宗法制农村社会的拙朴之美。由于把山水景物、田园意趣纳入作品中,废名小说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领域,也赢得了“乡土抒情诗”之美誉。废名的创作对其后的作家如沈从文等亦产生了影响,曾有人说,“在现代抒情小说体式的发展史上,从郁达夫到沈从文,废名是中国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10],废名上承“五四”抒情传统,又在创新的基础上把抒情小说的接力棒传给了沈从文等后来者,这一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沈从文确实从废名那里吸取过养料,受到过浸染,这不仅见诸于沈从文自己的言谈,他的创作更是有力的印证。沈从文的那些以湘西农村生活为题材内容的散文化小说,就是抒情味、乡土味十足的小说,所抒写、流露的就是作者那种热爱湘西、“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11]的深挚情感,这种深沉的情感在文本中常常附着、投射在民俗民情的描写上,纯情人物的设置上,自然景物和人事谐合的描绘上。所以,在《边城》中,我们看到了古朴的茶峒城,独特的河街吊脚楼,热闹的龙舟大赛,不倚富仗势的船总儿子,天真纯情的翠翠姑娘;在《柏子》中,见到了不乏真情投入的水手与妓女之爱;而在《三三》中,则见到了宁静清幽的杨家碾房,咿咿呀呀的水车,如堆积蒸糕的山田,鱼、鸭游弋共享的水潭,无拘无束的少女三三……这一切,在沈从文笔下是那么诗情画意、和谐动人,它们把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对故乡的热爱、认同的情感表露无遗。
不独废名、沈从文,还有许多现代作家经由散文化小说而与抒情结缘,譬如萧红、汪曾祺等。在散文化小说的创作上颇有实绩的萧红,可说是一位极擅长悲情抒写的作家,她敏感于童年的孤寂,悲悯于东北人民的生与死,她痛心于女性遭受的摧残,忧戚于沉滞的生活、悲凉的人生……借助于自己那支本色天然的笔,她将这一切毕现于笔下,呈现于《生死场》、《呼兰河传》和《后花园》等小说中,当我们披阅这些作品,总不免会为其中浓烈的情愫所牵动,会为那些忧郁感伤的倾诉、艰涩凄苦的哀吟所震撼,甚至涌起久埋于心底的热泪。不过,在汪曾祺那里,抒情则很少与感伤关联,而通常与诗意氛围的营造相关。汪曾祺特别重视氛围的营造,他的散文化小说往往喜欢对环境风物、民俗民情进行恣意的抒写(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也有类似现象),其目的在于以此来营构充裕舒缓、不乏诗意的氛围,来揭示、歌咏江南水乡的美丽多姿、民风民俗的素朴可爱、人情人性的美好健康。除却他40年代的《老鲁》、《鸡鸭名家》外,在这方面颇有代表性的作品要数80年代所写的《大淖纪事》,这篇小说用大量的篇幅写了大淖的自然环境及乡风乡俗——那云光水影,那沙洲、茅草、芦苇蒿……还有大淖人与众不同的生活形态和道理伦理观念:大淖人世代相传,都是挑夫,都靠肩膀吃饭;大淖人多顺乎感情而行事,“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并且,这里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上个男人,都不是稀奇事,别人也不会以此为怪,“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标准:情愿。”这些描写,突出了水乡的景致风物,揭示了大淖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很少受传统道德观念束缚的自然纯朴的天性,也充分表现了作者对此情此景此人生的赞叹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性,与诗歌、散文甚至戏剧的抒情性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具体到散文化小说中,这种抒情性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风采,主要在于,它并不是简单的触景生情、借物抒怀,或者把作家的情感固化于某一段,某一句或某一个语词,而是将作者的感情内化于整个文本的字理行间,也就是说,作者的感情通常是通过整个文本来加以完整的传达的,这或许也正是散文化小说既近乎散文,又未曾完全与散文同声合气的一个表现吧。
当然,在小说家族中,抒情性特征并非为散文化小说所独有,“诗化小说”就同样拥有鲜明而强烈的抒情性特征,正因如此,有时人们不免模糊它们之间的界限,把它们当作同一种小说体式来加以谈说。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一点研究者早有发现,杨义就曾明确指出,散文化小说是“随意小说”,它“想发议论便议论,想写心情且来写心情”,结构亦自由、随意,而诗化小说则是“立意小说”,“它拆除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的堤坝,却把它引入诗意的清池”,“它不是在感情无法约束的时候写的,而是感情得以凝结,把它容纳在精心熔裁的结构修辞之中,使之神韵圆全,诗趣盎然”[6](P543 )。应该说,杨义对二者的分析是精到而准确的,它对于今天我们认识、区分“散文化小说”与“诗化小说”这两种小说体式,仍然是颇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不单是抒情的小说,也是非戏剧性的小说,非戏剧性特征是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的又一共性特征。这里,“非戏剧性特征”是就其结构特点而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小说就是戏剧性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结构常常为作者所精心安排,作者不仅讲求情节的因果关系,讲求矛盾冲突的发展变化,而且有时还讲究事件的巧合,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之下,小说故事不仅有开端、发展变化,而且有高潮、结局,这种起承转合、有头有尾的小说意味着谨严而有章法的结构,也意味着“戏剧性”。中国现代以来的散文化小说则打破了小说结构的戏剧化传统而对固有的程式规范进行了反叛,它们往往忽略结构剪裁,淡化、轻视情节事件,也不一定按情节故事的发生发展线索或某个人物的活动来谋篇布局,这种“非戏剧性”特征带来了小说写作的自由性与灵活性,也有助于小说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不讲情节,不设高潮,随意着笔,甚至几无剪裁,这种“非戏剧性”特征在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中是较为普通的——
郁达夫的《沉沦》,既无完整的情节,也不靠典型人物的行动来串连全篇,而主要以主人公“他”的心理情感的波动来缀连全篇,这正是他所说的那种“注意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而不将全力倾汇在外部事变的记述上的作品”[12],郁达夫的小说,多属此类。由于表面上的缺乏结构,郁氏小说曾招来微词,苏雪林就曾毫不客气地说:“郁氏作品不讲结构,原不算什么奇怪,但篇篇如此却也讨厌,更显得作者对文字缺乏安排组织的天才。”[13]其实,郁达夫的小说不讲结构并非无结构,只不过他以当时中国尚不多见的心理结构代替了传统小说的戏剧性结构而已,这种结构形成的小说更便于作者直抒胸臆。创造出这种小说形式,使郁达夫在中国现代小说文体发展史上功不可没,正如杨义所说:“他是以结构的心理化,推进现代小说的散文化的。”[14]
与郁达夫不同的是,废名不是以写心理情感的方式来写小说,而是以写作美文般的散文笔致来写小说的,但与郁达夫相似的是,废名同样的不重情节故事,即使他在讲述《竹林的故事》时,其实也是并不真正精心于故事的,他感兴趣的只是宁静优美的田园风光和一个个流动的琐细的生活图景,他所精心的则是如何将这些风光景致在诗的意境中加以展现。
而沈从文之所以被称为“文体作家”,首先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散文化小说这种特殊的小说体式。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亦体现出不重情节人物且有时并不刻意追求章法技巧的特点,他曾说,他“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到章法内取得成功”[15],他的受人称道的《边城》,即是不讲章法规范一例。这篇小说并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一开始即以引人入胜的情节抓住读者,而是由着作者的兴致,琐琐碎碎,优闲自得地讲起边城茶峒的地理风物、民风民俗,直到第五节才回到正题,讲述翠翠和爷爷的故事,这不免在节外生枝的同时,延缓了小说的叙述节奏,造成情节的延宕,它虽然于故事外告知我们许多别的“信息”,即仍不免令那些急于寻找故事情节的人感到失望。由于“信息量自然与叙述速度成反比”[6], 阅读这种采用含信息量大的叙述形式而不讲究情节故事的作品,是需要有一定耐心的。不过。《边城》尽管冗繁拖沓,却颇受人喜欢,这或许就是散文化小说的魅力所致吧。
在现代作家中,萧红是“才胜于学”的一个特例,由于文学修养的欠缺,她几乎完全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她的小说,若按传统的小说观来衡量,是有不少缺陷的,胡风在为萧红的《生死场》初版所写的后记中,就一面肯定了她的“创见”,一面总结了这篇小说的三个“弱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写里,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它的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通,不能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面前。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了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17]应该说,胡风的评价是中肯恰切、切中要害的,但若把第一、第二项“缺点”放入散文化小说中去看,又实在算不上什么缺点,相反,它们正是散文化小说的特点之所在,因为散文化小说不讲情节结构与人物刻划。萧红的小说正因具有散文化特征而与传统的小说学显得格格不入,但萧红自己对此颇不以为然,她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18]萧红的小说常常以不拘一格、率真自然见长而并不以功力、章法取胜。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其形式结构都显得极为松散与粗疏,不具备叙述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人物刻划也并不着力,而“‘形式’又反转来‘规定’了内容,使容纳其中的生活也‘散文化’了。越不用力,越不为预设的目的所拘限,她越象自己,任何过分的用力都反伤自然”[19],所以《生死场》近乎于几个人物零散生活片断的缀合,《呼兰河传》根本就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也都零零碎碎的,尤其让人惊异的是,它居然用整整半部的篇幅来写呼兰城及其风俗民情,这样的小说正是具有非戏剧性特征的不折不扣的散文化小说,它们是在一种近似于散文的“横切”结构中完成其艺术陈述的,而不是纵向的因果演绎而成的戏剧性的繁复情节的审美构成。
散文化小说偶尔也会遭遇或称之为散文、或称之为小说的找不着归宿的情况,贾平凹的散文化小说《商州三录》就是如此。由于它采用了散文式的章法结构,人们很难区分它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以至于在谈说它时,出现了“两栖现象”,或者把它归入散文之列,或者把它称之为小说,其实,它是二者的特征兼得而又并不失小说特质的散文化小说,它不追求因果关联、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而常常将从生活中信手拈来的一些人、事、景组成一个个清新明丽的画面,随着画面的推移流动,完成事件的叙述,也许,将它称之为非戏剧性小说,恐怕能使它摆脱“两栖”的尴尬。
当然,散文化小说对传统小说的戏剧性程式化结构的冲击、反叛,并没有走向彻底颠覆的极端,它把情节化淡,人物化虚,结构化散,却并不意味着将这些要素化无,这正是它与旧有小说风貌迥然不同而又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小说特质,未被“化”入他种体裁中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基于此,我不愿把新时期以来的“三无小说”划归入散文化小说之列,因为“三无小说”的“三无”——“无明确主题”,“无情节”,“无人物”与其说是把小说从古典形式的“有序”推向了现代嬗变的“无序”状态,还不如说是把小说推向了什么也不是的境地。
“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角度看山,会有不同的所见,同样,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散文化小说,自然也会有不同的发现,假如我们撇开其抒情与结构特点不论,单从题材的角度去看,又会发现散文化小说的又一个特征,那就是它往往不涉及重大题材,散文化小说的作者所关注的多是小人小事或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断,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这或许正是一些优秀的散文化小说作者一度被正统的文学史所冷落轻视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正是因为角度问题,使拙文对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特征的阐说不可能涵盖散文小说的所有特征,而且这种阐说本身或许尚有不少无力之处,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不是任何努力都毫无意义,说不定拙文能抛砖引玉也未可知。
收稿日期:1999—11—15
标签:小说论文; 沈从文论文; 郁达夫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散文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边城论文; 呼兰河传论文; 十日谈论文; 生死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