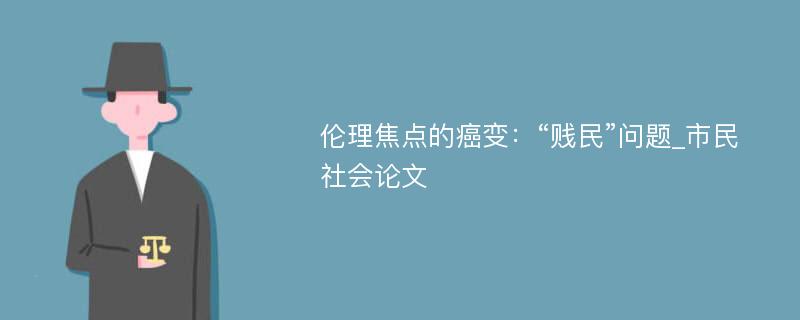
伦理病灶的癌变:“贱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贱民论文,病灶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6-0005-07
2004年4月23日,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在宿舍内连杀四位同学,令全社会震惊。然而,处决马加爵之后,校园暴力非但未有效控制,反而于短短几年内恶性发展,小学、幼儿园疯狂屠童案屡有发生,仅2010年上半年就连续发生五起。
面对日益恶化的情势,全社会陷入痛思。
“悲痛欲绝的伤亡者亲友们、目瞪口呆的社会,再次发出恸问:‘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办?’”[1]
2010年5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频发的杀童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问题在于,“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分析当然必要,但伦理学、道德哲学的缺场,使任何分析都不彻底,至少缺乏解释的深度和力度。仔细反思发现,这些社会灾难及其祸首的两个精神轨迹有待也必须揭示。
1.马加爵,马加爵们,如何从“贫”走向“贱”,再由“贱”走向“暴”?如何从弱势群体蜕变为暴力群体?其癌变的个体精神轨迹是什么?
2.这类恶性案件如何从个别事件演化为愈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从马加爵杀害同学恶化为校园屠童?其癌变的社会精神轨迹是什么?
精神哲学分析表明,这类恶性事件根源于伦理病灶,准确地说,是伦理病灶的癌变。其表象与后果是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但源头却是一种深刻的伦理问题和精神现象。因此,必须对它进行道德哲学和精神哲学分析,借此可以发现伦理问题恶化为社会问题、伦理病灶癌变为社会毒瘤的精神轨迹。这便是道德哲学分析,精神哲学分析的意义。
作为道德哲学与精神哲学分析的对象,这一问题研究的关键概念是:“贱民”;核心解释是:由“贱民”到“暴民”的精神癌变。
一、从“卑贱意识”到“贱民”:伦理及其精神链的断裂
“贱民”的病根是“贱”。理论上,“贱民”现象发生于市民社会领域,因“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伦理实体运动中的精神断裂而产生,是伦理实体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认同危机的恶性后果。它既是一种现实,以现实伦理关系中伦理地位的“贱”为基础,又是一种对现实的态度及其人格表现,是精神和意识的“自贱”。它是由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有机性断裂而形成的社会病态。
以市民社会和生活世界为载体,“贱民”的发生经过两次精神蜕变。它潜在于家庭向市民社会的伦理过渡及其断裂中,其表现形态是“卑贱意识”;形成于市民社会向国家的伦理过渡及其脱节中,其表现形态是“贱民”。如果进行精神哲学分析,那么,“贱民”发生于伦理世界解构,道德主体未能建构的教化世界或现实世界环节和精神发展阶段。
“卑贱意识”是“贱民”的精神基因和意识基础。根据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理论,人的精神的现实发展必须经过“伦理—教化—道德”三个发展阶段,由此形成“真实的精神”—“自身异化了的精神”—“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的精神发展的辩证过程,呈现为“伦理世界—现实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有机体系。伦理状态是人的精神的自然形态或原始形态,伦理世界是精神发展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个体与实体或他所处的共体直接同一。在这一阶段,精神呈现为家庭、民族诸伦理性实体,“实体就是没有意识到其自身的那种自为地存在着的精神本质。至于既认识到自己即是一个现实的意识同时又将其自身呈现于自己之前(意识到其自身)的那种自在而又自为地存在着的本质,就是精神”[2]。在伦理世界中,人的精神和行为受伦理必然性即伦理规律支配,表现为所谓“悲怆情愫”,但由于实体与精神直接同一,因而有归宿和认同。“精神既然是实体,而且是普遍的、自身同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那么它就是一切个人的行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消除的根据地和出发点——而且是一切个人的目的和目标,因为它是一切自我意识所思维的自在物。”[2]在伦理世界中,个体与家庭、民族两大伦理实体直接同一,以家庭与民族的伦理实体为绝对本质,个体及其精神的存在形态就是家庭成员与民族公民。
但是,伦理世界乃是一种直接的精神和简单意识,是一种伦理性的自然存在或所谓“无知之幕”,由于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规律,即所谓天伦与人伦、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的矛盾,在人的伦理行为中必然发生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两种伦理行为的分裂与对立。于是,原初的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精神形态便异化或现实化自身,进入教化世界。“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个体在这里赖以取得客观效准和现实性的手段,就是教化”[2](42)。精神的异化或现实化将伦理世界解构为抽象的原子式个人,由伦理状态进入所谓法权状态,由伦理世界进入生活世界,出现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实体的分裂与对峙。
教化是伦理世界的现实化,也是精神的现实化,在教化世界或生活世界,伦理存在和人的精神形态都发生深刻变化,个体与伦理实体的同一性必须透过两个中介或两种世俗形态才能实现:国家权力与财富。由此,人与伦理存在的原初的同一性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产生两种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的判断:高贵意识;卑贱意识。“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都与自己同一的意识,乃是高贵的意识”,“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这两种本质性都与自己不同一的那种意识,是卑贱意识”[2](51)。高贵意识是个体与国家权力和财富两种伦理存在同一的意识关系,卑贱意识则是个体与国家权力和财富两种伦理存在不同一的意识关系。由此,相应产生两种意识形态:善与恶。“判定或认出同一性来的那种意识关系就是善,认出不同一性来的那种意识关系就是恶;而且这两种方式的意识关系从此以后就可以被视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2](50)
于是,随着伦理世界向生活世界,或由伦理状态向教化状态的转化,人的精神和意识异化出所谓“高贵”与“卑贱”,“贱”于此第一次精神地也现实地诞生了。
不过,卑贱意识只是一种精神现象,由卑贱意识向“贱民”的现实转化,则发生于另一次伦理断裂,即市民社会与国家两大伦理实体的断裂之中。“贱民”的概念及其理论第一次出现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明确指出,“贱民”产生于市民社会领域。由于市民社会解散了家庭,形成社会分工和等级,出现贫富不均,因而必然导致贫困。但是,“贫民”与“贱民”既有关联又有根本区别。二者的相通之处是财富和权力方面的“贫”或贫困,根本区别在于精神或意识,即由贫困而产生的对待权力和财富的态度。贫困和贫富不均必然产生贱民,而贱民的出现又会加深贫富不均。“贱民”因“贫”而产生,但由“贫”生“贱”根本上是一次伦理蜕变。“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3]贫困使人丧失自尊和正义,但由“贫民”向“贱民”的转化是一种精神过程,它表现为一种情绪和态度,即对财富和权力的反抗与对立。“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结合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2](244)由于对财富和权力的“内心反抗”便出现由“贫民”向“贱民”的精神转化。但是,如果这种“贱”只是停留于“内心反抗”,一种自我意识的判断,那么它还有一定积极意识,乃至可以由此产生批判意识和革命倾向;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贱”继续蜕变,孳生一种人格和行为的“贱”。“此外,与这种情绪相联系的是,由于依赖偶然性,人也变得轻佻放浪,害怕劳动,而像那不勒斯的游民那样。这样,在贱民中就产生一种恶习,它不以自食其力为荣,而以恳扰求乞为生并作为它的权利。”[3](244-245)由此,“贱”便再次异化为一种人格,一种恶习。
由是观之,“贱民”之“贱”有三个基本结构,或经过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一,“自我意识”的“贱”,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判断,即由对财富和国家权力不同一关系判断所产生的“贱”,所谓“卑贱意识”;其二,社会态度的“贱”,是由贫困而产生的对财富和国家权力态度的“贱”,表现为一种伦理上“内心反抗”的情绪;其三,行为和人格的“贱”,表现为好逸恶劳的恶习。自我意识判断—社会境遇与伦理态度—行为人格,“贱”便在精神中一步步由意识透过态度,现实化人格与行为,由此具有恶的性质。从对于伦理存在的同一性关系的判断意识,或精神发展中的一种潜在可能(“卑贱意识”),现实化、客观化为一种令人同情的社会境遇(“贫民”),最后由对权力和财富“内心反抗”的“贱”,蜕化为人格行为的“贱”,沦为伦理道德的恶,从而在精神上沉沦了。在这个不断蜕化的进程中,贫困是产生贱民的客观根源和现实基础,所以,“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3](245)。但由“贫民”向“贱民”的转化,根本上是一种精神现象,准确地说,是社会问题与精神问题结合所导致的社会—精神现象。
“自我意识”的“贱”—社会态度的“贱”—人格行为的“贱”,就是“贱民”发生的精神轨迹。至于由“贱民”向“暴民”的恶变,则是人格行为的“贱”的癌扩散。
二、伦理出局:从“贱民”到“暴民”
精神现象学分析表明,“贱民”根本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和伦理现象,其症结在生活世界或市民社会中的特殊伦理存在,即国家权力与财富。它发端于伦理认同,即对于国家权力与财富关系的不同一性的自我意识;客观化于伦理现实或伦理境遇,即在国家权力和财富的伦理关系中贫困的现实;生成于伦理态度,即现实伦理关系中因贫困而导致的“内心反抗”;恶化为一种伦理人格,即好逸恶劳的人格和行为。“贱民”之“贱”,既是一种客观的“贱”,即现实经济与社会关系中的贫困;更是一种主观的“贱”,这种主观的“贱”有两面性,一是“贱社会”即对社会的“内心反抗”,一面是“自贱”,即在人格上作践自己。客观“贱”是基础,主观“贱”是生成条件。但是,如果只是停滞于此,“贱民”还只是在社会上产生一种因弱势而寄生的群体。严重的问题在于,伦理态度和伦理人格还会继续恶化,“内心反抗”外化为“现实反抗”;“贱”的伦理人格和弱势群体本质的结合,在特定条件下,使“贱”畸形化为“暴”,并内在极大的危险,将“贱”的“内心反抗”“暴”发于比自己更为弱势的群体,于是,校园屠童之类的恶性案件便发生。由此,“贱民”便癌变为“暴民”。
解释“贱民”问题,以及由“贱民”向“暴民”恶变的关键性概念是:“伦理出局”;形成这一问题的道德哲学与精神哲学根源是:市民社会与生活世界中的伦理存在形态及其与人的关系的异化。
问题的阐释关涉道德哲学乃至“人学”的基本问题: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转换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本始样态是什么?回答是:“伦理人”。
“伦理人”的假设追溯到中西道德哲学与精神哲学的经典理论。儒家哲学一方面以“仁”或道德说“人”,强调“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另一方面又以“礼”说“仁”,“克己复礼为仁”,认为“人”的真正生成必须经过礼仪化即伦理化的教养过程,而“仁”则是一种伦理上的“自化”,因此,人在本质上是“伦理人”,或首先是“伦理人”然后才是“道德人”。这种思路与黑格尔精神哲学正相契合。根据黑格尔精神哲学理论,人及其精神发展的第一个环节是伦理世界,伦理世界中的人是个体与实体同一的存在,具体呈现为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人的现实性的直接的和自然的形态,就是伦理世界,因而人从本性上说是“伦理人”。家庭成员与民族公民两种意识,以及天伦与人伦,或所谓“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是伦理世界中“伦理人”的意识形态及其行为规律。无论“成员”还是“公民”,都说明个体以实体为本质和存在方式。“成员”的真义是“个别性的家庭成员的行动和现实以家庭为其目的和内容”;“公民”之“公”,在于“一个人的心就是所有人的心”,个体只有体现共体的本质才有现实性与合理性。因此,人在本性上是“伦理人”,是以实体为现实性与合理性的伦理存在者。
但是,伦理是一种具体而辩证的存在,在社会生活的不同环节,在人的精神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伦理具有不同的存在形态。在伦理世界或精神发展的原初阶段,伦理存在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其形态是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在生活世界或现实化的精神世界中,伦理存在是被中介了的,其存在形态是国家权力和财富;在道德世界中,伦理存在表现为个体的德性,因为“德性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家庭和民族的伦理存在与个体直接而自然地同一;道德世界中的伦理存在透过德性主体的建构达到与个体的同一;最大也是最深刻的问题发生于生活世界。因为,一方面,国家权力和财富的伦理性往往在意识中被遮蔽,卑贱意识的产生便源于此;另一方面,它们作为普遍存在者的伦理性也很容易在现实中被异化,成为个人的“战利品”或私有物。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的精神、伦理存在的现实形态,是一个辩证结构和辩证过程,具体地说,是“家庭、民族—国家权力、财富—德性”的辩证发展过程,因而国家权力和财富作为伦理存在者本性的遮蔽或异化,将导致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断裂,从而产生深刻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形成被肢解的碎片化的人和人格,导致人的精神的病态和变态。
如前所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贱民问题发生于市民社会领域。根据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伦理作为一种客观精神,在现实化自身的过程中,表现为由三个精神环节构成的辩证运动。家庭:直接而自然的普遍性或精神;市民社会:形式普遍性和异化了的精神;国家:现实的普遍性和精神。市民社会虽然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但它只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环节,它解构了家庭,但又未达到国家,它的形式普遍性决不意味着合理性,也并不意味着现实性。家庭是人的精神的家园,“因为对意识来说,最初的东西、神的东西和义务的渊源,正是家庭的同一性”[3](196)。而且,家庭具有一种特殊的伦理功能和伦理形态意义:照顾个人需要的特殊性,为个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家庭是实体性的整体,它的职责在于照料个人的特殊方面,它既要考虑到他的手段和技能,使其能从普遍财富中有所得,又要考虑到他丧失工作能力时的生活和给养。”[3](241)
市民社会解构了家庭的同一性,也颠覆了人的最初的安身立命的基地。“市民社会把个人从这种联系中揪出,使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变得生疏,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这样,个人就成为市民社会的子女,市民社会对他得提出要求,他对市民社会也可主张权利。”[3](241)从本性上说,市民社会解构家庭的自然伦理形态后,应该担当起作为“公众家庭”或“普遍家庭”的职能和使命,以满足个体的特殊急需,这就是公共机构和同业公会存在的意义。市民社会的“普遍权力接替了家庭的地位,它不但顾到他们的直接匮乏,而且顾到他们嫌恶劳动的情绪,邪僻乖戾,以及从这种善中和他们所受不法待遇的感情中产生出来的其他罪恶”[3](243)。问题在于,市民社会是一种形式普遍性的法权状态,充满冲突,也内在着精神分裂的可能。“市民社会是个人利益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3](309)市民社会不仅与人的特殊急需疏隔,而且本身就是制造冲突的舞台。市民社会不仅制造了贫困,而且滋生了与贫困相联系的态度和情绪,并由此导致产生恶与罪的可能。
内在于市民社会的这种危机决定了它必须向国家过渡。国家作为“国”之“家”,应当是“公众家庭”的现实。黑格尔对国家、家庭、市民社会的关系有一个比喻性的诠释:家庭好比感受性,市民社会好比感受刺激性,而国家则是神经系统,是有组织的。国家“调整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规律,是映现在它们中的理性东西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的根据和最后真理是精神,它是它们的普遍目的和被知道的对象”[3](264-265)。对个体及其利益来说,国家一方面是外在必然性和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这是国家的力量所在。“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3](261)在国家中,精神的自为形态是爱国心,而爱国心作为一种政治情绪,本质上是一种信任,是对国家普遍目的和个人特殊利益的统一,或个人的特殊利益包含于国家普遍目的中的信任和信念。爱国心“是这样一种意识:我的实体性的和特殊的利益包含和保存在把我单个的人来对待的他物(这里就是国家)的利益和目的中,因此这个他物对我来说就根本不是他物。我有这种意识就自由了。”[3](267)问题在于,应然不是实然。国家作为个人利益和普遍目的真实的结合体,必须透过国家权力和财富两大伦理存在体现,权力的公共性和财富的普遍性是国家作为伦理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当这两个条件不具备或不充分时,国家的伦理合法就遭致怀疑和动摇。现实状况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当今中国面临两大深刻的社会问题,一是干部腐败;二是分配不公①。干部腐败使国家权力成为少数人的战利品,动摇甚至解构其伦理公共性;分配不公直接消解财富的伦理性。而当这两大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国家作为个人利益和普遍目的统一的伦理本性和精神信念,就不可避免地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动摇和颠覆了。
人在本性上是伦理存在者或“伦理人”,个体对社会的伦理认同和社会对个体的伦理接纳是人的自我同一性和社会同一性的精神基础。走出家庭之后,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伦理人”的身份必须也只能在与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关系中才能确证。市民社会作为“公众家庭”功能的匮乏,国家普遍生活中官员腐败和分配不公两大问题的严重存在,必然的社会和精神后果,就是使一部分人“伦理出局”,它们事实上被抛出伦理实体之外,至少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伦理实体之外,成为缺乏伦理关怀和伦理归宿的“伦理局外人”,遭遇忽视、冷落甚至难以生存的命运,从而产生对社会的“内心反抗”。这种“内心反抗”在两种情况下特别有可能从“贱”恶化为“暴”。一是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伦理实体中“出局”的同时,在家庭伦理实体中也“出局”,由此产生一种彻底的绝望,这就是“暴民”事件常常与家庭问题相伴随的缘由,因为这是一种彻底的“出局”,也是一种彻底的绝望。二是当“出局”的境遇和人格中潜在的暴力倾向相遇时,“贱民”便成为“暴民”。“暴民”之“暴”,一是“暴力”,二是“残暴”,表现为一种歇斯底里的反抗、仇恨和暴力。而由于“贱”的精神特质和弱势的地位,他们往往将施暴的目标选择为表面上更加弱势的对象,于是校园屠童事件便频频发生,它表现了“暴民”的一种彻底的懦弱和虚弱,在这类事件中,“暴”恰恰是“贱”的极端表达。
“贱民”的癌变及其向“暴民”的转化,在于“伦理出局”,这一假设在马加爵事件中可以得到验证。在马加爵事件中,有两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个细节是,他杀的是与他关系比较好,或相对不太欺侮他的四位同学,而不是平时的“仇人”。那一次,他们对他的嘲弄,让他无比暴怒。往日,他忍受了生活上诸多难以想象的困苦和他人的偏见,已经产生“内心的反抗”,但这些“朋友”也嘲弄他,他感到在这个共同体中彻底地被抛弃了,他“出局”了,于是惨案发生。第二个细节是,在作案过程中,有另一个同学偶尔来到现场,他非但没有杀他,还在狱中遗书中祝他“好人一生平安”,因为这是一位在重要时刻帮助过他的人,是一个在伦理上接纳和关怀他的人。由此可见,马加爵事件的病灶在伦理,是伦理病灶,具体地说是“伦理出局”癌变的社会与法律后果。
三、“伦理安全”与“精神援助”
问题的学理解释决不能代替现实解决。“贱民”问题的道德哲学与精神哲学解释的意义在于:(1)伦理的问题必须也只能首先伦理地解释和解决,在这个伦理难题不断涌现的时代,在这个需要伦理又稀缺伦理的时代,社会应当像上个世纪40年代罗素所预言的那样,学会伦理地思考,学者应当学会伦理地解释和解决具有深刻伦理内涵的那些问题;(2)“贱民”问题发出的学术信号和社会信号是:伦理问题到底如何癌变为严重的社会法律问题?它彻底动摇了以往那种把伦理问题只当作“精神文明”的“软问题”的看法,在这里,“软问题”成了彻头彻尾的“硬问题”和“大问题”;(3)它向社会,也向伦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个紧迫课题:如何防止由“卑贱意识”向“贱民”、由“贱民”向“暴民”的癌变?
问题解决的根本,当然是在精神上消除“卑贱意识”及其产生的客观基础——贫困,建立个体与国家权力和财富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不仅客观地存在这种同一性,而且在意识中精神地把握这种同一性关系,从而以“高贵意识”取代“卑贱意识”。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也是伦理学研究、道德哲学研究必须进行的学术和学科推进,即确立两大理念和概念:“伦理安全”、“精神援助”。
由于伦理是人的精神与社会生活最深刻的基础,由于当今中国文化仍然是伦理型文化;因此,伦理安全不仅理论上是一个社会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安全,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具基础性的安全②。一般说来,伦理安全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伦理安全,或者说,社会生活是否具有伦理安全感,其核心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状况,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相互帮助的可能性、人际交往中的危险度、公共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危机感,等等;二是个人的伦理安全感,即个人在居于其内的共同体中是否具有基本的伦理上的安全性和安全感,核心问题是:在所遭遇的共同体中,个人的“安身立命”是否具有最基本的伦理条件和伦理保障?显然,第二种意义上的伦理安全是“贱民”问题解释和解决的着力点,虽然它的后果是社会的伦理安全。
个人伦理安全的核心问题,是伦理上的被承认和被接纳。由于人的基本属性和精神家园是“伦理人”,“承认自己是人,并尊敬他人为人”的“法的命令”的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获得“伦理承认”,包括自我承认和社会承认。伦理承认的基本方面,是被某种——至少获得一种结构的伦理共同体或伦理实体接纳,由此获得伦理上的关怀和归宿。“伦理承认”的基本内容,是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社会关系体系中获得起码的平等和自尊,不被歧视和侵害;伦理承认的底线是:不为所有伦理共同体所抛弃,或者说不在伦理上“出局”,沦为所谓“伦理局外人”。其中,“伦理局外人”和“伦理出局”有精微而深刻的区别,因为“伦理局外人”可能是主动的,他们可能是伦理上的游离态或“伦理旁观者”,而“伦理出局”则是“被出局”或被清除出局,是怀着希望的绝望。伦理承认是“让人有活下去的希望”的底线,一旦“伦理出局”,社会的伦理实体就无疑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至此,“贱民”流为“暴民”就不可避免了。
根据以上阐释,如果将伦理的存在形态或所谓伦理场区分为“家庭、民族—国家权力、财富—德性主体”三个结构及其辩证体系,那么,家庭、国家权力和财富关系中的安全,或者说,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中的伦理安全便是解决“贱民”问题的现实关键。当今中国社会,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向市场经济原子式个人的“法权状态”过渡,但远未建立所谓“后单位制”。“单位制”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典型的也是中国式的“公众家庭”,一旦这个公众家庭解体,而市民社会这个“第二家庭”又未能建立,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便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成为缺乏归宿的游子,这就是当今社会生活水平提高而人们的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国家生活中大量而严重地存在的官员腐败与分配不公,使人们至少使那些弱势群体丧失了基本的伦理安全感甚至伦理上的希望。而社会激变导致的家庭伦理关系和家庭伦理实体的不稳定,又使人们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最后基地和精神避难所。于是,无论在家庭、还是市民社会、国家伦理实体中,伦理风险,伦理的不安全感,大量而深刻地存在。这种深刻的伦理风险与贫困的现实,与贫困的群体结合,极易滋生和培育“贱民”,准确地说,极易使“贫民”转化为“贱民”;而它一旦与那些具有暴力和暴虐倾向的人格结合,并遭遇某一爆发点,“贱民”便极易恶变为“暴民”。于是,校园暴力,乃至屠童之类的恶性事件便发生了。
伦理上安全,才能使贫困的人“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必须建立“国家—市民社会—家庭”的伦理安全体系。首先,完善国家作为伦理实体的本性,通过官员腐败与分配不公两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重建社会对于国家“普遍目的与个人福利同一”的信念和信心,也重建对国家的伦理信心和爱国政治情绪。其次,建立市民社会中的伦理共同体,使人们在经济博弈的同时有情感上的归宿,填补“单位制”的“公众家庭”解体之后的社会伦理真空。最后,最基本,也是最后的防线,是建立成熟的家庭伦理,保持家庭的基本稳定性与安全度,一旦在家庭中不安全,或者没有家庭的安全,人便在伦理上彻底地不安全,彻底地丧失伦理安全感了。
解决“贱民”问题必须消灭贫困,但消灭贫困并不就能根除“贱民”现象,因为“贱民”不仅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精神现象,是经济贫困、伦理贫困、精神贫困的综合体,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精神贫困或精神问题,在由“贫民”向“贱民”、由“贱民”向“暴民”异化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必须对其实施“精神援助”。“精神援助”之所以必须,还是因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伦理存在,只有转化为个体内在的伦理存在,即德性时,才可能能动地防止“贫民”向“贱民”、“贱民”向“暴民”的异化,因此,“道德援助”应当成为“精神援助”的重要内容乃至核心方面。“贫困的主观方面,以及一般说来,一切各类的匮乏——每个人在他一生的自然循环中都要遭遇到匮乏——的主观方面,要求同样一种主观的援助,无论其出于特殊情况或来自同情和爱都好。这里尽管有一切普遍的设施,道德仍然大有用场。”[3](243)道德之所以“大有用场”,“精神援助”之所以必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任何时候,贫困总是存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贫困有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两种,绝对贫困即便消灭,相对贫困总是难以消除,而相对贫困恰恰是产生精神问题和幸福感匮乏的重要土壤。“尽管财富过剩,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这就是说,它所占有的属于它所有的财产,如果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总是不够的。”[3](245)值得注意的是,“精神援助”决不只是一种教育,而是一种精神建设和“精神照顾”,包括“照顾他们嫌恶劳动的情绪”,即克服成为和可能成为贱民的那些恶习。其中一个重要课题是,社会如何透过精神与文化建设,帮助人们建立超越各种人生和人伦矛盾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地,就像传统社会中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进退互补、自给自足的精神基地一样。也许,只有这样的基地在人的精神中真正培育和建构起来,“贱民”和“暴民”问题才有可能主观地得到解决。
注释:
①这是本人率领的国家重大项目组经过几年调查的结果。
②根据我们进行的全国性大调查,伦理而不是法律途径仍是当今中国人建立和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首选,而且选择率远居法律手段之上,由此可以推断,中国文化仍然是伦理文化,或者说,伦理型文化的传统取向并没有根本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