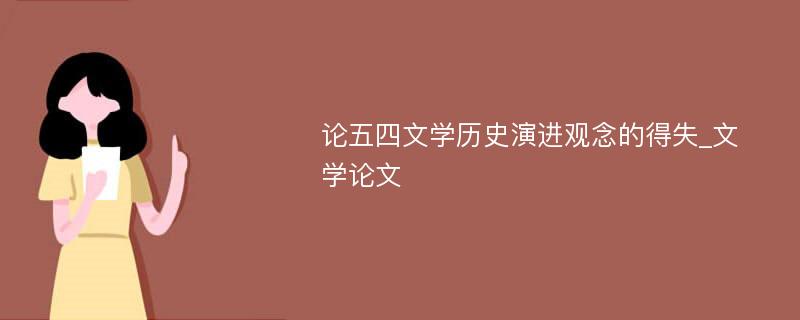
试论“五四”时期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的得与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观念论文,时期论文,得与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翻开一本本世纪文学史后面附的文学年表,你就会发现中西文学所呈现的不同风貌:即以波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而言,美国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宣布参战开始至1945年战争结束止,文学年表上列出的重要作品有福克纳的《去吧,摩西》(1942年),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1943年),贝娄的《挂起来的人》(1944年),斯泰因《我所目睹的战争》(1945年)以及赖特的《黑孩子》(1945年)等。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正在进行的战争与文学的直接关联。美国文学以二战为背景的作品大量出现,大概要在十年之后,文学自有其一条独立的发展路线。而在中国抗战文学年表上,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是抗战史的缩影,从1938年抗协成立不久就有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1940年有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同年有“战国策”派的出现及对“战国策”派的批判;1941年国民党成立“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提出“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1942年延安的文艺整风运动等等。文艺作品也绝大部分都取材于正在进行的抗战。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它与中国介入战争的深度广度有关,抗战是民族求生存的神圣的战争,作家作为民族的一员自觉地投身于战争,以笔为枪服务于抗战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情况与中国
一、“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的历史的文学观
五四新文学的首倡者首先给人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他们具有一种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使命感。他们的主张建立在一种把握住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先见之上,因此他们的要求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要求。波普曾这样说过:“历史决定论的倾向吸引着感到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尤其是感到应该干预人类事务并拒绝承认现有事态不可避免的那些人。”(注: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新文学的首倡者都是不满于已然的现实,而想创造一种新的合乎理想的现实的历史变革者,这就给他们的历史要求带上了一种反自然主义的主观意志色彩。胡适对旧文学的发难即源于一种“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的使命感。要完成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革命,胡适首先要做的论证是文学不能不“变”,所以他的文学进化观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讲“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而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由此可知胡适首先做的是将文学作“脱魅”处理,将文学视作是一种社会文化存在而非审美存在。这样将文学等同于历史之后,就去除了文学所具有的“人学”特性及所具有的“永恒”、“普遍”之类非时间性的审美特性,而得出文学随时代一同全盘进化的结论。而文学史不同于历史的特性就在于* 文学史等同于社会史,就会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受到忽视和伤害。其次,强调文学的时代特性,实际上也就是假设有一个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中心意识的存在,它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由某种内部原则来束扎成型。“这种单一的‘内在精神’制约着从道德、艺术、政治体制到哲学的全部形式;要不就是,社会的两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都由主导的经济模式所决定,不论它是封建领主和农奴构成的等级关系,还是正规的、由金钱买卖调节的自由商品交换制度。”(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4页。)文学只有表现出了这种蛛网式的社会联系就可以说它真实反映了这个时代。但这种单一的整体的时代精神在五四时期并不存在,文化领域和政治经济领域各行其事,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文化偏至”的道路,有着为政治经济原因所不能决定的它自己的发展方向。有的论著囿于社会决定论的模式,先罗列出一套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然后以此来图解范围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样一种凌驾于文学史之上的社会观念并不足以说明文学领域区别于其它领域的独特性。鲁迅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就不会有大艺术的产生。”(注: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文学创
胡适所讲的文学进化观念的第二层意思是“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步。”(注:胡适《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9、第50页。)他指出中国戏剧由歌舞一变而为戏优,再变而为杂戏,三变成为结构大致完成的元杂剧。韵文的进化图式为:“三百篇变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而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骚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注:胡适转引自《国故新知论》,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0页。)这样,依此类推,白话文就成为文学进化的最高阶级,白话文之前的文学就是“死的、笨的、无生气的”,只有新文学才是“活的文学运动”。显然这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因为并不存在同生物学上的物种相当的文学类型,而进化论正是以物种为其基础的。而且真正的“新”,必须是有历史、有渊源的“新”,不能割断文学创新与文学传统的关系。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倒也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僵化保守的积弊所提出的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如对已失去意义的文学“遗形物”的看法以及文学在某个阶段须依赖外来文学的刺激才能发展,都对新文学的建设起到了正面作用。总之,胡适是一位相信进化论的实证主义哲学家,他认为文学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研究文学的目的是通过它来研究社会,其方式是用社会历史的一般状态来实证文学。胡适的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研究,他研究《红楼梦》即是对曹雪芹的身世考证,而不涉及审美的评判。就他对《红楼梦》的私见,他认为《红》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里面“没有一个polt(结构)”。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带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的特点。他首先从语言、形式入手证明了白话文之取代文言文,新形式之取代旧形式的历史合理性。并且身体力行写出了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尝试集》的创作原则就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赤裸裸地表现出情感来”就行了,这从文学的审美观念上来说显然是一种退步。宋代的严羽早就说过:“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
如果说胡适代表的主要是一种启蒙时代的实用理性,那么陈独秀、李大钊等则代表着一种价值理性。他们持有一种乐观的社会进步信念,坚信理性的进步会给人带来幸福完美的生活。李大钊曾这样强调理性的重要:“以人的理性为求得真理的准则,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依其理性以改革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进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塞进步。”(注:《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陈独秀将文明历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将东西文化差异视为是时代的、历史的差异,根据进步原则判定“孰为新鲜活泼,孰为陈腐朽败”,因之提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急起直追以科学、人权并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见《新青年》,1卷4号,1915年12月15日。)的新文化主张。周作人、鲁迅则提出现代“人”的观念,认为五四首先要做的是“开辟人荒”。这种反传统的思想启蒙为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现代价值的原点,虽不无偏颇,但功不可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是应该完全肯定的。但从思想、学理的角度讲,都有时代的局限。特别是他们论证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方式,是将旧文学等同于专制意识形态,认为非对之进行全盘否定,不足以建立新文学。这就割断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传承关系* 种批评方式埋下了伏笔,到了三十年代,太阳社就有人出来宣告“阿Q的死亡”,是否是“前进作家”成为一个作家能否被文坛主流认可的标准。四十年代进而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我们虽对此不可无“了解之同情”,但也不能不指出它对文学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总之,文学既不是完全他律的,也不是完全自律的,自律和他律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单纯地强调某一方,往往不能正确地解释文学发展的规律。所以于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文本主义的观念来对前者的偏颇予以匡正。首先,历史主义地看待文学,往往过于强调了文学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决定性关系,它注重了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共性,忽视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个性。这就为庸俗社会学在文学领域的泛滥埋下了伏笔。“文学史”也是一种历史,但它天然地接近于“野史”,而不是“正史”,它对“正史”,往往取一种拾遗补阙,揭发伏藏,或质疑颠覆的态度。其次,文学的进化非如胡适所说那样直接简单,文学发展中有“变”也有不变,文学进化绝非是一个由鸡蛋变成鸡的直线上升过程。文学的演进除了社会文化因素之外,还有其自主的规律。决定文学发展的还有形式、技巧,话语结构等内在因素。第三,传统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之间还应该有一个人的心理结构的层面。人的心理结构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对于一切理论学说和行为方式具有能动的选择、重构作用,藉此避免一种潜在的危险即文学在要与整体信奉的社会意识保持一致的要求下失去抵抗力,没有个人的话语,只有时代的合唱。同样“自由也不尽是对必然的认识”,
过批判。总之,这种擂台式的文坛大概是西方不曾有的,它与中国具有的泛政治化的国情有关。文学写作在西方是一种自发的、个人的行为,作家也可能不无政治热情,不乏民族意识,但他会付诸行动,甚至喋血杀场,而不是“以笔代枪”,这大概与西方的文学传统及作家所持的个人化的文学观念有关。
二、来自反对者的不同的声音
新文学的首倡者坚信的社会进步观念首先来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所接受的进化论主要凭借于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译自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对之进行加工,发展成一种以人持天、救亡图存的适合中国需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这种加工表现为严复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则的偏爱和对人类进步主要表现为一种伦理进步的漠视之上,他批驳了适合中国需要的赫胥黎关于人的进化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未说,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而严复之所以不同意赫胥黎将人类进化过程视作是不同于自然界的伦理进化过程,而认同斯宾塞任天为治的社会进化论,是基于他所眼见耳闻、亲身经历的十九、二十世纪人类生存竞争的残酷现实。“强权即公理”,“贫弱就会受制于人”的“力本论”是人类生存的反道德的“厚黑学”,他于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看不到道德对此的制约,要生存,就只能投入这种残酷的竞争,在竞争中取胜的才配生存。这种学说对中国伦理本位的文化自然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唤起了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但其实际效果却并不单纯。据时人记载:“自十九世纪物竞天择说兴,而利己主义、强权主义、军国主义之相继迭起,于
这种乐观主义的社会进步论者在当时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冯友兰曾如是评说进化论:“生物学中之演化论谓天演竞争,适者生存,颇有人即以此之故,谓宇宙之物日在进步之中。中国近译演化为进化,愈滋误会。其实所谓演化,如所谓革命,乃指一种秩序变动,其所产生结果为进步亦可为退步,本不定也。且所谓适者,乃适于环境,然适于环境者未必即真好,不适于环境者未必即真不好,所谓‘阳春白雪’在庸俗者耳中,不能与‘下里巴人’争胜,然吾人不能因此即谓后者之果真优于前者。故吾人即以人的标准批评宇宙诸物之变动,亦未必有何证据能使吾人决其变动之必为进步的也。”“进化”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新的也并不天然地就高于旧的,未来也并不天然就胜过现在。进化论者所信奉的“时间神话”,及“创新崇拜”在当时即已受到质疑。抨击这种进步主义最为尖锐的是潘光旦,直言其所迷信的是一种“进步鬼”的东西。其时蔡元培、吴稚晖、蒋梦麟等先生在讨论“姓、婚姻和家庭的存废问题”,几乎都一致认为随着社会进步,这些东西都会“在五十年内”或更多时间内统统废除。社会学家潘光旦写了篇文章专门批驳其进化观念的陈腐。潘光旦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把社会演化当作一种完全自动的过程,似乎是完全超出人
五四新文化倡导者所提出的文学革命主张在当时就受到了来自不同文化立场的责难。这种反对的声音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林纾、辜鸿铭等人,都是为“旧文化所化之人”,以一种遗老的态度拼死卫道,对新文学及其代表的现代价值持彻底反对态度,这是一种趋于没落的声音。另一类如章士钊和《学衡》派的人物的情况就不太一样。章士钊从文化传承、新旧关系和文化运动这种大众参与方式三个方面对《新青年》的全盘西化、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和文学的平民化提出质疑,也能言之成理,道出了文化、文学演化的复杂性,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并不能靠“骂倒”了事。《学衡》派的观点与“文学革命”的理论就更构成一种互补性。首先《学衡》派对《新青年》所倡导的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是肯定的。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要求自由,致意于文化之普及藉促国民之自觉而推翻压倒国民之制度,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注:丁晓强《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转引自《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第2期。)。但“学衡派”的新文化观则建立在对西方近现代实证主义、浪漫主义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拨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立场之上,致力于捍卫阐发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永恒性的人文价值,这就与五四《新青年派》形成了对立的关* 在文学观念上,他们也倾向于视文学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反对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夫历代文学之流变,原仅一‘文学的时代发展’,安可胶执进化之说,牵强附会,谓为‘文学的历史进化’。质言之,文学之历史流变,非文学之递嬗进化,乃文学之推衍发展,非文学之器物的时代革新,乃文学之领土的随时广大。非文学为适应其时代环境,而新陈代谢,变化上进,乃文学之因缘其历史环境,而推陈出新,积厚外伸也。”(注:《潘光旦文集》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页。)这种观点显然较之文学进化论更能说明文学的一般发展规律。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形式演变的动力在于文学自身,“艺术作品是在和其它艺术作品的联系中并借助于这些作品的组合而被感觉的,不仅是模仿的作品,而是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和某种原型对照和对立而创造的,新的形式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新的内容,而是为了代替已经失去审美特质的旧形式。”他们认为文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打破陈旧的自动化了的不能引起人们的感受注意的旧形式的一个不断陌生化的过程。这种观点也有将文学发展简单化的倾向,特别是忽略了社会与文学发展之间的一种辩证的张力关系。但它强调文学发展自律的一面,可* 《学衡》派的“文化番达主义”(Vandalism)之忧,似也不无道理,并非只是“狼来了”的杞人之忧。所谓“文化番达主义”即一种文化毁灭主义,一种反智主义。“文化之亡,或由外力,或由内铄。”“文化之遭内铄迁古而其方向错误者,亦可以致亡,亦足以破灭固有之文化而无所利,其为弊类,初不逊于蛮族铁骑之凭陵扫荡。”(注:吴宓《白璧德之人文主义》,见《国故新知论》,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五四先驱者以“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将国粹与救亡绝对对立起来,这在“救亡”是第一义的时代,是一种清醒的务实主义态度,但从长远的文化建设而言是不利的。“保人还是保文化(国粹)”之构成如此尖锐的冲突,是与本世纪初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系的,无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冷酷现实,中国无以自存,但自存是否要以捐弃否定全部固有文化为代价则是值得商榷的,这也是当时政治民族主义同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所在。关键在于这种二元对立是不是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是不是人在面临这个问题时都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会导致“非此即彼”的结果?五四先驱者将思想文化的变革视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的思路,使他们强化了这种二元对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更激烈地冲突还在于文言和白话之争,一方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注: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散文·诗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一方则将废文言而取白话,甚至将汉字拉丁化的做法斥为“丧心病狂”。这种对立显然也带有整体主义独断论色彩。完全用白话作诗的诗人很快就感觉到了这种白话工具本身的“笨拙”(俞平伯),而新文学的大家们也没有苛求自己完全用白话写作。至于汉字拉丁化的问题,则要听专家的意见,语言心理学家的一篇《汉字易学、易记证》的论文也许比思想家、文学家们的诸多言论都要来得实在和有说服力。
总之,在新文学即将走完它的百年历程的今天,我们对当初对立双方的争执都应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一元价值观向人们许诺只要实现了某种价值,其它价值也就迟早都会实现,它相信所有美好的价值都是能够统一的。而价值多元论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许诺人们能够并行不悖地同时实现多个价值,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多种价值之间的彼此冲突、相互抵牾、难以调和,因此实现某一价值几乎总是会有损于其它价值,而并非带动促进其它价值。因此价值一元论虽因提出了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使人们一开始感到希望,但最终会失望;价值多元论虽让人一开始就感到扫兴和失望,但它也让人摆脱了整体主义的乌托邦迷妄,以务实的态度来逐步解决诸多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为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艾恺的一句话对我们大概不无启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它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思潮的冲突,将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未来。”(注:艾恺(美)《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引自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卷,1997年版第4期。)
标签:文学论文; 胡适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新青年论文; 读书论文; 学衡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