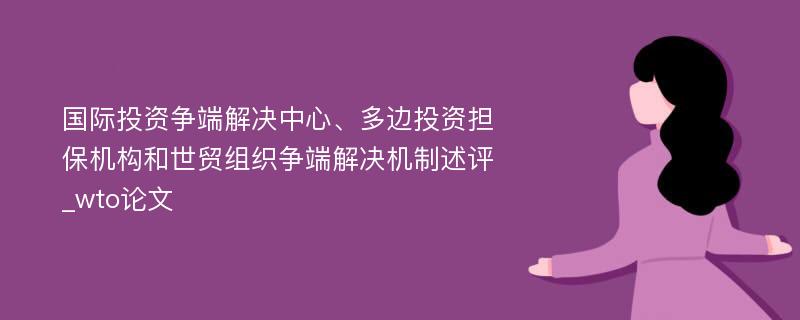
ICSID、MIGA、WTO争端解决机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争端论文,机制论文,ICSID论文,MIGA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4)04-0049-03
良好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的构建不仅仅是一国改善其国内投资条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也是国际经济法良性发展及国际投资解决机制步入法治的重要保证。对于此,在整个国际投资法律机制发展的进程中,人们已作了诸多的努力,以探求各种可行的法律方法,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二类:其一是当事人之间自己解决的方法,即协商或谈判方法;其二是当事人求助第三者解决的方法,这包括调解、司法诉讼、仲裁及外交保护等。然而,实践证明,由于国际投资争端的特殊性,上述有些方法若不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解决,或者说若在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及其他相关国家之间缔结一些具有严格约束性的国际条约,争端解决的结果可能并不尽人意。对于此,在国际上,已开发出了一些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机制,在WTO成立以前,这主要表现在1965年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ICSID)及1988年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MIGA)。后来,在WTO成立后,伴随着《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协议》,WTO解决机制已开始渗入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机制中,这无疑是国际投资法发展进程中一个实质性的飞越,然而如何客观且公正地看待其实然性效应及其与上述二争端解决法律机制之间的协调问题,对于该机制的运用及对国际投资法的发展亦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ICSID公约所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
1965年,为了使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非政治化,在国际上达成了ICSID公约,公约设立了“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中心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主要有二种,即调解与仲裁。笔者认为,ICSID所确立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中心对管辖权的规定;其二是中心的排他管辖性;其三是中心在适用法律上所体现出的特点。以下对此进行必要的分析:
就管辖而言,公约第25条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定:一是主体要件,据公约的规定,争议当事人一方必须是缔约国国家或缔约国指派到中心的该国任何组成部分或机构,他方必须是另一缔约国国民,这一概念不仅包括具有另一缔约国国籍的自然人或法人,且还包括具有争端一方缔约国国籍而为外国人控制的法人,然而对于这一方当事人,为了公约之目的,还需要双方事先进行约定。[1]二是主观要件,对于在公约缔约国之间所产生的投资争端并不因为双方是公约的缔约国就必然地接受中心的管辖,双方当事人还必须书面达成将争议提交中心管辖的意思一致性,同意一经作出,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予以撤销。三是客观要件,投资争议必须是直接产生于投资的法律争议,“投资”既包括传统类型的资本投资,也包括各种现代类型的非资本出资形式的投资,如服务合同与技术转让等。此外,“法律争议”是指在中心管辖范围内的权利冲突,纯粹的利益冲突则不属于法律争议。争议必须与法律权利或义务的范围有关,或者与违反法律义务而引起的赔偿性质或范围有关。
就中心管辖的排他性而言,这主要体现在公约26条对东道国当地救济的排他性及第27条对投资者本国外交保护权的排他性。公约第26条规定,除非另有约定,双方同意提交中心管辖的仲裁案件,不得再提交其他任何程序解决,而其他任何机构也不应受理。然而,争议缔约国一方可以要求把首先用尽当地各种行政或司法补救办法,作为其同意提交中心仲裁的一个条件。第27条规定,对于双方已同意或提交中心仲裁的争议,投资者本国不得行使外交保护权或提出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要求,除非争议的国家一方未能遵守和履行对此项争议所作出的裁决。
中心仲裁所应适用的法律。公约第42条对中心仲裁所适用的法律也作出规定,其具体规则如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未选择法律的补救规则、禁止拒绝裁决的原则及公平与善意的原则。实际上,中心在法律适用上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第二个层面上,即未选择法律的补救规则上,据该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如无此协议,法庭应适用争端缔约国的法律,这包括关于冲突法的规则,及可以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总结学者们的探讨,其优越之处有二:一是在当事人缺少对适用法律选择的情况下,它可以避免一般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有助于使当事人预先知晓法庭所应适用的法律规则,因此可以达到鼓励当事人积极利用中心的效果;二是这种规定在适用东道国法律与适用国际法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协调,从而在实质上避免了投资争端解决的政治化问题。
评:客观而言,对于ICSID所创立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应从积极与消极效应二个层面进行客观的分析。就积极方面来说,笔者认为由于公约毕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问题在相互协调与妥协基础上第一次所作的比较成功的尝试,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国家的主张与利益,同时从中心的管辖权等来分析,它所规定的解决方法具有自愿性、有效性与灵活性等特点。比如,公约对东道国当地救济的相对排斥性及对投资者母国外交保护权的绝对排它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就法庭在适用法律上所作的安排来说,笔者以为,它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比如从所能适用的法律排列顺序上来看,其首选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这一安排已充分说明了投资争端本身性质的特殊性,也间接地说明了投资契约从其性质而言是属于私人之间的契约,而非所谓的“国家契约”。再者,对东道国法律与国际法在适用选择上所作的规则也不能说不是个创新,固然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它至少在一定层面上解决了东道国法律与国际法在适用上的冲突问题。因此,ICSID公约所缔造的中心自其诞生时起,它所确立的投资争端解决法律制度已使传统的国际投资法在争端解决方面发生了从量到质的转变。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际投资争端法治化的到来。固守卡尔沃主义的拉美国家对公约态度的转变就是对中心所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之效应的一个有力回应。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中心所确立的解决机制也并非完善的,它也存在一些漏洞,这无疑使其实际效应大打折扣。其一,笔者认为公约的规定弹性条款太多,如对于产生的投资法律争议问题公约并没有作出明文的规定,目前所作的界定也只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其次,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所适用法律的情况下,公约也并没有解决东道国法律和国际法在适用上何者优先的问题,这种真空的存在无疑使投资争议的当事人对争端所将适用的法律不能产生合理的预期。此外,该条款也没有较好地解决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矛盾;其二,公约第52条关于撤销措施的规定更是令人对中心争端解决机制的实然性结果产生疑问。如该条规定,当事人任何一方可以基于下列一个或几个理由,向中心秘书长提出申请,要求撤销裁决:法庭组成不当、法庭显然超越其权力、有严重违背基本程序规则的情况、法庭成员有受贿行为及裁决未陈述其依据的理由。实际上,该条款在具体的案例中也得到广泛的利用,如从公约生效至1992年为止,中心产生了13个裁决,在这些裁决中,撤销措施便被使用了6次。[2]难怪有诸多学者认为,这些撤销决定给了中心仲裁致命的一击,没有人会再拟定中心仲裁的条款,因为中心裁决是如此地缺乏终局性,当事人将会被中心冗长且耗资巨大的程序击退,即使再次诉诸中心也是冒险,因为这也许又是一次徒劳。[3]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心这个可行与有用的争端解决机制正在变成一个“鸡肋”,因为它的控制体制已失去了控制。
二、MIGA所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
1988年成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也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以前的争端解决法律制度相比,它也有些闪光之处,作者认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在承保的险种上,机构将违约险作为一个独立的险别来加以承保,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创新。二是关于合格投资者的国籍的规定,公约也显得颇有特色,如对于自然人来说,合格的投资者必须是东道国以外的会员国国民。对于法人来说,则须在东道国以外的成员国境内组成并且其主要营业地位于该国境内,即兼采了成立地和主要营业地的复合标准,若不符合这一标准,则采取资本控制标准,即多数资本为东道国以外的会员国国民所拥有,该法人才能成为合格投资者。[4]机构关于合格投资者的另一大特点是有资格取得担保的法人不必限于归私人所有,而只要其在商业基础经营就可以了,这种处理方式就将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大多不予承保的非私人性质企业包括在内,这无疑在扩大了机构的承保主体的同时,也增加了机构在处理投资争议时的受案范围。三是MIGA机制在争端解决方式上的特色,公约针对不同的情形为四种类型的争议设立了解决程序,这主要表现在公约第56-58条中。对此四种争议可表述如下:
其一是机构与其成员之间或机构成员国之间因对公约的解释与适用等所产生的争议,对于该种争议应提交机构董事会裁决,如成员国对裁决结果不服,则可将争议提交机构理事会作出终局性的裁决。
其二是机构与担保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合同履行而产生的争议,对于此种争议应将其提交仲载,并依据合同中的规定及提及的规则进行终局性的裁决。
其三是机构作为投资者之代位求偿人同其成员国东道国因为代位求偿权的实现所发生之争端。对于此种争端,应按照公约附件二中所规定的程序或机构与相关成员国所达成的协议条款予以解决。
其四是对于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形的争端,或机构和前成员国之间的所有争议,应按公约附件二规定的程序来解决。
评:如何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问题一直是国际投资法领域中的一个让人棘手的难题。然而,作为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法律制度的一次创新,MIGA及其所创建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意义是深远的。作者认为,从表面来看似乎公约并没有就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解决问题作出直接的规定,但是从实质上来分析该种机制以机构的代位求偿权为枢纽而在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之间就争端友好解决事项造就了一种缓冲机制,这种机制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原则上将投资者同东道国之间的求偿关系及解决程序分解为二种相对独立的求偿关系及解决程序,即以机构为中心,一方面是其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及解决程序,另一方面是其同东道国之间的求偿关系及解决程序。这种分解式的争端处理方式固然是对东道国国家主权的一种制约,因为它将其与投资者之间的争议上升到了国际法的高度,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的是这种高度的上升是以东道国的意向为基础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东道国主权的表现。这无疑是对传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在理念上的一种突破。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定及程序谅解》确立了一套较为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这种争端解决机制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程序方面,这种争端解决机制在程序方面由六个部分组成,即强制性的双边协商;选择性的调停、斡旋及仲裁;公正独立的专家小组程序;上诉审查程序;争端解决机构的接受或批准及受监控和管制的制裁程序。[5]
其二是在适用范围上,该法律文件效力主要表现在对物适用、对时效适用及对人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就对物之适用范围来说,在不损害特别或另外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前提下,《关于争端解决规定及程序谅解》适用于与WTO体系所有法律文件相关的任何争端,如谅解书第1条第1款便规定:“本谅解的各项规则及程序应适用于根据本谅解附件一所列的各协定的协商和争端解决条款所提起的各项争端。这些协定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货物贸易多边协定》、《服务贸易协定》、《民用航空器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谅解》、《政府采购协定》及《货物贸易多边协定》等。另外,就所涉争端而言,其包括违法之诉与非违法之诉;在时效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只适用于《WTO协定》生效后世界贸易成员国之间因适用上述国际法律文件所发生的争端。如《关于争端解决规定及程序谅解》第3条第11款规定,本谅解只应适用于在世界贸易组织生效之日或之后根据适用协定协商条款提出的新的协商请求。关于在WTO协定生效前根据1947年关贸总协定或其他任何适用协定的前身协定所作出的协商要求的争端,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前直接有效的,有关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应继续适用;在对人的效力方面,《关于争端解决规定及程序谅解》主要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相互之间因解释和适用上述国际法律文件所产生的各种争端。此外,在原则上,世界组织成员国与其成员国之间因解释与适用上述法律文件所产生的争端亦应依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定及程序谅解》加以解决。同时,谅解文件第24条第1款也对不发达国家规定了一些特殊规则,如其规定在确定与不发达国家有关的某项争端的原因及争端解决程序的所有阶段,应对不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给予特别考虑。
其三是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性质而言,作者认为这种机制是一种新型的、独特的国际经济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从其属性来说,它既非全司法性的,又非全政治性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反其呈现出的是一种司法性与政治性相兼容的特色。
评:虽然WTO并非以国际投资法律问题为主要目的,然而其对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法律问题等的规定这一做法,已使WTO间接地切入到了国际投资法领域,与此相关的争端解决问题也必将被纳入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在一定层面上来说,这是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因为它已在实然上突破了传统国际投资法的空间。同时,由于WTO协定在本质上还有一个不同于其它国际公约的特点,那就是定期与不定期的多边贸易谈判不时地使WTO法律体系处于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这一特点肯定也会带动国际投资法在该区域的发展。此外,尽管WTO争端解决机制具有“二条脚走路”色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司法解决方式在投资争议解决中的作用日益得到加强。如就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而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已开始迫使几乎所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一体化组织如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为不断强化其争端解决机制,使之法律化与法院化。[6]对于这一特性,有的学者将其形容为“国际法的硬法化”。如赵维田先生就认为,乌拉圭回合之谈判正是基于国际法的硬法化趋势,努力从各个方面用法律统制全局,加之穿上和国内法相同的甲胄,以求彻底洗去“弱法”的阴影。其关键在于强化执法司法机制,同时收紧各种例外,尤其是“免除义务”这个大口子。[7]其次是与贸易相关的投资争端为一种较特殊性的争议,就目前的国际法制而言,世界各国还没有找到较好的解决方法,其主要障碍在于难以制定一个对一国投资立法权进行限制的造法性国际公约,然而WTO法律规则体系则采取了TRIMS协议、TRIPS协议及GATS协议等方式切入了国际投资法领域,这无疑意味着一些全新性的多边国际投资实体法规则的创立,它为逐步废除某些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具有比较明显的扭曲作用的投资立法与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实体法依据,也为投资者或贸易商人借助WTO途径对其遭受的损害进行补救提供了强有力的程序法规则。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对该争端解决机制有个客观的认识,因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主要是借助WTO的实体法规则发挥作用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说,WTO体制对投资立法与投资政策的影响还是有限度的,其主要集中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补贴与反补贴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及国民待遇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所以从实质上来分析,WTO规则并没有广泛地涉及到投资问题,且其这种切入式的方法也具有迂回的特点,所以其范围也是有限的。再者,尽管正如同有些学者曾言,WTO争端解决机制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司法色彩的外衣,但是这些革新并不能全部改变WTO规则作为一种国际法规则的“软法性”特点。因此,若从这一方面来探讨,作者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效用的发挥在实质上还是摆脱不了以“政治解决模式”为核心的框框。
收稿日期:2004-03-20
标签:wto论文; 法律论文; 投资论文;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国际法论文; wto争端解决机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