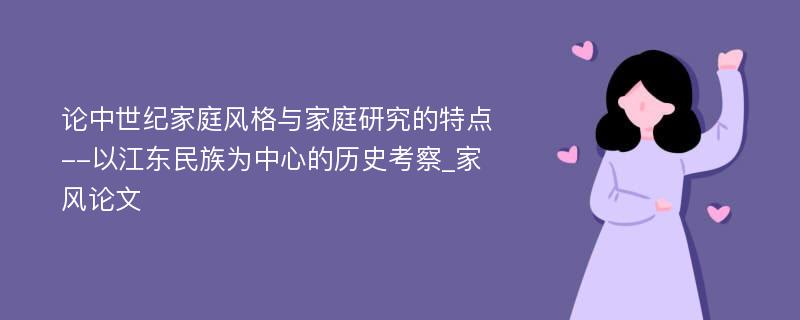
论中古时期世族家风、家学之特质——以江东世族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族论文,家风论文,中古论文,特质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4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910(2003)03-0010-08
一、文化:认识中古世族的一个重要视角
世家大族的兴起和衰落是中古时期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决定当时历史发展变化的主导因素之一。长期以来,海内外的前贤时哲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多从世族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来考察其特质,因而在门阀政治及其相关制度、田庄经济及其生产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难计其数,其中出现了不少重复或雷同性的研究。
不可否认,政治上的权势垄断与经济上的大土地私人占有确是中古世族的本质特征,从这一角度探究门阀世族的兴衰,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世族门第的形成并非仅仅由经济因素决定,还有其他因素;并非所有豪横乡曲的“土豪”都能成为“士族”,要实现由豪强向士族的转变,一个必具的因素便是文化。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士族形成问题时指出:“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在多数情形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这从两汉公私学校之发达的情形,以及当时邹鲁所流行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谚语,可以推想得之。”[1](P222)可见从汉代起豪强要转化为“士族”,即所谓“文化世族”,必须走通经入仕的道路。以江东世族为例,如吴兴沈氏虽素来“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2](《宋书·自叙》)但晋、宋间并无人认为沈氏是高级世族,其门第未显,比之顾、陆等江东传统世族,其差异主要在文化方面。然而,当晋末沈氏卷入孙恩之乱而惨遭家祸以后,沈道虔、沈麟士等沈氏文士隐居乡里,潜心学业,教授子弟,从而改变了其家族风尚,推动沈氏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齐、梁间沈氏便成为人才辈出的文化世族,社会地位大为提高。
特别是在士族社会地位形成后,文化往往成为士族门第的主要标志,以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其重要性更加突出。各世家大族要想保持门第兴盛,世代承传,必须加强对其子弟的文化教育,培养其德行和才干。孙吴时陆逊便说:“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而陆逊本人虽出将入相,权倾一时,但他并不重财富积累,死时“家无余财”,[3](《三国志·陆逊传》)但陆氏子孙皆凭借才、德,扭转危局,重振家族之权势地位。此例可谓典型。
一般说来,中古时代,那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家族尽管暂时遇到挫折,但其代有才人,家道不堕,而有些权势之家尽管豪横一时,但文化基础不深厚,一旦在政治上失势,则门第急剧中衰。钱穆先生对此有深切的体悟,他曾指出:“今人论此一时代之门第,大都只看其在政治上之特种优势,在经济上之特种凭藉,而未能注意及于当时门第中人之生活实况,及其内心想象。因此所见浅薄,无以抉发一时代之共同精神所在。今所谓门第中人者,……为此门第之所赖以维系而久在者,则必在上有贤父兄,在下有贤子弟,若此二者俱无,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盈,岂可支持此门第几百年而不弊不败?”[4]确实,历史上因缘际会、乘时而起的权势豪门可谓多矣,但大多都难免旋生旋灭的命运。而中古世族多能传承十数代,绵延数百年,这其中一定还有“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盈”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一因素主要便是家族文化。
另外,还必须指出,中古时代,由于世局动荡,文化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统一时代,学术文化的中心往往在王朝的都城,与政治中心一致。但汉末以后,除西晋有过短暂统一之外,南北分裂,东西对峙,华夏文化传续于世家大族之中,可以说每一个世家大族就是一个学术文化的重镇或堡垒。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有论云:“盖有自东汉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5](P131)学术文化的“地方化”、“家门化”,是中古时代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点,要真正了解当时之社会文化现象,必须从研究世族文化入手,否则,很难把握其特质。对此,钱穆先生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文中通过详实的考论后,有一段精辟的总结:“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其相互间种种复杂错综之关系,实当就当时门第背景为中心而贯串说之,始可获得其实情与真相,……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一分之功绩。”钱穆先生的有关研究和议论,是对陈寅恪先生上述论点的发挥。他指出,只有将当时学术文化与世族门第结合,“始可获得其实情与真相”,一语中的。因此,从文化的视角剖析中古世家大族,应该说是世族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不过,中古世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在思想文化上当然有其共通的特性和价值取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古世族又是一个包容性很丰富的概念,具体情况十分复杂。如以世族门第形成先后论,便有所谓“旧出门户”、“新出门户”的分别。世族阶层中具体家族的地位升降是不断发生着的,新、旧家族的社会地位、心理状态、文化传统都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将魏晋时期形成的世族与汉代旧门相比,魏晋“新出门户”便明显表现出儒、玄并综的文化面貌,而与汉儒恪守经学不同。这种差异反映在思想、行为等各个方面。如果按照世族门第高下分别,又有高级士族与次等士族的差异,其间的文化取向也颇为不同。按照地域划分,则有来自中土的侨姓世族、江东土著世族、关陇世族、山东世族等等地域世族群体的概念。不同的地域有各自的文化传统,这也就造成了各地域世族群体的文化差异。在准确把握和体认世族文化普遍特点的情况下,进一步分析其中的种种特殊性,从而全面了解世族文化的“实情与真相”,要求我们深入剖析具体家族的文化传统。就当时世族精神文化传统而言,主要表现形式为其家风与家学。
二、以儒家学说为基调的世族“家风”
中古世族文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家风与家学。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曾指出:“所属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钱穆先生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文中也曾指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由此可见,家风与家学不仅是世族文化的主要表征,而且还发挥维系家族传衍的功用。
何谓“家风”?一般说来,家风就是世族精神文化传统。一种精神或行为方式在某一宗族内延续三代以上,便可视为某一家族之文化传统,构成其家风。家风是世族文化的基调和底色,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世代相承。家风的承传主要有赖于家教。披览中古时期的相关历史文化典籍,载有大量的当时世族之家诫、家训、门律、门范、素范;世族掌门人物辞世,往往留有遗言、遗令,同样是家族的规范,用以教子弟、诫传人。南北朝之末有集大成式的《颜氏家训》一书,可谓中古家族教育的经典。为了向子孙传递家族文化精神,各世族又修撰“家谱”、“家传”、“家录”以及以辞赋等形式写作的“祖德颂”之类的纪念文字(又有诔、赞等文体)。王伊同先生在《五朝门第》第七章《高门之风范》中专设“家教”一节,他在详引各世族训诫之言后指出:“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处事,有以见异”,“巨宗重臣,咸有训诫”。
中古世族往往传承十数代,绵延数百年,房支众多,如果没有一套宗族戒律或规范,那是很难维护宗族和睦的。从当时家训的总体情况看,其共同的特征是培养世族子弟“能具孝友之内行”。这便决定了世族社会家教的核心内容是儒家道德规范。过去有一种肤浅的看法,以为中古玄学思潮带来了人性的解放,摧垮了汉代的礼法传统。毋庸讳言,《世说新语·任诞篇》所记述的魏晋名士的种种放荡行为确也是事实,但这并非当时世族文化的主流。钱穆先生曾指出:“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6](P309)这便指出了世族家教之内容“皆从两汉儒学传来”。余英时先生辨析中古士风指出:“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者也。”他认为当时所谓儒学衰微,主要是指“经国之儒学乃失其社会文化之效用”,士人之“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7](P398-399)这说明魏晋玄风并未能改变当时以儒学齐家的社会状况。
世族人物为延续宗族的精神传统,维系宗族内的和睦友善,特别重视孝义之道,使之成为当时最根本的道德观念。《晋书》卷八八《孝友传序》称:“大矣哉,孝之为德也。……用之于国,动天地而降休征;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虽百六之灾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犹为继踵。”晋代之重视孝道于此可见。南北朝历代正史皆设有《孝义传》、《孝行传》。另据《隋书·经籍志》,可见自晋至梁,又有《孝子传》8家96卷。由于朝廷提倡,世族力行,孝义之风播及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为了教育世族子弟,当时尤重《孝经》,南齐王俭便直言“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8](《南齐书·陆澄传》)(注:在重视孝道的风气下,《孝经》研究成为显学之一。查《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可见,著录当时《孝经》之注疏有18部,合63卷;亡佚59部,114卷。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又考得11部。甚至连僧人也注疏《孝经》。据《宋书》卷九七《夷蛮传》,僧人慧琳“有才章,兼外内之学”,深得宋文帝宠信,“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注《孝经》及《庄子·逍遥篇》等。慧琳注《孝经》等,主要是迎合世俗社会的文化倾向。)通观当时史籍,可见各世族无不刻意讲求孝行实践,即使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这样玄化甚深的侨姓世族代表,其子弟依然以孝友传家。清人李慈铭对此颇有感触,他在《越缦堂读书记》有关《南史》的一条札记中说:“王、谢子弟,浮华矜躁,服用奢淫,而能仍世贵显者,盖其门风孝友,有过他氏,马粪乌衣,自相师友,家庭之际,雍睦可亲。谢密、王微,尤为眉目,三代两汉,如两人者,亦不多得,读其佳传,为之叹想。”确实,就宗族孝道而言,魏晋南北朝绝不逊色于两汉。就江东世族的情况看,前文所考诸家,无一不重视孝义,顾、陆、虞、贺等传统儒学世家自不待言。即便是玄化较深的吴郡张氏、后起的吴兴沈氏,在孝行方面的表现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其实例罗列已详,此不赘言。(注:北朝的情况也如此,隋朝重臣苏威为苏绰之子,他曾对隋文帝说:“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何用多为!”可见北方世族对《孝经》与孝行的重视。)
由于中古世族倡导孝道,导致了当时社会道德观念的某些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忠、孝关系的倒错。依照儒家传统的学说,忠、孝是一组对立统一、互为补充的观念,但东汉后期思想界的名理之辩造成了忠、孝概念的逐渐分离。特别是入晋后,随着世族门阀制度的形成,世族社会家族本位意识进一步增强,士人忠节观念淡化,对国家易姓多坦然处之,与世浮沉。《南齐书》卷二三传论说:“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一七“六朝忠臣无殉节”条中指出,当时士人“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已,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他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二“江左世族元功臣”条中又指出:“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履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赵瓯北指斥六朝世族不能殉节虽不免苛求,但所言其“与时推迁”,则为不争的事实。确实,六朝世族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恪守先亲后君、孝重于忠的观念。对此,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一文中指出:“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正是这种新的忠孝观念给世族人物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唐先生又指出:“后世往往不满于五朝士大夫那种对于王室兴亡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在门阀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而与王室的恩典无关,加上自晋以来所提倡的孝行足以掩护其行为,因此他们对于王朝兴废的漠视是必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9](P238,247)比之既往的道德苛责,唐长孺先生的分析要冷静得多,他的结论验证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句名言。
以上所述乃世族社会家教、家风之共同特征。不过,也应看到各世族之家风也有其个性特点。以往论者对世族社会风尚的“共相”,即带有普遍性的风气关注较多,而对其“殊相”,即各族家风的独特性注意不够。但实际上,由于各族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家风差异是难免的。检核有关史籍,这样的记载非止一二例。《世说新语·方正》:“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庾顗不以王衍之作派为意,“我自用我法”。此事发生在西晋。同书《品藻》载:“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殷浩不与桓温相竞,“宁作我”。此事发生在东晋。这两例所说虽皆指个人,但实际上表明两个宗族的家风不同。最典型的恐怕要算王、谢家风之别了,《世说新语·贤嫒》载:“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谢道韫与王凝之结婚,道韫“大薄凝之”、“意大不说”,其根源在王、谢家风不同。甚至同一宗族的不同房支,其家教并非完全一致。对世族家风的差异,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喏,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可自知。昔在江南,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不劳翰墨。汝曹生于戎马之间,视听之所不晓,故聊记录,以传示子孙。”由颜之推所述,可见所谓“士大夫风操”“家门颇有不同”,这是对儒家礼法理解不同,“自为节度,相承行之”造成的。当然,这种差异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本质的分别。
就江东世族的情况看,以吴“四姓”为例,他们虽然都是兴自汉代的儒学旧族,但在共同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情况下,汉晋间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门风,《世说新语·赏誉》所谓“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是也。其他如吴兴沈氏,会稽虞、贺、孔诸姓,其门风也各有特点。有论者指出,上述有关吴“四姓”的品目仅限于孙吴,东晋南朝便不适用了。确实,孙吴灭亡后,吴“四姓”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其“旧目”便丧失了凭藉。但我们也应看到,任何一种家族文化精神都不会因为家势的变迁而汰除殆尽,相反,它作为一种家族文化潜在的“因子”,像血液一样在家族间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制约着世族子弟的言行。正因为如此,东晋南朝时期我们仍然能辨明吴姓世族旧风的余绪,有的甚至进入隋唐遗风犹存。
另外,有一点必须指出,江东世族作为一个区域群体,在门风上与侨姓世族有别。比如东晋南朝时代虽然江东世族同样与时推迁,以家族利益为本位,但与侨姓世族则有所不同,江东人士则显得较为忠直,如吴郡陆氏、会稽虞氏、孔氏等皆有“奉公尽诚”的事迹。他们的家族教育虽重孝道,但仍不忘忠义,《晋书·列女传》便记载虞潭母对潭自幼“便训以忠义”,常教导潭“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虞氏如此,顾、陆、孔诸姓也莫不如此。即便是南朝时期玄化甚深的吴郡张氏,在东晋时也有张祎列入《晋书·忠义传》,他宁愿饮药自裁,而不愿为刘裕谋害晋恭帝。另外,相对于侨姓世族而言,江东世族普遍“谙练故实”,重视吏能。这样的具体事例尚有不少,表明自汉末、孙吴以降,江东世族的忠义之风遗绪尚存。
三、以礼学为核心兼容并蓄的世族“家学”
如果说家风主要侧重于对世族子弟的精神品格的塑造,那么家学则主要侧重于对世族子弟学术艺能的培养,两者相辅相承。就家学而言,世族社会既有其共同的学术文化习尚,即所谓“共相”,诸世族也各有特色,即所谓“殊相”。中古世族之家学,就其传授方式而言,与两汉经学有一定的联系。汉代经学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传授的,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昌明时代》中指出:“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在《经学极盛时代》中又说:“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汉时不修家法之戒,盖极严矣。”在重“师法”、“家法”的学术传授方式下,出现了一些经学世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累世经学”条有言:“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并列举了主要的经学世家。实际上,在汉代通经入仕的选举制度下,世族多重习经,以期提升家族门望,久而久之,各族便形成了家学传统。
世族家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儒家之礼学,目的依然是为了敦睦宗族,延续家世。《颜氏家训·勉学》说:“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可见世族子弟自幼便习礼。《朱子语类》卷八四“《礼》四”总论有云:“诸儒议礼颇有好处,……六朝人多精于此。毕竟当时此学自专门名家,朝廷有礼事,便用此等人议之。”同书“《礼》一”“论考礼纲领”条又云:“南北朝是甚时节,而士大夫间礼学不废。有考礼者,说得亦自好。”近代学者章太炎在《五朝学》中指出:“江左之士,蠢迪检柙,丧纪、祭祀、婚姻之式,少有疑殆,虽文士沙门犹质之,载在《通典》,岂可诬哉(据《南史·何承天传》: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各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又《徐勉传》:受诏知撰五礼,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然则《通典》所载,二十分之一耳)?”钱穆先生据《隋书·经籍志》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共有《礼》学著作136部,1622卷;亡佚221部,2186卷。钱先生又统计了此期其他经典的著述数量,指出:“若以著作数量作为当时对经学中某一部分重视与否之衡量标准,则此时代之经学最重《礼》,次《春秋》,《易》居第三位。”[4]难怪《朱子语类》卷八六载朱熹之言曰:“《五经》中,《周礼疏》最好,《诗》与《礼记》次之,《书》与《易》疏乱道。”当时《礼》学著作量大质高,正是世族社会普遍重视的结果。
东晋南朝之《礼》学最重《丧服》。《丧服》本为《仪礼》中的一篇,汉晋之际受到特别的重视。西晋挚虞以为此篇“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丧服》一卷,卷不盈握,而争说纷然”。[10](《晋书·礼志序》)究其原因,正与世族的兴起与门阀制度的形成有关,因为宗族中的亲疏远近有赖于丧服制度加以区别。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三中有论云:“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他在详述相关史实及历代评论后指出:“六朝尚清言、习浮华之世,讲论服制,如此谨严。所以其时期功去官,犹遵古礼;除服宴客,致罣弹章,足见江左立国,犹知明伦理,重本原,故能以东南一隅,抗衡中国百余年。”章太炎《经学略说》中也一再谈到这一现象:“《丧服》一篇,自汉末以至六朝,讲究精密,《通典》录其议论,多至二三十卷”;“六朝人天性独厚,守礼最笃,其视君臣之义,不若父子之恩,讲论《丧服》,多有精义”;“南朝二百七十余年,国势虽不盛强,而维持人纪,为功特多。《丧服》一篇,师儒无不悉心探讨,以是团体固结,虽陵夷而不至澌灭。……今讲《仪礼》,自以《丧服》为最要。”[11](P105-107)由此,可见《丧服经》的研究在当时的盛况。由于《丧服》之注疏成为当时显学,甚至僧人也讲论《丧服》。(注: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曾讲《丧服》,雷次宗等曾从之受学。《宋书》卷九三《隐逸传》载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尤明《三礼》,后曾入京师讲《丧服》。又据《高僧传》卷第六《义解三》载慧远“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远兴学庐山,宗炳、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等皆与之游,“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预学徒,莫不依拟。时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后别著义疏,首称雷氏,宗炳因寄书嘲之曰:‘昔与足下共于释和上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类非一。”由此,雷次宗之《丧服义疏》得之慧远明矣。检核《高僧传》等典籍,尚有多例,不俱引。)
另外,在礼制中世族人物特重朝仪典章,这是他们为官入仕的重要条件,关系到门第的兴衰。如琅邪王氏世代蝉联,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王氏子弟“练悉朝仪”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王导一脉为王氏显支,其子孙皆精擅典制,如导曾孙王弘“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2](《宋书·王弘传》)宋、齐间的王俭尤以精通礼仪著名。王彪之一支也如此,《宋书·王准之传》载“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准之仕于元嘉中,“究识旧仪,问无不对”,以致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准之所撰《仪注》,“朝廷至今遵用之”。
江东世族在礼学方面也如此。《陈书·儒林传》载顾氏“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可见江东世族非常重视宗族内的儒学教育。东晋南朝,江东世族人物多有参与礼制建设的记载。如东晋虞喜“博学好古”,司马睿有礼事,“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咨访焉”。[10](《晋书·儒林·虞喜传》)会稽孔氏“明练治体”,如南齐孔稚珪参预修订《律文》,梁、陈间的孔奂在侯景乱后,“每事草创,宪章故事,无复存在,奂博物强识,甄明故实,同无不知,仪注体式,笺表书翰,皆出于奂”。又载奂“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服悦”。[12](《陈书·孔奂传》)南朝孔氏人物多有出任尚书仪曹郎等职者,皆与其精悉典制有关。即便是后起的文化世族吴兴沈氏,梁、陈间的沈约、沈文阿、沈洙、沈不害等,皆以精悉朝仪、官仪显名。当然,就礼制而言,江东诸族中尤以会稽贺氏为最。贺氏自汉代以礼学兴,历经六朝,延及隋唐,数百年间绵延不绝,始终以礼学相传,是典型的礼学世家。东晋初,贺循有“当时儒宗”之誉,史载“朝廷初建,动有疑议,宗庙制度皆循所定,朝野咨询,为一时儒宗”。[3](《三国志·贺邵传》注引虞预《晋书》)直到南朝梁代,贺玚、贺琛等,皆为广有生徒的大儒,并参预“创定礼乐”。相对于侨姓世族而言,江东土著世族的礼学传授更多地保持着汉代家学的传统。可以说,以礼学为中心的儒学研究确是江东世族家学的核心。
当然,不可否认,东晋南朝世族之学术文化还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倾心玄学。东晋南朝时期士大夫行为上礼玄双修,学术上经学玄化,蔚为风气。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六朝清谈之习”条中指出:“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五经中惟崇《易》理,其他尽阁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是当时(指梁代)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晋人虚伪之习未改,且又甚焉。”瓯北所论虽未尽合实际,但就其指出江左经学玄化之风而言则颇有见地。
从江东土著世族的情况看,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之初,处于孙吴割据状态下的江东世族当时几乎没有受到玄学的影响。永嘉之乱后,随着侨姓世族的南迁,玄学风靡江左,本土世族开始深入接触玄学,并在不同程度上玄化。对此,唐长孺先生指出:“永嘉乱后,大批名士南渡,本来盛行于京洛的玄学和一些新的理论,从此随着这些渡江名士传播到江南。以琅邪王氏、陈郡谢氏、殷氏为首的侨姓高门在江左大畅玄风固不必论,一向偏于保守的江南学门,如吴郡陆氏、会稽虞氏、贺氏等,虽然大体上仍传授汉代以来累世相承的家学,但也不免逐渐为侨人风尚所移,开始重视玄理。特别是吴郡张氏,家世相传,研习玄学,受到新学风的影响更深。”[13](P212)这种学术上的“与时推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江东世族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南北人士间的合流。当然,就玄学理论而言,江东人物少有贡献,即便是被誉为再现“正始之音”的张绪,其所谈论依旧是正始玄学的命题,他们真正精擅的还是儒学。
从总体上看,在玄学方面,江东土著世族在总体上比侨姓世族差。而在其内部,吴郡张、顾、陆诸姓比之会稽虞、孔诸族,其玄化程度则要深的多,这使得他们更便于与侨姓世族沟通,从而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上升诸方面都不无益处。会稽世族虽也有不同程度玄化的迹象,但其水平不能与吴郡世族相比,有的虽在学理上重视玄学,但在为人气质和谈论方面尚未名士化,显得更为守旧,囿于经、律并治的汉儒传统。这在侨人占据优势地位,玄学思潮盛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自然妨碍了他们与侨人之间的深入交流,对他们的社会声望和仕宦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可见江东世族学术文化的变异,不仅关乎学风之兴废,而且牵涉到其家族社会地位的升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江东各宗族的不同支系或个人,有时对待玄学的态度也有差异,如南朝时期顾琛、顾欢、陆澄、孔稚珪、张融等人个性鲜明,具有较为强烈的江东文化本位的意识,这便决定了他们在当时的文化交融与整合中持有较为独特的态度。这充分表现出了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与经学、玄学之演进相关的是中古文学与史学的勃兴。就史学言,汉代以来,经、史并称,史学附属于经术。魏晋以降,史学获得了相对独立发展的地位,诚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得那样,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14](P384)史学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著述的繁荣,比之以往,魏晋南北朝史书的种类、数目都大有增加。据周一良先生统计,“从数字看,东汉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中《春秋》项下所收史部著作,只《国语》、《世本》、《战国策》及《史记》等十一种三百五十余篇(卷)。到梁阮孝绪《七录》记传录所收,四百余年间,骤增至一千二十种,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即种类增加了一千倍;卷数增加四十余倍”。[14)(P390)刘知几《史通·杂述篇》概述当时正史之外的史著“其流有十”,其中所谓“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皆与世族社会的文化观念有关。从有关江东世族的情况看,各大族皆有家传、家史、重要人物的别传,也有地区性的人物合传,如《会稽先贤传》、《会稽典录》、《吴录》及为数不小的地记著作。江东各族无不代有治史者,吴郡顾、陆,会稽虞氏等自不待言,次一等的如吴兴沈氏(如沈约)、姚氏(如姚察、姚思廉),会稽谢氏(如谢承、谢沈)也可谓世代治史,成就卓著,中古史学之繁盛,有他们的一份功绩。
就文学观念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时代。伴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士风的变异,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经术束缚下的小道蔚为大国,特别是当时的统治者多爱尚文学,将文学作为取仕的重要条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古文学观念的变革。《梁书》卷一四传末引姚察所论云:“观夫两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其间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不少中古时代的大家族都重视文章之事,以此传家。近代刘师培研究中古文学,有一论断云:“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15](P88)如东晋南朝侨姓世族的代表陈郡谢氏、琅邪王氏,皆为文学世族。谢氏子弟皆能文,出现了谢灵运、谢朓等一流的诗人。关于王氏重文,沈约曾感叹云“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梁代王筠也以此自豪:“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16](《梁书·王筠传》)这里将“爵位蝉联”与“文才相继”联系起来,确实反映出中古文学地位的上升。江东土著世族也多重文,如吴郡陆氏、张氏等,是比较典型的文学世家,其家族不仅文士数量多,而且文学贡献也大,即便是晚起的吴兴沈氏,也致力此道,齐、梁间的沈约竟成为“一代文宗”,这对于其家族地位的提升大有助益。
除了经术、玄学与文史等学术文化之外,世家大族还特别重视其他才艺之事,以培养其子弟的性情与爱好,这是当时名士风流所必具的因素。《颜氏家训·杂艺篇》中提到书法、绘画、射箭、卜筮、医疗、弹琴、围棋、算术、博弈、投壶之类,名目甚多,其中尤以书、画二事最受重视。在书法方面,琅邪王氏世代善书,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书圣”。之所以如此,王氏重视书道的传授,视之为“家学”秘传。《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人名·王廙传》载王廙《与羲之论学画》有云:“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予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励之。嗟尔羲之,可不勖哉!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这是王廙向王羲之传授书画之法。据传为王羲之所作之《笔势论序》有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父不亲教,自古述之。……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之诸友。……此之笔论,可谓家宝家珍,学而秘之,世有名誉。”可见王氏世代之书艺相传,视为“家宝家珍”。王氏如此,其他世族也重此艺,反映了世族社会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
如果说江东土著在书法方面主要是取法侨人,那么在绘画方面则表现出了足够的创造性,出现了一批代表当时绘画最高水平的艺术家。如吴郡顾氏有顾恺之、顾野王等,陆氏有陆探微、陆杲等,张氏有张僧繇父子等,皆世代相传。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有云:“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这里明确指出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符合中古时代的实际情况。
纵观中古文学、艺术史,江东土著世族虽在某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在总体上却是追随和效仿侨人重视文义的文化精神,这与他们习玄是一脉相承的。相较之下,吴地世族在文学、艺术方面与侨人接触渐深,所获亦多,其中陆氏、张氏在文学上可以与侨姓名门相媲美;顾氏则是杰出的艺术世家。会稽世族也多能文、习书画,但其风不浓,其势不盛,影响不大,与吴郡世族有差距。这与他们在习玄方面的态度颇为相似。这也同样影响到了二地世族社会地位的升降。
此外,在星历算术、土木机械和医药等方面也重家传。如《南史》卷七二《文学·祖冲之传》载,冲之祖昌宋时任大匠卿,“冲之稽古,有机思”,先后造作指南车、欹器等;又“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冲之“又特善算”,注《九章算术》,“造《缀述》数十篇”。冲之又精于天文历法,他以刘宋何承天之历法“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历者难之,不能屈”。冲之子恒“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梁武世,恒改进乃父之历法,“于是始行焉”。恒子皓亦“少传家业,善算历”。范阳祖氏世代传习机械、算术、历法,形成了鲜明的家学特色。又如《南史》卷三二《张邵传附徐文伯传》载,东海徐氏居钱唐,自徐熙得《扁鹊镜经》以来,“精心学之,遂名震海内”,其生子秋夫,“弥工其术”。秋夫子道度、叔向“皆能精其业”,道度子文伯“亦精其业”,文伯子雄“亦传家业,尤工诊察”;叔向子嗣伯亦精通诊治之道。又据《北史》卷九○《艺术传》,东海徐氏传人徐謇流落北魏,以“善医药”得宠于魏孝文帝和文明冯太后。徐之才、徐之范兄弟亦以“大善医术”显名于北魏、北齐之间。东海徐氏自东晋延至隋代,可考者有八代以医术荣显家门。在江东本土大族中,也有这样以方技术业传家的例证,如吴兴武康姚氏便是一个世代“家业”相承的医术世家。[17](《周书·姚憎垣传》)这种家学承继的状况,与当时的秘术家传的家教方式有关。
最后还须指出,宗教信仰也是中古世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世家大族虽多有深厚的儒学积淀,并且儒、玄并综,但他们又多崇信佛、道,形成了儒、玄、道、释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尤以琅邪王氏最为著名。直到南朝末王褒训诫子弟还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16](《梁书·王规传》)王氏既是经术礼法世家,又是天师道世家,并且世代崇佛,甚至间有出家者。从江东各家族的情况看,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与琅邪王氏基本相同。如吴郡顾、陆、张三姓之主体皆崇信佛教,且与道教间有往来。像吴兴沈氏、会稽孔氏这样著名的天师道世家,虽有个别排佛者,但其主流人物则主张“会同道、佛”、儒、释同源。佛教是外来宗教,东晋南朝时期广泛地渗透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之所以如此,与世族之倡导关系甚大。中古世族之家教也多以佛教能涵养人心。《颜氏家训·归心篇》说:“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渍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归周、孔而背释氏,何其迷也!”正是在这种儒、释均善的思想指导下,世族阶层采取了诸教并蓄的态度,表现出了相当的包容性。这种文化心态有利于世族社会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2-12-12
标签:家风论文; 文化论文; 廿二史札记论文; 汉朝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东晋论文; 通典论文; 六朝论文; 南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