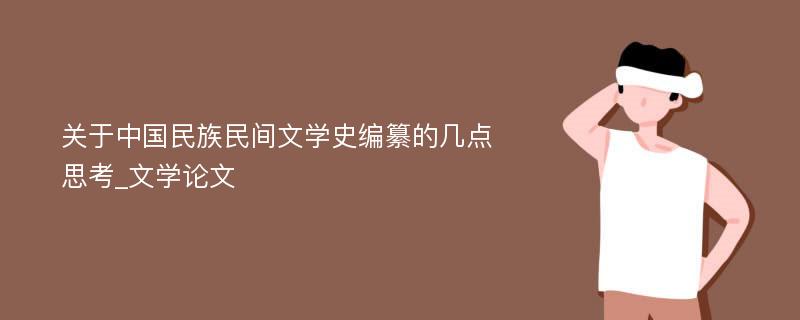
关于中国民族民间文学史编写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民族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3)06-0119-04
民间文学史的写作向来是个攻坚难题,遇到的明障暗礁让人防不胜防,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无案可查的多,难以断代,序列难以建立。相比之下,汉族民间文学就好得多。但即便如此,敢于啃这块硬骨头者寡。从19世纪90年代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面世,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各种综合性或体裁性文学史、文学史纲要、文学史简编、小说史、戏剧史、女性文学史以及相关论著,大约有400多种,其中冠以史字的约占100多种,即1/4多一点。这些文学史当中,民间文学史或与此相近的著作,不过几种,其中真正的民间文学史,首推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上下册),被誉为“第一部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系统性专著”。该书的序列是:第一章 何为俗文学,第二章 古代歌谣(先秦),第三章 汉代俗文学(主要是民歌),第四章 六朝民歌、新乐府,第五章 唐代民间歌赋,第六章 敦煌变文,第七章 宋金元杂剧词,第八章 鼓子词和诸宫调(宋金文),第九章 元代散曲,第十章 明代民歌,第十一章 宝卷(说唱),第十二章 弹词,第十三章 鼓词与子弟书,第十四章 清代民歌。
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比较完整的民间文学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9年10月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但这部史书也没有统一的年代,而是按体裁“各自为政”,全书分为神话编、传说编、故事编、歌谣编、叙事诗编、曲艺小戏编和谚语谜语编,各编有自己的年代演化序列,不完全统一。如传说编分为上古到战国末、秦汉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5个时期,而故事编则分为先秦至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代4个时期,歌谣编分为先秦、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6个时期,分期之难可见一斑。民间文学史面世之少,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长久以来诗歌垄断文坛造成的轻视民间文学传统观念的束缚,更主要的是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无时间可考,无作者可稽,演化脉络不易辨识,草蛇灰线不易寻求,造成序列上的重叠、断层、混杂、无序。
从理论上讲,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演化过程,也就是都有自己的时间序列。“世界上的因果链条应当在某个时候有个开端。”由于“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1]于是从开端之后便显出某一事物自己的序列,一个发展的时间序列。民间文学的发展,也无法逃避这样的规律。只不过由于其构成作品内部结构的组合方式及外部表征,着眼于主题的展现和深化,因而时间等表层形态深藏其间,有隐显之分,常不易辨识,不易把握,并非没有运动的轨迹。这和现代戏剧一开始就标明发生的时间,是不相同的。那时人们讲一个故事,编一首民歌,意在再现或表现某种情绪、情感,而不在乎时间和空间,因为文学的任务是提供审美价值。
但正如维特根斯坦和韦兹所主张的,艺术乃是一个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概念。由于新的条件和新的情况总是不断出现,于是新的艺术和艺术运动便不断发生。按照H·G·布洛克的文艺新解即新的艺术观,文学艺术对于现实而言,无非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和表现。但再现并非是简单的复制,或像从窗户里所看到的外部世界,“而是从一种特定的人类观点、立场或角度和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对现实作的再现和解释。”[2]也就是说在再现中,作者的个性、某个时代的文化观、某种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手段,形成了制约文艺创作的4要素。正像柏拉图在《诗学》中所说的,诗人描述或模仿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或事物,而是“可能发生或出现的某一类事物。所谓可能的,就是很有希望出现或必然要出现的。”[2]至于表现,则是艺术家情感的喷涌。现代一种理论认为,文学艺术的概念基本上是一种情感表现的概念。即从某种情感状态或体验向审美理解转化,使情感的释放和涌出,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变成一种艺术的理解。这种冲动或理解源于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体验,就像托尔斯泰所说的,一个少年遭遇一只狼的恐惧,在后来的多次转述中不仅表现出他心有余悸的恐惧情绪,也使听者受到感染并产生恐惧,虽然听者没有遇到那只狼。这使我们领悟到,“在艺术品内,许多新的审美意义被‘创造’出来,它们反过来又映照着作品之外的普通世界,使我们看到以往普通经验中未曾经历过和未曾接触过的方面和维度。”[2]
“映照作品之外的普通世界”,这是我们揭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包括断代在内的诸多秘密的理论依据,是我们藉以打开民族民间文学这一宝库的钥匙。用中国传统的提法,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既如此,从折射中当可观照时代,民间作品也不例外。从这里可以看出,民间文学文本,常包含着两个层次,一个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当时人们的意识,这构成了该文本的核心。这核心在后来的转述中,像一根有吸附力的魔棒一样不断粘附后来的历史碎片,使之产生粘附层。因此,我们只要细心剥开粘附层,露出核心层,便可以大体确定作品产生的年代。关于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断代,20多年来我们有很多的突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我们出版了几十部单一民族文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等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编写综合性的包含有55个民族文学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曾对当时已出版的25种单一民族文学史中民间文学作品的断代进行过结构性剖析,并对尚未出版本民族文学史的30个民族的民间作品的断代进行了多年探讨,总结出了断代3元素,这就是角色元素、情节元素、年代元素。民族民间作品的内部结构是由题材、主题、结构、角色、情节、细节、手法、风格、词语、形象、线索、场面、意境等元素组合而成的,这些元素都可能体现出作品产生的年代,但最重要的还是上述3元素。据对50篇(部)民族民间作品的剖析,从角色上体现出其产生时代或年代的占52%;从情节中反映作品时代或年代的占48%。上述两类情况中,有14%的作品明确标有年代,其它则是零星的。作品直接标明时代或年代的虽然比较少,但无论是角色或情节,均需与相应的史籍相印证,故这14%并不反映真正的比例,在角色和情节或细节中都包含有这一要素。
在断代实践中,我们遇到几类不同的作品,需要不同的方法来断代。第一类是有明确或比较明确的时间标记的,包括朝代、年号、干支纪年等,这主要是部分民间传说、叙事长诗、民间戏剧、民间说唱、时政歌等作品。不过作品的产生一般都比某个事件稍后,不可能同步,但也不能离得太远。不过有些历史题材的作品须慎重分析,综合比较。如侗族《斗牛词》一开头就唱“东汉末年,曹操篡权。三国鼎立,八方混战。”此词不可能产生于东汉末年。看其词后半部提到诸葛亮七擒孟获,可知《斗牛词》当产生于明代《三国演义》面世之后。
第二类作品虽无年代标记,但其人物、情节或事件可以找到参照物,所以也属于比较容易定位的作品。这类作品中的角色,一般为历史上确有其人,如民族英雄、农民起义领袖、明君贤相、文化名人等,作品中虽然没有年代或朝代标记,但有其它史籍可作旁证,因而可以确定或大致确定其产生的年代。这里主要通过角色元素来断代。有的作品提到了事件,却没有真实的角色,这时候只能通过情节元素来断代。在这里,情节中展示出来的事件过程,虽属文学虚构,却是可以通过史籍的相关记载来判定年代的。《勉王起兵又重来》肯定产生于侗族起义领袖吴勉在洪武十一年(1378)起义的事迹之后不久;《叶限》注明秦汉故事;《孤儿传》肯定产生于成吉思汗开展统一漠南草原的军事行动时代;《翼王派兵到我家》当产生于1851-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期间,等等,皆有较明确的年代。因此,角色性质、特征是年代的一个代码或符号。
第三类是从角色到情节都是泛指的作品,不仅产生年代深深隐藏在演绎情节文字的背后,而且粘附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碎片,把作品产生的年代覆盖了若干层。这类作品的年代难以断定,且占了民间文学作品的大多数,成为编写民间文学史的拦路虎。在这类作品中,有一种是角色有较强的时代色彩,比如阶级社会不同阶段的被压迫者奴隶、奴婢、“子女”,“灰”(注:壮语“奴隶”音译。)、“生口”、隶、贱隶、男女、家奴、阿加、呷西(锅庄娃子)、长工、农夫、牧工、猎手、乞丐、挑夫等。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国王、君、皇帝、可汗、王爷、相、将、公主、土官、山官、宗本、黑彝、财主、牧主、鱼霸、地主、酋帅、帅、渠帅、首领等。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阶级结构,故而作品中出现的正反角色,常常成为确定其产生的大致年代或时代的主要依据,先断定属于社会发展史上的哪个阶段,而后从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确定其是否可与具体年代或具体朝代相印证,这是一个由粗到细的鉴别过程。角色身上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其表层如服饰、语言、动作习惯、使用工具、生活习俗乃至更深层的某一时代的民族心理,都会有特定时代的烙印。即便在滚动中产生情节的变异,只要从中分离出文本的核心,去掉后来粘附的碎片,便不难确定其时代或年代,犹如一幅古画上有很多收藏者的印章,但作者只有一个。
当作品的角色是泛指或没有明确的角色,如民歌中仅是一种情绪的涌动和渲染,就只有依靠情节、细节甚至整个作品的内容,来判断其产生的时代,这种综合性的剖析,比鉴别角色代码要复杂得多。但“有证据表明,某些情感特征不完全是一种相对性的东西(文化环境不同,意义也就不同),它们在极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有着相同的意义。”因此,再隐蔽的年代也会有踪迹可循。按“帕里——洛德理论”,口头作品“每一次表演都不仅仅只是一次表演;它是一次再创作”,“变异的模式包括细节的精雕细刻、删繁就简、某一序列中次序的改变或颠倒、材料的添加或省略、主题的置换更替,以及常常出现的不同的结尾方式等等。”[3](P101)但作品在千百次复述中又有其相对稳定的核心,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称之为“传统”,他指出:“故事的叙述,或其叙述的核心要素,持久牢固地粘连在一起,并轻而易举地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中,这正好证明存在着一个演唱的传统。”[3](P105)“传统并没有衰落,而是存在于绵延持续的复兴与更新之中。”[3](P110)这种传统又被艾伯特·洛德(Albert Bates Lord)称为“传统单元”,它包括“程式单元”和“主题单元”,所谓“主题单元”是指“在传统口头诗歌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叙事的或描写的要素”,这与中国所理解的主题不同,它近于“母题”。这种“传统单元”又被称为“复诵部件”,而具有可塑部分则被称为“构想部件”,前者可保持作品的相对稳定性,后者则使歌手、故事家“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境”。欧美口头文学的分辨派则把“传统单元”或“复诵部件”称之为“年代累层”。[3](P89)从这里看出,民间文学作品按其积累层次分为相对稳定的核心部分,即“传统单元”、“复诵部件”或“年代累层”。另一部分为“构想部件”,它在积累中粘附了不同层次的历史积淀。这就像考古学上的文化遗址,在其最早的文化层之上日积月累又压上了若干文化层,最下层最为古老,最上层最为晚近。民间文学史家的断代任务,就是挖掘其原生层,寻找初始年代。也就是将“复诵部件”和“构想部件”分开,寻找出“传统单元”,便可以进行断代。这是艰难的,但同时又是可行的。这里以情节元素为突破口,寻找核心的初始的情节结构,结合题材、主题、时代背景、时代风格和手法,以及“帕里——洛德理论”中的“程式”,即“一种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在相同步格条件下,用以传达一个基本的观念”的“名词——特性形容词”,某一特殊词语表达方式,常常是一个特定时期文学中特有的现象。以上各方面的综合比较,引入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语义学等方法,可以大抵断定作品的时代。然而不少作品目前还只能判断产生它的社会形态,要剖析到相应的朝代或年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方面已作出了不少成绩。纳西族著名的长诗《创世纪》,时间跨度很长,内容几乎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几个历史阶段。诗中的“石板不发烫,蜜蜂不搬家;主人不凶恶,奴仆不逃跑。”反映的是奴隶制。而子劳阿普包办女儿婚姻,则是封建婚制。但长诗的核心还是原始社会生活,如狩猎生活,原始刀耕火种,万物有灵,血缘婚痕迹,父子连名制,从天上迁到人间,等等,可以断定雏形是原始社会高级阶段即父系氏族时代的产物,奴隶制、农奴制的社会生活是后来增补上去的
基诺族的《织布能手白腊薇》,说的是小伙子腰杰与白腊薇相恋,另一女子车施也喜欢腰杰,但腰杰不喜欢她。车施恼羞成怒,竟凶残地杀死白腊薇。白腊薇死后先后化为鱼、花和鸟,用超人间神力惩治车施这位害人的富家女子,而后白腊薇神奇地还原为人形,与腰杰结为夫妻。这个故事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有超人间情节,但显然不是神话,带有阶级社会矛盾的色彩。基诺族新中国建立前处于从氏族社会末期到阶级社会的过渡中,已产生借贷、原始租佃、雇工等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按作品产生的社会形态,当属于奴隶制萌芽到向农奴制转化的初期。由于基诺族处于附近民族的农奴制强烈影响之下,奴隶制不可能得到发展,而云南边疆的农奴制残余形态一直保持到民国期间。故而基诺族的阶级分化很快转向农奴制,但这一转化还没有完成,新中国即诞生,于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此作品产生的年代当在清末或民国期间。
壮族《贼歌》(发表时译为《唱离乱》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叙述一对男女青年正在热恋之中,却被归德土官拉去出征,他和士兵们一路行军,经过今马山乔利,一路烧杀抢劫,最后到达上林、忻城一带,与“贼”生死搏斗,杀得血流放河。归来后他感到罪恶深重,深深忏悔,求恋人宽恕。抓兵的是归德土官,归德土州地处今平果县西南,建于唐,1915年改流。据考证,在长达1000年里,自归德行军经今马山乔利到达上林一带,发生激烈战斗的,当是明万历八年(1580)广西巡抚调归德等田州土兵镇压上林、忻城、来宾三县交界的八寨壮瑶农民起义。诗中既骂起义军为“贼”,也忏悔自己去杀义军是“官逼哥做贼”,内容与史实相对照,便可以确定此诗大约产生于16世纪末叶即八寨之战后不久。又根据民俗,此次战争由于规模大,战斗激烈,右江一带土司兵伤亡惨重。平农民起义后,田东壮人便于每年阴历二月廿九日在仰岩举行大规模追荐亡灵法事,并诵此诗以示忏悔。此可作佐证。
总之,根据作品的情节、细节,结合其主题思想和题材选取,与相应的民族历史演化阶段和历史事件互相印证,多数或大多数作品是可以断代的。但是,这种判断却难以量化,即难以与具体朝代、具体年代相对应,一般而言,能确定具体年月是少数,确定朝代多一些,对大多数民歌、长诗和民间故事传说而言,只能判断其产生于社会发展史上的哪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根据以上断代的3个元素,目前已出版的单一或综合性的民族文学史,可构建5种不同长度和容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史。(1)中央王朝更替框架。这是一种回应《中华文学通史》那样接近于中国朝代更替的构架,该书设置了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五代文学、宋辽金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10个部分。这一构架近于朝代序列,也可以说是王国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4]的延伸。几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大抵就是这个框架。这一框架对汉文学而言,具有最大的容量。但少数民族如用此框架,可能绝大部分作品将被排斥在外,因为能与中央王朝朝代对应的民族民间作品,实在太少,故而目前用此框架的单一民族文学史很少。《回族古代文学史》设元代回族文学、明代回族文学、清代回族文学3编,内容以作家文学领衔。而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或仅有少数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难以做到。(2)大跨度断代框架。此为文学发展与朝代更替相结合的框架,即通常的远古文学、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但各民族文学史中的远古文学、古代文学(有的还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3个阶段)的上下限多不相同。例如新版《瑶族文学史》的远古文学为“公元581年以前,南北朝以前”,古代文学为“公元581-1839,隋唐至鸦片战争”。而《羌族文学史》的民间文学部分,远古民间文学为公元前205年以前,古代民间文学为“公元前206年-公元1840年”,两本文学史相差甚大,而羌族古代民间文学跨度竟达2046年,这也出于无奈。《壮族文学史》实际上也属于此类结构。第一编“布洛陀时代的文学(?—公元前221年)”实为秦汉前的远古文学;第二编“莫一大王时代的文学(公元前221年—公元1271年)”实为中古文学,上下限为秦汉到唐宋;第三编为“《嘹歌·唱离乱》时代的文学(公元1271年—1840年)”,实为近古文学。这种框架容量稍大,但由于跨度较大,难以真正反映民间文学本身的运动规律,线条较为粗糙,不过也实现了文学轨迹的大波峰排列,总体上可看出发展的趋向。(3)混合断代框架。此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混合断代框架结构。如《白族文学史》(张文勋本),第一编为“南诏以前的白族文学”(公元748年以前),第二编为“南诏大理国时代的白族文学”(公元748-1253年),第三编为“元明清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白族文学”(公元1254-1949年)。此种框架容量稍大,也较能反映某一民族的文学奔流直泻或迂回激荡的运动轨迹。但对绝大多数从未建立过地方政权的民族,无法用此框架。综合性的民族文学史当然只能以中央王朝的序列作为坐标。(4)文学运动框架。此为按文学本体运动规律之轨迹设置的框架,如《傣族文学史》第一章为“古歌谣时期”,第二章为“创世神话时期”,第三章为“叙事长诗时期”,第四章为“悲剧叙事诗时期”,第五章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傣族文学”。其中第一、第二章实为远古文学,第三、第四章为奴隶制和农奴制时代文学。特别是“悲剧叙事诗时期”,以下层奴隶、农奴的悲剧为结局,开创了傣族文学从虚幻走向现实的一场文学革命,导致长诗的繁荣。这一框架总的来说有较大容量。文学本身的草蛇灰线也易于显现,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如何向前发展的,其波浪式推进所显示的阶段性序列,能给我们许多的启示。不过这种框架要建立在对众多文本的剖析上,离开对文学语言的深刻理解难以进行。(5)社会发展史框架。这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史为座标来观照文学的框架结构。从理论上讲,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总会对意识产生相应的制约,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包括相应的文学。原始社会的文学和封建社会的文学,在题材、手法和风格上肯定有显著的差别。不少民族文学史都采取这种框架,如《藏族文学史》、《蒙古族文学史》都是这种结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吸取此种结构之长,在纵向上设有“原始社会时期民族文学”、“奴隶社会时期民族文学”、“封建社会时期民族文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文学”、“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文学”5编,38章。在横向上海一社会发展阶段按体裁安排章节。每一体裁之下按北方、西北、西南、华南、中东南5个板块分述,以综述涵盖其特征,形成了一种纵横网络结构。这种框架的优点,首先是能够适应大部分民族民间作品只能鉴别其相应社会形态的客观实际,同时便于照顾到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体现出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但这种框架也是出于无奈,它容量虽大文学轨迹却较模糊,虽然可以归纳出某一社会阶段的社会背景和文学特点,但较难于揭示文学本身的运动规律,比如一个漫长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曾出现的若干次文学思潮。另外也不易探索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展与汉文学演化各阶段的相应关系,反映出主流文化下文学思潮对边缘文化中民族民间文学的辐射力度。
通观以上5种框架结构,它们各有长处,各有相应的容量,可以适应不同的需要。特别是在当前大多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尚一时无法探索其较清晰的产生年代,跨度较大且容量也较大的情况下,可以作为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予以运用,以此作为向更缜密的民族民间文学史推进的基础。企图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5种框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各显所长,通过促进民族文学史、民族民间文学史编撰的百花齐放,必能从中寻找出较为满意的框架。我们的目标是追寻接近于主流文化中汉文学发展的历史分期,使汉文学史和少数民族文学史接近于运动过程中的共振和谐。综合各种框架来看,我认为比较理想的框架应当是前疏后密,循波逐浪,增大容量,贴近主流,最后显示出从区域共生到中华趋同。所谓循波逐浪,说的是民族民间文学史框架要力求建立在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的共振和民族文学自身的波浪式运动轨迹上。但是,在中华文学的范围内,民族文学的轨迹不可能脱离主流文化的运动,因此,贴近主流不是人为的粘合,而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学发展的实际。根据这样的构想,我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比较理想的是《中华文学通史》框架,可以稍做变通,即:一、古代民族民间文学:1、先秦民间文学。2、汉三国民间文学。3、晋南北朝民间文学。4、唐五代民间文学。5、宋辽金夏民间文学。6、元民间文学。7、明民间文学。8、清民间文学(止于1840年)。二、近现代民族民间文学:1、近代民间文学。2、现代民间文学。三、当代民族民间文学。要按这一框架来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史》,其难度是很大的,需要对汉族古籍和民族古籍做大量的剥离工作,需要对大量少数民族民间作品进行断代研究,更需要有好多部包括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综合性民族文学史来逐步完成。在这个基础上,编写出56个民族的文学水乳交融的、或至少比较接近于中国文学演化规律的《中华文学史》或《中国民间文学史》,以体现出中华各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血肉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