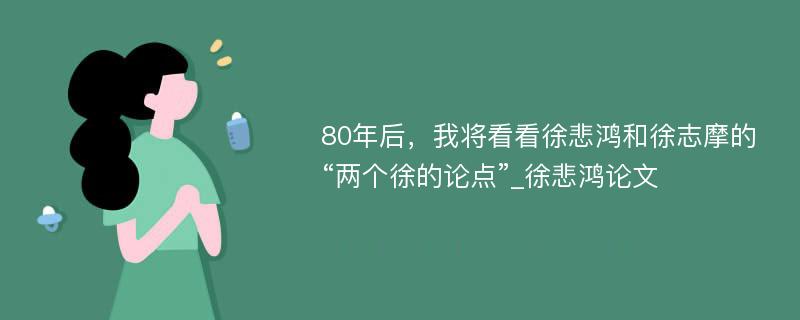
八十年后再看徐悲鸿、徐志摩的“二徐之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徐悲鸿论文,再看论文,摩的论文,八十年论文,徐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9年4月10日,旧中国第一届美展举办之际曾发生过的徐悲鸿、徐志摩之间的辩论,对于中国美术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80年前美术创作方法论之争,时至今日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二徐之辩”的直接导火线是1929年由国民党教育部组织的“第一次全国美展”。由这个展览所引发的争论,其关注的焦点在于:1.对西方艺术史的认知问题;2.对西方主流艺术大师的评价问题;3.中国美术人的创作观念与态度;4.展览会主办人倾向性问题。“二徐之辩”的争论是在三个常委之间进行的。可以说,主要原因是不同的艺术观所导致的一场争论,其本身虽然没有涉及艺术观的大是大非问题,但事实上,不同的艺术观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美术界?它的直接影响又是什么?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检审这一重大理论之争,对当下的理论研究意义重大。
一、“二徐之辩”争论的背景
20世纪头20年里,向往西画艺术并且艺术旨趣相投的画家曾组成各种美术社团,不断地宣传西画的精神,引入与中国绘画完全不同的理论概念,这在中国美术界引起不同的反响。“二徐之辩”是中国美术史必然出现的一场争论。从1905年到1937年,二百二十多名中国美术留学生回国后,全国各地美术学校纷纷设立,画会风起云涌,西画创作队伍日益壮大。“二徐之辩”这场争论的产生,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一时期内悄然兴起的西画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艺术思潮,盛极一时的全国美展等诸多因素,都是这场争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事实上,西画东输才是这场“二徐之辩”的主因。“西画东输”后,中国文化界所产生的思想变化十分激烈。因艺术观念的不同,不仅在美术界引起不同的争议,而且在文化界也掀起不小的波澜,在美术实践、美术理论、创作方法论、美术史观等诸多方面都产生很大争议。特别是在西画、国画上的争议比较大,歧异也大。
1929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中国举办破天荒的全国美术展览,于是成立一个展览会总务,下设有七人常务委员,即徐悲鸿、王一亭、李毅士、林风眠、刘海粟、江小鹣、徐志摩。1929年4月10日,在上海如期举办“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全部展品在486个画室中展出,其中西画有354件,国画有1300多件,全部展品2000余件①。内容包罗万象,是一次最具“包容性”的展览。展览主办者还出版了由徐志摩、陈小蝶(1897-1989)、杨清磬等人编辑的《美展汇刊》进行宣传。这次展览规模真是盛况空前,不仅有书画,也有雕刻、建筑及工艺美术,不仅有当代美术,也有古代式样的及外国的作品参展。就书画而言,当时对中国画并没有争议,而是在西画的艺术观上引起争论,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西画东输”后,西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即在二十多年里,对西画这个新事物人们普遍缺乏理论常识,传统美术与新潮美术、东西方观念存在差异性,还有美术界的人为不和因素等,特别是在当时追求新潮的时代,在“西画样式”风景画、肖像画等现代美术思潮作品在展览中所占的比例较大的情况下,其争论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当时被陈小蝶称为“现代国画派”的一千三百多件中国画也在陈列之中。在陈小蝶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里,我们可以看到陈小蝶将展出的国画分为六派:复古派(顾鹤逸、冯超然、吴岱秋、王晓汀)、新进派(如钱瘦铁、郑午昌、张大千、许征白等)、折中派(高剑父、陈树人、何香凝、汤建猷、方人定等)、美专派(刘海粟、吕凤子、王显韶)、南画派(金城、萧谦中、齐白石)与文人派(吴湖帆、吴仲熊、陈子清、郑曼青、狄平子)。美术家、评论家、实业家陈小蝶的这种分类方法只是表面化的一种说法。针对这一时期美术界的状况,美术史家姜丹书在文中曾作过这样的总结:“一般艺术思潮,当然以现代的环境为背景,故多解放的、自由的、无忌惮的。一般作风也当然在思潮的笼罩之下,多为自我表现的、崭新的,甚而至于怪异的。”无怪乎徐志摩在《美展弁言》中对首次美展充满了信心:“我们留心看着吧,从一时代的文艺创作得来的消息是不能错误的。”然而,当徐悲鸿发现整个展览中的作品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参展的油画作品受到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很大时,拒绝将自己的作品送去展出。原因在于他不情愿这样做,这与他的艺术观出入很大。
针对西画与国画的认识,“习洋画的青年,对于国画很看不起,他们以为将来中国习画的人非都习洋画不可;反过来说:一班治国画的前辈,他们脑筋里只记得几个古人的名字,很瞧不起洋画,以为洋画与他们毫无关系。前者是‘洋化’,后者是‘拟古化’。‘采他人之长,补吾人之短’是艺术上应有的事。艺术是有世界性的东西,既没有界限,也不可固守”。②在实践上,分成两个阵营是历史必然存在的现象,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艺术观本身。在当时具有理论建树意义的是梁启超与汪亚尘二人。梁启超于1922年先后在上海美专、北京美术学校发表演说“美术与生活”和“美术与科学”,对美术的理论问题发表了他的观点,并首次提出“美术人”的概念。他认为,现代文化的根底在于科学,美术是从“真美合一”的观念发展而来的,即“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真正的艺术作品,最要紧的是描写出事物的特征……美术家的观察,不但以周遍精密为能事,最重要的是深刻。”③梁启超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对中国画的看法与认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提倡美术的“科学性”,只有科学性存在,才能达到“真美合一”的境界。最后达到他所认为的“美术之趣味”,在于:1.对意境的赏析;2.内心世界的艺术创作;3.现实与超越境界。
正是在梁启超“真美合一”的基础之上,当时年轻的画家汪亚尘提出艺术的“时代精神”。他首次阐述了“艺术的时代精神”的概念,并认为:“艺术是时代生活的明镜,在时代上映照时候,常常有种奇异的反射,跟着这种反射的印象而后现于画面上,才不失时代的精神。”“艺术最高的意义,完全由作家内心的表出,在心灵上的传达上,应该有两个信条:一创造的深索,二描出的技能。”“一方面要把中国固有艺术的精神重新振拔,一方面要把西洋艺术的长处采入到国画上去,两下融合起来,成为时代的艺术。”④综上所述,在美术创作理论与艺术观念更新的问题上,在“西画东输”后,中国的美术界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主要体现在:1艺术史观的美术理论与时代精神的问题;2.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认识问题;3.创作方法论问题;4.艺术价值取向与中国美术的发展态势问题等。“二徐之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个讨论虽然从1929年开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结束,但在各方面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
二、“二徐之辩”的核心内容与影响
1929年4月,徐悲鸿在《美展》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惑》的文章,引发针对西方主流艺术的争论。徐悲鸿的文章有两千多字,表达出他留学法国8年的心路之旅,即他的艺术史观。他对当时法国的主流艺术印象派—后印象派的艺术并不认同,而对于法国的古典绘画持高度赞扬的观点。徐悲鸿说,法国派之大,乃在其容纳一切。他先说他比较赞同的艺术家,比方说普鲁东、达仰、安格尔等人⑤。他文中的这些欧洲著名油画家的名字虽然与今天的翻译不同,但不影响我们识别出他们都是以古典风格的写实主义为指向的。在这里,徐悲鸿有一句最为重要的话,欧洲在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生发出许多“变象”,而不是发展的进程。接着,他认为“虽以马奈(Manet)之庸,雷诺阿(Renoir)之俗,塞尚(Cezanne)之浮,马蒂斯(Matisse)之劣,纵悉反对方向所有之恶性,而藉卖画商人之操纵宣传,亦能震撼一时,昭昭在人耳目”。⑥即用庸、俗、浮、劣四个字来概括马奈、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他后来甚至还将马蒂斯译成“马蹄死”。
他还说,假如中国国民政府要成立一个大规模的美术馆的话,要是收藏三五千元一件的塞尚、马蒂斯的作品的话,“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披发入山,不顾再见此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也”。⑦今天回过头来看,假如当时真的成立国家美术馆收藏塞尚、马蒂斯、雷诺阿作品的话,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也不需要用大量资金来引进印象派的作品到中国展览,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了。那会节省多少的资金,可历史并不能假设。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使徐悲鸿对西方当代绘画艺术有如此大的异议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与徐悲鸿8年留学的心路之旅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8年里,徐悲鸿经常被经费拮据所困扰,⑧如他在1925年至1939年多次到新加坡去画作品出让。他的作品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多半是无人问津,而在东方,情况大为不同。当时的东方十分认同写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徐悲鸿在新加坡留下了他在法国期间的大部分素描手稿和在那里创作的《奴隶与狮子》、《放下你的鞭子》等名作。这些作品在2006年至2007年都出现在香港的拍卖会上。相反,徐悲鸿回到国内后创作的多半是以素描打稿的国画,如《愚公移山》等作品。在徐悲鸿看来,当时法国印象派以后的作品是低水平的。因为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画家生存竞争激烈,“无暇治及高深”的缘故,特别是印象派之类的画家,“彼等之画一小时可作两幅”,其水平可想而知,而且是完全由画商操纵的。从这些言词中可见,徐悲鸿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若就事论事的话,徐悲鸿存在很大的偏见。
第二,徐悲鸿在留学期间,学的是学院写实派风格油画,并没有对西方当时的主流绘画产生过浓厚兴趣,对西方当代美术史论的研究更是无从谈起。他留学时特别关注的是法国学院派写实作品和古典画家的作品,曾专门临摹过西方大画家如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等少数几个人的作品。此外,没有任何文献记录他对印象派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有过兴趣,完全规避了盛行于当时欧洲的现代主义潮流,要么不谈,要么微词不断,或者干脆贬上几句。比如,他到德国时,对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Kampf)的那些表现怪诞的绘画表示过他的疑问,甚至是不屑一顾。在提及印象派时,明确用庸俗、低劣的字眼加以挖苦。
第三,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时,几乎看不到他与当时欧洲绘画艺术领域的大画家们有过密切的交往,多数是他参观学习欧洲古典艺术的频繁活动。1919年3月,徐悲鸿和蒋碧微留学的时候,先在英国伦敦停留。徐悲鸿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大英皇家画会展览会等,特别是委拉斯凯兹(Velazquez 1599-1660)、透纳(J.M.W.Turner 1775-1851)以及康斯太勃(John Constable 1776-1837)的作品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同年秋天,徐悲鸿入法国朱利安画院学习素描。几个月后,他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老师是历史画家弗拉孟。但因弗拉孟年老多病,很多课是由曾获罗马大奖的科尔蒙(Fernand-Anne Piestre Cormon 1845-1924)上的。1920年冬,徐悲鸿结识并拜学院写实画家达仰(Dagnan-Boveret 1852-1929)为师,直至1927年徐悲鸿回国前,这位法国人一直都是徐悲鸿的老师。在欧洲学习期间,因为经济拮据方面的原因,1921年夏天,徐悲鸿到过德国。在德国,门采尔(Adolf Menzel 1815-1905)、塞冈蒂尼的作品对他产生过影响,但那也都是古典风格的作品。
第四,我们从文字以及其他文献里看不到徐悲鸿对16至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的思想与观念背景的真正理解,更多的是出自他个人的好恶。徐悲鸿学的是欧洲学院写实派的内容,当时的法国也属于传统派的油画观念,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以西方学院写实为引入中国油画的主导思想,这就存在相当大的认知偏差。差不多在1920年以后,徐悲鸿开始发表言论,强调写实绘画总是与历史、真实乃至科学发生关联,油画的科学性是首当其冲的。这种理论说法,并不是徐悲鸿一个人的,而是当时的知识界、科学界所达成的某种共识。他一直在推崇普吕东等人的“高妙”与“华贵”。事实上,他们在技术与方法上,受到了太多的属于学院派的梅索尼埃(Jean-Louis-Ernest Meissonier 1815-1891)、热罗姆(Jean-Leon Gerome 1824-1904)的影响。徐悲鸿推崇的是学院教育,倡导的也是学院写实风格,所以才拿他们来说事。徐悲鸿的这种艺术观在其文章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第五,西方油画的写实语言,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无疑具有视觉上的冲击性。徐悲鸿的艺术观在于他以学院式的理性思维、科学(当时学者称之为数学的)的观念来推导出中国油画的内在发展逻辑,即通过对素描基础的强调,渐渐形成中国的、被认为符合科学的写实传统。
其实,比徐悲鸿晚一年(1920)留学法国巴黎大学法国文学及艺术史专业的林文铮(1903-1989)对当时欧洲绘画史的讲述相对而言是正确的。他对美术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929年1月,早在“二徐之辩”以前,林文铮写道:“由18世纪末叶之写实主义而有19世纪初期大卫之古典主义;由德拉克罗瓦之浪漫主义,而有库尔贝诸家之写实主义;由毕沙罗、莫奈等之印象主义而有塞尚之表象主义;到了立体派和未来派等可以认为现代艺术最热烈的变迁了。综观这百年来欧洲艺坛之沿革,其派别虽如何复杂,归纳起来,不过是理想精神和写实精神之互相倾轧,亦即是情感理智之上下而已。……近代艺术之巨变,完全是受了社会思潮之影响,因为艺术演化之步骤,是和社会思潮之变迁一致的。例如大卫之作风,是和孟德斯鸠的学说及拿破仑朝代之精神很吻合的;德拉克罗瓦之作风,是和卢梭、夏多布里昂之文学同志趣的;库尔贝的作风,是和孔德实验主义相辉映的;莫奈、雷诺阿的作风,是和罗帝之散文、魏尔伦之诗相近的;塞尚的作风,是和柏格森之哲学有同样的倾向;可见艺术与时代思潮之密切关系了。”⑨可是,林文铮的文章是在1931年才发表,今天我们不知道徐悲鸿是否看过。
尽管欧洲的学院写实主义风格处于非主流艺术的地位,但从1921年到1929年,当时的法国在艺术领域里的激进主义者正在向超现实主义方向进发,毕加索已经离开了他于1907年开始的立体主义进入了新古典主义时期。在德国,1911年臻于顶峰的德国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马尔克(Franz Marc 1880-1916)、马克(August Macke 1887-1914)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托·迪克斯(Otto Dix 1891-1969)和格罗兹(George Grosz 1893-1959)保持了表现主义在形式上的夸张,并正在向着新客观主义的方向演变。有一点是需要特别说明的,那就是欧洲学院式的写实主义风格教育仍旧在法国乃至于欧洲学院里盛行着。这也是为什么徐悲鸿一再坚持学院写实风格的主要依据所在。
为什么徐悲鸿会有这样的艺术观念?我们从“二徐之辩”中可以看出其中的缘由来。在这场争论中,徐悲鸿、徐志摩、李毅士三位艺术家各执己见,言辞激昂。由于他们各人的经历、所处的环境、艺术观点等都有方方面面的差异,在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问题上,自然是产生争议的。1929年的“二徐之辩”是中国西画发展史上第一次公开的不同艺术观点之间的论争,对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美术界的研究氛围,标志着中国西画运动从创作到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场论争奠定了中国西画向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以后诸多艺术观点和主张,都可以在这场论争中找到端绪。
“二徐之辩”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是:对西方部分当代艺术家认同与否?
在同一期上,徐志摩发表了《我也惑》一文来回应徐悲鸿。徐志摩赞扬徐悲鸿的“新艺术观”,同时又称他是个“热情的古道人”:“热情的古道人。就你不轻阿附,不论在人事上或在绘事上的气节与风格言,你不是一个今人。在你的言行的后背,你坚强地保守着你独有的美与德的准绳——这,不论如何,在现代是值得赞美的。”⑩紧接着,徐志摩指明徐悲鸿从来不反对毕加索、凡·高和高更,同时指出徐悲鸿对塞尚、马蒂斯的谩骂过于言重,并把这种谩骂比之于英国当时的批评家罗斯金骂画家惠斯勒。在徐志摩看来,塞尚、马蒂斯的画风被中国画家所效仿,“那是个必然的倾向,固无可喜悦,抱憾却亦无须”。他追述了塞尚进行艺术探索的艰苦历程,然后辩解道:“塞尚在现代画术上正如罗丹在塑术上的影响,早已是不可磨灭、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个人艺术的评价亦已然渐次的确定——却不料在这年上,在中国,尤其是你的见解,悲鸿,还发见到1895年以前巴黎市上的回声,我如何能不诧异,如何能不惑?……话再说回头,假如你只说你不喜欢,甚而厌恶塞尚以及他的同流的作品,那是声明你的品位、个人好恶,我决没有话说。但你却指斥他‘无耻’‘卑鄙’‘商业’的。我为古人辩诬,为艺术批评争身价,不能不告罪饶舌。如其在艺术界也有殉道的志士,塞尚当然是一个。如其近代有名的画家中有到死卖不到钱的,同时金钱的计算从不孱入他纯艺的努力的人,塞尚当然是一个。如其近代画史上有性格孤高,耿介淡泊,完全遗世独立,终身的志愿但求实现他个人独到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人,塞尚当然是一个。换一句话说,如其近代画史上有‘无耻’‘卑鄙’一类字眼最应用不上的一个人,塞尚是那一个人。”
“你说他们的画一小时可作两三幅。这话并不过于失实,凡·高当初穷极时平均每天作画两三幅,每幅平均换得一个法郎的代价——三个法郎足够他一天的面包咖啡与板烟!……你不但亲自见过塞尚的作品,并且据你自己说,见到过三百多幅的多,那在中国竟许没有第二个。你何以偏偏不反对皮加粟(Picasso),不反对凡·高与高更,这见证你并不是一个固执成见的古典派或画院派的人。你品评事物所根据的是,活的感觉,不是死的法则。不杂意气,亦无有成见。……什么叫做一个美术家?除是他凭着绘画的或雕造的形象想要表现他独自感受到的某种性灵的经验?技巧有它的地位,知识也有它的用处,但单凭任何高深的技巧与知识,一个作家不能造作出你我可以承认的纯艺术的作品……”(11)
今天,平心而论,徐悲鸿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渗入了自己的意气,多有成见与固执的成分在里面。相对而言,徐志摩的批判则要平和得多,是一种“同情式”的美术批评。这与两人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联,徐悲鸿是个画家,出自于个人好恶的居多,而作为评论家的徐志摩则更多地以他的生平阅历为基准,持论尚能公正。
“二徐之辩”争论的第二个焦点是:二人的艺术观、教育观大相径庭。
徐志摩的这篇文章在《美展》上连载了两期,徐悲鸿、徐志摩之间的争论还在继续。今天,我们从“二徐之辩”针锋相对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两个人的不同艺术观,不同的艺术主张和信念。他们二人的艺术观念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徐悲鸿的艺术观在他连载两期的《“惑”之不解》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他说:“弟亦深恶痛绝院体式之美术……吾最服大批评家Taine之言,曰艺人之致力,恒分二期,初期悉为真之感觉,逮经验渐丰,则由意造,而真意漓。”(12)徐悲鸿的教育观是反对“当下”的“院体式”的美术教育,而对西方传统的“学院式”美术教育十分推崇,他的艺术观是先“自然之真”,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是一回事,然后再到中国画式的“意境”,即达到“弟对美术之主观,为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13)。他反对“为庸为俗”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但不是全盘否定,如赞同毕加索和高更等。
其实,在徐悲鸿的内心有两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一个是对学院写实风格的认同,另外一个就是对寓言类历史画的宏大叙事的描述。大约是从1927年底,徐悲鸿开始了他的《田横五百士》的创作。在今天我们也认为这是体现徐悲鸿艺术主张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品。徐悲鸿画的布面油画《田横五百士》,取材于《史记》,创作于1928年至1930年,画中站在田横对面的一个穿绿衣的人就是徐悲鸿本人的自画像,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中的第一次把自己画在画面中,另一次是在《汲水图》(2005年由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拍卖过)中。蒋碧微后来曾回忆说:“1928年开始,悲鸿除了去中大教课外,全力创作取材于《史记》田横故事的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也回忆:“父亲作此画时,正是日寇入侵,蒋介石妥协不抵抗,许多人媚敌求荣之时,父亲意在通过田横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歌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所尊崇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以激励广大人民抗击日寇。”徐悲鸿在创作这幅杰作时,任务相当艰巨,画面上的每个人物都有模特儿,他先画了精确的素描稿,然后画到画布上。画面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着重刻画出田横不屈的激情。田横面容肃穆地拱手向岛上的壮士们告别,在那双炯炯的眼睛里没有凄婉、悲伤,而是闪着凝重、坚毅、自信的光芒。壮士中有人沉默,有人忧伤,也有人表示愤怒和反对他离去,那个瘸了腿的人正在急急向前,好像是要阻止田横去雒阳。整鞍待发的马站在一旁,不安地扭动着头颈,浓重的白云沉郁地低垂着。整个画面呈现了强烈的悲剧气氛,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鲜明主题。
完成《田横五百士》之后,徐悲鸿开始了取材于《列子》里关于伯乐推荐人才的《九方皋》的绘制。1931年完成,长351厘米,宽139厘米。他要借助《九方皋》倾吐内心的抑郁,抒发渴望发掘人才的美好意愿。这幅中国画,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位朴实的劳动者——九方皋的形象。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察看面前的那些马,而那匹黑色的雄马仿佛突然见到了知音,它发出快乐的嘶鸣,扬起钢铁般的蹄子,跃跃欲试。徐悲鸿笔下的马都是奔放不羁的野马,从来不戴缰辔,画中黑色的雄马却例外戴着缰辔。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徐悲鸿笑答:“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制。”
在《田横五百士》创作后,徐悲鸿“改良”后的中国画一直就有争议。有人认为他的改良、折中中西艺术的观念有问题,也有人认为他的艺术才气不在中国画领域……似乎徐悲鸿的“中国画”并未能得到中国画界的一致性认可。人们对他的中国画的批评集中在一点:嫁接中西方面的生硬。生硬与生拙不同,生拙是一种品位,而生硬则是一种状态。
徐志摩的艺术观与徐悲鸿恰恰相反,徐志摩在语言形式上是追求艺术美的,但他不是钻到象牙塔中去为艺术而艺术者。他有理想,并把对理想的追求看得高于一切。朱自清曾称徐志摩“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沈从文说,徐的作品给我们的感觉是“动”,文字的动,感情的动,活泼而轻盈。确实,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诗充满了爱、美和自由。《海韵》中的女郎,《黄鹂》中的黄鹂,都体现出这一点。思维想象也如同野马般自由驰骋,无拘无束。
“二徐之辩”争论的第三个焦点是:如何看待西方现代绘画决定着中国的创作方法论的问题?
在杨清磬写的《“惑”后小言》中说得清楚,当时的情况是:“我觉得在此中华民国生活趣味低落之时期,人群智慧与灵感,为毒氛熏染,漫无生息。”正当“二徐之辩”之际,犹如“冷火中爆出个热栗子来”(14)。画家李毅士受到当时西方艺术的影响,一直提倡“美术所注重的是情感,科学所注重的是实象”(15)。李毅士以《我不惑》为题介入到“二徐之辩”中来。他说:“我想悲鸿先生的态度,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换一句话说,是主观的态度。志摩先生的言论,是评论家的口气。把主观抛开了讲话,所以他们双方的话,讲不拢来。”(16)
如同徐悲鸿一样,“和事佬”一般的李毅士代表着当时画家的心声。他说以他研究了二十多年西画的经验来说,对塞尚、马蒂斯的画“实在还有点不懂”,“假若我的儿子要学他们的画风,我简直要把他重重地打一顿”。尽管他承认塞尚、马蒂斯的作品是“十二分的天性流露”,但还是以社会效果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反对他们的画风在中国流行。他说:“如果塞尚和马蒂斯一类的作品在中国有了代价,那么我知道希腊、罗马的古风是再也不会攒入中国的艺术界来。欧洲几百年来的文明,在中国再也没有地位了。”李毅士主张:“欧洲数百年来艺术的根基多少融化了,再把那触目的作风,如塞尚、马蒂斯一类的作品输入中国来。”同时,他对中国美术界的担心,在今天也是如此。他说:“单就现在中国的艺术状况而言,有几个人肯耐心地研究学术?有几个人不愿由一条捷径来换得名利?”(17)
在当时,画家多半都是认为“美术之大道,在追索自然”。即以追求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者居多,那时中国引入西方“当下”流行的美术观念及艺术更多的是来源于日本。无怪乎徐悲鸿发出这样的声音:“今日之称怪杰,作领袖者,能好好写得一只狗否?但在中国今日,只须说不做贼便够了。”(18)在徐悲鸿看来,中国自宋代后写实主义精神的丢失,无疑有太多的缺憾与无奈。他认为徐志摩之所以竭力为塞尚辩护是“激于侠情的义愤”,因为塞尚“奋励一生……含垢忍辱,实能博得人深厚之同情”。他提出自己的写实主张是“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不必先有什么主义,横亘胸中,使为目障”。他认为:“艺Art Plastignt之元素,为form,色次之。……形既不存,何云艺乎?”对西方“当下”美术的拒斥,特别是对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的抵触,虽然不等于说将西方印象派以后的艺术在中国彻底根除,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西方多元化艺术在中国的流行。
“二徐之辩”对于今天而言具有现实意义,由这场争论所引发的问题并没有在停止争论后得以解决。无论徐悲鸿、徐志摩、李毅士三人的观点偏颇与否,他们对待学术问题严肃认真的态度都值得尊重。这也是我们回顾这场论争应该得到的一个启示。徐悲鸿把写实主义作为自己的艺术坐标,并引进了一整套学院式美术教育,在中国画改良方面,冲击了乾嘉以来中国画坛陈陈相因的积习,由“面对古人”转向面对自然,由临摹转向写生,这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成就上来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徐悲鸿一直居于中国美术教育界的高位,他的“独执偏见,一意孤行”,他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褊狭认识和拒绝排斥,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和表现力,限制了美术的多元化发展。我们在肯定徐悲鸿功绩的同时,也不能回避他的不足与局限。当然也不能求全责备,苛求于前辈。我们应当在20世纪美术的整个环境与语境下,对其重新加以认识,或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加以甄别,做到不偏不弃,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因为这在国际美术界并不是先例,如曾经为透纳辩护过的英国大批评家罗斯金,后来也不免错骂了惠斯勒,更何况对欧洲当代艺术抱有成见的徐悲鸿。
注释:
①见陈小蝶在《美展汇刊》上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一文,1929年4月出版。许多大学者的文中说有354件,那只是油画作品的数量。
②原文收在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10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③梁氏认为美术趣味在于:第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第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第三,他界之冥构与蓦进。参见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89—9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④见汪亚尘发表在《晨报》上的《为治现代艺术者进一解》,收录在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101—10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⑤见《惑》一文,收录在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200—201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原文是:“普吕动(Prud'hon)之高妙,安葛尔(Ingres)之华贵,特拉克罗利(Delacroix)之壮丽,毕于维史(Puvis de Chavanne)之伟大,薄奈(Bonnat)、爱耐(Henner)之坚卓敏锐,干连(Carriere)之飘渺虚和,达仰(Dagnan-Bouveret)、白司姜勒班习(Bastien-Lepage)及爱倍尔(Hebert)之精微幽深,谷洛(Corot)之逸韵,倍难尔(Besnard)之浑博,薄特理(Baudry)之清雅,吕特(Rude)之强,骆荡(Rodin)之雄,干尔波(Carpeau)之能,米莱(Millet)之苍莽沉寂,穆耐(Monet)之奇变瑰丽,又沉着茂密如孤而倍(Courbet),诙诡滑稽如陀绵(Daumier),挥洒自如如穆落(Morot),便捷轻利之特茄史(Degas),神秘如穆罗(Moreau),博精动物如排理(Barye)。”
⑥见前引书,第201页。
⑦见前引书,第202页。
⑧为了解决经济危机,1925年底徐悲鸿到了新加坡。1926年2月初,徐悲鸿回国参加了田汉在上海举办的梅花会,展出过油画作品四十余件,在此次展览上,他受到蔡元培、林风眠、郁达夫、郭沫若、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关注,很快徐悲鸿再次到巴黎。在游历了瑞士和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之后,徐悲鸿于1927年8月,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上海。
⑨参见林文铮著:《何为艺术》,第15—25页,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版。
⑩见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第203—21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11)见前引书,第203—211页。
(12)见前引书,第218—219页。
(13)见前引书,第220页。
(14)见前引书,第226页。
(15)见前引书,第113页。
(16)见前引书,第214页。
(17)见前引书,第216—217页。
(18)见前引书,第222页。
标签:徐悲鸿论文; 徐志摩论文; 油画论文; 美术学专业论文; 油画人物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美术论文; 田横五百士论文; 国画论文; 陈小蝶论文; 写实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