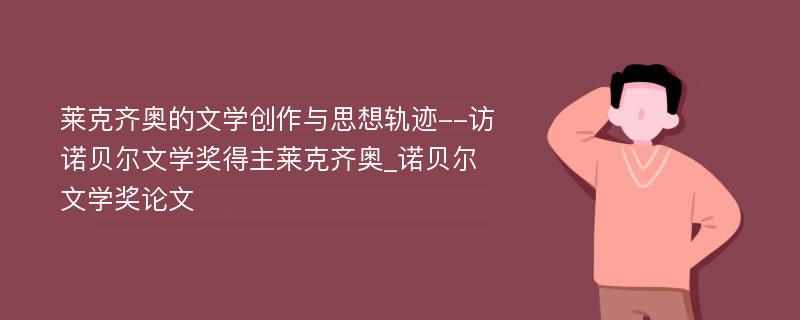
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追踪——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莱论文,诺贝尔论文,文学创作论文,奖得主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11月中下旬的巴黎,天气已经有些冷。今年仿佛格外的阴冷,竟然下起了雪。不过,走在拉丁区,似乎还是像往年一样,还是一样的人群,居多的还是老师和学生。目光还是那样清澈,神情还是那样宁静,全然看不出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慌和不安。也许是读书人的缘故吧,关心的更多的还是精神世界。走进周围的书店,映入眼帘的是11月份陆续开奖的获奖图书。有龚古尔奖、法兰西学院大奖、费米娜奖、雷诺多奖,还有杜拉斯奖,一本本都扎上了红色的腰带,彼此凑在一起,显得格外的热闹。在这些书不远的地方,大多辟有专门的一栏,摆放着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Jean-Made Gustave Le Clezio)的作品,早期的和新近的都有,也有研究他的一些专著。看到他的书,不免想起与他二十多年的交往,更想有机会在巴黎再见上这位老朋友一面。
自他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们通过电邮,通了多封信。生怕打搅他,信每次写得都短短的,我可以想象,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定特别的忙,要忙着跟媒体打交道,跟书商打交道,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可我没有想到,他还是像过去一样,离开了热闹的巴黎,离开了媒体。他写信告诉我,他去了加拿大,又去了英国的一个小地方,那里连互联网几乎都不通。后来他又去了毛里求斯,去接受当地设立的一个文学奖。那个奖是十年前设立的,两年一次,他已经是第二次获奖了。2008年11月26号晚上,他回到巴黎,28日早晨,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住处接到了他的电话,约定下午4点在处于大学街的勒诺克斯旅馆的见面。他说,旅馆很安静,有个不错的酒吧,我们可以好好叙叙,不会被打搅。
在阵阵寒风中,我和南京大学的高方博士,如约到了勒诺克斯旅馆,但不好意思,有些迟到了。走进旅馆,右侧的酒吧里,静静地坐着勒克莱齐奥。他身上穿着羽绒服,围着围巾,下着牛仔裤,脚上穿着运动鞋。见我们进来,他马上起身,迎上前来,跟我们握手问候。
勒克莱齐奥:许钧先生,你好。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外面的天气很冷啊,感觉你们的手都冻冷了。
许钧:勒克莱齐奥先生,这位是南京大学的高方博士,是南京大学的老师。她做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和接受》,里面还特别写到你为《四世同堂》法译本第一卷写的序。我们这次又在巴黎见面,太高兴了。时间过得真快。那次我们在南京见面后,15年过去了。
勒克莱齐奥:是的。真快,记得巴金到法国访问时好像说过:“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美好的人生太短了。”可是你跟以前一样,真的没有变。
许钧:还是变多了。我这次给你带来了一份小礼物,是条领带,是用南京的古老工艺品云锦制作的。
勒克莱齐奥:太谢谢你了。我正需要一条领带呢,很快要去斯德哥尔摩领奖。这条领带太漂亮了,又是古老工艺的,我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一定要戴上它。我也给你带来了你喜欢的东西,是我的一本新书,叫《饥饿的前奏》(Ritournelle de la faim),上面我写了几句话:“许钧先生,谨以此书纪念我们真实的相遇和(因南京下大雪)未成的相见,并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与友谊”。
许钧:今年元月下雪,你到北京参加《乌拉尼亚》(Ourania)的颁奖仪式,因为那场雪灾,我在南京火车站等了六个多小时,一直到凌晨3点多,可最终火车还是没有启程。记得是那天早上8点多钟,我给你打了电话,因为9点钟颁奖仪式就要开始了。我衷心地祝贺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多年前,自从翻译了你的《沙漠》(Désert)。一书后,对你的创作我一直很关注,也很喜欢。三年前,我给瑞典文学院写信推荐时,表达的是我的一种愿望,一种希望,但也是出于我对你创作的喜爱和信念。坦率地说,这次获奖出乎你的预料吗?
勒克莱齐奥:真的非常感谢你在中国为我做的一切。你对我的创作一直很忠诚。这次获奖,实在地说,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的。确实,这几年,文学界一直在议论某某某有获奖的可能,虽然我也在其中,但从有可能到成为现实,机会还是很少的。那天我在巴黎家中,电话响了,我夫人接的,说是找我的,对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通知我获奖了。真是个好消息,我很惊喜。
许钧:我在与你的通信中,已经给你介绍过,你的作品当中先后有7部被翻译、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具体有《沙漠》(又名“沙漠的女儿”,1983年)、《诉讼笔录》(1992年)、《少年心事——梦多与其他的故事》(1992年)、《战争》(1994年)、《流浪的星星》(1999年)、《金鱼》(2001年)和《乌拉尼亚》(2007年)。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在你众多的作品中选择了这7部加以翻译和介绍,对这一选择你怎么看?
勒克莱齐奥:这一选择很好,应该说与我写作发展的情况是相当一致的。当然,在时间顺序上,稍有不同。应该是《诉讼笔录》(Le Procès Verbal)先翻译出来的。关于作品的主要内容,中国翻译家所选择的这些作品比较看重的是我在写作上所追求的社会性介入。比如说《诉讼笔录》一书,是我年轻时写的。写这样一部书,与当时法国的政治与社会状况有关,也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当时法国正经历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为一个青年,随时都有可能被征召入伍。我对自己的前途,对社会的前途,感到迷茫,从心理上说,也有些害怕和不安。写这样一部作品,当然也涉及到我对社会的一些看法。在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政治介入和社会介入。我写的《沙漠》也一样,表明了我对殖民主义的立场,我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至于去年在中国出版的《乌拉尼亚》,这是我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的思考。书中对坎波斯的描写,有理想主义的层面,也有现实的层面,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还是给人希望的。
许钧:最近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法国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主任米歇尔·缪拉教授、巴黎第八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萨莫约教授,还有批评家,比如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评委萨拉娜芙教授,他们对你的创作都比较肯定,意见也相当一致,他们认为你的创作可以明显区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63年到70年代末,第二个时期是从80年代初至今。前期的作品如《诉讼笔录》、《逃遁之书》、《战争》、《洪水》等,这些作品在创作上可以说与法国当时的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情况紧密相连的,是与法兰西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你在小说艺术上有自己的探索,对人与社会的关系有自己的思考。第二个阶段似乎越来越脱离法兰西语境,出现了世界主义的明显特征,表现出了对他者,对有可能消失的文明的关注。像《寻金者》、《奥尼查》、《乌拉尼亚》等。对于创作上的这一分界,你有明确的意识与追求吗?
勒克莱齐奥:对我的创作的这一分界,我看,还是一种表面的理解。实际上,由于我个人的出身和经历,以及接受教育的情况,我一直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是法兰西,我出生在法国,中小学和大学教育都是在法国完成的。另一个世界与我父亲有关,他一直是英国籍。他生活在非洲,可以说是第三世界。我有两个国籍,最早是法国籍和英国籍,后来毛里求斯独立后,英国籍变成了毛里求斯籍。我一直在这两个世界中游走。在毛里求斯英辖时期,我有几个姑妈在那里生活,生活很困难。所以我对处于辉煌地位的法兰西文化的认同也一直有些困难。我的身上,有一部分是属于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的世界。关于创作,正是因为我个人的这些经历,有时会着重于法兰西世界,有时会关注另一个世界,也就是处于主流文明之外的那个世界。我想那是正常的。
许钧:对你的作品,不少批评家认为,你很早就看到了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我也认为你具有某种预见性,看到了当代社会中人们一直没有看到,甚至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比如在45年前,你就在《诉讼笔录》中提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边缘性问题,还有对于弱势文明的关注。这几天,具体说就在11月25号到27号,法兰西公学院举办了有关莱维·斯特劳斯及其作品的研讨会。长期以来,莱维·斯特劳斯(Lévy Strauss)先生一直在关注世界上有可能消失、失落的文明,呼吁保护那些古老的文明,给这些文明以平等的地位。你的作品也许是对莱维·斯特劳斯所代表的这一人文主义思潮的另一种体现。你是否认同他对他者以及其他文明的关注?
勒克莱齐奥:是的。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对莱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和思想很感兴趣。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我们之间关系很好,我们经常见面。每次见面,我都能诧异地感觉到他对西方文明的那种有所保留的看法。他当然认为西方文明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认为拉美印地安文明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古老的文明没有表达自身的权力。在莱维·斯特劳斯开始研究这些古老的文明时,他就有了明确的战斗的姿态,要关心这些文明,让这些文明有同等的表达自身的权力,而且以不同的形式,比如书写的形式、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这些文明的历史与现状。
许钧:你的创作也表现了这些意识,不过他是在思想研究层面,你是在诗学创作层面。
勒克莱齐奥: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我非常愿意跟他一起交谈,因为我们在一起谈的不是人类学,而是文学。他是个对文学非常敏感,对文学很有修养的人。对法国历史上的一些文学家,特别是关注自然的文学家,比如说卢梭,他很了解。所以跟他一起谈文学,非常愉快。不过,即使我跟他之间没有见面,我跟他在思想上也是相通的,与他的精神交流是自发的。就我而言,我对西方文明之外的那些文明,那些不同的文明,一直就怀有一种兴趣。这种兴趣与关注,也许与我父亲有关。他在非洲生活了很长时间,是在尼日利亚。
许钧:你小的时候,好像是7岁的时候,离开尼斯去找过他。在去非洲的船上,你还用小学生的作业本写过小说,是这样吗?
勒克莱齐奥:我到尼日利亚去过,跟我父亲生活过两年,因为父亲是英国籍,战争时期不能回法国,不然维希的贝当政府会抓他。我小的时候确实尝试过写过一些东西。那次在船上写的东西算是我最早的创作经历吧。
许钧:这次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跟中国不少记者谈起,你的创作经历很长,足足有45年了。在你的创作经历中,你始终在探索,探索小说的艺术,试图通过小说的艺术去揭示人的存在中难以看清或难以意识到的东西,进而加以质疑。我的这种看法不知是不是对的?
勒克莱齐奥:谈到小说的艺术,这确实太复杂了。小说是什么?这是很难用几句话来界定清楚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文学界的焦点在于探索或创造小说的新的可能性。那个时期,大家都在探讨小说的艺术,但我看到了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走上了形式主义的极端,就会导致对形式的过分追求,内容反而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在法国,对小说的艺术的探索不太一样了,也比较自由了。没有谁会规定小说应该怎么写。小说本身也比较自由了。在小说中什么都可以写,也可以采取任何一种形式去写,古典的形式也好,现代的形式也好。就小说的形式的探索而言,再也比不过乔伊斯,他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已经到了极致。乔伊斯对小说的艺术的探索,包括新小说派,都有贡献,他们都走得很远,我们总不能只是模仿吧。过去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已经到了极端了。现在我们所做的比较平凡,就小说的形式的创造而言,我们也比较现实了,不像过去那些年代那么雄心勃勃。
许钧:在你的小说创作中,我发现你用的词很简洁,很有力量,有时特别具有讽刺的力量。你是否有明确的追求?
勒克莱齐奥:是的。词语的使用,表明了一种言语的选择。词语是对现实的逼近,我认为每个作家对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都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对语言的使用,我们不要太有野心,认为语言会直接表现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作家要善于抓住词语,要谨慎用词。用到恰到好处,就有了力量。
许钧:在写作中,往往有一种倾向,词不达意,达不到表达自身的意图。而你在创作中,特别注意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想表达的东西。
勒克莱齐奥:上次在北京,我和董强与几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在一起,我们谈到了中国语言中经常使用的艺术,就是双关语。那天谈了不少,一句话有表面的意思,也有深层的涵义,领会了特别让人好笑。类似的双关语,我觉得在法语中不是特别多,但是很有意思。确实,用词要谨慎,要注意讽刺的力量。
许钧:在你的作品中,这种讽刺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你早期的《诉讼笔录》中,主人公亚当被当作疯子,可在你的笔下,他说的话、用的词,特别准确、科学。而那个医学院的大学生,却戴着一副大墨镜,说明他看人看事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是歪曲的,不是科学的。这是一种反讽。但在你最近的作品《乌拉尼亚》中,你用的词语好像特别具有诗意。这是一种追求,还是因为你年纪大了,有了变化?
勒克莱齐奥:这是一种追求。我小的时候就梦想创造某种语言,以此为乐,用诗一样的语言去描写一个不存在的世界。不过在《乌拉尼亚》中,有两个故事,比如写坎波斯学院时,用的是讽刺性的语言。这部小说中,实际上有现实的成分。我知道历史上,在巴西,有过类似这样的坎波斯学院,当然名字不一样。我是想写出那些人类学家的处境,由于他们自身的缺陷,所有的努力都归于了失败。两个故事,一个写的是理想的学院,一个写的是理想的城市。结果两个理想都没有实现,都有问题。
许钧:人都有理想,但现实往往残酷,这也许就是人类面临的尴尬境地吧。在你的创作中,我发现你对人与传统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关注。在《战争》一书中,你对现代社会,对消费社会有可能引起的问题看得很透。
勒克莱齐奥:关于人与自然,我想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传统对此问题比较敏感。他们对自然很关注,而法兰西的文学传统,对精神,对逻辑比较看重,也是比较关注城市的一种文学。我说的是法语文学。我小的时候读过一些撒克逊传统的文学作品,像吉卜林的一些作品。这位作家把自然世界引入到文学作品中,去探索人类有过的一种神话式的过去。人类的存在不是仅仅由城市文化构成的。人类的过去,人类的神话阶段是与自然力量以及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我在过去读的那些作品,对我是很重要的。
许钧:这些作品,给你的创作起到了影响作用,留下了痕迹,是吗?
勒克莱齐奥:是的。杰克·伦敦也一样,他是一个青年读者很喜欢的作家,他的作品写得很深刻。
许钧:你在写作《诉讼笔录》时,在前言中你用了一个词,叫做“假冒的现实主义”。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你的作品中,你揭示了许多尖锐的现实的问题,如殖民主义问题、消费主义问题、人被物化的问题,等等。可有趣的是,你用了一种语言,可称之为假冒的现实主义的语言。试图用另一种笔触来揭示现实中人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这一点对我们研究者而言,很值得探讨。
勒克莱齐奥:问题很简单,因为现实主义是不够的,心理分析也不够。都不足以解释全部现实,不足以去揭示人类存在的全部现实。总有一部分我们难以捕捉到。即使是逻辑分析,现实主义的描写,都无法做到。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莱维·斯特劳斯我很感兴趣。莱维·斯特劳斯关注人类所有的文明和知识,而不是只关注城市文明。比如他特别关注自然的层面。人类一旦进入了自然的层面,就会发现人对社会,对人的存在的某种认识是有偏差的。有必要融合各种知识和利用各种手段去认识现实。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有很多缺陷,其缺陷是明显的。比如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用再现实的手法,也难以揭示其不言而明的实在性。
许钧:你说的这一切,可以说很清楚地对你的创作有了某种说明。像《诉讼笔录》这部小说,很难用一种形式进行界定。读前几章,看到亚当给米歇尔写的信,读者会以为是部情感小说,在后面,看到医生对亚当的心理分析,又可能会以为是部心理分析小说。你试图去打破各种界限,调动各种可能性,去揭示你想揭示的现实。
勒克莱齐奥:不管怎么说,小说的界限,不能总是处于讲故事的层面,不能总是限于对细节的描写。比如爱情,有各种形式,如果看小说,只想看到爱情故事,看到对环境的描写,那是不够的,那就看不到人的存在的各个隐秘的层面了。
许钧:你在创造中不断地变换手法,在不断的自我摧毁与决裂中不断形成新的手法。实际上,你的小说往往是导向一种新的可能性,小说的结尾都不是一种定局。
勒克莱齐奥:是的。我的小说最终的结局都有可能是另一部小说的开始。
许钧:我在《乌拉尼亚》中发现,你的每一章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没有结束的,而是成了下一章的开始。你的小说写作是开放式的,同时对人类存在的质询也是开放性的。两者之间是互为关照的。
勒克莱齐奥:我在《乌拉尼亚》中采取的那种章尾和章首相互衔接的方法,参考的是一个墨西哥的历史学家的写作方法,他的名字叫路易斯·贡扎拉孜(Louis Gonzalaz),我不知道他的作品在中国有没有被翻译。他是微型历史学派的创始者,他有一部书在法国被翻译过来,题目直接翻译过来,叫《空中的村庄》。可翻译成法文后,题目变成了《孤独的障碍》。他以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为基点,以山区的这个小村庄的历史来体现人类的历史。那是一个乡村,居住的是农民,是他的家乡。他善于叙述历史,小中见大。每一章的章尾作为下一章起始的写法,我是学他的,所以我把这本书题献给了他,向他致敬。当然,与我想讲述的故事,形式上也是一致的。因为故事本身也是没有结尾的。
许钧:关于你的近作,也就是刚刚出版的那本《饥饿的前奏》,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前的那个时期,人们感觉到了危险的迫近,但谁也无法阻止。这是《寻金者》和《奥尼查》等书的继续吗?
勒克莱齐奥:这几部书之间,有着相似性。我写这部书,是因为我的母亲。我母亲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当然比小说的主人公大几岁。我觉得当时的战争就像是人发烧,温度不断升高,谁也阻止不了。在那段历史中,法西斯主义不断升温,极右势力不断升温,在欧洲普遍都有。不仅在德国,在西班牙,在意大利都有,那是非常可怖的。我母亲去过西班牙,去过意大利,感觉到战争不可避免。她到意大利去,感到那里的制度是独裁。在街上走,警察让你走左行道,你绝对不可以走右行道。她看到这种状态,看到了独裁的制度,认为就是这种独裁最终会导致战争。我查阅了当时的一些报刊资料,一些文献,想尽量弄清楚为什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许钧:今天这个时代有了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现代社会过度物质化,过度的消费主义,人的信任发生了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人类遭受了惩罚,像这次金融危机。你的这部小说是否也是影射这一形式的战争。
勒克莱齐奥:是的。人与人之间不信任,难以交流,相互提防,是消费社会难以避免的一些结果,还有对金钱的贪婪,有危机存在。这些情况,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洲有相似的地方,是很严重的。我在书中也谈了我家族的历史,我们家就是在那个时候破产的。我们家原来是个有产者,可在那个时代全部都失去了。当然,战争也不是绝境,人类总有绝处逢生的希望。在我们社会目前所处的环境中,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乐观的解决方法的。
许钧:目前你是否已经开始创作别的作品了?
勒克莱齐奥:是的。上一部没有写完,新的作品就已经开始写了。这部新作品,我想借鉴乔伊斯在《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们守灵》中采取的一些手法。要想写的是殖民帝国如何坍塌的历史。殖民帝国是如何坍塌的,我一直都想弄明白。过去的那些殖民强国,都依恋过去辉煌的历史,但它们现在所能维持的,只是一种强大的外表而已。所有理想的东西都消失了。
许钧:是的。不落的太阳坠落了。可对于这样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你为什么要采用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手法呢?
勒克莱齐奥:我不愿写历史小说。我们要反思过去,一方面要考虑我们所继承的那段历史,另一方面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的处境。要试着用现代的手法去写过去。
许钧:最后想提一个问题,与你的创作无关。你是否读过一些中国文学作品。
勒克莱齐奥:我读过,比如《四世同堂》。我很喜欢老舍的作品。他的作品的法文本,我几乎都读过,有的英译本我也读过。他有一些中短篇,对自然因素的描写,我觉得很有意思。对老北京的描写,也让我喜欢。虽然现在的北京跟过去的北京不太一样了。他写作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但也有其他的笔触,像超自然的神秘的因素等。比如《正红旗下》,比如《月牙儿》等。许多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社会,实际上不完全是。对于中国的古典作品在法国的传播,艾田蒲(René Etiemble)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有些极端,但他主持的《认识东方》丛书,组织翻译了中国的四大名著,有的我读过。不过我对中国当代作品了解很少,几乎没有读过。我承认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知道的不多。
许钧:再过十几天,你就要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了,是12月10号吧。你在颁奖仪式上的演讲写好了吗?是用法语写的吗?
勒克莱齐奥:写好了,是用法语写的。
许钧:长吗?
勒克莱齐奥:要讲一个小时一刻钟左右,比较长,15到20页呢。我届时会把演讲词发给你。
许钧:谢谢你。今天谈的非常愉快。真诚地邀请你明年四月份去南京。现在我想请你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
勒克莱齐奥:好的,我明年一定去南京。我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吧。“致中国读者:在此我要对你们说,我对中国一直怀有友好的情谊和兴趣,我也希望能不断增进我们国家之间的友好联系。我希望经常去中国,在中华文化中发现给人以希望的新的理由所在,让世上的人们看到相互理解和进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勒克莱齐奥,2008年11月28日。”
标签:诺贝尔文学奖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诺贝尔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