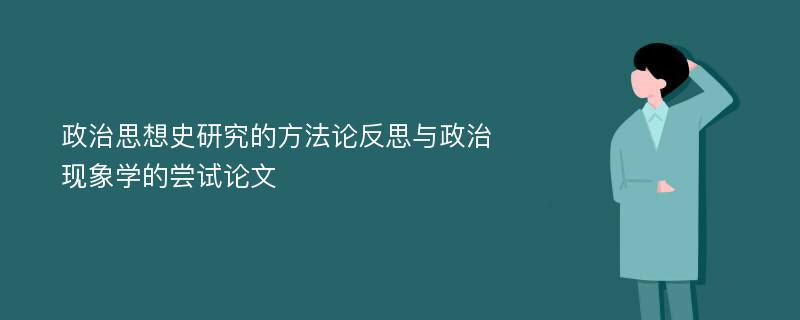
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与政治现象学的尝试
刘训练
(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300387)
目前国内学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及偏重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一种“依附性研究”或“依傍性研究”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该领域内的主要议题都是由国外学术界设定的。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在相关学科中的边缘性地位,这种状态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可以预见这种状态还将持续一段时期。
就西方学术界本身而言,在政治思想史领域,自“二战”以来,方法论上的探索层出不穷,流派纷呈,目前已经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施特劳斯学派、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三家稳居主导,知识社会学、观念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等传统思想史研究进路继续推陈出新,新文化史、话语分析等新兴交叉学科方法不断渗透与迁移;同时,晚近也出现了一种各家各派在方法论上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国外学术界在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上的进展无疑也影响了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对国外相关争论的介绍、述评层面,这正是“依附性研究”的一种反映:学术积淀不足、理论准备不够,自然谈不上对这些方法论的消化、吸收,并将其运用于具体的研究实践;相比之下,将这些方法运用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倒是有些成效的。笔者以下想就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状,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的观察。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除了极少数国别的、断代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对具体思想家(及其主要著作)和理论专题的研究。对于政治思想家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从柏拉图到密尔那十几位伟大的思想家展开的,而且多数以他们的核心文本为中心,少数研究则在文本之外也关注了其社会—政治“语境”;与此相应,在这些研究中,哲学范式多于历史学范式。
结合教材中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的实验,对盖革-弥勒计数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进行简要介绍。盖革-弥勒计数器由高压电源、盖革-弥勒计数管(G-M管)以及定标器组成。其中,高压电源为计数管提供电压;定标器记录由计数管输出的脉冲;G-M管根据其外形可分为钟罩型和圆柱型,内部充有惰性气体。
关于理论专题(也就是特定主题),研究范围则要宽广一些,有些集中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流派(ideologies),有些集中于正义、自由、平等、共同体等价值理念(values and principles),有些集中于政体、民主、宪政、分权等制度安排(systems and structures),还有些则集中于社会契约、自然法(自然权利)、国家理性、乌托邦等“单元观念”(unit ideas)。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方面,我们发现,现有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这样的偏向(这些偏向当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重视政治史、哲学史,忽视社会生活史、文化史;重视“大传统”、精英文化、经典文本,忽视“小传统”、大众文化、普通文本和图像等非文字的文本;重视人的理性因素,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情感和激情;重观念、哲理甚于政制、习俗;重逻辑推导、抽象思辨甚于情感引导、形象直观;重视社会结构、阶级和派系斗争等宏观因素,忽视社会机制、心理机制等中观和微观因素,等等。① 当然,笔者的这些观察可能也没有什么新意。对于思想史研究的某些一般性问题,葛兆光先生在他十几年前的《思想史的写法》《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著作中就有所批评和反思。但我们不得不说,到目前为止这种状况起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
这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自然有着无可置疑的正当性、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笔者自己就一直在主要从事这样的研究),但它们很容易导致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技术化和分工过细等问题(笔者自己长期以来就坚持专业化、技术化的学术旨趣和学术追求),特别是在教学中,我们发现,这样的研究很难激发青年学生对政治学的兴趣。换言之,带有这些偏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很可能无助于我们对现实中各种政治现象的理解,因而也就无从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世界”本身。② 以笔者粗浅的观察,国内偏重于英美分析进路的政治哲学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的分析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自由而平等的人,其主要的论证方法是讲理和逻辑论证。这个出发点和论证方法本身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它们未必有助于我们对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因为就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体验而言,大多数人并不接受这样的出发点和前提,他们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也不是讲理。
当然,在思考与探索的过程中,笔者也确实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影响。比如,徐贲教授关于公共伦理与社会记忆的一系列研究和评论② 徐贲教授曾经向我们推荐“另一类讨论公共伦理问题的书”:博克(Sissela Bok)的《撒谎》(Lying )和《秘密》(Secrets ),霍耐特(Axel Honneth)的《争取承认:社会冲突的道德规则》(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古丁(Robert E.Goodin)的《保护易受伤害者》(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 )(参见刘小磊主编:《我书架上的神明续编:66位学者谈影响他们人生的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就让笔者注意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些社会伦理现象始终伴随着人类,而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也观察到了这些现象并有所阐述,但由于它们在人为划定的当代学科体系中并不属于“政治学”,所以无法在政治学的视野中得到系统的建构,其重要性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些现象包括:尊严、羞耻、恐惧、荣誉、忠诚、关爱、同情、信任、怨恨、野心、嫉妒、伪善、脆弱性,等等。这些现象都关乎人类最基本的心理、情感和行为机制,对此缺乏关注的政治学理论是不可能有生命力和解释力的。
其次,既然荣誉和荣耀是一种普遍的人类需求,那么,无论哪种文化,无论哪个民族,无论在哪个时期,都会有其自身的荣誉供给机制;当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对待荣誉、荣耀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和变化。
原料:PVDF为Solvay公司出品。硝酸锌六水合物(Zn(NO3)2·6H2O)、2-甲基咪唑(HmIM)、甲醇(MeOH)、聚乙烯吡咯烷酮(PVP,MW=24 000)、N,N-二甲基乙酰胺(DMAc)以及聚乙二醇(PEG, 2 000, 4 000, 6 000, 10 000 和 20 000)均由 Adamas 公司购得。牛血清蛋白(BSA,MW=68 000)和卵清蛋白(OVA,MW=44 000)由南京奥多福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得。所用去离子水(DI)产自实验室自制二级反渗透装置。
再次,荣誉、荣耀往往与德性问题纠缠在一起。从理论上说,人们获得荣誉或荣耀应当是基于其优良美善的内在特质、品性及其行为表现(道德德性、道德价值),而荣誉是对美德的“回报”或“奖赏”;但从社会供给来看,共同体所嘉奖的是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在具体的政治情境中又会有不同群体授予的荣誉,后者依据的是政治德性甚至个别群体的利益或看法;再考虑到人类行为(动机)的隐蔽性与复杂性,所以必然会产生德性与荣誉、荣耀的一致性和分离的问题。
例如,关于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研究肯定绕不开对雅典民主的认识和评价,以往我们只关注当时知识精英的反应,但他们大多持反民主的立场。结果,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名色诺芬的“老寡头”、修昔底德等人的反民主论证和对雅典民主的负面描述,虽然不排除他们的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包含了一些赞成民主的记述和民主派的观念。雅典也许没有民主派的理论家,但如果没有民众的普遍支持以及它在制度上的优点,雅典民主能够存续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雅典的民主,就必须借助于经典文本之外的材料(包括考古材料、戏剧作品,等等)来重构民主的论证。特别是,以往我们喜欢追随古代知识精英的观点,认为陶片放逐法是雅典民主的一大污点。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晏绍祥老师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就对陶片放逐法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依据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它的作用,“从陶片放逐法有助于雅典政治稳定的角度看,它符合克里斯提尼的精神,也实现了他改革的期望,是民主政治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① 晏绍祥:《雅典陶片放逐法考辨》,《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
由此,笔者进一步想到,著名政治理论家埃尔斯特(JonElster)对“机制”(mechanism)的强调以及他在代表作《心灵的炼金术》中对羞耻、嫉妒、荣誉等社会情感的研究可以成为我们所谓“政治现象学”的理论来源或者研究范本。① 有论者曾经指出,埃尔斯特在哲学层次上受到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影响,参见埃尔斯特:《社会黏合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者序第3页。 研究对象自不必说,在研究方法方面,正如该书封底的评论者所言:“从社会心理学、历史学、博弈论、神经科学、小说、哲学等不同的领域吸收灵感来源”;具体到研究材料上,埃尔斯特在这本书中不但使用了亚里士多德、法国道德学家以及文学作品(戏剧与小说)等“文本”,还分析了古代希腊、中世纪冰岛的世仇、现代欧洲早期的决斗、地中海地区的族间仇杀等历史情境。② 埃尔斯特:《心灵的炼金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参见郭忠华对埃尔斯特的访谈:《社会科学如何对社会现象作出有效解释:关于“机制”“工具箱”问题的对话》,《南国学术》2014年第1期。
基于以上的反思和思考,接下来笔者就以自己近些年来一直在关注的“荣誉—荣耀”议题为例,谈一谈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可能的拓展——这些到底能不能算作“政治现象学”的研究实例,笔者并没有把握,权且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同仁。
生物源于生活,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生活中各个环节都与生物息息相关。因此,学好生物课程对我们的生活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生活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局限于课本上的生物知识,要善于发现身边的生物内容,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结合,将生物理论内容充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更加全面地了解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
在《诗与批评》文末,闻一多说:“但是,谁是批评家呢?我不知道。”[15]223此是反语,他不仅以文学史家自居,还是以批评家自居的。至少,在1941年左右,闻一多已经整理了大量的唐代诗歌和诗人资料。他曾对寄寓在他家搜集毕业论文资料的郑临川说:“这是我多年抄集下来关于唐代诗人的资料,好些是经过整理的。”[11]5闻一多有意做诗的批评家,而且致力于编制“技术高、技术精”[15]222的选本,郑临川说:“当我替先生抄写整理《唐诗大系》选诗的篇目时,先生曾告诉我,这些篇目每年要审定增损一次,可见先生对唐诗的研究仍然没有中断。”[11]224
首先,荣誉、荣耀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因而也是人类行为最基本的动机之一。④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散见其主要著作各处),激发人类行为的欲求主要有三种:安全(生命)、财产(财富)、名誉(荣耀)。斯宾诺莎则说:“那些在生活中最常见,并且由人们的行为所表明,被当作是最高幸福的东西,归纳起来,大约不外三项:财富、荣誉、感官快乐”(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必然需要来自他人和同伴的肯定、赞赏与褒奖;相比较而言,出类拔萃的人比普通人更关注荣耀而非财富,但普通人也要寻求和维护最基本的名誉(换言之就是“体面”)。如果据此做进一步区分的话,一般意义上的名誉、荣誉与荣耀的差异主要在于强度和稀缺程度,概言之,只有卓越的人、“大人物”才会追求更高的荣誉和荣耀。在民主社会中,荣誉向所有人开放,但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有价值的荣誉和荣耀;否则的话,它就不足以成为一种激励。
香港理工大学曾乃明博士在《社会工作者本身的道德情怀》中对“价值”有深刻的反思。他提到,当西方社会工作者谈到“价值”时,往往会将其放在理性的层面,着重将“价值”转化成专业的守则。专业守则好像教条一样,无疑起规范作用,但这套专业守则缺乏一份生命的力量去支撑我们每日在复杂的一线工作里做出道德的实践。他认为社会工作的价值牵扯的层面不只是理性上的理解,更牵涉到感性的投入、渴慕、追求和自我约束;要求自身在行动上尽我所能让这种价值在实践里呈现出来。
最高的荣誉和荣耀是不朽的名声(immortalreputation),从哲学上说,对不朽名声的追求是人类对抗死亡的一种心理机制。正是对死亡和死后沉寂无名的恐惧、对通过后人的追忆来延长有限生命的渴慕,激发了人们寻求永久的名声与荣耀。⑤ “自然界不但以某种方法赋予人类以一定程度的永生,而且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培植了一种达到永生的渴望,我们用我们可能有的每种方法来表示这种渴望。这种渴望的一种表示是希求名誉和不希望死后默默无闻”(柏拉图:《法律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毫无疑问,荣誉和荣耀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现象,在道德与政治领域发挥着独特的心理作用。③ 荣誉(honor/honour,名誉)、荣耀(glory)、名望(reputation,声望)、名声(fame)这些概念在具体的语境中有程度不一的差异,但总体上又可以作为同义或近义的概念并列使用。 现在就让我们对此做一些初步的“现象学还原”。
总体上说,对荣誉和荣耀的追求是一种正面的价值,尤其是和对财富的追求相比更是如此;但这里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对荣誉的过分追求以及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会使之成为一种负面的价值,“雄心”与“野心”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表述。同时,由于荣誉、荣耀的稀缺性以及它在根本上还是一种比较性的心理感受,所以,它还会引发嫉妒等问题,使之走向反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拓展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推进我们对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的理解呢?首先,在研究对象上,我们可以扩展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以古典政治思想为例——不再局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及其经典文本,不再局限于政体这些传统的议题;也不必限于伊索克拉底之类不那么重要的思想家和演说词、诗歌、戏剧之类更间接但更生动的文本,甚至也不必限于各种制度形态(比如,陶片放逐法、作为教育制度的“埃菲比亚”和“阿高盖”),而是可以把建筑与空间(比如,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仪式与活动(比如,赛会、节庆、葬礼、会饮)、人物与事件(比如,阿尔喀比亚德、哈尔莫狄欧斯和阿里斯托盖通刺杀僭主)等都纳入研究对象。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该综合运用哲学人类学、政治心理学、道德心理学、新文化史、图像研究(图像历史学)、文化研究、话语分析等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多种方法,对上述对象展开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
就荣誉的供给而言,一方面,荣誉、荣耀与金钱、财富构成对照(希罗多德《历史》记载,波斯人曾经惊叹于希腊人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相互竞赛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荣誉”);但另一方面,荣誉、荣耀的供给也会出现物化的问题,在精神满足之外往往还会伴随着物质奖赏(比如,古希腊“泛希腊赛会”的获胜者只有“桂冠”的象征性奖励,但在返回家乡之后可以得到城邦给予的各种丰厚的物质奖励)。在现实政治中,荣誉通常还会物化为权力和官职,① 参见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8-120页。 最终可能导致荣誉的异化问题——在此情况下,对荣誉的追求与对权力(甚至财富)的追求融为一体,都是出于野心。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一个由多方面指标组成的复杂体系,指标的选取应该能够适当反映各地区在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状况,并能满足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对比分析的需要。为了保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在制定过程中遵循科学性、综合性、代表性、可操作性、时间序列数据可比性等原则。
由此,政治史上,从来不乏以“面包与马戏”的方式寻求民粹式独裁并大获成功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思想史上,众多的思想家一方面从理论上不断重申德性对于荣誉的优先性,② 就像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对于我们所追求的善来说,荣誉显得太肤浅。因为荣誉取决于授予者而不是取决于接受者,而我们的直觉是,善是一个人的属己的、不易被拿走的东西。此外,人们追求荣誉似乎是为确证自己的优点,至少是,他们寻求从有智慧的人和认识他们的人那里得到荣誉,并且是因德性而得到荣誉。这就表明,德性在爱活动的人们看来是比荣誉更大的善,甚至还可以假定它比荣誉更加是政治的生活的目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页)。 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制度安排上以原则、目的与方式来约束和引导对荣誉、荣耀的追求。③ 马基雅维利提出,应当研究共和国的公民“凭以获得声望的方式”:“公共的方式是指,一个人为了公共的利益,提出好的建议、做出更好的行动,从而取得声望。……如果那些名声是通过前述的另一种方式即私人的途径取得的,那么它们就极其危险而且完全有害”(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535-536页)。
问题是,这样的拓展能否命名为“政治现象学”呢?对此,笔者没有任何确信和底气。事实上,由于受自身学力的限制,笔者无意将作为一种哲学运动的现象学基本方法运用于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彭斌教授对此可能更加关注),也没有援引国外目前已经出现的以“PoliticalPhenomenology”为名的学术资源(王海洲教授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才真正配得上政治现象学之名,而笔者的上述设想以及下面的一点尝试多少有些闭门造车的意思。
既然荣誉、荣耀是如此普遍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那么,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社会—政治思想家以及文学家、艺术家就不可能忽视它们,从而产生了大量关于它们的哲学思考与文艺作品。如果从这一议题出发,重新审视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论域,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对某个历史时期西方政治文化的整体考察,还是对某个思想家及其特定议题的具体研究,都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视角、观点和看法,增进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认知。以下我们扼要地回顾一下荣誉、荣耀和德性议题在西方古典政治文明中的生成与发展。
自尼采和布克哈特以来,古史学界越来越认识到,“赛会(agon)精神”对于古希腊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所谓“赛会”不仅包括体育比赛、军事训练和战争等身体上的赛会,而且还包括政治演说、法庭诉讼、哲学论辩、诗歌和戏剧比赛等精神或思想上的赛会。就像芬利指出的,“希腊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赛会,其精神的根源就是他们‘对荣誉的无比热爱’(philotimia)”;并且,赛会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赛会的目的就是揭示和认可“德性”(arete),“arete是agon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能”。④ 参见王大庆:《古代希腊赛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相关引文转引自该书第8、30页。 这一视角对于我们理解古希腊的政治文化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我们确实看到了相关研究成果的产生:既有探讨赛会与古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有将赛会所展现的“表演文化”与雅典民主联系起来的研究;后者甚至成为雅典民主研究的新进展,“向观念上更为统一的方法更进了一步”。⑤ 参见JohannP.Arnason,Peter Murphyeds.,Agon,Logos,Polis:The Greek Achievement and Its After math,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2001;Simon Goldhill,Robin Osborne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Athenian Democra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对“表演文化”在推动雅典民主研究中的作用的评论,参见法伦格:《古希腊的公民与自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3页。
在更微观的层面,我们可以认为,古希腊的政治学是一种德性政治学,对公民的德性教育在其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以往对古希腊政治哲学的研究,要么更加关注政体问题而非德性问题,要么更加关注德性的哲学维度而非其心理学—政治学维度,而荣誉—荣耀议题的引入则可以让我们对公民德性的培养与教育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只袜子何以由“臭”而“香”?这要追究大诗人刘禹锡,于《马嵬行》中一改白乐天、杜甫和温庭筠众诗人“天子赐缢死”成论,持“贵人饮金屑”说,横生“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这一枝节。由是,这只“凌波袜”,身价陡涨,一因着太真妃“玉体”而贵;一因籍曹子建《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而名。
从最强的意义上说,公民德性就是公民(包括政治家和普通公民)为了公共利益(也就是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从稍弱的意义上说,公民德性就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既然人们天然具有为了私人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的“腐化”倾向,那么就公民的德性教育而言,最稳妥的办法莫过于首先寻求连接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桥梁来解决公民德性的动机不足难题;在古希腊哲人关于公民德性教育之心理基础与行为机制的阐述中,荣誉与荣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限于篇幅,我们这里跳过引文和论证,直接转向结论。古希腊哲人在坚持德性本身之价值与优先性的同时,从未否认荣誉对德性培养的激励作用。当然,既然荣誉在他们看来只具有次生的工具性价值(经典的比喻是“德性的影子”),那么,它就只有在服从、服务于德性的时候才是正当的。就像有学者所评论的:“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确实考虑和利用过荣誉感;他似乎看到了荣誉感是无法根除的人性,而且容纳了这样的荣誉感”,但“荣誉感需要批判和细心引导,以避免它产生破坏力”。像阿尔喀比亚德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私化荣誉感”就是有害的。① 路德维希:《爱欲与城邦:希腊政治理论中的欲望和共同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405、406 页。
如果说德性与荣誉、荣耀之间的难题在古希腊哲人这里只是以哲学论辩的方式展现的话,那么,对于“时刻追求荣耀、渴望赞美,超过其他一切民族”的罗马人来说,它则以更加政治的方式再现了二者之间的张力,特别是在西塞罗这个西方历史上“最为贪求荣耀的政治家”身上,这种张力在思想与政治两个维度上都得以凸显——笔者已经在一项题为“在德性与荣耀之间”的关于西塞罗政治思想和罗马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揭示了这一点。在此项研究中,笔者便充分使用了古代历史学家的记载与现代历史学家的相关研究来说明罗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荣耀和德性的供给方式,同时有意识地以西塞罗的《论义务》为中心,而没有像以往的研究那样只关注他的《论共和国》和《论法律》,并尽量征引他的演说和书信,也算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吧。
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兴起,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一直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德性概念本身大致经历了一种从古典时代的道德德性、中世纪的宗教德性向现代的政治德性、社会德性的演化,而世俗化的荣誉和荣耀概念在后基督教时代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德性与荣誉二者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动。甚至到了21世纪,一种旨在重申荣誉以便为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下的个体能动性提供激励和鼓舞的思路还能进入政治理论家的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这就充分说明,作为人类行为基本动力机制之一的荣誉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研究。
标签:古希腊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