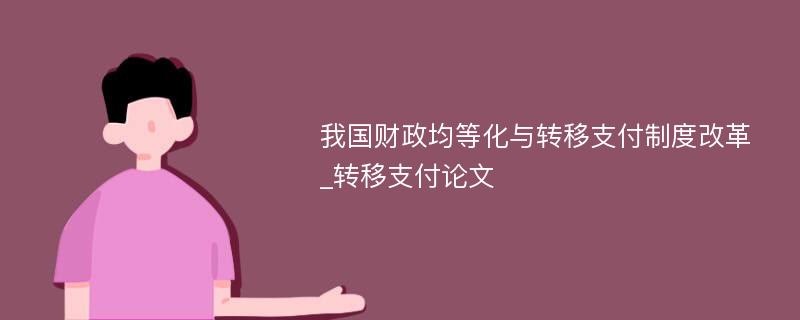
中国的财政均等化与转移支付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等论文,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转移支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1/4个世纪中,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成长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准,使绝大多数中国人迅速摆脱了贫困并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与此同时,在确保超过全球人口总量1/5的人口公平分享日益增大的“经济蛋糕”和“公共服务蛋糕”方面,仍需克服一系列困难和障碍,并把财政均等置于政府政策议程的优先位置。
一、规模庞大且迅速增长的政府间转移支付
最近10余年来,中国的GDP以令人晕眩的速度(9%—10%)增长,而政府财政收支更是以大约相当于GDP增速两倍的超高速度增长。考虑到这段时间里物价总水平相对稳定,经济崛起带来的财政崛起,尤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规模也在迅速崛起。根据预算安排,2006年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补助增加到12697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22222亿元的57%;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额29600亿元的43%,相对规模之大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只有日本等极少数国家能够相提并论)。在联邦制国家中,联邦对州与地方的转移支付通常不超过联邦支出的1/3,但在中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占中央支出的比重高得多(2005年为57%)。2005年,美国联邦、州与地方三级政府的总支出为38,59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支出约为24,720亿美元,联邦政府对州与地方政府的补助总额为4,260亿美元,约占联邦政府支出的17%,约占州与地方支出总额的31%,①分别比中国同期低40和14个百分点。事实上,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相对规模也要大得多。
中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相对规模之所以远大于其他国家,与公共支出(公共服务)责任过度下放这一事实密切相关。②中国是个单一制的政府结构和具有集权传统的国家,但服务责任的下放比多数联邦制国家走得更远,甚至在其他国家通常由国家级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在中国也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参见表1)。
表1 服务责任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分配(2005/%)
中央 地方 合计
社会保障与就业
4555 100
教育情
1090 100
医疗卫生 496 100
资料来源:财政部:关于200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案的报告。
表1显示,2005年医疗卫生支出的96%由地方政府负责。这个比例比美国要高得多。在公共医疗和卫生保健支出中,美国联邦政府在2005年承担了55%,州政府承担45%。公共联邦补助是政府为低收入人士提供的主要项目是公共医疗补助,联邦和州在2005年分别提供1820和1380亿美元。该项目由联邦政府确定受益的范围及符合条件人员的范围,具体的福利发放及人选区由州政府确定。联邦政府承担的份额与“州人均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比率决定,联邦承担的比率由50—83%不等。③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地方政府在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方面的责任也大得多。2003—2004财政年度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承担了31%(州与地方承担69%)的教育支出、62%(州与地方承担38%)的医疗保健支出以及92%(州与地方承担8%)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支出。④
在服务责任下放的同时,中央政府将大量的财政资源通过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转移给地方政府。因此,就地方支出占全部公共支出比重而言,中国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高得多。由于中国地方政府高水准支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支撑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度比许多国家高得多。2005年,中国地方政府总收入中的43%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而在美国这个比例(2004年)约为22%,⑤比中国低整整21个百分点。
二、巨大且日益拉大的财政差距与服务差距
引人注目是,虽然政府间转移支付相对规模十分庞大,但证据显示中国各地区间的财政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正迅速扩大,并远远超过备受关注的地区间经济(人均收入)差距。按照2004年的数据测算,在中国31个省级辖区中,五个人均财政支出(含中央的转移支付与税收返还)最高的省级辖区的人均支出,相当于五个人均支出最低辖区的人均支出的7.7倍;其中,人均支出最高辖区(上海8008元)相当于最低辖区(河南908元)的8.8倍(参见表2)。
表2 地区间经济差距、财政能力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
计量指标比值
经济差距城乡人均收入(2005)
3.2∶1
财政能力差距 5个最高辖区/5个最低辖区(2004)7.7∶1
最高辖区/最低辖区(2004) 8.8∶1
公共服务差距 城乡医疗卫生资源 7.4∶1
城乡小学生均财政支出(2000)
4.5∶1
表2显示中国的地区差距非常大。首先是经济差距。地区间经济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0493元∶3255元=3.22∶1,比前些年进一步扩大。⑥令人不安的是:与地区间经济差距相比,中国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似乎更大。由于存在巨大的公共服务不平等,贫困地区居民获得教育与卫生保健的机会显著地低于发达地区。中国卫生资源(医疗、护士、医疗设施与设备等)的大约80%分布在占全国人口35%的城市,其余20%分布在占全国人口65%的农村。据此换算,城乡居民人均享受的医疗卫生资源之比为(80%/35%)∶(20%∶65%)=7.4∶1。
教育资源的城乡不平等分布情况也十分严重。农村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全国用于小学教育的政府支出为849亿元,其中用于农村的为497亿元;用于城市小学为352亿元。当年城市小学生在校人数为1680.9万人,县镇和农村则多达10862.6万人,后者是前者的6倍多。折算下来,城市与农村(包括县镇)小学生均教育支出之比为2094元∶458元=4.5∶1。⑦与教育和卫生保健相比,养老保障方面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虽然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但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几乎没有保障可言,城市人口享受养老保障的人口比率比农村高得多。另外,在基础设施、干净饮用水和能源供应和互联网普及率等方面,农村与城市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三、现行转移支付的类别与结构
规模巨大但均等效果不佳,显示目前的转移支付体制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缺陷。
表3 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的规模与结构(亿元人民币/%)
草药200020012002200320042005
直接补助236534543863436059117330
一般目的
67011361335186426043813
占总额— — — 23%26%33%
特定日的 169523182528249633373517
占总额— — — 30%34%31%
税收返还 — — — 388040264144
占总额 — — — 47%40%36%
总计 — — — 8240996711474
注:(1)资料来源:2004年及以前年度数据来自《中国统计鉴定》(2004);2005年数据来自财政部:财政部:关于200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2006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2)税收返还中包括“体制补助”。
由表3可知,目前转移支付的主要部分是税收返还(包括数额不大的原体制补助),虽然近年来相对规模有所下降,但目前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仍然超过1/3。然而与许多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和德国)不同,在中国,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是按来源地规则设计的。在此规则下,各辖区获得的税收返还数额只是取决于向中央政府“贡献”多少税收,不取决于各辖区的人口、人均收入、地理特征以及其他影响财政能力(标准收入)和支出需求(标准支出)的因素。在地区差距很大而且没有其他有效手段时,这种做法产生很大的问题。收入来源地规则意味着地方掌握的资源越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地方居民越富有,获得的转移就越多,导致公共服务参差不齐。⑧
逆向均等化问题也出现在特定目的转移支付中。从原理上讲,特定目的转移支付应严格地基于“外溢”原则设计。根据这项原则,一项需要委托地方实施和管理(如治理沙尘暴)的某项服务产生的利益,如果有80%溢出到其他辖区,那么,中央政府即应补偿该项服务成本的80%,其余20%由地方配套解决。然而事实上,中国目前的专项转移支付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原则。
无论如何,只要中央鼓励地方供应的服务项目的利益并未完全外溢到其他辖区,那么,要求地方配套就是合理的。⑨但这样一来也会产生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由于发达地区有能力提供中央要求的全部配套资金,但贫困地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大量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最终流向了发达地区而非贫困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脆弱的项目管理和监督能力,“政出多门”、“钱出多门”且缺乏有效协调的条块分割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专项转移的逆向均等化效果。
从严格意义上(以财政能力与支出需求作为分配基础)讲,在现行的各类转移支付中,具有确切的正面均等效果的转移支付仅限于始于1995年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但其总量占一般目的转移支付的比重不到30%(2005年为29%),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不到10%(2005年为9.8%)。至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始于2000年)中,也只有一部分遵循了财政均等化的内在逻辑(以财政能力与支出需求的差额作为分配基础),其余部分采用来源地规则(哪里来就分配到哪里去)分配。在这里采用来源地分配规则旨在激励民族地区的征税努力(增收积极性),目的无可厚非,但与财政均等化的内在要求并不吻合。
在一般目的转移支付中,规模位居第二的“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又如何呢?这项始于1998年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转移支付,直接分配给了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粗略地看似乎具有正面的均等化效果。然而,结论远非这么简单。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央政府虽然把资金分配给了相对贫困的辖区,但这些资金被直接用于补贴地方政府的运营成本!从终极意义上讲,“真正的”财政均等化,只是针对当地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从中受惠的“服务”而言的均等化,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基本卫生保健这类涉及公民权益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向贫困地区提供补助以支持它们向发达地区攀比工资与福利,如同支持它们攀比公务用车、公费出国(旅游)或豪华奢侈的办公条件一样,都有违财政均等概念的本质意涵。
始于2001年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是针对农村税费减免导致地方收入减少,而由中央政府提供的补偿性转移支付。2005年农村税费改革的中央财政为此转移支付662亿元,比2004年增长26.3%。⑩这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分配给了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以及民族地区和财政困难地区,但游戏规则是补偿中央减免农村税费导致的地方收入损失。应注意到这个规则与财政均等目标的规则(以财政能力和支出需求为基础)是不一致的,因为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有些发达地区因农村税费减免遭受的收入损失,比某些贫困地区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这项转移支付将被更多地分配给发达地区。作为初步结论,本文认为这项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是不确定的。
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规模相当的“三奖一补”转移支付始于2005年。中央政府的意图是就是提供激励:激励贫困地区增收节支以缓解日益加深的基层财政困难。很清楚,这项转移支付并不与财政均等因素挂钩,虽然出发点良好,但毕竟不合财政均等目标的内在要求,因此,其均等效果是不确定的。
根据以上对转移支付结构和特征的初步分析可知,在目前约占地方收入43%、中央支出57%、总额达11474亿元人民币的转移支付中,完全遵循严格的均等化规则的转移支付充其量也不到20%(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约占10%),而超过80%的部分与财政均等化要么与财政均等的内在逻辑不符,要么其实际效果捉摸不定。其中,合计占转移支付总量67%(2005年)的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完全是按照不同于财政均等目标的内在逻辑和规则设计的,其实际的均等化效果极可能是负面的。
四、控制导向和短期目标压倒均等目标
自相矛盾的是:在一再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情况下,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反而设计出整体而言无法促进均等目标的转移支付体制呢?这里有三个可能的答案。(1)目前的转移支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博弈的产物,中央政府需要通过这一体制实现纵向控制的意图,同时又要消弭地方的不满和改革的阻力;(2)中央政府赋予了转移支付体制过多且往往相互冲突的功能与目标,在目标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均等目标有意无意地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3)省以下地方政府没有建立起严格的、主要以均等目标为导向的二级或三级转移支付体制。(11)下面只对前面两个原因稍作些分析。
从宏观上看,目前的转移支付体制是范围更大的政府间财政安排的一个组成部分。单一制的政府结构、中央集权的传统、对地方政府不听中央号令的担忧和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促使中央政府建立起一套偏重纵向控制功能(而非横向均等功能)的政府间财政安排。从历史上看,东亚国家大多具有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强有力控制的传统(中国尤其典型),而政府间财政安排被当作实施纵向控制的最佳工具。偏重控制功能的政府间财政安排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
◆税权高度集中。中央政府认为可以给地方一些钱(税收和非税收入),但征税权(主要是确定税基和税率的权力)则由中央控制甚至完全垄断(中国目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支出(服务)责任高度分散。在有效管理大多数公共服务方面,中央政府需要高度依赖地方。
认识到这一点,中央政府倾向于将范围广泛的支出责任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基层地方政府),同时保留监督权和主要的决策权。
◆偏重填补纵向财政缺口的转移支付。税权的高度集中和支出责任的高度分散相结合,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纵向财政缺口(地方政府的自有收入远不足以抵补支出),转移支付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填补纵向缺口的工具。
在这里,转移支付同时实现了中央政府“想要的”三重意图:控制征税权,下放支出责任(效果类似于向地方转嫁赤字),让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形成对中央的高度依赖。很清楚,这三重意图都服务于加强对地方控制这一根本目的,而转移支付——更一般地讲是包括转移支付、支出责任划分和税收划分在内的整个政府间财政安排,被当作实现纵向控制目的利器。在控制导向的支配下,均等目标往往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与“控制导向”压倒“均等导向”类似的是:政府间转移支付经常被当作应付一大堆短期问题的工具,而疲于应付短期问题的转移支付经常与财政均等的指导方针相冲突。作为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体制和政策经常处于变动中,而这种变动不可避免地将一大堆恼人的、不得不随时应付的短期问题抛洒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面前。减免农村税费,地方的收入遭受损失,中央怎么办?中央政府决定给公务员涨工资,可是贫困地区没有足够的钱来涨工资,中央该怎么办?基层财政那么困难,需要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增收节支缓解财政困难,中央政府又该怎么办?诸如此类的短期问题虽然明显地与均等目标不一致。
本部分讨论表明:中国在1994年建立的以税收分享(tax sharing)和直接补助(direct grants)构成的现行转移支付体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财政均等因素,但总体而言是非常不充分的,而且没有严格遵循财政均等概念的内在逻辑。因此,迄今为止,中央政府财政转移的大部分仍然是根据非均等因素被分配给各地方辖区的,这是导致财政均等化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1.虽然人们通常关注和担忧的是经济财富的两极分化,但严峻的现实是:目前中国地区间财政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同样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局面,而且其影响和后果丝毫也不亚于经济财富的两极分化。因此,仅仅致力缩小经济差距和消除经济贫困(economic poverty)的政策是不够的,消除财政能力贫困(poverty of fiscal capability)和公共服务贫困(poverty of public service),需要被置于政府战略和国家政策层面更为优先的位置。
2.系统地推进财政均等目标,首先需要对目前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作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以满足均等的基本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对地方辖区的财政能力和支出需求进行切实的计量,以此作为公式化转移的基础。更一般地讲,需要一个更具再分配功能的转移支付体制。
3.协调均等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冲突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把转移支付作为控制地方政府的手段,还是作为疲于应付短期问题的权益之计,都可能导致与财政均等目标之间的冲突,并削弱中央政府推动财政均等目标的努力和效果。目前偏重纵向控制的财政结构虽然可以将财政均等因素包容其中,但在许多方面与均等概念并不一致。
注释:
①雷蒙德C.斯哥帕驰:美国政府间预算框架,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国际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美国中美关系学会联合举办(北京),2006.07.10-11。
②根据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理论,支出责任应下放给那些不至于产生外溢、具有起码财政能力、并且管理上能够胜任的规模最小的地理辖区。此外,成功的财政分权还需要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受托责任(acoountability)。在这些基本要求尚未具备时的服务责任下放,称为过度下放(excess transfer to a lower level)。
③雷蒙德C.斯哥帕驰:美国政府间预算框架,中国政府问财政关系国际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美国中美关系学会联合举办(北京),2006.07.10-11.
④艾伦.莫里斯:澳大利亚的财政均衡化体制,政府间财政关系国际研讨会(新疆),中国财政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联合举办(新疆乌鲁木齐)2004.07,会议论文。
⑤同注(22)。
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汇制。
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计算.
⑧理查德.M.伯德,罗伯.特.D.埃贝尔,克里斯蒂.I.沃利克:财政分权: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1。
⑨在这里,配套比率是4∶1(或1∶0.25),即中央每补助4元钱,地方需拿出1元钱的配套资金。
⑩财政部:关于200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06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11)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可视为一级转移支付,省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可视为二级转移支付;地市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可视为三级转移支付。
标签:转移支付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央财政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政府服务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