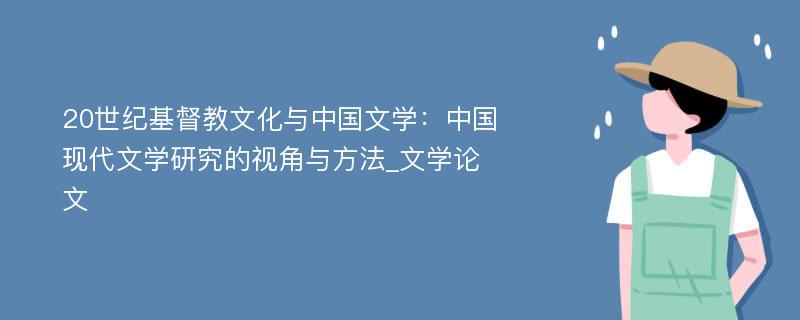
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视角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前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以社会学的方法为主,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成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的翻版。倘若说1984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的翻译出版,使我们认识到文学研究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区别,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大都为外部研究的话;那么,1985年前后对诸多西方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与学习,使我们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我们文学研究的方法。从方法论的视角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说开国内文学研究方法的风气之先,新批评、原型批评、比较文学、叙事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等研究方法,都先后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所用,虽然这种对于研究方法的热情和实验存在着囫囵吞枣简单模仿的不足,但却拓开了国内文学研究的新局面。除此而外,以文化学的视角与方法进行研究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学者不仅探析现代文学创作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研究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还梳理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诸如佛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道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等。本文拟从文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出发,谈谈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一
闻一多在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时,指出了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受印度佛教的影响,第二次是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他说:“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小说戏剧是欧洲文学的主干,至少是特色),你说这是碰巧吗?”闻一多认为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由扎根而开花了”,而西方基督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正继续着“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发展”。(注: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宗教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它和文学在历史源起、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都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然而,由于它们各自的特性和关系,它们之间又互为影响,宗教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由于基督教文化是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就成为解开西方文学的巨大的密码。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由于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强大势力,基督教在中国漫长而坎坷的传教过程中始终未能形成气候,直至鸦片战争以后,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定,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使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深入。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教会医院、育婴堂、救济所等,扩大了教会的影响与势力。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许多作家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许地山、冰心、庐隐、老舍、苏雪林等曾先后受洗入教成为基督徒,冰心、张资平、郁达夫、庐隐、萧乾等都曾是教会学校的学生,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巴金、曹禺等曾十分喜爱阅读《圣经》,这些都使中国现代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五四”时期,新文学先驱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否定的决绝态度中,以窃得西方的火来煮自己的肉的精神,使基督教文化也成为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崇尚耶稣基督的伟大人格、推崇基督教文化中的人道精神,一时成为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虔心追求。这使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流溢着十分浓郁的基督教色彩,也使我们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可能。翻开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在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见到基督教的色彩和影响:鲁迅的《复仇(其二)》,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旧约与恋爱诗》,陈独秀的《基督教与中国人》,胡适的《基督教与中国》,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商人妇》、《玉官》,茅盾的《耶稣之死》、《参孙的复仇》,王统照的《微笑》、《十五年后》、《相识者》,冰心的《最后的安息》、《相片》、《我的学生》,庐隐的《余泪》、《女人的心》、《何处是归程》,苏雪林的《棘心》、《绿天》,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上帝的儿女们》、《约檀河之水》、《约伯之泪》,郭沫若的《落叶》、《双簧》、《圣者》,郁达夫的《南迁》、《迷羊》,老舍的《二马》、《正红旗下》、《老张的哲学》,萧乾的《皈依》、《昙》、《鹏程》、《参商》,巴金的《新生》、《田惠世》,曹禺的《雷雨》、《日出》,滕固的《石像的复活》、《二人之间》、《少年宣教师的秘密》,徐訏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彼岸》、《时与光》,张晓风的《我是一棵树》、《如果你有一首歌》、《小小的烛光》,北村的《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孙权的故事》……我们还可以列出诸多的作家:田汉、林语堂、沈从文、冯至、石评梅、徐志摩、陈梦家、胡也频、陆志韦、叶灵凤、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艾青、欧阳山、陈映真、张系国、七等生、史铁生……在他们的创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有关基督教的内容。综观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历史,与基督教相关的作家与作品甚多,这使我们展开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课题的研究有着坚实的基础。
朱维之写于40年代初的《基督教与文学》被人誉为“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中的第一部参考书”(注:刘廷芳:《基督教与文学·序》,《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第5页。),该著从耶稣与文学、圣经与文学、圣歌与文学、祈祷与文学、说教与文学的角度,分别阐述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还从诗歌散文与基督教、小说戏剧与基督教的视角,分析基督教与文学的关联,谈散文时点到谢冰心、许地山、苏雪林、张若谷、周作人;谈小说时说到苏雪林、老舍、张资平、滕固、郁达夫、胡也频、朱雯、巴金等。朱维之是最早将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与基督教联系起来思考研究的,虽然他只是在详尽地阐述了外国文学与基督教关系后,简略地提到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关联,但朱维之却有着勿容置疑的开拓者之功。在朱维之撰成《基督教与文学》40年以后,美国学者罗宾逊(Lewis Robinson)开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基督教”的课题,出版了《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罗宾逊认为:“中国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参照耶稣的行为标准来指出基督教行为的矛盾,并进而指出基督教自身的矛盾。这一创作方法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对现代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注: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导言》。)罗宾逊的著作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细致地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的著作。该著独到的学术视角、细致入微的分析、客观公允的评价,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好评,也激起了人们对此课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此后,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界,杨剑龙、王本朝、马佳、王学富等也都先后开始关注此方面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关的论文,马佳出版了《十字架下的徘徊》一著,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也即将出版。该著择取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15位作家为研究对象,分别梳理他们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研究他们创作中所蕴涵的基督教色彩与精神。
德国神学家K·J·库舍尔在他所编的《神学与文学》一书的《几点说明》中,谈及编辑此书的意义时说:“它们要打开对宗教感兴趣者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在文学领域实际上可以发现一块独创性的语言练习、创造性的想象和勇于反省的绿洲。这片绿洲将为那些古老的宗教问题注入新的时代活力。对那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们,它们则可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被肯定的、还是有争议的宗教——都一再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注:《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55页。)宗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后也给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作家的创作源泉。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是一片新拓开的绿洲,我们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在这片新拓开的绿洲上,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耕耘,以期有更大的收获。
二
要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首先应该梳理中国二十世纪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与西方作家生活在浓郁的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不同,中国二十世纪作家们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缺少西方作家的那种刻骨铭心的虔诚,他们对基督教文化大都取一种“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态度,他们对基督教文化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甚至可以说各取所需。对于中国二十世纪与基督教文化相关的作家,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分为三类。一类为清醒的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者。他们大都能站在宗教文化历史的视角,较为深入与辩证地观照基督教,既看到基督教文化中的某些不足,也接受基督教文化中的有益思想。陈独秀在指出“一切的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的同时(注;陈独秀:《偶像破坏论》。),却呼吁“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注: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3号。)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文中批判中世纪宗教对科学、思想自由等方面的压制,在《摩罗诗力说》中却盛赞希伯来文化,“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未艾。”周作人在《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中深刻地针砭基督教对妇女的歧视,但在《圣书与中国文学》的讲演中指出:“其次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许地山虽然是基督徒,但他是一位宗教学家,对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都颇有研究。他“不满于现代教会固执的教义,和传统的仪文”(注:张祝龄:《对于许地山教授的一个回忆》。),他提倡“谋诸宗教的沟通”,认为“宗教当使人对于社会、个人负归善、精进的责任”(注:许地山:《宗教的生长与死亡》,《东方杂志》1992年第19卷10期。)。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许地山都可归入清醒的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者之列。另一类为基督教的皈依者。他们大都与基督教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自身都有着皈依基督的经历,他们较少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基督教,却常常用赞赏的心态礼赞主耶稣。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她虔诚地对上帝祷告:“永远在你的座前作圣洁的女儿,光明的使者”(注:冰心:《晚祷(一)》。)。庐隐在慕贞学院的孤寂病痛中皈依了基督,她真诚地相信“我们这些人生下来也都有罪,除了信耶稣,不能逃出地狱。”(注:庐隐:《庐隐自传·童年时代》。)苏雪林赴法国留法时皈依了天主,她说:“基督教的神却是活泼,无尽慈祥,无穷宽大,抚慰人的疾苦,像父亲对于女儿一样的。”(注:苏雪林:《棘心》。)张晓风“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的行事为人实在是遵循基督的圣范”(注:林治平:《更好的一半——我妻晓风》。),她仰慕基督为爱而牺牲自我的品格,她说:“如果关怀和爱必须包括受伤,那么就不要完整,只要撕裂,基督不同于世人的,岂不正在那双钉痕宛在的受伤的手掌吗?”(注:张晓风《受创》。)北村1992年3月皈依了基督,他说“人活着是有意义的,没有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注: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冰心、庐隐、苏雪林、张晓风、北村都可归入基督教的皈依者之列。第三类为对教会现状的不满者。他们大都自小与教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教会的生活和现状有十分深入的了解,他们看到了教会诸多的阴暗面,表现出对教会深深的不满。张资平13岁进了教会学校广益中西学堂读书,其父是该校的中文教员。张资平“便发觉教会内部的虚伪,就连宣教师们的言行,也不能一一和《圣经》里的教条一致。”(注:张资平:《资平自传》。)他便在《冲积期化石》、《上帝的儿女们》等作品中全力揭露教会内部的阴暗腐败。萧乾过了近10年教会学校的生活,他说:“白天,在一个教会学堂里,我看的是一般奴性十足的法利赛人,捧着金皮圣经,嫖着三等窑子。”(注:萧乾:《忧郁者的自白》。)他在《鹏程》、《昙》、《参商》等作品中就揭露传教士的虚伪险毒。老舍曾经参加了基督教的“率真会”、“青年服务部”,对教会的生活十分了解。他在《二马》、《正红旗下》等作品中对外国传教士、中国的吃洋教者的丑恶行径作了揭露针砭。第四类为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者。他们大都是无神论者,却也对基督教文化很感兴趣。他们或能十分娴熟地引用《圣经》,或能十分深刻地借用基督教典故,或能十分生动地描述基督徒的生活使他们的笔底也流溢出基督教的色彩。早期的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他说,“基督教乃是历史上最大的伪善”,“基督教乃是人类最大欺骗与最大耻辱”(注: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但是,巴金在创作中常常十分娴熟地引用《圣经》经文,在《田惠世》中还写出了“一个宗教者的生与死”(注:巴金:《田惠世·后记》。)。年轻的曹禺苦苦地探索人生道路,他“从老子到佛教、到基督教、天主教,一直到马克思”(注:转引自鸟韦·克苏特:《戏剧家曹禺》,见《曹禺研究资料》(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9页。),什么都看。他说:“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注: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曹禺在《雷雨》中让周朴园最后皈依了天主,在《日出》中引用了许多《圣经》的经文。郭沫若因其妻子佐藤富子是教徒而深受影响,他甚至宣称要皈依基督。他的《漂流三部曲》以《圣经》的意象构思作品,他的《落叶》让失恋的主人公皈依基督。
我们将与基督教文化相关的中国现代作家分为如上几种类型,是为了区分他们对基督教文化接受和受影响的不同程度,以利于我们据此展开对他们的思想和创作的深入研究。我们的这种区分也并非绝对的。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关系和态度,抓住他们的个性特征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他们思想与创作的真谛。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选择,进行深入的研究:诸如鲁迅推崇基督的充满着爱与牺牲的救世精神;周作人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人道主义的精髓;许地山关注人性在受窘压的状态下的挣扎;冰心充满了基督的博爱精神;庐隐深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响,形成其创作的感伤风格悲剧色彩;苏雪林为耶稣伟大的人格所感化,细致地描绘人物对基督的皈依历程;而张资平努力揭露神职人员的“一面教人认罪,一面背着人作恶”;萧乾全力针砭教会中“一般奴性十足的法利赛人”;老舍则在揭露牧师教徒的虚伪卑劣时,还塑造了具有基督牺牲精神的理想人物。如此种种,使这些作家的创作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独特个性和风采。
中国现代作家在接受基督教文化时,虽然他们每人都有着自己心中的基督,每人都从基督教文化中各取所需,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他们大都不看重基督的“三位一体”、“基督复活”、“预言应验”等说,大都不在意基督教的礼议,而重视基督教的博爱、宽容、平等、牺牲等具有人道意味的精神。他们往往将此作为批判封建传统的武器、医治民族病态的良药。他们常常将《圣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并不在意其中的神迹奇事、上帝启示,而为其中非凡的想象、绚丽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深刻的典故、多样的手法吸引。他们从《圣经》中有所借鉴,丰富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三
对于“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课题的研究,大概也可归入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之列。这种研究必须在对两种文学与文化的影响途径、接受方式等诸多复杂情况的梳理中,必须在对两种文学与文化的细致对照分析中,理出其中的因果联系,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美国文学理论家约瑟夫·T·肖谈到不同国家间的文学影响时说:“影响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细节、意向、借用,甚或出源——当然,这些都包括在内,而是一种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成为艺术品有机部分,并通过艺术作品再现出来的东西……一个作家所受的文学影响,最终将渗透到他的文学作品之中,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决定他们的作品的基本灵感和艺术表现,如果没有这种影响、这种灵感和艺术表现,就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或者不会在作家的这个发展阶段出现。”(注: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38页。)这就告诉我们,影响研究必须立足于从整体上来观照、把握,而并不局限于许多具体的细节等。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作家,他对别的作家的作品的接受,他受其他作家创作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模仿,而应该化解到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之中,渗透到他的文学作品之中,成为其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观之,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理清基督教文化对具体作家、具体创作的具体影响时,一定不能忽视对这种影响的整体的观照与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作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基督教牧师,他从小在读经祈祷的基督教环境中成长。谈到基督教时,他说:“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圣经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我遗憾地说,我们搬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和审美上与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虽然充满邪恶,腐败及贫穷,但同时也有欢愉和满足)断绝关系。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总之,它意味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尤其赞赏,它意味着对赞成女子受教育及反对立妾制度及缠足,保持明显而坚决的态度。”(注: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6页。)在林语堂的这段话中,接受基督教就意味着接受西方,就意味着进步,就意味着反对立妾制度及缠足。显然,“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转型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全面批判与否定,成为当时的时代特征,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思想和方法,也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新文学先驱者们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大都是立足于接受西方进步思潮的视角,立足于以基督教文化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儒家的伦理道德。基督教文化的引入对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人生追求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何看待基督教文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转型期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如何看待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历程中的作用和位置,都需要我们作深入细致的思考与研究。
一种外来文化的引入,总是有一个与本土文化的冲突、渗透、融汇的过程,如佛教在由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历程。对基督教文化来说,它也有一个中国本土化的过程。1921年,神学家贾玉铭在《神道学》中曾经说:“中国人对于宗教,素抱一种齐物观,如儒释道之教理,虽迥然有别,然终能调和,使合而一。此种调和性,对于中华基督教会前途不无关系。”中国二十世纪作家们在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过程中,无论是正影响,还是负影响,也有着这样一种调和的倾向。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心态和眼光观照基督教,总是重塑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基督。陈独秀就曾经说:“我们应该崇拜的,不是犹太人眼里四十六年造成的神殿,是耶稣心里三日再造的,比神殿更大的本尊。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二为一。”(注: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3号。)他们大都不在意于基督的神性,而看重基督的人性,看重基督伟大的人格。那种对世人的关爱和怜恤,那种牺牲自我拯救他人的无私品格,那种将人类的苦难和未来负在身上的崇高责任,都使中国现代作家以之为模范,并将对基督伟大人格的仰慕崇尚,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思想的精髓结合起来,为祖国的发达、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奋斗。
西欧各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常常是从翻译《圣经》开始的。马丁·路德对《圣经》的翻译使德国的语言走向了规范化。中国“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也与《圣经》的翻译有着关联。周作人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很可笑,现在想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的关系。”(注: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记载,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时已有《圣经》的中文译述,基督教经典的汉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明清之际,传教士罗明坚、利马窦、庞迪我、艾儒略、阳玛诺等先后以中文翻译过《圣经》的某些章节。18世纪末,法国传教士贺清泰首次较完整系统地将《圣经》译为中文。1823年,由马礼逊、米怜合译的《神天圣书》的出版成为中国最早的中文《圣经》全译本。1891年底,狄考文、富善等主持了《圣经》的重译工作,于1919年初出版了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发行数以百万计。这部用汉语白话翻译的《圣经》,译文准确审慎、行文流畅上口、用语通俗明了,被视为白话文的典范。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在“五四”前的出版发行,对中国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必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基督是为了拯救有罪的世人而被钉上十字架的,十字架就成了牺牲自我拯救民众精神的象征。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大都崇尚为解脱民众的苦难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提到要为民众自觉地背上十字架。冰心说:“我只是一个弱者/光明的十字架/容我背上吧”(《春水·二十六》)郁达夫说:“我们是沉沦在/悲苦的地狱之中的受难者,/我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在共同的运命底下,/向着永远的灭亡前进!”(《〈茑萝集〉献纳之辞》)郭沫若为耶稣的话语所感动,他对基督说,“我还要陪你再钉一次十字架”(《孤鸿》)。老舍则提出“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双十》)。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大都受儒道思想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入则建功立业,退则归隐山林……这林林总总的思想传统都构成了中国士大夫的人格的内核。法国学者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著里说:“这种宗教改变了中国人的习惯,对一些过去形成的思想提出了质疑,特别是会损害当时已成定格之局面的危险。”(注: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藉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第9页。)基督教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同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因而也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作家们的人格理想。因此,深入地展开基督教与中国作家的人格建构,也是一个值得开掘的课题。
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需要我们从多方面进行思考和开拓,诸如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文学观念、审美理想、忏悔意识等,诸如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叙事方式、人道精神、浪漫风格等,都值得我们去作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它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生、发展,对于细致梳理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对于准确把握中国作家的创作个性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课题。基督教文化在传入的过程中,它与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构成了既有冲突碰撞、又有渗透融合的复杂关系。作为个体的中国作家,他们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又是各取所需、不尽相同的。我们必须在把握共性的同时,注意不同作家的不同个性,将微观的分析与宏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探析出其中的真谛。
标签:文学论文; 基督教论文; 基督教文化论文; 圣经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艺术论文; 皈依论文; 周作人论文; 耶稣论文; 天主教论文;
